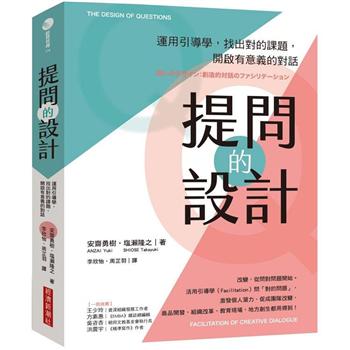●觸發提問的四種溝通類型
提問所產生的效果,不只刺激提問對象的思考及情感,也能觸發溝通。
►提問,能觸發群體溝通
提問會刺激提問對象的思考及情感,面對問題的個人,會在腦中思考擁有個人特色的意見,或是想出新點子,也可能產生新的疑問或有疙瘩。
這就像是思考的「種子」,即使面對同樣的提問,每個人的答案都有所不同,當這些提問在同一個場域彼此碰撞時,就會觸動溝通。
從提問衍生的四種溝通類型,包括「辯論」、「議論」、「對話」、「閒聊」(【表1-1】):
辯論:決定哪一方立場正確的談話
討論:為了達成共識或制定決策,尋求全員皆可接受的解方的談話
對話:在自由的氣氛中,進行賦予嶄新定義的談話
閒聊:在自由的氣氛中,進行輕鬆的問候或資訊交流的談話
【表1-1】四種不同的溝通類型
①辯論
所謂的辯論(debate),是針對特定主題,分成不同意見的立場(例如贊成派和反對派等),各自闡述意見,然後判定哪一方意見正確的一種溝通。
在辯論中,最終成為結論的主張,未必能得到在場全體的認同。為的只是勝負,有可能是邏輯上正確的某人的主張,最後獲得採用而成為最終結論。即使是反對意見,但也有可能發生無法提出有力主張說服的某人「輸掉了辯論」。
② 討論
所謂的討論(discussion),是只針對特定主題,為了達成相關人士的共識或做出決策所進行的談話。重視符合邏輯的條理、主張的正確程度和效率,目的是透過溝通「做出結論」。不同於需要決定勝負的辯論,著眼點放在全體合作,引導出大家都能接受的「答案」。
③ 對話
所謂的對話(dialogue),是針對特定主題,在自由的氣氛中,彼此分享各自「賦予的意義」,期待在這過程中深化相互理解,或是進行賦予嶄新意義的溝通。
對話不同於討論或辯論,並沒有對錯輸贏,對話並不需要試圖打敗對方或導出答案。
面對與自己不同的意見時,也不必急於做出判斷或給予評價,而是了解對方是在怎樣的前提下賦予事物定義,也就是重視「深層理解」。對話就是從彼此的談話中找到交集,增進彼此理解。
④ 閒聊
所謂的閒聊(chat),和對話也同樣是在自由的氣氛下進行,不過,指的是更隨興的溝通。不需要深入分享彼此的價值觀或賦予事物定義的程度,而是建立在輕鬆的問候或資訊的交流上。
如果主題是私人話題,那也不見得是「閒聊」。例如像「漫畫」這種興趣嗜好類的主題,或許從「最近覺得有趣的漫畫有哪些?」的提問開始,就能衍生出熱烈的「閒聊」。
提問若是「沒有人氣的漫畫應該馬上停止連載嗎?」這類,或許就會激發一場熱絡的「辯論」,如果提出「應該在國中時期閱讀的漫畫有哪些?」這個提問,試圖展開一場討論,或許也很有趣。
倘若期待關於漫畫的「對話」,不妨詢問「什麼是好漫畫?」分享彼此的想法。
►因對話而改變的個人認知
在這四種溝通類型中,能撼動認知與改變關係的是「對話」。
「辯論」、「討論」和「閒聊」,可以在不需要詢問每位參與者的認知,也不必藉由「相互理解」重組彼此關係的情況下進行。
不過,「對話」重視的是「每個人對於事物賦予的定義」,也就是分享個人對於事物的認知,成為促進相互理解的切入點。
提問的本質(4)
透過對話面對問題的過程中,可以內省個人認知
想像一下,例如被問到「什麼是好漫畫?」然後深入對話的情況。自有記憶以來就常看漫畫的A,回憶小時候入迷的幾部作品,懷念當時雀躍的心情,或許會想:「這應該是讀完後還能長期留在記憶中的作品吧?」「所謂能留在記憶裡的漫畫,應該是能帶領我們進入日常無法體驗的世界的劇情吧?」
另一方面,成人後才開始看漫畫的B,或許是將重點放在能從中學習到可在人生中派上用場的教訓,從記憶中回顧可實際發揮作用的場面,舉凡以商務為題材的漫畫、或是非虛構的歷史漫畫等。A和B各自對於漫畫的理解所隱含的認知,完全是不同層次。
因為A把漫畫當成「非日常體驗」,而B則視為「對日常生活有益的工具」。這背後存在的價值觀,恐怕會讓A和B在面對提問之際,未必能客觀看待。因為,對自己而言太過「理所當然」的事,要在日常生活達到後設認知(metacognition,客觀思考自己的思考)並不容易。
不過,當兩個人有對話機會,那麼各自的默認前提,就會成為第一個後設認知的對象。在不同的前提下說出各自的經驗或意見,一開始對彼此而言,或許會認為是「有些不對勁的意見」。
不過在對話溝通中,筆者會鼓勵大家先不要急著對不同的意見做出判斷或評價,而是在理解是在什麼樣的前提下發言,以及背景為何。在這過程中,我們會因為對於站在與自己不同前提的其他人有更深入的理解,進而相對意識到自身的前提為何,那就是引導進入後設認知的關鍵。
在將默認前提視為後設認知的過程中,能引發重新建構自我前提的「反映」。所謂的「反映」,指的是在內省自身經驗之後,對於過去的經驗賦予意義、或是重新建構對事物看法的認知過程(【圖1-3】)。反映有許多層次,有時候會賦予過去經驗意義,或是獲得能運用在未來的教訓,有時也會對於自己至今不自覺的認知,而感到不對勁或糾結,甚至大幅改變價值觀。
成人教育學領域中的偉人傑克·馬濟洛(Jack Mezirow)主張,對於成人而言最重要的學習,是改變對於現實的認知方式,並將此過程訂定為下列的「改造型學習」。
改造型學習的過程:
1. 引起混亂的兩難困境
2. 伴隨恐懼、憤怒、罪惡感、恥辱感等情感的自我探究
3. 重新審視典範(paradigm)
4. 認知到他者也會與自己分享同樣的不滿及改造過程
5. 為形塑新角色或新關係而探究其他選項
6. 規畫行動計畫
7. 掌握為執行自我計畫所需的新知識或技能
8. 暫定嘗試新角色和關係
9. 建立在一個新的角色或關係中的能力與自信。
10. 將新觀點(對事物的看法)重新統整到自己的生活中
正如馬濟洛認為「引起混亂的兩難困境」為認知改造過程的起點,如此劇烈變化的認知改造,有時還會伴隨「痛苦」。透過對話,擁有一個能分享意義的「對象」,不僅是一個能讓自我重新審視隱含前提的「比較對象」,也是一起克服變化的「夥伴」,是一個重要的存在。
►在尋求賦予共通意義的過程中,關係將獲得重組
對話的過程,並不只是讓個人認知得到內省。以先前列舉的漫畫為例,不需要「討論」、「漫畫是非日常的體驗?還是為了在日常發揮效用的工具?」之後再下結論。在對話中,接觸不同的價值觀,運用後設認知了解自己的前提,相互拋出直白的疑問,從不同的角度試著闡述意見,並且尋找交集(【圖1-4】)。
例如,為了解彼此的前提,拋出各種疑問:
「為什麼這個人會執著於非日常的狀態?」
「開始閱讀漫畫的契機是什麼?」
「都在什麼時候看漫畫?」
「為什麼這個人會堅持一定要有效果?」
「看漫畫的動機,小時候和現在都是一樣的嗎?」
「比較不會去閱讀專門解決問題的實用書嗎?」
關於「為什麼會賦予這樣的意義呢?」在彼此逐漸理解的過程中,會開始產生種種關於探索共通意義的提問。例如:
「比較沒有日常生活感的漫畫,真的就沒有幫助嗎?」「人類會為了在日常生活中派上用場而看漫畫嗎?」「就算劇情設定在『非日常』,但正因為劇情能讓讀者從日常生活中產生共鳴,才會覺得有趣不是嗎?」等,一面浮現新提問,一面從中尋找共通的意義。
在這過程中,像是「如果是要用來解決問題的工具,可以閱讀實用書。漫畫終究是人類追求有趣的文化創作,或許正因為讀者會沉迷於其中,所以才能獲得對人生有益教訓的副產品」,或許這是在相互理解後,能達到為其賦予全新意義的共識。
專門研究組織內部對話模式的管理學者宇田川元一,以馬丁.布伯(Martin Buber)和米哈伊爾.巴赫汀(Mikhail Bakhtin)的對話相關理論為基礎,重新將「對話」這種溝通模式定義為「建構新關係」。建構新關係的四個步驟如下:
①注意到鴻溝的存在
②遙望鴻溝的另一邊
③設計跨越鴻溝的橋梁
④在鴻溝上架設橋梁
每個人自身擁有的隱含前提的不同,造成的溝通斷絕,在這裡以「鴻溝」來表現。也就是說,所謂「遙望鴻溝的另一邊」,就是想像與自己不同的他者認知。在宇田川的對話流程中,那道連接不同認知的「橋梁」的定位,是因為創造出全新的共同認知之後,結果形成新關係的建立(【圖1-5】)。
提問的本質(5)
透過對話和面對提問的過程,重新建構群體關係
►創造式對話有助於發想新點子
透過對話建立新關係之際,不僅能加深理解,有時還會創造出新點子。
肯尼斯·格根(Kenneth J. Gergen)和蘿恩·赫斯特(Lone Hersted)合著的《對話管理》(暫譯,Relational Leading: Practices for Dialogically Based Collaboration)書中,提出關於對話通常會存在數個目的和流程模式,也指出,參加者的交談在「好像要去哪個新的境界」所產生的對話中,包含「學習」,同時也形成「創新」的基礎。也就是指,參與這場對話的人的思考及情感,在受到影響的同時,讓當事者原本尚未參與對話之前並未擁有的共通認知,因對話受到刺激,進而產生全新的「創意」對話。
提問所產生的效果,不只刺激提問對象的思考及情感,也能觸發溝通。
►提問,能觸發群體溝通
提問會刺激提問對象的思考及情感,面對問題的個人,會在腦中思考擁有個人特色的意見,或是想出新點子,也可能產生新的疑問或有疙瘩。
這就像是思考的「種子」,即使面對同樣的提問,每個人的答案都有所不同,當這些提問在同一個場域彼此碰撞時,就會觸動溝通。
從提問衍生的四種溝通類型,包括「辯論」、「議論」、「對話」、「閒聊」(【表1-1】):
辯論:決定哪一方立場正確的談話
討論:為了達成共識或制定決策,尋求全員皆可接受的解方的談話
對話:在自由的氣氛中,進行賦予嶄新定義的談話
閒聊:在自由的氣氛中,進行輕鬆的問候或資訊交流的談話
【表1-1】四種不同的溝通類型
①辯論
所謂的辯論(debate),是針對特定主題,分成不同意見的立場(例如贊成派和反對派等),各自闡述意見,然後判定哪一方意見正確的一種溝通。
在辯論中,最終成為結論的主張,未必能得到在場全體的認同。為的只是勝負,有可能是邏輯上正確的某人的主張,最後獲得採用而成為最終結論。即使是反對意見,但也有可能發生無法提出有力主張說服的某人「輸掉了辯論」。
② 討論
所謂的討論(discussion),是只針對特定主題,為了達成相關人士的共識或做出決策所進行的談話。重視符合邏輯的條理、主張的正確程度和效率,目的是透過溝通「做出結論」。不同於需要決定勝負的辯論,著眼點放在全體合作,引導出大家都能接受的「答案」。
③ 對話
所謂的對話(dialogue),是針對特定主題,在自由的氣氛中,彼此分享各自「賦予的意義」,期待在這過程中深化相互理解,或是進行賦予嶄新意義的溝通。
對話不同於討論或辯論,並沒有對錯輸贏,對話並不需要試圖打敗對方或導出答案。
面對與自己不同的意見時,也不必急於做出判斷或給予評價,而是了解對方是在怎樣的前提下賦予事物定義,也就是重視「深層理解」。對話就是從彼此的談話中找到交集,增進彼此理解。
④ 閒聊
所謂的閒聊(chat),和對話也同樣是在自由的氣氛下進行,不過,指的是更隨興的溝通。不需要深入分享彼此的價值觀或賦予事物定義的程度,而是建立在輕鬆的問候或資訊的交流上。
如果主題是私人話題,那也不見得是「閒聊」。例如像「漫畫」這種興趣嗜好類的主題,或許從「最近覺得有趣的漫畫有哪些?」的提問開始,就能衍生出熱烈的「閒聊」。
提問若是「沒有人氣的漫畫應該馬上停止連載嗎?」這類,或許就會激發一場熱絡的「辯論」,如果提出「應該在國中時期閱讀的漫畫有哪些?」這個提問,試圖展開一場討論,或許也很有趣。
倘若期待關於漫畫的「對話」,不妨詢問「什麼是好漫畫?」分享彼此的想法。
►因對話而改變的個人認知
在這四種溝通類型中,能撼動認知與改變關係的是「對話」。
「辯論」、「討論」和「閒聊」,可以在不需要詢問每位參與者的認知,也不必藉由「相互理解」重組彼此關係的情況下進行。
不過,「對話」重視的是「每個人對於事物賦予的定義」,也就是分享個人對於事物的認知,成為促進相互理解的切入點。
提問的本質(4)
透過對話面對問題的過程中,可以內省個人認知
想像一下,例如被問到「什麼是好漫畫?」然後深入對話的情況。自有記憶以來就常看漫畫的A,回憶小時候入迷的幾部作品,懷念當時雀躍的心情,或許會想:「這應該是讀完後還能長期留在記憶中的作品吧?」「所謂能留在記憶裡的漫畫,應該是能帶領我們進入日常無法體驗的世界的劇情吧?」
另一方面,成人後才開始看漫畫的B,或許是將重點放在能從中學習到可在人生中派上用場的教訓,從記憶中回顧可實際發揮作用的場面,舉凡以商務為題材的漫畫、或是非虛構的歷史漫畫等。A和B各自對於漫畫的理解所隱含的認知,完全是不同層次。
因為A把漫畫當成「非日常體驗」,而B則視為「對日常生活有益的工具」。這背後存在的價值觀,恐怕會讓A和B在面對提問之際,未必能客觀看待。因為,對自己而言太過「理所當然」的事,要在日常生活達到後設認知(metacognition,客觀思考自己的思考)並不容易。
不過,當兩個人有對話機會,那麼各自的默認前提,就會成為第一個後設認知的對象。在不同的前提下說出各自的經驗或意見,一開始對彼此而言,或許會認為是「有些不對勁的意見」。
不過在對話溝通中,筆者會鼓勵大家先不要急著對不同的意見做出判斷或評價,而是在理解是在什麼樣的前提下發言,以及背景為何。在這過程中,我們會因為對於站在與自己不同前提的其他人有更深入的理解,進而相對意識到自身的前提為何,那就是引導進入後設認知的關鍵。
在將默認前提視為後設認知的過程中,能引發重新建構自我前提的「反映」。所謂的「反映」,指的是在內省自身經驗之後,對於過去的經驗賦予意義、或是重新建構對事物看法的認知過程(【圖1-3】)。反映有許多層次,有時候會賦予過去經驗意義,或是獲得能運用在未來的教訓,有時也會對於自己至今不自覺的認知,而感到不對勁或糾結,甚至大幅改變價值觀。
成人教育學領域中的偉人傑克·馬濟洛(Jack Mezirow)主張,對於成人而言最重要的學習,是改變對於現實的認知方式,並將此過程訂定為下列的「改造型學習」。
改造型學習的過程:
1. 引起混亂的兩難困境
2. 伴隨恐懼、憤怒、罪惡感、恥辱感等情感的自我探究
3. 重新審視典範(paradigm)
4. 認知到他者也會與自己分享同樣的不滿及改造過程
5. 為形塑新角色或新關係而探究其他選項
6. 規畫行動計畫
7. 掌握為執行自我計畫所需的新知識或技能
8. 暫定嘗試新角色和關係
9. 建立在一個新的角色或關係中的能力與自信。
10. 將新觀點(對事物的看法)重新統整到自己的生活中
正如馬濟洛認為「引起混亂的兩難困境」為認知改造過程的起點,如此劇烈變化的認知改造,有時還會伴隨「痛苦」。透過對話,擁有一個能分享意義的「對象」,不僅是一個能讓自我重新審視隱含前提的「比較對象」,也是一起克服變化的「夥伴」,是一個重要的存在。
►在尋求賦予共通意義的過程中,關係將獲得重組
對話的過程,並不只是讓個人認知得到內省。以先前列舉的漫畫為例,不需要「討論」、「漫畫是非日常的體驗?還是為了在日常發揮效用的工具?」之後再下結論。在對話中,接觸不同的價值觀,運用後設認知了解自己的前提,相互拋出直白的疑問,從不同的角度試著闡述意見,並且尋找交集(【圖1-4】)。
例如,為了解彼此的前提,拋出各種疑問:
「為什麼這個人會執著於非日常的狀態?」
「開始閱讀漫畫的契機是什麼?」
「都在什麼時候看漫畫?」
「為什麼這個人會堅持一定要有效果?」
「看漫畫的動機,小時候和現在都是一樣的嗎?」
「比較不會去閱讀專門解決問題的實用書嗎?」
關於「為什麼會賦予這樣的意義呢?」在彼此逐漸理解的過程中,會開始產生種種關於探索共通意義的提問。例如:
「比較沒有日常生活感的漫畫,真的就沒有幫助嗎?」「人類會為了在日常生活中派上用場而看漫畫嗎?」「就算劇情設定在『非日常』,但正因為劇情能讓讀者從日常生活中產生共鳴,才會覺得有趣不是嗎?」等,一面浮現新提問,一面從中尋找共通的意義。
在這過程中,像是「如果是要用來解決問題的工具,可以閱讀實用書。漫畫終究是人類追求有趣的文化創作,或許正因為讀者會沉迷於其中,所以才能獲得對人生有益教訓的副產品」,或許這是在相互理解後,能達到為其賦予全新意義的共識。
專門研究組織內部對話模式的管理學者宇田川元一,以馬丁.布伯(Martin Buber)和米哈伊爾.巴赫汀(Mikhail Bakhtin)的對話相關理論為基礎,重新將「對話」這種溝通模式定義為「建構新關係」。建構新關係的四個步驟如下:
①注意到鴻溝的存在
②遙望鴻溝的另一邊
③設計跨越鴻溝的橋梁
④在鴻溝上架設橋梁
每個人自身擁有的隱含前提的不同,造成的溝通斷絕,在這裡以「鴻溝」來表現。也就是說,所謂「遙望鴻溝的另一邊」,就是想像與自己不同的他者認知。在宇田川的對話流程中,那道連接不同認知的「橋梁」的定位,是因為創造出全新的共同認知之後,結果形成新關係的建立(【圖1-5】)。
提問的本質(5)
透過對話和面對提問的過程,重新建構群體關係
►創造式對話有助於發想新點子
透過對話建立新關係之際,不僅能加深理解,有時還會創造出新點子。
肯尼斯·格根(Kenneth J. Gergen)和蘿恩·赫斯特(Lone Hersted)合著的《對話管理》(暫譯,Relational Leading: Practices for Dialogically Based Collaboration)書中,提出關於對話通常會存在數個目的和流程模式,也指出,參加者的交談在「好像要去哪個新的境界」所產生的對話中,包含「學習」,同時也形成「創新」的基礎。也就是指,參與這場對話的人的思考及情感,在受到影響的同時,讓當事者原本尚未參與對話之前並未擁有的共通認知,因對話受到刺激,進而產生全新的「創意」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