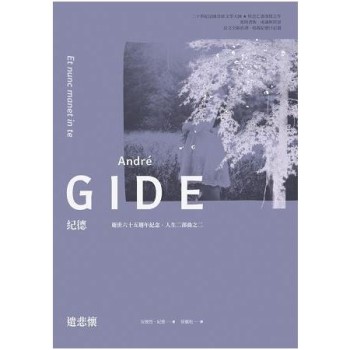昨天晚上我想著她,和她說話,就像我過去經常和她說話那樣,而且在想像中比實際當著她的面更輕鬆自在;然後我倏地想到:她已經不在人間了啊⋯⋯
有時我確實會到離她很遠的地方,一走就是許多天。但打從孩提時代開始,我就養成向她報告一天的收穫,並在心神中將她與我的悲傷和喜悅聯想在一起。昨天晚上我就是這麼做的,但忽然間我想起來,她已經死了。
一切驟然失去了顏色,變得暗淡無光,無論是近來我對一段遠離她的時光所作的回想,或是我回想那些事的那一刻;因為我在思緒中重新經歷那些事,都是為了她。我立刻明白,失去她以後,我的存在也變得枉然,再也不知道為什麼自己現在還活著。
我不太喜歡我為了尊重她的謙虛而在我的書寫中替她取的「艾曼紐」這名字。她真正的名字之所以令我歡喜,可能只是因為自小開始,她在我心目中就一直召喚出優雅、溫柔、聰慧和善良的形象。當其他人也取這名字時,我會覺得它彷彿遭到篡奪,我覺得彷彿唯獨她有權利用這個名字。當我為我的《窄門》創造出「艾莉莎」這名字時,那並非出自矯情,而是基於保留。艾莉莎只能有一個。
可我書裡的艾莉莎並不是她。我描繪的不是她的圖像。她只是成為我構思女主角的出發點,我不認為她曾在其中認出多少自己的身影。她從沒和我談過那本書,因此我只能推測她讀它時可能有過的思索。那些思索對我而言一直帶著悲痛的色彩,就像一切源自她內心那股深沉哀愁的東西;我是在很久之後才開始揣測出那種哀愁的,因為她那極其含蓄的性格一直阻止她將其顯露、表達出來。
我為我的書設想出來的劇情無論再怎麼美,難道它不是在向她證明,面對現實劇碼的我一直是盲目的?想必她感覺自己比艾莉莎簡單得多,比她正常、平凡得多(我的意思是說:比較不像高乃依描繪的女性角色,比較不緊繃)?因為她無時無刻不在懷疑自己,懷疑自己的美麗、優點,懷疑一切為自身光輝、價值造就力量的事物。我相信,後知後覺的我對她的理解終於清楚多了,但在我的愛意最強烈的時候,我對她的誤解居然能深到那般程度!因為我的愛意使勁做的事並非讓我接近她,而是設法讓她接近我發明的那個理想人物。至少這是我現在的感覺,而且我不認為但丁對貝緹麗彩的行為與此有何不同。在她已不在人世的此刻,我之所以企圖重新找到、重新描繪她的往昔身影,那也是──特別是──為了一種做出補償的需求。我不想讓艾莉莎的幽靈遮蔽了她真正的存在。瑪德蓮很堅持不要我試圖到她妹妹臨終的床前見她最後一面。我從塞內加爾回來以後,得知華倫汀在經過兩個月的可怕折磨以後,終於剛步入她還能盼得的唯一安寧。我打算立刻趕往她家弔唁,兩位外甥女在那裡等著我,但瑪德蓮先是發了電報,然後又打電話,求我別去:「懇切拜託你在和我見面以前不要回艾裴隆街。」由於巴黎還沒有任何人知道我回來的消息,我在那兒沒別的事,趕忙搭上第一班火車就到了庫佛維爾。我問她為什麼那樣堅持,她說:「一想到你會看到華倫汀的美麗臉孔因為死前的掙扎而完全走樣,我就覺得很痛苦。有人告訴我她變得面目全非,那不是我希望你對她保有的記憶。」在那個當頭,我認出她那種從任何難以承受的情景前本能抽離的個性,但在我眼裡,她給我的理由只對她自己有效。基於同理心,我可以理解那些理由,但我無法贊同它們。罷了。當我突然接到她去世的消息,再度回到庫佛維爾,我正準備推開她小房間那扇門時,我想起那天,也就是一個月之前她對我說的話。我在希特雷的依芳.德雷斯特朗日那裡逗留了一陣,是她開車載我回庫佛維爾的,她把我留下來人就走了────沒錯,瑪德蓮的冰冷遺體就在那小房間裡,而就在我要打開那扇門時,我遲疑了一下,心想她是不是也會對我說同樣的話:「別來見我最後一面。」然後我又想,由於她沒經過所謂臨終前的痛苦掙扎,我再度看到的她應該和兩週前我離開她時差不多,只不過因為死亡而變得寂靜罷了。
當我走近她安息的床時,我很驚訝她的臉龐呈現出來的嚴肅。她的嫻淑及客氣向來為她的善良賦予如此光芒四射的力量,但那些特質彷彿只駐居於她的眼神中。於是,由於她的雙眼已經闔上,現在,她的五官線條中除了肅穆,沒留下其他東西;又於是,我望向她的最後那一眼提醒我的只會是她在生前必然早已對我的生活做出的嚴厲評判,而全然不是她那種難以言喻的柔情。她溫和地責備密友雅涅絲.柯波 的縱容習性。話說回來,她自己救助窮人時也對他們的缺失和弱點非常縱容,不過面對那些找不出任何藉口可以解釋他們為何沉淪在貧困中的人時,她倒會把自己武裝起來,顯得緊繃且不耐。她那種嚴厲完全不是出於天性,不過一旦她認為某個事物是罪惡,光是不允許它出現在自己身上對她而言還不夠(尤有甚者,她對罪惡的極端嫌惡使她毫不費力就能做到這點),而且她似乎覺得,假如她不能大剌剌地譴責別人身上的罪惡,她就等於是在鼓勵罪惡。她堅決相信我們的社會、文化、風俗全都因為自滿和鬆懈而逐漸解體,而在她所認為的鬆懈中,她願意看到的只有軟弱,而毫無自由主義或慷慨的成分。她的善良本質緩和了那一切,而如果有些人主要只見識過她那柔光四射般的優雅嫻淑,我在這點上表述的意見恐怕會使他們感到詫異。我遇到過一些頑強的清教徒,她和那些人毫無相像之處。
不,若要按照我的願望、我的職責談論她,我不能用這種方式。我一旦設法描繪出某個圖像,許許多多回憶就會猛地起而否決它。我還是盡可能單純地回想就好。
由於她從不說自己的事,我完全不知道她最早的記憶是什麼。她倒存在於我所有幼時記憶裡。回溯到最久遠的初始,我看到的是她;除此之外,在我最稚嫩的歲月中,就只有一片闇黑,我只是在其中摸索前行。不過她之所以開始在我的人生中扮演她的角色,是拜一個悲劇事件之賜,我在《窄門》和《如果麥子不死》裡頭都說過這件事。當時我們年紀多大?她十四,我十二,應該是這樣沒錯。我沒法確切記得了。不過在那以前,我已經能尋溯到她的微笑,甚至我似乎覺得,都是因為我對她的愛意將我喚醒,我才對存在這件事有所意識,才開始真正存在。這彷彿是在說,我身上的一切除了源自她的部分以外,沒有任何良善之處。我的童稚之愛跟我最早的宗教熱忱交融在一塊;或者至少是因為她的緣故,那份愛意讓某種仿效心理滲進了我的宗教情懷。我似乎也覺得,在我趨近上帝的同時,我也趨近了她,而我喜歡在那種緩慢的昇華進程中感覺她和我周遭的土地逐漸縮小。倘若我不曾認識她,我會變成什麼?今天的我可以問自己這個問題,但在當時,這個問題並不存在。拜她之賜,我在我的糾結思路間隨處都能找到晶瑩閃亮的線索。雖然我在她的思緒中看到的是一片清明透徹,我必須承認我的內心充滿暗影,只有最好的那部分會與她產生交感。當時我的愛意是如此充沛而強勁,現在我似乎覺得那份愛只是更深地分裂了我的本性,而且想必我很快就明白,儘管我自以為把整個人付出給了她(那時我還多麼童稚天真!),我對她的崇拜之情並無法消除其他那些部分。
有些人在知道我此方面的想法以後,非常詫異一股那麼聖潔的影響力竟完全不足以讓我的書寫免於不純淨的成分。我們的表親奧嘉.卡亞特曾經向她表示過這種詫異,瑪德蓮告訴我當時她給的回答是:「我不認為自己有權利在任何方面改變他的思考傾向,而且如果安德烈可能為了顧慮我而寫出不完全是他認為自己該寫的東西,我會怨自己。」我寫的書有不少她從沒讀過,首先是因為她會刻意把目光從令她感覺不愉快或難受的事物移開;不過我認為她也是希望留給我更大的自由,不必冒著受她責難的風險、不必害怕會傷害她,她要讓我擁有如此的寫作自由。
儘管我說了這些,不過當然我對此無法確定。即便是靈魂最透明的人,也不會讓別人看見其中的許多折曲,就算是愛著自己的人也不例外。無論是評論文章、辱罵言論,想必都已經提供給她足夠的訊息,讓她知道我的一部分創作具有何種性質,即使她從沒親自看過那些作品。她對我小心掩藏了她可能從中感受到的痛苦。不過就在不久前,在一封她寫給我的信裡,有一句對我發出警訊的話,它似乎與我前面所寫的有所矛盾:「假使你能知道那些文字為我帶來的悲傷,你就不會把它寫出來。」(不過這裡所指的文字跟所謂「善良風俗」無關,而是一段乍看之下具有褻瀆性質的論述,是《新法蘭西評論》刊登的,而她的目光不巧瞄到那些詞句。)那時我似乎覺得她逾越了她的角色⋯⋯我們之間沒有多做什麼解釋。我只是當作沒這回事,而她對我的愛也讓她採取了同樣態度。
有時我確實會到離她很遠的地方,一走就是許多天。但打從孩提時代開始,我就養成向她報告一天的收穫,並在心神中將她與我的悲傷和喜悅聯想在一起。昨天晚上我就是這麼做的,但忽然間我想起來,她已經死了。
一切驟然失去了顏色,變得暗淡無光,無論是近來我對一段遠離她的時光所作的回想,或是我回想那些事的那一刻;因為我在思緒中重新經歷那些事,都是為了她。我立刻明白,失去她以後,我的存在也變得枉然,再也不知道為什麼自己現在還活著。
我不太喜歡我為了尊重她的謙虛而在我的書寫中替她取的「艾曼紐」這名字。她真正的名字之所以令我歡喜,可能只是因為自小開始,她在我心目中就一直召喚出優雅、溫柔、聰慧和善良的形象。當其他人也取這名字時,我會覺得它彷彿遭到篡奪,我覺得彷彿唯獨她有權利用這個名字。當我為我的《窄門》創造出「艾莉莎」這名字時,那並非出自矯情,而是基於保留。艾莉莎只能有一個。
可我書裡的艾莉莎並不是她。我描繪的不是她的圖像。她只是成為我構思女主角的出發點,我不認為她曾在其中認出多少自己的身影。她從沒和我談過那本書,因此我只能推測她讀它時可能有過的思索。那些思索對我而言一直帶著悲痛的色彩,就像一切源自她內心那股深沉哀愁的東西;我是在很久之後才開始揣測出那種哀愁的,因為她那極其含蓄的性格一直阻止她將其顯露、表達出來。
我為我的書設想出來的劇情無論再怎麼美,難道它不是在向她證明,面對現實劇碼的我一直是盲目的?想必她感覺自己比艾莉莎簡單得多,比她正常、平凡得多(我的意思是說:比較不像高乃依描繪的女性角色,比較不緊繃)?因為她無時無刻不在懷疑自己,懷疑自己的美麗、優點,懷疑一切為自身光輝、價值造就力量的事物。我相信,後知後覺的我對她的理解終於清楚多了,但在我的愛意最強烈的時候,我對她的誤解居然能深到那般程度!因為我的愛意使勁做的事並非讓我接近她,而是設法讓她接近我發明的那個理想人物。至少這是我現在的感覺,而且我不認為但丁對貝緹麗彩的行為與此有何不同。在她已不在人世的此刻,我之所以企圖重新找到、重新描繪她的往昔身影,那也是──特別是──為了一種做出補償的需求。我不想讓艾莉莎的幽靈遮蔽了她真正的存在。瑪德蓮很堅持不要我試圖到她妹妹臨終的床前見她最後一面。我從塞內加爾回來以後,得知華倫汀在經過兩個月的可怕折磨以後,終於剛步入她還能盼得的唯一安寧。我打算立刻趕往她家弔唁,兩位外甥女在那裡等著我,但瑪德蓮先是發了電報,然後又打電話,求我別去:「懇切拜託你在和我見面以前不要回艾裴隆街。」由於巴黎還沒有任何人知道我回來的消息,我在那兒沒別的事,趕忙搭上第一班火車就到了庫佛維爾。我問她為什麼那樣堅持,她說:「一想到你會看到華倫汀的美麗臉孔因為死前的掙扎而完全走樣,我就覺得很痛苦。有人告訴我她變得面目全非,那不是我希望你對她保有的記憶。」在那個當頭,我認出她那種從任何難以承受的情景前本能抽離的個性,但在我眼裡,她給我的理由只對她自己有效。基於同理心,我可以理解那些理由,但我無法贊同它們。罷了。當我突然接到她去世的消息,再度回到庫佛維爾,我正準備推開她小房間那扇門時,我想起那天,也就是一個月之前她對我說的話。我在希特雷的依芳.德雷斯特朗日那裡逗留了一陣,是她開車載我回庫佛維爾的,她把我留下來人就走了────沒錯,瑪德蓮的冰冷遺體就在那小房間裡,而就在我要打開那扇門時,我遲疑了一下,心想她是不是也會對我說同樣的話:「別來見我最後一面。」然後我又想,由於她沒經過所謂臨終前的痛苦掙扎,我再度看到的她應該和兩週前我離開她時差不多,只不過因為死亡而變得寂靜罷了。
當我走近她安息的床時,我很驚訝她的臉龐呈現出來的嚴肅。她的嫻淑及客氣向來為她的善良賦予如此光芒四射的力量,但那些特質彷彿只駐居於她的眼神中。於是,由於她的雙眼已經闔上,現在,她的五官線條中除了肅穆,沒留下其他東西;又於是,我望向她的最後那一眼提醒我的只會是她在生前必然早已對我的生活做出的嚴厲評判,而全然不是她那種難以言喻的柔情。她溫和地責備密友雅涅絲.柯波 的縱容習性。話說回來,她自己救助窮人時也對他們的缺失和弱點非常縱容,不過面對那些找不出任何藉口可以解釋他們為何沉淪在貧困中的人時,她倒會把自己武裝起來,顯得緊繃且不耐。她那種嚴厲完全不是出於天性,不過一旦她認為某個事物是罪惡,光是不允許它出現在自己身上對她而言還不夠(尤有甚者,她對罪惡的極端嫌惡使她毫不費力就能做到這點),而且她似乎覺得,假如她不能大剌剌地譴責別人身上的罪惡,她就等於是在鼓勵罪惡。她堅決相信我們的社會、文化、風俗全都因為自滿和鬆懈而逐漸解體,而在她所認為的鬆懈中,她願意看到的只有軟弱,而毫無自由主義或慷慨的成分。她的善良本質緩和了那一切,而如果有些人主要只見識過她那柔光四射般的優雅嫻淑,我在這點上表述的意見恐怕會使他們感到詫異。我遇到過一些頑強的清教徒,她和那些人毫無相像之處。
不,若要按照我的願望、我的職責談論她,我不能用這種方式。我一旦設法描繪出某個圖像,許許多多回憶就會猛地起而否決它。我還是盡可能單純地回想就好。
由於她從不說自己的事,我完全不知道她最早的記憶是什麼。她倒存在於我所有幼時記憶裡。回溯到最久遠的初始,我看到的是她;除此之外,在我最稚嫩的歲月中,就只有一片闇黑,我只是在其中摸索前行。不過她之所以開始在我的人生中扮演她的角色,是拜一個悲劇事件之賜,我在《窄門》和《如果麥子不死》裡頭都說過這件事。當時我們年紀多大?她十四,我十二,應該是這樣沒錯。我沒法確切記得了。不過在那以前,我已經能尋溯到她的微笑,甚至我似乎覺得,都是因為我對她的愛意將我喚醒,我才對存在這件事有所意識,才開始真正存在。這彷彿是在說,我身上的一切除了源自她的部分以外,沒有任何良善之處。我的童稚之愛跟我最早的宗教熱忱交融在一塊;或者至少是因為她的緣故,那份愛意讓某種仿效心理滲進了我的宗教情懷。我似乎也覺得,在我趨近上帝的同時,我也趨近了她,而我喜歡在那種緩慢的昇華進程中感覺她和我周遭的土地逐漸縮小。倘若我不曾認識她,我會變成什麼?今天的我可以問自己這個問題,但在當時,這個問題並不存在。拜她之賜,我在我的糾結思路間隨處都能找到晶瑩閃亮的線索。雖然我在她的思緒中看到的是一片清明透徹,我必須承認我的內心充滿暗影,只有最好的那部分會與她產生交感。當時我的愛意是如此充沛而強勁,現在我似乎覺得那份愛只是更深地分裂了我的本性,而且想必我很快就明白,儘管我自以為把整個人付出給了她(那時我還多麼童稚天真!),我對她的崇拜之情並無法消除其他那些部分。
有些人在知道我此方面的想法以後,非常詫異一股那麼聖潔的影響力竟完全不足以讓我的書寫免於不純淨的成分。我們的表親奧嘉.卡亞特曾經向她表示過這種詫異,瑪德蓮告訴我當時她給的回答是:「我不認為自己有權利在任何方面改變他的思考傾向,而且如果安德烈可能為了顧慮我而寫出不完全是他認為自己該寫的東西,我會怨自己。」我寫的書有不少她從沒讀過,首先是因為她會刻意把目光從令她感覺不愉快或難受的事物移開;不過我認為她也是希望留給我更大的自由,不必冒著受她責難的風險、不必害怕會傷害她,她要讓我擁有如此的寫作自由。
儘管我說了這些,不過當然我對此無法確定。即便是靈魂最透明的人,也不會讓別人看見其中的許多折曲,就算是愛著自己的人也不例外。無論是評論文章、辱罵言論,想必都已經提供給她足夠的訊息,讓她知道我的一部分創作具有何種性質,即使她從沒親自看過那些作品。她對我小心掩藏了她可能從中感受到的痛苦。不過就在不久前,在一封她寫給我的信裡,有一句對我發出警訊的話,它似乎與我前面所寫的有所矛盾:「假使你能知道那些文字為我帶來的悲傷,你就不會把它寫出來。」(不過這裡所指的文字跟所謂「善良風俗」無關,而是一段乍看之下具有褻瀆性質的論述,是《新法蘭西評論》刊登的,而她的目光不巧瞄到那些詞句。)那時我似乎覺得她逾越了她的角色⋯⋯我們之間沒有多做什麼解釋。我只是當作沒這回事,而她對我的愛也讓她採取了同樣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