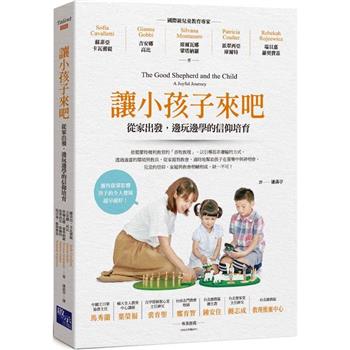為什麼需要宗教教育?
在一開始,我想花一點時間,和你一起省思這些問題,或許你也會有同樣的疑問,或是其他人也曾問過你類似的問題:
.兒童有能力活出與神的關係嗎?
.宗教教育能否回應兒童靈性上的重要需求?這是兒童需要的嗎?
.還是只是因為我們重視宗教教育,就想把宗教教育強加在兒童身上?
.若是缺乏某種形式的宗教培養,是否會影響兒童的協調發展?
.宗教究竟是讓我們的生命更豐富,還是更複雜?
我要以兩個不同層面的方式,來探索與回應上述的問題。
兒童自己的回應
第一種方式,是觀察沒有宗教教育的情況下,兒童能否展現「活出與神關係」的能力。這很不容易,因為這需要敏銳的注意力,才能看見人類靈性中某些潛能的表徵。過去數年間,我們持續記錄不同家庭與文化背景中的兒童,在沒有接受過任何宗教培育的情況下所發生的事件 ,以下是一個例子。
有一個三歲半的女孩問她的父親,世界是從哪裡來的。她的父親為無信仰者,講了一篇長長的道理,來說明世界並不是被誰創造出來的。在長篇大論之後,他又說有些人認為一切來自大能的造物主,他們稱之為「神」。在這個時候,小女孩開始高興地在房間裡跑來跑去,說:「我就知道你剛剛說的不是真的,是祂!是祂!」她的祖母當時也在場,雖然身為無神論者,但她告訴我們這個故事。當小女孩的爸爸在講話的時候,小女孩覺得他某種程度上背棄了她,但因為語言能力不足而無法反駁。當她父親說出那個字的時候,她立即抓住那個詞,並且說:「是祂!是祂!我知道你剛剛說的不是真的。」
這僅是許多經驗中的一個,帶領我見到各處兒童都擁有極大的宗教潛能,事實上,他們的宗教潛能十分強大,使我必須捫心自問:在兒童與神之間,是否存在著一種神秘的連結?
與兒童一起的旅程
第二個回答這些問題的方法,則是去觀察兒童本身以及他們如何回應。我們想要知道,是什麼碰觸了兒童的內在深處、讓他們喜樂地接受,又是哪些東西僅留於知識層次,因為我們希望我們傳授的內容能夠豐富兒童的心、生命和心智。大腦的認知很重要,但我們更應該用心去體會,如果我從聖經的角度來使用「心」這個詞,指的便是全然的自我。
對我們來說,認識天主各種愛的層次是很重要的,這同時也呼應了兒童的需求。知道兒童真正的需要,或許就是宗教教育與教理課程最迫切的問題。
最主要的是,基督宗教的訊息,正如聖若望(約翰)所說,是讓人們知道「天主是愛」(若望/約翰一書4:7)。然而愛有數種形式,例如在聖經中,神是新郎,有許多資料指出神對子民的愛是配偶之愛,但是我們不能跟兒童講述神就像是新郎,這種愛的面貌適合青少年或成年人對愛的渴求。
在神給我們的無窮而豐盛的愛當中,最能滿足兒童需求的愛的面貌是什麼呢?如果我們不知道兒童的需求,那我們說的和兒童聽到的可能不在同一個層次,說出來的話與被聽到的話並沒有交集。因此,一切端賴於我們如何向兒童呈現神。
要確認這一點,基督的「善牧」(好牧人)形象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向兒童示範「善牧的比喻」時,我注意到兒童迫切地想聆聽這則比喻,他們不斷地要求:「再講一次,我還想再聽一次。」看到兒童一再地操作「善牧」教具也令我十分訝異(善牧教具是用一個木製圓盤作為羊棧,其上有上漆的木製牧羊人和羊)。許多同事也在不同國家中注意到相同的現象,然後我們才體認到「善牧」觸及兒童深處的心弦,滿足了兒童的重要需求。
當然,從地下墓穴時期到今日的復活節禮儀,「善牧」是一個基督論(Christological)的形象,是基督徒傳統的根基。比喻中蘊含的秘密正回應著兒童的主要需求:對於建立關係的需求,以及對於保護之愛的需求。兒童正處於對保護的敏感期,而善牧的比喻能夠滿足這個具「保護之愛」特質的需求。
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說明當兒童在與神的關係中受到幫助時,他們會給出的回應。最重要的一點,是「善牧」(以及其他之後會說明的主題)在不同國家與環境的兒童身上,會引發出相似的回應,不論是出身於義大利的農家、工人家庭、中產階級家庭(甚至是吉普賽家庭)的兒童、非洲未能入學的兒童、貧窮或是中上階級的墨西哥兒童、阿根廷和哥倫比亞的兒童,以及在美國和加拿大的許多社區裡的兒童,皆是如此。
還有許多其他的例子,不只限於這些兒童個人,而是許多地方的兒童都用同樣的方式回應,這揭示了兒童確實擁有的潛能,讓我們窺見兒童的宗教世界,也促使我提問:難道這一切是因為他們是「兒童」嗎?
兒童的宗教世界
當我們和兒童相處時,事實上我們是與活在另一個世界的人相處。兒童活在一個不同的宗教世界,他們活出與神關係的方式,與我們成人大相逕庭。例如,所有人都知道,我們不能用和成人談論神的方式,去和三歲的兒童談論神,而這為我們帶來難題。姑且讓我們暫停討論,先進入一下兒童的世界。
兒童的宗教生命中有一個特質,就是當他們受到幫助而能更接近神時,兒童會擁有「喜樂」的能力,他們感受到一種特別的喜樂。
有許多事情能讓兒童感到開心,但開心有數種不同的層次。有一種開心比較像是「情緒上的興奮」,這有時還會導致緊張、疲倦和焦躁。當兒童接近神時,他們所感到的開心,是會讓他們感覺平靜、放鬆的喜樂,就像心靈深處的心弦被撩撥,他們要持續去聽從內心深處發出的聲音;也像是有人找到一個能夠給予生命的地方,一旦找著了,就不願離去。
就是這種喜樂讓兒童全然投入。有一次,在我和一些兒童一起祈禱了蠻長時間之後,一個叫做絲蒂芬妮的小女孩說:「我的身體很開心。」彷彿她和神同在時,感受到了生理上的喜悅。兒童全然地投入他們的生命,當他們祈禱或是聆聽天主聖言時,是不帶保留的全然投入。
在兒童聆聽「善牧比喻」時,總是有這種喜樂的回應,和善牧在一起時,兒童顯現出安然舒適的樣子。孩子能夠輕易且自發地由衷表達他們的宗教感受,似乎這對他們來說,是再自然不過的事。
這些喜樂的回應是非常重要的,滿足兒童的關鍵需求就是最令人欣喜之事。這些回應告訴我們宗教培育並不是我們強加給兒童的,反之,宗教經驗的深刻以及它所帶來的寧靜感受是如此強大,才足以回應兒童內在的關鍵需求。當我們幫助兒童與神相會時,我們正是在回應兒童未說出口的請求:「幫助我,讓我自己更接近神。幫助我,讓我更加成為我自己。」
為什麼要在孩子年幼時就提供宗教教育?
現在我們要進入另一個層次的問題,你可能也問過這些問題,或是有人問過你這些問題:
.六歲之前的兒童,有必要提供宗教教育嗎?
.為什麼要那麼早開始?
.等到孩子大一點再開始不是比較好嗎?等他們上學後再開始,或是當他們開始有「邏輯推理能力」(大約六或七歲)的時候再開始?
我對這些問題的回應是基於兒童已經是人的基礎,而不是未來會長成的青少年或是準成人。兒童是有能力也有需求的人,吶喊著「現在請滋養我」。
生命的前幾年是最富創造力的時期,為數眾多的心理學者表示,人類百分之八十的能力都是在三歲之前形成的。如果每個兒童都擁有這個最豐富、最具創造力的階段,那麼兒童的宗教發展與靈性成長,在這個階段也具有同等的創造力。兒童不只擁有宗教能力,更有一種特別的宗教「饑渴」,當兒童饑渴時,他必須立即得到餵養,而不能等到明日。
要滿足這樣的饑渴,對我們來說並不容易,因為兒童活出與神關係的方式,和我們成人的方式十分不同,當我們試圖滋養兒童對神的渴望時,這同時也帶給我們重要的泉源。畢竟神不只是成人的神,誠如耶穌所說,我們必須要像兒童一樣才能進入天主的國,那兒童必定有值得我們學習之處。
兒童的方法
讓我們來談談兒童所擁有的,特別的宗教需求和宗教能力。兒童的宗教需求已在前述有所討論,我比較想要給你一些例子,讓你知道我所謂兒童的宗教「能力」是什麼意思,然後我會多加討論其中一些能力。
有一天,一群婦女來參觀我們的教理中心,他們注意到一個五歲女孩在揉麵,一個麵團加入酵母而另一團沒有,要看看這兩個麵團的差異(這是一個和酵母比喻相關的活動,之後會再說明)。我問小女孩是否願意向客人解釋她正在做的事,因為一個小孩做麵包並非尋常之事。當我問她的時候,她說:「我正在看天國是如何長大的。」就像她真的親眼見到天國在她面前滋長一樣。
另外一個我想到的例子,是在我進入學齡前宗教教育工作領域的初期。我在向一群四到六歲的兒童示範聖洗聖事(洗禮),我想要幫助他們理解覆手禮的動作,也就是呼求聖神(聖靈)降臨的手勢。我不知道這些孩子可以懂多少,我猜想這對他們而言可能太過困難,但我想試試,所以我把我的戒指拿下來,放在我的手裡,然後手心向下,鬆開手掌而讓戒指掉落。
我重複了兩到三次,然後說:「當我要給你禮物的時候,我必須要把我的手伸出去,並把手掌打開,不然就沒辦法把禮物從我手中交到你手中。」然後我又再做了一次動作,這次沒有使用戒指當道具,我說:「神父在聖洗聖事中做這個動作,但我們沒有看到他手上有掉東西下來,那他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彷彿我問的是一個太顯而易見的問題,兒童馬上回覆:「因為他給我們的是聖神。」對兒童來說,就是這麼簡單而明確。
在一開始,我想花一點時間,和你一起省思這些問題,或許你也會有同樣的疑問,或是其他人也曾問過你類似的問題:
.兒童有能力活出與神的關係嗎?
.宗教教育能否回應兒童靈性上的重要需求?這是兒童需要的嗎?
.還是只是因為我們重視宗教教育,就想把宗教教育強加在兒童身上?
.若是缺乏某種形式的宗教培養,是否會影響兒童的協調發展?
.宗教究竟是讓我們的生命更豐富,還是更複雜?
我要以兩個不同層面的方式,來探索與回應上述的問題。
兒童自己的回應
第一種方式,是觀察沒有宗教教育的情況下,兒童能否展現「活出與神關係」的能力。這很不容易,因為這需要敏銳的注意力,才能看見人類靈性中某些潛能的表徵。過去數年間,我們持續記錄不同家庭與文化背景中的兒童,在沒有接受過任何宗教培育的情況下所發生的事件 ,以下是一個例子。
有一個三歲半的女孩問她的父親,世界是從哪裡來的。她的父親為無信仰者,講了一篇長長的道理,來說明世界並不是被誰創造出來的。在長篇大論之後,他又說有些人認為一切來自大能的造物主,他們稱之為「神」。在這個時候,小女孩開始高興地在房間裡跑來跑去,說:「我就知道你剛剛說的不是真的,是祂!是祂!」她的祖母當時也在場,雖然身為無神論者,但她告訴我們這個故事。當小女孩的爸爸在講話的時候,小女孩覺得他某種程度上背棄了她,但因為語言能力不足而無法反駁。當她父親說出那個字的時候,她立即抓住那個詞,並且說:「是祂!是祂!我知道你剛剛說的不是真的。」
這僅是許多經驗中的一個,帶領我見到各處兒童都擁有極大的宗教潛能,事實上,他們的宗教潛能十分強大,使我必須捫心自問:在兒童與神之間,是否存在著一種神秘的連結?
與兒童一起的旅程
第二個回答這些問題的方法,則是去觀察兒童本身以及他們如何回應。我們想要知道,是什麼碰觸了兒童的內在深處、讓他們喜樂地接受,又是哪些東西僅留於知識層次,因為我們希望我們傳授的內容能夠豐富兒童的心、生命和心智。大腦的認知很重要,但我們更應該用心去體會,如果我從聖經的角度來使用「心」這個詞,指的便是全然的自我。
對我們來說,認識天主各種愛的層次是很重要的,這同時也呼應了兒童的需求。知道兒童真正的需要,或許就是宗教教育與教理課程最迫切的問題。
最主要的是,基督宗教的訊息,正如聖若望(約翰)所說,是讓人們知道「天主是愛」(若望/約翰一書4:7)。然而愛有數種形式,例如在聖經中,神是新郎,有許多資料指出神對子民的愛是配偶之愛,但是我們不能跟兒童講述神就像是新郎,這種愛的面貌適合青少年或成年人對愛的渴求。
在神給我們的無窮而豐盛的愛當中,最能滿足兒童需求的愛的面貌是什麼呢?如果我們不知道兒童的需求,那我們說的和兒童聽到的可能不在同一個層次,說出來的話與被聽到的話並沒有交集。因此,一切端賴於我們如何向兒童呈現神。
要確認這一點,基督的「善牧」(好牧人)形象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向兒童示範「善牧的比喻」時,我注意到兒童迫切地想聆聽這則比喻,他們不斷地要求:「再講一次,我還想再聽一次。」看到兒童一再地操作「善牧」教具也令我十分訝異(善牧教具是用一個木製圓盤作為羊棧,其上有上漆的木製牧羊人和羊)。許多同事也在不同國家中注意到相同的現象,然後我們才體認到「善牧」觸及兒童深處的心弦,滿足了兒童的重要需求。
當然,從地下墓穴時期到今日的復活節禮儀,「善牧」是一個基督論(Christological)的形象,是基督徒傳統的根基。比喻中蘊含的秘密正回應著兒童的主要需求:對於建立關係的需求,以及對於保護之愛的需求。兒童正處於對保護的敏感期,而善牧的比喻能夠滿足這個具「保護之愛」特質的需求。
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說明當兒童在與神的關係中受到幫助時,他們會給出的回應。最重要的一點,是「善牧」(以及其他之後會說明的主題)在不同國家與環境的兒童身上,會引發出相似的回應,不論是出身於義大利的農家、工人家庭、中產階級家庭(甚至是吉普賽家庭)的兒童、非洲未能入學的兒童、貧窮或是中上階級的墨西哥兒童、阿根廷和哥倫比亞的兒童,以及在美國和加拿大的許多社區裡的兒童,皆是如此。
還有許多其他的例子,不只限於這些兒童個人,而是許多地方的兒童都用同樣的方式回應,這揭示了兒童確實擁有的潛能,讓我們窺見兒童的宗教世界,也促使我提問:難道這一切是因為他們是「兒童」嗎?
兒童的宗教世界
當我們和兒童相處時,事實上我們是與活在另一個世界的人相處。兒童活在一個不同的宗教世界,他們活出與神關係的方式,與我們成人大相逕庭。例如,所有人都知道,我們不能用和成人談論神的方式,去和三歲的兒童談論神,而這為我們帶來難題。姑且讓我們暫停討論,先進入一下兒童的世界。
兒童的宗教生命中有一個特質,就是當他們受到幫助而能更接近神時,兒童會擁有「喜樂」的能力,他們感受到一種特別的喜樂。
有許多事情能讓兒童感到開心,但開心有數種不同的層次。有一種開心比較像是「情緒上的興奮」,這有時還會導致緊張、疲倦和焦躁。當兒童接近神時,他們所感到的開心,是會讓他們感覺平靜、放鬆的喜樂,就像心靈深處的心弦被撩撥,他們要持續去聽從內心深處發出的聲音;也像是有人找到一個能夠給予生命的地方,一旦找著了,就不願離去。
就是這種喜樂讓兒童全然投入。有一次,在我和一些兒童一起祈禱了蠻長時間之後,一個叫做絲蒂芬妮的小女孩說:「我的身體很開心。」彷彿她和神同在時,感受到了生理上的喜悅。兒童全然地投入他們的生命,當他們祈禱或是聆聽天主聖言時,是不帶保留的全然投入。
在兒童聆聽「善牧比喻」時,總是有這種喜樂的回應,和善牧在一起時,兒童顯現出安然舒適的樣子。孩子能夠輕易且自發地由衷表達他們的宗教感受,似乎這對他們來說,是再自然不過的事。
這些喜樂的回應是非常重要的,滿足兒童的關鍵需求就是最令人欣喜之事。這些回應告訴我們宗教培育並不是我們強加給兒童的,反之,宗教經驗的深刻以及它所帶來的寧靜感受是如此強大,才足以回應兒童內在的關鍵需求。當我們幫助兒童與神相會時,我們正是在回應兒童未說出口的請求:「幫助我,讓我自己更接近神。幫助我,讓我更加成為我自己。」
為什麼要在孩子年幼時就提供宗教教育?
現在我們要進入另一個層次的問題,你可能也問過這些問題,或是有人問過你這些問題:
.六歲之前的兒童,有必要提供宗教教育嗎?
.為什麼要那麼早開始?
.等到孩子大一點再開始不是比較好嗎?等他們上學後再開始,或是當他們開始有「邏輯推理能力」(大約六或七歲)的時候再開始?
我對這些問題的回應是基於兒童已經是人的基礎,而不是未來會長成的青少年或是準成人。兒童是有能力也有需求的人,吶喊著「現在請滋養我」。
生命的前幾年是最富創造力的時期,為數眾多的心理學者表示,人類百分之八十的能力都是在三歲之前形成的。如果每個兒童都擁有這個最豐富、最具創造力的階段,那麼兒童的宗教發展與靈性成長,在這個階段也具有同等的創造力。兒童不只擁有宗教能力,更有一種特別的宗教「饑渴」,當兒童饑渴時,他必須立即得到餵養,而不能等到明日。
要滿足這樣的饑渴,對我們來說並不容易,因為兒童活出與神關係的方式,和我們成人的方式十分不同,當我們試圖滋養兒童對神的渴望時,這同時也帶給我們重要的泉源。畢竟神不只是成人的神,誠如耶穌所說,我們必須要像兒童一樣才能進入天主的國,那兒童必定有值得我們學習之處。
兒童的方法
讓我們來談談兒童所擁有的,特別的宗教需求和宗教能力。兒童的宗教需求已在前述有所討論,我比較想要給你一些例子,讓你知道我所謂兒童的宗教「能力」是什麼意思,然後我會多加討論其中一些能力。
有一天,一群婦女來參觀我們的教理中心,他們注意到一個五歲女孩在揉麵,一個麵團加入酵母而另一團沒有,要看看這兩個麵團的差異(這是一個和酵母比喻相關的活動,之後會再說明)。我問小女孩是否願意向客人解釋她正在做的事,因為一個小孩做麵包並非尋常之事。當我問她的時候,她說:「我正在看天國是如何長大的。」就像她真的親眼見到天國在她面前滋長一樣。
另外一個我想到的例子,是在我進入學齡前宗教教育工作領域的初期。我在向一群四到六歲的兒童示範聖洗聖事(洗禮),我想要幫助他們理解覆手禮的動作,也就是呼求聖神(聖靈)降臨的手勢。我不知道這些孩子可以懂多少,我猜想這對他們而言可能太過困難,但我想試試,所以我把我的戒指拿下來,放在我的手裡,然後手心向下,鬆開手掌而讓戒指掉落。
我重複了兩到三次,然後說:「當我要給你禮物的時候,我必須要把我的手伸出去,並把手掌打開,不然就沒辦法把禮物從我手中交到你手中。」然後我又再做了一次動作,這次沒有使用戒指當道具,我說:「神父在聖洗聖事中做這個動作,但我們沒有看到他手上有掉東西下來,那他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彷彿我問的是一個太顯而易見的問題,兒童馬上回覆:「因為他給我們的是聖神。」對兒童來說,就是這麼簡單而明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