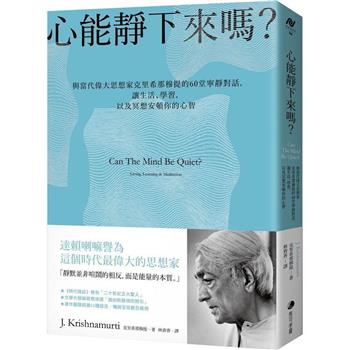第一部 對生活的探索
第三章 生命之流
他個子很高,穿著得體,眼神十分銳利。他學習佛法,因為這項學問確實滋養了他的智識,而且他也喜愛佛教的人生觀。雖然他生為基督徒,但基督教除了在上帝的愛中服務之外,沒有任何意義,只會讓人變得更無助。但後來,就連佛教也無法滿足他,所以他脫離了佛教。儘管他像是不怎麼認真地換過一種又一種的哲學觀點、一個又一個所謂的導師,但他的心智堪稱敏銳、靈活、樂於質疑與探究。他相當舒適地坐在一張扶手椅上,雙腿交疊,鞋子擦得光亮。你可以從他的雙手看出很多事:他的手指短而禿,但很纖細;他說他從事大量的園藝工作,以蒔花養卉為樂,並讓他的草坪免受蒲公英與雜草蔓延之害。他說,他的房子很大,他結婚了,但膝下無子;從他對這棟房子的描述來看,房子必定很漂亮,裡頭滿是古老的家具及擦得光亮的地板。他似乎也熱愛美食。但讓人納悶的是,他為什麼要絮絮叨叨地述說這些事。
鋪著綠色地毯與好看窗簾的房間讓人深感愉悅,從這個房間可以俯瞰一片翠綠草坪和一株美極了的鬱金香樹;在這初夏時分,大朵大朵的鬱金香綻放得如此燦爛動人。左側有一棵壯觀的老雪松,已經漸漸枯萎凋零了。越過草坪的另一邊是一片田野及小樹林、矮灌木叢與若干田地。這是個宜人的所在,寧靜祥和,不受往來車水馬龍的干擾,極為美麗而寂靜,你能確實感受到這片大地的脈動:四周圍繞著枝葉蓊鬱的林木,樹齡久遠、樹形優美,在傍晚投擲出深長的樹影。觀賞它們是一大樂事,當你觀看時,整片大地都改變了:一切似乎都鮮活了起來,而你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不只是坐在屋內那把堅實的椅子上,而是在外頭,融入那令人悸動的美與寂靜之中。你並不只是認同它們或是參與其中──這並非某種認同的智識過程──而是,你就是它們的一部分,你屬於它們。它們是你的朋友,它們的颯颯作響就是你的低語,它們的移動就存在於你的心智與心靈之中。這並非想像,因為想像會捉弄你,或是透過幻想、過度敏感的反應、所謂愛的不真實情感狀態來欺騙你,但事實並非如此。事實是,你與大地、天空、林木實為一體,並無分別,草坪的翠綠及樹木的暗影,都是你心智與心靈中的色彩,黃色並不渴望變成更為飽滿的鮮黃,翠綠的草坪在傍晚的光線下顯得生氣勃勃,彷彿你的每一個部分都身在其中。一隻雉雞走過草坪,你也跟著它一起,消失在一叢灌木後頭。
這個男人說:「我去了今天早晨的集會以及其他的集會。一條河流經我的房子,一條令人愉快的蔭涼河流;它蜿蜒地盈滿我所挖掘的許多小水池,但主流從我的屋旁流過。我也挖掘了其他水池,那是我的工作,一個星期當中我也會做些其他類型的工作,好貼補我的收入。但我似乎遇到了瓶頸,不太清楚自己怎麼了:我可以相當清晰而巧妙地思考、論辯,也大量閱讀,但這一切似乎變得十分空虛,我的生活似乎停滯了下來,就連我花了無數心思照料的花卉與草坪,也無法再帶給我任何樂趣。」
有一條河流經你的房子,它不停地流啊流,而你挖掘了好些小水池,引入河水來盈滿這些水池,讓睡蓮得以在水池中生長。你有點像這些睡蓮,是吧?心滿意足、毫髮無傷、舒適地生活在這些小水池中。而流經你的那條河,就是生命。
「是的,我了解你的意思。那正是我為我的生活所做的一切,你這麼快就看出來,真是怪了。」他沉默了好一會兒,注視著我,顯得相當震驚。不久之後,他問:「現在我該怎麼辦?」
屋內一片沉寂,他的問題在沉默中迴盪。他找到了自己的答案,但他做不到,因此他問出同樣的問題:「一個人如何能放下他為自己挖掘的小水池,以及花園、房子、書籍、家具、妻子,然後進入那條河流之中,永遠隨其逐流?」
河流可以流過每個障礙物,因為它有著源源不絕的河水。可能偶有流動緩慢的逆流或形成停滯不前的死水,但成為它們的還是那條河;而在雨季時,它們全都會被大量的河水沖走。河流始終川流不息,流過岩石、島嶼和田野。河流源源不竭,生命也是如此。
「我必須放下,」他問:「我悉心挖掘的小水池、我的草坪和樹木嗎?」
這個問題沒有答案,這條美好的河流有著樹蔭、湍流和以及水池(有些是活水,有些是死水)。沒有「如何」,因為你若是問了「如何」,你就永遠無法放下那些水池、房子、花園,永遠只能坐在岸邊看著河水流逝。永遠沒有「如何」,只有跳進河中、永遠隨其逐流的行動。
第十一章 比較滋生不滿
四隻禿鷹蹲踞在高大的羅望子樹上,牠們是脖頸光禿、翅膀巨大的龐然大物;禿鷹凝視著河面,等待屍體浮起──人類的屍體或動物的屍體。兩、三隻禿鷹會飛落在這些屍體上,同時趕跑烏鴉;等牠們飽餐一頓後,再飛回樹上。但這天早晨,牠們非常平靜地蹲踞在樹上,一動也不動。不一會兒,五隻烏鴉飛來了,逗弄起這些禿鷹,飛到牠們面前去拉扯牠們的翅膀,或者拍打自己的翅膀去挑釁牠們,直到其中一隻禿鷹飛了起來,然後一隻烏鴉試圖騎在牠的背上。這群烏鴉就這麼對禿鷹搗亂了至少半個小時,直到禿鷹終於飛走並越過河流,然後烏鴉們占據了禿鷹原來的位置,開始大肆歡慶、呼朋引伴。
這是個清新晴朗、陽光普照的早晨。河水生氣蓬勃,似乎捕捉了整個宇宙的光芒,尤其在這天早晨,河水幾乎靜止不動、波瀾不興,見不到一絲漣漪。當太陽從對岸的樹梢升起時,河水染成了金色,旋即又轉成銀色。大地的美與愛,廣袤無垠、無邊無際。
我們走過一道搖搖晃晃的小橋,跨越一條骯髒的淺溪,上岸並沿著數千年來朝聖的神聖路徑,朝佛陀說法的所在前進。眼前有羅望子樹、芒果樹、小村落和空蕩蕩的寺廟。
「我感到極度的不滿。我有些積蓄,我不必每天去上班、浪費我的生命,但我的不滿吞噬了我。我閱讀、冥想、跟人聊天,這些都讓我很開心,但是沒多久,這股深沉不安、無休止的不滿就會驀然淹沒我,似乎沒有任何書籍、冥想或是其他事物可以帶給我平靜。過一陣子,等這股不滿之情消褪,我又會恢復對冥想的熱切追尋、對自己的深度探索,以及對心智的探究、詢問、質疑和尋求。然而要不了多久,即便我並不想要,這股不滿、不安之情再次如浪潮般席捲而來,幾乎讓我窒息。數年來,我始終聆聽你的教導,也多次傾聽你的演講、與他人討論,但不知為何,這些年來,這種不滿與不安的重擔仍然存在。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另一個人說:「我住在這裡兩年了,我去過許多地方,也看到這個國家的許多美麗事物、舞蹈、令人驚嘆的色彩,以及美好的大地、丘陵、山巒、河流。我自然也跟許多人交談過,但經過這一切,我感覺這個國家正在分崩離析、四分五裂。我並非試圖將這個國家拿來與其他國家比較,我只是看著它,就像你經常強調的,不帶任何譴責、偏見或是想像的結論,但我可以感覺到一種衰退的劇變正在發生。或許一直以來皆是如此,不管是在英國統治之前或之後;我只是納悶,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當然,政客永遠無法解決問題,托缽僧、學者也是如此。只要看看眼前的這個女人,她看來是多麼奄奄一息、汙穢不堪,不存在一絲活力;她懷裡的孩子又是多麼瘦小、淚眼汪汪,不知笑聲為何物。疾病、貧窮以及伴隨而來的沉淪與墮落,蔓延了這整片大地。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成千上百萬的人都是這樣,但政府與人民似乎對此毫不關心,每個人變得如此冷酷無情、麻木不仁。我經常看著這幅景象,不僅熱淚盈眶,內心也淌著淚水。我並非沮喪消沉或是絕望地看待這一切,但我經常疑惑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我想,就像世界各地的其他人一樣,有些人要的是權力;就像全世界的所有政客,他們喋喋不休說著行話,透過排除異己的黨派、意識形態、狡辯和偽善,做出種種承諾,然而這些承諾全都是紙上空談。
「住在這裡,我能幫的忙有限,我盡可能幫助每個人,但我也知道這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彷彿一條水量洶湧、水深莫測的浩瀚大河,勢不可擋地奔流入海,這個國家正是如此,但這片大地、山丘、稻田、為白雪覆蓋的山巒,卻是無與倫比的美麗。或許它們會為這片飢餓的土地帶來些許滿足與慰藉。」
另一個人說道:「我也發現自己什麼都不想做。我必須工作謀生,但我不想去做任何事;想到我的餘生都得浪費在打字、速記、操作機器或是在學校教書上,我嚇壞了,我真的很害怕去做這些事。我的積蓄可能撐不了太久,一年之後,我還是得回去工作,但我不想承擔工作的責任,也不想對任何事或任何人負責。我曾經工作,但我發現工作讓我深感厭倦,所以兩個月之後,我懼怕到丟下一切、一走了之。」
雲層中的落日映照得天空絢麗多彩,呈現出金黃和紫色,甚至部分是泛著些許淡黃的綠色。大地之美在你眼前展開,緜延不絕的田野、林木及遠方層層疊疊的山巒。
你為何不滿?這股不安之情的意義何在?你是否希望你的心智被某件事物占據,以至於你的心智不斷尋尋覓覓,想找到某件它所感興趣的事?是否你的心智想要全心全意沉浸於某項行動之中,想要致力於某件事物、某種信仰或是某個活動?是否因為如此,它才會如此不安?是否有任何事物可以百分百地吸引你、讓你深感興趣,以至於這項興趣足以化解這樣的不安與不滿?
「我不認為我對某件事物特別感興趣。我工作過,但似乎沒有什麼事特別吸引我,很快地,我厭倦了工作,覺得無聊。我想拋下一切、一走了之。但是當我真的一走了之,過一陣子之後,我又變得焦躁不安,不滿的火焰再度燃燒起來,臻至絕望的境地。我嘗試閱讀以逃離這種情緒,但很快又深陷其中。」
這種不滿之所以產生,是否因為你活在一個充滿比較的世界,拿自己來與他人做比較,從比較級的觀點來思考,認為這個比那個更好?你是否陷入了更多、更好這類的用語當中?是比較滋生了這種不滿,還是你試圖找出一種抑制這種不滿的方法?
「我並不是想要壓抑它或粉飾它,而是試圖與它共存、了解它、找出它存在的原因,但我一直沒能做到。或許正如你所指出,真正的原因是我拿自己來與他人做比較。」
這種制約,是從童年開始的比較所致,包括在中小學、學院、大學等等,不斷地拿自己與他人、高高在上的技術專家、聖人、富人或是掌權者做比較。又或者,你拿自己與你所拼湊出來的某個典範或形象做比較。這種持續不斷的比較必然會滋生不滿。
「沒錯,我一直拿自己與你做比較。現在,我了解我也必須放掉那個我所形塑的你、那個我總是拿來與自己比較的形象。如此一來,我才能做回我自己。」
「你自己」正是比較的結果。你處於一種比較的心態,當你說:「當我不與他人比較時,我就能做回我自己。」你會成為什麼樣的人,仍然是受比較的心態所制約的結果。事實上,沒有做你自己這回事,因為你自己是時間、比較、絕望與悲傷、歡愉與恐懼等過程的結果,所以要緊的並不是做你自己,而是不帶比較心態地活著。當你這麼做時,你的心智將產生截然不同的質量,活在截然不同的維度裡,讓你得以擁有巨大的能量並卸除比較心念的重擔,你會變得更輕盈、更自由。
啊!我用了更輕盈、更自由的字眼──這又是一種比較,我們要說的不是這個意思。你會感覺輕盈,因為你的整個存在擺脫了那數百年來不斷累積的包袱。你能否過上不與他人比較的一天,保有不去比較的心態──一種只去觀察、不去比較與衡量的心態?因為衡量會帶給我們極大的幻象與錯覺,衡量的心態會告訴你:「我一直是、也將會是更好更棒的某某。」這種衡量只會導致各種形式的欺騙、虛偽,以及衝突。唯有當心智完全擺脫所有的比較時,才有真正的自由可言。
第二部 對學習的探索
第三十三章 思想滋生分歧
有一條小路蜿蜒於馬鈴薯田與冬麥田間,再往前是一大片開著白花的青豆。穿越羅望子樹與芒果園,綠鸚鵡與兀鷹蹲踞在最高的樹上;經過古老的村莊,那裡的寺廟歷史悠久到像是歲月在這裡凍結了。麥田裡有一頭大公牛,背上隆起了一坨巨大的肉峰,但牠看來似乎完全無害。你走過牠,幾個男孩跑來把牠趕到另一片田裡,之後又繼續追趕牠,但公牛從未攻擊他們。你經常看到牠躺在樹蔭底下打盹,或是沉思地反芻著。
塵土飛揚的小徑上有許多托缽僧,都是帶著乞缽、穿著破鞋的老僧人。這裡的村莊汙穢不堪,老人坐在山羊、狗兒、牛隻中間曬著太陽。沿著這條小徑,成千上萬的朝聖者走向那條河;在遠離河流的路上,村民們每天都步行到大城市販售他們的農產,換取幾個硬幣、一點油、一些布料,或是一個新的自行車打氣筒。他們去城裡的路上會喋喋不休地高聲談笑,但在回家的路上,他們會沉默地走回自己的村莊,穿越搖搖晃晃的橋,沿著小斜坡往上走。這是個多麼美麗的國家、又是多麼汙穢而墮落的城鎮,河流寂靜無聲地流經這些城鎮,接受了它們的髒汙,但在繼續往前流時,又將自己洗乾淨了,似乎從未受到任何傷害與汙染。那天早晨,河流平靜地在金色陽光下流淌著。
我們坐在房間裡俯瞰河流,兀鷹在蔚藍天空中盤旋得愈來愈高,兩隻鴿子在陽臺上築巢;那天早上不會太冷,予人深沉的平靜感。大約有三十個男孩與女孩坐在地板上,他們全都很害羞,但又想問許多問題;其中一個終於鼓起勇氣開口:「為什麼我要相信上帝?我們的父母與我們周遭的人都相信,所以我們也必須相信,但為什麼我們要相信呢?」
一個梳洗得很乾淨、面色紅潤、神情坦率的女孩說道:「我真的對上帝不感興趣,我不知道你為什麼想討論這個問題,我關心的是我的生活以及正確生活的方式,討論上帝似乎與我所關心的事並不相干。上帝對老一輩的人或許是必要的,但不會影響我的生活。討論這個問題似乎毫無用處。」
你不想知道為什麼數以百萬計的人對上帝感興趣嗎?
女孩回答:「或許我長大後會感興趣,但不是現在。我想了解生命以及如何生活,上帝跟這些有什麼關係?」
你知道,人類受了許多苦,人類的生命就是一場巨大的苦難;人類始終處於矛盾與衝突之中,事物變化無常、來來去去,充滿了太多的不確定性。因此有史以來,人類一直想知道是否有某些永恆不變的事物存在;他們說生命無常,會消逝、終止,所以他們想找到或相信某些不會消滅、永遠存在、不受人類影響而腐壞的事物。雖然不知道這樣的事物是否存在,他們相信、也真心希望它們存在。數千年以來,人類一直如此深信,並為自己的信仰而互相殘殺,還引發宗教戰爭──除了一、兩個宗教之外。
你說你對這些不感興趣,為什麼你會不感興趣?這是人類存在的一部分。你或許不相信上帝,但你或許相信原則、完美狀態、天國或天堂,這全是同一件事,你當然必須對人類所有的努力感興趣。你或許對數學不感興趣,但數學是你教育的一部分;同理,你必須對觸及人類心智的一切深感興趣,包括它的悲傷、困惑、荒謬、相信上帝或不相信上帝。你也必須關心生活、愛,以及死,因為這一切也是存在的一部分。所以,請注意那個男孩的問題,他問的是,為什麼一個人應該相信上帝;這是一個很自然的問題,因為他與你周遭的每個人都相信上帝,也是你的傳統、教養的一部分;甚至那些被教導不相信上帝的國家,這也是它們的人民教養的一部分。所以,讓我們來了解為什麼人類希望相信某些他們從自己的痛苦、易變、以及困惑中投射出來的事物;難道你不希望擁有某種安全感、某些可以依附或是保護你的事物嗎?
男孩與女孩面面相覷,臉色凝重而帶著躊躇,他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不僅僅是少數人,而是地球上的所有人都必須擁有安全感、食物、衣物,以及住所。失去了實質的安全感,就會對明天感到恐懼;而只要存在恐懼,我們的心智就無法正確而理智地運作。然而,就國家與國家彼此相互對抗的現況而言,實質的安全感極為匱乏,因此為了要擁有安全感與人身安全,我們緊抓著我們的小房子、一塊土地、家庭和工作不放;同時,我們也想擁有內心深處的安全感,讓自己感到安全、不受干擾,儘管我們知道死亡與痛苦依然存在,也知道生命就是一場對抗巨大孤獨感的持續奮戰。
因此我們告訴自己──但不是刻意地──一定存在某種不朽的、絕對的事物,而我們相信它的存在。這樣的事物往往與我們的現況相反,所以我們會說,上帝是愛、是永恆的美與和平,並將這個信念代代相傳下去。我們會說我們是猶太教徒、印度教徒、回教徒或是基督教徒。這種帶有所謂安全感的分歧,反而分裂了人們,從而帶來不安全感、戰爭以及仇恨。這一點很清楚,不是嗎?你可以看到你周遭的人,一群人對抗另一群人,一個人對抗另一個人;你的信仰將你與那些和你不同信仰的人區隔開來。你或許談論著要愛你的鄰舍,但是在這些話語背後,你的信仰、傳統,以及你對自己特定信仰的深信不疑隨之而來特有的傲慢與自負,卻讓你與他人產生了疏離與隔閡。所以,你知道了為什麼我們要篤信宗教,而為了那樣的信仰,我們樂於互相殘殺。所有的宗教都會談論愛與善待彼此,但信仰本身卻摧毀了仁慈、愛和深切真摯的善意。
「我明白你所說的話,先生,但是為什麼這種對自身安全的渴望,會以信仰的方式出現?」
正如我們所說,如果我們失去安全感,也就是秩序,我們的身體就無法正常而健全地運作;對所有的動物來說,安全感是首要的需求,對我們來說也是如此。我們所有人──而不僅是少數富裕的人──都必須擁有基本的物質生活必需品,這是絕對必要的;但如果你們將自己區分為印度教徒、回教徒或是其他群體,這一點就不可能做得到。這意味著,你們不能再稱自己為印度教徒、回教徒或者其他。別給你們自己貼上標籤,我們是人類、不是標籤;你們可以不再稱呼自己是這個、或是那個嗎?若非如此,你們只會給人類製造出更大的苦難。這也是你們教育的一部分,教育不只是研習學科而已。
其中一個男孩說:「我或許可以不再稱呼自己是個回教徒,但我周遭的人呢?我的父母可能會嚇壞了,而且很氣我。」
那麼,你會屈服於他們,然後回到那個自稱為回教徒的團體嗎?就像你必須學習數學一樣,你也必須學習在你的父母因為你不相信他們所相信的事物而對你生氣時,如何去應對;你必須學習如何處理關係,而不只是被告知要如何遵守規矩。這一切太困難了嗎?倘若是的話,你可以一步一步來,先採行一部分,從中學習一些事物,然後再繼續學習;別只是說因為你父母會生你的氣,所以你必須對他們讓步。學習與他們共處,而毋須相信他們所相信的事物。反抗他們、給自己建造一個小孤島、認為你可以自己過活或是加入其他反抗者的行列──然後他們又會建造出他們的孤島,與其他的孤島對立──這些都毫無益處,只會繼續帶來更多的分裂、敵對和戰爭。這就是人類的歷史。
我們必須與他人和平共處,因此我們必須了解這種分歧的信仰是如何產生。在內心深處,我們都嚇壞了,而且我們無法消除這種恐懼;於是我們投射出一個我們稱之為上帝的形象,我們以自己的形象創造出上帝,並且絕望地依附著這個上帝的形象,因為我們深受苦難,因為我們不但彼此爭戰、更與自己交戰,因為生命充滿了不確定性;而到了最後,我們總是難逃一死。所以,我們緊握著我們所創造出來的這個形象、象徵、由我們的手或心智創造出來的事物不放;重要的不是你相信什麼,而是你為什麼相信。倘若你深入探討,必定會發現那是因為我們內心都希望擁有一種堅實的安全感、內在的平靜,一種沉靜不朽的清澈明晰感。因此,思想遂發明了各種準則、形象和試探性的希望,並將自己區分為恆常與無常;本身是無常的它,卻創造出一種恆常。思想將世界區分為各種民族、群體,以及相對於團體的個體等等,沒完沒了。這種分歧不但在我們的外在世界屢見不鮮,也在我們的內在世界持續進行,它是一種我們自己與自己玩的遊戲,只會導致無盡的恐懼、蠻橫和暴行。
所以,你明白了思想如何滋生出仇恨敵意與狂妄自大,以及如何創造出它所謂的上帝與愛的形象。這些對立物,其實都是思想的產物,而人類卻永無休止地陷入其中。這一切全跟「愛」沒有半點關係,對吧?你知道我們說的這個字是什麼意思嗎?良善、仁慈、無所畏懼、不嫉妒。愛不是思想的產物。思想的產物具備了二元性的特質,也就是彼此對立,但因為愛並非由思想所組成,它沒有任何的對立物。去理解這一點是一件很棒的事,花些時間,就像你學習地理一樣去觀察這一切,就像你學習板球一樣去學習它。然後,你將會領悟到,任何形式的信仰都會變得完全沒有必要,你可以在沒有任何準則與公式的情況下活著。
第三章 生命之流
他個子很高,穿著得體,眼神十分銳利。他學習佛法,因為這項學問確實滋養了他的智識,而且他也喜愛佛教的人生觀。雖然他生為基督徒,但基督教除了在上帝的愛中服務之外,沒有任何意義,只會讓人變得更無助。但後來,就連佛教也無法滿足他,所以他脫離了佛教。儘管他像是不怎麼認真地換過一種又一種的哲學觀點、一個又一個所謂的導師,但他的心智堪稱敏銳、靈活、樂於質疑與探究。他相當舒適地坐在一張扶手椅上,雙腿交疊,鞋子擦得光亮。你可以從他的雙手看出很多事:他的手指短而禿,但很纖細;他說他從事大量的園藝工作,以蒔花養卉為樂,並讓他的草坪免受蒲公英與雜草蔓延之害。他說,他的房子很大,他結婚了,但膝下無子;從他對這棟房子的描述來看,房子必定很漂亮,裡頭滿是古老的家具及擦得光亮的地板。他似乎也熱愛美食。但讓人納悶的是,他為什麼要絮絮叨叨地述說這些事。
鋪著綠色地毯與好看窗簾的房間讓人深感愉悅,從這個房間可以俯瞰一片翠綠草坪和一株美極了的鬱金香樹;在這初夏時分,大朵大朵的鬱金香綻放得如此燦爛動人。左側有一棵壯觀的老雪松,已經漸漸枯萎凋零了。越過草坪的另一邊是一片田野及小樹林、矮灌木叢與若干田地。這是個宜人的所在,寧靜祥和,不受往來車水馬龍的干擾,極為美麗而寂靜,你能確實感受到這片大地的脈動:四周圍繞著枝葉蓊鬱的林木,樹齡久遠、樹形優美,在傍晚投擲出深長的樹影。觀賞它們是一大樂事,當你觀看時,整片大地都改變了:一切似乎都鮮活了起來,而你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不只是坐在屋內那把堅實的椅子上,而是在外頭,融入那令人悸動的美與寂靜之中。你並不只是認同它們或是參與其中──這並非某種認同的智識過程──而是,你就是它們的一部分,你屬於它們。它們是你的朋友,它們的颯颯作響就是你的低語,它們的移動就存在於你的心智與心靈之中。這並非想像,因為想像會捉弄你,或是透過幻想、過度敏感的反應、所謂愛的不真實情感狀態來欺騙你,但事實並非如此。事實是,你與大地、天空、林木實為一體,並無分別,草坪的翠綠及樹木的暗影,都是你心智與心靈中的色彩,黃色並不渴望變成更為飽滿的鮮黃,翠綠的草坪在傍晚的光線下顯得生氣勃勃,彷彿你的每一個部分都身在其中。一隻雉雞走過草坪,你也跟著它一起,消失在一叢灌木後頭。
這個男人說:「我去了今天早晨的集會以及其他的集會。一條河流經我的房子,一條令人愉快的蔭涼河流;它蜿蜒地盈滿我所挖掘的許多小水池,但主流從我的屋旁流過。我也挖掘了其他水池,那是我的工作,一個星期當中我也會做些其他類型的工作,好貼補我的收入。但我似乎遇到了瓶頸,不太清楚自己怎麼了:我可以相當清晰而巧妙地思考、論辯,也大量閱讀,但這一切似乎變得十分空虛,我的生活似乎停滯了下來,就連我花了無數心思照料的花卉與草坪,也無法再帶給我任何樂趣。」
有一條河流經你的房子,它不停地流啊流,而你挖掘了好些小水池,引入河水來盈滿這些水池,讓睡蓮得以在水池中生長。你有點像這些睡蓮,是吧?心滿意足、毫髮無傷、舒適地生活在這些小水池中。而流經你的那條河,就是生命。
「是的,我了解你的意思。那正是我為我的生活所做的一切,你這麼快就看出來,真是怪了。」他沉默了好一會兒,注視著我,顯得相當震驚。不久之後,他問:「現在我該怎麼辦?」
屋內一片沉寂,他的問題在沉默中迴盪。他找到了自己的答案,但他做不到,因此他問出同樣的問題:「一個人如何能放下他為自己挖掘的小水池,以及花園、房子、書籍、家具、妻子,然後進入那條河流之中,永遠隨其逐流?」
河流可以流過每個障礙物,因為它有著源源不絕的河水。可能偶有流動緩慢的逆流或形成停滯不前的死水,但成為它們的還是那條河;而在雨季時,它們全都會被大量的河水沖走。河流始終川流不息,流過岩石、島嶼和田野。河流源源不竭,生命也是如此。
「我必須放下,」他問:「我悉心挖掘的小水池、我的草坪和樹木嗎?」
這個問題沒有答案,這條美好的河流有著樹蔭、湍流和以及水池(有些是活水,有些是死水)。沒有「如何」,因為你若是問了「如何」,你就永遠無法放下那些水池、房子、花園,永遠只能坐在岸邊看著河水流逝。永遠沒有「如何」,只有跳進河中、永遠隨其逐流的行動。
第十一章 比較滋生不滿
四隻禿鷹蹲踞在高大的羅望子樹上,牠們是脖頸光禿、翅膀巨大的龐然大物;禿鷹凝視著河面,等待屍體浮起──人類的屍體或動物的屍體。兩、三隻禿鷹會飛落在這些屍體上,同時趕跑烏鴉;等牠們飽餐一頓後,再飛回樹上。但這天早晨,牠們非常平靜地蹲踞在樹上,一動也不動。不一會兒,五隻烏鴉飛來了,逗弄起這些禿鷹,飛到牠們面前去拉扯牠們的翅膀,或者拍打自己的翅膀去挑釁牠們,直到其中一隻禿鷹飛了起來,然後一隻烏鴉試圖騎在牠的背上。這群烏鴉就這麼對禿鷹搗亂了至少半個小時,直到禿鷹終於飛走並越過河流,然後烏鴉們占據了禿鷹原來的位置,開始大肆歡慶、呼朋引伴。
這是個清新晴朗、陽光普照的早晨。河水生氣蓬勃,似乎捕捉了整個宇宙的光芒,尤其在這天早晨,河水幾乎靜止不動、波瀾不興,見不到一絲漣漪。當太陽從對岸的樹梢升起時,河水染成了金色,旋即又轉成銀色。大地的美與愛,廣袤無垠、無邊無際。
我們走過一道搖搖晃晃的小橋,跨越一條骯髒的淺溪,上岸並沿著數千年來朝聖的神聖路徑,朝佛陀說法的所在前進。眼前有羅望子樹、芒果樹、小村落和空蕩蕩的寺廟。
「我感到極度的不滿。我有些積蓄,我不必每天去上班、浪費我的生命,但我的不滿吞噬了我。我閱讀、冥想、跟人聊天,這些都讓我很開心,但是沒多久,這股深沉不安、無休止的不滿就會驀然淹沒我,似乎沒有任何書籍、冥想或是其他事物可以帶給我平靜。過一陣子,等這股不滿之情消褪,我又會恢復對冥想的熱切追尋、對自己的深度探索,以及對心智的探究、詢問、質疑和尋求。然而要不了多久,即便我並不想要,這股不滿、不安之情再次如浪潮般席捲而來,幾乎讓我窒息。數年來,我始終聆聽你的教導,也多次傾聽你的演講、與他人討論,但不知為何,這些年來,這種不滿與不安的重擔仍然存在。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另一個人說:「我住在這裡兩年了,我去過許多地方,也看到這個國家的許多美麗事物、舞蹈、令人驚嘆的色彩,以及美好的大地、丘陵、山巒、河流。我自然也跟許多人交談過,但經過這一切,我感覺這個國家正在分崩離析、四分五裂。我並非試圖將這個國家拿來與其他國家比較,我只是看著它,就像你經常強調的,不帶任何譴責、偏見或是想像的結論,但我可以感覺到一種衰退的劇變正在發生。或許一直以來皆是如此,不管是在英國統治之前或之後;我只是納悶,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當然,政客永遠無法解決問題,托缽僧、學者也是如此。只要看看眼前的這個女人,她看來是多麼奄奄一息、汙穢不堪,不存在一絲活力;她懷裡的孩子又是多麼瘦小、淚眼汪汪,不知笑聲為何物。疾病、貧窮以及伴隨而來的沉淪與墮落,蔓延了這整片大地。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成千上百萬的人都是這樣,但政府與人民似乎對此毫不關心,每個人變得如此冷酷無情、麻木不仁。我經常看著這幅景象,不僅熱淚盈眶,內心也淌著淚水。我並非沮喪消沉或是絕望地看待這一切,但我經常疑惑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我想,就像世界各地的其他人一樣,有些人要的是權力;就像全世界的所有政客,他們喋喋不休說著行話,透過排除異己的黨派、意識形態、狡辯和偽善,做出種種承諾,然而這些承諾全都是紙上空談。
「住在這裡,我能幫的忙有限,我盡可能幫助每個人,但我也知道這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彷彿一條水量洶湧、水深莫測的浩瀚大河,勢不可擋地奔流入海,這個國家正是如此,但這片大地、山丘、稻田、為白雪覆蓋的山巒,卻是無與倫比的美麗。或許它們會為這片飢餓的土地帶來些許滿足與慰藉。」
另一個人說道:「我也發現自己什麼都不想做。我必須工作謀生,但我不想去做任何事;想到我的餘生都得浪費在打字、速記、操作機器或是在學校教書上,我嚇壞了,我真的很害怕去做這些事。我的積蓄可能撐不了太久,一年之後,我還是得回去工作,但我不想承擔工作的責任,也不想對任何事或任何人負責。我曾經工作,但我發現工作讓我深感厭倦,所以兩個月之後,我懼怕到丟下一切、一走了之。」
雲層中的落日映照得天空絢麗多彩,呈現出金黃和紫色,甚至部分是泛著些許淡黃的綠色。大地之美在你眼前展開,緜延不絕的田野、林木及遠方層層疊疊的山巒。
你為何不滿?這股不安之情的意義何在?你是否希望你的心智被某件事物占據,以至於你的心智不斷尋尋覓覓,想找到某件它所感興趣的事?是否你的心智想要全心全意沉浸於某項行動之中,想要致力於某件事物、某種信仰或是某個活動?是否因為如此,它才會如此不安?是否有任何事物可以百分百地吸引你、讓你深感興趣,以至於這項興趣足以化解這樣的不安與不滿?
「我不認為我對某件事物特別感興趣。我工作過,但似乎沒有什麼事特別吸引我,很快地,我厭倦了工作,覺得無聊。我想拋下一切、一走了之。但是當我真的一走了之,過一陣子之後,我又變得焦躁不安,不滿的火焰再度燃燒起來,臻至絕望的境地。我嘗試閱讀以逃離這種情緒,但很快又深陷其中。」
這種不滿之所以產生,是否因為你活在一個充滿比較的世界,拿自己來與他人做比較,從比較級的觀點來思考,認為這個比那個更好?你是否陷入了更多、更好這類的用語當中?是比較滋生了這種不滿,還是你試圖找出一種抑制這種不滿的方法?
「我並不是想要壓抑它或粉飾它,而是試圖與它共存、了解它、找出它存在的原因,但我一直沒能做到。或許正如你所指出,真正的原因是我拿自己來與他人做比較。」
這種制約,是從童年開始的比較所致,包括在中小學、學院、大學等等,不斷地拿自己與他人、高高在上的技術專家、聖人、富人或是掌權者做比較。又或者,你拿自己與你所拼湊出來的某個典範或形象做比較。這種持續不斷的比較必然會滋生不滿。
「沒錯,我一直拿自己與你做比較。現在,我了解我也必須放掉那個我所形塑的你、那個我總是拿來與自己比較的形象。如此一來,我才能做回我自己。」
「你自己」正是比較的結果。你處於一種比較的心態,當你說:「當我不與他人比較時,我就能做回我自己。」你會成為什麼樣的人,仍然是受比較的心態所制約的結果。事實上,沒有做你自己這回事,因為你自己是時間、比較、絕望與悲傷、歡愉與恐懼等過程的結果,所以要緊的並不是做你自己,而是不帶比較心態地活著。當你這麼做時,你的心智將產生截然不同的質量,活在截然不同的維度裡,讓你得以擁有巨大的能量並卸除比較心念的重擔,你會變得更輕盈、更自由。
啊!我用了更輕盈、更自由的字眼──這又是一種比較,我們要說的不是這個意思。你會感覺輕盈,因為你的整個存在擺脫了那數百年來不斷累積的包袱。你能否過上不與他人比較的一天,保有不去比較的心態──一種只去觀察、不去比較與衡量的心態?因為衡量會帶給我們極大的幻象與錯覺,衡量的心態會告訴你:「我一直是、也將會是更好更棒的某某。」這種衡量只會導致各種形式的欺騙、虛偽,以及衝突。唯有當心智完全擺脫所有的比較時,才有真正的自由可言。
第二部 對學習的探索
第三十三章 思想滋生分歧
有一條小路蜿蜒於馬鈴薯田與冬麥田間,再往前是一大片開著白花的青豆。穿越羅望子樹與芒果園,綠鸚鵡與兀鷹蹲踞在最高的樹上;經過古老的村莊,那裡的寺廟歷史悠久到像是歲月在這裡凍結了。麥田裡有一頭大公牛,背上隆起了一坨巨大的肉峰,但牠看來似乎完全無害。你走過牠,幾個男孩跑來把牠趕到另一片田裡,之後又繼續追趕牠,但公牛從未攻擊他們。你經常看到牠躺在樹蔭底下打盹,或是沉思地反芻著。
塵土飛揚的小徑上有許多托缽僧,都是帶著乞缽、穿著破鞋的老僧人。這裡的村莊汙穢不堪,老人坐在山羊、狗兒、牛隻中間曬著太陽。沿著這條小徑,成千上萬的朝聖者走向那條河;在遠離河流的路上,村民們每天都步行到大城市販售他們的農產,換取幾個硬幣、一點油、一些布料,或是一個新的自行車打氣筒。他們去城裡的路上會喋喋不休地高聲談笑,但在回家的路上,他們會沉默地走回自己的村莊,穿越搖搖晃晃的橋,沿著小斜坡往上走。這是個多麼美麗的國家、又是多麼汙穢而墮落的城鎮,河流寂靜無聲地流經這些城鎮,接受了它們的髒汙,但在繼續往前流時,又將自己洗乾淨了,似乎從未受到任何傷害與汙染。那天早晨,河流平靜地在金色陽光下流淌著。
我們坐在房間裡俯瞰河流,兀鷹在蔚藍天空中盤旋得愈來愈高,兩隻鴿子在陽臺上築巢;那天早上不會太冷,予人深沉的平靜感。大約有三十個男孩與女孩坐在地板上,他們全都很害羞,但又想問許多問題;其中一個終於鼓起勇氣開口:「為什麼我要相信上帝?我們的父母與我們周遭的人都相信,所以我們也必須相信,但為什麼我們要相信呢?」
一個梳洗得很乾淨、面色紅潤、神情坦率的女孩說道:「我真的對上帝不感興趣,我不知道你為什麼想討論這個問題,我關心的是我的生活以及正確生活的方式,討論上帝似乎與我所關心的事並不相干。上帝對老一輩的人或許是必要的,但不會影響我的生活。討論這個問題似乎毫無用處。」
你不想知道為什麼數以百萬計的人對上帝感興趣嗎?
女孩回答:「或許我長大後會感興趣,但不是現在。我想了解生命以及如何生活,上帝跟這些有什麼關係?」
你知道,人類受了許多苦,人類的生命就是一場巨大的苦難;人類始終處於矛盾與衝突之中,事物變化無常、來來去去,充滿了太多的不確定性。因此有史以來,人類一直想知道是否有某些永恆不變的事物存在;他們說生命無常,會消逝、終止,所以他們想找到或相信某些不會消滅、永遠存在、不受人類影響而腐壞的事物。雖然不知道這樣的事物是否存在,他們相信、也真心希望它們存在。數千年以來,人類一直如此深信,並為自己的信仰而互相殘殺,還引發宗教戰爭──除了一、兩個宗教之外。
你說你對這些不感興趣,為什麼你會不感興趣?這是人類存在的一部分。你或許不相信上帝,但你或許相信原則、完美狀態、天國或天堂,這全是同一件事,你當然必須對人類所有的努力感興趣。你或許對數學不感興趣,但數學是你教育的一部分;同理,你必須對觸及人類心智的一切深感興趣,包括它的悲傷、困惑、荒謬、相信上帝或不相信上帝。你也必須關心生活、愛,以及死,因為這一切也是存在的一部分。所以,請注意那個男孩的問題,他問的是,為什麼一個人應該相信上帝;這是一個很自然的問題,因為他與你周遭的每個人都相信上帝,也是你的傳統、教養的一部分;甚至那些被教導不相信上帝的國家,這也是它們的人民教養的一部分。所以,讓我們來了解為什麼人類希望相信某些他們從自己的痛苦、易變、以及困惑中投射出來的事物;難道你不希望擁有某種安全感、某些可以依附或是保護你的事物嗎?
男孩與女孩面面相覷,臉色凝重而帶著躊躇,他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不僅僅是少數人,而是地球上的所有人都必須擁有安全感、食物、衣物,以及住所。失去了實質的安全感,就會對明天感到恐懼;而只要存在恐懼,我們的心智就無法正確而理智地運作。然而,就國家與國家彼此相互對抗的現況而言,實質的安全感極為匱乏,因此為了要擁有安全感與人身安全,我們緊抓著我們的小房子、一塊土地、家庭和工作不放;同時,我們也想擁有內心深處的安全感,讓自己感到安全、不受干擾,儘管我們知道死亡與痛苦依然存在,也知道生命就是一場對抗巨大孤獨感的持續奮戰。
因此我們告訴自己──但不是刻意地──一定存在某種不朽的、絕對的事物,而我們相信它的存在。這樣的事物往往與我們的現況相反,所以我們會說,上帝是愛、是永恆的美與和平,並將這個信念代代相傳下去。我們會說我們是猶太教徒、印度教徒、回教徒或是基督教徒。這種帶有所謂安全感的分歧,反而分裂了人們,從而帶來不安全感、戰爭以及仇恨。這一點很清楚,不是嗎?你可以看到你周遭的人,一群人對抗另一群人,一個人對抗另一個人;你的信仰將你與那些和你不同信仰的人區隔開來。你或許談論著要愛你的鄰舍,但是在這些話語背後,你的信仰、傳統,以及你對自己特定信仰的深信不疑隨之而來特有的傲慢與自負,卻讓你與他人產生了疏離與隔閡。所以,你知道了為什麼我們要篤信宗教,而為了那樣的信仰,我們樂於互相殘殺。所有的宗教都會談論愛與善待彼此,但信仰本身卻摧毀了仁慈、愛和深切真摯的善意。
「我明白你所說的話,先生,但是為什麼這種對自身安全的渴望,會以信仰的方式出現?」
正如我們所說,如果我們失去安全感,也就是秩序,我們的身體就無法正常而健全地運作;對所有的動物來說,安全感是首要的需求,對我們來說也是如此。我們所有人──而不僅是少數富裕的人──都必須擁有基本的物質生活必需品,這是絕對必要的;但如果你們將自己區分為印度教徒、回教徒或是其他群體,這一點就不可能做得到。這意味著,你們不能再稱自己為印度教徒、回教徒或者其他。別給你們自己貼上標籤,我們是人類、不是標籤;你們可以不再稱呼自己是這個、或是那個嗎?若非如此,你們只會給人類製造出更大的苦難。這也是你們教育的一部分,教育不只是研習學科而已。
其中一個男孩說:「我或許可以不再稱呼自己是個回教徒,但我周遭的人呢?我的父母可能會嚇壞了,而且很氣我。」
那麼,你會屈服於他們,然後回到那個自稱為回教徒的團體嗎?就像你必須學習數學一樣,你也必須學習在你的父母因為你不相信他們所相信的事物而對你生氣時,如何去應對;你必須學習如何處理關係,而不只是被告知要如何遵守規矩。這一切太困難了嗎?倘若是的話,你可以一步一步來,先採行一部分,從中學習一些事物,然後再繼續學習;別只是說因為你父母會生你的氣,所以你必須對他們讓步。學習與他們共處,而毋須相信他們所相信的事物。反抗他們、給自己建造一個小孤島、認為你可以自己過活或是加入其他反抗者的行列──然後他們又會建造出他們的孤島,與其他的孤島對立──這些都毫無益處,只會繼續帶來更多的分裂、敵對和戰爭。這就是人類的歷史。
我們必須與他人和平共處,因此我們必須了解這種分歧的信仰是如何產生。在內心深處,我們都嚇壞了,而且我們無法消除這種恐懼;於是我們投射出一個我們稱之為上帝的形象,我們以自己的形象創造出上帝,並且絕望地依附著這個上帝的形象,因為我們深受苦難,因為我們不但彼此爭戰、更與自己交戰,因為生命充滿了不確定性;而到了最後,我們總是難逃一死。所以,我們緊握著我們所創造出來的這個形象、象徵、由我們的手或心智創造出來的事物不放;重要的不是你相信什麼,而是你為什麼相信。倘若你深入探討,必定會發現那是因為我們內心都希望擁有一種堅實的安全感、內在的平靜,一種沉靜不朽的清澈明晰感。因此,思想遂發明了各種準則、形象和試探性的希望,並將自己區分為恆常與無常;本身是無常的它,卻創造出一種恆常。思想將世界區分為各種民族、群體,以及相對於團體的個體等等,沒完沒了。這種分歧不但在我們的外在世界屢見不鮮,也在我們的內在世界持續進行,它是一種我們自己與自己玩的遊戲,只會導致無盡的恐懼、蠻橫和暴行。
所以,你明白了思想如何滋生出仇恨敵意與狂妄自大,以及如何創造出它所謂的上帝與愛的形象。這些對立物,其實都是思想的產物,而人類卻永無休止地陷入其中。這一切全跟「愛」沒有半點關係,對吧?你知道我們說的這個字是什麼意思嗎?良善、仁慈、無所畏懼、不嫉妒。愛不是思想的產物。思想的產物具備了二元性的特質,也就是彼此對立,但因為愛並非由思想所組成,它沒有任何的對立物。去理解這一點是一件很棒的事,花些時間,就像你學習地理一樣去觀察這一切,就像你學習板球一樣去學習它。然後,你將會領悟到,任何形式的信仰都會變得完全沒有必要,你可以在沒有任何準則與公式的情況下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