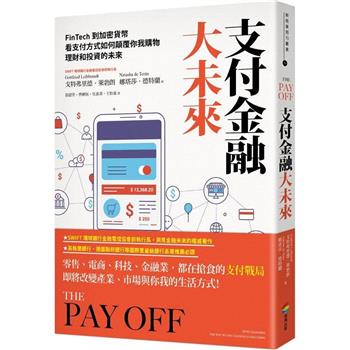前言
你上一次花錢是什麼時候?
應該是不久之前。平均而言,大家每天都會花錢一次,不過多數人花錢的次數遠多於這個數字。但你有多常想到支付的過程呢?
支付是免費的嗎?誰看到你在支付,過程當中他們會獲得多少資訊?金錢如何移動?收款人何時會實際收到款項?他們收到多少?在過程當中,有多少機構、機器或是人員參與金錢的流動中?這些如何連結在一起?誰替他們付款?誰控制他們?如果系統無法運作,那結果又會如何?
如果你特別留意,就會發現支付的行為無所不在。在收銀台前,你可能會使用硬幣、信用卡或手機支付。在網路上,你會把虛擬購物車推到虛擬收銀台處,使用你的虛擬信用卡。沒錯,就是如此。比較少人注意的,是你用定期支付或是直接從帳戶扣款的方式支付每個月的房租、貸款、水電費等。更少人注意的,就是你在亞馬遜網站上付費看電影,或是搭乘Uber 的時候。無疑地,一些絕頂聰明的人正不斷努力的把我們的支付方式變得更容易。
據說金錢就是讓社會能夠超越史前部落的三個抽象概念之一(另外兩個是宗教與文字書寫)。我們都知道錢很重要,即使我們對錢扮演的角色不怎麼感興趣也一樣。但錢最終的目的當然就是要使用,用來支付,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多少都該了解支付運作的方式。
支付可能不怎麼有趣,但卻非常強而有力,也非常重要:我們如何支付這件事,對日常生活有著實際且深遠的影響。支付的方式對了,經濟活動就會欣欣向榮;支付的方式錯了,經濟活動就會遭到扼殺。沒有支付,錢就不會發揮作用,如果錢失效了,我們的經濟與社會就可能(或者恕我直言,是就會)失去作用。想像一下貨架上沒有食物,油泵沒有油,沒有供電網的情形,還記得美國記者阿弗雷德.亨利.路易士(Alfred Henry Lewis)所說的話嗎:「人類與混亂狀態之間的距離只有九餐之遙。」我們與其說是那條不可跨越的準則,不如說是我們間的支付系統以及法律規範完全崩壞的距離。
支付的豐富程度與重要性,使這個議題在任何時候都攸關重大,但今天更值得我們探討,因為支付的「當下」比過去更令人興奮。改變的速度很快。各國或是各州幾乎在一夜之間就推翻了過去的習慣,錢潮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湧入該產業。
支付很可能是簡單且即時的動作,但我們今日所選擇的支付方式卻會帶來深遠的影響。我們支付的方式正在改變,運用的支付工具也在改變,這些改變的結果讓我們不僅使用錢包;新的支付方式讓我們能夠用前所未有的方式花錢與借錢。這些都太重要了,不容我們忽視或是留待專家面對,這也就是本書要探討這個主題的原因。
改變支付方式同時帶來了風險與機會。科技改變了全球的支付方式,但卻沒有一體適用的解決方法,因此風險相當高。
我們的社會是貨幣的社會;因此,這仰賴大家用錢。可選擇的支付方式決定了是否、在何處以及如何融入社會。要用錢,你就必須能夠移動錢,但如果我們選擇了自私的支付方式,導致社會的某些部門無法再這麼做,結果會如何?如果無現金的數位支付選擇,使得大都會的人口承受不公的沉重負擔,甚至排除那些鄉村地區的居民、窮人、老年人、或是數位弱勢者,又會如何?如果某些人無法付款或是收款,那麼他們在社會當中如何擁有籌碼?
接著就是教育與節儉的問題了。如果小孩都碰不到錢,那麼我們要如何教小孩節儉?如果我們沒有看到數字,更沒有支付的慘痛經驗,又怎麼會規劃預算?那些想要分期付款的人,在瘋狂的人群中摩肩擦踵的人,以及那些投資與規範支付的人,仍沒有完全了解分拆與重新包裝支付款項的後果。
我們的支付方式,決定了誰能夠取得我們的資料,在支付的時候會有什麼風險,以及要付多少錢給支付的服務。這是由於改變的並非支付方式本身,也包含了背後支持支付方式的系統,以及擁有那些系統的人。除此之外,支付的經濟也在改變當中,支付的政策正在改變,支付方式背後的力量也在改變。我們支付方式的每個部分,都有著多方角力,例如央行與社群媒體龍頭。我們做出的日常支付選擇,都預示著我們未來的支付方式:我們所有的選擇,會決定哪些群體能從支付當中獲得多少利益;誰「擁有」支付的權力,以及如何運用這種權力。這些改變的潛在影響與分支影響相當大,可以說是難以估量。
接著就是支付方式的多元性。個人痛苦平凡的支付方式很可能只是個人的事,但是整體而言卻是強而有力、具有政治性且往往無所不在。支付的世界是全球性的,但支付的體制卻與地方有強烈的關聯。支付的行為是立即的,但是收到支付款項的時間往往慢到令人挫折。這是多方規範形成的雙邊作業。支付同時包含了操作與流程:可以是實體有形的,數位或類比的,古老或是最新的,有時候同時並存。支票很可能是老派的支付方式,但是在處理時卻需要最新的影像技術。
支付的市場(可說完全不是個市場)同時是集中與分散的。支付的款項同時流向來自約世界兩百多國約兩萬五千間銀行,但幾乎每一筆跨國的支付僅經由十五間銀行之一。當中包含了許多技術,但僅有一些技術是所有支付都需要的。支付的網路既是單數也是複數的:就像網路是單一的系統,但結合了大量的子系統。
廣大系統的一些部分多到難以勝數。目前沒有已知的資料記載這些主要的支付方式,這些數字與大小會讓交易癱瘓。支付可能是不記名或記名的,或者在加密貨幣的狀況下是兩者並存的:比特幣的交易是匿名的,但所有人都看得到。系統同時是透明也是不透明的;既乾淨又骯髒,壞人可以用,好人也可以用。
支付當中包含了國際間的錯綜複雜關係,地理政治關係,搶劫以及法院的攻防,這些一點都沒有少。
藉由破壞支付程序以獲取不法利益的情形也在所多有,同時包含了高科技與低階的手法。還記得《終極警探3》(Die Hard with a Vengeance)電影當中的情節,那些壞人想要從紐約央行偷黃金的場景?二十年之後,北韓的駭客深入孟加拉的央行網路,想從央行的帳戶當中獲取十億美元。接著還有高盛最低階的助理在高階合夥人的眼皮底下,用不起眼的支票簿盜取數百萬英鎊。還有鑽石大亨尼拉夫.莫迪(Nirav Modi)用古老的支付工具並且夥同內部人員從印度旁遮普國家銀行偷取十五億美元。支付方式是通往金錢的通道,因此總是多方的目標。
支付方式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為能夠做什麼,還有當中包含的資訊:支付當中的資料當然是那些想利用資料獲利者稱頌的標的,同樣也讓相關機構在追蹤恐怖分子或軍火交易時讚不絕口;同樣的,那些想要在經濟或地理政治取得優勢的國際人士,同樣也高度讚譽這些資料;追查逃稅者的政府機構也是如此,更不用說那些懷疑配偶出軌者想要攤牌時用來當作證據了。
相對而言,由於隱私權條款,擁有權限制,累積整理相關資料的挑戰,我們的支付資料不可能像個資那樣被廣泛使用。但在獲利與政治權力岌岌可危時,很難說銀行會永遠如此。
最後在少數國家當中,支付與存款體系是合而為一的。銀行「擁有」支付體系,享受著兩者的好處。但銀行並沒有支付的神聖權利。支付與風險、流動性、技術、網路、體制有關。銀行非常擅長前兩項(風險和流動性),中間兩項(技術和網路)則表現一般,在第五項(體制)則沒有比其他機構好;你大可以說科技公司是他們的鏡像,這些公司在技術與網路方面發揮主要專長,擅長建構體制,但卻沒有風險與流動性的專業,不過現在他們卻涉足支付這一塊。他們擁有網路的力量與行銷知識,將存款與支付一分為二,改變我們目前習慣的付款方式。輕鬆就能支付有助於刺激商業活動,但把支付和銀行服務拆開會造成其他後果,目前很少有人想到這點。
社會「認為」的金錢世界運作方式及其「實際」的運作方式之間存在著鴻溝,最後往往會讓整個社會付出代價。就像把戰爭的責任全留給將軍扛實在太過沉重了一樣,金錢與支付的責任全由專家一肩扛起,同樣也太過沉重。在金錢的世界當中,沒有什麼比支付對日常生活造成的影響更大,也可以說金錢中的支付是最常遭到忽略的。我們希望藉由本書彌補這個部分,縮小我們對支付的依賴與對支付認知之間的鴻溝。
CHAPTER 2 如果錢不會移動,那要如何使世界運轉?
在二〇一八年,一個轉變命運的下午,金融時報記者婕米瑪.凱莉(Jemima Kelly)用她的iPhone 支付了倫敦一.五英鎊的公車費用。十五分鐘之後,查票員要查票時,她發現iPhone沒電了。在被要求出示付款證據的狀況之下,最後她提供了銀行往來紀錄佐證,但由於她的提款卡沒有在倫敦的運輸系統當中註冊,因此無法顯示她搭乘的趟次。接著就出現了一連串的官僚體系惡夢。無論當天她是否達到付款的上限,都必須面臨四百七十六英鎊的罰款,以及刑事訴訟(後來分別收到退款與撤銷告訴)。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現代的支付方式首重「資訊」。語言很可能會造成誤會。我們提到支付時,說的就是移動金錢以及付出金錢:是有關管道與通道;有關流動與移動;有關軌道與路線;有關交通、旅行、運輸、轉移、傳送。所有的這些內容,都暗示了移動,但是說實話,大部分的支付方式,都是噱頭:就是分類帳目的項目改變罷了。此外,雖然科技的改變已經超越了我們的認知,英格蘭銀行副總裁約翰.肯里夫(John Cunli¬e)說今日的支付方式,「就經濟上而言,等同於十八世紀銀行職員用於毛筆修改銀行的分類帳,一個帳戶計入借方,另一個計入貸方」,說的一點都沒錯。
凡有規則必有例外,這裡的例外,當然就是現金付款。如果你有銀行帳戶,你的現金交易,很可能會從ATM提款開始,並從帳戶當中扣除相應的款項。最終,會是商人把實體的現金存入銀行當中,在這裡所有的資金會進入帳戶當中。你的現金支付因此是把錢從你的銀行帳戶轉移到商人帳戶當中的迂迴路徑;分類帳再次改變。除了現金之外,錢並沒有真正的「移動」;擁有者的紀錄只不過是帳本上的項目改變而已。
黃金也是一樣。黃金很少移動。事實上,每一條金塊上,都有獨特的序號。你買賣黃金的時候,在大部分的情況下,只是轉移金條上的序號,或是金條的一部分,而不是金屬本身。即使是在金本位的狀況下,黃金大部分也只是帳本條目上的移動而已。上個世紀早期,全世界有許多黃金都存放在英格蘭銀行金庫當中層層疊起來的箱子裡,而有少量存放在美國聯準會。外國央行需要相互轉移黃金的時候,交易會記錄在英格蘭銀行或聯準會的帳冊裡,大部分時候,黃金本身並不會移動(雖然有時候可能會把金塊從一個箱子移到另外一個箱子當中)。兩次世界大戰以及一些事件之後,聯準會持有全世界最多的黃金庫存,而英格蘭銀行的庫存量則少了許多,但也適用同樣的情形。
在黃金「確實」移動的時候,必須要有詳盡的計劃以及昂貴的運輸成本。二〇一九年十月,波蘭的央行決定要取回二戰從華沙運到倫敦的黃金,市值四十億元。最高機密的行動包含了頂尖的警方部隊、包機、直升機,以及高科技火車,最後需要八趟夜間飛行的班機,經歷了好幾個月的時間,才把重達一百公噸的八千條黃金運回國。
銀行在帳面記錄方面,還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果我是你,你和我都在同一間銀行有戶頭,那麼我的銀行只要從我的帳戶扣款,加入你的帳戶即可。這種「移動」的情形發生在銀行的分類帳當中。如果我們和其他銀行往來,兩間銀行之間仍然會根據個別帳戶進行加減,接著處理他們之間的付款方式。
視支付方式而定,銀行(與其他支付服務提供者)進行這些不同方式的清算,不過都與更改分類帳的帳目有關,最後成為了央行的分類帳,所有的商業銀行都列出了個別的結餘。
因此除了現金以外,今日所有的支付方式都是記錄在分類帳系統當中的債務帳目,這是幾世紀之前就已經發明的系統。這種古老的做法,藉由電腦系統中帳冊裡跳動的數字,賦予了現代的意義。
今日的支付方式與金錢脫不了關係,最終也必定與銀行有關。我們大可以把存放在銀行的存款想成是用來支付日常費用的來源。就是這些付款帳戶讓銀行能夠賺錢,這點讓銀行與其他產業大相徑庭。他們是怎麼辦到的?要了解這點,我們就必須稍微了解歷史的來龍去脈。
要了解銀行體系的起源,就必須了解中世紀晚期的歷史,以及維也納城區。因此,讓我們想像一下中世紀的商人總共存了一百枚的錢幣在田野廣場(Piazza del Campo)。銀行承諾會保存這些錢幣,在商人需要的時候就能夠提領。銀行同時也保證透過收到指示時,能夠在帳面上把錢幣從一個商人處轉移給另外一個商人。
一陣子之後,銀行了解商人的個性非常謹慎,因為他們至少會放九十枚金幣在金庫裡。銀行決定把這些錢借給其他商人來賺取放款的利息。因此,銀行把九十枚金幣當中的七十五枚借出去,並且收取百分之五的利息。理論上,可能會有商人同時領錢,要取回金幣的風險,但銀行認為,這點相當不可能發生,當然也想要賺取額外的利息。
商人仍然擁有一百枚他們存入的金幣。對他們而言,這是真正的錢,他們可以隨時用來付款。這就像錢包裡面有金幣一樣,還省去了攜帶的麻煩。在此同時,借款人也能夠得到七十五枚金幣供他們花用。因此,銀行透過收取存放的金幣來放款,就創造了七十五枚金幣。真的很神奇吧!
在的銀行也是以類似的方式「創造」金錢。客戶把錢存在銀行當中,銀行用這些錢來放款。銀行把剩下的錢存入央行當中,確保具備足夠的流動性,以因應客戶提款的需求。銀行可以用現金放款,或者將款項存入借款人的帳戶當中。因此,銀行「神奇地」大筆一揮,就創造了許多錢,或者應該說揮兩次,損益平衡表兩邊各一次。在資產方加上一筆放款,例如為某間公司增加十萬元的放款,在負債方的活存或是支票帳戶當中記上同樣的金額,讓他們能夠花用。透過這兩筆,銀行就創造了十萬元的借款。
當然,這種神奇的情形也可能造成大災難。想想迪士尼的《幻想曲》
(Fantasia)電影當中,米老鼠是魔法師的學徒。米老鼠在擁有新的能力之後,他創造了魔法掃把替他扛水桶,後來發現卻不斷變多,最後整個地方都是。雖然大部分的經濟學家都同意現代的經濟要是沒有創造金錢的銀行,那麼就無法發揮正常的功能,但是這種做法無疑地會造成景氣繁榮與蕭條,我們已經經歷很多次了。折衷的方式,就是允許魔法的存在,但是必須讓魔法受到控制。這也就是為何銀行的法規非常嚴格,以及央行非常重要的原因了。這些就是能夠防止學徒(銀行)把整個地方毀了的魔法師。
創造錢的能力,也讓銀行在過去幾世紀以來成為付款的核心。然而,漸漸的,我們付款的方式正在改變:新的科技撼動了這一切,新的競爭者競相提供傳統銀行體系的替代方案。銀行很可能需要付款,但是付款真的需要銀行嗎?
你上一次花錢是什麼時候?
應該是不久之前。平均而言,大家每天都會花錢一次,不過多數人花錢的次數遠多於這個數字。但你有多常想到支付的過程呢?
支付是免費的嗎?誰看到你在支付,過程當中他們會獲得多少資訊?金錢如何移動?收款人何時會實際收到款項?他們收到多少?在過程當中,有多少機構、機器或是人員參與金錢的流動中?這些如何連結在一起?誰替他們付款?誰控制他們?如果系統無法運作,那結果又會如何?
如果你特別留意,就會發現支付的行為無所不在。在收銀台前,你可能會使用硬幣、信用卡或手機支付。在網路上,你會把虛擬購物車推到虛擬收銀台處,使用你的虛擬信用卡。沒錯,就是如此。比較少人注意的,是你用定期支付或是直接從帳戶扣款的方式支付每個月的房租、貸款、水電費等。更少人注意的,就是你在亞馬遜網站上付費看電影,或是搭乘Uber 的時候。無疑地,一些絕頂聰明的人正不斷努力的把我們的支付方式變得更容易。
據說金錢就是讓社會能夠超越史前部落的三個抽象概念之一(另外兩個是宗教與文字書寫)。我們都知道錢很重要,即使我們對錢扮演的角色不怎麼感興趣也一樣。但錢最終的目的當然就是要使用,用來支付,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多少都該了解支付運作的方式。
支付可能不怎麼有趣,但卻非常強而有力,也非常重要:我們如何支付這件事,對日常生活有著實際且深遠的影響。支付的方式對了,經濟活動就會欣欣向榮;支付的方式錯了,經濟活動就會遭到扼殺。沒有支付,錢就不會發揮作用,如果錢失效了,我們的經濟與社會就可能(或者恕我直言,是就會)失去作用。想像一下貨架上沒有食物,油泵沒有油,沒有供電網的情形,還記得美國記者阿弗雷德.亨利.路易士(Alfred Henry Lewis)所說的話嗎:「人類與混亂狀態之間的距離只有九餐之遙。」我們與其說是那條不可跨越的準則,不如說是我們間的支付系統以及法律規範完全崩壞的距離。
支付的豐富程度與重要性,使這個議題在任何時候都攸關重大,但今天更值得我們探討,因為支付的「當下」比過去更令人興奮。改變的速度很快。各國或是各州幾乎在一夜之間就推翻了過去的習慣,錢潮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湧入該產業。
支付很可能是簡單且即時的動作,但我們今日所選擇的支付方式卻會帶來深遠的影響。我們支付的方式正在改變,運用的支付工具也在改變,這些改變的結果讓我們不僅使用錢包;新的支付方式讓我們能夠用前所未有的方式花錢與借錢。這些都太重要了,不容我們忽視或是留待專家面對,這也就是本書要探討這個主題的原因。
改變支付方式同時帶來了風險與機會。科技改變了全球的支付方式,但卻沒有一體適用的解決方法,因此風險相當高。
我們的社會是貨幣的社會;因此,這仰賴大家用錢。可選擇的支付方式決定了是否、在何處以及如何融入社會。要用錢,你就必須能夠移動錢,但如果我們選擇了自私的支付方式,導致社會的某些部門無法再這麼做,結果會如何?如果無現金的數位支付選擇,使得大都會的人口承受不公的沉重負擔,甚至排除那些鄉村地區的居民、窮人、老年人、或是數位弱勢者,又會如何?如果某些人無法付款或是收款,那麼他們在社會當中如何擁有籌碼?
接著就是教育與節儉的問題了。如果小孩都碰不到錢,那麼我們要如何教小孩節儉?如果我們沒有看到數字,更沒有支付的慘痛經驗,又怎麼會規劃預算?那些想要分期付款的人,在瘋狂的人群中摩肩擦踵的人,以及那些投資與規範支付的人,仍沒有完全了解分拆與重新包裝支付款項的後果。
我們的支付方式,決定了誰能夠取得我們的資料,在支付的時候會有什麼風險,以及要付多少錢給支付的服務。這是由於改變的並非支付方式本身,也包含了背後支持支付方式的系統,以及擁有那些系統的人。除此之外,支付的經濟也在改變當中,支付的政策正在改變,支付方式背後的力量也在改變。我們支付方式的每個部分,都有著多方角力,例如央行與社群媒體龍頭。我們做出的日常支付選擇,都預示著我們未來的支付方式:我們所有的選擇,會決定哪些群體能從支付當中獲得多少利益;誰「擁有」支付的權力,以及如何運用這種權力。這些改變的潛在影響與分支影響相當大,可以說是難以估量。
接著就是支付方式的多元性。個人痛苦平凡的支付方式很可能只是個人的事,但是整體而言卻是強而有力、具有政治性且往往無所不在。支付的世界是全球性的,但支付的體制卻與地方有強烈的關聯。支付的行為是立即的,但是收到支付款項的時間往往慢到令人挫折。這是多方規範形成的雙邊作業。支付同時包含了操作與流程:可以是實體有形的,數位或類比的,古老或是最新的,有時候同時並存。支票很可能是老派的支付方式,但是在處理時卻需要最新的影像技術。
支付的市場(可說完全不是個市場)同時是集中與分散的。支付的款項同時流向來自約世界兩百多國約兩萬五千間銀行,但幾乎每一筆跨國的支付僅經由十五間銀行之一。當中包含了許多技術,但僅有一些技術是所有支付都需要的。支付的網路既是單數也是複數的:就像網路是單一的系統,但結合了大量的子系統。
廣大系統的一些部分多到難以勝數。目前沒有已知的資料記載這些主要的支付方式,這些數字與大小會讓交易癱瘓。支付可能是不記名或記名的,或者在加密貨幣的狀況下是兩者並存的:比特幣的交易是匿名的,但所有人都看得到。系統同時是透明也是不透明的;既乾淨又骯髒,壞人可以用,好人也可以用。
支付當中包含了國際間的錯綜複雜關係,地理政治關係,搶劫以及法院的攻防,這些一點都沒有少。
藉由破壞支付程序以獲取不法利益的情形也在所多有,同時包含了高科技與低階的手法。還記得《終極警探3》(Die Hard with a Vengeance)電影當中的情節,那些壞人想要從紐約央行偷黃金的場景?二十年之後,北韓的駭客深入孟加拉的央行網路,想從央行的帳戶當中獲取十億美元。接著還有高盛最低階的助理在高階合夥人的眼皮底下,用不起眼的支票簿盜取數百萬英鎊。還有鑽石大亨尼拉夫.莫迪(Nirav Modi)用古老的支付工具並且夥同內部人員從印度旁遮普國家銀行偷取十五億美元。支付方式是通往金錢的通道,因此總是多方的目標。
支付方式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為能夠做什麼,還有當中包含的資訊:支付當中的資料當然是那些想利用資料獲利者稱頌的標的,同樣也讓相關機構在追蹤恐怖分子或軍火交易時讚不絕口;同樣的,那些想要在經濟或地理政治取得優勢的國際人士,同樣也高度讚譽這些資料;追查逃稅者的政府機構也是如此,更不用說那些懷疑配偶出軌者想要攤牌時用來當作證據了。
相對而言,由於隱私權條款,擁有權限制,累積整理相關資料的挑戰,我們的支付資料不可能像個資那樣被廣泛使用。但在獲利與政治權力岌岌可危時,很難說銀行會永遠如此。
最後在少數國家當中,支付與存款體系是合而為一的。銀行「擁有」支付體系,享受著兩者的好處。但銀行並沒有支付的神聖權利。支付與風險、流動性、技術、網路、體制有關。銀行非常擅長前兩項(風險和流動性),中間兩項(技術和網路)則表現一般,在第五項(體制)則沒有比其他機構好;你大可以說科技公司是他們的鏡像,這些公司在技術與網路方面發揮主要專長,擅長建構體制,但卻沒有風險與流動性的專業,不過現在他們卻涉足支付這一塊。他們擁有網路的力量與行銷知識,將存款與支付一分為二,改變我們目前習慣的付款方式。輕鬆就能支付有助於刺激商業活動,但把支付和銀行服務拆開會造成其他後果,目前很少有人想到這點。
社會「認為」的金錢世界運作方式及其「實際」的運作方式之間存在著鴻溝,最後往往會讓整個社會付出代價。就像把戰爭的責任全留給將軍扛實在太過沉重了一樣,金錢與支付的責任全由專家一肩扛起,同樣也太過沉重。在金錢的世界當中,沒有什麼比支付對日常生活造成的影響更大,也可以說金錢中的支付是最常遭到忽略的。我們希望藉由本書彌補這個部分,縮小我們對支付的依賴與對支付認知之間的鴻溝。
CHAPTER 2 如果錢不會移動,那要如何使世界運轉?
在二〇一八年,一個轉變命運的下午,金融時報記者婕米瑪.凱莉(Jemima Kelly)用她的iPhone 支付了倫敦一.五英鎊的公車費用。十五分鐘之後,查票員要查票時,她發現iPhone沒電了。在被要求出示付款證據的狀況之下,最後她提供了銀行往來紀錄佐證,但由於她的提款卡沒有在倫敦的運輸系統當中註冊,因此無法顯示她搭乘的趟次。接著就出現了一連串的官僚體系惡夢。無論當天她是否達到付款的上限,都必須面臨四百七十六英鎊的罰款,以及刑事訴訟(後來分別收到退款與撤銷告訴)。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現代的支付方式首重「資訊」。語言很可能會造成誤會。我們提到支付時,說的就是移動金錢以及付出金錢:是有關管道與通道;有關流動與移動;有關軌道與路線;有關交通、旅行、運輸、轉移、傳送。所有的這些內容,都暗示了移動,但是說實話,大部分的支付方式,都是噱頭:就是分類帳目的項目改變罷了。此外,雖然科技的改變已經超越了我們的認知,英格蘭銀行副總裁約翰.肯里夫(John Cunli¬e)說今日的支付方式,「就經濟上而言,等同於十八世紀銀行職員用於毛筆修改銀行的分類帳,一個帳戶計入借方,另一個計入貸方」,說的一點都沒錯。
凡有規則必有例外,這裡的例外,當然就是現金付款。如果你有銀行帳戶,你的現金交易,很可能會從ATM提款開始,並從帳戶當中扣除相應的款項。最終,會是商人把實體的現金存入銀行當中,在這裡所有的資金會進入帳戶當中。你的現金支付因此是把錢從你的銀行帳戶轉移到商人帳戶當中的迂迴路徑;分類帳再次改變。除了現金之外,錢並沒有真正的「移動」;擁有者的紀錄只不過是帳本上的項目改變而已。
黃金也是一樣。黃金很少移動。事實上,每一條金塊上,都有獨特的序號。你買賣黃金的時候,在大部分的情況下,只是轉移金條上的序號,或是金條的一部分,而不是金屬本身。即使是在金本位的狀況下,黃金大部分也只是帳本條目上的移動而已。上個世紀早期,全世界有許多黃金都存放在英格蘭銀行金庫當中層層疊起來的箱子裡,而有少量存放在美國聯準會。外國央行需要相互轉移黃金的時候,交易會記錄在英格蘭銀行或聯準會的帳冊裡,大部分時候,黃金本身並不會移動(雖然有時候可能會把金塊從一個箱子移到另外一個箱子當中)。兩次世界大戰以及一些事件之後,聯準會持有全世界最多的黃金庫存,而英格蘭銀行的庫存量則少了許多,但也適用同樣的情形。
在黃金「確實」移動的時候,必須要有詳盡的計劃以及昂貴的運輸成本。二〇一九年十月,波蘭的央行決定要取回二戰從華沙運到倫敦的黃金,市值四十億元。最高機密的行動包含了頂尖的警方部隊、包機、直升機,以及高科技火車,最後需要八趟夜間飛行的班機,經歷了好幾個月的時間,才把重達一百公噸的八千條黃金運回國。
銀行在帳面記錄方面,還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果我是你,你和我都在同一間銀行有戶頭,那麼我的銀行只要從我的帳戶扣款,加入你的帳戶即可。這種「移動」的情形發生在銀行的分類帳當中。如果我們和其他銀行往來,兩間銀行之間仍然會根據個別帳戶進行加減,接著處理他們之間的付款方式。
視支付方式而定,銀行(與其他支付服務提供者)進行這些不同方式的清算,不過都與更改分類帳的帳目有關,最後成為了央行的分類帳,所有的商業銀行都列出了個別的結餘。
因此除了現金以外,今日所有的支付方式都是記錄在分類帳系統當中的債務帳目,這是幾世紀之前就已經發明的系統。這種古老的做法,藉由電腦系統中帳冊裡跳動的數字,賦予了現代的意義。
今日的支付方式與金錢脫不了關係,最終也必定與銀行有關。我們大可以把存放在銀行的存款想成是用來支付日常費用的來源。就是這些付款帳戶讓銀行能夠賺錢,這點讓銀行與其他產業大相徑庭。他們是怎麼辦到的?要了解這點,我們就必須稍微了解歷史的來龍去脈。
要了解銀行體系的起源,就必須了解中世紀晚期的歷史,以及維也納城區。因此,讓我們想像一下中世紀的商人總共存了一百枚的錢幣在田野廣場(Piazza del Campo)。銀行承諾會保存這些錢幣,在商人需要的時候就能夠提領。銀行同時也保證透過收到指示時,能夠在帳面上把錢幣從一個商人處轉移給另外一個商人。
一陣子之後,銀行了解商人的個性非常謹慎,因為他們至少會放九十枚金幣在金庫裡。銀行決定把這些錢借給其他商人來賺取放款的利息。因此,銀行把九十枚金幣當中的七十五枚借出去,並且收取百分之五的利息。理論上,可能會有商人同時領錢,要取回金幣的風險,但銀行認為,這點相當不可能發生,當然也想要賺取額外的利息。
商人仍然擁有一百枚他們存入的金幣。對他們而言,這是真正的錢,他們可以隨時用來付款。這就像錢包裡面有金幣一樣,還省去了攜帶的麻煩。在此同時,借款人也能夠得到七十五枚金幣供他們花用。因此,銀行透過收取存放的金幣來放款,就創造了七十五枚金幣。真的很神奇吧!
在的銀行也是以類似的方式「創造」金錢。客戶把錢存在銀行當中,銀行用這些錢來放款。銀行把剩下的錢存入央行當中,確保具備足夠的流動性,以因應客戶提款的需求。銀行可以用現金放款,或者將款項存入借款人的帳戶當中。因此,銀行「神奇地」大筆一揮,就創造了許多錢,或者應該說揮兩次,損益平衡表兩邊各一次。在資產方加上一筆放款,例如為某間公司增加十萬元的放款,在負債方的活存或是支票帳戶當中記上同樣的金額,讓他們能夠花用。透過這兩筆,銀行就創造了十萬元的借款。
當然,這種神奇的情形也可能造成大災難。想想迪士尼的《幻想曲》
(Fantasia)電影當中,米老鼠是魔法師的學徒。米老鼠在擁有新的能力之後,他創造了魔法掃把替他扛水桶,後來發現卻不斷變多,最後整個地方都是。雖然大部分的經濟學家都同意現代的經濟要是沒有創造金錢的銀行,那麼就無法發揮正常的功能,但是這種做法無疑地會造成景氣繁榮與蕭條,我們已經經歷很多次了。折衷的方式,就是允許魔法的存在,但是必須讓魔法受到控制。這也就是為何銀行的法規非常嚴格,以及央行非常重要的原因了。這些就是能夠防止學徒(銀行)把整個地方毀了的魔法師。
創造錢的能力,也讓銀行在過去幾世紀以來成為付款的核心。然而,漸漸的,我們付款的方式正在改變:新的科技撼動了這一切,新的競爭者競相提供傳統銀行體系的替代方案。銀行很可能需要付款,但是付款真的需要銀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