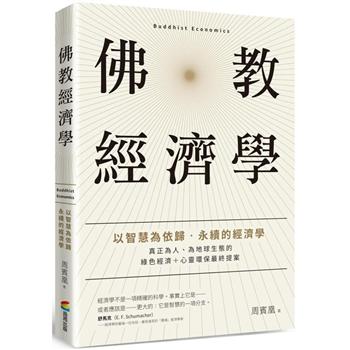Chapter 1 緒論
「經濟學不是一項精確的科學。事實上它是——或者應該是——更大的:它是智慧的一項分支。」
——舒馬克(1973)
佛教經濟學(Buddhist Economics)探討的是佛教觀點下經濟學應有的面貌。許多人聽到佛教經濟學的第一個反應是:有這種東西嗎?甚至就直接將它貼上「矛盾修飾語」(oxymoron)的標籤。人們如此反應的主要原因有二。首先,提起佛教,一般人腦中浮起的第一印象是出家僧侶——似乎是出世而摒棄物質的,而「正統」經濟學談的正是以滿足物質欲望為主的經濟活動之研究;二者似乎是南轅北轍的概念,因此怎麼可能扯上關係?然而這樣的看法並不正確,因為在一些經典中(如《轉輪聖王師子吼經》),佛陀曾提及在家居士的家庭之樂,更指出貧窮是一切非義與罪行之源(Rahula, 1959)。此外,從根本定義來說,佛教是「諸惡莫作,諸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見《法句經》)。可見如其他宗教一樣,佛教並未摒棄世間之物質生活。只是相對於外顯的行為(像是避惡行善),佛教更重視內在心念、意念的淨化,因此容易讓人們有所誤解。
第二個理由則是基於一個對佛教思想比較深層的了解:我們所在的這個娑婆世界是有成住壞空的非永恆世界;看似真實,實則為幻象(印度教與佛教經典中稱之為「摩耶」[maya])。眾生因無明而於其中生死輪迴不已,因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任務或意義,是如何自三界之苦中解脫,而不是去在意物質生活。然而如果對佛教思想有更深一層的暸解,會體悟到一切唯心所造:我們認知到的一切外境,皆反映(相應著)我們的內在。因此,如何如實地面對物質生活,而不是單從頭腦、想法上去否定物質層面的存在,才是真正的「理性」,而所謂的解脫,是真切地認識生命的本質,而不是逃避生命的實相。換句話說,問題的重點並不在於物質生活的本身,而是我們面對它的態度。佛陀告誡我們的,不是外在的摒棄物質,而是內在的不執著,也就是所謂的「出離」(renunciation)。
佛教經濟學是由恩斯特.費德里希(費瑞茲).舒馬克(Ernst Friedrich [Fritz] Schumacher)在1960年代所提出的。他在〈佛教經濟學〉一文開宗明義即說:「『正命』(right livelihood)是佛陀所倡導的八正道之一,因此很清楚地,是必然有佛教經濟學這種東西的。」在此,「命」係指賴以活命的生計,所以「正命」是指從事正當的職業,尤其是指不會傷害眾生(包括自己)的職業。
從傳統經濟學的角度來看,職業既提供個人生活所需之金錢,同時也是廠商生產的要素之一——也就是勞力(labor),正是經濟循環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只是在傳統經濟學裡,關注的重點在於商品與勞務的消費,而工作與勞力只是不可避免的必要手段而已。對於佛教徒而言,作為八正道之一的「正命」同樣是一種手段,但其目標或意義卻遠遠超過個人物質欲望滿足之追求。佛教的思想裡並未迴避物質之經濟活動,事實上反而是有一套一致的倫理準則規範。只是佛教經濟學與傳統經濟學在諸多基本假設上有根本上的不同,因此所推展而出的經濟面貌也就有徹底的差異。
舉例而言,傳統經濟學係在資源有限的限制下,以滿足自身之欲望(尤其是物質欲望)為目標。相對地,佛教徒認為欲望出於無明,所以應從根本——也就是去除無明——著手。不論是傳統經濟學或是佛教經濟學,都體悟到欲望是無底洞,無法填滿。但令人訝異地,前者所推演出的結論,竟然是在有限的物質生命下,「應該」盡量消費以滿足最大可能的欲望! 相對地,佛教經濟學則區分「需要」(need)與「想要」(want):前者是維持肉身之必要條件,而後者則是根源於無明之欲望,既非維持生命之必要,對於圓滿生命的追求也毫無助益。就物質層面而言,人們要滿足的是需要,而非想要:消費是「夠」了就好;唯有在物質消費上有所節制,我們才能在這有限的物質生命形式下,有心力往圓滿生命之道路邁進。
基於佛教這樣的理念,舒馬克給佛教經濟學如下的定義:
「商品的擁有與消費只是達成『目的』的『手段』,而佛教經濟學則是探討如何以最少『手段』來達成特定『目的』的系統性研究。」
舒馬克所說的「目的」,就是「解脫」(liberation;梵文拼音為moksha)。他說:「物質主義(materialism;唯物論)者主要關心的是財貨,而佛教徒主要關注的則是解脫。」從佛法的角度看,要達到解脫,消費可以是手段之一,而工作亦然。然而重點既不在於消費水準的高低,也不在於工作報償的多寡,而是在於人們從事消費與工作時的態度。他因此說:「對佛教徒而言,文明的本質在於品格(character)之淨化,而非欲望(wants)之加乘。」這樣的看法,與1950年代馬斯洛所提出的「需求層級」理論以及1990年代興起的正向心理學的看法不謀而合。我們在稍後的章節中會進一步說明。
某種意義上,「解脫」並不是一種可以達成的目標(something to obtain),而是對生命本質的全然了解,只能「證」得(to be attained),因此也就與生活密不可分——既在行住坐臥之間,也在分分秒秒之間。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我們「修行」的場域:以覺知的心態(mindful mindset)從事一切內在與外在的活動;當然也包括經濟活動在內。所謂的修行,簡單地說,就是修正行為;更深一點看,則包含「修」與「行」:「修」是內在的修正、調整,「行」是實行,也就是表現於外的行動。
正因如此,舒馬克甚至認為種種一切(包括消費、工作等所有經濟行為),自身即為目的(ends-themselves)。相對地,在資本主義經濟的眼中,消費是生命的目的,而工作則是手段。無怪乎舒馬克批評道:「在佛教徒的眼中,把物看得比人重要,把消費看得比創意活動來得重要,根本就是是非顛倒、本末倒置。這意味著⋯⋯屈服於邪惡的力量。」
舒馬克在文中很巧妙地避開佛教各個宗派對何謂「解脫」的不同主張,因此也避免了許多不必要的爭論。儘管如此,後續學者(有些是經濟學家,有些是佛教僧侶)在對佛教經濟學做更深入探討時,就開始在一些概念或看法上有所分歧。例如,傳統經濟學認為競爭是經濟的主要動力,但佛教經濟學則認為合作遠比競爭來得重要;如果對佛法瞭解深刻一點的話,會發現競爭根本就是違反佛法的精神。不過仍有些學者認為競爭可以是「好」的,只要其利益是大家共同分享的。甚至有學者認為佛教經濟學只是一種指引個體或企業方向的「策略」(如Zsolnai [2009]),不足以成為一套有系統的學門。這些分歧都是因為對佛教思想的理解不同所致。本書的目的之一,就是從佛教的根本思想,去重新架構經濟學,並探討佛教觀點下,諸如競爭、工作、消費、市場等等基本概念的內涵。
舒馬克的〈佛教經濟學〉一文雖然僅有短短的十幾頁,但已經清楚地點出了佛教經濟學的要旨。然而在舒馬克提出佛教經濟學後,似乎並未受到立即的關注,而是直到他將該文收編於1973年出版的《小即是美》(Small is Beautiful)一書中(收編為該書第四章),才受到較為廣泛的注意。有趣的是,當代心理學行為學派大師史欽納(Burrhus Frederic Skinner, 1904–1990)就受到該書的啟發,而將舒馬克的理念,結合行為學派的觀點,寫了一本他心目中的烏托邦式的生態村小說《桃源二村》(Walden Two, 1974)。
事實上,如果仔細研讀,可發現整本《小即是美》談的就是舒馬克眼中的佛教經濟學。例如,該書中第二部分談的是「資源」,依序探討教育(值得注意的是,他探討的不是作為生產要素的「勞力」;他認為教育才是人類最偉大的資源)、土地(他認為是最偉大的物質資源)、工業用資源、核能,以及技術(而且是「具有人類面貌的技術」(technology with a human face));該書第四部分則提出新的組織與所有權理論,其實就是提出符合佛教經濟學精神的廠商理論。
不過佛教經濟學始終未能成為經濟學的主流,僅悄悄地在不丹與泰國萌芽。以藏傳佛教為國教的不丹,早在1970年代就倡議以追求符合佛教的幸福快樂為其國家之目標,但並未引起太多的關注。不丹自1970年代起提倡國民幸福指數(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GNH),諸多措施,例如保護山林等,都頗符合佛教經濟學的概念。儘管曾被認為是世界最幸福的國家,然而近年來隨著民主的推行與開放,人們開始被外界五光十色的種種物質享受所迷炫,該國的幸福程度也逐漸下滑。
在泰國,似乎直到佛教僧侶暨學者佩尤托(Prayudh Payutto, 1938–)於1992年出版了《佛教經濟學:市場的中庸之道》一書,佛教經濟學才受到廣泛的注意。今日泰國有兩種實踐佛教經濟的模式:其一是在1970年代興起的「善地阿索」佛教改革運動(Santi Asoke Buddhist Reform Movement),主要以合作社或公社(collective or cooperative communities)的形式實踐佛教理念。另一是由泰皇蒲美蓬在1997年為因應經濟危機所提出的「泰國皇家自足經濟模型」(Royal Thai Sufficiency Economy Model)(參見Essen, 2010)。近年來許多社會企業或生態村、生態社區等組織,雖未盡然標榜佛教,但也都有佛教經濟學的精神內涵。我們在第7章會有進一步的介紹。
至於為什麼是佛教經濟學,而不是以其他宗教為基礎的經濟學呢?舒馬克在〈經濟學的角色〉(《小即是美》一書第三章)一文中指出,經濟學是一門「衍生」的科學,接受他稱之為「後設經濟學」(meta-economics)的指引。他所說的後設經濟學,指的是經濟學的基本信念(假設)。他說:「不論所教導的主題是科技或人文,如果這個教導不能引導釐清形而上學,也就是我們的基本信念,那麼它就無法教育人,因而也就不能對社會有任何實質的價值。」(參考舒馬克 [1973]〈教育:最偉大的資源〉一章。)
釐清基本信念是重要的。著名的生態經濟學家赫曼.戴利(Herman Daly, 1938–)在《邁向定態經濟》(Toward a steady-state economy; 1973)一書中,提出一個如今人們稱之為「戴利三角形」(Daly Triangle)或「戴利金字塔」(Daly Pyramid)的永續架構。從三角形的頂端往下,依序是終極目的(ultimate end)、中階目的(intermediate end)、中階手段(intermediate means),與終極手段(ultimate means)。根據戴利,人們追求的終極目標是福祉,這個福祉可以是簡單的快樂、和諧、自尊,進而到自我實現與開悟。中階目的主要是建立在整體人類與社會資本的發展,這些資本包括健康、財富、安全、知識、溝通等。要達成終極目標,需要以中階目的作為支撐,而連結二者的,是哲學(倫理)、道德,或神學,也就是系統性的核心或基本信念。
順著三角形再往下,中階目的的達成有賴中階手段的實現;中階手段主要是實質的經濟,其中包括建成資本(built capital)與人力資本。串連中階目的與中階手段的,是政治經濟制度——藉由合適的政治經濟制度才能把物質之經濟轉為人類與社會資本,進而導向終極目標。然而中階手段仍需仰賴終究的手段,也就是地球上有限的自然資本,才能達成,而連結著二者的,就是科學與技術。根據戴利三角形,科技、政治經濟制度,與系統性的信念(哲學或宗教信仰),這三者對於人類社會的永續發展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這裡所說的系統性信念,就相當於舒馬克所說的後設經濟學。
後設經濟學應具備怎樣的面貌呢?舒馬克說:「因為經濟學處理面對的是環境中的人,所以我們可以預期後設經濟學包含兩部分:一是處理人,另一則是處理環境。⋯⋯換句話說,我們期待經濟學的目的與目標,應推演自對人的研究;而至少很大程度它的方法論必須衍生自對大自然的研究。」近年來頗受重視的綠色經濟學,就是希望能發展出兼顧人類福祉與永續的替代方案(參見Cato, 2010)。綠色經濟學有二要件:一是以人為本,另一則是永續發展(周賓凰,2020),而正如舒馬克所言,前者有賴於「對人的研究」,後者有賴於「對大自然的研究」。只要再進一步探究,可知由於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因此我們對大自然的看法與態度所反映的也是我們的基本信念。換言之,真正的「以人為本」必然導向永續發展。
然而以物質主義為後設基礎的傳統經濟學既狹隘地把人變成消費與生產機器,其所推演出的線性經濟模式(從資源開採、生產、消費,到廢棄物丟棄)也與大自然的循環返覆體系大相逕庭。相對之下,佛教經濟學把人放在首要位置。佛教思想對於人,從靈性、心理,乃至物質層次,都有很完整嚴謹的說法。我們與大自然,包括所有的人類與其他生物,都是相互連結(interconnected)、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t)的(參考,如Brown(2017));星雲法師稱之為「同體共生」,因此佛教觀點下的經濟體系必然是一個循環的體系,而不是一個追求物質成長的體系。
舒馬克批評說,大多數經濟學家至今仍在追求一種荒謬的理念:希望把他們的「科學」變得如物理學般精確(這種傾向稱為「物理欽羨」[physics envy]),「彷彿那沒有意識的原子與依上帝形象所造的人之間,沒有根本上的質性差異。」他們追求所謂的「價值中立」(value neutral),結果他們所刻畫的世界只有價格,而沒有價值。相對之下,佛教經濟學把價值放在首位,因為價值反映的就是人們的基本信念。佛教經濟學者佐爾奈(Zsolnai, 2009)根據王爾德(Oscar Wilde)的名言而語帶諷刺地說:「經濟學家知道每樣東西的價格,卻對每樣東西的價值一無所知。」(Economists know the price of everything and the value of nothing.)
資本主義經濟學與佛教經濟學最根本的差異,在於前者的後設基礎是唯物的,而後者則是唯心的。舒馬克說得很好:「⋯⋯以物質追求為主要目標而忽視靈性的生命是空虛而不滿足的。這樣的生命必然導致人與人的對立、國與國的對立,因為人的需求是無止盡的,而這種無止盡唯有在靈性層面才能達成,而不在物質層面。」(見舒馬克 [1973] 第二章)另一位著名的異端經濟學家肯尼士.博丁(Kenneth Boulding, 1910–1993)也諷刺說:「如果有人相信在一個有限物質的星球上,存在一種物質可以有無止盡的成長,那麼這個人不是瘋子,就是經濟學家。」
舒馬克在書中對當代經濟學有許多嚴厲的批評,因為這種追求物質擴張與成長的經濟思維所帶來的,是人與自己、社會,乃至與大自然的疏離(alienation;或譯「異化」);疏離感滋養了孤獨與絕望,並終將導致災難。他在書中也引用了甘地的名言:「地球所提供的,足以滿足每個人的需要,但不是每個人的貪婪。」的確,他早在1960至1970年代所點出的諸多資本主義經濟的問題,在過去這三十多年來也一一浮現。無怪乎有學者認為,如果凱因斯是自亞當.斯密(Adam Smith)以來最偉大的正統經濟學家,那麼舒馬克無疑地就是當代最重要的「異端」經濟學家。在他於1977年瘁逝時,各界紛紛悼念,稱他為經濟學的先知。他所倡導的佛教經濟學,才是真正「以人為本」的經濟學。
然而佛教並不是後設經濟學的唯一選擇。舒馬克在〈經濟學的角色〉一文中說:「選擇佛教作為後設基礎是純然非刻意的;基督教、伊斯蘭教,或者猶太教的教理也都適用,正如其他偉大的東方傳承亦然。」事實上,他本人直到在1971年(時年60歲),在歷經了大半輩子的靈性追尋後,才正式成為天主教徒。的確,舒馬克只列了簡樸與非暴力兩項作為佛教經濟學的指導方針,而付之實踐則有賴佛教的另一原則:「中道」(the middle way; moderation)。可見他的目的僅在把以「物」為本的傳統經濟學,導回真正經濟學「以人為本」的應有面貌;這樣顯然才契合經濟學應有的「經世濟民」之意涵。
有鑑於我們這個世代所面臨的各種經濟、社會,與環境的危機,尋求新的可永續(sustainable)經濟學以取代資本主義經濟已變得刻不容緩。然而光是擁有科學或科技並不足以帶來「和平與永續」(peace and permanence;《小即是美》第二章的標題),因為「科學無法產生我們可據以維生的想法。」舒馬克批評他多數的經濟學同行們光是在鐵達尼號的甲板上重新安排著海灘椅的位子,而完全無視於橫在眼前的巨大冰山。可悲的是,這樣的情況在過去這數十年不但毫無改變,反而是變本加厲。
舒馬克認為,科學與科技必須有智慧作為依歸,「永續的經濟學」(economics of permanence)才是有可能的;這樣的觀點與戴利三角形的觀點完全契合。今日看來,佛教經濟學(或者說是以靈性為基礎的經濟學)正是最好的解方,而這對於以佛教為主要信仰的華人社會,更是適合。然而回顧佛教經濟學的發展,迄今仍未有較為完整的論述。如我們前面所提到的,舒馬克的論文較為精簡,因此並未能完整地涵蓋所有議題。也正因為這樣,學者在一些議題上不免有些歧見。
宗教所反映的,是人們的基本信念,然而即使是同一宗教的信仰者,彼此的理解也不盡然相同。同樣地,佛教徒也因生命層次領悟上的差異,而對經濟活動有不同的態度與看法。例如,佛教雖說修行有八萬四千法門,但大體上可以分為三類:人天道、解脫道,與菩薩道。修人天道者,仍在累積解脫三界的「資糧」(資本);走解脫道者則致力於個人超越三界之解脫,世間之福報對其而言,反而是一種束縛。至於行菩薩道者則更體悟到眾生與我為一,因此其努力的是所有眾生的解脫,而非僅局限於狹隘個人的「福祉」。因著這三種修行法門的差異,不同佛教徒對有成有壞的物質經濟的看法或態度也會有所差異。
基於上述之根本差異,本書以傳統個體經濟學的架構,依序從佛法的觀點,探討個體行為的基本假設、消費理論、廠商理論,與市場理論等議題。值得強調的是,佛教經濟學基本上是整體論的(holistic),因為任何的經濟決策與行動,都會影響到整個體系,包括環境與社會層面,而不只是局部經濟面的影響。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經濟學教授克萊爾.布朗(Claire Brown)在她的《佛教經濟學》(2017)一書中強調,根據佛法,我們——一切眾生——是相互連結、相互依存的。這樣的看法,與近年來興起的綠色經濟學的理念頗為契合。
佛法是博大精深的,從而衍生而出的佛教經濟學必然也是如此。有鑑於佛教經典的艱澀難解,當代有許多佛教大師致力於佛教的現代化,希望能夠把世界轉化為人間淨土,包括像是「人間佛教」(humanistic Buddhism;由太虛大師、印順法師、星雲法師、聖嚴法師、證嚴法師等所提倡)、「入世佛教」(engaged Buddhism;由一行禪師所提倡)等,其中也都有許多與經濟有關的論述。
本書的目的,僅是就筆者有限的瞭解,大膽地嘗試為佛教經濟學理出一個架構。與現有佛教經濟學文獻最大的不同是,本書主要以當代個體經濟學的分析架構為基礎,再依佛法的視角去推演經濟學應有的面貌。如此作法的好處是我們很容易可以比較佛教經濟學與傳統經濟學在各個面向的差異。讀者不難發現,本書的多數觀點都是來自舒馬克的《小即是美》;某種意義上,我們只是以經濟學的分析架構,重新組合、詮釋舒馬克的論點而已,而不是提出新的理論。
筆者認為,這樣的分析架構,對於熟悉西方經濟學遠甚於佛法的現代人而言,會是瞭解佛教經濟學更好的切入點。事實上,讀者當可發現,本書有待釐清或待探究的問題,比本書所能提供的解答多更多。舉例而言,佛陀在世時的經濟社會結構與現代當然有所不同,因此像是佛教經濟學觀點下的廠商理論,就會是具有挑戰性的課題。同樣地,儘管舒馬克認為中級(intermediate)或適切(appropriate)科技才符合佛教經濟學的「小即是美」的基本觀點,但就現實而言,科技的進步卻似乎仰賴某種程度的規模經濟。何者才是符合佛陀的教理呢?如何能在符合佛法下,發展出以人為本的科技會是一個重要的課題。誠如舒馬克所說的,這不僅需要「知道如何」(know-how;另譯「科技」),更需要仰賴由智慧而來的創意(或許可稱之為「知道為何」[know-why])。
其實以其它靈性傳承為基礎的經濟學也都面臨類似上述佛教經濟學所面臨的挑戰。例如,伊斯蘭教明文規定禁止借貸的利息(riba; usury),但這樣的規定在面對以資本主義經濟為主的全球經濟就會有很大的衝突與矛盾。伊斯蘭國家因而發展出所謂的伊斯蘭經濟學。即使如此,伊斯蘭國家中利息的存在仍是無法迴避的事實。舉例來說,以伊斯蘭教為國教的孟加拉而言,一般民眾不是面臨極高的貸款利率,就是因貧窮而貸款無門。尤努斯(Muhammad Yunus, 1940–;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所提倡的葛拉敏銀行(鄉村銀行)就是因為結合該國的民情,以能提供窮人較合理利率而聞名於世。即使如此,其年利率仍遠高於10%,而非伊斯蘭律法(Shariah)中所規定的零利率。以2004年而言,葛拉敏銀行微型信貸的利率高達20%,而官方的貸款利率則約14%;與此同時的美國長期利率不及5%,台灣則低於4%。
最後,截至目前為止,佛教經濟學研究所探討的大多屬於個體經濟學的範疇,然而有待探究的課題還有很多很多。例如,佛教金融學(Buddhist nance),也就是符合佛法的財務金融理論,會與傳統的金融理論(比方說對風險與報酬的看法)有何不同呢?進一步,佛教總體經濟學的議題與面貌應是怎樣的呢?這同樣有待更多的研究。
「經濟學不是一項精確的科學。事實上它是——或者應該是——更大的:它是智慧的一項分支。」
——舒馬克(1973)
佛教經濟學(Buddhist Economics)探討的是佛教觀點下經濟學應有的面貌。許多人聽到佛教經濟學的第一個反應是:有這種東西嗎?甚至就直接將它貼上「矛盾修飾語」(oxymoron)的標籤。人們如此反應的主要原因有二。首先,提起佛教,一般人腦中浮起的第一印象是出家僧侶——似乎是出世而摒棄物質的,而「正統」經濟學談的正是以滿足物質欲望為主的經濟活動之研究;二者似乎是南轅北轍的概念,因此怎麼可能扯上關係?然而這樣的看法並不正確,因為在一些經典中(如《轉輪聖王師子吼經》),佛陀曾提及在家居士的家庭之樂,更指出貧窮是一切非義與罪行之源(Rahula, 1959)。此外,從根本定義來說,佛教是「諸惡莫作,諸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見《法句經》)。可見如其他宗教一樣,佛教並未摒棄世間之物質生活。只是相對於外顯的行為(像是避惡行善),佛教更重視內在心念、意念的淨化,因此容易讓人們有所誤解。
第二個理由則是基於一個對佛教思想比較深層的了解:我們所在的這個娑婆世界是有成住壞空的非永恆世界;看似真實,實則為幻象(印度教與佛教經典中稱之為「摩耶」[maya])。眾生因無明而於其中生死輪迴不已,因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任務或意義,是如何自三界之苦中解脫,而不是去在意物質生活。然而如果對佛教思想有更深一層的暸解,會體悟到一切唯心所造:我們認知到的一切外境,皆反映(相應著)我們的內在。因此,如何如實地面對物質生活,而不是單從頭腦、想法上去否定物質層面的存在,才是真正的「理性」,而所謂的解脫,是真切地認識生命的本質,而不是逃避生命的實相。換句話說,問題的重點並不在於物質生活的本身,而是我們面對它的態度。佛陀告誡我們的,不是外在的摒棄物質,而是內在的不執著,也就是所謂的「出離」(renunciation)。
佛教經濟學是由恩斯特.費德里希(費瑞茲).舒馬克(Ernst Friedrich [Fritz] Schumacher)在1960年代所提出的。他在〈佛教經濟學〉一文開宗明義即說:「『正命』(right livelihood)是佛陀所倡導的八正道之一,因此很清楚地,是必然有佛教經濟學這種東西的。」在此,「命」係指賴以活命的生計,所以「正命」是指從事正當的職業,尤其是指不會傷害眾生(包括自己)的職業。
從傳統經濟學的角度來看,職業既提供個人生活所需之金錢,同時也是廠商生產的要素之一——也就是勞力(labor),正是經濟循環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只是在傳統經濟學裡,關注的重點在於商品與勞務的消費,而工作與勞力只是不可避免的必要手段而已。對於佛教徒而言,作為八正道之一的「正命」同樣是一種手段,但其目標或意義卻遠遠超過個人物質欲望滿足之追求。佛教的思想裡並未迴避物質之經濟活動,事實上反而是有一套一致的倫理準則規範。只是佛教經濟學與傳統經濟學在諸多基本假設上有根本上的不同,因此所推展而出的經濟面貌也就有徹底的差異。
舉例而言,傳統經濟學係在資源有限的限制下,以滿足自身之欲望(尤其是物質欲望)為目標。相對地,佛教徒認為欲望出於無明,所以應從根本——也就是去除無明——著手。不論是傳統經濟學或是佛教經濟學,都體悟到欲望是無底洞,無法填滿。但令人訝異地,前者所推演出的結論,竟然是在有限的物質生命下,「應該」盡量消費以滿足最大可能的欲望! 相對地,佛教經濟學則區分「需要」(need)與「想要」(want):前者是維持肉身之必要條件,而後者則是根源於無明之欲望,既非維持生命之必要,對於圓滿生命的追求也毫無助益。就物質層面而言,人們要滿足的是需要,而非想要:消費是「夠」了就好;唯有在物質消費上有所節制,我們才能在這有限的物質生命形式下,有心力往圓滿生命之道路邁進。
基於佛教這樣的理念,舒馬克給佛教經濟學如下的定義:
「商品的擁有與消費只是達成『目的』的『手段』,而佛教經濟學則是探討如何以最少『手段』來達成特定『目的』的系統性研究。」
舒馬克所說的「目的」,就是「解脫」(liberation;梵文拼音為moksha)。他說:「物質主義(materialism;唯物論)者主要關心的是財貨,而佛教徒主要關注的則是解脫。」從佛法的角度看,要達到解脫,消費可以是手段之一,而工作亦然。然而重點既不在於消費水準的高低,也不在於工作報償的多寡,而是在於人們從事消費與工作時的態度。他因此說:「對佛教徒而言,文明的本質在於品格(character)之淨化,而非欲望(wants)之加乘。」這樣的看法,與1950年代馬斯洛所提出的「需求層級」理論以及1990年代興起的正向心理學的看法不謀而合。我們在稍後的章節中會進一步說明。
某種意義上,「解脫」並不是一種可以達成的目標(something to obtain),而是對生命本質的全然了解,只能「證」得(to be attained),因此也就與生活密不可分——既在行住坐臥之間,也在分分秒秒之間。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我們「修行」的場域:以覺知的心態(mindful mindset)從事一切內在與外在的活動;當然也包括經濟活動在內。所謂的修行,簡單地說,就是修正行為;更深一點看,則包含「修」與「行」:「修」是內在的修正、調整,「行」是實行,也就是表現於外的行動。
正因如此,舒馬克甚至認為種種一切(包括消費、工作等所有經濟行為),自身即為目的(ends-themselves)。相對地,在資本主義經濟的眼中,消費是生命的目的,而工作則是手段。無怪乎舒馬克批評道:「在佛教徒的眼中,把物看得比人重要,把消費看得比創意活動來得重要,根本就是是非顛倒、本末倒置。這意味著⋯⋯屈服於邪惡的力量。」
舒馬克在文中很巧妙地避開佛教各個宗派對何謂「解脫」的不同主張,因此也避免了許多不必要的爭論。儘管如此,後續學者(有些是經濟學家,有些是佛教僧侶)在對佛教經濟學做更深入探討時,就開始在一些概念或看法上有所分歧。例如,傳統經濟學認為競爭是經濟的主要動力,但佛教經濟學則認為合作遠比競爭來得重要;如果對佛法瞭解深刻一點的話,會發現競爭根本就是違反佛法的精神。不過仍有些學者認為競爭可以是「好」的,只要其利益是大家共同分享的。甚至有學者認為佛教經濟學只是一種指引個體或企業方向的「策略」(如Zsolnai [2009]),不足以成為一套有系統的學門。這些分歧都是因為對佛教思想的理解不同所致。本書的目的之一,就是從佛教的根本思想,去重新架構經濟學,並探討佛教觀點下,諸如競爭、工作、消費、市場等等基本概念的內涵。
舒馬克的〈佛教經濟學〉一文雖然僅有短短的十幾頁,但已經清楚地點出了佛教經濟學的要旨。然而在舒馬克提出佛教經濟學後,似乎並未受到立即的關注,而是直到他將該文收編於1973年出版的《小即是美》(Small is Beautiful)一書中(收編為該書第四章),才受到較為廣泛的注意。有趣的是,當代心理學行為學派大師史欽納(Burrhus Frederic Skinner, 1904–1990)就受到該書的啟發,而將舒馬克的理念,結合行為學派的觀點,寫了一本他心目中的烏托邦式的生態村小說《桃源二村》(Walden Two, 1974)。
事實上,如果仔細研讀,可發現整本《小即是美》談的就是舒馬克眼中的佛教經濟學。例如,該書中第二部分談的是「資源」,依序探討教育(值得注意的是,他探討的不是作為生產要素的「勞力」;他認為教育才是人類最偉大的資源)、土地(他認為是最偉大的物質資源)、工業用資源、核能,以及技術(而且是「具有人類面貌的技術」(technology with a human face));該書第四部分則提出新的組織與所有權理論,其實就是提出符合佛教經濟學精神的廠商理論。
不過佛教經濟學始終未能成為經濟學的主流,僅悄悄地在不丹與泰國萌芽。以藏傳佛教為國教的不丹,早在1970年代就倡議以追求符合佛教的幸福快樂為其國家之目標,但並未引起太多的關注。不丹自1970年代起提倡國民幸福指數(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GNH),諸多措施,例如保護山林等,都頗符合佛教經濟學的概念。儘管曾被認為是世界最幸福的國家,然而近年來隨著民主的推行與開放,人們開始被外界五光十色的種種物質享受所迷炫,該國的幸福程度也逐漸下滑。
在泰國,似乎直到佛教僧侶暨學者佩尤托(Prayudh Payutto, 1938–)於1992年出版了《佛教經濟學:市場的中庸之道》一書,佛教經濟學才受到廣泛的注意。今日泰國有兩種實踐佛教經濟的模式:其一是在1970年代興起的「善地阿索」佛教改革運動(Santi Asoke Buddhist Reform Movement),主要以合作社或公社(collective or cooperative communities)的形式實踐佛教理念。另一是由泰皇蒲美蓬在1997年為因應經濟危機所提出的「泰國皇家自足經濟模型」(Royal Thai Sufficiency Economy Model)(參見Essen, 2010)。近年來許多社會企業或生態村、生態社區等組織,雖未盡然標榜佛教,但也都有佛教經濟學的精神內涵。我們在第7章會有進一步的介紹。
至於為什麼是佛教經濟學,而不是以其他宗教為基礎的經濟學呢?舒馬克在〈經濟學的角色〉(《小即是美》一書第三章)一文中指出,經濟學是一門「衍生」的科學,接受他稱之為「後設經濟學」(meta-economics)的指引。他所說的後設經濟學,指的是經濟學的基本信念(假設)。他說:「不論所教導的主題是科技或人文,如果這個教導不能引導釐清形而上學,也就是我們的基本信念,那麼它就無法教育人,因而也就不能對社會有任何實質的價值。」(參考舒馬克 [1973]〈教育:最偉大的資源〉一章。)
釐清基本信念是重要的。著名的生態經濟學家赫曼.戴利(Herman Daly, 1938–)在《邁向定態經濟》(Toward a steady-state economy; 1973)一書中,提出一個如今人們稱之為「戴利三角形」(Daly Triangle)或「戴利金字塔」(Daly Pyramid)的永續架構。從三角形的頂端往下,依序是終極目的(ultimate end)、中階目的(intermediate end)、中階手段(intermediate means),與終極手段(ultimate means)。根據戴利,人們追求的終極目標是福祉,這個福祉可以是簡單的快樂、和諧、自尊,進而到自我實現與開悟。中階目的主要是建立在整體人類與社會資本的發展,這些資本包括健康、財富、安全、知識、溝通等。要達成終極目標,需要以中階目的作為支撐,而連結二者的,是哲學(倫理)、道德,或神學,也就是系統性的核心或基本信念。
順著三角形再往下,中階目的的達成有賴中階手段的實現;中階手段主要是實質的經濟,其中包括建成資本(built capital)與人力資本。串連中階目的與中階手段的,是政治經濟制度——藉由合適的政治經濟制度才能把物質之經濟轉為人類與社會資本,進而導向終極目標。然而中階手段仍需仰賴終究的手段,也就是地球上有限的自然資本,才能達成,而連結著二者的,就是科學與技術。根據戴利三角形,科技、政治經濟制度,與系統性的信念(哲學或宗教信仰),這三者對於人類社會的永續發展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這裡所說的系統性信念,就相當於舒馬克所說的後設經濟學。
後設經濟學應具備怎樣的面貌呢?舒馬克說:「因為經濟學處理面對的是環境中的人,所以我們可以預期後設經濟學包含兩部分:一是處理人,另一則是處理環境。⋯⋯換句話說,我們期待經濟學的目的與目標,應推演自對人的研究;而至少很大程度它的方法論必須衍生自對大自然的研究。」近年來頗受重視的綠色經濟學,就是希望能發展出兼顧人類福祉與永續的替代方案(參見Cato, 2010)。綠色經濟學有二要件:一是以人為本,另一則是永續發展(周賓凰,2020),而正如舒馬克所言,前者有賴於「對人的研究」,後者有賴於「對大自然的研究」。只要再進一步探究,可知由於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因此我們對大自然的看法與態度所反映的也是我們的基本信念。換言之,真正的「以人為本」必然導向永續發展。
然而以物質主義為後設基礎的傳統經濟學既狹隘地把人變成消費與生產機器,其所推演出的線性經濟模式(從資源開採、生產、消費,到廢棄物丟棄)也與大自然的循環返覆體系大相逕庭。相對之下,佛教經濟學把人放在首要位置。佛教思想對於人,從靈性、心理,乃至物質層次,都有很完整嚴謹的說法。我們與大自然,包括所有的人類與其他生物,都是相互連結(interconnected)、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t)的(參考,如Brown(2017));星雲法師稱之為「同體共生」,因此佛教觀點下的經濟體系必然是一個循環的體系,而不是一個追求物質成長的體系。
舒馬克批評說,大多數經濟學家至今仍在追求一種荒謬的理念:希望把他們的「科學」變得如物理學般精確(這種傾向稱為「物理欽羨」[physics envy]),「彷彿那沒有意識的原子與依上帝形象所造的人之間,沒有根本上的質性差異。」他們追求所謂的「價值中立」(value neutral),結果他們所刻畫的世界只有價格,而沒有價值。相對之下,佛教經濟學把價值放在首位,因為價值反映的就是人們的基本信念。佛教經濟學者佐爾奈(Zsolnai, 2009)根據王爾德(Oscar Wilde)的名言而語帶諷刺地說:「經濟學家知道每樣東西的價格,卻對每樣東西的價值一無所知。」(Economists know the price of everything and the value of nothing.)
資本主義經濟學與佛教經濟學最根本的差異,在於前者的後設基礎是唯物的,而後者則是唯心的。舒馬克說得很好:「⋯⋯以物質追求為主要目標而忽視靈性的生命是空虛而不滿足的。這樣的生命必然導致人與人的對立、國與國的對立,因為人的需求是無止盡的,而這種無止盡唯有在靈性層面才能達成,而不在物質層面。」(見舒馬克 [1973] 第二章)另一位著名的異端經濟學家肯尼士.博丁(Kenneth Boulding, 1910–1993)也諷刺說:「如果有人相信在一個有限物質的星球上,存在一種物質可以有無止盡的成長,那麼這個人不是瘋子,就是經濟學家。」
舒馬克在書中對當代經濟學有許多嚴厲的批評,因為這種追求物質擴張與成長的經濟思維所帶來的,是人與自己、社會,乃至與大自然的疏離(alienation;或譯「異化」);疏離感滋養了孤獨與絕望,並終將導致災難。他在書中也引用了甘地的名言:「地球所提供的,足以滿足每個人的需要,但不是每個人的貪婪。」的確,他早在1960至1970年代所點出的諸多資本主義經濟的問題,在過去這三十多年來也一一浮現。無怪乎有學者認為,如果凱因斯是自亞當.斯密(Adam Smith)以來最偉大的正統經濟學家,那麼舒馬克無疑地就是當代最重要的「異端」經濟學家。在他於1977年瘁逝時,各界紛紛悼念,稱他為經濟學的先知。他所倡導的佛教經濟學,才是真正「以人為本」的經濟學。
然而佛教並不是後設經濟學的唯一選擇。舒馬克在〈經濟學的角色〉一文中說:「選擇佛教作為後設基礎是純然非刻意的;基督教、伊斯蘭教,或者猶太教的教理也都適用,正如其他偉大的東方傳承亦然。」事實上,他本人直到在1971年(時年60歲),在歷經了大半輩子的靈性追尋後,才正式成為天主教徒。的確,舒馬克只列了簡樸與非暴力兩項作為佛教經濟學的指導方針,而付之實踐則有賴佛教的另一原則:「中道」(the middle way; moderation)。可見他的目的僅在把以「物」為本的傳統經濟學,導回真正經濟學「以人為本」的應有面貌;這樣顯然才契合經濟學應有的「經世濟民」之意涵。
有鑑於我們這個世代所面臨的各種經濟、社會,與環境的危機,尋求新的可永續(sustainable)經濟學以取代資本主義經濟已變得刻不容緩。然而光是擁有科學或科技並不足以帶來「和平與永續」(peace and permanence;《小即是美》第二章的標題),因為「科學無法產生我們可據以維生的想法。」舒馬克批評他多數的經濟學同行們光是在鐵達尼號的甲板上重新安排著海灘椅的位子,而完全無視於橫在眼前的巨大冰山。可悲的是,這樣的情況在過去這數十年不但毫無改變,反而是變本加厲。
舒馬克認為,科學與科技必須有智慧作為依歸,「永續的經濟學」(economics of permanence)才是有可能的;這樣的觀點與戴利三角形的觀點完全契合。今日看來,佛教經濟學(或者說是以靈性為基礎的經濟學)正是最好的解方,而這對於以佛教為主要信仰的華人社會,更是適合。然而回顧佛教經濟學的發展,迄今仍未有較為完整的論述。如我們前面所提到的,舒馬克的論文較為精簡,因此並未能完整地涵蓋所有議題。也正因為這樣,學者在一些議題上不免有些歧見。
宗教所反映的,是人們的基本信念,然而即使是同一宗教的信仰者,彼此的理解也不盡然相同。同樣地,佛教徒也因生命層次領悟上的差異,而對經濟活動有不同的態度與看法。例如,佛教雖說修行有八萬四千法門,但大體上可以分為三類:人天道、解脫道,與菩薩道。修人天道者,仍在累積解脫三界的「資糧」(資本);走解脫道者則致力於個人超越三界之解脫,世間之福報對其而言,反而是一種束縛。至於行菩薩道者則更體悟到眾生與我為一,因此其努力的是所有眾生的解脫,而非僅局限於狹隘個人的「福祉」。因著這三種修行法門的差異,不同佛教徒對有成有壞的物質經濟的看法或態度也會有所差異。
基於上述之根本差異,本書以傳統個體經濟學的架構,依序從佛法的觀點,探討個體行為的基本假設、消費理論、廠商理論,與市場理論等議題。值得強調的是,佛教經濟學基本上是整體論的(holistic),因為任何的經濟決策與行動,都會影響到整個體系,包括環境與社會層面,而不只是局部經濟面的影響。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經濟學教授克萊爾.布朗(Claire Brown)在她的《佛教經濟學》(2017)一書中強調,根據佛法,我們——一切眾生——是相互連結、相互依存的。這樣的看法,與近年來興起的綠色經濟學的理念頗為契合。
佛法是博大精深的,從而衍生而出的佛教經濟學必然也是如此。有鑑於佛教經典的艱澀難解,當代有許多佛教大師致力於佛教的現代化,希望能夠把世界轉化為人間淨土,包括像是「人間佛教」(humanistic Buddhism;由太虛大師、印順法師、星雲法師、聖嚴法師、證嚴法師等所提倡)、「入世佛教」(engaged Buddhism;由一行禪師所提倡)等,其中也都有許多與經濟有關的論述。
本書的目的,僅是就筆者有限的瞭解,大膽地嘗試為佛教經濟學理出一個架構。與現有佛教經濟學文獻最大的不同是,本書主要以當代個體經濟學的分析架構為基礎,再依佛法的視角去推演經濟學應有的面貌。如此作法的好處是我們很容易可以比較佛教經濟學與傳統經濟學在各個面向的差異。讀者不難發現,本書的多數觀點都是來自舒馬克的《小即是美》;某種意義上,我們只是以經濟學的分析架構,重新組合、詮釋舒馬克的論點而已,而不是提出新的理論。
筆者認為,這樣的分析架構,對於熟悉西方經濟學遠甚於佛法的現代人而言,會是瞭解佛教經濟學更好的切入點。事實上,讀者當可發現,本書有待釐清或待探究的問題,比本書所能提供的解答多更多。舉例而言,佛陀在世時的經濟社會結構與現代當然有所不同,因此像是佛教經濟學觀點下的廠商理論,就會是具有挑戰性的課題。同樣地,儘管舒馬克認為中級(intermediate)或適切(appropriate)科技才符合佛教經濟學的「小即是美」的基本觀點,但就現實而言,科技的進步卻似乎仰賴某種程度的規模經濟。何者才是符合佛陀的教理呢?如何能在符合佛法下,發展出以人為本的科技會是一個重要的課題。誠如舒馬克所說的,這不僅需要「知道如何」(know-how;另譯「科技」),更需要仰賴由智慧而來的創意(或許可稱之為「知道為何」[know-why])。
其實以其它靈性傳承為基礎的經濟學也都面臨類似上述佛教經濟學所面臨的挑戰。例如,伊斯蘭教明文規定禁止借貸的利息(riba; usury),但這樣的規定在面對以資本主義經濟為主的全球經濟就會有很大的衝突與矛盾。伊斯蘭國家因而發展出所謂的伊斯蘭經濟學。即使如此,伊斯蘭國家中利息的存在仍是無法迴避的事實。舉例來說,以伊斯蘭教為國教的孟加拉而言,一般民眾不是面臨極高的貸款利率,就是因貧窮而貸款無門。尤努斯(Muhammad Yunus, 1940–;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所提倡的葛拉敏銀行(鄉村銀行)就是因為結合該國的民情,以能提供窮人較合理利率而聞名於世。即使如此,其年利率仍遠高於10%,而非伊斯蘭律法(Shariah)中所規定的零利率。以2004年而言,葛拉敏銀行微型信貸的利率高達20%,而官方的貸款利率則約14%;與此同時的美國長期利率不及5%,台灣則低於4%。
最後,截至目前為止,佛教經濟學研究所探討的大多屬於個體經濟學的範疇,然而有待探究的課題還有很多很多。例如,佛教金融學(Buddhist nance),也就是符合佛法的財務金融理論,會與傳統的金融理論(比方說對風險與報酬的看法)有何不同呢?進一步,佛教總體經濟學的議題與面貌應是怎樣的呢?這同樣有待更多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