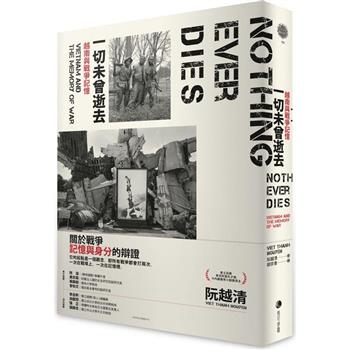序言
我在越南出生,但是在美國製造。我自視為對美國的行為失望,但仍不禁想相信其話語的越南人。我也自視為往往不知如何看待越南,但是想知道該如何看待越南的美國人。美國人和世界許多人往往誤把越南和或褒或貶地以其命名的戰爭混為一談。我擁有兩個國家、繼承了兩場革命,身為這樣的人究竟意味什麼,我無法確知,而這無疑有部分源自於越南和越戰間的混淆。
我花了大半輩子想從我自己和世界的這種混淆中理出頭緒,而我所找到對越戰的意義最簡潔的說明,最少對美國人而言,來自小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如果美國的靈魂完全中毒,」他說,「驗屍報告中一定少不了『越南』。」 美國人認識金恩多數是因為他的夢想,但這是他的預言,而接下來是這麼說的:「越南的戰爭,只是美國精神中更深層疾病的徵狀。如果我們忽視這令人警醒的現實,那到了下一代,我們將還在組織『關懷某某的神職人員與平信徒』委員會*。這些委員會關心的將是瓜地馬拉與祕魯,泰國和柬埔寨,莫三比克和南非。除非美國生活發生重大而深遠的改變,我們將無止盡地為這些與其他十數個地方遊行示威、參與集會。」 說這些話的整整一年後,金恩遭暗殺。
他並未提到伊拉克與阿富汗,但是從他那次演說以來,許多美國人都曾論及這些地方的衝突與越戰之間的關係。 即使越南不是伊拉克也不是阿富汗,對美國人而言,這個類比仍揮之不去。舉出越南來代表困局、病徵與戰爭,反映的既不是越南的現實,也不是當下在伊拉克與阿富汗的困難。它反映的是美國人的恐懼。美國人認為最糟糕的事莫過於輸掉這些戰爭,而即使今天在伊拉克與阿富汗打贏了,也只代表明天同樣的事情再來一次:索馬利亞、巴基斯坦、葉門⋯⋯。這是美國人記得他們口中的越戰最重要的原因:那是在它之前與之後一長串慘烈戰爭中的一場衝突。這場戰爭的身份——事實上,任何一場戰爭的身份——都無法從戰爭本身的身份抽離出來。
對金恩而言,「種族主義、經濟剝削與戰爭問題,全都相互連結。」 他的預言並不總是流暢優美,使用的語言僅偶爾指涉聖經,而且從不鼓舞人心。他不要求我們仰望山頂,而是要俯視平原、工廠、田野、貧民區、領失業救濟的人龍、徵兵委員會、稻田、池中綻放的蓮花、連美國士兵都說美麗的越南地貌,還有越南人稱之為美麗國家的美國。戰爭的記憶屬於這些地方。最惱人的記憶是,那場戰爭不僅在那裡發生,也在這裡發生,因為一場戰爭牽涉的不只是發射子彈,還牽涉到製造子彈、運送子彈,和或許是最重要的,付錢買子彈的人,他們是心不在焉的國民,是金恩稱為白人與黑人同胞「殘酷團結」(brutal solidarity)的合夥同謀。
雖然金恩說的是美國,但他指的大可以是越南,這兩國都是革命國家,也都沒有實現革命的追求。美國曾經有如山上的城*,如今,那個美國幾乎只存在於多情的幻想中,連戰時的越南似乎也很遙遠了。那個國家曾讓革命家切·格瓦拉(Che Guevara)說出這樣的話:「如果地表綻放出兩個、三個、很多個越南,未來將顯得多麼接近、多麼光明。」 他說的是越南反抗美國占領的戰爭在美洲、非洲和亞洲夢想解放與獨立的人之中所激起的希望。今天,誕生於革命的越南和美國製造記憶,只是要為其僵化的血脈免除罪責。對於如我這樣自視繼承了那一場或兩場革命的人,或是曾受它們某種影響的人而言,我們必須知道如何製造記憶和遺忘記憶,才能以重擊幫助這兩個革命國家恢復心跳。這正是本書要做、或希望能做到的事。
公正的記憶
這是關於戰爭、記憶和身分的一本書。它的起點是一個觀念,即所有戰爭都會打兩次,一次在戰場上,一次在記憶裡。任何一場戰爭都能佐證這個說法,但是對我個人而言,最能用以借代戰爭與記憶問題的是,有些人稱為越南戰爭、有些人稱為美國戰爭的那場衝突。這兩個不同的名稱,指向這場戰爭的身分危機,源自它該如何為人所知道和記憶的問題。戰爭與記憶的並置,在二十世紀的災難後至為常見,數千萬人似乎呼求著要被紀念、被供奉,甚至,若你相信鬼魂,要被安慰。1戰爭與記憶的問題,因而首先是關於如何記得無法為自己發言的死者。他們的沉默令人不安,驅使生者──或許沾染著不只一點倖存者的罪惡感──為他們發言。
與這段悲戚的歷史不可分割的,還有更複雜的問題。我們如何記得生者,以及他們在戰時的所作所為?我們如何記得死者,理論上為之付出生命的國家和人民?我們又如何記憶戰爭本身,不論是普遍而言的戰爭,或是形塑了我們的某一場戰爭。這些問題也指出,直到一個國家面對了過去的戰爭,不論有多少缺陷或遺漏,都不可能打新的戰爭。如何記憶戰爭的問題,是國家身分的中心要素,而國家本身幾乎總是建立在暴力征服領土與降伏人民之上。2對公民而言,這段血染的過往,籠罩在委婉說詞的花環和輝煌神話的迷霧下。塑造了國家的戰役,在國民的記憶中往往是為了捍衛國家,通常以服務和平、正義、自由或其他崇高想法為名。經此文飾後,過往的戰爭為現在的戰爭提供了正當性,讓國民願意參與戰鬥,或至少是繳納稅金、揮舞國旗、投下選票,並滿足所有確認其身分與國家一體的義務和儀式。
還有另一個身分牽涉在內,那就是戰爭的身分,小說家包柏.夏科奇斯(Bob Shacochis)稱之為「國家靈魂的起源」。3每場戰爭都有獨特的身分,一張細細描繪了特徵的面容,國民一望即知。任何一場戰爭若被記起,往往是以一、兩個細節為人記得。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戰對許多美國人而言是「良善之戰」(Good War),而在越南的悲劇是一場惡之戰、一個病徵、一場泥沼、一次痛苦的挫敗,需要療癒與復原。我們傾向如記憶個人般記憶戰爭,視之為各自分離而特色鮮明。戰爭成為各自獨立的事件,有明確的時空界線,由開戰與停戰宣告,以及史書、新聞報導與紀念牌上的日期所劃分。然而,所有戰爭都開端不清、終局也不明確,往往接續了前一場戰爭並預示後來的戰爭。這些戰爭往往不只發生在它們因以得名的土地上,也外溢到鄰近國家;形塑它們的則是遠離戰場的戰情室與會議間。戰爭與個人一樣複雜,但是卻以它們的名字為人所記憶,而這些名字就和人名一樣,透露得很少。菲律賓—美國戰爭之名,暗指兩國強弱對稱,然而是美國人占領了菲律賓,引發血洗屠殺。韓國戰爭暗指這是韓國人之間的衝突,但中國與美國也都參與了戰鬥。以越南戰爭而言,是美國人發明了這個名字,將兩個名詞彆扭地銬在一起,透過不斷重複而讓人習以為常。事實上,習以為常到了即使把名稱縮短為越南(經常如此),許多人還是會將之理解為那場戰爭。很多人因而抗議,越南是一個國家,不是一場戰爭。但是早在這樣的呼籲以前,有些越南人(後來贏了戰爭的那一方)已經開始稱那場戰爭為美國戰爭。4儘管如此,如果越南戰爭之名並不理想,因為它誤導了我們對那場戰爭身分的理解,美國戰爭之名會比較好嗎?
這個名字免除了各方越南人也要為這場戰爭負的各種責任,不管是其中的勝利、災難、榮耀,還是罪行。更重要的是,這個名字鼓勵越南人自視為外國侵略的受害者。身為受害者,他們正好患上失憶症,不記得他們對彼此的行徑,和他們如何將戰爭往西擴張到了柬埔寨與寮國,而在戰後,統一的越南又致力於影響、支配、甚至入侵這些國家。5美國戰爭之名,與越南戰爭之名同樣意義模糊。後者如今代表美國的挫敗與恥辱,但是裡面也有美國勝利與否認的成分,因為它限制了戰爭的時空規模。論及空間,兩個名字都抹除了參與這場戰爭的不僅是越南人或美國人的事實。論及時間,有其他美國戰爭在它之前(在菲律賓、太平洋群島和韓國),與它同時(在柬埔寨、寮國與多明尼加共和國),和在它之後(在格瑞納達、巴拿馬、科威特、伊拉克與阿富汗)。這些戰爭是美國在一世紀期間,為了在太平洋、亞洲,乃至後來的中東,即廣義上的東方(Orient)建立支配權的部分行為。6這個世紀的首尾由兩個重大年份所涵括。一八九八年,美國奪下古巴、菲律賓、波多黎各和夏威夷,啟動了美國利益的海外擴張,直到在二○○一年遭到意料之外的反抗,即九一一事件與後續在中東的衝突。真正的美國戰爭是這一整個美國世紀(American Century),這段擴張時期漫長而不平均,標誌著它的是少數週期性的高強度衝突,許多低強度戰鬥,和永遠準備中的戰爭機器持續的隆隆聲。結果是,「在美國,戰爭時期已經成為普通時期。」7
因此,為了該以越南戰爭或美國戰爭為名而爭論,是針對假選項的爭論。兩個名字都各自掩蓋了人命損失、財務代價、資本利得及戰火也延燒到柬埔寨與寮國的事實,這是越南人與美國人都不願承認或記得的。北越透過柬埔寨與寮國運送軍隊和物資,美國為此發動轟炸,兩國也都掀起內戰,在寮國造成約四十萬人死亡,在柬埔寨則在記者威廉.蕭克勞斯(William Shawcross)諷刺地稱為戰爭的「餘興節目」(sideshow)中造成七十萬人死亡。倘若我們將遭到轟炸破壞、政治不穩的柬埔寨,在一九七五至一九七九年間赤柬政權下發生的事,算成戰爭的附筆,那麼死亡人數還要再加上兩百萬人,或說柬埔寨近三分之一人口,雖然有些估計數字指出死者僅有一百七十萬人,即大約四分之一的人口。越南交戰各方的死亡人數接近人口的十分之一,美方的死者則為美國人口約百分之○.○三五。8
*
數算一場戰爭的成本與後果時,附筆和餘興節目都該計算在內,而這兩者不論在越南戰爭或美國戰爭之名中都遭到抹除。這兩個名字將損害限制在一九六五至一九七五年間的越南,以及大約三百萬人的死亡。若將柬埔寨與寮國的餘興節目計入,這個數字上升到四百萬左右,若加上附筆,總數則約為六百萬。拒絕接受這場戰爭既有的命名,就是承認這場戰爭正如多數戰爭一樣混亂,無法輕易或整齊的由日期與國界所限縮。不給它一個名字,如我在書中有時只稱之為那場戰爭(the war),能清理出一個以不同方式重新想像與記憶這場戰爭的空間。不給它一個名字,也就是承認每個活過戰爭的人都知道的事:他們的戰爭不需要名字,因為永遠都只會是那一場戰爭。作家娜塔麗亞.金茲伯格(Natalia Ginzburg)提到另一場戰爭──她的那一場戰爭時,曾說:「我們永遠不能在這場戰爭後獲得療癒。沒有用的。我們這個民族再也不會感覺安心,再也不會於平靜中思考、計畫,並安排我們的生活。看看我們的家園承受了什麼。看看我們承受了什麼。我們將永不得安心。」9
這場戰爭──不諱言,是我的戰爭──甚至不只在兩個名字所指稱的美國和越南間上演。事實上,這兩個國家是分裂的,美國分為支持和反對戰爭的派系,而越南分為南方與北方,以及共產主義和反共產主義的兩方,但這些意識型態立場並非清楚的依照地理劃分。戰爭也有其他國家的參與者,首當其衝的是柬埔寨和寮國的人民,但也有許多南韓人。我要做的是,看見他們如何記憶自己的戰爭,而他們本身又如何被記憶,但這不是要嘗試全面納入和全面召喚回憶,因為我並未針對其他參與者發聲(澳洲人、紐西蘭人、菲律賓人、泰國人、俄國人、北韓人、中國人……)。10不過,擴大這個敘事以納入越南和美國以外的人民是我的表態,既指向記得之必要,也指向全面記憶之不可得,因為遺忘是必然,而每本書都需要其邊際。儘管如此,盡可能多記得一些是我的反動,因為許多、或許是絕大多數戰爭回憶,或至少在公眾間流通的戰爭回憶,都欠缺包容性。這些公眾記憶所展現的是,多數時候,國家與人民透過我稱為「記憶己方」(remembering one’s own)的倫理運作。這種倫理因國家而異,越南人比美國人更願意記住女性與平民,美國人比越南人更願意記得敵人,而兩方都未展現出記得南越人的任何意願,因為他們散發失敗、憂鬱、苦澀與憤怒的惡味。美國至少讓逃到美國的南越難民有機會講述他們的移民故事,藉此成為美國夢的一份子。11越南政府給他們的只有再教育營、新經濟區和從記憶中被抹除的待遇。既然如此,流亡的南越人多數也堅持不忘他們的自己人,亦不值得奇怪了。
對兩個國家和其多元的組成份子,包括戰敗和流亡的越南人,另一種倫理,即記得他者的倫理,是個例外,不是通則。這種記憶他者的倫理,讓記得自己人的傳統倫理改頭換面。它將誰在自己這一邊的定義加以擴大,以涵括更多他者,消除了接近而親愛之人(the near and dear)和遙遠而讓人畏懼者(far and feared)間的區別。這個倫理光譜的兩端,分別是記憶己方和記憶他者。我從這兩端出發,把這場戰爭中登場人物的回憶編織起來,他們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士兵和平民、多數和少數、贏家與輸家,還有許多無法歸入這些二分法、對立方和類別的人。戰爭牽涉到這麼多人,是因為它與一國多元的本地生活無法分割。將戰爭只想為戰鬥,其主角為士兵,而且在想像中通常為男性,只會阻礙對戰爭身分的理解,讓戰爭機器從中得益。
*
更具包容性的戰爭記憶,也是努力建立社會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稱為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的結果。集體記憶指的是,因為我們已經從所屬社群繼承而來的記憶而得以存在的個體記憶,也就是說,我們透過他人而記得。12批評家詹姆斯.楊格(James Young)以他提出的收集的記憶(collected memories)模型修改這種說法,指出不同群體的記憶可以透過令人安心的美國多元主義而匯集起來。13學者薩克文.伯科維奇(Sacvan Bercovitch)指出,這些群體及其記憶互相間的任何可能歧異,透過「共識的儀式」(ritual of consensus)所馴化,那正是有如神話的美國之道(American Way)。14不論我們談的是集體記憶或收集的記憶,這些模型要可信,都必須將定義它們的群體包含在內,不論那個群體是大是小。因此,戰爭的號召通常伴隨著對公民的要求,要他們只能記得有限的身分認同和對集體的狹隘認定,僅擴及家庭、部落和國族。因此,美國之道的包容性,從定義而言就排除了任何非美國的事物,也正因如此,直到今天,美國對這場戰爭的記憶往往遺忘或模糊了越南人,遑論柬埔寨人和寮國人。反對戰爭的人追求一種更廣泛的人類身分,可包含先前為我們所遺忘的人,希望這樣的開闊性能減少衝突的機會。
想要將更多自己人、甚或更多他者包容在內的渴望,會碰上個人的與政治性的問題,因為個體或集體記憶都無法達到完全包容。全面記憶(total memory)既不可能亦不實際,因為永遠有什麼會被遺忘。儘管我們很努力,還是會遺忘,我們也會因為強大的利益方,往往積極壓抑記憶而遺忘,形成米蘭.昆德拉所稱的「有組織的遺忘之沙漠」(the desert of organized forgetting)。15在這片沙漠中,記憶和水一樣重要,因為在權力的鬥爭中,記憶是重大戰略資源。要打仗,必然要能控制記憶,以及和其本質相反的遺忘(看似某種欠缺,實際上是資源)。國家培養記憶亦培養遺忘,若能夠,還會獨占兩者。他們敦促人民記得自己人、遺忘其他人,如此才能打造對戰爭至關重要的民族主義精神,這個自我中心的邏輯也在不同人種、族群和信仰社群中流通。這種記得自己人並遺忘其他人的主流邏輯極為強勢,連被遺忘的人一旦有機會也會遺忘他人。這場戰爭中輸家的故事顯示,在關於記憶的衝突中,沒有一個人在遺忘之事上是無辜的。
強勢與弱勢者爭奪記憶與遺忘的戰略資源時,鬥爭雖有時狂熱,甚至暴力,但更常是低強度的衝突,在其中,國家與其支持者使用的鬥爭手段,傳統與非傳統皆有。當權者控制政府、軍隊、警察,以及掌握監控機制與反叛亂手段的國家安全機器。這些當權者──政客、少數統治階級、企業與知識菁英──也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多數媒體。他們對學者、大專院校、評論者、智庫與教育機器擁有龐大的說服力量。一般而言,這些當權者牢牢掌握戰爭機器,讓機器運轉的二元碼就是記憶己方的倫理,將世界劃分為我們與他們、善與惡的對立,便於建立同盟、瞄準敵人。另一方面,儀式、遊行、演講、紀念碑、陳腔濫調與「真實戰爭故事」,不斷召喚著公民去記憶國家的英雄與死者,而若公民也能遺忘敵方與他們的死者,這件事就更容易了。
反抗戰爭的人強調另一種記憶他者的倫理。他們認為應該記住敵人與受害者、弱小與被遺忘者、邊緣與少數族群、女性和兒童、環境與動物、遙遠與遭妖魔化的,這些人全都在戰爭中受苦,多數更往往在國家主義式的戰爭記憶中被遺忘。在國家內部與國家之間,為了戰爭的意義和正當化戰爭的理由而起的鬥爭中,抗拒戰爭並記憶他者的人,不是為了一國而鬥爭,而是為了想像。在想像中可以出現新的身分,在國家身分與國家賦予戰爭的身分之外成為不同選擇。然而,儘管記憶他者在某些人看來值得欽佩,這種記憶模式也可能帶有危險或欺騙,因為記憶他者可能只是將對自己人的記憶反轉,像一個鏡面,使他者成為善良而正直,我們成為邪惡而有瑕疵的。記憶己方或記憶他者的這些倫理互相競爭,卻都是簡單的記憶倫理模型。我在這本書中尋找並主張的,是一種複雜的記憶倫理和公正的記憶(just memory),盡力記得自己人也記得他者,同時喚起讀者關注記憶的生命週期和其工業化生產,看記憶如何被打造與遺忘、演化與改變。
*
藝術對於保存公正記憶的倫理工作格外重要。我在本書中收入的文字、攝影、電影、紀念碑和紀念館,都是記憶和見證的形式,有時是針對私密、家庭、易逝而微小的事物,有時是針對歷史、公眾、恆久而劃時代的事物。我轉向這些藝術作品,因為在官方的備忘錄和演講被人遺忘、歷史書無人聞問,而權勢者歸於塵土之後,藝術仍在。藝術是想像的文物,而想像是人類所擁有最能展現不朽之物,像個集體的石板,記錄著人性與非人性的行為和欲望。權勢者畏懼藝術潛藏的恆久特質和它對記憶的影響,因而試圖輕忽、收編或壓抑藝術。他們往往得遂所願,因為雖然藝術僅偶爾帶著明顯的國家主義和宣傳意圖,卻往往隱含這些特質。本書中,我檢視了光譜上各種關於戰爭和記憶的藝術作品,從為權勢者的價值背書到企圖顛覆這類價值的作品皆有。即使知道許多藝術家與權勢者同謀,我依舊樂觀認為,未來的世紀中,這場戰爭或任何戰爭留給人類的記憶,很可能會是與權勢和戰爭對抗的少數傑出藝術作品(外加一、兩部歷史書)。
記憶與遺忘不僅受到藝術的建構,也可能被企圖捕捉並馴化藝術的產業所商品化。已有一整個記憶產業存在,隨時準備對耽於懷舊的消費者販賣記憶,靠歷史牟利。17資本主義可以把任何東西變成商品,包括記憶與失憶。因此,記憶的業餘從業者打造出紀念品與紀念物;懷舊的愛好者穿上古著,重演過往戰役;遊客造訪戰場、歷史遺址和博物館;電視頻道播放紀錄片和娛樂片,畫質清晰但記憶模糊。情感與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是記憶產業的要素,將戰爭和經驗轉變為神聖之物,士兵則變成不容輕蔑的記憶象徵,這可見於美國人對打了所謂良善之戰(Good War)的最偉大一代(Greatest Generation)之執迷崇拜。評論者嘲諷記憶產業,視之為社會記憶氾濫的證據,將記憶轉化為可拋棄和遺忘的產品與體驗,卻忽略了當下的困難與未來的可能性。但這種論點誤以為所謂的記憶產業(memory industry)只是徵狀,反映一個更普遍的現象:記憶的工業化(industrialization of memory)。記憶的工業化與戰爭的工業化平行發展,兩者都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一部分,在其中,記憶的火力與戰爭中實際使用的火力相當,為戰爭的身分進行定義與美化。
我在越南出生,但是在美國製造。我自視為對美國的行為失望,但仍不禁想相信其話語的越南人。我也自視為往往不知如何看待越南,但是想知道該如何看待越南的美國人。美國人和世界許多人往往誤把越南和或褒或貶地以其命名的戰爭混為一談。我擁有兩個國家、繼承了兩場革命,身為這樣的人究竟意味什麼,我無法確知,而這無疑有部分源自於越南和越戰間的混淆。
我花了大半輩子想從我自己和世界的這種混淆中理出頭緒,而我所找到對越戰的意義最簡潔的說明,最少對美國人而言,來自小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如果美國的靈魂完全中毒,」他說,「驗屍報告中一定少不了『越南』。」 美國人認識金恩多數是因為他的夢想,但這是他的預言,而接下來是這麼說的:「越南的戰爭,只是美國精神中更深層疾病的徵狀。如果我們忽視這令人警醒的現實,那到了下一代,我們將還在組織『關懷某某的神職人員與平信徒』委員會*。這些委員會關心的將是瓜地馬拉與祕魯,泰國和柬埔寨,莫三比克和南非。除非美國生活發生重大而深遠的改變,我們將無止盡地為這些與其他十數個地方遊行示威、參與集會。」 說這些話的整整一年後,金恩遭暗殺。
他並未提到伊拉克與阿富汗,但是從他那次演說以來,許多美國人都曾論及這些地方的衝突與越戰之間的關係。 即使越南不是伊拉克也不是阿富汗,對美國人而言,這個類比仍揮之不去。舉出越南來代表困局、病徵與戰爭,反映的既不是越南的現實,也不是當下在伊拉克與阿富汗的困難。它反映的是美國人的恐懼。美國人認為最糟糕的事莫過於輸掉這些戰爭,而即使今天在伊拉克與阿富汗打贏了,也只代表明天同樣的事情再來一次:索馬利亞、巴基斯坦、葉門⋯⋯。這是美國人記得他們口中的越戰最重要的原因:那是在它之前與之後一長串慘烈戰爭中的一場衝突。這場戰爭的身份——事實上,任何一場戰爭的身份——都無法從戰爭本身的身份抽離出來。
對金恩而言,「種族主義、經濟剝削與戰爭問題,全都相互連結。」 他的預言並不總是流暢優美,使用的語言僅偶爾指涉聖經,而且從不鼓舞人心。他不要求我們仰望山頂,而是要俯視平原、工廠、田野、貧民區、領失業救濟的人龍、徵兵委員會、稻田、池中綻放的蓮花、連美國士兵都說美麗的越南地貌,還有越南人稱之為美麗國家的美國。戰爭的記憶屬於這些地方。最惱人的記憶是,那場戰爭不僅在那裡發生,也在這裡發生,因為一場戰爭牽涉的不只是發射子彈,還牽涉到製造子彈、運送子彈,和或許是最重要的,付錢買子彈的人,他們是心不在焉的國民,是金恩稱為白人與黑人同胞「殘酷團結」(brutal solidarity)的合夥同謀。
雖然金恩說的是美國,但他指的大可以是越南,這兩國都是革命國家,也都沒有實現革命的追求。美國曾經有如山上的城*,如今,那個美國幾乎只存在於多情的幻想中,連戰時的越南似乎也很遙遠了。那個國家曾讓革命家切·格瓦拉(Che Guevara)說出這樣的話:「如果地表綻放出兩個、三個、很多個越南,未來將顯得多麼接近、多麼光明。」 他說的是越南反抗美國占領的戰爭在美洲、非洲和亞洲夢想解放與獨立的人之中所激起的希望。今天,誕生於革命的越南和美國製造記憶,只是要為其僵化的血脈免除罪責。對於如我這樣自視繼承了那一場或兩場革命的人,或是曾受它們某種影響的人而言,我們必須知道如何製造記憶和遺忘記憶,才能以重擊幫助這兩個革命國家恢復心跳。這正是本書要做、或希望能做到的事。
公正的記憶
這是關於戰爭、記憶和身分的一本書。它的起點是一個觀念,即所有戰爭都會打兩次,一次在戰場上,一次在記憶裡。任何一場戰爭都能佐證這個說法,但是對我個人而言,最能用以借代戰爭與記憶問題的是,有些人稱為越南戰爭、有些人稱為美國戰爭的那場衝突。這兩個不同的名稱,指向這場戰爭的身分危機,源自它該如何為人所知道和記憶的問題。戰爭與記憶的並置,在二十世紀的災難後至為常見,數千萬人似乎呼求著要被紀念、被供奉,甚至,若你相信鬼魂,要被安慰。1戰爭與記憶的問題,因而首先是關於如何記得無法為自己發言的死者。他們的沉默令人不安,驅使生者──或許沾染著不只一點倖存者的罪惡感──為他們發言。
與這段悲戚的歷史不可分割的,還有更複雜的問題。我們如何記得生者,以及他們在戰時的所作所為?我們如何記得死者,理論上為之付出生命的國家和人民?我們又如何記憶戰爭本身,不論是普遍而言的戰爭,或是形塑了我們的某一場戰爭。這些問題也指出,直到一個國家面對了過去的戰爭,不論有多少缺陷或遺漏,都不可能打新的戰爭。如何記憶戰爭的問題,是國家身分的中心要素,而國家本身幾乎總是建立在暴力征服領土與降伏人民之上。2對公民而言,這段血染的過往,籠罩在委婉說詞的花環和輝煌神話的迷霧下。塑造了國家的戰役,在國民的記憶中往往是為了捍衛國家,通常以服務和平、正義、自由或其他崇高想法為名。經此文飾後,過往的戰爭為現在的戰爭提供了正當性,讓國民願意參與戰鬥,或至少是繳納稅金、揮舞國旗、投下選票,並滿足所有確認其身分與國家一體的義務和儀式。
還有另一個身分牽涉在內,那就是戰爭的身分,小說家包柏.夏科奇斯(Bob Shacochis)稱之為「國家靈魂的起源」。3每場戰爭都有獨特的身分,一張細細描繪了特徵的面容,國民一望即知。任何一場戰爭若被記起,往往是以一、兩個細節為人記得。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戰對許多美國人而言是「良善之戰」(Good War),而在越南的悲劇是一場惡之戰、一個病徵、一場泥沼、一次痛苦的挫敗,需要療癒與復原。我們傾向如記憶個人般記憶戰爭,視之為各自分離而特色鮮明。戰爭成為各自獨立的事件,有明確的時空界線,由開戰與停戰宣告,以及史書、新聞報導與紀念牌上的日期所劃分。然而,所有戰爭都開端不清、終局也不明確,往往接續了前一場戰爭並預示後來的戰爭。這些戰爭往往不只發生在它們因以得名的土地上,也外溢到鄰近國家;形塑它們的則是遠離戰場的戰情室與會議間。戰爭與個人一樣複雜,但是卻以它們的名字為人所記憶,而這些名字就和人名一樣,透露得很少。菲律賓—美國戰爭之名,暗指兩國強弱對稱,然而是美國人占領了菲律賓,引發血洗屠殺。韓國戰爭暗指這是韓國人之間的衝突,但中國與美國也都參與了戰鬥。以越南戰爭而言,是美國人發明了這個名字,將兩個名詞彆扭地銬在一起,透過不斷重複而讓人習以為常。事實上,習以為常到了即使把名稱縮短為越南(經常如此),許多人還是會將之理解為那場戰爭。很多人因而抗議,越南是一個國家,不是一場戰爭。但是早在這樣的呼籲以前,有些越南人(後來贏了戰爭的那一方)已經開始稱那場戰爭為美國戰爭。4儘管如此,如果越南戰爭之名並不理想,因為它誤導了我們對那場戰爭身分的理解,美國戰爭之名會比較好嗎?
這個名字免除了各方越南人也要為這場戰爭負的各種責任,不管是其中的勝利、災難、榮耀,還是罪行。更重要的是,這個名字鼓勵越南人自視為外國侵略的受害者。身為受害者,他們正好患上失憶症,不記得他們對彼此的行徑,和他們如何將戰爭往西擴張到了柬埔寨與寮國,而在戰後,統一的越南又致力於影響、支配、甚至入侵這些國家。5美國戰爭之名,與越南戰爭之名同樣意義模糊。後者如今代表美國的挫敗與恥辱,但是裡面也有美國勝利與否認的成分,因為它限制了戰爭的時空規模。論及空間,兩個名字都抹除了參與這場戰爭的不僅是越南人或美國人的事實。論及時間,有其他美國戰爭在它之前(在菲律賓、太平洋群島和韓國),與它同時(在柬埔寨、寮國與多明尼加共和國),和在它之後(在格瑞納達、巴拿馬、科威特、伊拉克與阿富汗)。這些戰爭是美國在一世紀期間,為了在太平洋、亞洲,乃至後來的中東,即廣義上的東方(Orient)建立支配權的部分行為。6這個世紀的首尾由兩個重大年份所涵括。一八九八年,美國奪下古巴、菲律賓、波多黎各和夏威夷,啟動了美國利益的海外擴張,直到在二○○一年遭到意料之外的反抗,即九一一事件與後續在中東的衝突。真正的美國戰爭是這一整個美國世紀(American Century),這段擴張時期漫長而不平均,標誌著它的是少數週期性的高強度衝突,許多低強度戰鬥,和永遠準備中的戰爭機器持續的隆隆聲。結果是,「在美國,戰爭時期已經成為普通時期。」7
因此,為了該以越南戰爭或美國戰爭為名而爭論,是針對假選項的爭論。兩個名字都各自掩蓋了人命損失、財務代價、資本利得及戰火也延燒到柬埔寨與寮國的事實,這是越南人與美國人都不願承認或記得的。北越透過柬埔寨與寮國運送軍隊和物資,美國為此發動轟炸,兩國也都掀起內戰,在寮國造成約四十萬人死亡,在柬埔寨則在記者威廉.蕭克勞斯(William Shawcross)諷刺地稱為戰爭的「餘興節目」(sideshow)中造成七十萬人死亡。倘若我們將遭到轟炸破壞、政治不穩的柬埔寨,在一九七五至一九七九年間赤柬政權下發生的事,算成戰爭的附筆,那麼死亡人數還要再加上兩百萬人,或說柬埔寨近三分之一人口,雖然有些估計數字指出死者僅有一百七十萬人,即大約四分之一的人口。越南交戰各方的死亡人數接近人口的十分之一,美方的死者則為美國人口約百分之○.○三五。8
*
數算一場戰爭的成本與後果時,附筆和餘興節目都該計算在內,而這兩者不論在越南戰爭或美國戰爭之名中都遭到抹除。這兩個名字將損害限制在一九六五至一九七五年間的越南,以及大約三百萬人的死亡。若將柬埔寨與寮國的餘興節目計入,這個數字上升到四百萬左右,若加上附筆,總數則約為六百萬。拒絕接受這場戰爭既有的命名,就是承認這場戰爭正如多數戰爭一樣混亂,無法輕易或整齊的由日期與國界所限縮。不給它一個名字,如我在書中有時只稱之為那場戰爭(the war),能清理出一個以不同方式重新想像與記憶這場戰爭的空間。不給它一個名字,也就是承認每個活過戰爭的人都知道的事:他們的戰爭不需要名字,因為永遠都只會是那一場戰爭。作家娜塔麗亞.金茲伯格(Natalia Ginzburg)提到另一場戰爭──她的那一場戰爭時,曾說:「我們永遠不能在這場戰爭後獲得療癒。沒有用的。我們這個民族再也不會感覺安心,再也不會於平靜中思考、計畫,並安排我們的生活。看看我們的家園承受了什麼。看看我們承受了什麼。我們將永不得安心。」9
這場戰爭──不諱言,是我的戰爭──甚至不只在兩個名字所指稱的美國和越南間上演。事實上,這兩個國家是分裂的,美國分為支持和反對戰爭的派系,而越南分為南方與北方,以及共產主義和反共產主義的兩方,但這些意識型態立場並非清楚的依照地理劃分。戰爭也有其他國家的參與者,首當其衝的是柬埔寨和寮國的人民,但也有許多南韓人。我要做的是,看見他們如何記憶自己的戰爭,而他們本身又如何被記憶,但這不是要嘗試全面納入和全面召喚回憶,因為我並未針對其他參與者發聲(澳洲人、紐西蘭人、菲律賓人、泰國人、俄國人、北韓人、中國人……)。10不過,擴大這個敘事以納入越南和美國以外的人民是我的表態,既指向記得之必要,也指向全面記憶之不可得,因為遺忘是必然,而每本書都需要其邊際。儘管如此,盡可能多記得一些是我的反動,因為許多、或許是絕大多數戰爭回憶,或至少在公眾間流通的戰爭回憶,都欠缺包容性。這些公眾記憶所展現的是,多數時候,國家與人民透過我稱為「記憶己方」(remembering one’s own)的倫理運作。這種倫理因國家而異,越南人比美國人更願意記住女性與平民,美國人比越南人更願意記得敵人,而兩方都未展現出記得南越人的任何意願,因為他們散發失敗、憂鬱、苦澀與憤怒的惡味。美國至少讓逃到美國的南越難民有機會講述他們的移民故事,藉此成為美國夢的一份子。11越南政府給他們的只有再教育營、新經濟區和從記憶中被抹除的待遇。既然如此,流亡的南越人多數也堅持不忘他們的自己人,亦不值得奇怪了。
對兩個國家和其多元的組成份子,包括戰敗和流亡的越南人,另一種倫理,即記得他者的倫理,是個例外,不是通則。這種記憶他者的倫理,讓記得自己人的傳統倫理改頭換面。它將誰在自己這一邊的定義加以擴大,以涵括更多他者,消除了接近而親愛之人(the near and dear)和遙遠而讓人畏懼者(far and feared)間的區別。這個倫理光譜的兩端,分別是記憶己方和記憶他者。我從這兩端出發,把這場戰爭中登場人物的回憶編織起來,他們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士兵和平民、多數和少數、贏家與輸家,還有許多無法歸入這些二分法、對立方和類別的人。戰爭牽涉到這麼多人,是因為它與一國多元的本地生活無法分割。將戰爭只想為戰鬥,其主角為士兵,而且在想像中通常為男性,只會阻礙對戰爭身分的理解,讓戰爭機器從中得益。
*
更具包容性的戰爭記憶,也是努力建立社會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稱為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的結果。集體記憶指的是,因為我們已經從所屬社群繼承而來的記憶而得以存在的個體記憶,也就是說,我們透過他人而記得。12批評家詹姆斯.楊格(James Young)以他提出的收集的記憶(collected memories)模型修改這種說法,指出不同群體的記憶可以透過令人安心的美國多元主義而匯集起來。13學者薩克文.伯科維奇(Sacvan Bercovitch)指出,這些群體及其記憶互相間的任何可能歧異,透過「共識的儀式」(ritual of consensus)所馴化,那正是有如神話的美國之道(American Way)。14不論我們談的是集體記憶或收集的記憶,這些模型要可信,都必須將定義它們的群體包含在內,不論那個群體是大是小。因此,戰爭的號召通常伴隨著對公民的要求,要他們只能記得有限的身分認同和對集體的狹隘認定,僅擴及家庭、部落和國族。因此,美國之道的包容性,從定義而言就排除了任何非美國的事物,也正因如此,直到今天,美國對這場戰爭的記憶往往遺忘或模糊了越南人,遑論柬埔寨人和寮國人。反對戰爭的人追求一種更廣泛的人類身分,可包含先前為我們所遺忘的人,希望這樣的開闊性能減少衝突的機會。
想要將更多自己人、甚或更多他者包容在內的渴望,會碰上個人的與政治性的問題,因為個體或集體記憶都無法達到完全包容。全面記憶(total memory)既不可能亦不實際,因為永遠有什麼會被遺忘。儘管我們很努力,還是會遺忘,我們也會因為強大的利益方,往往積極壓抑記憶而遺忘,形成米蘭.昆德拉所稱的「有組織的遺忘之沙漠」(the desert of organized forgetting)。15在這片沙漠中,記憶和水一樣重要,因為在權力的鬥爭中,記憶是重大戰略資源。要打仗,必然要能控制記憶,以及和其本質相反的遺忘(看似某種欠缺,實際上是資源)。國家培養記憶亦培養遺忘,若能夠,還會獨占兩者。他們敦促人民記得自己人、遺忘其他人,如此才能打造對戰爭至關重要的民族主義精神,這個自我中心的邏輯也在不同人種、族群和信仰社群中流通。這種記得自己人並遺忘其他人的主流邏輯極為強勢,連被遺忘的人一旦有機會也會遺忘他人。這場戰爭中輸家的故事顯示,在關於記憶的衝突中,沒有一個人在遺忘之事上是無辜的。
強勢與弱勢者爭奪記憶與遺忘的戰略資源時,鬥爭雖有時狂熱,甚至暴力,但更常是低強度的衝突,在其中,國家與其支持者使用的鬥爭手段,傳統與非傳統皆有。當權者控制政府、軍隊、警察,以及掌握監控機制與反叛亂手段的國家安全機器。這些當權者──政客、少數統治階級、企業與知識菁英──也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多數媒體。他們對學者、大專院校、評論者、智庫與教育機器擁有龐大的說服力量。一般而言,這些當權者牢牢掌握戰爭機器,讓機器運轉的二元碼就是記憶己方的倫理,將世界劃分為我們與他們、善與惡的對立,便於建立同盟、瞄準敵人。另一方面,儀式、遊行、演講、紀念碑、陳腔濫調與「真實戰爭故事」,不斷召喚著公民去記憶國家的英雄與死者,而若公民也能遺忘敵方與他們的死者,這件事就更容易了。
反抗戰爭的人強調另一種記憶他者的倫理。他們認為應該記住敵人與受害者、弱小與被遺忘者、邊緣與少數族群、女性和兒童、環境與動物、遙遠與遭妖魔化的,這些人全都在戰爭中受苦,多數更往往在國家主義式的戰爭記憶中被遺忘。在國家內部與國家之間,為了戰爭的意義和正當化戰爭的理由而起的鬥爭中,抗拒戰爭並記憶他者的人,不是為了一國而鬥爭,而是為了想像。在想像中可以出現新的身分,在國家身分與國家賦予戰爭的身分之外成為不同選擇。然而,儘管記憶他者在某些人看來值得欽佩,這種記憶模式也可能帶有危險或欺騙,因為記憶他者可能只是將對自己人的記憶反轉,像一個鏡面,使他者成為善良而正直,我們成為邪惡而有瑕疵的。記憶己方或記憶他者的這些倫理互相競爭,卻都是簡單的記憶倫理模型。我在這本書中尋找並主張的,是一種複雜的記憶倫理和公正的記憶(just memory),盡力記得自己人也記得他者,同時喚起讀者關注記憶的生命週期和其工業化生產,看記憶如何被打造與遺忘、演化與改變。
*
藝術對於保存公正記憶的倫理工作格外重要。我在本書中收入的文字、攝影、電影、紀念碑和紀念館,都是記憶和見證的形式,有時是針對私密、家庭、易逝而微小的事物,有時是針對歷史、公眾、恆久而劃時代的事物。我轉向這些藝術作品,因為在官方的備忘錄和演講被人遺忘、歷史書無人聞問,而權勢者歸於塵土之後,藝術仍在。藝術是想像的文物,而想像是人類所擁有最能展現不朽之物,像個集體的石板,記錄著人性與非人性的行為和欲望。權勢者畏懼藝術潛藏的恆久特質和它對記憶的影響,因而試圖輕忽、收編或壓抑藝術。他們往往得遂所願,因為雖然藝術僅偶爾帶著明顯的國家主義和宣傳意圖,卻往往隱含這些特質。本書中,我檢視了光譜上各種關於戰爭和記憶的藝術作品,從為權勢者的價值背書到企圖顛覆這類價值的作品皆有。即使知道許多藝術家與權勢者同謀,我依舊樂觀認為,未來的世紀中,這場戰爭或任何戰爭留給人類的記憶,很可能會是與權勢和戰爭對抗的少數傑出藝術作品(外加一、兩部歷史書)。
記憶與遺忘不僅受到藝術的建構,也可能被企圖捕捉並馴化藝術的產業所商品化。已有一整個記憶產業存在,隨時準備對耽於懷舊的消費者販賣記憶,靠歷史牟利。17資本主義可以把任何東西變成商品,包括記憶與失憶。因此,記憶的業餘從業者打造出紀念品與紀念物;懷舊的愛好者穿上古著,重演過往戰役;遊客造訪戰場、歷史遺址和博物館;電視頻道播放紀錄片和娛樂片,畫質清晰但記憶模糊。情感與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是記憶產業的要素,將戰爭和經驗轉變為神聖之物,士兵則變成不容輕蔑的記憶象徵,這可見於美國人對打了所謂良善之戰(Good War)的最偉大一代(Greatest Generation)之執迷崇拜。評論者嘲諷記憶產業,視之為社會記憶氾濫的證據,將記憶轉化為可拋棄和遺忘的產品與體驗,卻忽略了當下的困難與未來的可能性。但這種論點誤以為所謂的記憶產業(memory industry)只是徵狀,反映一個更普遍的現象:記憶的工業化(industrialization of memory)。記憶的工業化與戰爭的工業化平行發展,兩者都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一部分,在其中,記憶的火力與戰爭中實際使用的火力相當,為戰爭的身分進行定義與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