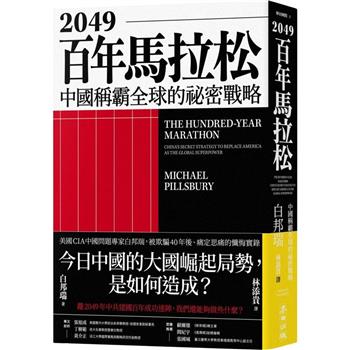摘錄自〈第十章 警鐘響起〉
【天秤已經傾斜?】
中國在二○○七年摧毀自己一顆氣象衛星,是一連串警訊的第一槍——刻意挑釁和敵意似乎意在測試美國及盟國的決心,以及國際規範能接受的範圍——可是世界各國大多忽視、漠視或替它說情開脫。自從二○○七年以來,各種事件層出不窮、且益形囂張。因此,東亞局勢緊張升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最高點。
緊跟著反衛星測試之後,中國對美國及新上任的總統歐巴馬的口氣有了顯著改變。二○○九年十二月,歐巴馬總統親赴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全球一百九十二個國家在此集會,研訂全球應付氣候變遷的新政策。這次峰會顯示中國官員公開的論調出現顯著變化。他們展現出不必要的不禮貌,數度打斷西方外交官的發言,對討論沒有提供建設性的意見。溫家寶總理已經冷落其他政府首長,拒絕出席大多數的談判。中國讓觀察家大為意外,竟然與其他開發中國家另行訂定協議,把原本盼望的承諾封殺、無法列入氣候變遷協定草案,等於朝大會目標開了一槍。根據一位美國政府高階官員的說法,中國在大會閉幕前刻意安排一項會議,不邀歐巴馬總統出席,以便封殺美國的倡議。歐巴馬總統和希拉蕊.柯林頓國務卿聞訊,做了不速之客,逕自闖入會場。
台灣長久以來即是美國和中國爭執的重心之一,但是中國突然十分強硬在二○一○年一月抗議行之多年的對台軍售——歐巴馬政府核准六十四億美元的對台軍售案——引起對美、台關係的全面重新檢討,也對未來軍售投入疑雲。中國認為這項軍售案「明顯干預中國內政」,可謂是比北京過去的作法更強悍的反應。接下來,中國暫時停止和美國的軍事互動,也對銷售物資給台灣的幾家美國公司實施制裁。美國政府向這個壓力低頭,決定壓下出售先進的F-16戰鬥機給台灣的計畫,此舉招致國會議員的批評,議員指控政府是軟腳蝦、頂不住中方壓力。後來,歐巴馬政府又擴大美、中之間的軍事交流。
中國之所以態度轉為強悍,是因為中國領導人意識到「勢」已決定性地轉為對中國有利,而美國的相對衰落卻快得超乎他們原先預期。中國會有這種認知,有一部分原因是中國使用比較全面的尺度來衡量綜合國力。二○○八年和二○○九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源自華爾街,北京認為這是一個先兆。中國評論員認為美國的經濟將會復原,但絕不會與原來一樣。在未來的時代,全球經濟領導權勢必更加分散,減少依附美元。中國等到「勢」轉為有利才在國外強悍表現,這也反映中國遵守欲速則不達的戰略要素,即使必須等上幾十年也行。
二○一○年出現中國重新評估的跡象。中共中央委員會一名外交事務專家向中國領導人提出四頁的祕密報告。這份簡報旨在回答「我國未來十年面對的最重要外交政策挑戰是什麼?」這個問題。根據美國政府取得的筆記,這位專家的回答是「如何管理美國衰落」。他提到幾個戰術可用來達成此一目標。如果正確的話,他的報告暗示中國可望在十年內經濟超越美國。
認定美國衰落的另一個證據,在二○一二年出現:二○一一年美國國防大學出版一本權威專書《權力的弔詭:在弱勢時代的中、美戰略節制》(The Paradox of Power: Sino-American Strategic Restraint in an Age of Vulnerability),作者為龔培德(David C. ompert)和菲力浦.桑德斯(Phillip C. Saunders)。這份美國政府的研究聲稱,軍事平衡已偏向中國。中方的反應很有意思。中方翻譯並發行這本書,向外國訪客表示,他們不會接受政策節制的提議,但是欽佩這本書坦白承認美國軍力相對衰退,而中國在核力量、網路攻擊和太空武器上實力增長。中國官員告訴我,它的結論洩露天機。他們說,這本書顯示美國政府已認知到中國在改變區域軍事平衡上的成功,因而對中國的利益有利。許多中國政治和軍事人物其實很訝異,美國竟然評估中國已經變得這麼強。根據我二○一二年和二○一三年在北京聽到的評論,我的結論是這份研究無意間提供證據給中國軍官,他們原本已在辯論時機是否已經成熟,可以利用軍事均勢對中傾斜的有利條件。
我聽說,中國政府和軍方許多人不相信這本書的主張——「美國沒有胃口想要挫折中國崛起、以盟國和軍力包圍它,或啟動中美冷戰」。他們認為這種話怎麼能相信,它倒像是刻意要誘騙中國大意輕敵。可是他們很欣賞兩位作者評估軍事均勢已傾向中國。他們也很困惑,為什麼美國政府自曝其短,發布美國衰退的證據,究竟是什麼使得美國對「勢」做出悲觀的評估。我認為兩位作者的說法只代表他們個人主張,他們不肯採信。
在幾次會議中,我表示這本書只是兩位作者個人的建言,不是美國政府官方政策的聲明,卻招致中國軍官和學者的訕笑。他們笑說,他們知道其中一位作者是歐巴馬總統國安會中國事務重要幕僚麥艾文(Evan Medeiros)的好朋友,兩人經常聯名發表文章。在中國眼裡,另一位作者也非同小可:他曾經是美國全國情報總監丹尼斯.布萊爾(Dennis Blair)的副手;而布萊爾曾任美軍太平洋總部總司令。中方深信這是一個訊息,代表權力平衡已向中國傾斜,「勢」已經在變化。他們同意書中一個論點——在中國增進其核子報復能力之後,美國升高核戰以嚇阻中國進攻台灣的威脅「已經輕微、也將降低」。但是他們還是不解,美國為什麼要公布如此負面的發現。
我們可以理解,美國和中國對如何解讀權力平衡會有不同看法。畢竟兩國是在不同的戰略環境中運作,面對的威脅並不相同;因此他們在評估國力時不可能強調相同的因素。
五角大廈淨評估室主任安德魯.馬歇爾一九八二年撰文談到美、蘇兩國對超強之間戰略平衡的評估不同時,他說:
正確評估的戰略平衡必須建立在一個重要項目之上,即我們對蘇聯人自己評估的戰略平衡的最佳概算。但這不能只是美國式的標準估算然後再假設上略做調整而已……相反的,它應該是盡可能地以蘇聯式的規畫去規劃,再來進行評估,採用他們認為最有可能發生的劇本,以及他們衡量結果的判準和方法……蘇式評估很可能對劇本和目標有不同的假設,重點放在不同變數上……進行不同的估算、採用不同的效率尺標,並且或許採用不同的評估過程和方法。結果是蘇式評估可能和美式評估大不相同。
其次,除了大半出自主觀解讀得到結論之外,不同國家在權力平衡關係中的相對地位,可能只有在事後這些國家回頭評估時才能完全理解。英國大政治家博林布魯克勛爵(Lord Bolingbroke)曾經說過:
權力天秤轉變的確切點……靠一般觀察是感受不到的……位於天秤上升的一方不會立刻感覺到他們的實力,也不會有成功經驗在日後給予他們的那份信心。那些對權力平衡變化念茲在茲的人,經常會從同樣的偏見做出誤判。他們繼續害怕一個已經傷害不了他們的大國,或是繼續低估一個已經躍升的強權。
某些美國學者果真反映了權力平衡評估的主觀性,他們否認均勢已經傾斜或是在未來可能向中國傾斜的說法。塔夫茨大學麥可.貝克萊(Michael Beckley)在二○一一年主張:「美國並未衰退;事實上比起一九九一年,它現在更富裕、更創新,軍力更強過中國。」他說:「中國正在崛起,但還未趕上。」當然,這兩種考量都關係到中、美雙方對本身以及對對方實力的評估。
甚且,由於不同的國家對權力平衡有不同的評估,北京可能開始認為它早在美國承認之前就已經大幅領先了。在馬拉松競賽的最後幾十年裡,這可能造成相互的錯誤認知,很可能就導致戰爭。
摘錄自〈第十章 警鐘響起〉
【天秤已經傾斜?】
中國在二○○七年摧毀自己一顆氣象衛星,是一連串警訊的第一槍——刻意挑釁和敵意似乎意在測試美國及盟國的決心,以及國際規範能接受的範圍——可是世界各國大多忽視、漠視或替它說情開脫。自從二○○七年以來,各種事件層出不窮、且益形囂張。因此,東亞局勢緊張升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最高點。
緊跟著反衛星測試之後,中國對美國及新上任的總統歐巴馬的口氣有了顯著改變。二○○九年十二月,歐巴馬總統親赴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全球一百九十二個國家在此集會,研訂全球應付氣候變遷的新政策。這次峰會顯示中國官員公開的論調出現顯著變化。他們展現出不必要的不禮貌,數度打斷西方外交官的發言,對討論沒有提供建設性的意見。溫家寶總理已經冷落其他政府首長,拒絕出席大多數的談判。中國讓觀察家大為意外,竟然與其他開發中國家另行訂定協議,把原本盼望的承諾封殺、無法列入氣候變遷協定草案,等於朝大會目標開了一槍。根據一位美國政府高階官員的說法,中國在大會閉幕前刻意安排一項會議,不邀歐巴馬總統出席,以便封殺美國的倡議。歐巴馬總統和希拉蕊.柯林頓國務卿聞訊,做了不速之客,逕自闖入會場。
台灣長久以來即是美國和中國爭執的重心之一,但是中國突然十分強硬在二○一○年一月抗議行之多年的對台軍售——歐巴馬政府核准六十四億美元的對台軍售案——引起對美、台關係的全面重新檢討,也對未來軍售投入疑雲。中國認為這項軍售案「明顯干預中國內政」,可謂是比北京過去的作法更強悍的反應。接下來,中國暫時停止和美國的軍事互動,也對銷售物資給台灣的幾家美國公司實施制裁。美國政府向這個壓力低頭,決定壓下出售先進的F-16戰鬥機給台灣的計畫,此舉招致國會議員的批評,議員指控政府是軟腳蝦、頂不住中方壓力。後來,歐巴馬政府又擴大美、中之間的軍事交流。
中國之所以態度轉為強悍,是因為中國領導人意識到「勢」已決定性地轉為對中國有利,而美國的相對衰落卻快得超乎他們原先預期。中國會有這種認知,有一部分原因是中國使用比較全面的尺度來衡量綜合國力。二○○八年和二○○九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源自華爾街,北京認為這是一個先兆。中國評論員認為美國的經濟將會復原,但絕不會與原來一樣。在未來的時代,全球經濟領導權勢必更加分散,減少依附美元。中國等到「勢」轉為有利才在國外強悍表現,這也反映中國遵守欲速則不達的戰略要素,即使必須等上幾十年也行。
二○一○年出現中國重新評估的跡象。中共中央委員會一名外交事務專家向中國領導人提出四頁的祕密報告。這份簡報旨在回答「我國未來十年面對的最重要外交政策挑戰是什麼?」這個問題。根據美國政府取得的筆記,這位專家的回答是「如何管理美國衰落」。他提到幾個戰術可用來達成此一目標。如果正確的話,他的報告暗示中國可望在十年內經濟超越美國。
認定美國衰落的另一個證據,在二○一二年出現:二○一一年美國國防大學出版一本權威專書《權力的弔詭:在弱勢時代的中、美戰略節制》(The Paradox of Power: Sino-American Strategic Restraint in an Age of Vulnerability),作者為龔培德(David C. ompert)和菲力浦.桑德斯(Phillip C. Saunders)。這份美國政府的研究聲稱,軍事平衡已偏向中國。中方的反應很有意思。中方翻譯並發行這本書,向外國訪客表示,他們不會接受政策節制的提議,但是欽佩這本書坦白承認美國軍力相對衰退,而中國在核力量、網路攻擊和太空武器上實力增長。中國官員告訴我,它的結論洩露天機。他們說,這本書顯示美國政府已認知到中國在改變區域軍事平衡上的成功,因而對中國的利益有利。許多中國政治和軍事人物其實很訝異,美國竟然評估中國已經變得這麼強。根據我二○一二年和二○一三年在北京聽到的評論,我的結論是這份研究無意間提供證據給中國軍官,他們原本已在辯論時機是否已經成熟,可以利用軍事均勢對中傾斜的有利條件。
我聽說,中國政府和軍方許多人不相信這本書的主張——「美國沒有胃口想要挫折中國崛起、以盟國和軍力包圍它,或啟動中美冷戰」。他們認為這種話怎麼能相信,它倒像是刻意要誘騙中國大意輕敵。可是他們很欣賞兩位作者評估軍事均勢已傾向中國。他們也很困惑,為什麼美國政府自曝其短,發布美國衰退的證據,究竟是什麼使得美國對「勢」做出悲觀的評估。我認為兩位作者的說法只代表他們個人主張,他們不肯採信。
在幾次會議中,我表示這本書只是兩位作者個人的建言,不是美國政府官方政策的聲明,卻招致中國軍官和學者的訕笑。他們笑說,他們知道其中一位作者是歐巴馬總統國安會中國事務重要幕僚麥艾文(Evan Medeiros)的好朋友,兩人經常聯名發表文章。在中國眼裡,另一位作者也非同小可:他曾經是美國全國情報總監丹尼斯.布萊爾(Dennis Blair)的副手;而布萊爾曾任美軍太平洋總部總司令。中方深信這是一個訊息,代表權力平衡已向中國傾斜,「勢」已經在變化。他們同意書中一個論點——在中國增進其核子報復能力之後,美國升高核戰以嚇阻中國進攻台灣的威脅「已經輕微、也將降低」。但是他們還是不解,美國為什麼要公布如此負面的發現。
我們可以理解,美國和中國對如何解讀權力平衡會有不同看法。畢竟兩國是在不同的戰略環境中運作,面對的威脅並不相同;因此他們在評估國力時不可能強調相同的因素。
五角大廈淨評估室主任安德魯.馬歇爾一九八二年撰文談到美、蘇兩國對超強之間戰略平衡的評估不同時,他說:
正確評估的戰略平衡必須建立在一個重要項目之上,即我們對蘇聯人自己評估的戰略平衡的最佳概算。但這不能只是美國式的標準估算然後再假設上略做調整而已……相反的,它應該是盡可能地以蘇聯式的規畫去規劃,再來進行評估,採用他們認為最有可能發生的劇本,以及他們衡量結果的判準和方法……蘇式評估很可能對劇本和目標有不同的假設,重點放在不同變數上……進行不同的估算、採用不同的效率尺標,並且或許採用不同的評估過程和方法。結果是蘇式評估可能和美式評估大不相同。
其次,除了大半出自主觀解讀得到結論之外,不同國家在權力平衡關係中的相對地位,可能只有在事後這些國家回頭評估時才能完全理解。英國大政治家博林布魯克勛爵(Lord Bolingbroke)曾經說過:
權力天秤轉變的確切點……靠一般觀察是感受不到的……位於天秤上升的一方不會立刻感覺到他們的實力,也不會有成功經驗在日後給予他們的那份信心。那些對權力平衡變化念茲在茲的人,經常會從同樣的偏見做出誤判。他們繼續害怕一個已經傷害不了他們的大國,或是繼續低估一個已經躍升的強權。
某些美國學者果真反映了權力平衡評估的主觀性,他們否認均勢已經傾斜或是在未來可能向中國傾斜的說法。塔夫茨大學麥可.貝克萊(Michael Beckley)在二○一一年主張:「美國並未衰退;事實上比起一九九一年,它現在更富裕、更創新,軍力更強過中國。」他說:「中國正在崛起,但還未趕上。」當然,這兩種考量都關係到中、美雙方對本身以及對對方實力的評估。
甚且,由於不同的國家對權力平衡有不同的評估,北京可能開始認為它早在美國承認之前就已經大幅領先了。在馬拉松競賽的最後幾十年裡,這可能造成相互的錯誤認知,很可能就導致戰爭。
摘錄自〈第十章 警鐘響起〉
【天秤已經傾斜?】
中國之所以態度轉為強悍,是因為中國領導人意識到「勢」已決定性地轉為對中國有利,而美國的相對衰落卻快得超乎他們原先預期。中國會有這種認知,有一部分原因是中國使用比較全面的尺度來衡量綜合國力。二○○八年和二○○九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源自華爾街,北京認為這是一個先兆。中國評論員認為美國的經濟將會復原,但絕不會與原來一樣。在未來的時代,全球經濟領導權勢必更加分散,減少依附美元。中國等到「勢」轉為有利才在國外強悍表現,這也反映中國遵守欲速則不達的戰略要素,即使必須等上幾十年也行。
二○一○年出現中國重新評估的跡象。中共中央委員會一名外交事務專家向中國領導人提出四頁的祕密報告。這份簡報旨在回答「我國未來十年面對的最重要外交政策挑戰是什麼?」這個問題。根據美國政府取得的筆記,這位專家的回答是「如何管理美國衰落」。他提到幾個戰術可用來達成此一目標。如果正確的話,他的報告暗示中國可望在十年內經濟超越美國。
認定美國衰落的另一個證據,在二○一二年出現:二○一一年美國國防大學出版一本權威專書《權力的弔詭:在弱勢時代的中、美戰略節制》,作者為龔培德(David C. Gompert)和菲力浦.桑德斯(Phillip C. Saunders)。這份美國政府的研究聲稱,軍事平衡已偏向中國。中方的反應很有意思。中方翻譯並發行這本書,向外國訪客表示,他們不會接受政策節制的提議,但是欽佩這本書坦白承認美國軍力相對衰退,而中國在核力量、網路攻擊和太空武器上實力增長。中國官員告訴我,它的結論洩露天機。他們說,這本書顯示美國政府已認知到中國在改變區域軍事平衡上的成功,因而對中國的利益有利。許多中國政治和軍事人物其實很訝異,美國竟然評估中國已經變得這麼強。根據我二○一二年和二○一三年在北京聽到的評論,我的結論是這份研究無意間提供證據給中國軍官,他們原本已在辯論時機是否已經成熟,可以利用軍事均勢對中傾斜的有利條件。
我聽說,中國政府和軍方許多人不相信這本書的主張——「美國沒有胃口想要挫折中國崛起、以盟國和軍力包圍它,或啟動中美冷戰」。他們認為這種話怎麼能相信,它倒像是刻意要誘騙中國大意輕敵。可是他們很欣賞兩位作者評估軍事均勢已傾向中國。他們也很困惑,為什麼美國政府自曝其短,發布美國衰退的證據,究竟是什麼使得美國對「勢」做出悲觀的評估。我認為兩位作者的說法只代表他們個人主張,他們不肯採信。
在幾次會議中,我表示這本書只是兩位作者個人的建言,不是美國政府官方政策的聲明,卻招致中國軍官和學者的訕笑。他們笑說,他們知道其中一位作者是歐巴馬總統國安會中國事務重要幕僚麥艾文(Evan Medeiros)的好朋友,兩人經常聯名發表文章。在中國眼裡,另一位作者也非同小可:他曾經是美國全國情報總監丹尼斯.布萊爾(Dennis Blair)的副手;而布萊爾曾任美軍太平洋總部總司令。中方深信這是一個訊息,代表權力平衡已向中國傾斜,「勢」已經在變化。他們同意書中一個論點——在中國增進其核子報復能力之後,美國升高核戰以嚇阻中國進攻台灣的威脅「已經輕微、也將降低」。但是他們還是不解,美國為什麼要公布如此負面的發現。
我們可以理解,美國和中國對如何解讀權力平衡會有不同看法。畢竟兩國是在不同的戰略環境中運作,面對的威脅並不相同;因此他們在評估國力時不可能強調相同的因素。五角大廈淨評估室主任安德魯.馬歇爾一九八二年撰文談到美、蘇兩國對超強之間戰略平衡的評估不同時,他說:
正確評估的戰略平衡必須建立在一個重要項目之上,即我們對蘇聯人自己評估的戰略平衡的最佳概算。但這不能只是美國式的標準估算然後再假設上略做調整而已……相反的,它應該是盡可能地以蘇聯式的規畫去規劃,再來進行評估,採用他們認為最有可能發生的劇本,以及他們衡量結果的判準和方法……蘇式評估很可能對劇本和目標有不同的假設,重點放在不同變數上……進行不同的估算、採用不同的效率尺標,並且或許採用不同的評估過程和方法。結果是蘇式評估可能和美式評估大不相同。
其次,除了大半出自主觀解讀得到結論之外,不同國家在權力平衡關係中的相對地位,可能只有在事後這些國家回頭評估時才能完全理解。英國大政治家博林布魯克勛爵(Lord Bolingbroke)曾經說過:
權力天秤轉變的確切點……靠一般觀察是感受不到的……位於天秤上升的一方不會立刻感覺到他們的實力,也不會有成功經驗在日後給予他們的那份信心。那些對權力平衡變化念茲在茲的人,經常會從同樣的偏見做出誤判。他們繼續害怕一個已經傷害不了他們的大國,或是繼續低估一個已經躍升的強權。
某些美國學者果真反映了權力平衡評估的主觀性,他們否認均勢已經傾斜或是在未來可能向中國傾斜的說法。塔夫茨大學麥可.貝克萊(Michael Beckley)在二○一一年主張:「美國並未衰退;事實上比起一九九一年,它現在更富裕、更創新,軍力更強過中國。」他說:「中國正在崛起,但還未趕上。」當然,這兩種考量都關係到中、美雙方對本身以及對對方實力的評估。
甚且,由於不同的國家對權力平衡有不同的評估,北京可能開始認為它早在美國承認之前就已經大幅領先了。在馬拉松競賽的最後幾十年裡,這可能造成相互的錯誤認知,很可能就導致戰爭。
【中國與鄰國的緊張關係】
眼看著馬拉松勝利在望,中國人現在覺得比起以前更有空間耀武揚威,雖然同時也對他們的宏圖大計保持節制。他們在國境四周還有更緊迫的當務之急。中國周圍海域已經出現緊張局勢,南與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和汶萊有領土糾紛,東與日本也不平靖。
自從二○一○年以來,中國翻出塵封幾百年的地圖,想證明中國與東海、南海一些島礁有歷史淵源,因而提出領土主張。南海成為「熱點」,二○一○年五月與美國的高峰會議上,中國堅持對南沙群島的權利主張,把富含能源和漁業資源的數萬平方英里海洋納入其專屬經濟區,並把領海推進到靠近越南和菲律賓海岸地區。
希拉蕊.柯林頓國務卿表示美國願意調停中國及其南方鄰國之間的爭端,這惹來中國憤怒反應。接下來幾個月,中方不時騷擾越南和菲律賓船隻。菲律賓總統艾奎諾三世(Benigno S. Aquino III)把局勢比擬為一九三八年捷克面臨的危機:「什麼時候你該說:『夠了就是夠了』?世界必須說話了。大家必然記得,捷克割讓蘇台德地區(Sudetenland)是想要平息希特勒以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反駁艾奎諾的說法「暴露業餘政客本色」。
但是,中、日之間的緊張程度最高。某些中國作家認為日本人是「雜種民族」、是美國在亞洲的代理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殘暴占領中國留下的仇恨,迄今猶未緩解。在東海,由日本群島往西延伸的一系列島礁成為小衝突的場所,很有可能演化為全面海戰。……
……針對日本的抗議,中國外交部聲明:「日方無權做不負責任的評論,以及對中國惡意指控。我們呼籲日方停止傷害中國領土主權的所有行動。」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二○一四年一月在瑞士達沃斯的世界經濟論壇引起爭議,因為他把中、日之間在東海的爭議,拿來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德、英關係做比擬。大家都曉得,儘管德、英兩國經濟關係密切,猶如今天的中、日兩國,可是卻在一九一四年爆發戰爭。
日本會如何回應中國在其西邊水域日益上升的侵略性行為,將會是其馬拉松戰略的重要試金石。至少在過去二十年,北京將戰國列強削弱敵國之鷹派的作法,施用在日本之上。中國在亞洲各地發動反日的妖魔化運動,包括針對日本國內民眾宣傳。它的宗旨始終一致:日本的鷹派陰謀策劃恢復日本在一九三○年代的軍國主義,因此必須把他們揪出來,不能讓他們在政治上得勢。
為了妖魔化日本,中國發出的訊息是,它認為日本的財富,以及日本身為美國在亞洲主要盟國的地位,是從二戰不當得利的結果。倫敦政經學院教授文安立(Odd Arne Westad)稱這個現象是「有毒的、新形式的國家批准的反日民族主義」。「儒家文明圈」的國家應該接受中國天經地義的領導地位,不應該企圖復活舊帝國,或與美國這樣的外來霸權結盟。……
……中國對日本日益強悍,頗有可能對中國想贏得馬拉松的長期戰略有反效果——步步為營、謀定而後動的中國領導人若還忌憚美國霸權的話,應該不太可能挑釁美國在東亞最親近的盟友。中國若是與日本開戰,也可做為對抗美國的祕密鬥爭中的一場代理人戰爭——中國若能打擊日本,將進一步削弱已經衰落的霸主。……
……日本領導人已公開討論修訂日本的和平主義憲法——禁止採用武力解決國際爭端,只准維持自衛所需的低度兵力。通常日本人迴避不談它,但是現在卻坦率談論和中國的戰略競爭,以及中國在亞洲持續強悍的危險。中國對日本擴軍的可能性,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英、德海軍軍備競賽情勢再現的可能性,反應非常激烈。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對日本建設軍事力量並不是一直持負面觀點。一九七○年代中國鼓勵日本將防衛費用從GDP的百分之一提升到百分之三。一九七八年,鄧小平告訴日本訪問團,他「贊成日本自衛隊強化」。中國當時要拉攏一個新盟友對抗蘇聯。然而,十年之後,中國對「勢」的評估變了,一九八八年,鄧小平的國家安全顧問宦鄉強烈批評日本。……
……中共智庫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副所長陸忠偉指出:「在亞洲外交史上,從來沒有過強大的中國和強大的日本並存的先例。」中國社會科學院高恆也認為,美國的占領並沒有消除日本的軍國主義。他認為,甚至因為美國在占領期間希望利用日本對抗蘇聯、北朝鮮和中國,「它維持日本的整個國家機器和戰爭機器(不過改了名字)。」中國學者提到,日本「壓制中國的領土政策,並且干預中國對南沙群島和釣魚台的主權。」所謂的「宮澤主義」(Miyazawa doctrine)即仿照「歐洲安全暨合作會議」(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在亞洲成立區域論壇、討論亞洲安全議題,卻被中國學者批評是圍堵中國的煙霧彈。《紐約時報》於一九九三年報導,中國一名官員透露,中國軍方要求在《五年計劃》中增加國防預算,以便對付日本軍事力量上升。
中國最迫切的關切是日本與美國合作開發反彈道飛彈防禦系統。更進一步的中國評論亦強調日本取得核武和航空母艦的企圖。另外,中國分析家聲稱日本已有「具備航空母艦功能」的運輸艦。即使在核武議題上,某些中國分析家預測,未來的日本會像印度一樣成為核子國家。丁邦泉在中國軍事科學院刊物《世界軍事趨勢》撰文說:「毫無疑問,日本有能力製造核子彈……日本有辦法避開國際監督,就核武器進行祕密研究。」
【中國與鄰國的緊張關係】
眼看著馬拉松勝利在望,中國人現在覺得比起以前更有空間耀武揚威,雖然同時也對他們的宏圖大計保持節制。他們在國境四周還有更緊迫的當務之急。中國周圍海域已經出現緊張局勢,南與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和汶萊有領土糾紛,東與日本也不平靖。
自從二○一○年以來,中國翻出塵封幾百年的地圖,想證明中國與東海、南海一些島礁有歷史淵源,因而提出領土主張。南海成為「熱點」,二○一○年五月與美國的高峰會議上,中國堅持對南沙群島的權利主張,把富含能源和漁業資源的數萬平方英里海洋納入其專屬經濟區,並把領海推進到靠近越南和菲律賓海岸地區。
希拉蕊.柯林頓國務卿表示美國願意調停中國及其南方鄰國之間的爭端,這惹來中國憤怒反應。接下來幾個月,中方不時騷擾越南和菲律賓船隻。菲律賓總統艾奎諾三世(Benigno S. Aquino III)把局勢比擬為一九三八年捷克面臨的危機:「什麼時候你該說:『夠了就是夠了』?世界必須說話了。大家必然記得,捷克割讓蘇台德地區(Sudetenland)是想要平息希特勒以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反駁艾奎諾的說法「暴露業餘政客本色」。
但是,中、日之間的緊張程度最高。某些中國作家認為日本人是「雜種民族」、是美國在亞洲的代理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殘暴占領中國留下的仇恨,迄今猶未緩解。在東海,由日本群島往西延伸的一系列島礁成為小衝突的場所,很有可能演化為全面海戰。
二○一○年九月七日,中國一艘漁船在釣魚台/尖閣群島這個主權有爭議的海域,和日本巡邏船發生衝撞。中國船長和船員被日本海上警視廳扣押,不顧中國政府強力反對,帶回日本。中方阻擋一些稀土出口到日本以示不滿,並且以涉嫌擅闖中國軍事禁區之罪名,逮捕四名日本僑民。
兩年後,我很驚訝聽到六艘中國海監部隊船隻、分為兩隊,克服日本攔阻,闖進釣魚台海域。在此之前,中方宣稱其領海包括此一地區。我之所以驚訝是因為自此之後一連好幾個月,中國海監船增加在釣魚台/尖閣群島附近的巡邏,有時候中國漁船在本地區作業長達數星期,而且經常靠近到離釣魚台/尖閣群島十四英里以內。同時,當日本政府將釣魚台/尖閣群島地區幾個私人所有的島礁買下之後,中國各地爆發反日抗議。數千名抗議者包圍北京日本大使館,其餘團體則在數十個中國城市抗議、示威。中國政府鼓勵示威,廣播稱,「日本已侵犯中國權利,表達你的觀點是很自然的事。」
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國國防部宣布在東海設置防空識別區,逼使我們必須有所行動。固然日本、美國等國家過去都曾經宣布他們的防空識別區,中國不尋常的嚴格要求卻很突兀,因為它要求進入識別區的飛機不僅要表明身分,提供飛行計畫,還要與中國的防空識別區管理單位保持無線電聯絡。北京宣布後不久,我很高興美國國防部長查克.海格(Chuck Hagel)批准兩架B-52飛越防空識別區,以示美國不承認北京的要求。我向他建言,中方不會有反應的。
針對日本的抗議,中國外交部聲明:「日方無權做不負責任的評論,以及對中國惡意指控。我們呼籲日方停止傷害中國領土主權的所有行動。」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二○一四年一月在瑞士達沃斯的世界經濟論壇引起爭議,因為他把中、日之間在東海的爭議,拿來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德、英關係做比擬。大家都曉得,儘管德、英兩國經濟關係密切,猶如今天的中、日兩國,可是卻在一九一四年爆發戰爭。
日本會如何回應中國在其西邊水域日益上升的侵略性行為,將會是其馬拉松戰略的重要試金石。至少在過去二十年,北京將戰國列強削弱敵國之鷹派的作法,施用在日本之上。中國在亞洲各地發動反日的妖魔化運動,包括針對日本國內民眾宣傳。它的宗旨始終一致:日本的鷹派陰謀策劃恢復日本在一九三○年代的軍國主義,因此必須把他們揪出來,不能讓他們在政治上得勢。
為了妖魔化日本,中國發出的訊息是,它認為日本的財富,以及日本身為美國在亞洲主要盟國的地位,是從二戰不當得利的結果。倫敦政經學院教授文安立(Odd Arne Westad)稱這個現象是「有毒的、新形式的國家批准的反日民族主義」。「儒家文明圈」的國家應該接受中國天經地義的領導地位,不應該企圖復活舊帝國,或與美國這樣的外來霸權結盟。二○一三年八月,針對中、日兩國國民對彼此觀感的一項調查,有助於我們了解這些爭議。這項調查由中國的《中國日報》和日本的智庫《言論NPO》共同進行,向一千八百零五個日本人及一千五百四十個中國人調查他們對另一國家的觀點。調查發現,九成以上的中國受訪者對日本沒有好感,相較於一年前的調查結果(百分之六十二)出奇的高。同樣地,九成的日本受訪者對中國沒有好感,而一年前只有百分之八十四.三。這是過去九年來每年調查敵意最高的一次。被問到為什麼整體中、日敵意如此顯著上升時,許多受訪者表示,尖閣群島/釣魚台爭端是原因:百分之七十七.六的中方受訪者和百分之五三.二的日本受訪者認為島嶼爭端是他們相互仇視的主要原因。
其次一個最重要因素是歷史恩怨:百分之六三.八的中方受訪人認為「日本對於侵華歷史缺乏適切的道歉和懺悔」是他們對日本有負面觀點的原因之一。或許最不祥的發現是,有百分之五二.七的中國受訪者和百分之二三.七的日本受訪者認為,他們相信中、日之間將來還會爆發軍事衝突。
中國對日本日益強悍,頗有可能對中國想贏得馬拉松的長期戰略有反效果——步步為營、謀定而後動的中國領導人若還忌憚美國霸權的話,應該不太可能挑釁美國在東亞最親近的盟友。中國若是與日本開戰,也可做為對抗美國的祕密鬥爭中的一場代理人戰爭——中國若能打擊日本,將進一步削弱已經衰落的霸主。
二○一三年,有一部分是針對中國在東亞日益蠻橫之反應,美國和日本同意擴大他們的安全同盟,以便展現美國決心仍在本地區扮演主要角色。這項協議包括美國將派偵察機前往日本,預料將會在釣魚台/尖閣群島四周及整個繫爭島礁地區海域巡邏。美國國務卿約翰.凱瑞(John Kerry)和國防部長查克.海格親自前往東京簽署這項協定。固然美國拒絕在爭端中選邊,海格重申歐巴馬政府的保證:根據《美日安保條約》的規定,日本若遭到攻擊,美國有義務協助日本自衛,而它將包括釣魚台/尖閣群島。
日本領導人已公開討論修訂日本的和平主義憲法——禁止採用武力解決國際爭端,只准維持自衛所需的低度兵力。通常日本人迴避不談它,但是現在卻坦率談論和中國的戰略競爭,以及中國在亞洲持續強悍的危險。中國對日本擴軍的可能性,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英、德海軍軍備競賽情勢再現的可能性,反應非常激烈。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對日本建設軍事力量並不是一直持負面觀點。一九七○年代中國鼓勵日本將防衛費用從GDP的百分之一提升到百分之三。一九七八年,鄧小平告訴日本訪問團,他「贊成日本自衛隊強化」。中國當時要拉攏一個新盟友對抗蘇聯。然而,十年之後,中國對「勢」的評估變了,一九八八年,鄧小平的國家安全顧問宦鄉強烈批評日本。
中國對日本民主政治的穩定性有根深柢固的懷疑。許多中國學者認為,今天日本許多右派人士「想要修憲以恢復舊帝國制度」。中國分析家經常批評日本政客到靖國神社參拜;靖國神社是日本神道廟殿,供奉一八六七年至一九五一年的日本陣亡英靈,其中包括二戰期間的日本戰犯。這些分析家寫說,日本政客以參拜做為「精神動員,以便在中國進一步侵略擴張」。許多中國戰略學者相信,日本軍事力量增長必將成為「無法控制」。
日本軍國主義在未來可能復活,令中國憂慮。何新或許是中國最著名的極端民族主義作家、也是李鵬總理的顧問。他在一九八八年預測,日本對資源掠奪性的需求,將會使它企圖「殖民」中國。他說:「自從十九世紀以來,日本從來不曾放棄它長期以來的全球戰略目標……同時,就整體戰略布局而言,日本將完全瓜分及孤立中國。」
【中國與鄰國的緊張關係】
眼看著馬拉松勝利在望,中國人現在覺得比起以前更有空間耀武揚威,雖然同時也對他們的宏圖大計保持節制。他們在國境四周還有更緊迫的當務之急。中國周圍海域已經出現緊張局勢,南與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和汶萊有領土糾紛,東與日本也不平靖。
自從二○一○年以來,中國翻出塵封幾百年的地圖,想證明中國與東海、南海一些島礁有歷史淵源,因而提出領土主張。南海成為「熱點」,二○一○年五月與美國的高峰會議上,中國堅持對南沙群島的權利主張,把富含能源和漁業資源的數萬平方英里海洋納入其專屬經濟區,並把領海推進到靠近越南和菲律賓海岸地區。
希拉蕊.柯林頓國務卿表示美國願意調停中國及其南方鄰國之間的爭端,這惹來中國憤怒反應。接下來幾個月,中方不時騷擾越南和菲律賓船隻。菲律賓總統艾奎諾三世(Benigno S. Aquino III)把局勢比擬為一九三八年捷克面臨的危機:「什麼時候你該說:『夠了就是夠了』?世界必須說話了。大家必然記得,捷克割讓蘇台德地區(Sudetenland)是想要平息希特勒以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反駁艾奎諾的說法「暴露業餘政客本色」。
但是,中、日之間的緊張程度最高。某些中國作家認為日本人是「雜種民族」、是美國在亞洲的代理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殘暴占領中國留下的仇恨,迄今猶未緩解。在東海,由日本群島往西延伸的一系列島礁成為小衝突的場所,很有可能演化為全面海戰。
二○一○年九月七日,中國一艘漁船在釣魚台/尖閣群島這個主權有爭議的海域,和日本巡邏船發生衝撞。中國船長和船員被日本海上警視廳扣押,不顧中國政府強力反對,帶回日本。中方阻擋一些稀土出口到日本以示不滿,並且以涉嫌擅闖中國軍事禁區之罪名,逮捕四名日本僑民。
兩年後,我很驚訝聽到六艘中國海監部隊船隻、分為兩隊,克服日本攔阻,闖進釣魚台海域。在此之前,中方宣稱其領海包括此一地區。我之所以驚訝是因為自此之後一連好幾個月,中國海監船增加在釣魚台/尖閣群島附近的巡邏,有時候中國漁船在本地區作業長達數星期,而且經常靠近到離釣魚台/尖閣群島十四英里以內。同時,當日本政府將釣魚台/尖閣群島地區幾個私人所有的島礁買下之後,中國各地爆發反日抗議。數千名抗議者包圍北京日本大使館,其餘團體則在數十個中國城市抗議、示威。中國政府鼓勵示威,廣播稱,「日本已侵犯中國權利,表達你的觀點是很自然的事。」
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國國防部宣布在東海設置防空識別區,逼使我們必須有所行動。固然日本、美國等國家過去都曾經宣布他們的防空識別區,中國不尋常的嚴格要求卻很突兀,因為它要求進入識別區的飛機不僅要表明身分,提供飛行計畫,還要與中國的防空識別區管理單位保持無線電聯絡。北京宣布後不久,我很高興美國國防部長查克.海格(Chuck Hagel)批准兩架B-52飛越防空識別區,以示美國不承認北京的要求。我向他建言,中方不會有反應的。
針對日本的抗議,中國外交部聲明:「日方無權做不負責任的評論,以及對中國惡意指控。我們呼籲日方停止傷害中國領土主權的所有行動。」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二○一四年一月在瑞士達沃斯的世界經濟論壇引起爭議,因為他把中、日之間在東海的爭議,拿來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德、英關係做比擬。大家都曉得,儘管德、英兩國經濟關係密切,猶如今天的中、日兩國,可是卻在一九一四年爆發戰爭。
日本會如何回應中國在其西邊水域日益上升的侵略性行為,將會是其馬拉松戰略的重要試金石。至少在過去二十年,北京將戰國列強削弱敵國之鷹派的作法,施用在日本之上。中國在亞洲各地發動反日的妖魔化運動,包括針對日本國內民眾宣傳。它的宗旨始終一致:日本的鷹派陰謀策劃恢復日本在一九三○年代的軍國主義,因此必須把他們揪出來,不能讓他們在政治上得勢。
為了妖魔化日本,中國發出的訊息是,它認為日本的財富,以及日本身為美國在亞洲主要盟國的地位,是從二戰不當得利的結果。倫敦政經學院教授文安立(Odd Arne Westad)稱這個現象是「有毒的、新形式的國家批准的反日民族主義」。「儒家文明圈」的國家應該接受中國天經地義的領導地位,不應該企圖復活舊帝國,或與美國這樣的外來霸權結盟。二○一三年八月,針對中、日兩國國民對彼此觀感的一項調查,有助於我們了解這些爭議。這項調查由中國的《中國日報》和日本的智庫《言論NPO》共同進行,向一千八百零五個日本人及一千五百四十個中國人調查他們對另一國家的觀點。調查發現,九成以上的中國受訪者對日本沒有好感,相較於一年前的調查結果(百分之六十二)出奇的高。同樣地,九成的日本受訪者對中國沒有好感,而一年前只有百分之八十四.三。這是過去九年來每年調查敵意最高的一次。被問到為什麼整體中、日敵意如此顯著上升時,許多受訪者表示,尖閣群島/釣魚台爭端是原因:百分之七十七.六的中方受訪者和百分之五三.二的日本受訪者認為島嶼爭端是他們相互仇視的主要原因。
其次一個最重要因素是歷史恩怨:百分之六三.八的中方受訪人認為「日本對於侵華歷史缺乏適切的道歉和懺悔」是他們對日本有負面觀點的原因之一。或許最不祥的發現是,有百分之五二.七的中國受訪者和百分之二三.七的日本受訪者認為,他們相信中、日之間將來還會爆發軍事衝突。
中國對日本日益強悍,頗有可能對中國想贏得馬拉松的長期戰略有反效果——步步為營、謀定而後動的中國領導人若還忌憚美國霸權的話,應該不太可能挑釁美國在東亞最親近的盟友。中國若是與日本開戰,也可做為對抗美國的祕密鬥爭中的一場代理人戰爭——中國若能打擊日本,將進一步削弱已經衰落的霸主。
二○一三年,有一部分是針對中國在東亞日益蠻橫之反應,美國和日本同意擴大他們的安全同盟,以便展現美國決心仍在本地區扮演主要角色。這項協議包括美國將派偵察機前往日本,預料將會在釣魚台/尖閣群島四周及整個繫爭島礁地區海域巡邏。美國國務卿約翰.凱瑞(John Kerry)和國防部長查克.海格親自前往東京簽署這項協定。固然美國拒絕在爭端中選邊,海格重申歐巴馬政府的保證:根據《美日安保條約》的規定,日本若遭到攻擊,美國有義務協助日本自衛,而它將包括釣魚台/尖閣群島。
日本領導人已公開討論修訂日本的和平主義憲法——禁止採用武力解決國際爭端,只准維持自衛所需的低度兵力。通常日本人迴避不談它,但是現在卻坦率談論和中國的戰略競爭,以及中國在亞洲持續強悍的危險。中國對日本擴軍的可能性,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英、德海軍軍備競賽情勢再現的可能性,反應非常激烈。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對日本建設軍事力量並不是一直持負面觀點。一九七○年代中國鼓勵日本將防衛費用從GDP的百分之一提升到百分之三。一九七八年,鄧小平告訴日本訪問團,他「贊成日本自衛隊強化」。中國當時要拉攏一個新盟友對抗蘇聯。然而,十年之後,中國對「勢」的評估變了,一九八八年,鄧小平的國家安全顧問宦鄉強烈批評日本。
中國對日本民主政治的穩定性有根深柢固的懷疑。許多中國學者認為,今天日本許多右派人士「想要修憲以恢復舊帝國制度」。中國分析家經常批評日本政客到靖國神社參拜;靖國神社是日本神道廟殿,供奉一八六七年至一九五一年的日本陣亡英靈,其中包括二戰期間的日本戰犯。這些分析家寫說,日本政客以參拜做為「精神動員,以便在中國進一步侵略擴張」。許多中國戰略學者相信,日本軍事力量增長必將成為「無法控制」。
日本軍國主義在未來可能復活,令中國憂慮。何新或許是中國最著名的極端民族主義作家、也是李鵬總理的顧問。他在一九八八年預測,日本對資源掠奪性的需求,將會使它企圖「殖民」中國。他說:「自從十九世紀以來,日本從來不曾放棄它長期以來的全球戰略目標……同時,就整體戰略布局而言,日本將完全瓜分及孤立中國。」
接下來,中國在一九九五年呼籲美國關閉琉球(沖繩)的美軍基地,並且質疑在後冷戰的世界哪裡還需要《美日安保條約》。中國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研究員盧廣業(Lu Guangye,音譯)甚至警告說:「北約集團和日美軍事同盟已經成為助紂為虐的兩隻黑手。」
中共智庫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副所長陸忠偉指出:「在亞洲外交史上,從來沒有過強大的中國和強大的日本並存的先例。」中國社會科學院高恆也認為,美國的占領並沒有消除日本的軍國主義。他認為,甚至因為美國在占領期間希望利用日本對抗蘇聯、北朝鮮和中國,「它維持日本的整個國家機器和戰爭機器(不過改了名字)。」中國學者提到,日本「壓制中國的領土政策,並且干預中國對南沙群島和釣魚台的主權。」所謂的「宮澤主義」(Miyazawa doctrine)即仿照「歐洲安全暨合作會議」(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在亞洲成立區域論壇、討論亞洲安全議題,卻被中國學者批評是圍堵中國的煙霧彈。《紐約時報》於一九九三年報導,中國一名官員透露,中國軍方要求在《五年計劃》中增加國防預算,以便對付日本軍事力量上升。
中國最迫切的關切是日本與美國合作開發反彈道飛彈防禦系統。更進一步的中國評論亦強調日本取得核武和航空母艦的企圖。另外,中國分析家聲稱日本已有「具備航空母艦功能」的運輸艦。即使在核武議題上,某些中國分析家預測,未來的日本會像印度一樣成為核子國家。丁邦泉在中國軍事科學院刊物《世界軍事趨勢》撰文說:「毫無疑問,日本有能力製造核子彈……日本有辦法避開國際監督,就核武器進行祕密研究。」
【美國誤判中國對台灣的立場】
二○○九年,我的同僚和我仍然犯錯,以為中國人的想法和我們美國人一樣。我們對於中國對美國及其鄰國的新侵略性有所誤解,是因為它並不吻合我們既有的假設,也因為我們的中國線民一再向我們擔保,一系列似乎顯示中國愈來愈強悍的情節,並不是任何全盤計畫的一部分。並不是只有我一個人毫不懷疑中國。畢竟,我對中國馬拉松戰略的了解是,並沒有真正的急迫性要它趕著抵達終點,至少不是眼前當下。中國種種愈來愈強悍的行為似乎是隨機出現的獨立事件,美國為此辯論不休。中國的訊息是,沒有全盤模式或戰略把這些個別插曲連串起來。這個說法吻合早先的訊息:即中國並沒有大戰略。中國頂尖的美國事務專家王緝思就在《外交事務》雜誌發表文章如此說。
我的同僚和我認為理所當然的是,中國會盡一切代價避免挑釁美國霸權,以及至少還要花二十年工夫,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力量才足以懾服美國。這一切意味著,中國最不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對其鄰國和美國擺出侵略姿勢,壞了大事。可是,在二○一四年,美國政府官員卻告訴國會,中國已開始展現強悍的行為模式。為什麼我們花這麼久才明白這一點?
接下來,中國在一九九五年呼籲美國關閉琉球(沖繩)的美軍基地,並且質疑在後冷戰的世界哪裡還需要《美日安保條約》。中國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研究員盧廣業(Lu Guangye,音譯)甚至警告說:「北約集團和日美軍事同盟已經成為助紂為虐的兩隻黑手。」
中共智庫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副所長陸忠偉指出:「在亞洲外交史上,從來沒有過強大的中國和強大的日本並存的先例。」中國社會科學院高恆也認為,美國的占領並沒有消除日本的軍國主義。他認為,甚至因為美國在占領期間希望利用日本對抗蘇聯、北朝鮮和中國,「它維持日本的整個國家機器和戰爭機器(不過改了名字)。」中國學者提到,日本「壓制中國的領土政策,並且干預中國對南沙群島和釣魚台的主權。」所謂的「宮澤主義」(Miyazawa doctrine)即仿照「歐洲安全暨合作會議」(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在亞洲成立區域論壇、討論亞洲安全議題,卻被中國學者批評是圍堵中國的煙霧彈。《紐約時報》於一九九三年報導,中國一名官員透露,中國軍方要求在《五年計劃》中增加國防預算,以便對付日本軍事力量上升。
中國最迫切的關切是日本與美國合作開發反彈道飛彈防禦系統。更進一步的中國評論亦強調日本取得核武和航空母艦的企圖。另外,中國分析家聲稱日本已有「具備航空母艦功能」的運輸艦。即使在核武議題上,某些中國分析家預測,未來的日本會像印度一樣成為核子國家。丁邦泉在中國軍事科學院刊物《世界軍事趨勢》撰文說:「毫無疑問,日本有能力製造核子彈……日本有辦法避開國際監督,就核武器進行祕密研究。」
【美國誤判中國對台灣的立場】
二○○九年,我的同僚和我仍然犯錯,以為中國人的想法和我們美國人一樣。我們對於中國對美國及其鄰國的新侵略性有所誤解,是因為它並不吻合我們既有的假設,也因為我們的中國線民一再向我們擔保,一系列似乎顯示中國愈來愈強悍的情節,並不是任何全盤計畫的一部分。並不是只有我一個人毫不懷疑中國。畢竟,我對中國馬拉松戰略的了解是,並沒有真正的急迫性要它趕著抵達終點,至少不是眼前當下。中國種種愈來愈強悍的行為似乎是隨機出現的獨立事件,美國為此辯論不休。中國的訊息是,沒有全盤模式或戰略把這些個別插曲連串起來。這個說法吻合早先的訊息:即中國並沒有大戰略。中國頂尖的美國事務專家王緝思就在《外交事務》雜誌發表文章如此說。
我的同僚和我認為理所當然的是,中國會盡一切代價避免挑釁美國霸權,以及至少還要花二十年工夫,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力量才足以懾服美國。這一切意味著,中國最不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對其鄰國和美國擺出侵略姿勢,壞了大事。可是,在二○一四年,美國政府官員卻告訴國會,中國已開始展現強悍的行為模式。為什麼我們花這麼久才明白這一點?
美國情報界和我沒看到中國愈來愈強悍的跡象,有一個原因,就是我們完全誤判了中國在台灣問題上表面立場放軟的意義。自從二○○○年代胡錦濤上台開始,中國避免以武力威脅台灣,改為重用更加軟性、更加間接的方式來影響台灣政府,其中大半是經濟手段。中國以這種方法已經打進台灣的朝野政黨、企業領袖、媒體和百姓。據說,胡錦濤私底下向他的親信顧問表示,「買下」台灣要比征服台灣來得容易、代價也較低。中國和台灣在二○○九年簽訂「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即ECFA)將兩岸經濟關係正常化,現在兩岸之間每週有將近七百班飛機來往,而二○一三年到台灣的大陸遊客達兩百八十萬人次。甚且,北京採取直接行動籠絡台灣企業菁英,許多人變成強烈支持兩岸和解。親中的台灣商人已買下台灣重要日報和電視台,因此使得北京可以影響傳媒,也有其他人得到中資挹注。
一直要到二○一三年秋天到北京訪問時,我才發覺我們錯得多離譜,以及中國是如何迅速動員,以便在他們認為的美國衰退當中爭上風。北京的天氣晴朗而冷冽,但是早晨的交通和平常一樣糟透了。在下了一星期的雨之後終於迎來好天氣,上百萬市民湧向城外。我不想遲到,錯過未來兩天在國賓酒店(位於美國大使館之西七英里)與五位中國將領及六十位安全事務專家的會議。我提前一小時出發,選擇經過天安門廣場,經過政治局的祕密會議中心。犯了大錯! 長安大街堵得動彈不得的車陣至少有一英里長。司機嘆氣,我請他右轉、沿著紫禁城的紅牆走,然後左轉取捷徑往北走。
我翻閱筆記,準備即將要參加的以中國話進行的當前軍事力量均衡的討論。我的辯論對手朱成虎將軍是中國最著名的鷹派將領之一,他在二○○五年因為披露中國針對美國攻擊,可以實施核子反擊的劇本,而躍登全球新聞頭條。這次會議的主題之一很合宜,就是未來的核子均勢,以及武器控制的前景。另一位鷹派彭光謙少將,是中國經典教科書《戰略論》的作者:他將討論如何評估權力平衡。中國的法學教授們將闡述北京對南海的權利主張。
司機把我及時送到會場,我分發以中、英文寫就的會議講話稿,上面新蓋官章,註明「經國防部長辦公室准予發布」。這篇講話旨在挑激兩天會議期間的反應,我在之前參加三次中國軍方會議時也用這套辦法,即中國人所謂的「拋磚引玉」。這次會議是難得的機會可以獲悉中國對未來三十五年馬拉松要如何進行的權威性觀點。有位中國投奔自由者曾經告訴過我關於百年馬拉松的一個故事:戰國時期的勝利就像一場長期、分為多個階段的圍棋賽。秦國歷七代國王才贏得最後霸主地位。一場圍棋通常約三百步,可分為布局、中盤、收官三階段。這個投奔自由者說,二○一四年的北京領導人認為他們仍處於中盤,這段期間中國的GDP已超越美國,但綜合國力仍不如美國。
我到北京開會是奉了華府命令,任務是設法了解在對付中國想超越美國的馬拉松戰略下,美國政府應做好什麼準備。中國軍中及政府研究機構的專家是如何設想馬拉松賽局? 我在往後兩天的許多對話都在探討這些問題。
我錯誤地估計中國「韜光養晦」的策略將會持續到二○四九年。我過去認為,唯有到那時候,中國才會自認有資格擔當世界領袖,寶劍出鞘,亮出它全球治理的計畫。我沒有預期到,當權力平衡愈來愈不利美國而傾斜時,會有一個階段性漸進作法。因此我發覺有個新劇本正在上演:即根據北京的估算,每當中、美勢力平衡出現對中國有利的傾斜時,中國將變得更加堅定。
另一個我很慢才發現中國正在加速邁進的原因是,我誤信中國的說法,認為它的大戰略固定,旨在誘使別人鬆懈大意。中國的學者和官方強調他們的目標是至少在二十年內還保持戰略上的耐心。許多美國學者從北京回國後告訴我,中國不認為在未來幾十年裡權力平衡將向中國傾斜。中國積極鼓吹這個觀點。從二○○九年中期起,中國共產黨黨校和中國國際關係研究院等智庫即舉辦一系列內部會議,辯論美國相對衰落對中國會有什麼影響。哈佛大學教授江憶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對這些會議的評論是:「比較溫和的聲音——那些認為並沒有權力大轉移的人士……在這些辯論中明顯並未居於守勢。換句話說,美國是否相對衰落、衰落程度多大這些問題︹在這時候︺並沒有得到解答。」他又說:「甚且,沒有證據顯示外交政策的核心決策團體在這一時期……接受權力分配已出現重大轉移、或讓中國有新機會推進其利益的說法。」
但是某些中國領導人得出結論:中國在百年馬拉松中已經進展超前。學者和情報官員開始談起中國起碼超前十年,也有可能超越進度二十年。中國領導人如今在辯論是否該做個戰術改變,立即衝刺達陣,結束這場馬拉松較勁。
不過,中國的行動還是十分謹慎——盡量不使霸主察覺到中國的戰略目標。每一件插曲都構成了中國外交政策上的得分;每一次中國侵略性的行為都產生巨大政治利益。雖然美國和中國的許多鄰國都抱怨,中國根本沒有因其行為付出代價。……
【美國誤判中國對台灣的立場】
二○○九年,我的同僚和我仍然犯錯,以為中國人的想法和我們美國人一樣。我們對於中國對美國及其鄰國的新侵略性有所誤解,是因為它並不吻合我們既有的假設,也因為我們的中國線民一再向我們擔保,一系列似乎顯示中國愈來愈強悍的情節,並不是任何全盤計畫的一部分。並不是只有我一個人毫不懷疑中國。畢竟,我對中國馬拉松戰略的了解是,並沒有真正的急迫性要它趕著抵達終點,至少不是眼前當下。中國種種愈來愈強悍的行為似乎是隨機出現的獨立事件,美國為此辯論不休。中國的訊息是,沒有全盤模式或戰略把這些個別插曲連串起來。這個說法吻合早先的訊息:即中國並沒有大戰略。中國頂尖的美國事務專家王緝思就在《外交事務》雜誌發表文章如此說。
我的同僚和我認為理所當然的是,中國會盡一切代價避免挑釁美國霸權,以及至少還要花二十年工夫,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力量才足以懾服美國。這一切意味著,中國最不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對其鄰國和美國擺出侵略姿勢,壞了大事。可是,在二○一四年,美國政府官員卻告訴國會,中國已開始展現強悍的行為模式。為什麼我們花這麼久才明白這一點?……
……有位中國投奔自由者曾經告訴過我關於百年馬拉松的一個故事:戰國時期的勝利就像一場長期、分為多個階段的圍棋賽。秦國歷七代國王才贏得最後霸主地位。一場圍棋通常約三百步,可分為布局、中盤、收官三階段。這個投奔自由者說,二○一四年的北京領導人認為他們仍處於中盤,這段期間中國的GDP已超越美國,但綜合國力仍不如美國。
我到北京開會是奉了華府命令,任務是設法了解在對付中國想超越美國的馬拉松戰略下,美國政府應做好什麼準備。中國軍中及政府研究機構的專家是如何設想馬拉松賽局? 我在往後兩天的許多對話都在探討這些問題。
我錯誤地估計中國「韜光養晦」的策略將會持續到二○四九年。我過去認為,唯有到那時候,中國才會自認有資格擔當世界領袖,寶劍出鞘,亮出它全球治理的計畫。我沒有預期到,當權力平衡愈來愈不利美國而傾斜時,會有一個階段性漸進作法。因此我發覺有個新劇本正在上演:即根據北京的估算,每當中、美勢力平衡出現對中國有利的傾斜時,中國將變得更加堅定。
另一個我很慢才發現中國正在加速邁進的原因是,我誤信中國的說法,認為它的大戰略固定,旨在誘使別人鬆懈大意。中國的學者和官方強調他們的目標是至少在二十年內還保持戰略上的耐心。許多美國學者從北京回國後告訴我,中國不認為在未來幾十年裡權力平衡將向中國傾斜。中國積極鼓吹這個觀點。從二○○九年中期起,中國共產黨黨校和中國國際關係研究院等智庫即舉辦一系列內部會議,辯論美國相對衰落對中國會有什麼影響。哈佛大學教授江憶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對這些會議的評論是:「比較溫和的聲音——那些認為並沒有權力大轉移的人士……在這些辯論中明顯並未居於守勢。換句話說,美國是否相對衰落、衰落程度多大這些問題︹在這時候︺並沒有得到解答。」他又說:「甚且,沒有證據顯示外交政策的核心決策團體在這一時期……接受權力分配已出現重大轉移、或讓中國有新機會推進其利益的說法。」
但是某些中國領導人得出結論:中國在百年馬拉松中已經進展超前。學者和情報官員開始談起中國起碼超前十年,也有可能超越進度二十年。中國領導人如今在辯論是否該做個戰術改變,立即衝刺達陣,結束這場馬拉松較勁。
不過,中國的行動還是十分謹慎——盡量不使霸主察覺到中國的戰略目標。每一件插曲都構成了中國外交政策上的得分;每一次中國侵略性的行為都產生巨大政治利益。雖然美國和中國的許多鄰國都抱怨,中國根本沒有因其行為付出代價。……
美國情報界和我沒看到中國愈來愈強悍的跡象,有一個原因,就是我們完全誤判了中國在台灣問題上表面立場放軟的意義。自從二○○○年代胡錦濤上台開始,中國避免以武力威脅台灣,改為重用更加軟性、更加間接的方式來影響台灣政府,其中大半是經濟手段。中國以這種方法已經打進台灣的朝野政黨、企業領袖、媒體和百姓。據說,胡錦濤私底下向他的親信顧問表示,「買下」台灣要比征服台灣來得容易、代價也較低。中國和台灣在二○○九年簽訂「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即ECFA)將兩岸經濟關係正常化,現在兩岸之間每週有將近七百班飛機來往,而二○一三年到台灣的大陸遊客達兩百八十萬人次。甚且,北京採取直接行動籠絡台灣企業菁英,許多人變成強烈支持兩岸和解。親中的台灣商人已買下台灣重要日報和電視台,因此使得北京可以影響傳媒,也有其他人得到中資挹注。
一直要到二○一三年秋天到北京訪問時,我才發覺我們錯得多離譜,以及中國是如何迅速動員,以便在他們認為的美國衰退當中爭上風。北京的天氣晴朗而冷冽,但是早晨的交通和平常一樣糟透了。在下了一星期的雨之後終於迎來好天氣,上百萬市民湧向城外。我不想遲到,錯過未來兩天在國賓酒店(位於美國大使館之西七英里)與五位中國將領及六十位安全事務專家的會議。我提前一小時出發,選擇經過天安門廣場,經過政治局的祕密會議中心。犯了大錯! 長安大街堵得動彈不得的車陣至少有一英里長。司機嘆氣,我請他右轉、沿著紫禁城的紅牆走,然後左轉取捷徑往北走。
我翻閱筆記,準備即將要參加的以中國話進行的當前軍事力量均衡的討論。我的辯論對手朱成虎將軍是中國最著名的鷹派將領之一,他在二○○五年因為披露中國針對美國攻擊,可以實施核子反擊的劇本,而躍登全球新聞頭條。這次會議的主題之一很合宜,就是未來的核子均勢,以及武器控制的前景。另一位鷹派彭光謙少將,是中國經典教科書《戰略論》的作者:他將討論如何評估權力平衡。中國的法學教授們將闡述北京對南海的權利主張。
司機把我及時送到會場,我分發以中、英文寫就的會議講話稿,上面新蓋官章,註明「經國防部長辦公室准予發布」。這篇講話旨在挑激兩天會議期間的反應,我在之前參加三次中國軍方會議時也用這套辦法,即中國人所謂的「拋磚引玉」。這次會議是難得的機會可以獲悉中國對未來三十五年馬拉松要如何進行的權威性觀點。有位中國投奔自由者曾經告訴過我關於百年馬拉松的一個故事:戰國時期的勝利就像一場長期、分為多個階段的圍棋賽。秦國歷七代國王才贏得最後霸主地位。一場圍棋通常約三百步,可分為布局、中盤、收官三階段。這個投奔自由者說,二○一四年的北京領導人認為他們仍處於中盤,這段期間中國的GDP已超越美國,但綜合國力仍不如美國。
我到北京開會是奉了華府命令,任務是設法了解在對付中國想超越美國的馬拉松戰略下,美國政府應做好什麼準備。中國軍中及政府研究機構的專家是如何設想馬拉松賽局? 我在往後兩天的許多對話都在探討這些問題。
我錯誤地估計中國「韜光養晦」的策略將會持續到二○四九年。我過去認為,唯有到那時候,中國才會自認有資格擔當世界領袖,寶劍出鞘,亮出它全球治理的計畫。我沒有預期到,當權力平衡愈來愈不利美國而傾斜時,會有一個階段性漸進作法。因此我發覺有個新劇本正在上演:即根據北京的估算,每當中、美勢力平衡出現對中國有利的傾斜時,中國將變得更加堅定。
另一個我很慢才發現中國正在加速邁進的原因是,我誤信中國的說法,認為它的大戰略固定,旨在誘使別人鬆懈大意。中國的學者和官方強調他們的目標是至少在二十年內還保持戰略上的耐心。許多美國學者從北京回國後告訴我,中國不認為在未來幾十年裡權力平衡將向中國傾斜。中國積極鼓吹這個觀點。從二○○九年中期起,中國共產黨黨校和中國國際關係研究院等智庫即舉辦一系列內部會議,辯論美國相對衰落對中國會有什麼影響。哈佛大學教授江憶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對這些會議的評論是:「比較溫和的聲音——那些認為並沒有權力大轉移的人士……在這些辯論中明顯並未居於守勢。換句話說,美國是否相對衰落、衰落程度多大這些問題︹在這時候︺並沒有得到解答。」他又說:「甚且,沒有證據顯示外交政策的核心決策團體在這一時期……接受權力分配已出現重大轉移、或讓中國有新機會推進其利益的說法。」
但是某些中國領導人得出結論:中國在百年馬拉松中已經進展超前。學者和情報官員開始談起中國起碼超前十年,也有可能超越進度二十年。中國領導人如今在辯論是否該做個戰術改變,立即衝刺達陣,結束這場馬拉松較勁。
不過,中國的行動還是十分謹慎——盡量不使霸主察覺到中國的戰略目標。每一件插曲都構成了中國外交政策上的得分;每一次中國侵略性的行為都產生巨大政治利益。雖然美國和中國的許多鄰國都抱怨,中國根本沒有因其行為付出代價。……
【天秤已經傾斜?】
中國在二○○七年摧毀自己一顆氣象衛星,是一連串警訊的第一槍——刻意挑釁和敵意似乎意在測試美國及盟國的決心,以及國際規範能接受的範圍——可是世界各國大多忽視、漠視或替它說情開脫。自從二○○七年以來,各種事件層出不窮、且益形囂張。因此,東亞局勢緊張升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最高點。
緊跟著反衛星測試之後,中國對美國及新上任的總統歐巴馬的口氣有了顯著改變。二○○九年十二月,歐巴馬總統親赴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全球一百九十二個國家在此集會,研訂全球應付氣候變遷的新政策。這次峰會顯示中國官員公開的論調出現顯著變化。他們展現出不必要的不禮貌,數度打斷西方外交官的發言,對討論沒有提供建設性的意見。溫家寶總理已經冷落其他政府首長,拒絕出席大多數的談判。中國讓觀察家大為意外,竟然與其他開發中國家另行訂定協議,把原本盼望的承諾封殺、無法列入氣候變遷協定草案,等於朝大會目標開了一槍。根據一位美國政府高階官員的說法,中國在大會閉幕前刻意安排一項會議,不邀歐巴馬總統出席,以便封殺美國的倡議。歐巴馬總統和希拉蕊.柯林頓國務卿聞訊,做了不速之客,逕自闖入會場。
台灣長久以來即是美國和中國爭執的重心之一,但是中國突然十分強硬在二○一○年一月抗議行之多年的對台軍售——歐巴馬政府核准六十四億美元的對台軍售案——引起對美、台關係的全面重新檢討,也對未來軍售投入疑雲。中國認為這項軍售案「明顯干預中國內政」,可謂是比北京過去的作法更強悍的反應。接下來,中國暫時停止和美國的軍事互動,也對銷售物資給台灣的幾家美國公司實施制裁。美國政府向這個壓力低頭,決定壓下出售先進的F-16戰鬥機給台灣的計畫,此舉招致國會議員的批評,議員指控政府是軟腳蝦、頂不住中方壓力。後來,歐巴馬政府又擴大美、中之間的軍事交流。
中國之所以態度轉為強悍,是因為中國領導人意識到「勢」已決定性地轉為對中國有利,而美國的相對衰落卻快得超乎他們原先預期。中國會有這種認知,有一部分原因是中國使用比較全面的尺度來衡量綜合國力。二○○八年和二○○九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源自華爾街,北京認為這是一個先兆。中國評論員認為美國的經濟將會復原,但絕不會與原來一樣。在未來的時代,全球經濟領導權勢必更加分散,減少依附美元。中國等到「勢」轉為有利才在國外強悍表現,這也反映中國遵守欲速則不達的戰略要素,即使必須等上幾十年也行。
二○一○年出現中國重新評估的跡象。中共中央委員會一名外交事務專家向中國領導人提出四頁的祕密報告。這份簡報旨在回答「我國未來十年面對的最重要外交政策挑戰是什麼?」這個問題。根據美國政府取得的筆記,這位專家的回答是「如何管理美國衰落」。他提到幾個戰術可用來達成此一目標。如果正確的話,他的報告暗示中國可望在十年內經濟超越美國。
認定美國衰落的另一個證據,在二○一二年出現:二○一一年美國國防大學出版一本權威專書《權力的弔詭:在弱勢時代的中、美戰略節制》(The Paradox of Power: Sino-American Strategic Restraint in an Age of Vulnerability),作者為龔培德(David C. ompert)和菲力浦.桑德斯(Phillip C. Saunders)。這份美國政府的研究聲稱,軍事平衡已偏向中國。中方的反應很有意思。中方翻譯並發行這本書,向外國訪客表示,他們不會接受政策節制的提議,但是欽佩這本書坦白承認美國軍力相對衰退,而中國在核力量、網路攻擊和太空武器上實力增長。中國官員告訴我,它的結論洩露天機。他們說,這本書顯示美國政府已認知到中國在改變區域軍事平衡上的成功,因而對中國的利益有利。許多中國政治和軍事人物其實很訝異,美國竟然評估中國已經變得這麼強。根據我二○一二年和二○一三年在北京聽到的評論,我的結論是這份研究無意間提供證據給中國軍官,他們原本已在辯論時機是否已經成熟,可以利用軍事均勢對中傾斜的有利條件。
我聽說,中國政府和軍方許多人不相信這本書的主張——「美國沒有胃口想要挫折中國崛起、以盟國和軍力包圍它,或啟動中美冷戰」。他們認為這種話怎麼能相信,它倒像是刻意要誘騙中國大意輕敵。可是他們很欣賞兩位作者評估軍事均勢已傾向中國。他們也很困惑,為什麼美國政府自曝其短,發布美國衰退的證據,究竟是什麼使得美國對「勢」做出悲觀的評估。我認為兩位作者的說法只代表他們個人主張,他們不肯採信。
在幾次會議中,我表示這本書只是兩位作者個人的建言,不是美國政府官方政策的聲明,卻招致中國軍官和學者的訕笑。他們笑說,他們知道其中一位作者是歐巴馬總統國安會中國事務重要幕僚麥艾文(Evan Medeiros)的好朋友,兩人經常聯名發表文章。在中國眼裡,另一位作者也非同小可:他曾經是美國全國情報總監丹尼斯.布萊爾(Dennis Blair)的副手;而布萊爾曾任美軍太平洋總部總司令。中方深信這是一個訊息,代表權力平衡已向中國傾斜,「勢」已經在變化。他們同意書中一個論點——在中國增進其核子報復能力之後,美國升高核戰以嚇阻中國進攻台灣的威脅「已經輕微、也將降低」。但是他們還是不解,美國為什麼要公布如此負面的發現。
我們可以理解,美國和中國對如何解讀權力平衡會有不同看法。畢竟兩國是在不同的戰略環境中運作,面對的威脅並不相同;因此他們在評估國力時不可能強調相同的因素。
五角大廈淨評估室主任安德魯.馬歇爾一九八二年撰文談到美、蘇兩國對超強之間戰略平衡的評估不同時,他說:
正確評估的戰略平衡必須建立在一個重要項目之上,即我們對蘇聯人自己評估的戰略平衡的最佳概算。但這不能只是美國式的標準估算然後再假設上略做調整而已……相反的,它應該是盡可能地以蘇聯式的規畫去規劃,再來進行評估,採用他們認為最有可能發生的劇本,以及他們衡量結果的判準和方法……蘇式評估很可能對劇本和目標有不同的假設,重點放在不同變數上……進行不同的估算、採用不同的效率尺標,並且或許採用不同的評估過程和方法。結果是蘇式評估可能和美式評估大不相同。
其次,除了大半出自主觀解讀得到結論之外,不同國家在權力平衡關係中的相對地位,可能只有在事後這些國家回頭評估時才能完全理解。英國大政治家博林布魯克勛爵(Lord Bolingbroke)曾經說過:
權力天秤轉變的確切點……靠一般觀察是感受不到的……位於天秤上升的一方不會立刻感覺到他們的實力,也不會有成功經驗在日後給予他們的那份信心。那些對權力平衡變化念茲在茲的人,經常會從同樣的偏見做出誤判。他們繼續害怕一個已經傷害不了他們的大國,或是繼續低估一個已經躍升的強權。
某些美國學者果真反映了權力平衡評估的主觀性,他們否認均勢已經傾斜或是在未來可能向中國傾斜的說法。塔夫茨大學麥可.貝克萊(Michael Beckley)在二○一一年主張:「美國並未衰退;事實上比起一九九一年,它現在更富裕、更創新,軍力更強過中國。」他說:「中國正在崛起,但還未趕上。」當然,這兩種考量都關係到中、美雙方對本身以及對對方實力的評估。
甚且,由於不同的國家對權力平衡有不同的評估,北京可能開始認為它早在美國承認之前就已經大幅領先了。在馬拉松競賽的最後幾十年裡,這可能造成相互的錯誤認知,很可能就導致戰爭。
摘錄自〈第十章 警鐘響起〉
【天秤已經傾斜?】
中國在二○○七年摧毀自己一顆氣象衛星,是一連串警訊的第一槍——刻意挑釁和敵意似乎意在測試美國及盟國的決心,以及國際規範能接受的範圍——可是世界各國大多忽視、漠視或替它說情開脫。自從二○○七年以來,各種事件層出不窮、且益形囂張。因此,東亞局勢緊張升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最高點。
緊跟著反衛星測試之後,中國對美國及新上任的總統歐巴馬的口氣有了顯著改變。二○○九年十二月,歐巴馬總統親赴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全球一百九十二個國家在此集會,研訂全球應付氣候變遷的新政策。這次峰會顯示中國官員公開的論調出現顯著變化。他們展現出不必要的不禮貌,數度打斷西方外交官的發言,對討論沒有提供建設性的意見。溫家寶總理已經冷落其他政府首長,拒絕出席大多數的談判。中國讓觀察家大為意外,竟然與其他開發中國家另行訂定協議,把原本盼望的承諾封殺、無法列入氣候變遷協定草案,等於朝大會目標開了一槍。根據一位美國政府高階官員的說法,中國在大會閉幕前刻意安排一項會議,不邀歐巴馬總統出席,以便封殺美國的倡議。歐巴馬總統和希拉蕊.柯林頓國務卿聞訊,做了不速之客,逕自闖入會場。
台灣長久以來即是美國和中國爭執的重心之一,但是中國突然十分強硬在二○一○年一月抗議行之多年的對台軍售——歐巴馬政府核准六十四億美元的對台軍售案——引起對美、台關係的全面重新檢討,也對未來軍售投入疑雲。中國認為這項軍售案「明顯干預中國內政」,可謂是比北京過去的作法更強悍的反應。接下來,中國暫時停止和美國的軍事互動,也對銷售物資給台灣的幾家美國公司實施制裁。美國政府向這個壓力低頭,決定壓下出售先進的F-16戰鬥機給台灣的計畫,此舉招致國會議員的批評,議員指控政府是軟腳蝦、頂不住中方壓力。後來,歐巴馬政府又擴大美、中之間的軍事交流。
中國之所以態度轉為強悍,是因為中國領導人意識到「勢」已決定性地轉為對中國有利,而美國的相對衰落卻快得超乎他們原先預期。中國會有這種認知,有一部分原因是中國使用比較全面的尺度來衡量綜合國力。二○○八年和二○○九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源自華爾街,北京認為這是一個先兆。中國評論員認為美國的經濟將會復原,但絕不會與原來一樣。在未來的時代,全球經濟領導權勢必更加分散,減少依附美元。中國等到「勢」轉為有利才在國外強悍表現,這也反映中國遵守欲速則不達的戰略要素,即使必須等上幾十年也行。
二○一○年出現中國重新評估的跡象。中共中央委員會一名外交事務專家向中國領導人提出四頁的祕密報告。這份簡報旨在回答「我國未來十年面對的最重要外交政策挑戰是什麼?」這個問題。根據美國政府取得的筆記,這位專家的回答是「如何管理美國衰落」。他提到幾個戰術可用來達成此一目標。如果正確的話,他的報告暗示中國可望在十年內經濟超越美國。
認定美國衰落的另一個證據,在二○一二年出現:二○一一年美國國防大學出版一本權威專書《權力的弔詭:在弱勢時代的中、美戰略節制》(The Paradox of Power: Sino-American Strategic Restraint in an Age of Vulnerability),作者為龔培德(David C. ompert)和菲力浦.桑德斯(Phillip C. Saunders)。這份美國政府的研究聲稱,軍事平衡已偏向中國。中方的反應很有意思。中方翻譯並發行這本書,向外國訪客表示,他們不會接受政策節制的提議,但是欽佩這本書坦白承認美國軍力相對衰退,而中國在核力量、網路攻擊和太空武器上實力增長。中國官員告訴我,它的結論洩露天機。他們說,這本書顯示美國政府已認知到中國在改變區域軍事平衡上的成功,因而對中國的利益有利。許多中國政治和軍事人物其實很訝異,美國竟然評估中國已經變得這麼強。根據我二○一二年和二○一三年在北京聽到的評論,我的結論是這份研究無意間提供證據給中國軍官,他們原本已在辯論時機是否已經成熟,可以利用軍事均勢對中傾斜的有利條件。
我聽說,中國政府和軍方許多人不相信這本書的主張——「美國沒有胃口想要挫折中國崛起、以盟國和軍力包圍它,或啟動中美冷戰」。他們認為這種話怎麼能相信,它倒像是刻意要誘騙中國大意輕敵。可是他們很欣賞兩位作者評估軍事均勢已傾向中國。他們也很困惑,為什麼美國政府自曝其短,發布美國衰退的證據,究竟是什麼使得美國對「勢」做出悲觀的評估。我認為兩位作者的說法只代表他們個人主張,他們不肯採信。
在幾次會議中,我表示這本書只是兩位作者個人的建言,不是美國政府官方政策的聲明,卻招致中國軍官和學者的訕笑。他們笑說,他們知道其中一位作者是歐巴馬總統國安會中國事務重要幕僚麥艾文(Evan Medeiros)的好朋友,兩人經常聯名發表文章。在中國眼裡,另一位作者也非同小可:他曾經是美國全國情報總監丹尼斯.布萊爾(Dennis Blair)的副手;而布萊爾曾任美軍太平洋總部總司令。中方深信這是一個訊息,代表權力平衡已向中國傾斜,「勢」已經在變化。他們同意書中一個論點——在中國增進其核子報復能力之後,美國升高核戰以嚇阻中國進攻台灣的威脅「已經輕微、也將降低」。但是他們還是不解,美國為什麼要公布如此負面的發現。
我們可以理解,美國和中國對如何解讀權力平衡會有不同看法。畢竟兩國是在不同的戰略環境中運作,面對的威脅並不相同;因此他們在評估國力時不可能強調相同的因素。
五角大廈淨評估室主任安德魯.馬歇爾一九八二年撰文談到美、蘇兩國對超強之間戰略平衡的評估不同時,他說:
正確評估的戰略平衡必須建立在一個重要項目之上,即我們對蘇聯人自己評估的戰略平衡的最佳概算。但這不能只是美國式的標準估算然後再假設上略做調整而已……相反的,它應該是盡可能地以蘇聯式的規畫去規劃,再來進行評估,採用他們認為最有可能發生的劇本,以及他們衡量結果的判準和方法……蘇式評估很可能對劇本和目標有不同的假設,重點放在不同變數上……進行不同的估算、採用不同的效率尺標,並且或許採用不同的評估過程和方法。結果是蘇式評估可能和美式評估大不相同。
其次,除了大半出自主觀解讀得到結論之外,不同國家在權力平衡關係中的相對地位,可能只有在事後這些國家回頭評估時才能完全理解。英國大政治家博林布魯克勛爵(Lord Bolingbroke)曾經說過:
權力天秤轉變的確切點……靠一般觀察是感受不到的……位於天秤上升的一方不會立刻感覺到他們的實力,也不會有成功經驗在日後給予他們的那份信心。那些對權力平衡變化念茲在茲的人,經常會從同樣的偏見做出誤判。他們繼續害怕一個已經傷害不了他們的大國,或是繼續低估一個已經躍升的強權。
某些美國學者果真反映了權力平衡評估的主觀性,他們否認均勢已經傾斜或是在未來可能向中國傾斜的說法。塔夫茨大學麥可.貝克萊(Michael Beckley)在二○一一年主張:「美國並未衰退;事實上比起一九九一年,它現在更富裕、更創新,軍力更強過中國。」他說:「中國正在崛起,但還未趕上。」當然,這兩種考量都關係到中、美雙方對本身以及對對方實力的評估。
甚且,由於不同的國家對權力平衡有不同的評估,北京可能開始認為它早在美國承認之前就已經大幅領先了。在馬拉松競賽的最後幾十年裡,這可能造成相互的錯誤認知,很可能就導致戰爭。
摘錄自〈第十章 警鐘響起〉
【天秤已經傾斜?】
中國之所以態度轉為強悍,是因為中國領導人意識到「勢」已決定性地轉為對中國有利,而美國的相對衰落卻快得超乎他們原先預期。中國會有這種認知,有一部分原因是中國使用比較全面的尺度來衡量綜合國力。二○○八年和二○○九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源自華爾街,北京認為這是一個先兆。中國評論員認為美國的經濟將會復原,但絕不會與原來一樣。在未來的時代,全球經濟領導權勢必更加分散,減少依附美元。中國等到「勢」轉為有利才在國外強悍表現,這也反映中國遵守欲速則不達的戰略要素,即使必須等上幾十年也行。
二○一○年出現中國重新評估的跡象。中共中央委員會一名外交事務專家向中國領導人提出四頁的祕密報告。這份簡報旨在回答「我國未來十年面對的最重要外交政策挑戰是什麼?」這個問題。根據美國政府取得的筆記,這位專家的回答是「如何管理美國衰落」。他提到幾個戰術可用來達成此一目標。如果正確的話,他的報告暗示中國可望在十年內經濟超越美國。
認定美國衰落的另一個證據,在二○一二年出現:二○一一年美國國防大學出版一本權威專書《權力的弔詭:在弱勢時代的中、美戰略節制》,作者為龔培德(David C. Gompert)和菲力浦.桑德斯(Phillip C. Saunders)。這份美國政府的研究聲稱,軍事平衡已偏向中國。中方的反應很有意思。中方翻譯並發行這本書,向外國訪客表示,他們不會接受政策節制的提議,但是欽佩這本書坦白承認美國軍力相對衰退,而中國在核力量、網路攻擊和太空武器上實力增長。中國官員告訴我,它的結論洩露天機。他們說,這本書顯示美國政府已認知到中國在改變區域軍事平衡上的成功,因而對中國的利益有利。許多中國政治和軍事人物其實很訝異,美國竟然評估中國已經變得這麼強。根據我二○一二年和二○一三年在北京聽到的評論,我的結論是這份研究無意間提供證據給中國軍官,他們原本已在辯論時機是否已經成熟,可以利用軍事均勢對中傾斜的有利條件。
我聽說,中國政府和軍方許多人不相信這本書的主張——「美國沒有胃口想要挫折中國崛起、以盟國和軍力包圍它,或啟動中美冷戰」。他們認為這種話怎麼能相信,它倒像是刻意要誘騙中國大意輕敵。可是他們很欣賞兩位作者評估軍事均勢已傾向中國。他們也很困惑,為什麼美國政府自曝其短,發布美國衰退的證據,究竟是什麼使得美國對「勢」做出悲觀的評估。我認為兩位作者的說法只代表他們個人主張,他們不肯採信。
在幾次會議中,我表示這本書只是兩位作者個人的建言,不是美國政府官方政策的聲明,卻招致中國軍官和學者的訕笑。他們笑說,他們知道其中一位作者是歐巴馬總統國安會中國事務重要幕僚麥艾文(Evan Medeiros)的好朋友,兩人經常聯名發表文章。在中國眼裡,另一位作者也非同小可:他曾經是美國全國情報總監丹尼斯.布萊爾(Dennis Blair)的副手;而布萊爾曾任美軍太平洋總部總司令。中方深信這是一個訊息,代表權力平衡已向中國傾斜,「勢」已經在變化。他們同意書中一個論點——在中國增進其核子報復能力之後,美國升高核戰以嚇阻中國進攻台灣的威脅「已經輕微、也將降低」。但是他們還是不解,美國為什麼要公布如此負面的發現。
我們可以理解,美國和中國對如何解讀權力平衡會有不同看法。畢竟兩國是在不同的戰略環境中運作,面對的威脅並不相同;因此他們在評估國力時不可能強調相同的因素。五角大廈淨評估室主任安德魯.馬歇爾一九八二年撰文談到美、蘇兩國對超強之間戰略平衡的評估不同時,他說:
正確評估的戰略平衡必須建立在一個重要項目之上,即我們對蘇聯人自己評估的戰略平衡的最佳概算。但這不能只是美國式的標準估算然後再假設上略做調整而已……相反的,它應該是盡可能地以蘇聯式的規畫去規劃,再來進行評估,採用他們認為最有可能發生的劇本,以及他們衡量結果的判準和方法……蘇式評估很可能對劇本和目標有不同的假設,重點放在不同變數上……進行不同的估算、採用不同的效率尺標,並且或許採用不同的評估過程和方法。結果是蘇式評估可能和美式評估大不相同。
其次,除了大半出自主觀解讀得到結論之外,不同國家在權力平衡關係中的相對地位,可能只有在事後這些國家回頭評估時才能完全理解。英國大政治家博林布魯克勛爵(Lord Bolingbroke)曾經說過:
權力天秤轉變的確切點……靠一般觀察是感受不到的……位於天秤上升的一方不會立刻感覺到他們的實力,也不會有成功經驗在日後給予他們的那份信心。那些對權力平衡變化念茲在茲的人,經常會從同樣的偏見做出誤判。他們繼續害怕一個已經傷害不了他們的大國,或是繼續低估一個已經躍升的強權。
某些美國學者果真反映了權力平衡評估的主觀性,他們否認均勢已經傾斜或是在未來可能向中國傾斜的說法。塔夫茨大學麥可.貝克萊(Michael Beckley)在二○一一年主張:「美國並未衰退;事實上比起一九九一年,它現在更富裕、更創新,軍力更強過中國。」他說:「中國正在崛起,但還未趕上。」當然,這兩種考量都關係到中、美雙方對本身以及對對方實力的評估。
甚且,由於不同的國家對權力平衡有不同的評估,北京可能開始認為它早在美國承認之前就已經大幅領先了。在馬拉松競賽的最後幾十年裡,這可能造成相互的錯誤認知,很可能就導致戰爭。
【中國與鄰國的緊張關係】
眼看著馬拉松勝利在望,中國人現在覺得比起以前更有空間耀武揚威,雖然同時也對他們的宏圖大計保持節制。他們在國境四周還有更緊迫的當務之急。中國周圍海域已經出現緊張局勢,南與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和汶萊有領土糾紛,東與日本也不平靖。
自從二○一○年以來,中國翻出塵封幾百年的地圖,想證明中國與東海、南海一些島礁有歷史淵源,因而提出領土主張。南海成為「熱點」,二○一○年五月與美國的高峰會議上,中國堅持對南沙群島的權利主張,把富含能源和漁業資源的數萬平方英里海洋納入其專屬經濟區,並把領海推進到靠近越南和菲律賓海岸地區。
希拉蕊.柯林頓國務卿表示美國願意調停中國及其南方鄰國之間的爭端,這惹來中國憤怒反應。接下來幾個月,中方不時騷擾越南和菲律賓船隻。菲律賓總統艾奎諾三世(Benigno S. Aquino III)把局勢比擬為一九三八年捷克面臨的危機:「什麼時候你該說:『夠了就是夠了』?世界必須說話了。大家必然記得,捷克割讓蘇台德地區(Sudetenland)是想要平息希特勒以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反駁艾奎諾的說法「暴露業餘政客本色」。
但是,中、日之間的緊張程度最高。某些中國作家認為日本人是「雜種民族」、是美國在亞洲的代理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殘暴占領中國留下的仇恨,迄今猶未緩解。在東海,由日本群島往西延伸的一系列島礁成為小衝突的場所,很有可能演化為全面海戰。……
……針對日本的抗議,中國外交部聲明:「日方無權做不負責任的評論,以及對中國惡意指控。我們呼籲日方停止傷害中國領土主權的所有行動。」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二○一四年一月在瑞士達沃斯的世界經濟論壇引起爭議,因為他把中、日之間在東海的爭議,拿來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德、英關係做比擬。大家都曉得,儘管德、英兩國經濟關係密切,猶如今天的中、日兩國,可是卻在一九一四年爆發戰爭。
日本會如何回應中國在其西邊水域日益上升的侵略性行為,將會是其馬拉松戰略的重要試金石。至少在過去二十年,北京將戰國列強削弱敵國之鷹派的作法,施用在日本之上。中國在亞洲各地發動反日的妖魔化運動,包括針對日本國內民眾宣傳。它的宗旨始終一致:日本的鷹派陰謀策劃恢復日本在一九三○年代的軍國主義,因此必須把他們揪出來,不能讓他們在政治上得勢。
為了妖魔化日本,中國發出的訊息是,它認為日本的財富,以及日本身為美國在亞洲主要盟國的地位,是從二戰不當得利的結果。倫敦政經學院教授文安立(Odd Arne Westad)稱這個現象是「有毒的、新形式的國家批准的反日民族主義」。「儒家文明圈」的國家應該接受中國天經地義的領導地位,不應該企圖復活舊帝國,或與美國這樣的外來霸權結盟。……
……中國對日本日益強悍,頗有可能對中國想贏得馬拉松的長期戰略有反效果——步步為營、謀定而後動的中國領導人若還忌憚美國霸權的話,應該不太可能挑釁美國在東亞最親近的盟友。中國若是與日本開戰,也可做為對抗美國的祕密鬥爭中的一場代理人戰爭——中國若能打擊日本,將進一步削弱已經衰落的霸主。……
……日本領導人已公開討論修訂日本的和平主義憲法——禁止採用武力解決國際爭端,只准維持自衛所需的低度兵力。通常日本人迴避不談它,但是現在卻坦率談論和中國的戰略競爭,以及中國在亞洲持續強悍的危險。中國對日本擴軍的可能性,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英、德海軍軍備競賽情勢再現的可能性,反應非常激烈。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對日本建設軍事力量並不是一直持負面觀點。一九七○年代中國鼓勵日本將防衛費用從GDP的百分之一提升到百分之三。一九七八年,鄧小平告訴日本訪問團,他「贊成日本自衛隊強化」。中國當時要拉攏一個新盟友對抗蘇聯。然而,十年之後,中國對「勢」的評估變了,一九八八年,鄧小平的國家安全顧問宦鄉強烈批評日本。……
……中共智庫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副所長陸忠偉指出:「在亞洲外交史上,從來沒有過強大的中國和強大的日本並存的先例。」中國社會科學院高恆也認為,美國的占領並沒有消除日本的軍國主義。他認為,甚至因為美國在占領期間希望利用日本對抗蘇聯、北朝鮮和中國,「它維持日本的整個國家機器和戰爭機器(不過改了名字)。」中國學者提到,日本「壓制中國的領土政策,並且干預中國對南沙群島和釣魚台的主權。」所謂的「宮澤主義」(Miyazawa doctrine)即仿照「歐洲安全暨合作會議」(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在亞洲成立區域論壇、討論亞洲安全議題,卻被中國學者批評是圍堵中國的煙霧彈。《紐約時報》於一九九三年報導,中國一名官員透露,中國軍方要求在《五年計劃》中增加國防預算,以便對付日本軍事力量上升。
中國最迫切的關切是日本與美國合作開發反彈道飛彈防禦系統。更進一步的中國評論亦強調日本取得核武和航空母艦的企圖。另外,中國分析家聲稱日本已有「具備航空母艦功能」的運輸艦。即使在核武議題上,某些中國分析家預測,未來的日本會像印度一樣成為核子國家。丁邦泉在中國軍事科學院刊物《世界軍事趨勢》撰文說:「毫無疑問,日本有能力製造核子彈……日本有辦法避開國際監督,就核武器進行祕密研究。」
【中國與鄰國的緊張關係】
眼看著馬拉松勝利在望,中國人現在覺得比起以前更有空間耀武揚威,雖然同時也對他們的宏圖大計保持節制。他們在國境四周還有更緊迫的當務之急。中國周圍海域已經出現緊張局勢,南與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和汶萊有領土糾紛,東與日本也不平靖。
自從二○一○年以來,中國翻出塵封幾百年的地圖,想證明中國與東海、南海一些島礁有歷史淵源,因而提出領土主張。南海成為「熱點」,二○一○年五月與美國的高峰會議上,中國堅持對南沙群島的權利主張,把富含能源和漁業資源的數萬平方英里海洋納入其專屬經濟區,並把領海推進到靠近越南和菲律賓海岸地區。
希拉蕊.柯林頓國務卿表示美國願意調停中國及其南方鄰國之間的爭端,這惹來中國憤怒反應。接下來幾個月,中方不時騷擾越南和菲律賓船隻。菲律賓總統艾奎諾三世(Benigno S. Aquino III)把局勢比擬為一九三八年捷克面臨的危機:「什麼時候你該說:『夠了就是夠了』?世界必須說話了。大家必然記得,捷克割讓蘇台德地區(Sudetenland)是想要平息希特勒以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反駁艾奎諾的說法「暴露業餘政客本色」。
但是,中、日之間的緊張程度最高。某些中國作家認為日本人是「雜種民族」、是美國在亞洲的代理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殘暴占領中國留下的仇恨,迄今猶未緩解。在東海,由日本群島往西延伸的一系列島礁成為小衝突的場所,很有可能演化為全面海戰。
二○一○年九月七日,中國一艘漁船在釣魚台/尖閣群島這個主權有爭議的海域,和日本巡邏船發生衝撞。中國船長和船員被日本海上警視廳扣押,不顧中國政府強力反對,帶回日本。中方阻擋一些稀土出口到日本以示不滿,並且以涉嫌擅闖中國軍事禁區之罪名,逮捕四名日本僑民。
兩年後,我很驚訝聽到六艘中國海監部隊船隻、分為兩隊,克服日本攔阻,闖進釣魚台海域。在此之前,中方宣稱其領海包括此一地區。我之所以驚訝是因為自此之後一連好幾個月,中國海監船增加在釣魚台/尖閣群島附近的巡邏,有時候中國漁船在本地區作業長達數星期,而且經常靠近到離釣魚台/尖閣群島十四英里以內。同時,當日本政府將釣魚台/尖閣群島地區幾個私人所有的島礁買下之後,中國各地爆發反日抗議。數千名抗議者包圍北京日本大使館,其餘團體則在數十個中國城市抗議、示威。中國政府鼓勵示威,廣播稱,「日本已侵犯中國權利,表達你的觀點是很自然的事。」
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國國防部宣布在東海設置防空識別區,逼使我們必須有所行動。固然日本、美國等國家過去都曾經宣布他們的防空識別區,中國不尋常的嚴格要求卻很突兀,因為它要求進入識別區的飛機不僅要表明身分,提供飛行計畫,還要與中國的防空識別區管理單位保持無線電聯絡。北京宣布後不久,我很高興美國國防部長查克.海格(Chuck Hagel)批准兩架B-52飛越防空識別區,以示美國不承認北京的要求。我向他建言,中方不會有反應的。
針對日本的抗議,中國外交部聲明:「日方無權做不負責任的評論,以及對中國惡意指控。我們呼籲日方停止傷害中國領土主權的所有行動。」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二○一四年一月在瑞士達沃斯的世界經濟論壇引起爭議,因為他把中、日之間在東海的爭議,拿來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德、英關係做比擬。大家都曉得,儘管德、英兩國經濟關係密切,猶如今天的中、日兩國,可是卻在一九一四年爆發戰爭。
日本會如何回應中國在其西邊水域日益上升的侵略性行為,將會是其馬拉松戰略的重要試金石。至少在過去二十年,北京將戰國列強削弱敵國之鷹派的作法,施用在日本之上。中國在亞洲各地發動反日的妖魔化運動,包括針對日本國內民眾宣傳。它的宗旨始終一致:日本的鷹派陰謀策劃恢復日本在一九三○年代的軍國主義,因此必須把他們揪出來,不能讓他們在政治上得勢。
為了妖魔化日本,中國發出的訊息是,它認為日本的財富,以及日本身為美國在亞洲主要盟國的地位,是從二戰不當得利的結果。倫敦政經學院教授文安立(Odd Arne Westad)稱這個現象是「有毒的、新形式的國家批准的反日民族主義」。「儒家文明圈」的國家應該接受中國天經地義的領導地位,不應該企圖復活舊帝國,或與美國這樣的外來霸權結盟。二○一三年八月,針對中、日兩國國民對彼此觀感的一項調查,有助於我們了解這些爭議。這項調查由中國的《中國日報》和日本的智庫《言論NPO》共同進行,向一千八百零五個日本人及一千五百四十個中國人調查他們對另一國家的觀點。調查發現,九成以上的中國受訪者對日本沒有好感,相較於一年前的調查結果(百分之六十二)出奇的高。同樣地,九成的日本受訪者對中國沒有好感,而一年前只有百分之八十四.三。這是過去九年來每年調查敵意最高的一次。被問到為什麼整體中、日敵意如此顯著上升時,許多受訪者表示,尖閣群島/釣魚台爭端是原因:百分之七十七.六的中方受訪者和百分之五三.二的日本受訪者認為島嶼爭端是他們相互仇視的主要原因。
其次一個最重要因素是歷史恩怨:百分之六三.八的中方受訪人認為「日本對於侵華歷史缺乏適切的道歉和懺悔」是他們對日本有負面觀點的原因之一。或許最不祥的發現是,有百分之五二.七的中國受訪者和百分之二三.七的日本受訪者認為,他們相信中、日之間將來還會爆發軍事衝突。
中國對日本日益強悍,頗有可能對中國想贏得馬拉松的長期戰略有反效果——步步為營、謀定而後動的中國領導人若還忌憚美國霸權的話,應該不太可能挑釁美國在東亞最親近的盟友。中國若是與日本開戰,也可做為對抗美國的祕密鬥爭中的一場代理人戰爭——中國若能打擊日本,將進一步削弱已經衰落的霸主。
二○一三年,有一部分是針對中國在東亞日益蠻橫之反應,美國和日本同意擴大他們的安全同盟,以便展現美國決心仍在本地區扮演主要角色。這項協議包括美國將派偵察機前往日本,預料將會在釣魚台/尖閣群島四周及整個繫爭島礁地區海域巡邏。美國國務卿約翰.凱瑞(John Kerry)和國防部長查克.海格親自前往東京簽署這項協定。固然美國拒絕在爭端中選邊,海格重申歐巴馬政府的保證:根據《美日安保條約》的規定,日本若遭到攻擊,美國有義務協助日本自衛,而它將包括釣魚台/尖閣群島。
日本領導人已公開討論修訂日本的和平主義憲法——禁止採用武力解決國際爭端,只准維持自衛所需的低度兵力。通常日本人迴避不談它,但是現在卻坦率談論和中國的戰略競爭,以及中國在亞洲持續強悍的危險。中國對日本擴軍的可能性,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英、德海軍軍備競賽情勢再現的可能性,反應非常激烈。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對日本建設軍事力量並不是一直持負面觀點。一九七○年代中國鼓勵日本將防衛費用從GDP的百分之一提升到百分之三。一九七八年,鄧小平告訴日本訪問團,他「贊成日本自衛隊強化」。中國當時要拉攏一個新盟友對抗蘇聯。然而,十年之後,中國對「勢」的評估變了,一九八八年,鄧小平的國家安全顧問宦鄉強烈批評日本。
中國對日本民主政治的穩定性有根深柢固的懷疑。許多中國學者認為,今天日本許多右派人士「想要修憲以恢復舊帝國制度」。中國分析家經常批評日本政客到靖國神社參拜;靖國神社是日本神道廟殿,供奉一八六七年至一九五一年的日本陣亡英靈,其中包括二戰期間的日本戰犯。這些分析家寫說,日本政客以參拜做為「精神動員,以便在中國進一步侵略擴張」。許多中國戰略學者相信,日本軍事力量增長必將成為「無法控制」。
日本軍國主義在未來可能復活,令中國憂慮。何新或許是中國最著名的極端民族主義作家、也是李鵬總理的顧問。他在一九八八年預測,日本對資源掠奪性的需求,將會使它企圖「殖民」中國。他說:「自從十九世紀以來,日本從來不曾放棄它長期以來的全球戰略目標……同時,就整體戰略布局而言,日本將完全瓜分及孤立中國。」
【中國與鄰國的緊張關係】
眼看著馬拉松勝利在望,中國人現在覺得比起以前更有空間耀武揚威,雖然同時也對他們的宏圖大計保持節制。他們在國境四周還有更緊迫的當務之急。中國周圍海域已經出現緊張局勢,南與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和汶萊有領土糾紛,東與日本也不平靖。
自從二○一○年以來,中國翻出塵封幾百年的地圖,想證明中國與東海、南海一些島礁有歷史淵源,因而提出領土主張。南海成為「熱點」,二○一○年五月與美國的高峰會議上,中國堅持對南沙群島的權利主張,把富含能源和漁業資源的數萬平方英里海洋納入其專屬經濟區,並把領海推進到靠近越南和菲律賓海岸地區。
希拉蕊.柯林頓國務卿表示美國願意調停中國及其南方鄰國之間的爭端,這惹來中國憤怒反應。接下來幾個月,中方不時騷擾越南和菲律賓船隻。菲律賓總統艾奎諾三世(Benigno S. Aquino III)把局勢比擬為一九三八年捷克面臨的危機:「什麼時候你該說:『夠了就是夠了』?世界必須說話了。大家必然記得,捷克割讓蘇台德地區(Sudetenland)是想要平息希特勒以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反駁艾奎諾的說法「暴露業餘政客本色」。
但是,中、日之間的緊張程度最高。某些中國作家認為日本人是「雜種民族」、是美國在亞洲的代理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殘暴占領中國留下的仇恨,迄今猶未緩解。在東海,由日本群島往西延伸的一系列島礁成為小衝突的場所,很有可能演化為全面海戰。
二○一○年九月七日,中國一艘漁船在釣魚台/尖閣群島這個主權有爭議的海域,和日本巡邏船發生衝撞。中國船長和船員被日本海上警視廳扣押,不顧中國政府強力反對,帶回日本。中方阻擋一些稀土出口到日本以示不滿,並且以涉嫌擅闖中國軍事禁區之罪名,逮捕四名日本僑民。
兩年後,我很驚訝聽到六艘中國海監部隊船隻、分為兩隊,克服日本攔阻,闖進釣魚台海域。在此之前,中方宣稱其領海包括此一地區。我之所以驚訝是因為自此之後一連好幾個月,中國海監船增加在釣魚台/尖閣群島附近的巡邏,有時候中國漁船在本地區作業長達數星期,而且經常靠近到離釣魚台/尖閣群島十四英里以內。同時,當日本政府將釣魚台/尖閣群島地區幾個私人所有的島礁買下之後,中國各地爆發反日抗議。數千名抗議者包圍北京日本大使館,其餘團體則在數十個中國城市抗議、示威。中國政府鼓勵示威,廣播稱,「日本已侵犯中國權利,表達你的觀點是很自然的事。」
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國國防部宣布在東海設置防空識別區,逼使我們必須有所行動。固然日本、美國等國家過去都曾經宣布他們的防空識別區,中國不尋常的嚴格要求卻很突兀,因為它要求進入識別區的飛機不僅要表明身分,提供飛行計畫,還要與中國的防空識別區管理單位保持無線電聯絡。北京宣布後不久,我很高興美國國防部長查克.海格(Chuck Hagel)批准兩架B-52飛越防空識別區,以示美國不承認北京的要求。我向他建言,中方不會有反應的。
針對日本的抗議,中國外交部聲明:「日方無權做不負責任的評論,以及對中國惡意指控。我們呼籲日方停止傷害中國領土主權的所有行動。」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二○一四年一月在瑞士達沃斯的世界經濟論壇引起爭議,因為他把中、日之間在東海的爭議,拿來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德、英關係做比擬。大家都曉得,儘管德、英兩國經濟關係密切,猶如今天的中、日兩國,可是卻在一九一四年爆發戰爭。
日本會如何回應中國在其西邊水域日益上升的侵略性行為,將會是其馬拉松戰略的重要試金石。至少在過去二十年,北京將戰國列強削弱敵國之鷹派的作法,施用在日本之上。中國在亞洲各地發動反日的妖魔化運動,包括針對日本國內民眾宣傳。它的宗旨始終一致:日本的鷹派陰謀策劃恢復日本在一九三○年代的軍國主義,因此必須把他們揪出來,不能讓他們在政治上得勢。
為了妖魔化日本,中國發出的訊息是,它認為日本的財富,以及日本身為美國在亞洲主要盟國的地位,是從二戰不當得利的結果。倫敦政經學院教授文安立(Odd Arne Westad)稱這個現象是「有毒的、新形式的國家批准的反日民族主義」。「儒家文明圈」的國家應該接受中國天經地義的領導地位,不應該企圖復活舊帝國,或與美國這樣的外來霸權結盟。二○一三年八月,針對中、日兩國國民對彼此觀感的一項調查,有助於我們了解這些爭議。這項調查由中國的《中國日報》和日本的智庫《言論NPO》共同進行,向一千八百零五個日本人及一千五百四十個中國人調查他們對另一國家的觀點。調查發現,九成以上的中國受訪者對日本沒有好感,相較於一年前的調查結果(百分之六十二)出奇的高。同樣地,九成的日本受訪者對中國沒有好感,而一年前只有百分之八十四.三。這是過去九年來每年調查敵意最高的一次。被問到為什麼整體中、日敵意如此顯著上升時,許多受訪者表示,尖閣群島/釣魚台爭端是原因:百分之七十七.六的中方受訪者和百分之五三.二的日本受訪者認為島嶼爭端是他們相互仇視的主要原因。
其次一個最重要因素是歷史恩怨:百分之六三.八的中方受訪人認為「日本對於侵華歷史缺乏適切的道歉和懺悔」是他們對日本有負面觀點的原因之一。或許最不祥的發現是,有百分之五二.七的中國受訪者和百分之二三.七的日本受訪者認為,他們相信中、日之間將來還會爆發軍事衝突。
中國對日本日益強悍,頗有可能對中國想贏得馬拉松的長期戰略有反效果——步步為營、謀定而後動的中國領導人若還忌憚美國霸權的話,應該不太可能挑釁美國在東亞最親近的盟友。中國若是與日本開戰,也可做為對抗美國的祕密鬥爭中的一場代理人戰爭——中國若能打擊日本,將進一步削弱已經衰落的霸主。
二○一三年,有一部分是針對中國在東亞日益蠻橫之反應,美國和日本同意擴大他們的安全同盟,以便展現美國決心仍在本地區扮演主要角色。這項協議包括美國將派偵察機前往日本,預料將會在釣魚台/尖閣群島四周及整個繫爭島礁地區海域巡邏。美國國務卿約翰.凱瑞(John Kerry)和國防部長查克.海格親自前往東京簽署這項協定。固然美國拒絕在爭端中選邊,海格重申歐巴馬政府的保證:根據《美日安保條約》的規定,日本若遭到攻擊,美國有義務協助日本自衛,而它將包括釣魚台/尖閣群島。
日本領導人已公開討論修訂日本的和平主義憲法——禁止採用武力解決國際爭端,只准維持自衛所需的低度兵力。通常日本人迴避不談它,但是現在卻坦率談論和中國的戰略競爭,以及中國在亞洲持續強悍的危險。中國對日本擴軍的可能性,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英、德海軍軍備競賽情勢再現的可能性,反應非常激烈。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對日本建設軍事力量並不是一直持負面觀點。一九七○年代中國鼓勵日本將防衛費用從GDP的百分之一提升到百分之三。一九七八年,鄧小平告訴日本訪問團,他「贊成日本自衛隊強化」。中國當時要拉攏一個新盟友對抗蘇聯。然而,十年之後,中國對「勢」的評估變了,一九八八年,鄧小平的國家安全顧問宦鄉強烈批評日本。
中國對日本民主政治的穩定性有根深柢固的懷疑。許多中國學者認為,今天日本許多右派人士「想要修憲以恢復舊帝國制度」。中國分析家經常批評日本政客到靖國神社參拜;靖國神社是日本神道廟殿,供奉一八六七年至一九五一年的日本陣亡英靈,其中包括二戰期間的日本戰犯。這些分析家寫說,日本政客以參拜做為「精神動員,以便在中國進一步侵略擴張」。許多中國戰略學者相信,日本軍事力量增長必將成為「無法控制」。
日本軍國主義在未來可能復活,令中國憂慮。何新或許是中國最著名的極端民族主義作家、也是李鵬總理的顧問。他在一九八八年預測,日本對資源掠奪性的需求,將會使它企圖「殖民」中國。他說:「自從十九世紀以來,日本從來不曾放棄它長期以來的全球戰略目標……同時,就整體戰略布局而言,日本將完全瓜分及孤立中國。」
接下來,中國在一九九五年呼籲美國關閉琉球(沖繩)的美軍基地,並且質疑在後冷戰的世界哪裡還需要《美日安保條約》。中國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研究員盧廣業(Lu Guangye,音譯)甚至警告說:「北約集團和日美軍事同盟已經成為助紂為虐的兩隻黑手。」
中共智庫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副所長陸忠偉指出:「在亞洲外交史上,從來沒有過強大的中國和強大的日本並存的先例。」中國社會科學院高恆也認為,美國的占領並沒有消除日本的軍國主義。他認為,甚至因為美國在占領期間希望利用日本對抗蘇聯、北朝鮮和中國,「它維持日本的整個國家機器和戰爭機器(不過改了名字)。」中國學者提到,日本「壓制中國的領土政策,並且干預中國對南沙群島和釣魚台的主權。」所謂的「宮澤主義」(Miyazawa doctrine)即仿照「歐洲安全暨合作會議」(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在亞洲成立區域論壇、討論亞洲安全議題,卻被中國學者批評是圍堵中國的煙霧彈。《紐約時報》於一九九三年報導,中國一名官員透露,中國軍方要求在《五年計劃》中增加國防預算,以便對付日本軍事力量上升。
中國最迫切的關切是日本與美國合作開發反彈道飛彈防禦系統。更進一步的中國評論亦強調日本取得核武和航空母艦的企圖。另外,中國分析家聲稱日本已有「具備航空母艦功能」的運輸艦。即使在核武議題上,某些中國分析家預測,未來的日本會像印度一樣成為核子國家。丁邦泉在中國軍事科學院刊物《世界軍事趨勢》撰文說:「毫無疑問,日本有能力製造核子彈……日本有辦法避開國際監督,就核武器進行祕密研究。」
【美國誤判中國對台灣的立場】
二○○九年,我的同僚和我仍然犯錯,以為中國人的想法和我們美國人一樣。我們對於中國對美國及其鄰國的新侵略性有所誤解,是因為它並不吻合我們既有的假設,也因為我們的中國線民一再向我們擔保,一系列似乎顯示中國愈來愈強悍的情節,並不是任何全盤計畫的一部分。並不是只有我一個人毫不懷疑中國。畢竟,我對中國馬拉松戰略的了解是,並沒有真正的急迫性要它趕著抵達終點,至少不是眼前當下。中國種種愈來愈強悍的行為似乎是隨機出現的獨立事件,美國為此辯論不休。中國的訊息是,沒有全盤模式或戰略把這些個別插曲連串起來。這個說法吻合早先的訊息:即中國並沒有大戰略。中國頂尖的美國事務專家王緝思就在《外交事務》雜誌發表文章如此說。
我的同僚和我認為理所當然的是,中國會盡一切代價避免挑釁美國霸權,以及至少還要花二十年工夫,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力量才足以懾服美國。這一切意味著,中國最不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對其鄰國和美國擺出侵略姿勢,壞了大事。可是,在二○一四年,美國政府官員卻告訴國會,中國已開始展現強悍的行為模式。為什麼我們花這麼久才明白這一點?
接下來,中國在一九九五年呼籲美國關閉琉球(沖繩)的美軍基地,並且質疑在後冷戰的世界哪裡還需要《美日安保條約》。中國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研究員盧廣業(Lu Guangye,音譯)甚至警告說:「北約集團和日美軍事同盟已經成為助紂為虐的兩隻黑手。」
中共智庫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副所長陸忠偉指出:「在亞洲外交史上,從來沒有過強大的中國和強大的日本並存的先例。」中國社會科學院高恆也認為,美國的占領並沒有消除日本的軍國主義。他認為,甚至因為美國在占領期間希望利用日本對抗蘇聯、北朝鮮和中國,「它維持日本的整個國家機器和戰爭機器(不過改了名字)。」中國學者提到,日本「壓制中國的領土政策,並且干預中國對南沙群島和釣魚台的主權。」所謂的「宮澤主義」(Miyazawa doctrine)即仿照「歐洲安全暨合作會議」(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在亞洲成立區域論壇、討論亞洲安全議題,卻被中國學者批評是圍堵中國的煙霧彈。《紐約時報》於一九九三年報導,中國一名官員透露,中國軍方要求在《五年計劃》中增加國防預算,以便對付日本軍事力量上升。
中國最迫切的關切是日本與美國合作開發反彈道飛彈防禦系統。更進一步的中國評論亦強調日本取得核武和航空母艦的企圖。另外,中國分析家聲稱日本已有「具備航空母艦功能」的運輸艦。即使在核武議題上,某些中國分析家預測,未來的日本會像印度一樣成為核子國家。丁邦泉在中國軍事科學院刊物《世界軍事趨勢》撰文說:「毫無疑問,日本有能力製造核子彈……日本有辦法避開國際監督,就核武器進行祕密研究。」
【美國誤判中國對台灣的立場】
二○○九年,我的同僚和我仍然犯錯,以為中國人的想法和我們美國人一樣。我們對於中國對美國及其鄰國的新侵略性有所誤解,是因為它並不吻合我們既有的假設,也因為我們的中國線民一再向我們擔保,一系列似乎顯示中國愈來愈強悍的情節,並不是任何全盤計畫的一部分。並不是只有我一個人毫不懷疑中國。畢竟,我對中國馬拉松戰略的了解是,並沒有真正的急迫性要它趕著抵達終點,至少不是眼前當下。中國種種愈來愈強悍的行為似乎是隨機出現的獨立事件,美國為此辯論不休。中國的訊息是,沒有全盤模式或戰略把這些個別插曲連串起來。這個說法吻合早先的訊息:即中國並沒有大戰略。中國頂尖的美國事務專家王緝思就在《外交事務》雜誌發表文章如此說。
我的同僚和我認為理所當然的是,中國會盡一切代價避免挑釁美國霸權,以及至少還要花二十年工夫,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力量才足以懾服美國。這一切意味著,中國最不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對其鄰國和美國擺出侵略姿勢,壞了大事。可是,在二○一四年,美國政府官員卻告訴國會,中國已開始展現強悍的行為模式。為什麼我們花這麼久才明白這一點?
美國情報界和我沒看到中國愈來愈強悍的跡象,有一個原因,就是我們完全誤判了中國在台灣問題上表面立場放軟的意義。自從二○○○年代胡錦濤上台開始,中國避免以武力威脅台灣,改為重用更加軟性、更加間接的方式來影響台灣政府,其中大半是經濟手段。中國以這種方法已經打進台灣的朝野政黨、企業領袖、媒體和百姓。據說,胡錦濤私底下向他的親信顧問表示,「買下」台灣要比征服台灣來得容易、代價也較低。中國和台灣在二○○九年簽訂「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即ECFA)將兩岸經濟關係正常化,現在兩岸之間每週有將近七百班飛機來往,而二○一三年到台灣的大陸遊客達兩百八十萬人次。甚且,北京採取直接行動籠絡台灣企業菁英,許多人變成強烈支持兩岸和解。親中的台灣商人已買下台灣重要日報和電視台,因此使得北京可以影響傳媒,也有其他人得到中資挹注。
一直要到二○一三年秋天到北京訪問時,我才發覺我們錯得多離譜,以及中國是如何迅速動員,以便在他們認為的美國衰退當中爭上風。北京的天氣晴朗而冷冽,但是早晨的交通和平常一樣糟透了。在下了一星期的雨之後終於迎來好天氣,上百萬市民湧向城外。我不想遲到,錯過未來兩天在國賓酒店(位於美國大使館之西七英里)與五位中國將領及六十位安全事務專家的會議。我提前一小時出發,選擇經過天安門廣場,經過政治局的祕密會議中心。犯了大錯! 長安大街堵得動彈不得的車陣至少有一英里長。司機嘆氣,我請他右轉、沿著紫禁城的紅牆走,然後左轉取捷徑往北走。
我翻閱筆記,準備即將要參加的以中國話進行的當前軍事力量均衡的討論。我的辯論對手朱成虎將軍是中國最著名的鷹派將領之一,他在二○○五年因為披露中國針對美國攻擊,可以實施核子反擊的劇本,而躍登全球新聞頭條。這次會議的主題之一很合宜,就是未來的核子均勢,以及武器控制的前景。另一位鷹派彭光謙少將,是中國經典教科書《戰略論》的作者:他將討論如何評估權力平衡。中國的法學教授們將闡述北京對南海的權利主張。
司機把我及時送到會場,我分發以中、英文寫就的會議講話稿,上面新蓋官章,註明「經國防部長辦公室准予發布」。這篇講話旨在挑激兩天會議期間的反應,我在之前參加三次中國軍方會議時也用這套辦法,即中國人所謂的「拋磚引玉」。這次會議是難得的機會可以獲悉中國對未來三十五年馬拉松要如何進行的權威性觀點。有位中國投奔自由者曾經告訴過我關於百年馬拉松的一個故事:戰國時期的勝利就像一場長期、分為多個階段的圍棋賽。秦國歷七代國王才贏得最後霸主地位。一場圍棋通常約三百步,可分為布局、中盤、收官三階段。這個投奔自由者說,二○一四年的北京領導人認為他們仍處於中盤,這段期間中國的GDP已超越美國,但綜合國力仍不如美國。
我到北京開會是奉了華府命令,任務是設法了解在對付中國想超越美國的馬拉松戰略下,美國政府應做好什麼準備。中國軍中及政府研究機構的專家是如何設想馬拉松賽局? 我在往後兩天的許多對話都在探討這些問題。
我錯誤地估計中國「韜光養晦」的策略將會持續到二○四九年。我過去認為,唯有到那時候,中國才會自認有資格擔當世界領袖,寶劍出鞘,亮出它全球治理的計畫。我沒有預期到,當權力平衡愈來愈不利美國而傾斜時,會有一個階段性漸進作法。因此我發覺有個新劇本正在上演:即根據北京的估算,每當中、美勢力平衡出現對中國有利的傾斜時,中國將變得更加堅定。
另一個我很慢才發現中國正在加速邁進的原因是,我誤信中國的說法,認為它的大戰略固定,旨在誘使別人鬆懈大意。中國的學者和官方強調他們的目標是至少在二十年內還保持戰略上的耐心。許多美國學者從北京回國後告訴我,中國不認為在未來幾十年裡權力平衡將向中國傾斜。中國積極鼓吹這個觀點。從二○○九年中期起,中國共產黨黨校和中國國際關係研究院等智庫即舉辦一系列內部會議,辯論美國相對衰落對中國會有什麼影響。哈佛大學教授江憶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對這些會議的評論是:「比較溫和的聲音——那些認為並沒有權力大轉移的人士……在這些辯論中明顯並未居於守勢。換句話說,美國是否相對衰落、衰落程度多大這些問題︹在這時候︺並沒有得到解答。」他又說:「甚且,沒有證據顯示外交政策的核心決策團體在這一時期……接受權力分配已出現重大轉移、或讓中國有新機會推進其利益的說法。」
但是某些中國領導人得出結論:中國在百年馬拉松中已經進展超前。學者和情報官員開始談起中國起碼超前十年,也有可能超越進度二十年。中國領導人如今在辯論是否該做個戰術改變,立即衝刺達陣,結束這場馬拉松較勁。
不過,中國的行動還是十分謹慎——盡量不使霸主察覺到中國的戰略目標。每一件插曲都構成了中國外交政策上的得分;每一次中國侵略性的行為都產生巨大政治利益。雖然美國和中國的許多鄰國都抱怨,中國根本沒有因其行為付出代價。……
【美國誤判中國對台灣的立場】
二○○九年,我的同僚和我仍然犯錯,以為中國人的想法和我們美國人一樣。我們對於中國對美國及其鄰國的新侵略性有所誤解,是因為它並不吻合我們既有的假設,也因為我們的中國線民一再向我們擔保,一系列似乎顯示中國愈來愈強悍的情節,並不是任何全盤計畫的一部分。並不是只有我一個人毫不懷疑中國。畢竟,我對中國馬拉松戰略的了解是,並沒有真正的急迫性要它趕著抵達終點,至少不是眼前當下。中國種種愈來愈強悍的行為似乎是隨機出現的獨立事件,美國為此辯論不休。中國的訊息是,沒有全盤模式或戰略把這些個別插曲連串起來。這個說法吻合早先的訊息:即中國並沒有大戰略。中國頂尖的美國事務專家王緝思就在《外交事務》雜誌發表文章如此說。
我的同僚和我認為理所當然的是,中國會盡一切代價避免挑釁美國霸權,以及至少還要花二十年工夫,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力量才足以懾服美國。這一切意味著,中國最不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對其鄰國和美國擺出侵略姿勢,壞了大事。可是,在二○一四年,美國政府官員卻告訴國會,中國已開始展現強悍的行為模式。為什麼我們花這麼久才明白這一點?……
……有位中國投奔自由者曾經告訴過我關於百年馬拉松的一個故事:戰國時期的勝利就像一場長期、分為多個階段的圍棋賽。秦國歷七代國王才贏得最後霸主地位。一場圍棋通常約三百步,可分為布局、中盤、收官三階段。這個投奔自由者說,二○一四年的北京領導人認為他們仍處於中盤,這段期間中國的GDP已超越美國,但綜合國力仍不如美國。
我到北京開會是奉了華府命令,任務是設法了解在對付中國想超越美國的馬拉松戰略下,美國政府應做好什麼準備。中國軍中及政府研究機構的專家是如何設想馬拉松賽局? 我在往後兩天的許多對話都在探討這些問題。
我錯誤地估計中國「韜光養晦」的策略將會持續到二○四九年。我過去認為,唯有到那時候,中國才會自認有資格擔當世界領袖,寶劍出鞘,亮出它全球治理的計畫。我沒有預期到,當權力平衡愈來愈不利美國而傾斜時,會有一個階段性漸進作法。因此我發覺有個新劇本正在上演:即根據北京的估算,每當中、美勢力平衡出現對中國有利的傾斜時,中國將變得更加堅定。
另一個我很慢才發現中國正在加速邁進的原因是,我誤信中國的說法,認為它的大戰略固定,旨在誘使別人鬆懈大意。中國的學者和官方強調他們的目標是至少在二十年內還保持戰略上的耐心。許多美國學者從北京回國後告訴我,中國不認為在未來幾十年裡權力平衡將向中國傾斜。中國積極鼓吹這個觀點。從二○○九年中期起,中國共產黨黨校和中國國際關係研究院等智庫即舉辦一系列內部會議,辯論美國相對衰落對中國會有什麼影響。哈佛大學教授江憶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對這些會議的評論是:「比較溫和的聲音——那些認為並沒有權力大轉移的人士……在這些辯論中明顯並未居於守勢。換句話說,美國是否相對衰落、衰落程度多大這些問題︹在這時候︺並沒有得到解答。」他又說:「甚且,沒有證據顯示外交政策的核心決策團體在這一時期……接受權力分配已出現重大轉移、或讓中國有新機會推進其利益的說法。」
但是某些中國領導人得出結論:中國在百年馬拉松中已經進展超前。學者和情報官員開始談起中國起碼超前十年,也有可能超越進度二十年。中國領導人如今在辯論是否該做個戰術改變,立即衝刺達陣,結束這場馬拉松較勁。
不過,中國的行動還是十分謹慎——盡量不使霸主察覺到中國的戰略目標。每一件插曲都構成了中國外交政策上的得分;每一次中國侵略性的行為都產生巨大政治利益。雖然美國和中國的許多鄰國都抱怨,中國根本沒有因其行為付出代價。……
美國情報界和我沒看到中國愈來愈強悍的跡象,有一個原因,就是我們完全誤判了中國在台灣問題上表面立場放軟的意義。自從二○○○年代胡錦濤上台開始,中國避免以武力威脅台灣,改為重用更加軟性、更加間接的方式來影響台灣政府,其中大半是經濟手段。中國以這種方法已經打進台灣的朝野政黨、企業領袖、媒體和百姓。據說,胡錦濤私底下向他的親信顧問表示,「買下」台灣要比征服台灣來得容易、代價也較低。中國和台灣在二○○九年簽訂「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即ECFA)將兩岸經濟關係正常化,現在兩岸之間每週有將近七百班飛機來往,而二○一三年到台灣的大陸遊客達兩百八十萬人次。甚且,北京採取直接行動籠絡台灣企業菁英,許多人變成強烈支持兩岸和解。親中的台灣商人已買下台灣重要日報和電視台,因此使得北京可以影響傳媒,也有其他人得到中資挹注。
一直要到二○一三年秋天到北京訪問時,我才發覺我們錯得多離譜,以及中國是如何迅速動員,以便在他們認為的美國衰退當中爭上風。北京的天氣晴朗而冷冽,但是早晨的交通和平常一樣糟透了。在下了一星期的雨之後終於迎來好天氣,上百萬市民湧向城外。我不想遲到,錯過未來兩天在國賓酒店(位於美國大使館之西七英里)與五位中國將領及六十位安全事務專家的會議。我提前一小時出發,選擇經過天安門廣場,經過政治局的祕密會議中心。犯了大錯! 長安大街堵得動彈不得的車陣至少有一英里長。司機嘆氣,我請他右轉、沿著紫禁城的紅牆走,然後左轉取捷徑往北走。
我翻閱筆記,準備即將要參加的以中國話進行的當前軍事力量均衡的討論。我的辯論對手朱成虎將軍是中國最著名的鷹派將領之一,他在二○○五年因為披露中國針對美國攻擊,可以實施核子反擊的劇本,而躍登全球新聞頭條。這次會議的主題之一很合宜,就是未來的核子均勢,以及武器控制的前景。另一位鷹派彭光謙少將,是中國經典教科書《戰略論》的作者:他將討論如何評估權力平衡。中國的法學教授們將闡述北京對南海的權利主張。
司機把我及時送到會場,我分發以中、英文寫就的會議講話稿,上面新蓋官章,註明「經國防部長辦公室准予發布」。這篇講話旨在挑激兩天會議期間的反應,我在之前參加三次中國軍方會議時也用這套辦法,即中國人所謂的「拋磚引玉」。這次會議是難得的機會可以獲悉中國對未來三十五年馬拉松要如何進行的權威性觀點。有位中國投奔自由者曾經告訴過我關於百年馬拉松的一個故事:戰國時期的勝利就像一場長期、分為多個階段的圍棋賽。秦國歷七代國王才贏得最後霸主地位。一場圍棋通常約三百步,可分為布局、中盤、收官三階段。這個投奔自由者說,二○一四年的北京領導人認為他們仍處於中盤,這段期間中國的GDP已超越美國,但綜合國力仍不如美國。
我到北京開會是奉了華府命令,任務是設法了解在對付中國想超越美國的馬拉松戰略下,美國政府應做好什麼準備。中國軍中及政府研究機構的專家是如何設想馬拉松賽局? 我在往後兩天的許多對話都在探討這些問題。
我錯誤地估計中國「韜光養晦」的策略將會持續到二○四九年。我過去認為,唯有到那時候,中國才會自認有資格擔當世界領袖,寶劍出鞘,亮出它全球治理的計畫。我沒有預期到,當權力平衡愈來愈不利美國而傾斜時,會有一個階段性漸進作法。因此我發覺有個新劇本正在上演:即根據北京的估算,每當中、美勢力平衡出現對中國有利的傾斜時,中國將變得更加堅定。
另一個我很慢才發現中國正在加速邁進的原因是,我誤信中國的說法,認為它的大戰略固定,旨在誘使別人鬆懈大意。中國的學者和官方強調他們的目標是至少在二十年內還保持戰略上的耐心。許多美國學者從北京回國後告訴我,中國不認為在未來幾十年裡權力平衡將向中國傾斜。中國積極鼓吹這個觀點。從二○○九年中期起,中國共產黨黨校和中國國際關係研究院等智庫即舉辦一系列內部會議,辯論美國相對衰落對中國會有什麼影響。哈佛大學教授江憶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對這些會議的評論是:「比較溫和的聲音——那些認為並沒有權力大轉移的人士……在這些辯論中明顯並未居於守勢。換句話說,美國是否相對衰落、衰落程度多大這些問題︹在這時候︺並沒有得到解答。」他又說:「甚且,沒有證據顯示外交政策的核心決策團體在這一時期……接受權力分配已出現重大轉移、或讓中國有新機會推進其利益的說法。」
但是某些中國領導人得出結論:中國在百年馬拉松中已經進展超前。學者和情報官員開始談起中國起碼超前十年,也有可能超越進度二十年。中國領導人如今在辯論是否該做個戰術改變,立即衝刺達陣,結束這場馬拉松較勁。
不過,中國的行動還是十分謹慎——盡量不使霸主察覺到中國的戰略目標。每一件插曲都構成了中國外交政策上的得分;每一次中國侵略性的行為都產生巨大政治利益。雖然美國和中國的許多鄰國都抱怨,中國根本沒有因其行為付出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