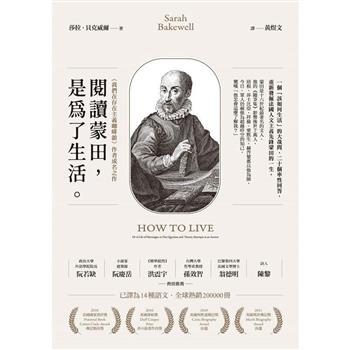問題:如何生活?(節錄)
二十一世紀到處可見不吝於表現自我的人。如果你上網瀏覽部落格、推特、YouTube、臉書與一些個人網頁,你會發現在這片網路大海裡可以捕撈到數千名有趣的人物,他們使出千奇百怪的手法,只為了吸引瀏覽者的注意。這些人持之以恆地談論自己;他們每天貼文,在網上聊天,把自己做的每件事拍照上傳。他們一方面展現出無拘無束、活潑外向的性格,另一方面也顯現出少見的反思與內省。
以文字描述自己可以創造出一面鏡子,旁人可以藉由這面鏡子看出自己的人性,這種想法的產生並非理所當然,它是被創造出來的,且可以追溯到某個人身上,那就是米歇爾.艾坎.德.蒙田。蒙田是貴族、政府官員與葡萄莊園園主,生於一五三三年,卒於一五九二年,他一直生活在法國西南部的佩里戈爾地區。他平安度過混亂時代,管理自己的家產,以法官身分審理法院案件,曾治理過波爾多,並且成為該市有史以來最隨和的市長。
蒙田總共寫了一百零七篇隨筆,有些只有一兩頁的篇幅,有些則屬長篇。這些隨筆很少解釋或教導任何事物。蒙田把自己呈現成一個腦子裡想到什麼就匆匆記下的人,隨時振筆疾書,不斷捕捉心靈的感受與狀態。他以這些經驗做為向自己提問的根據,特別是某個讓他深感興趣、同時是當時人們關注的大問題,我們可以用幾個簡單的字來表達這個問題:「如何生活?」
這個問題不同於「應該如何生活」這類倫理問題。蒙田固然對道德兩難的問題感興趣,但他關心的不是人應該做什麼,而是人實際上做了什麼。
他描述了一切足以讓我們感同身受的細節,有時還遠超過我們需要的程度。蒙田無來由地告訴我們:他唯一喜歡的水果是瓜類;他喜歡躺著做愛,不喜歡站著做愛;他不會唱歌;他喜歡活潑的朋友,機智的問答總能讓他雀躍不已。但蒙田也描述了一些言語難以形容、甚至難以察覺的感覺:懶惰、勇氣或猶豫不決是什麼感覺;愛慕虛榮、想改掉過於膽小的毛病又是什麼感覺。他甚至描述了單純活著是什麼感覺。
蒙田花了二十多年的時間探索這些現象,他不斷質問自己,並且建立自我的形象──這是一幅不斷變動的自畫像,讀者感受到的是一個活生生的蒙田,彷彿他就坐在你身旁,注視著你的一舉一動。他能說出令人驚奇的話語。蒙田出生的時間距今已近五百年,在這漫長的歲月裡,許多事物改變了,無論風俗還是信仰恐怕都已難以辨識;然而閱讀蒙田的作品卻能讓人經歷一連串熟悉的震撼,二十一世紀的讀者將驚覺蒙田與他們之間幾乎不存在任何隔閡。
無論是蒙田的時代還是我們的時代,這種從他人身上看到自己的感覺總會讓人興奮不已。十六世紀蒙田的崇拜者阿寇德曾說,凡是讀過蒙田《隨筆集》的人都會產生一種錯覺,以為這些文章是他們自己寫的。二十世紀小說家紀德說:「我幾乎要把蒙田的傑作當成自己的作品了,他簡直就是另一個我。」斯蒂芬.褚威格這名奧國作家在二次大戰期間被迫流亡,曾一度瀕臨自殺邊緣,他發現蒙田是他唯一真正的朋友:「這裡的『你』反映出我的『我』,此刻一切距離都泯除了。」書頁上的鉛字漸漸模糊,換得活生生的人走入房內。「四百年就像輕煙般消散無蹤。」
這些感想的產生有跡可循,因為《隨筆集》並不宣揚偉大的意義,也沒有核心的本旨,更沒有需要發展的論點。《隨筆集》並未要求讀者該如何閱讀它:你愛怎麼讀就怎麼讀。蒙田盡情傾洩自己的想法,從不擔心自己在某頁說了某事,到了下頁乃至於下一句又說出完全相反的觀點。蒙田應該會把惠特曼這幾行詩當成自己的座右銘:
我自相矛盾嗎?
很好,那麼我就是自相矛盾,
(我心胸寬大,能夠包容各種不同的說法。)
本書是一部談論蒙田這個人與這名作者的作品。本書也討論蒙田舉辦的這場漫長宴會──四百三十年來不斷累積的共同與私人對話。這趟旅程將是古怪而顛簸的,因為蒙田的作品在每個時代的遭遇並不平順。我的故事將隨著這些潮流行進,它也將「昏昏沉沉、跌跌撞撞」,經常地轉變航向。
絕大多數閱讀《隨筆集》的讀者總想從中得到一些收穫。他們也許在尋找樂子,或尋求啟發,或歷史的理解,或某種純屬個人的啟悟。小說家福樓拜的朋友對於該如何閱讀蒙田感到苦惱,而他的建議是:
不要像孩子一樣想從中得到樂趣,也不要像野心家一樣想從中得到指示。你閱讀他的目的只有一個:「為了生活」。
這個問題將貫串全書,章節將採取二十種解答的形式來表現,每個解答都是想像蒙田可能給予的答案。這裡將不會出現漂亮工整的解答,但這二十篇回應的「隨筆」將可讓我們一窺這段漫長對話的部分片斷,並且充分享受蒙田本人的陪伴。他將是最和藹可親的對話者與東道主。
我們問:如何生活?蒙田說:做沒有人做過的事(節錄)
一五七〇年代交錯上演著和平與戰爭的插曲。蒙田的生活沒變,寫作也持續不輟。這十年絕大多數的時間,他一直從事寫作與修改最初完成的幾篇隨筆,然後於一五八〇年交由波爾多當地的出版商西蒙‧米朗吉出版。
縱然是首次出版,《隨筆集》卻已獨特不群,不過還是能夠巧妙地排入書市既有的分類之中,譬如古典文集與大眾作品。《隨筆集》完美結合了兩種商業利基:令人驚奇的原創性與易於分類。
蒙田作品最早出現的版本,與現在我們閱讀的有很大的差異。它分為兩卷,絕大多數的篇章都輕薄短小。這些作品已經帶有蒙田好奇、多疑與求變的性格,提到了各種令人困惑與怪誕的人類行為。當時的讀者對於特殊的書籍很感興趣,蒙田的《隨筆集》馬上就找到了熱情的知音。
米朗吉第一次出版的印量不多,大概只有五、六百冊,而且很快就賣完了。兩年後,他出版了第二版,並做了一些改變。五年後,在一五八七年,《隨筆集》再次改版,並且交由巴黎的尚‧里榭出版。此時,《隨筆集》已成為法國貴族流行的讀物。蒙田自己也說《隨筆集》受歡迎的程度遠超過他的預期,它成了咖啡桌上供人翻覽的精裝書,廣受貴婦們的喜愛。
《隨筆集》的讚賞者中甚至包括了亨利三世。一五八〇年底,蒙田前往巴黎,依照慣例向國王獻上他的作品。亨利告訴他,他喜歡這本書,而據說蒙田這麼回答:「想必陛下也會喜歡我這個人。」
照理來說,蒙田這種風格應該會成為他成功的障礙。如此公開寫下每日的觀察與內心想法,等於是觸犯了禁忌。你不應該在書裡抒寫自己,就算想寫,也只能記錄你的偉大事蹟。聖奧古斯丁曾經寫過自己,但目的是為了鍛鍊靈魂與記錄對上帝的探索,而不是為了讚頌自己能成為奧古斯丁的奇妙歷程。
蒙田確實曾讚頌自己能成為蒙田,這讓一些讀者感到不安。古典學者斯卡里傑尤其對蒙田在一五八八年版的坦率言論感到惱火,蒙田在書中說自己喜歡白酒甚於紅酒。(其實斯卡里傑說得太簡略,蒙田是告訴我們說他從喝紅酒改成喝白酒,然後又改成喝紅酒,接著又改成喝白酒。)另一名學者杜普伊則問道:「誰想知道他喜歡什麼?」這種作風也惹惱了巴斯卡與馬爾布朗許,馬爾布朗許說蒙田「厚顏無恥」,巴斯卡認為他應該適可而止。
唯有在浪漫主義來臨之時,蒙田坦率表達自己的做法才不只受到欣賞,還受到喜愛。蒙田尤其吸引了英吉利海峽對岸的讀者。英國評論家帕提森在一八五六年寫道,在人們眼中,蒙田的自我中心使他的形象躍然紙上,如同小說人物一般。而聖約翰評論道,所有真正的「蒙田愛好者」都喜愛他的「連篇廢話」,因為那使他的性格看起來真實,也使讀者從他身上找到了自己。
早在一五八〇年的版本,蒙田就以他的內心世界吸引了讀者目光。以下這段話不是出自日後充滿冒險的篇章,而是來自他的第一版:
我把目光轉而向內,聚精會神地注視著。每個人都看向自己眼前的事物;至於我,則看向自己的內心。我持續觀察自己,打量自己……在自己的內心打滾。
蒙田不斷地轉身朝向自己,層層疊疊地增厚與加深描述,結果形成一種巴洛克式的摺綴衣紋,布滿洶湧狂暴的波浪紋飾。無怪乎蒙田有時被稱為首開先河的巴洛克時代作家,儘管他的生存年代比巴洛克時代早得多。蒙田形容他的《隨筆集》是「荒誕不經的」,如同「怪物的軀體」。
在政治上蒙田是個保守主義者,但他卻從一開始就成為一名文學革命家。他寫作的方式違背常軌,不遵循普遍的範式,而是自然地帶出談話的韻律。他省略了連結,跳過論理的步驟,只是引用材料而不做任何處理。
蒙田《隨筆集》起初呈現出傳統作品的風貌,從偉大古典作家的花園裡採集了一束花,加上對外交與戰場倫理的全新思考。然而,一旦打開書本,這束花馬上就像奧維德的生物一樣變形成畸形的怪物,並且只靠一樣事物將牠們結合在一起,那就是蒙田。幾乎沒有人比他更能如此全面地違反傳統。這本書不僅醜怪,原本應該謙虛地隱沒在背景的事物,居然凸顯為本書的主軸。
一五七〇年代是蒙田寫作初試啼聲的十年,一五八〇年代則是他晉身名作家的十年。第二個十年使《隨筆集》的篇幅足足增加了一倍,也使蒙田從無名小卒變成了明星。此外,一五八〇年代也使他離開了寧靜的吉衍鄉下,前往瑞士、日耳曼與義大利長期旅行。聲名鵲起的他在各地受到熱烈款待,他之後也成為了波爾多的市長。旅行使蒙田在文學上更有發展,使他成為公眾人物。旅行也損壞了蒙田的健康,耗盡他的精力,使他成為受人緬懷的人物。
二十一世紀到處可見不吝於表現自我的人。如果你上網瀏覽部落格、推特、YouTube、臉書與一些個人網頁,你會發現在這片網路大海裡可以捕撈到數千名有趣的人物,他們使出千奇百怪的手法,只為了吸引瀏覽者的注意。這些人持之以恆地談論自己;他們每天貼文,在網上聊天,把自己做的每件事拍照上傳。他們一方面展現出無拘無束、活潑外向的性格,另一方面也顯現出少見的反思與內省。
以文字描述自己可以創造出一面鏡子,旁人可以藉由這面鏡子看出自己的人性,這種想法的產生並非理所當然,它是被創造出來的,且可以追溯到某個人身上,那就是米歇爾.艾坎.德.蒙田。蒙田是貴族、政府官員與葡萄莊園園主,生於一五三三年,卒於一五九二年,他一直生活在法國西南部的佩里戈爾地區。他平安度過混亂時代,管理自己的家產,以法官身分審理法院案件,曾治理過波爾多,並且成為該市有史以來最隨和的市長。
蒙田總共寫了一百零七篇隨筆,有些只有一兩頁的篇幅,有些則屬長篇。這些隨筆很少解釋或教導任何事物。蒙田把自己呈現成一個腦子裡想到什麼就匆匆記下的人,隨時振筆疾書,不斷捕捉心靈的感受與狀態。他以這些經驗做為向自己提問的根據,特別是某個讓他深感興趣、同時是當時人們關注的大問題,我們可以用幾個簡單的字來表達這個問題:「如何生活?」
這個問題不同於「應該如何生活」這類倫理問題。蒙田固然對道德兩難的問題感興趣,但他關心的不是人應該做什麼,而是人實際上做了什麼。
他描述了一切足以讓我們感同身受的細節,有時還遠超過我們需要的程度。蒙田無來由地告訴我們:他唯一喜歡的水果是瓜類;他喜歡躺著做愛,不喜歡站著做愛;他不會唱歌;他喜歡活潑的朋友,機智的問答總能讓他雀躍不已。但蒙田也描述了一些言語難以形容、甚至難以察覺的感覺:懶惰、勇氣或猶豫不決是什麼感覺;愛慕虛榮、想改掉過於膽小的毛病又是什麼感覺。他甚至描述了單純活著是什麼感覺。
蒙田花了二十多年的時間探索這些現象,他不斷質問自己,並且建立自我的形象──這是一幅不斷變動的自畫像,讀者感受到的是一個活生生的蒙田,彷彿他就坐在你身旁,注視著你的一舉一動。他能說出令人驚奇的話語。蒙田出生的時間距今已近五百年,在這漫長的歲月裡,許多事物改變了,無論風俗還是信仰恐怕都已難以辨識;然而閱讀蒙田的作品卻能讓人經歷一連串熟悉的震撼,二十一世紀的讀者將驚覺蒙田與他們之間幾乎不存在任何隔閡。
無論是蒙田的時代還是我們的時代,這種從他人身上看到自己的感覺總會讓人興奮不已。十六世紀蒙田的崇拜者阿寇德曾說,凡是讀過蒙田《隨筆集》的人都會產生一種錯覺,以為這些文章是他們自己寫的。二十世紀小說家紀德說:「我幾乎要把蒙田的傑作當成自己的作品了,他簡直就是另一個我。」斯蒂芬.褚威格這名奧國作家在二次大戰期間被迫流亡,曾一度瀕臨自殺邊緣,他發現蒙田是他唯一真正的朋友:「這裡的『你』反映出我的『我』,此刻一切距離都泯除了。」書頁上的鉛字漸漸模糊,換得活生生的人走入房內。「四百年就像輕煙般消散無蹤。」
這些感想的產生有跡可循,因為《隨筆集》並不宣揚偉大的意義,也沒有核心的本旨,更沒有需要發展的論點。《隨筆集》並未要求讀者該如何閱讀它:你愛怎麼讀就怎麼讀。蒙田盡情傾洩自己的想法,從不擔心自己在某頁說了某事,到了下頁乃至於下一句又說出完全相反的觀點。蒙田應該會把惠特曼這幾行詩當成自己的座右銘:
我自相矛盾嗎?
很好,那麼我就是自相矛盾,
(我心胸寬大,能夠包容各種不同的說法。)
本書是一部談論蒙田這個人與這名作者的作品。本書也討論蒙田舉辦的這場漫長宴會──四百三十年來不斷累積的共同與私人對話。這趟旅程將是古怪而顛簸的,因為蒙田的作品在每個時代的遭遇並不平順。我的故事將隨著這些潮流行進,它也將「昏昏沉沉、跌跌撞撞」,經常地轉變航向。
絕大多數閱讀《隨筆集》的讀者總想從中得到一些收穫。他們也許在尋找樂子,或尋求啟發,或歷史的理解,或某種純屬個人的啟悟。小說家福樓拜的朋友對於該如何閱讀蒙田感到苦惱,而他的建議是:
不要像孩子一樣想從中得到樂趣,也不要像野心家一樣想從中得到指示。你閱讀他的目的只有一個:「為了生活」。
這個問題將貫串全書,章節將採取二十種解答的形式來表現,每個解答都是想像蒙田可能給予的答案。這裡將不會出現漂亮工整的解答,但這二十篇回應的「隨筆」將可讓我們一窺這段漫長對話的部分片斷,並且充分享受蒙田本人的陪伴。他將是最和藹可親的對話者與東道主。
我們問:如何生活?蒙田說:做沒有人做過的事(節錄)
一五七〇年代交錯上演著和平與戰爭的插曲。蒙田的生活沒變,寫作也持續不輟。這十年絕大多數的時間,他一直從事寫作與修改最初完成的幾篇隨筆,然後於一五八〇年交由波爾多當地的出版商西蒙‧米朗吉出版。
縱然是首次出版,《隨筆集》卻已獨特不群,不過還是能夠巧妙地排入書市既有的分類之中,譬如古典文集與大眾作品。《隨筆集》完美結合了兩種商業利基:令人驚奇的原創性與易於分類。
蒙田作品最早出現的版本,與現在我們閱讀的有很大的差異。它分為兩卷,絕大多數的篇章都輕薄短小。這些作品已經帶有蒙田好奇、多疑與求變的性格,提到了各種令人困惑與怪誕的人類行為。當時的讀者對於特殊的書籍很感興趣,蒙田的《隨筆集》馬上就找到了熱情的知音。
米朗吉第一次出版的印量不多,大概只有五、六百冊,而且很快就賣完了。兩年後,他出版了第二版,並做了一些改變。五年後,在一五八七年,《隨筆集》再次改版,並且交由巴黎的尚‧里榭出版。此時,《隨筆集》已成為法國貴族流行的讀物。蒙田自己也說《隨筆集》受歡迎的程度遠超過他的預期,它成了咖啡桌上供人翻覽的精裝書,廣受貴婦們的喜愛。
《隨筆集》的讚賞者中甚至包括了亨利三世。一五八〇年底,蒙田前往巴黎,依照慣例向國王獻上他的作品。亨利告訴他,他喜歡這本書,而據說蒙田這麼回答:「想必陛下也會喜歡我這個人。」
照理來說,蒙田這種風格應該會成為他成功的障礙。如此公開寫下每日的觀察與內心想法,等於是觸犯了禁忌。你不應該在書裡抒寫自己,就算想寫,也只能記錄你的偉大事蹟。聖奧古斯丁曾經寫過自己,但目的是為了鍛鍊靈魂與記錄對上帝的探索,而不是為了讚頌自己能成為奧古斯丁的奇妙歷程。
蒙田確實曾讚頌自己能成為蒙田,這讓一些讀者感到不安。古典學者斯卡里傑尤其對蒙田在一五八八年版的坦率言論感到惱火,蒙田在書中說自己喜歡白酒甚於紅酒。(其實斯卡里傑說得太簡略,蒙田是告訴我們說他從喝紅酒改成喝白酒,然後又改成喝紅酒,接著又改成喝白酒。)另一名學者杜普伊則問道:「誰想知道他喜歡什麼?」這種作風也惹惱了巴斯卡與馬爾布朗許,馬爾布朗許說蒙田「厚顏無恥」,巴斯卡認為他應該適可而止。
唯有在浪漫主義來臨之時,蒙田坦率表達自己的做法才不只受到欣賞,還受到喜愛。蒙田尤其吸引了英吉利海峽對岸的讀者。英國評論家帕提森在一八五六年寫道,在人們眼中,蒙田的自我中心使他的形象躍然紙上,如同小說人物一般。而聖約翰評論道,所有真正的「蒙田愛好者」都喜愛他的「連篇廢話」,因為那使他的性格看起來真實,也使讀者從他身上找到了自己。
早在一五八〇年的版本,蒙田就以他的內心世界吸引了讀者目光。以下這段話不是出自日後充滿冒險的篇章,而是來自他的第一版:
我把目光轉而向內,聚精會神地注視著。每個人都看向自己眼前的事物;至於我,則看向自己的內心。我持續觀察自己,打量自己……在自己的內心打滾。
蒙田不斷地轉身朝向自己,層層疊疊地增厚與加深描述,結果形成一種巴洛克式的摺綴衣紋,布滿洶湧狂暴的波浪紋飾。無怪乎蒙田有時被稱為首開先河的巴洛克時代作家,儘管他的生存年代比巴洛克時代早得多。蒙田形容他的《隨筆集》是「荒誕不經的」,如同「怪物的軀體」。
在政治上蒙田是個保守主義者,但他卻從一開始就成為一名文學革命家。他寫作的方式違背常軌,不遵循普遍的範式,而是自然地帶出談話的韻律。他省略了連結,跳過論理的步驟,只是引用材料而不做任何處理。
蒙田《隨筆集》起初呈現出傳統作品的風貌,從偉大古典作家的花園裡採集了一束花,加上對外交與戰場倫理的全新思考。然而,一旦打開書本,這束花馬上就像奧維德的生物一樣變形成畸形的怪物,並且只靠一樣事物將牠們結合在一起,那就是蒙田。幾乎沒有人比他更能如此全面地違反傳統。這本書不僅醜怪,原本應該謙虛地隱沒在背景的事物,居然凸顯為本書的主軸。
一五七〇年代是蒙田寫作初試啼聲的十年,一五八〇年代則是他晉身名作家的十年。第二個十年使《隨筆集》的篇幅足足增加了一倍,也使蒙田從無名小卒變成了明星。此外,一五八〇年代也使他離開了寧靜的吉衍鄉下,前往瑞士、日耳曼與義大利長期旅行。聲名鵲起的他在各地受到熱烈款待,他之後也成為了波爾多的市長。旅行使蒙田在文學上更有發展,使他成為公眾人物。旅行也損壞了蒙田的健康,耗盡他的精力,使他成為受人緬懷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