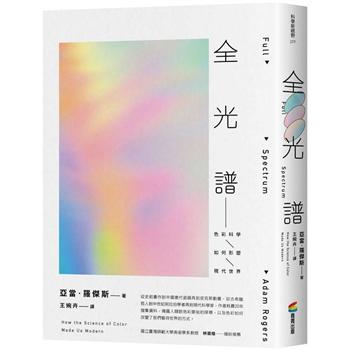一四九五到二○一五年間,針對色彩這個主題出版的書有三千兩百多本。這個總數的計算期間晚到不足納入希臘羅馬哲學家的著作,也沒有包含阿拉伯與中國的科學家與學者在西方世界通稱為中世紀時期所寫的書。因此,雖然三千兩百不是個小數目,卻遠低於實際數量。結果,我現在又寫了一本關於色彩的書。
簡單來說,本書大致上會來來回回談到色彩在物理與心智之間的發展。人會製造具有色彩的事物,以及能夠為人事物賦予色彩的材料,後者指的就是顏料、染料、油漆、化妝品等物品。接著,人會瞭解色彩的運作原理,以及物理、化學、神經科學方面的特性。具備上述知識後,人會製造出更多色彩。光波長會改變,但在瞭解與製造之間來回擺盪的情形永遠不會變。不過,我承認,我們在接下來數百頁的篇幅中將踏上的路途,比起筆直前進,更像是迂迴前行,甚至可說是特立獨行。
我將從人類開始實驗如何製造色彩談起,這些透露出當時世界線索的色彩,誕生於十萬年前中石器時代可遮風避雨的洞窟內。目前找到最古老的顏料製作工坊便是屬於這個時代,就位在南非布隆伯斯(Blombos)洞窟之中。我會說這是一個約略的起始點,因為人類這時開始把周遭世界的自然物質轉換成製造色彩的原料——以便應用於工藝、工具、藝術。
接下來會稍微離題,探討一下生物究竟是如何(以及為何會)看見色彩。分辨各種不同的光一定具有某種演化優勢,否則如此的能力就不會遺傳至今了。這種能力大概源自於某個古老的微生物,它與地球上任何生物都有所不同,跟我們人類之間的差異則大到彼此其實可以把對方視為外星生物。透過某種方式,這些小生物把以光為食的能力,例如光合作用,轉換成靠光的顏色就能判斷海下某處是否適合覓食。以色彩具體呈現出來的光,從動力來源轉變為知識。
不過,色彩直到人類開始出現貿易行為,才成為商業的一環。最早的人類文明擁有多種顏料,懂得創作五顏六色的藝術品,探討色彩代表的意義。人與人之間的貿易在西元早期數世紀如火如荼展開時,物品上的顏色可以大幅提高其價值。中國與阿拔斯帝國之間(以及絲路沿途各處)此消彼長的貿易興衰,背後推動的力量就是色彩。絲綢當然要染色,而染料基本上是一種由材料吸收的顏料,不光只是塗在表層而已。但本書要聚焦在另一種收益來源:陶瓷,具體來說是堅薄的瓷器,以及鑽研製瓷上釉的技術是如何推動數個文明的整體發展。
事實上,這些色彩本身以及色彩從何而來是如此重要,早期科學家不得不去瞭解色彩是由什麼所構成。這個故事經常始於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接著有如穿越時空般,跳至艾薩克.牛頓(Isaac Newton)。但在希臘人與啟蒙時代之間為其中的哲學與技術斷層搭起橋梁的,得歸功於數世紀阿拉伯學者、各國譯者與創新家所做的努力,這些人讀了亞里斯多德等人的著作後表示:「嗯,這樣不對。」有像波斯科學家法利西(Al-Farisi)這樣的人,讓光穿過裝滿水的球形玻璃,好把光與物理化為實際數值,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才得以展開。
少了啟蒙運動以及從科學角度瞭解世界的意識崛起,色彩學在十八、十九世紀就不會有活絡興盛的光景。正是在這個時期,眾人開始研發新顏料,製造出世上前所未見的色彩,並發明新方法,複製圖像,加以利用。同一個時代的人也終於明白眼睛感知色彩的原理,進而為現代物理學揭開序幕。
即便人類開始創造出愈來愈多的合成色彩,白色依然獨樹一格,不論是在化學性質上,還是象徵意義上皆然。其中鉛白這種顏料,從古埃及與羅馬帝國興盛時期開始便舉足輕重,毒性也可怕至極。
一八九三年,在芝加哥哥倫布紀念博覽會(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無色全白與下個世紀鮮明多彩的不和諧混雜,兩者間千年來的來回擺盪,到達了衝突最高潮。人們口中所謂的「白城」(White City),由當時的頂尖建築師與規劃師設計打造,仰賴的全是無趣的圓柱、殿堂、白色——不只是外觀,還包括種族。但其中一座建築物,也就是多色的運輸建築館(Transportation Building),鶴立雞群。這棟建築是由其中一位摩天大樓之父路易斯.蘇利文(Louis Sullivan)所打造,也是一項色彩理論的成果,其概念源自人腦是如何整合所見資訊的新科學。
一切都各就各位了。科學理論有了,需求也出現了。在工業革命的鼎盛時期,名為奧古斯特.羅西(Auguste Rossi)的工程師將會努力研究該如何利用由尼加拉瀑布發電的電爐,用鈦製造出更好的鋼合金——這真是十足的美國作風。這一切將徒勞無功,但在鑽研期間,他會發覺其中一種副產物可以當成白色顏料,也就是白得透亮的二氧化鈦粉末。不出數十年,這種白色粉末將主宰整個顏料製造業;如今,它依然獨占鰲頭。
二次大戰後,在世界各地大規模生產的顏色與色彩繽紛的物品開始激增,但一個難解之謎也隨之浮上檯面:每個人眼中所見的色彩都各有不同。不是每個人都以相同的字眼來表達相同的色彩,這個差異不只出現在人與人之間,也體現在文化與文化之間。不過,隨著色彩學和新顏料更普及,大家開始清楚瞭解到,一般人如何看見與感知色彩的這個謎團,一部分跟人使用什麼詞彙來形容色彩有關。於是,在一九七○年代,語言學家保羅.凱伊(Paul Kay)與人類學家布倫特.柏林(Brent Berlin)派調查人員前往世界各地,想瞭解大家是如何談論色彩,兩人的成果至今依然是瞭解人類環境界(譯註: Umwelt,德文「周遭世界」之意)的關鍵。我們已經證實,色彩這項工具不只改變了靠技術革新而帶來進步的世界,也能用來瞭解語言和認知的內在世界。
這方面的研究甚至深入擴及至大腦與心智:神經生理學家在二十世紀中葉便展開研究,想釐清人類腦袋中的那團黏糊糊肉塊是如何把光轉換成色彩的概念,相關研究目前仍在進行。這個科學領域依然相當振奮人心,我這麼說的意思其實是,目前尚未有人徹底瞭解背後的原理。而證明這個科學領域尚待研究的最佳證據之一,出現在二○一五年,當時,單單一張藍色連衣裙(是藍的,不是白的,好嗎?)的彩圖就讓全世界分成兩派。由於網路已經深入每個口袋與包包,隨處可見的高畫質螢幕讓人人都有辦法重新創造出色彩近乎無限的調色盤。但這種創造色彩的全能能力,受到一張在傍晚時分拍下,並導致眾人意見兩極的藍色連衣裙照考驗後,顯示出每個人對這種無限色彩都各有看法。解構分析這件事,或許也能讓科學家瞭解眼睛和大腦究竟是如何運作,才得以在周遭環境的色彩改變時,為我們打造出一個色彩恆常的世界。
這也將為色彩科技帶來未來發展的契機。多虧數位投影機與先進3D列印機的協助,調色師正在讓各種既有色彩煥然一新,並使得新舊色彩難以區別。瞭解眼睛是如何解讀色彩,又是如何維持對各種色彩的概念,得以讓藝術品修復師挽救抽象派畫家馬克.羅斯科(Mark Rothko)即將毀損的油畫作品,也可以讓人印出幾可亂真的藝術仿作——即便只有如黑箱作業般的人工智慧曉得其中的運作原理。
現今,所有螢幕、所有眼睛、所有大腦全都合力要創造出不可能出現的色彩,以及一種不單純是光譜,還能羅列情緒的頻譜。祕訣可能就在於亮度,也就是光影間的差距,其中一個極端仿自亮到不行的甲蟲,另一個則是所謂的超級黑顏料,導致現代藝術界四分五裂。皮克斯(Pixar)動畫工作室的色彩高手動畫師則橫跨在光影間的那條線上,透過目前所能打造的最先端科技,創造出只見於特殊銀幕上的色彩……也許有一天,他們運用雷射與編碼,就能喚起只存在於觀眾腦中,卻完全不屬於銀幕上的色彩。
這將會是影響深遠的一大成就,儘管從根本來看,他們依然還是想做到跟布隆伯斯洞窟自製顏料者一模一樣的事:超級簡化來說,就是讓光子躍入眼中,藉此喚起某種狀態、某種情緒、某種與周遭世界的緊密連結。這些人只不過現在對此更拿手了。
本書省略了不少相關內容。首先,我不打算花太多時間琢磨設計與色彩偏好的心理學,或是藍色多可靠、紅色多具威力的概念。主要是因為這些概念背後沒有太多科學證據支持。這些東西——抱歉——都是胡扯。或者也許更得體的說法會是,這些關於色彩意義的直覺看法因文化而異,也因時代而異,更因人而異。
同理,本書並沒有收錄每一種色彩的完整歷史,或者該說這不是一本眾多顏料以及其從何而來的型錄。我會在適當的時機稍微談一下歷史,因為不同顏料的發明過程向來都是揭開技術史的關鍵。不過,本書並非列出色彩或化學物質的清單。已經有其他作家寫過那些色彩史了,文筆也遠勝過我所能企及的程度。
讀個幾章後,你會看到飛車追逐,過程相當有趣。最後,幾個壞蛋會遭到逮捕,我不想在此先劇透。但我會說,在最終開庭審判的開場陳述時,辯方律師從檢察官手中借來了一小撮亮白的二氧化鈦粉末,因為它是促發這起案件的關鍵,接著,他表示:「iPhone出現前,向來就有白色事物。很久以前,房屋都漆上白色;很久以前,汽車就有白色款……沒錯,白色物品可以賣出這麼多,就是因為世上白色物品眾多,而製造這種白色粉末的技術,早就存在已久了。」
我不是要對這位律師不敬,但這種說法誤解了整個技術史以及人類與色彩之間的關係。就某種意義來說,這整本書基本上就等於是我把眼鏡往上一推,提出另一種看法。那個自稱是中國間諜的人為了數百萬美元,賭上(也因此喪失)他的自由,這個故事之所以合理,只不過是人類著迷於色彩的其中一例——不光是痴迷於其美學,更是其實際組成。人類向來渴望知曉色彩是由什麼所構成,以及要如何製造色彩與富有色彩的物品。這是人類最早出現的其中一個科學領域,如今也依然是我們最容易訴諸情感的領域。千年以來,哲學家、藝術家、科學家都不斷在爭論,形式(form,物體的形狀)與色彩究竟哪個重要。我個人的另類看法如下:這是假二分法。每個物體表面的所有色相(hue)與色調,都定義了我們的思維方式。這些色彩定義了我們生活的世界,我們希望能打造出來的世界。爭論點不在於是色彩還是形式,色彩就是形式,塑造出我們所處世界的樣貌。
簡單來說,本書大致上會來來回回談到色彩在物理與心智之間的發展。人會製造具有色彩的事物,以及能夠為人事物賦予色彩的材料,後者指的就是顏料、染料、油漆、化妝品等物品。接著,人會瞭解色彩的運作原理,以及物理、化學、神經科學方面的特性。具備上述知識後,人會製造出更多色彩。光波長會改變,但在瞭解與製造之間來回擺盪的情形永遠不會變。不過,我承認,我們在接下來數百頁的篇幅中將踏上的路途,比起筆直前進,更像是迂迴前行,甚至可說是特立獨行。
我將從人類開始實驗如何製造色彩談起,這些透露出當時世界線索的色彩,誕生於十萬年前中石器時代可遮風避雨的洞窟內。目前找到最古老的顏料製作工坊便是屬於這個時代,就位在南非布隆伯斯(Blombos)洞窟之中。我會說這是一個約略的起始點,因為人類這時開始把周遭世界的自然物質轉換成製造色彩的原料——以便應用於工藝、工具、藝術。
接下來會稍微離題,探討一下生物究竟是如何(以及為何會)看見色彩。分辨各種不同的光一定具有某種演化優勢,否則如此的能力就不會遺傳至今了。這種能力大概源自於某個古老的微生物,它與地球上任何生物都有所不同,跟我們人類之間的差異則大到彼此其實可以把對方視為外星生物。透過某種方式,這些小生物把以光為食的能力,例如光合作用,轉換成靠光的顏色就能判斷海下某處是否適合覓食。以色彩具體呈現出來的光,從動力來源轉變為知識。
不過,色彩直到人類開始出現貿易行為,才成為商業的一環。最早的人類文明擁有多種顏料,懂得創作五顏六色的藝術品,探討色彩代表的意義。人與人之間的貿易在西元早期數世紀如火如荼展開時,物品上的顏色可以大幅提高其價值。中國與阿拔斯帝國之間(以及絲路沿途各處)此消彼長的貿易興衰,背後推動的力量就是色彩。絲綢當然要染色,而染料基本上是一種由材料吸收的顏料,不光只是塗在表層而已。但本書要聚焦在另一種收益來源:陶瓷,具體來說是堅薄的瓷器,以及鑽研製瓷上釉的技術是如何推動數個文明的整體發展。
事實上,這些色彩本身以及色彩從何而來是如此重要,早期科學家不得不去瞭解色彩是由什麼所構成。這個故事經常始於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接著有如穿越時空般,跳至艾薩克.牛頓(Isaac Newton)。但在希臘人與啟蒙時代之間為其中的哲學與技術斷層搭起橋梁的,得歸功於數世紀阿拉伯學者、各國譯者與創新家所做的努力,這些人讀了亞里斯多德等人的著作後表示:「嗯,這樣不對。」有像波斯科學家法利西(Al-Farisi)這樣的人,讓光穿過裝滿水的球形玻璃,好把光與物理化為實際數值,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才得以展開。
少了啟蒙運動以及從科學角度瞭解世界的意識崛起,色彩學在十八、十九世紀就不會有活絡興盛的光景。正是在這個時期,眾人開始研發新顏料,製造出世上前所未見的色彩,並發明新方法,複製圖像,加以利用。同一個時代的人也終於明白眼睛感知色彩的原理,進而為現代物理學揭開序幕。
即便人類開始創造出愈來愈多的合成色彩,白色依然獨樹一格,不論是在化學性質上,還是象徵意義上皆然。其中鉛白這種顏料,從古埃及與羅馬帝國興盛時期開始便舉足輕重,毒性也可怕至極。
一八九三年,在芝加哥哥倫布紀念博覽會(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無色全白與下個世紀鮮明多彩的不和諧混雜,兩者間千年來的來回擺盪,到達了衝突最高潮。人們口中所謂的「白城」(White City),由當時的頂尖建築師與規劃師設計打造,仰賴的全是無趣的圓柱、殿堂、白色——不只是外觀,還包括種族。但其中一座建築物,也就是多色的運輸建築館(Transportation Building),鶴立雞群。這棟建築是由其中一位摩天大樓之父路易斯.蘇利文(Louis Sullivan)所打造,也是一項色彩理論的成果,其概念源自人腦是如何整合所見資訊的新科學。
一切都各就各位了。科學理論有了,需求也出現了。在工業革命的鼎盛時期,名為奧古斯特.羅西(Auguste Rossi)的工程師將會努力研究該如何利用由尼加拉瀑布發電的電爐,用鈦製造出更好的鋼合金——這真是十足的美國作風。這一切將徒勞無功,但在鑽研期間,他會發覺其中一種副產物可以當成白色顏料,也就是白得透亮的二氧化鈦粉末。不出數十年,這種白色粉末將主宰整個顏料製造業;如今,它依然獨占鰲頭。
二次大戰後,在世界各地大規模生產的顏色與色彩繽紛的物品開始激增,但一個難解之謎也隨之浮上檯面:每個人眼中所見的色彩都各有不同。不是每個人都以相同的字眼來表達相同的色彩,這個差異不只出現在人與人之間,也體現在文化與文化之間。不過,隨著色彩學和新顏料更普及,大家開始清楚瞭解到,一般人如何看見與感知色彩的這個謎團,一部分跟人使用什麼詞彙來形容色彩有關。於是,在一九七○年代,語言學家保羅.凱伊(Paul Kay)與人類學家布倫特.柏林(Brent Berlin)派調查人員前往世界各地,想瞭解大家是如何談論色彩,兩人的成果至今依然是瞭解人類環境界(譯註: Umwelt,德文「周遭世界」之意)的關鍵。我們已經證實,色彩這項工具不只改變了靠技術革新而帶來進步的世界,也能用來瞭解語言和認知的內在世界。
這方面的研究甚至深入擴及至大腦與心智:神經生理學家在二十世紀中葉便展開研究,想釐清人類腦袋中的那團黏糊糊肉塊是如何把光轉換成色彩的概念,相關研究目前仍在進行。這個科學領域依然相當振奮人心,我這麼說的意思其實是,目前尚未有人徹底瞭解背後的原理。而證明這個科學領域尚待研究的最佳證據之一,出現在二○一五年,當時,單單一張藍色連衣裙(是藍的,不是白的,好嗎?)的彩圖就讓全世界分成兩派。由於網路已經深入每個口袋與包包,隨處可見的高畫質螢幕讓人人都有辦法重新創造出色彩近乎無限的調色盤。但這種創造色彩的全能能力,受到一張在傍晚時分拍下,並導致眾人意見兩極的藍色連衣裙照考驗後,顯示出每個人對這種無限色彩都各有看法。解構分析這件事,或許也能讓科學家瞭解眼睛和大腦究竟是如何運作,才得以在周遭環境的色彩改變時,為我們打造出一個色彩恆常的世界。
這也將為色彩科技帶來未來發展的契機。多虧數位投影機與先進3D列印機的協助,調色師正在讓各種既有色彩煥然一新,並使得新舊色彩難以區別。瞭解眼睛是如何解讀色彩,又是如何維持對各種色彩的概念,得以讓藝術品修復師挽救抽象派畫家馬克.羅斯科(Mark Rothko)即將毀損的油畫作品,也可以讓人印出幾可亂真的藝術仿作——即便只有如黑箱作業般的人工智慧曉得其中的運作原理。
現今,所有螢幕、所有眼睛、所有大腦全都合力要創造出不可能出現的色彩,以及一種不單純是光譜,還能羅列情緒的頻譜。祕訣可能就在於亮度,也就是光影間的差距,其中一個極端仿自亮到不行的甲蟲,另一個則是所謂的超級黑顏料,導致現代藝術界四分五裂。皮克斯(Pixar)動畫工作室的色彩高手動畫師則橫跨在光影間的那條線上,透過目前所能打造的最先端科技,創造出只見於特殊銀幕上的色彩……也許有一天,他們運用雷射與編碼,就能喚起只存在於觀眾腦中,卻完全不屬於銀幕上的色彩。
這將會是影響深遠的一大成就,儘管從根本來看,他們依然還是想做到跟布隆伯斯洞窟自製顏料者一模一樣的事:超級簡化來說,就是讓光子躍入眼中,藉此喚起某種狀態、某種情緒、某種與周遭世界的緊密連結。這些人只不過現在對此更拿手了。
本書省略了不少相關內容。首先,我不打算花太多時間琢磨設計與色彩偏好的心理學,或是藍色多可靠、紅色多具威力的概念。主要是因為這些概念背後沒有太多科學證據支持。這些東西——抱歉——都是胡扯。或者也許更得體的說法會是,這些關於色彩意義的直覺看法因文化而異,也因時代而異,更因人而異。
同理,本書並沒有收錄每一種色彩的完整歷史,或者該說這不是一本眾多顏料以及其從何而來的型錄。我會在適當的時機稍微談一下歷史,因為不同顏料的發明過程向來都是揭開技術史的關鍵。不過,本書並非列出色彩或化學物質的清單。已經有其他作家寫過那些色彩史了,文筆也遠勝過我所能企及的程度。
讀個幾章後,你會看到飛車追逐,過程相當有趣。最後,幾個壞蛋會遭到逮捕,我不想在此先劇透。但我會說,在最終開庭審判的開場陳述時,辯方律師從檢察官手中借來了一小撮亮白的二氧化鈦粉末,因為它是促發這起案件的關鍵,接著,他表示:「iPhone出現前,向來就有白色事物。很久以前,房屋都漆上白色;很久以前,汽車就有白色款……沒錯,白色物品可以賣出這麼多,就是因為世上白色物品眾多,而製造這種白色粉末的技術,早就存在已久了。」
我不是要對這位律師不敬,但這種說法誤解了整個技術史以及人類與色彩之間的關係。就某種意義來說,這整本書基本上就等於是我把眼鏡往上一推,提出另一種看法。那個自稱是中國間諜的人為了數百萬美元,賭上(也因此喪失)他的自由,這個故事之所以合理,只不過是人類著迷於色彩的其中一例——不光是痴迷於其美學,更是其實際組成。人類向來渴望知曉色彩是由什麼所構成,以及要如何製造色彩與富有色彩的物品。這是人類最早出現的其中一個科學領域,如今也依然是我們最容易訴諸情感的領域。千年以來,哲學家、藝術家、科學家都不斷在爭論,形式(form,物體的形狀)與色彩究竟哪個重要。我個人的另類看法如下:這是假二分法。每個物體表面的所有色相(hue)與色調,都定義了我們的思維方式。這些色彩定義了我們生活的世界,我們希望能打造出來的世界。爭論點不在於是色彩還是形式,色彩就是形式,塑造出我們所處世界的樣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