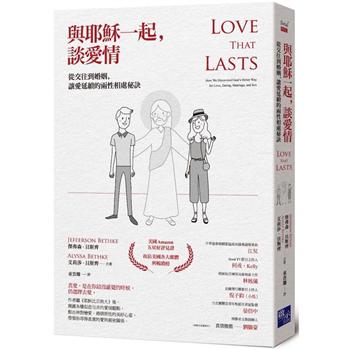即便很多電影不斷遊說我們相信所謂命中註定的「那一位」,但其實我不信這套。愛不是童話故事(當然,愛曾經是,但自〈創世記〉第三章開始,愛就變得錯綜複雜了), 就連好萊塢都深知這一點,所有最經典的愛情童話故事,都是在真實生活即將展開的那一刻,電影便結束了,不是在男女主角彼此允諾的瞬間,就是在他們正要開始一起生活的時候。
我真想看一部以「決定攜手共同生活」為開場白的電影。想看看那些演繹伴侶衝突、爭吵、承受壓力、傷害、痛苦、瑣碎家務、精疲力倦、挫折失落、待繳賬單……以及族繁不及備載的情緒與感受的電影。然後,我們再來看看電影謝幕前會如何告訴觀眾:「從此以後,他們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許多時候,因為我們誤以為那個對象就是「命中註定的那一位」,而把自己逼到苦不堪言。許多人終其一生尋尋覓覓「那一位」,卻少有人能徹底明白,所謂「那一位」不過是浪漫喜劇所虛構出來的想像,絕非出自聖經。
我怎麼知道艾莉莎是不是「那一位」? 因為我和她結婚了。就在我將我的生命與她結合的那一刻,她就成了「那一位」。我知道這麼說一點也不浪漫,但艾莉莎和我都同意,我們其實都可能和其他人結婚,或許婚後生活也會過得幸福而美滿。
重點不在於去尋找神話中的獨角獸,而是找到某位可以成為彼此最棒人生伴侶的人。坦白說,所謂「那一位」的說法一點也不合邏輯,搞不好只是一萬五千年前有個男人娶錯妻子(不是註定的那一位),然後展開無止境的循環,一路傳承到你我身上。
雖然我們不太願意承認,但事實上,想要尋找「那一位」的渴望,其實來自我們心裡,因為我們滿心期待和想像中的「那一位」結合,期待那是一個我們不必改變太多就超級適合的完美對象,於是我們不需要成長、不需要學習、更不需要改變。
但這樣的期望終將壓垮另一個人,因為沒有人可以承受那般沉重的壓力。人們免不了會互相傷害、使彼此失望,有誰能純潔無罪呢? 想成為別人的拯救者,是不可能達成的使命,唯有耶穌能夠承受這樣的重擔。如果我們明白自己的期待有多沉重,就能釋放自己,也釋放對方。
在上帝的守護下,會有一定程度的醞釀與安排而把兩個人連結一起。如果你尚未進入婚姻,上帝可能會為你預備一個你甚至從未謀面的人,所以我們需要格外留心。我經常看到許多伴侶試圖合理化自己的離婚,說他們的配偶根本就不是那一位。但艾莉莎和我早就明白,這世上有太多可以結婚的理想人選,只不過我們選擇了彼此。那才是真正最關鍵的重點。
我很期待有一部電影,描繪一對新人站在婚禮的祭壇前,如此表白:「在尋覓的過程中,我們有很多機會與其他人結婚,我從來就不相信有什麼命中註定的『那一位』,我只相信,我選擇了一個人來愛、來為他付出一輩子,而我,選擇了你。」
我知道這種電影永遠不會出現,因為這樣的情節太無聊了(而且毫無浪漫可言)。但事實是,真愛往往是無聊的。
真愛是在你不想動手的時候卻勉強自己去洗衣服,因為你的伴侶需要休息。
真愛是即便在你最沒感覺的時候,仍選擇去愛。而且,天天如是。
真愛是跟對方說第一百萬次的對不起。
真愛是想盡辦法,找機會為對方付出。
「無聊」鋪成一部爛電影,卻造就偉大的婚姻。愛情從來不是童話故事,也不是尋找風度翩翩的白馬王子。婚姻裡的美麗與神聖──同時也是最困難的部分──正是打從結婚那一刻開始,你一點一滴地發現對方不是你的的白馬王子(或白雪公主? 我們需要更多創意的童話名稱),發現對方不是你想像中的他(或她)。而彼時彼刻,才是真正喜樂出現的地方,就在一團混亂的戰壕之中。
◆感覺與承諾
兩性關係裡最悲慘的事情莫過於:你期待夢幻的童話故事,想從中得到婚姻以外的事物。那樣的心態將使你們的婚姻越走越辛苦,因為你根本沒有認清事實。你一心冀望的,其實並非愛的真義。
愛不是一種感覺。當然,在你約會時,對方深情地看你一眼,你可能就興奮得快暈倒了。但那種激蕩的感覺並不是愛。
前陣子在旅程中,我打算在機場的椅子上補眠。如果你也有過類似的經驗,就知道這樣不太可能真的睡著,但我還是想試試。我緊閉雙眼,看起來像是熟睡了,坐我隔壁的一對老夫妻大概覺得我不會聽到他們的對話,便開始聊天。他們大概六十歲左右,或許已經結婚三、四十年了,他們正與一位年約三十歲的女性聊天。聽對話內容,我判斷他們應該是在機場初次見面的朋友。聊了一陣子,開始聊到婚姻的話題,較年輕的那位女子提及她最近才剛離婚。老夫妻好奇問原因,她回答:「不知道為什麼,我和丈夫都不再感覺快樂。」
離婚的理由無奇不有,但她這個「不再感覺快樂」的說法卻把我給難倒了。快樂是一種感覺。我有時候感覺快樂,有時候不覺得快樂。有時候,婚姻裡的事物令我快樂, 但有時候,同樣的事物卻令我快樂不起來。那是一種稍縱即逝的感覺。有一個離婚理由可能跟那位女士講的很類似,就是你們不再相愛了。我不會責怪那位女士,因為她所做的,正是當代文化灌輸我們該去做的事──跟著感覺走,才是王道。
但是,因為不再相愛就要終止婚姻關係,那跟車子沒油就要把車子賣掉一樣奇怪。你不會把車子賣掉,而是會把油箱加滿,好好照顧它。你會定期把車子送去保養、檢查,有必要時就換個新車牌,就像你也需要更新你的婚約一般。愛從來不是一種感覺, 而是一份承諾,大家一同遵循。承諾比較像是汽車,感覺則類似掛在後面的拖車。你不能帶著一台拖車到處走,但如果拖車緊扣在汽車後面,那麼汽車去哪兒,拖車便跟到那兒。由承諾來驅動車子,感覺也會一起跟隨。但若由感覺來驅動車子,恐怕你會一整晚都坐在停車場裡,好奇自己怎麼哪裡也沒法去。
機場的那對老夫婦靜靜聽那位女士訴說,回了一句「真是遺憾」,然後禮貌性地鼓勵她。我略略睜開雙眼,捕捉到老夫妻眼神中一閃而過的心痛,彷彿想暗示對方:「親愛的,婚姻和快不快樂是兩回事啊。」
這對老夫妻結婚的時間比我活著的時間更長久,我確定這段期間總有些時候(我猜不會只有幾個月,而是以年來計算)他們會覺得不快樂,想要放棄這份愛情,開始思索結束可能會比繼續努力來得好。
沒有人能走過五十年的婚姻,只因為婚姻既簡單又輕鬆。
沒有人能走過五十年的婚姻,只因為他們一直處在「愛情狀態」。
沒有人能慶祝結婚五十週年,只因為浪漫的甜言蜜語一路牽引他們至此。那正是為何心理學家保羅.杜尼耶(Paul Tournier)這麼說道:「我結過七次婚,每一次都和同一個女人結婚。」
他從未離婚,他只是以一種特殊方式來形容他的婚姻不斷地改變與轉化,而那樣的轉變從來不是離婚的理由(請注意,我說的不是婚姻中的有毒元素,譬如色情成癮、婚外情或家暴,那是兩碼子事)。
我經常聽到一種說法,和我在機場聽到的對話有幾分類似:「我太太好像變了個人。有一天我醒來,發現她不再是我當初結婚的那個她了。」然後他們開始想:「這段婚姻應該結束了,因為我的伴侶已不再是我曾立下誓約的那一位。」
我要強調的是,有時候你的伴侶確實會變成另一個人。事實上,你的伴侶一直都在變成不同的人,因為人都會改變 ! 我自己也不再是五年前的那個我了,一年前的我和現在的我改變更大好嗎! 我們每個人都在改變、追尋與成長,期待自己變得更好。然而, 在婚姻祭壇前所立下的誓約,可以包容與含括那些改變。誓約就是在說:無論我們如何改變,婚約始終不變。
如果愛不是一份承諾,那麼,我們所說的婚約有何意義? 那句「直到死亡將我們分離」的意思,可不是指「直到我們對彼此沒有感覺」啊!
承擔的勇氣
在我的青少年時期,我對未來人生有一套預想,我只想做讓自己最快樂的事、把自己放在最快樂的位置、為自己找到最精彩的一切。於是,我的行動與決定都是以這個原則為依歸,簡單純粹的自我中心。當然,我的感情世界也是一樣,從高中開始,我把一切人際關係當成為我服務的管道,給我一切我想要的,其餘免談!我的人生就是要輕鬆愜意。
當然,我沒有公開承認或大聲說出來,但我就是活出了那樣的生命態度。其實我們或多或少也曾這麼活過。對我們而言,愛就是關乎我們自己;但對愛的本質而言,自私無法與真愛並存。我們都知道,不能一開始就大剌剌地表現出真正的自己,總要稍微隱瞞、掩飾一下,才能讓愛情關係在前幾天安全過關。大部分人都曉得,即便我們為對方付出或做出「極美好」的事,在我們內心深處,其實是期待能夠得到相應回饋的。作家柯絲丁.金(Kirsten King)曾經寫過一篇敏銳而露骨的文章,題目是〈我不欠任何人身體〉(I Don’t Owe Anyone My Body),文中敘述她在一個男女約會網站的配對下,兩次和一個名叫提姆的男生約會。在第二次約會之後,提姆想盡辦法要和柯絲丁上床,那幾乎已經是大部分女生心照不宣的一種壓力,但柯絲丁不為所動。最後提姆忍無可忍,一邊離開一邊生氣地說:「我帶你去吃吃喝喝,還請你去看表演。拜託,對你們這種隨便認識的女生,大部分男生根本不會像我這樣付出!」
雖然這是比較極端的例子,但我們其實對這種發展並不陌生,只不過我們做得比較有技巧而已。當我們和伴侶為了瑣碎的家事而爭執不下時,不也是這樣嗎? 把當年為對方所做的那些事情拿出來邀功。
也或許我們沒有說出口,卻在心裡抗辯:「但,都是我……」但,都是我把垃圾拿出去、都是我洗碗耶,為什麼她就不能讓我休息一下? 但,都是我辛苦工作才存到這些錢,為什麼因為她不想要,我就不能買一輛新車?
「愛」不是你應得的權利。不是你為誰做了什麼事,你就理當得到想要的東西。
如果是那樣,那是愛嗎?
愛是求取他人的最高福祉。愛是尊崇對方,使對方高於你。愛是耶穌。或者我們以另一種更貼切的說法來表達,如果你想要知道愛的面貌,看看耶穌吧! 那位宣告自己就是神的猶太導師,毫無保留地傾注每一份力量,不為自己,只為別人與上帝的耶穌。那位愛到傷痕累累的耶穌—那不是抽象的形容詞,而是真正的鞭打與傷痕。那位被釘在兩塊木頭上、並列於兩位罪犯之間,飽受酷刑折騰直到死去的耶穌。那位原本無辜卻要受苦至此的耶穌。那位死去的耶穌,因為他的死,我們才得以活。那位在人性對他做了最慘無人道的事情時,竟能說出最溫柔言辭的耶穌,他說:「父啊,原諒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知道。」
為一群人的過犯而求神寬恕的耶穌,卻在同一時刻被同樣一群人吐唾沫、羞辱、嘲笑。當我最終明白這一點時,我被徹底改變了—那改變了我追求、珍愛艾莉莎的心態,我願意為她冒險。當我們第一次約會時,我太年輕,因而在跟隨耶穌的事上,我並未做足功課。我沒有為愛承擔的勇氣,也不真正了解真愛是什麼。我沒想過要去承擔愛的風險或讓自己置身其中,因為我怕被拒絕,更怕因此而受傷。然而,就在我們分手時,我豁然了悟,原來冒險與承擔才是「愛」最重要的本質。勇於出擊才是愛的行動,而非「先觀望一下, 看看他們先採取什麼行動,我再來回應,免得到時候尷尬又受傷」。
我當時也不明白,原來愛是關乎付出,而非一種感覺;愛是關乎承諾,而非尋歡作樂;愛是攸關誓約,而非訂定合約。
我第二次對此領悟更多,是因為我決定去尋求愛的源頭。
我們不需要在那裡困惑、猜疑。我們知道什麼是愛—或至少我們已經知道「誰」 是愛了。
我真想看一部以「決定攜手共同生活」為開場白的電影。想看看那些演繹伴侶衝突、爭吵、承受壓力、傷害、痛苦、瑣碎家務、精疲力倦、挫折失落、待繳賬單……以及族繁不及備載的情緒與感受的電影。然後,我們再來看看電影謝幕前會如何告訴觀眾:「從此以後,他們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許多時候,因為我們誤以為那個對象就是「命中註定的那一位」,而把自己逼到苦不堪言。許多人終其一生尋尋覓覓「那一位」,卻少有人能徹底明白,所謂「那一位」不過是浪漫喜劇所虛構出來的想像,絕非出自聖經。
我怎麼知道艾莉莎是不是「那一位」? 因為我和她結婚了。就在我將我的生命與她結合的那一刻,她就成了「那一位」。我知道這麼說一點也不浪漫,但艾莉莎和我都同意,我們其實都可能和其他人結婚,或許婚後生活也會過得幸福而美滿。
重點不在於去尋找神話中的獨角獸,而是找到某位可以成為彼此最棒人生伴侶的人。坦白說,所謂「那一位」的說法一點也不合邏輯,搞不好只是一萬五千年前有個男人娶錯妻子(不是註定的那一位),然後展開無止境的循環,一路傳承到你我身上。
雖然我們不太願意承認,但事實上,想要尋找「那一位」的渴望,其實來自我們心裡,因為我們滿心期待和想像中的「那一位」結合,期待那是一個我們不必改變太多就超級適合的完美對象,於是我們不需要成長、不需要學習、更不需要改變。
但這樣的期望終將壓垮另一個人,因為沒有人可以承受那般沉重的壓力。人們免不了會互相傷害、使彼此失望,有誰能純潔無罪呢? 想成為別人的拯救者,是不可能達成的使命,唯有耶穌能夠承受這樣的重擔。如果我們明白自己的期待有多沉重,就能釋放自己,也釋放對方。
在上帝的守護下,會有一定程度的醞釀與安排而把兩個人連結一起。如果你尚未進入婚姻,上帝可能會為你預備一個你甚至從未謀面的人,所以我們需要格外留心。我經常看到許多伴侶試圖合理化自己的離婚,說他們的配偶根本就不是那一位。但艾莉莎和我早就明白,這世上有太多可以結婚的理想人選,只不過我們選擇了彼此。那才是真正最關鍵的重點。
我很期待有一部電影,描繪一對新人站在婚禮的祭壇前,如此表白:「在尋覓的過程中,我們有很多機會與其他人結婚,我從來就不相信有什麼命中註定的『那一位』,我只相信,我選擇了一個人來愛、來為他付出一輩子,而我,選擇了你。」
我知道這種電影永遠不會出現,因為這樣的情節太無聊了(而且毫無浪漫可言)。但事實是,真愛往往是無聊的。
真愛是在你不想動手的時候卻勉強自己去洗衣服,因為你的伴侶需要休息。
真愛是即便在你最沒感覺的時候,仍選擇去愛。而且,天天如是。
真愛是跟對方說第一百萬次的對不起。
真愛是想盡辦法,找機會為對方付出。
「無聊」鋪成一部爛電影,卻造就偉大的婚姻。愛情從來不是童話故事,也不是尋找風度翩翩的白馬王子。婚姻裡的美麗與神聖──同時也是最困難的部分──正是打從結婚那一刻開始,你一點一滴地發現對方不是你的的白馬王子(或白雪公主? 我們需要更多創意的童話名稱),發現對方不是你想像中的他(或她)。而彼時彼刻,才是真正喜樂出現的地方,就在一團混亂的戰壕之中。
◆感覺與承諾
兩性關係裡最悲慘的事情莫過於:你期待夢幻的童話故事,想從中得到婚姻以外的事物。那樣的心態將使你們的婚姻越走越辛苦,因為你根本沒有認清事實。你一心冀望的,其實並非愛的真義。
愛不是一種感覺。當然,在你約會時,對方深情地看你一眼,你可能就興奮得快暈倒了。但那種激蕩的感覺並不是愛。
前陣子在旅程中,我打算在機場的椅子上補眠。如果你也有過類似的經驗,就知道這樣不太可能真的睡著,但我還是想試試。我緊閉雙眼,看起來像是熟睡了,坐我隔壁的一對老夫妻大概覺得我不會聽到他們的對話,便開始聊天。他們大概六十歲左右,或許已經結婚三、四十年了,他們正與一位年約三十歲的女性聊天。聽對話內容,我判斷他們應該是在機場初次見面的朋友。聊了一陣子,開始聊到婚姻的話題,較年輕的那位女子提及她最近才剛離婚。老夫妻好奇問原因,她回答:「不知道為什麼,我和丈夫都不再感覺快樂。」
離婚的理由無奇不有,但她這個「不再感覺快樂」的說法卻把我給難倒了。快樂是一種感覺。我有時候感覺快樂,有時候不覺得快樂。有時候,婚姻裡的事物令我快樂, 但有時候,同樣的事物卻令我快樂不起來。那是一種稍縱即逝的感覺。有一個離婚理由可能跟那位女士講的很類似,就是你們不再相愛了。我不會責怪那位女士,因為她所做的,正是當代文化灌輸我們該去做的事──跟著感覺走,才是王道。
但是,因為不再相愛就要終止婚姻關係,那跟車子沒油就要把車子賣掉一樣奇怪。你不會把車子賣掉,而是會把油箱加滿,好好照顧它。你會定期把車子送去保養、檢查,有必要時就換個新車牌,就像你也需要更新你的婚約一般。愛從來不是一種感覺, 而是一份承諾,大家一同遵循。承諾比較像是汽車,感覺則類似掛在後面的拖車。你不能帶著一台拖車到處走,但如果拖車緊扣在汽車後面,那麼汽車去哪兒,拖車便跟到那兒。由承諾來驅動車子,感覺也會一起跟隨。但若由感覺來驅動車子,恐怕你會一整晚都坐在停車場裡,好奇自己怎麼哪裡也沒法去。
機場的那對老夫婦靜靜聽那位女士訴說,回了一句「真是遺憾」,然後禮貌性地鼓勵她。我略略睜開雙眼,捕捉到老夫妻眼神中一閃而過的心痛,彷彿想暗示對方:「親愛的,婚姻和快不快樂是兩回事啊。」
這對老夫妻結婚的時間比我活著的時間更長久,我確定這段期間總有些時候(我猜不會只有幾個月,而是以年來計算)他們會覺得不快樂,想要放棄這份愛情,開始思索結束可能會比繼續努力來得好。
沒有人能走過五十年的婚姻,只因為婚姻既簡單又輕鬆。
沒有人能走過五十年的婚姻,只因為他們一直處在「愛情狀態」。
沒有人能慶祝結婚五十週年,只因為浪漫的甜言蜜語一路牽引他們至此。那正是為何心理學家保羅.杜尼耶(Paul Tournier)這麼說道:「我結過七次婚,每一次都和同一個女人結婚。」
他從未離婚,他只是以一種特殊方式來形容他的婚姻不斷地改變與轉化,而那樣的轉變從來不是離婚的理由(請注意,我說的不是婚姻中的有毒元素,譬如色情成癮、婚外情或家暴,那是兩碼子事)。
我經常聽到一種說法,和我在機場聽到的對話有幾分類似:「我太太好像變了個人。有一天我醒來,發現她不再是我當初結婚的那個她了。」然後他們開始想:「這段婚姻應該結束了,因為我的伴侶已不再是我曾立下誓約的那一位。」
我要強調的是,有時候你的伴侶確實會變成另一個人。事實上,你的伴侶一直都在變成不同的人,因為人都會改變 ! 我自己也不再是五年前的那個我了,一年前的我和現在的我改變更大好嗎! 我們每個人都在改變、追尋與成長,期待自己變得更好。然而, 在婚姻祭壇前所立下的誓約,可以包容與含括那些改變。誓約就是在說:無論我們如何改變,婚約始終不變。
如果愛不是一份承諾,那麼,我們所說的婚約有何意義? 那句「直到死亡將我們分離」的意思,可不是指「直到我們對彼此沒有感覺」啊!
承擔的勇氣
在我的青少年時期,我對未來人生有一套預想,我只想做讓自己最快樂的事、把自己放在最快樂的位置、為自己找到最精彩的一切。於是,我的行動與決定都是以這個原則為依歸,簡單純粹的自我中心。當然,我的感情世界也是一樣,從高中開始,我把一切人際關係當成為我服務的管道,給我一切我想要的,其餘免談!我的人生就是要輕鬆愜意。
當然,我沒有公開承認或大聲說出來,但我就是活出了那樣的生命態度。其實我們或多或少也曾這麼活過。對我們而言,愛就是關乎我們自己;但對愛的本質而言,自私無法與真愛並存。我們都知道,不能一開始就大剌剌地表現出真正的自己,總要稍微隱瞞、掩飾一下,才能讓愛情關係在前幾天安全過關。大部分人都曉得,即便我們為對方付出或做出「極美好」的事,在我們內心深處,其實是期待能夠得到相應回饋的。作家柯絲丁.金(Kirsten King)曾經寫過一篇敏銳而露骨的文章,題目是〈我不欠任何人身體〉(I Don’t Owe Anyone My Body),文中敘述她在一個男女約會網站的配對下,兩次和一個名叫提姆的男生約會。在第二次約會之後,提姆想盡辦法要和柯絲丁上床,那幾乎已經是大部分女生心照不宣的一種壓力,但柯絲丁不為所動。最後提姆忍無可忍,一邊離開一邊生氣地說:「我帶你去吃吃喝喝,還請你去看表演。拜託,對你們這種隨便認識的女生,大部分男生根本不會像我這樣付出!」
雖然這是比較極端的例子,但我們其實對這種發展並不陌生,只不過我們做得比較有技巧而已。當我們和伴侶為了瑣碎的家事而爭執不下時,不也是這樣嗎? 把當年為對方所做的那些事情拿出來邀功。
也或許我們沒有說出口,卻在心裡抗辯:「但,都是我……」但,都是我把垃圾拿出去、都是我洗碗耶,為什麼她就不能讓我休息一下? 但,都是我辛苦工作才存到這些錢,為什麼因為她不想要,我就不能買一輛新車?
「愛」不是你應得的權利。不是你為誰做了什麼事,你就理當得到想要的東西。
如果是那樣,那是愛嗎?
愛是求取他人的最高福祉。愛是尊崇對方,使對方高於你。愛是耶穌。或者我們以另一種更貼切的說法來表達,如果你想要知道愛的面貌,看看耶穌吧! 那位宣告自己就是神的猶太導師,毫無保留地傾注每一份力量,不為自己,只為別人與上帝的耶穌。那位愛到傷痕累累的耶穌—那不是抽象的形容詞,而是真正的鞭打與傷痕。那位被釘在兩塊木頭上、並列於兩位罪犯之間,飽受酷刑折騰直到死去的耶穌。那位原本無辜卻要受苦至此的耶穌。那位死去的耶穌,因為他的死,我們才得以活。那位在人性對他做了最慘無人道的事情時,竟能說出最溫柔言辭的耶穌,他說:「父啊,原諒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知道。」
為一群人的過犯而求神寬恕的耶穌,卻在同一時刻被同樣一群人吐唾沫、羞辱、嘲笑。當我最終明白這一點時,我被徹底改變了—那改變了我追求、珍愛艾莉莎的心態,我願意為她冒險。當我們第一次約會時,我太年輕,因而在跟隨耶穌的事上,我並未做足功課。我沒有為愛承擔的勇氣,也不真正了解真愛是什麼。我沒想過要去承擔愛的風險或讓自己置身其中,因為我怕被拒絕,更怕因此而受傷。然而,就在我們分手時,我豁然了悟,原來冒險與承擔才是「愛」最重要的本質。勇於出擊才是愛的行動,而非「先觀望一下, 看看他們先採取什麼行動,我再來回應,免得到時候尷尬又受傷」。
我當時也不明白,原來愛是關乎付出,而非一種感覺;愛是關乎承諾,而非尋歡作樂;愛是攸關誓約,而非訂定合約。
我第二次對此領悟更多,是因為我決定去尋求愛的源頭。
我們不需要在那裡困惑、猜疑。我們知道什麼是愛—或至少我們已經知道「誰」 是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