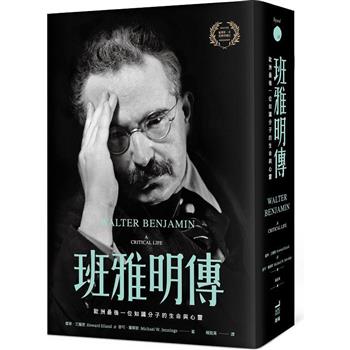引言
今日普遍認為,德國猶太裔批評家兼哲學家班雅明(1892-1940)是歐洲現代性最重要的見證者。儘管在西班牙邊界因躲避納粹而殞命,使得寫作生涯過早中斷,但他留下的作品不論深度廣度都令人驚嘆。一九二〇年代之前是他自稱「德國文學見習生」的階段,班雅明剖析浪漫主義批評、歌德與巴洛克時期的悲苦劇(Trauerspiel),論點至今仍然具有新意。一九二〇年代初,他眼光獨具,大力擁護蘇聯興起的激進文化與主導巴黎文壇的極端現代主義,而後又躋身如今稱作「威瑪文化」的藝文浪潮中心,協同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和莫霍利—納吉(László Moholy-Nagy)等好友,聯手塑造了新的觀看方式、一種前衛的現實主義,告別了代表威廉二世時期德國藝術與文學的菁英現代主義(mandarin modernism)。班雅明在這個階段確立了文名,令他產生了不切實際的幻想,自覺能成為「一流的德國文學批評家」。同時,他和好友克拉考爾(Siegfried Kracauer)可以說聯手開出了一個新領域,使得流行文化成為正當的研究課題。班雅明用隨筆探討兒童文學、玩具、賭博、筆跡學、色情刊物、旅行、民間藝術、邊緣族群如精神障礙者的藝術、食物與各種媒體,包括電影、廣播、攝影及畫報。他人生最後十年幾乎都在流亡,作品多半只是《拱廊街計畫》(The Arcades Project)的旁枝。拱廊街計畫是班雅明對法國十九世紀中葉誕生的都市商品資本主義的文化史考察,儘管只有碩大殘缺的「軀幹」,但班雅明所做的探索與反思卻催生了一系列的原創解析,包括一九三六年的話題經典〈藝術作品在其可技術複製的時代〉,以及標榜波特萊爾為書寫現代性的代表詩人的多篇隨筆。然而,班雅明不僅是出色的批評家和創新的理論家,他還留下了大量介於小說、報導、文化分析與回憶錄之間的作品。一九二八年完成的「蒙太奇之書」《單向街》(One-Way Street)與生前未出版的《柏林童年》(Berlin Childhood around 1900)都是當代傑作。總而言之,班雅明有許多作品都無法簡單歸類,除了長短篇散文,還有專文、隨筆、評論、哲學小品、自傳式小品、編史學小品、廣播稿、書信、文史文獻、短篇故事、日記、詩、對話錄、法文詩與散文翻譯,以及五花八門、長短和重要性不一的零碎反思。
這些作品喚起的濃縮「圖像世界」,讓我們一窺二十世紀最動盪的年代。班雅明生於一九〇〇年前後的柏林猶太富人之家,是典型的日耳曼帝國之子,他的回憶裡充滿了皇帝喜愛的恢宏建築。但他也是當時正急速蔓延的都市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後裔。一九〇〇年時,柏林是歐洲最現代的城市,隨時都有新科技誕生。年輕時他反對德國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因此戰時幾乎都待在瑞士,然而大戰的「滅絕之夜」在他的作品裡俯拾可見。威瑪共和那十四年,班雅明先是經歷了激進左派與激進右派於戰後的血腥對立,隨後是重創這個新興民主政體的惡性通膨,以及一九二〇年代末葉的政治分裂動盪,最終導致一九三三年希特勒與納粹掌權。和當時德國幾乎所有重量級知識分子一樣,班雅明於一九三三年春天潛逃出境,再也沒有回國。他人生最後七年以流亡者身分在巴黎度過,飽嘗孤離、貧困與出版管道難尋之苦。他始終無法忘記「世上有些地方能讓我賺得微薄收入,也有些地方能讓我憑藉微薄收入過活,卻沒有一個地方兩者兼具」。在他生涯盡頭,放眼只見戰爭的陰影正瀰漫歐洲。
如今班雅明辭世七十多年,為何作品依然深深打動一般讀者與學者?首先是他的思想充滿力量,其作品重塑了我們對許多重要作家、對寫作的可能性、對科技媒介的潛力與危害、對歐洲現代性作為一種歷史現象的理解。然而,要是忽略班雅明奇特的文字風格,那宛如蝕刻般獨樹一幟的語言媒介,就無法充分領略他的震撼力。班雅明就像文字的雕刻師,足以和他那個時代最靈敏、最穿透人心的作家平起平坐。而且他還是形式開創者。班雅明最具特色的作品都是以「思想圖像」(Denkbild)為基礎。這是他向詩人格奧爾格(Stefan George)借來的詞彙,意指一種結合哲學分析與具體意象以達成標誌性批判模仿(signature critical mimesis)的格言式散文。就連他看似不著邊際的隨筆也往往隱藏著按前衛蒙太奇原理編排的犀利「思想圖像」。班雅明找到的文學形式,其深刻與複雜的程度,不僅足以和同時代的海德格與維根斯坦相提並論,而且能藉由動人好記的散文引發共鳴,這正是他的天才所在。因此,閱讀班雅明不僅是一種智性活動,更是感官經驗,感覺就像初次品嚐沾了茶的瑪德蓮蛋糕,在你想像裡喚起種種隱約記得的世界。隨著文字逗留、聚集與置換,詞句將按著逐漸浮現的重組原理細微調動,緩緩釋放其顛覆心靈的潛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