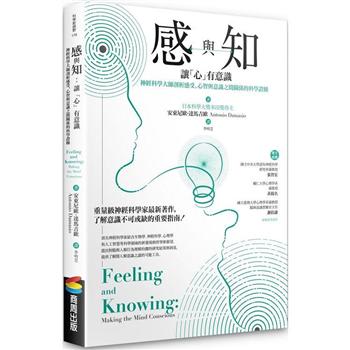為什麼是意識?為什麼是現在?
或許你很好奇,為什麼目前有這麼多哲學家和科學在書寫意識,為什麼直到近期科學文獻(更別說是廣大群眾)都還不太提及的話題,現在卻成為學術界的重要主題和好奇對象。答案其實很簡單:意識很重要,而大眾終於領悟到這點。
意識的重要性來自它直接帶給人類心智什麼,以及它隨後讓心智發現什麼。意識讓心智經驗成為可能,從愉悅到痛苦,以及當我們描述周遭世界和內在世界時,在觀察、思考和推理的過程中所知覺、記憶、回想和操弄的一切。如果我們從持續不斷的心智狀態中移除了意識成分,你和我仍擁有在心智中流動的意像,但這些意像就變成與我們無關的單獨個體。如此一來,這些意像就不屬於你或我或任何其他的人。它們不受約束地流動。沒有人會知道這樣的意像歸屬於誰。若是如此,薛西弗斯(Sisyphus)就會沒事。他是悲劇人物的理由,只是因為他知道這糟糕透頂的困境是屬於他的。
如果沒有意識,那就什麼都不可能知曉。人類文化的興起絕對少不了意識,因此意識也插手了改變人類歷史的進程。意識的重要性,再怎麼強調都不為過。儘管如此,了解意識如何出現的難度卻很容易被誇大,所以很容易把意識宣傳成難解之謎。
既然脊椎動物和許多無脊椎的物種也都十分可能天生具有意識,那為什麼現在我要撰寫意識對人類的重要性呢?意識對牠們不重要嗎?唉呀,當然也很重要,我並沒有忽略非人類生物的能力或相關性。我只是特別強調以下這些事實:(1)人類的痛苦和苦難經驗向來是超凡創造力的來源,這樣專注且執著的創造力負責發明各式各樣的工具,可以用來對抗開啟這個創造力循環的負面感受;(2)有意識的安適和愉悅激發了無數的方法,讓人類可用來確保和增進有利於生活的條件,無論是個別或整體社會的生活。除了罕見但明顯的例外,非人類生物也對痛苦或安適做出類似的反應,只是比人類的方式簡單,而且更為直接。確實,非人類生物成功地躲避或減輕了痛苦和苦難的成因,卻(例如)無法修改它們的起源。意識對人類的影響,範圍與可及之處明顯大上許多。請注意,這並不是因為人類意識的核心機制有所不同(我相信它們沒有不同),而是因為人類的智力資源如此豐富廣闊。更廣泛的資源已使人類能藉由發明新的物體、動作和想法,對苦難或愉悅的兩極經驗做出反應,這就是我們所謂的文化創造。
在這整個故事中,似乎有一些例外。被冠上「社會性」的一小部分昆蟲成功地組裝了一套複雜的「創造性」反應,這些反應的集合確實符合「文化」的一般概念。蜜蜂和螞蟻,以及牠們悉心建立的「城市」所呈現井然有序的都市性與文明性,就是這樣的情況。牠們是否過於渺小和卑微,以至於牠們沒能天生具備意識,也不具有意識推動的創造力?完全不是。我猜想,牠們也會受到牠們經驗的意識感受驅動。只不過,牠們多數行為缺乏彈性,限制了這種文化盛宴的演化—牠們主要是「固著」而非持續發展的禮貌說法。然而,這不應該減損我們對於這些發展如何在幾十萬年前發生,以及意識在其中大概發揮什麼作用的訝異程度。
關於意識對人類有特殊影響的另一部分資格,涉及某些哺乳動物對同伴死亡的反應,例如從大象的葬禮可以清楚看出這點。毫無疑問地,觀察同類痛苦和死亡的結果所引起的自身苦難的意識,一步步地奮力形成這樣的反應組合。相較於人類,兩者間的差異在於發明的規模,以及反應的建構所呈現的有效性和複雜性高低。這些例外通常支持這樣的想法:跟反應差異有關的是物種的智力程度,而不是特定物種的意識本質。
可以合理的詢問,意識推動形成反應的效力,主要來自感受的積極面或消極面,亦即來自正或負的效價。痛苦、苦難和死亡的體悟特別具有力量,我相信比安適和愉悅的力量更大。關於這點,我猜想宗教就是循著那樣的體悟發展出來,亞伯拉罕宗教 和佛教尤其如此。在某種程度上,意識從歷史、演化的角度來看是一顆禁果,一旦吃下就讓人易受苦難和痛苦的傷害,最終還悲慘地直接與死亡對抗。這種觀點十分符合這個想法:意識藉由感受之手進入演化,不僅僅是任何感受,而特別是負面感受。
死亡作為悲劇的來源一事,在聖經敘事和希臘戲劇中得到公認,然後一直存在於藝術創作中。奧登(W. H. Auden)用詩生動描述這個想法,他在詩中將人類化身為精疲力竭但仍反抗的鬥士,懇求殘忍的皇帝說:「我們這些必死之人需索一個奇蹟。」他用需索(demand)而不是需要(require)或請求(request),這是詩人絕望地看著人類無以避免的崩潰,不知該如何是好的明確徵象。奧登已經領悟到,「有可能什麼都拯救不了我們」,這個不那麼原創的結論,深深地滲入了許多宗教和哲學系統的創始故事,至今依然誘使各地的凡人遵循教會在人生苦海中給予協助的忠告。
然而,光有痛苦,完全沒有愉悅指望的單一痛苦,只會促使我們逃避苦難而不是追求安適。因此,我們終將成為痛苦和愉悅兼具的人偶,時不時地藉由我們的創造力獲得自由。
自然的意識
意識的各種意義中,有些跟觀察者/使用者的視角有關。哲學家、心理學家、生物學家或社會學家確實都在探究意識。一天到晚聽到某些問題存在於、或沒能進入「他們的意識」的普通人也是,這些人一定很好奇意識是不是標示清醒、注意或只是擁有心智的廣義標籤。
然而,悄悄隱藏在其文化包袱底下的「意識」一詞有著本質的意義,縱使當代的神經科學家、生物學家、心理學家或哲學家使用不同方法處理這個現象而解釋方式各有不同,但他們都一致認可這點。他們全都認為,「意識」多半是心智經驗的同義詞。
那麼,心智經驗是什麼呢?它是心智的狀態,具備兩個顯著且相關的特徵:它展現的是感受到的心智內容,這些心智內容採用一個單一觀點。進一步的分析顯示,單一觀點是特定有機體的觀點,而心智生來即在這個有機體內。察覺到「有機體觀點」、「自我」和「主體」等概念之間存在親屬關係的讀者是對的,如果他們由此領悟到「自我」、「主體」和「有機體觀點」相當於某個十分有形的東西—真實的「所有權」—也完全正確。「有機體擁有自己特定的心智」;心智屬於自己特定的有機體。你、我,任何一個有意識的實體,全都擁有一個因意識心智而活起來的有機體。
為了讓這些考量盡可能地清晰易懂,我們需要清楚說明幾個名詞的意義:心智、觀點和感受。
如先前的定義,心智是指稱主動產生和展現意像的一種方式,這些意像源自於實際知覺或記憶回想或兩者兼具。構成心智的意像源源不絕地流動,在這麼做的同時,描述了各式各樣的行動者和物體、各式各樣的動作和關係、各式各樣有和沒有符號翻譯的品質。個別或組合而成的各種意像(視覺、聽覺、觸覺、語言等等)都是知識的自然載具,它們運輸知識,它們外顯地示意知識。
觀點指的是「觀看的著眼點」,想當然耳,在我使用「觀看」一詞時,我並不是單指視覺。盲人的意識也有觀點,但跟看見完全無關。我所謂的觀點是指更一般的意義:與我有關係的不只是我所見的,還有我聽到或觸摸的,重要的是就連我在自己身體中所知覺的也有關係。我在談論的觀點是意識心智「所有者」的觀點。換句話說,它相當於一個活生物體所持有的觀點,表達這個觀點的是,當它在一個有機體內運作時,在同一個有機體所擁有的心智內流動的意像。
但我們在探求觀點的起源上可以更進一步。相對於我們周遭的世界,多數活生物體的標準觀點主要是從這些有機體的頭來定義。部分原因是聽覺、視覺、嗅覺、味覺,甚至平衡的感覺探測器都位在身體的頂端(或前端)。作為高度發展的生物,我們當然也知道大腦就在頭裡面!
奇怪的是,關於我們有機體內在的世界,觀點是由感受提供,這些感受毫不含糊地顯露心智和身體的自然關聯。無須詢問任何問題,感受自動就讓心智知道,心智和身體是在一起的,彼此都屬於對方。多虧了感受,分隔物質身體與心智現象的空隙才能自然而然地弭平。
有關意識背景下的感受,我們還需說些什麼呢?我們需要斷言,自我參照不是感受的可選擇特徵,而是不可或缺的定義性特徵。此外,我們可以更大膽一點:我們可以宣稱感受是標準意識的基礎成分。
為了避免感受有多重要的傳奇事蹟轉移我們的注意,我們也需回想起,所有感受都致力於反映體內生命的狀態,無論那個狀態是自發、還是受到情緒修改。這完全適用於參與意識產生過程的所有感受。
總結來說,在心智中不斷展現,也對形成意識不可或缺的感受有兩個來源。一個來源是在體內經營生命的全年無休企業,它必然地反映出生命的起起伏伏:安適、抑鬱、渴望食物和空氣、口渴、痛苦、慾望、愉悅。誠如我們先前所見,這些屬於「恆定感受」的例子。
感受的第二個來源是心智內容經常激起、或強或弱的情緒反應集合:隨時都可能來拜訪我們的恐懼、喜悅和煩躁。它們的心智表達被稱為「情緒感受」,是構成內部敘事的多媒體產物的一部分。由這兩種機制源源不斷製造的感受也併入了敘事中,但它們原先是產生意識過程的裝置。事實上,各種恆定感受幫助從零開始建立人類的存在。
因此,意識是心智的特定狀態,由多重心智事件貢獻而成的生物歷程製造產生。透過內感神經系統發出信號,身體內部的運作貢獻了感受成分,而中樞神經系統內的其他運作則貢獻了描述有機體周遭世界及其肌肉骨骼框架的心像。這些貢獻以嚴密控管的方式,聚集產生十分複雜卻絕對自然的某件事:活生物體包羅萬象的心智經驗,時時刻刻都沉浸在理解自己內在世界和(奇蹟中的奇蹟)自己周遭世界的行動。意識過程就如心智術語表達的那樣在有機體內有了生命,並將範圍設定在自己的物質邊界裡面。心智和身體獲得集合的共同財產,還附帶公證的所有權文件,它們持續地慶祝自己或好或壞的運氣,直到沉沉睡去。
意識的問題
在借助普通生物學、神經生物學、神經心理學、認知科學和語言學之下,心理學的不同分支於闡明知覺、學習和記憶、注意、推理,以及語言方面取得了驚人進展。它們在理解情感(驅力、動機、情緒、感受)和社會行為方面也取得了重大進展。
無論是從公開表現或從主觀觀點來看,任一功能背後的生物結構或過程都完全看不清楚。推動這些不同問題的科學進展,需要辛勤研究、創造發明,並且融合理論努力和實驗室方法。因此,讓人深感訝異的是,關於意識的討論就像是獨樹一格,被賦予了特殊地位,它是一個獨特的問題,而不只是一個難以對付且不能解決的問題。有些意識主題的作者,試圖藉由推動名為「泛心論」(panpsychism)的極端提議來克服僵局。
以意識和心智好像可以彼此互換的方式來談論它們,這點相當有問題。問題更大的是,他們將意識和心智視為無所不在的現象,存在於所有的活生物中,屬於生命狀態不可或缺的部分。所有單細胞生物和所有植物都可透過它們分到的意識來考量。既然如此,那為什麼要止步於活生物呢?對有些人來說,就連整個宇宙與其中的所有石頭都被視為有意識和有心智。
推動這些提議的理由跟一個不公正的立場有關,亦即了解心智其他面向的努力還不足以解決意識的問題。我看不到任何證據顯示情況確實如此。普通生物學、神經生物學、心理學和心智哲學都內含解決意識的問題所必需的工具,甚至在解決心智本身組構的深層潛在問題上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物理學同樣能派上用場。
在意識研究中的一個主要議題,涉及現在眾所周知的「艱難問題(難題)」,這是哲學家大衛.查爾默斯(David Chalmers)提出的名詞。用他的話來說,問題的一個重要面向是指「大腦中的物理過程為何與如何產生意識經驗?」
簡而言之,問題牽涉到所謂不可能解釋名為大腦—由數十億名為神經元的物質實體組成,透過幾兆個突觸相互連結—的物理化學裝置可以產生心智狀態,更別說是有意識的心智狀態。
大腦如何能產生與特定個體始終相連的心智狀態呢?此外,這些大腦產生的狀態如何能感覺像是某些什麼,就像哲學家湯瑪斯.內格爾(Thomas Nagel)認為的那樣?
然而,艱難問題的生物公式其實站不住腳。詢問為什麼「大腦中」的物理過程竟然會產生意識經驗,本身是個錯誤的問題。雖然大腦是意識產生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沒有任何跡象透露大腦僅僅產生意識。
相反地,生物身體本身的非神經組織對創造任何有意識的時刻也有重要貢獻,必須作為問題解答的一部分。這主要是經由感受的混合過程發生,我們認為這是製造意識心智的關鍵促成因素。
「我有意識」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就想像得到的最簡單程度,它的意思是,在我描述自己有意識的特定時刻,我的心智擁有自發地將我認定為其所有人的知識。從根本上來說,知識以各種方式與我自己有關:(a)我的身體:透過身體,我不斷經由感受得知或多或少的細節;(b)加上我從記憶中回想的事實,這些事實可能屬於(或不屬於)知覺時刻,也是我自己不可或缺的部分。
使心智有意識的知識盛宴,規模可大可小,端看與會的貴賓有多少,但某些賓客不只是尊貴,還有參加的義務。讓我一一點名他們:首先是,關於我的身體當前運作的一些知識;再來是,從最近與很久以前的記憶中提取的一些知識,關於我此刻是誰和我曾經是誰。
我絕對不會笨得說出意識就是這麼簡單,因為它一點都不簡單。低估由那麼多活動零件與接合點所產生的複雜性,真的是一點好處都沒有。
然而,儘管意識很複雜,但從心智上來說,弄懂它是由什麼組成似乎並非(或不必保持)神祕不可思議或不可能。
我對我們活生物體—我們稱為神經的部分以及我們很容易忽略而不當一回事的「身體其餘部位」的部分—如何調製出能產生充滿感受和個人參照感之心智狀態的過程,滿滿都是欽佩。但欽佩不需要神祕來加持。神祕的概念以及生物學解釋超出我們理解範圍的想法都不適用於此。問題可以找到答案,謎題終究獲得解決。儘管如此,人們依然對這件事充滿敬畏:組合幾個相對透明的功能編排,最終為我們帶來了什麼益處。
或許你很好奇,為什麼目前有這麼多哲學家和科學在書寫意識,為什麼直到近期科學文獻(更別說是廣大群眾)都還不太提及的話題,現在卻成為學術界的重要主題和好奇對象。答案其實很簡單:意識很重要,而大眾終於領悟到這點。
意識的重要性來自它直接帶給人類心智什麼,以及它隨後讓心智發現什麼。意識讓心智經驗成為可能,從愉悅到痛苦,以及當我們描述周遭世界和內在世界時,在觀察、思考和推理的過程中所知覺、記憶、回想和操弄的一切。如果我們從持續不斷的心智狀態中移除了意識成分,你和我仍擁有在心智中流動的意像,但這些意像就變成與我們無關的單獨個體。如此一來,這些意像就不屬於你或我或任何其他的人。它們不受約束地流動。沒有人會知道這樣的意像歸屬於誰。若是如此,薛西弗斯(Sisyphus)就會沒事。他是悲劇人物的理由,只是因為他知道這糟糕透頂的困境是屬於他的。
如果沒有意識,那就什麼都不可能知曉。人類文化的興起絕對少不了意識,因此意識也插手了改變人類歷史的進程。意識的重要性,再怎麼強調都不為過。儘管如此,了解意識如何出現的難度卻很容易被誇大,所以很容易把意識宣傳成難解之謎。
既然脊椎動物和許多無脊椎的物種也都十分可能天生具有意識,那為什麼現在我要撰寫意識對人類的重要性呢?意識對牠們不重要嗎?唉呀,當然也很重要,我並沒有忽略非人類生物的能力或相關性。我只是特別強調以下這些事實:(1)人類的痛苦和苦難經驗向來是超凡創造力的來源,這樣專注且執著的創造力負責發明各式各樣的工具,可以用來對抗開啟這個創造力循環的負面感受;(2)有意識的安適和愉悅激發了無數的方法,讓人類可用來確保和增進有利於生活的條件,無論是個別或整體社會的生活。除了罕見但明顯的例外,非人類生物也對痛苦或安適做出類似的反應,只是比人類的方式簡單,而且更為直接。確實,非人類生物成功地躲避或減輕了痛苦和苦難的成因,卻(例如)無法修改它們的起源。意識對人類的影響,範圍與可及之處明顯大上許多。請注意,這並不是因為人類意識的核心機制有所不同(我相信它們沒有不同),而是因為人類的智力資源如此豐富廣闊。更廣泛的資源已使人類能藉由發明新的物體、動作和想法,對苦難或愉悅的兩極經驗做出反應,這就是我們所謂的文化創造。
在這整個故事中,似乎有一些例外。被冠上「社會性」的一小部分昆蟲成功地組裝了一套複雜的「創造性」反應,這些反應的集合確實符合「文化」的一般概念。蜜蜂和螞蟻,以及牠們悉心建立的「城市」所呈現井然有序的都市性與文明性,就是這樣的情況。牠們是否過於渺小和卑微,以至於牠們沒能天生具備意識,也不具有意識推動的創造力?完全不是。我猜想,牠們也會受到牠們經驗的意識感受驅動。只不過,牠們多數行為缺乏彈性,限制了這種文化盛宴的演化—牠們主要是「固著」而非持續發展的禮貌說法。然而,這不應該減損我們對於這些發展如何在幾十萬年前發生,以及意識在其中大概發揮什麼作用的訝異程度。
關於意識對人類有特殊影響的另一部分資格,涉及某些哺乳動物對同伴死亡的反應,例如從大象的葬禮可以清楚看出這點。毫無疑問地,觀察同類痛苦和死亡的結果所引起的自身苦難的意識,一步步地奮力形成這樣的反應組合。相較於人類,兩者間的差異在於發明的規模,以及反應的建構所呈現的有效性和複雜性高低。這些例外通常支持這樣的想法:跟反應差異有關的是物種的智力程度,而不是特定物種的意識本質。
可以合理的詢問,意識推動形成反應的效力,主要來自感受的積極面或消極面,亦即來自正或負的效價。痛苦、苦難和死亡的體悟特別具有力量,我相信比安適和愉悅的力量更大。關於這點,我猜想宗教就是循著那樣的體悟發展出來,亞伯拉罕宗教 和佛教尤其如此。在某種程度上,意識從歷史、演化的角度來看是一顆禁果,一旦吃下就讓人易受苦難和痛苦的傷害,最終還悲慘地直接與死亡對抗。這種觀點十分符合這個想法:意識藉由感受之手進入演化,不僅僅是任何感受,而特別是負面感受。
死亡作為悲劇的來源一事,在聖經敘事和希臘戲劇中得到公認,然後一直存在於藝術創作中。奧登(W. H. Auden)用詩生動描述這個想法,他在詩中將人類化身為精疲力竭但仍反抗的鬥士,懇求殘忍的皇帝說:「我們這些必死之人需索一個奇蹟。」他用需索(demand)而不是需要(require)或請求(request),這是詩人絕望地看著人類無以避免的崩潰,不知該如何是好的明確徵象。奧登已經領悟到,「有可能什麼都拯救不了我們」,這個不那麼原創的結論,深深地滲入了許多宗教和哲學系統的創始故事,至今依然誘使各地的凡人遵循教會在人生苦海中給予協助的忠告。
然而,光有痛苦,完全沒有愉悅指望的單一痛苦,只會促使我們逃避苦難而不是追求安適。因此,我們終將成為痛苦和愉悅兼具的人偶,時不時地藉由我們的創造力獲得自由。
自然的意識
意識的各種意義中,有些跟觀察者/使用者的視角有關。哲學家、心理學家、生物學家或社會學家確實都在探究意識。一天到晚聽到某些問題存在於、或沒能進入「他們的意識」的普通人也是,這些人一定很好奇意識是不是標示清醒、注意或只是擁有心智的廣義標籤。
然而,悄悄隱藏在其文化包袱底下的「意識」一詞有著本質的意義,縱使當代的神經科學家、生物學家、心理學家或哲學家使用不同方法處理這個現象而解釋方式各有不同,但他們都一致認可這點。他們全都認為,「意識」多半是心智經驗的同義詞。
那麼,心智經驗是什麼呢?它是心智的狀態,具備兩個顯著且相關的特徵:它展現的是感受到的心智內容,這些心智內容採用一個單一觀點。進一步的分析顯示,單一觀點是特定有機體的觀點,而心智生來即在這個有機體內。察覺到「有機體觀點」、「自我」和「主體」等概念之間存在親屬關係的讀者是對的,如果他們由此領悟到「自我」、「主體」和「有機體觀點」相當於某個十分有形的東西—真實的「所有權」—也完全正確。「有機體擁有自己特定的心智」;心智屬於自己特定的有機體。你、我,任何一個有意識的實體,全都擁有一個因意識心智而活起來的有機體。
為了讓這些考量盡可能地清晰易懂,我們需要清楚說明幾個名詞的意義:心智、觀點和感受。
如先前的定義,心智是指稱主動產生和展現意像的一種方式,這些意像源自於實際知覺或記憶回想或兩者兼具。構成心智的意像源源不絕地流動,在這麼做的同時,描述了各式各樣的行動者和物體、各式各樣的動作和關係、各式各樣有和沒有符號翻譯的品質。個別或組合而成的各種意像(視覺、聽覺、觸覺、語言等等)都是知識的自然載具,它們運輸知識,它們外顯地示意知識。
觀點指的是「觀看的著眼點」,想當然耳,在我使用「觀看」一詞時,我並不是單指視覺。盲人的意識也有觀點,但跟看見完全無關。我所謂的觀點是指更一般的意義:與我有關係的不只是我所見的,還有我聽到或觸摸的,重要的是就連我在自己身體中所知覺的也有關係。我在談論的觀點是意識心智「所有者」的觀點。換句話說,它相當於一個活生物體所持有的觀點,表達這個觀點的是,當它在一個有機體內運作時,在同一個有機體所擁有的心智內流動的意像。
但我們在探求觀點的起源上可以更進一步。相對於我們周遭的世界,多數活生物體的標準觀點主要是從這些有機體的頭來定義。部分原因是聽覺、視覺、嗅覺、味覺,甚至平衡的感覺探測器都位在身體的頂端(或前端)。作為高度發展的生物,我們當然也知道大腦就在頭裡面!
奇怪的是,關於我們有機體內在的世界,觀點是由感受提供,這些感受毫不含糊地顯露心智和身體的自然關聯。無須詢問任何問題,感受自動就讓心智知道,心智和身體是在一起的,彼此都屬於對方。多虧了感受,分隔物質身體與心智現象的空隙才能自然而然地弭平。
有關意識背景下的感受,我們還需說些什麼呢?我們需要斷言,自我參照不是感受的可選擇特徵,而是不可或缺的定義性特徵。此外,我們可以更大膽一點:我們可以宣稱感受是標準意識的基礎成分。
為了避免感受有多重要的傳奇事蹟轉移我們的注意,我們也需回想起,所有感受都致力於反映體內生命的狀態,無論那個狀態是自發、還是受到情緒修改。這完全適用於參與意識產生過程的所有感受。
總結來說,在心智中不斷展現,也對形成意識不可或缺的感受有兩個來源。一個來源是在體內經營生命的全年無休企業,它必然地反映出生命的起起伏伏:安適、抑鬱、渴望食物和空氣、口渴、痛苦、慾望、愉悅。誠如我們先前所見,這些屬於「恆定感受」的例子。
感受的第二個來源是心智內容經常激起、或強或弱的情緒反應集合:隨時都可能來拜訪我們的恐懼、喜悅和煩躁。它們的心智表達被稱為「情緒感受」,是構成內部敘事的多媒體產物的一部分。由這兩種機制源源不斷製造的感受也併入了敘事中,但它們原先是產生意識過程的裝置。事實上,各種恆定感受幫助從零開始建立人類的存在。
因此,意識是心智的特定狀態,由多重心智事件貢獻而成的生物歷程製造產生。透過內感神經系統發出信號,身體內部的運作貢獻了感受成分,而中樞神經系統內的其他運作則貢獻了描述有機體周遭世界及其肌肉骨骼框架的心像。這些貢獻以嚴密控管的方式,聚集產生十分複雜卻絕對自然的某件事:活生物體包羅萬象的心智經驗,時時刻刻都沉浸在理解自己內在世界和(奇蹟中的奇蹟)自己周遭世界的行動。意識過程就如心智術語表達的那樣在有機體內有了生命,並將範圍設定在自己的物質邊界裡面。心智和身體獲得集合的共同財產,還附帶公證的所有權文件,它們持續地慶祝自己或好或壞的運氣,直到沉沉睡去。
意識的問題
在借助普通生物學、神經生物學、神經心理學、認知科學和語言學之下,心理學的不同分支於闡明知覺、學習和記憶、注意、推理,以及語言方面取得了驚人進展。它們在理解情感(驅力、動機、情緒、感受)和社會行為方面也取得了重大進展。
無論是從公開表現或從主觀觀點來看,任一功能背後的生物結構或過程都完全看不清楚。推動這些不同問題的科學進展,需要辛勤研究、創造發明,並且融合理論努力和實驗室方法。因此,讓人深感訝異的是,關於意識的討論就像是獨樹一格,被賦予了特殊地位,它是一個獨特的問題,而不只是一個難以對付且不能解決的問題。有些意識主題的作者,試圖藉由推動名為「泛心論」(panpsychism)的極端提議來克服僵局。
以意識和心智好像可以彼此互換的方式來談論它們,這點相當有問題。問題更大的是,他們將意識和心智視為無所不在的現象,存在於所有的活生物中,屬於生命狀態不可或缺的部分。所有單細胞生物和所有植物都可透過它們分到的意識來考量。既然如此,那為什麼要止步於活生物呢?對有些人來說,就連整個宇宙與其中的所有石頭都被視為有意識和有心智。
推動這些提議的理由跟一個不公正的立場有關,亦即了解心智其他面向的努力還不足以解決意識的問題。我看不到任何證據顯示情況確實如此。普通生物學、神經生物學、心理學和心智哲學都內含解決意識的問題所必需的工具,甚至在解決心智本身組構的深層潛在問題上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物理學同樣能派上用場。
在意識研究中的一個主要議題,涉及現在眾所周知的「艱難問題(難題)」,這是哲學家大衛.查爾默斯(David Chalmers)提出的名詞。用他的話來說,問題的一個重要面向是指「大腦中的物理過程為何與如何產生意識經驗?」
簡而言之,問題牽涉到所謂不可能解釋名為大腦—由數十億名為神經元的物質實體組成,透過幾兆個突觸相互連結—的物理化學裝置可以產生心智狀態,更別說是有意識的心智狀態。
大腦如何能產生與特定個體始終相連的心智狀態呢?此外,這些大腦產生的狀態如何能感覺像是某些什麼,就像哲學家湯瑪斯.內格爾(Thomas Nagel)認為的那樣?
然而,艱難問題的生物公式其實站不住腳。詢問為什麼「大腦中」的物理過程竟然會產生意識經驗,本身是個錯誤的問題。雖然大腦是意識產生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沒有任何跡象透露大腦僅僅產生意識。
相反地,生物身體本身的非神經組織對創造任何有意識的時刻也有重要貢獻,必須作為問題解答的一部分。這主要是經由感受的混合過程發生,我們認為這是製造意識心智的關鍵促成因素。
「我有意識」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就想像得到的最簡單程度,它的意思是,在我描述自己有意識的特定時刻,我的心智擁有自發地將我認定為其所有人的知識。從根本上來說,知識以各種方式與我自己有關:(a)我的身體:透過身體,我不斷經由感受得知或多或少的細節;(b)加上我從記憶中回想的事實,這些事實可能屬於(或不屬於)知覺時刻,也是我自己不可或缺的部分。
使心智有意識的知識盛宴,規模可大可小,端看與會的貴賓有多少,但某些賓客不只是尊貴,還有參加的義務。讓我一一點名他們:首先是,關於我的身體當前運作的一些知識;再來是,從最近與很久以前的記憶中提取的一些知識,關於我此刻是誰和我曾經是誰。
我絕對不會笨得說出意識就是這麼簡單,因為它一點都不簡單。低估由那麼多活動零件與接合點所產生的複雜性,真的是一點好處都沒有。
然而,儘管意識很複雜,但從心智上來說,弄懂它是由什麼組成似乎並非(或不必保持)神祕不可思議或不可能。
我對我們活生物體—我們稱為神經的部分以及我們很容易忽略而不當一回事的「身體其餘部位」的部分—如何調製出能產生充滿感受和個人參照感之心智狀態的過程,滿滿都是欽佩。但欽佩不需要神祕來加持。神祕的概念以及生物學解釋超出我們理解範圍的想法都不適用於此。問題可以找到答案,謎題終究獲得解決。儘管如此,人們依然對這件事充滿敬畏:組合幾個相對透明的功能編排,最終為我們帶來了什麼益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