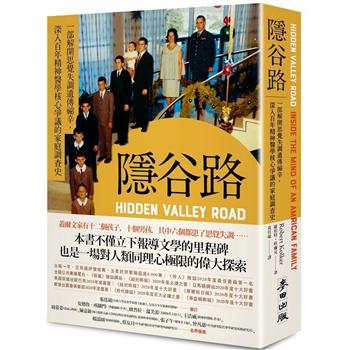2
一九○三年
德國,德勒斯登
一個有嚴重偏執與妄想的精神病患將他的親身經歷記錄下來,成了迄今受到最多分析、解讀、鑽研與探討的精神病例。而這樣的自傳簡直成了一本有字天書,幾乎無法閱讀,此事箇中頗有一定的道理。
丹尼爾.保羅.史瑞伯(Daniel Paul Schreber)成長於十九世紀中葉的德國。他的父親是那個年代著名的兒童教養專家,經常把子女當成自己的理論測試對象。據信,他和哥哥小時候是莫里茲.史瑞伯(Moritz Schreber)的第一批測試者,他們嚐過父親的冷水療法、飲食、運動養生法,還有一個由木頭和皮帶製成、用來強迫兒童坐直,被稱作史瑞伯姿勢矯正器的裝置。史瑞伯熬過了童年,長大後成就非凡,先後當上律師和法官。他結了婚,有了家庭,除了在四十幾歲時曾陷入短暫憂鬱,其餘似乎一切安好。然後,他突然在五十一歲精神崩潰。他在一八九四年被診斷出「被害妄想型精神錯亂」(paranoid form of “hallucinatory insanity”),其後九年,史瑞伯住在德勒斯登附近的松嫩施泰因療養院(Sonnenstein Asylum);這是德國第一家公立精神病院。
《一位神經疾病患者的回憶錄》(Memoirs of My Nervous Illness)是關於某種神祕疾病的第一部重要著作──該病當時被稱作早發性癡呆(dementia praecox),幾年後更名為思覺失調症(schizophrenia);史瑞伯在療養院生活的那幾年則是那本書的背景環境──至少從具體的環境而言是如此。該書出版於一九○三年,百年來,一切有關這項疾病的探討幾乎都免不了援引其中內容。到了蓋爾文家六個男孩發病的年代,現代心理學看待與治療他們的方法仍深受這個病例的論證影響。事實上,史瑞伯本人並沒有料到他的親身經歷會引發這麼大的注目。他寫這本回憶錄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爭取出院,而這說明了為什麼書中許多內容皆看似專門為一名讀者而寫,也就是收治他的保羅.艾米爾.傅萊契醫師(Dr. Paul Emil Flechsig)。本書始於他寫給傅萊契醫師的一封公開信,信中,史瑞伯先是為可能令醫師不舒服的內容致歉。史瑞伯只想澄清一件小事:傅萊契是不是過去九年來一直向他的大腦傳送祕密訊息的那個人?
在兩百多頁的篇幅中,與醫師進行宇宙間的心靈交融(史瑞伯寫道,「即使身處兩地,你照樣能影響我的神經系統」),是史瑞伯數十個詭異而神奇的經驗中的第一個,或許也是最有條有理的一個。史瑞伯以一種很可能只有他自己能破譯的方式,激情地書寫他在天上見到的兩顆太陽,以及他發現其中一顆太陽如影隨形地跟著他打轉。他用令人費解的文字說明一種大多數人都沒有注意到的、微妙的「神經語言」,洋洋灑灑寫了好多頁。他寫道,數百人的靈魂都使用這種神經語言向史瑞伯傳遞重要訊息,告訴他金星「洪水氾濫」、太陽系「支離破碎」、仙后座即將「匯聚成單一太陽」。
就此層面而言,史瑞伯和蓋爾文家的大兒子唐諾德有許多共通之處。多年後,在蓋爾文家位於隱谷路的住宅中,唐諾德會在七歲的瑪麗面前誦讀他的修士聖階禱文。史瑞伯和唐諾德一樣,相信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不僅是有形的,更是靈性的。無論是他或唐諾德或蓋爾文家的其他男孩,都並未在一定的距離之外、以超然的好奇心觀察他們的妄想;他們深陷其中,戰慄、驚奇、害怕、絕望,有時全部一湧而上。
既然無法跳脫,史瑞伯乾脆不遺餘力地把每個人拉進去──跟大家分享他的經驗。身處於他的宇宙,上一刻可能欣喜若狂,下一刻說不定就脆弱得不堪一擊。在回憶錄中,史瑞伯指控他的主治大夫傅萊契醫師使用神經語言對他施行他所謂的「靈魂謀殺」(史瑞伯解釋,靈魂很脆弱,如同「龐大的球體或纖維束」,堪比「一團棉絮或蜘蛛網」)。然後還有強暴。「由於我的病,」史瑞伯寫道,「我跟上帝產生了特殊關係,」──一種一開始極為酷似無玷受孕的關係。「我有女性生殖器官,儘管發育不良,但我的身體感覺到胎動,感受到人類胚胎生命的先兆……換句話說,發生了受精現象。」史瑞伯說他的性別出現變化,他懷孕了。他不認為這是上帝的恩賜,反而覺得受到侵犯。上帝是傅萊契醫師的共犯,甚至是「幕後黑手」,「像對待妓女般」利用他的身體。大多數時候,史瑞伯的宇宙是個可怕而緊繃的地方,充滿了恐懼。
他有一個遠大的抱負。「我的目的,」史瑞伯反思,「純粹是為了推廣一個重要領域──亦即宗教──的真知。」但事情並未如他所願。相反的,史瑞伯書寫的內容,倒是對越來越引發爭議的新興精神醫學更有貢獻得多。
最初──在人們把精神疾病的研究變成一門科學,並將其稱之為「精神醫學」(psychiatry)之前──瘋狂是靈魂的疾病,是一種活該被關進牢裡、遭到放逐或驅魔的失常現象。猶太教和基督教認為靈魂有別於肉體,靈魂是自我的本質,既可以聆聽上帝說話,也可以被魔鬼占據。掃羅王(KingSaul)是《聖經》所描述的第一個瘋子,當神的靈離開了他、惡魔的靈取而代之,他便喪失了心智。在中世紀法國,聖女貞德聽到的聲音被認為是異端邪教,是撒旦的傑作──貞德死後,人們換了一種說法,認為這是先知的聲音。即使是在當時,瘋狂的定義便已經常改來改去,變化多端。
只要稍微用心觀察,便可輕易看見瘋狂偶爾會出現在家族病史中。最有名的例子發生在王室。十五世紀,英格蘭的亨利六世國王首先出現多疑的症狀,接著變得緘默退縮,最後完全陷入妄想狀態。他的疾病成了權力鬥爭的託辭,引發了玫瑰戰爭。此病是家族遺傳:他的外祖父法國國王查理六世有同樣的病,查理的母親(波旁的讓娜)、舅父、外祖父和外曾祖父也一樣。不過,直到史瑞伯的時代,科學家和醫師才開始以生物角度探討瘋狂。一八九六年,德國精神病學家(psychiatrist)埃米爾.克雷佩林(Emil Kraepelin)採用「早發性癡呆」(dementia praecox)這個詞彙,顯示這個疾病始於年輕時期,有別於老年癡呆(praecox[早發]也是precocious[早熟]的拉丁字根)。克雷佩林認為早發性癡呆乃「毒素」所造成,或者「與迄今仍性質不明的某種腦損傷有關」。十二年後,瑞士精神病學家尤金.布魯勒(Eugen Bleuler)創造了「schizophrenia」這個術語,描述被克雷佩林統稱為早發性癡呆的大多數症狀。他也懷疑這項疾病有一定的生物因素。
布魯勒選擇使用這個新的詞彙,是因為它的拉丁字根──schizo(撕裂)──暗指心智功能出現尖銳而猛烈的分裂。後來事實證明這是個不幸的錯誤選擇。幾乎從那時起,流行文化──從《驚魂記》(Psycho)到《西碧兒》(Sybil)再到《三面夏娃》(The Three Faces of Eve)──便將思覺失調與人格分裂混為一談。錯得太離譜了。布魯勒企圖描述的是病人外在與內在世界的分裂,一種認知脫離了現實的狀態。思覺失調並非多重人格,而是在意識之外築起圍牆,最初是緩慢的,然後是突然一口氣隔絕開來,直到意識被完全包圍,再也接觸不到其他人眼中的真實世界。
不論精神病學家開始相信思覺失調症有什麼生物因素,迄今還沒有人能釐清這項疾病的確切性質。儘管起初似乎可以合理認為思覺失調症是遺傳性疾病,但這無法解釋後來某些憑空出現的病例,其中似乎也包括了史瑞伯的病例。思覺失調症的這個重大問題──家族遺傳抑或無端發生?──讓一代代理論家、治療師、生物學家以及後來的遺傳學家沉迷其中,推究到底。假如不知它的根源,何以得知應對方式?
史瑞伯的回憶錄出版八年後,佛洛伊德終於在一九一一年翻開了這本書,書中內容令他心醉神迷。這位維也納分析師兼理論家已被各方公認為探索心靈運作模式的先驅,備受推崇,而他原本對史瑞伯這類妄想症病患興趣缺缺。他在擔任神經科醫師期間見過這類病患,但他始終認為對他們進行精神分析不過是白費力氣。他認為,罹患思覺失調症意味著無藥可救──患者過於自戀,無法跟分析師進行有意義的交流,亦即無法「移情」(transference)。
但史瑞伯的書徹底扭轉了佛洛伊德的想法。書是佛洛伊德的徒弟、瑞士分析師卡爾.榮格(Carl Jung)寄來的,多年來,榮格不斷懇求他閱讀這本書。現在,佛洛伊德即使足不出戶,也可以與妄想症患者的內心世界親密接觸,窺探對方的每一個衝動。他在書裡所見到的一切,在在證實他原本對無意識的理解是正確無誤的。在向榮格致謝的信中,佛洛伊德將這本回憶錄稱為「一種啟示」。而在另一封信中,他聲稱史瑞伯本人「應該被聘為精神醫學教授和精神病院院長」。
佛洛伊德的《史瑞伯:妄想症案例的精神分析》(Psycho-Analytic Notes on an Autobiographical Account of a Case of Paranoia [Dementia Paranoides])出版於一九一一年(遺憾的是,史瑞伯在母親過世後重新住進療養院,隨後在此書出版的同年去世)。拜史瑞伯的回憶錄之賜,佛洛伊德如今堅信妄想不過是清醒夢(waking dreams)──與司空見慣的精神官能症都是由相同原因所引起, 並且可以用同樣的方式解讀。佛洛伊德發現(而如今廣為人知)的夢的符號與隱喻,他寫道,處處都呈現在這部回憶錄裡,一清二楚。佛洛伊德主張,史瑞伯的性別轉換與無性受孕象徵他對閹割的恐懼。他總結道,史瑞伯對其主治醫師傅萊契所表現出的固著(fixation)肯定與伊底帕斯情結有關。「別忘了,史瑞伯的父親也是醫師,」佛洛伊德洋洋得意地將所有線索串連起來,「他(史瑞伯)身上發生的那些荒誕神蹟,是對他父親醫術的尖酸諷刺。」
對於佛洛伊德的這番話,恐怕沒有人比榮格更覺得糾結。一九一一年三月,榮格在他位於瑞士波克羅次立(Burgholzli)的家中讀了該書初稿,立刻寫信給他的老師。他表示他覺得這本書「極其有趣,令人捧腹」,而且「文筆出色」。只有一個問題:榮格壓根不同意他的分析。榮格之所以反對,歸根究柢還是在於妄想性精神疾病的本質問題:思覺失調症是與生俱來的腦部疾患,還是生活的創傷造成?先天或後天?佛洛伊德在當時的精神醫學界獨樹一幟,堅信這項疾病完全出於「心因性」,或說是潛意識的傑作,而潛意識則很有可能由後天養成的童年經驗所形塑,或刻下了傷痕──大部分跟性有關。相較之下,榮格的看法比較傳統:思覺失調症至少有部分是器質性、生物性因素所致──很可能來自家族遺傳。
他們師徒倆經常為此爭執,多年來相持不下。不過對榮格來說,這只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他告訴佛洛伊德,不是所有事情都跟性有關──人們發瘋有時是因為別的原因,或許是某種先天因素。「在我看來,原欲(libido)的概念……必須靠遺傳因子補充其不足之處。」榮格寫道。
榮格寫了好幾封信,一再陳述同一論點。佛洛伊德從不接招;他來個相應不理,把榮格氣得半死。一九一二年,榮格發火了,開始摻雜個人情緒。「你把學生當成病人對待的作法是錯誤的,」榮格寫道,「這麼一來,你所製造的若非卑屈的兒子,就是無禮的學徒。與此同時,你始終是高高在上的父親。」
同年稍後,在紐約市福坦莫大學(Fordham University)的聽眾面前,榮格公開反對佛洛伊德,尤其強烈抨擊佛洛伊德對史瑞伯病例的解析。他表示,思覺失調「不能光靠喪失情慾來解釋」。
榮格知道佛洛伊德會把這番話視為異端。「他錯得離譜,」榮格後來省思「因為他根本不明白思覺失調的本質。」
佛洛伊德與榮格的決裂,大致在於兩人對瘋狂的本質所持的看法不同。早期精神分析中最偉大的夥伴關係就此結束,但有關思覺失調的根源與本質的爭論才剛剛開始。
一世紀後,估計全世界每一百人就有一人罹患思覺失調症──美國有超過三百萬人罹病,全球則有八千兩百萬名患者。根據一項統計數字,確診患者占據了全美精神病院的三分之一床位。而在另一項數據中,每年大約有四成的成年病患沒有接受任何治療。每二十個思覺失調症案例中就有一人以自殺告終。
如今,學術界充斥了數百篇以史瑞伯為主題的論文,每篇都遠遠跳出了佛洛伊德與榮格的範疇,以自己的角度探討這名患者以及他罹患的疾病。法國精神分析大師兼後結構主義教父賈克.拉岡(Jacques Lacan)表示,史瑞伯的問題源於挫折感,因為他無法成為他自己的母親所欠缺的陽具。到了一九七○年代,法國社會學家兼反文化運動代表人物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則認為史瑞伯是某種烈士,是社會力壓垮個人精神的犧牲者。直至今日,史瑞伯的回憶錄仍是一張完美的空白畫布,而史瑞伯本人則是理想的精神病患:一個無法還嘴的病人。與此同時,史瑞伯案例引發的思覺失調核心爭論──先天或後天?──已和我們對這項疾病的認知密不可分。
蓋爾文兄弟生於這個爭論年代。等到他們一一成年,醫界的看法已如不斷分裂的細胞,眾說紛紜。有人站在生物化學的角度,有人站在神經醫學的角度,有人則認為這項疾病跟遺傳有關,更有人持環境或病毒或細菌相關的說法。多倫多的精神病史學家愛德華.蕭爾特(Edward Shorter)曾說,「思覺失調症是一項有各種理論的疾病。」──而二十世紀輕而易舉便出現了數百種理論。至於思覺失調症的真相──病因為何、如何緩解──則依舊牢牢鎖在患者的內心深處。
試圖找出思覺失調生物之鑰的研究人員從未停止尋覓可以一舉平息先天與後天爭議的研究對象或實驗方法。但是,倘若有一大家子的史瑞伯──一群擁有相同遺傳基因、條件完備的研究對象──會怎麼樣?倘若有一組病例夠多的樣本,可以在其中某些或甚至全部病例中找到特定、可辨識的因子,會怎麼樣?
倘若有一個像唐和咪咪.蓋爾文這樣生了十二個小孩的家庭?事情會怎麼樣?
一九○三年
德國,德勒斯登
一個有嚴重偏執與妄想的精神病患將他的親身經歷記錄下來,成了迄今受到最多分析、解讀、鑽研與探討的精神病例。而這樣的自傳簡直成了一本有字天書,幾乎無法閱讀,此事箇中頗有一定的道理。
丹尼爾.保羅.史瑞伯(Daniel Paul Schreber)成長於十九世紀中葉的德國。他的父親是那個年代著名的兒童教養專家,經常把子女當成自己的理論測試對象。據信,他和哥哥小時候是莫里茲.史瑞伯(Moritz Schreber)的第一批測試者,他們嚐過父親的冷水療法、飲食、運動養生法,還有一個由木頭和皮帶製成、用來強迫兒童坐直,被稱作史瑞伯姿勢矯正器的裝置。史瑞伯熬過了童年,長大後成就非凡,先後當上律師和法官。他結了婚,有了家庭,除了在四十幾歲時曾陷入短暫憂鬱,其餘似乎一切安好。然後,他突然在五十一歲精神崩潰。他在一八九四年被診斷出「被害妄想型精神錯亂」(paranoid form of “hallucinatory insanity”),其後九年,史瑞伯住在德勒斯登附近的松嫩施泰因療養院(Sonnenstein Asylum);這是德國第一家公立精神病院。
《一位神經疾病患者的回憶錄》(Memoirs of My Nervous Illness)是關於某種神祕疾病的第一部重要著作──該病當時被稱作早發性癡呆(dementia praecox),幾年後更名為思覺失調症(schizophrenia);史瑞伯在療養院生活的那幾年則是那本書的背景環境──至少從具體的環境而言是如此。該書出版於一九○三年,百年來,一切有關這項疾病的探討幾乎都免不了援引其中內容。到了蓋爾文家六個男孩發病的年代,現代心理學看待與治療他們的方法仍深受這個病例的論證影響。事實上,史瑞伯本人並沒有料到他的親身經歷會引發這麼大的注目。他寫這本回憶錄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爭取出院,而這說明了為什麼書中許多內容皆看似專門為一名讀者而寫,也就是收治他的保羅.艾米爾.傅萊契醫師(Dr. Paul Emil Flechsig)。本書始於他寫給傅萊契醫師的一封公開信,信中,史瑞伯先是為可能令醫師不舒服的內容致歉。史瑞伯只想澄清一件小事:傅萊契是不是過去九年來一直向他的大腦傳送祕密訊息的那個人?
在兩百多頁的篇幅中,與醫師進行宇宙間的心靈交融(史瑞伯寫道,「即使身處兩地,你照樣能影響我的神經系統」),是史瑞伯數十個詭異而神奇的經驗中的第一個,或許也是最有條有理的一個。史瑞伯以一種很可能只有他自己能破譯的方式,激情地書寫他在天上見到的兩顆太陽,以及他發現其中一顆太陽如影隨形地跟著他打轉。他用令人費解的文字說明一種大多數人都沒有注意到的、微妙的「神經語言」,洋洋灑灑寫了好多頁。他寫道,數百人的靈魂都使用這種神經語言向史瑞伯傳遞重要訊息,告訴他金星「洪水氾濫」、太陽系「支離破碎」、仙后座即將「匯聚成單一太陽」。
就此層面而言,史瑞伯和蓋爾文家的大兒子唐諾德有許多共通之處。多年後,在蓋爾文家位於隱谷路的住宅中,唐諾德會在七歲的瑪麗面前誦讀他的修士聖階禱文。史瑞伯和唐諾德一樣,相信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不僅是有形的,更是靈性的。無論是他或唐諾德或蓋爾文家的其他男孩,都並未在一定的距離之外、以超然的好奇心觀察他們的妄想;他們深陷其中,戰慄、驚奇、害怕、絕望,有時全部一湧而上。
既然無法跳脫,史瑞伯乾脆不遺餘力地把每個人拉進去──跟大家分享他的經驗。身處於他的宇宙,上一刻可能欣喜若狂,下一刻說不定就脆弱得不堪一擊。在回憶錄中,史瑞伯指控他的主治大夫傅萊契醫師使用神經語言對他施行他所謂的「靈魂謀殺」(史瑞伯解釋,靈魂很脆弱,如同「龐大的球體或纖維束」,堪比「一團棉絮或蜘蛛網」)。然後還有強暴。「由於我的病,」史瑞伯寫道,「我跟上帝產生了特殊關係,」──一種一開始極為酷似無玷受孕的關係。「我有女性生殖器官,儘管發育不良,但我的身體感覺到胎動,感受到人類胚胎生命的先兆……換句話說,發生了受精現象。」史瑞伯說他的性別出現變化,他懷孕了。他不認為這是上帝的恩賜,反而覺得受到侵犯。上帝是傅萊契醫師的共犯,甚至是「幕後黑手」,「像對待妓女般」利用他的身體。大多數時候,史瑞伯的宇宙是個可怕而緊繃的地方,充滿了恐懼。
他有一個遠大的抱負。「我的目的,」史瑞伯反思,「純粹是為了推廣一個重要領域──亦即宗教──的真知。」但事情並未如他所願。相反的,史瑞伯書寫的內容,倒是對越來越引發爭議的新興精神醫學更有貢獻得多。
最初──在人們把精神疾病的研究變成一門科學,並將其稱之為「精神醫學」(psychiatry)之前──瘋狂是靈魂的疾病,是一種活該被關進牢裡、遭到放逐或驅魔的失常現象。猶太教和基督教認為靈魂有別於肉體,靈魂是自我的本質,既可以聆聽上帝說話,也可以被魔鬼占據。掃羅王(KingSaul)是《聖經》所描述的第一個瘋子,當神的靈離開了他、惡魔的靈取而代之,他便喪失了心智。在中世紀法國,聖女貞德聽到的聲音被認為是異端邪教,是撒旦的傑作──貞德死後,人們換了一種說法,認為這是先知的聲音。即使是在當時,瘋狂的定義便已經常改來改去,變化多端。
只要稍微用心觀察,便可輕易看見瘋狂偶爾會出現在家族病史中。最有名的例子發生在王室。十五世紀,英格蘭的亨利六世國王首先出現多疑的症狀,接著變得緘默退縮,最後完全陷入妄想狀態。他的疾病成了權力鬥爭的託辭,引發了玫瑰戰爭。此病是家族遺傳:他的外祖父法國國王查理六世有同樣的病,查理的母親(波旁的讓娜)、舅父、外祖父和外曾祖父也一樣。不過,直到史瑞伯的時代,科學家和醫師才開始以生物角度探討瘋狂。一八九六年,德國精神病學家(psychiatrist)埃米爾.克雷佩林(Emil Kraepelin)採用「早發性癡呆」(dementia praecox)這個詞彙,顯示這個疾病始於年輕時期,有別於老年癡呆(praecox[早發]也是precocious[早熟]的拉丁字根)。克雷佩林認為早發性癡呆乃「毒素」所造成,或者「與迄今仍性質不明的某種腦損傷有關」。十二年後,瑞士精神病學家尤金.布魯勒(Eugen Bleuler)創造了「schizophrenia」這個術語,描述被克雷佩林統稱為早發性癡呆的大多數症狀。他也懷疑這項疾病有一定的生物因素。
布魯勒選擇使用這個新的詞彙,是因為它的拉丁字根──schizo(撕裂)──暗指心智功能出現尖銳而猛烈的分裂。後來事實證明這是個不幸的錯誤選擇。幾乎從那時起,流行文化──從《驚魂記》(Psycho)到《西碧兒》(Sybil)再到《三面夏娃》(The Three Faces of Eve)──便將思覺失調與人格分裂混為一談。錯得太離譜了。布魯勒企圖描述的是病人外在與內在世界的分裂,一種認知脫離了現實的狀態。思覺失調並非多重人格,而是在意識之外築起圍牆,最初是緩慢的,然後是突然一口氣隔絕開來,直到意識被完全包圍,再也接觸不到其他人眼中的真實世界。
不論精神病學家開始相信思覺失調症有什麼生物因素,迄今還沒有人能釐清這項疾病的確切性質。儘管起初似乎可以合理認為思覺失調症是遺傳性疾病,但這無法解釋後來某些憑空出現的病例,其中似乎也包括了史瑞伯的病例。思覺失調症的這個重大問題──家族遺傳抑或無端發生?──讓一代代理論家、治療師、生物學家以及後來的遺傳學家沉迷其中,推究到底。假如不知它的根源,何以得知應對方式?
史瑞伯的回憶錄出版八年後,佛洛伊德終於在一九一一年翻開了這本書,書中內容令他心醉神迷。這位維也納分析師兼理論家已被各方公認為探索心靈運作模式的先驅,備受推崇,而他原本對史瑞伯這類妄想症病患興趣缺缺。他在擔任神經科醫師期間見過這類病患,但他始終認為對他們進行精神分析不過是白費力氣。他認為,罹患思覺失調症意味著無藥可救──患者過於自戀,無法跟分析師進行有意義的交流,亦即無法「移情」(transference)。
但史瑞伯的書徹底扭轉了佛洛伊德的想法。書是佛洛伊德的徒弟、瑞士分析師卡爾.榮格(Carl Jung)寄來的,多年來,榮格不斷懇求他閱讀這本書。現在,佛洛伊德即使足不出戶,也可以與妄想症患者的內心世界親密接觸,窺探對方的每一個衝動。他在書裡所見到的一切,在在證實他原本對無意識的理解是正確無誤的。在向榮格致謝的信中,佛洛伊德將這本回憶錄稱為「一種啟示」。而在另一封信中,他聲稱史瑞伯本人「應該被聘為精神醫學教授和精神病院院長」。
佛洛伊德的《史瑞伯:妄想症案例的精神分析》(Psycho-Analytic Notes on an Autobiographical Account of a Case of Paranoia [Dementia Paranoides])出版於一九一一年(遺憾的是,史瑞伯在母親過世後重新住進療養院,隨後在此書出版的同年去世)。拜史瑞伯的回憶錄之賜,佛洛伊德如今堅信妄想不過是清醒夢(waking dreams)──與司空見慣的精神官能症都是由相同原因所引起, 並且可以用同樣的方式解讀。佛洛伊德發現(而如今廣為人知)的夢的符號與隱喻,他寫道,處處都呈現在這部回憶錄裡,一清二楚。佛洛伊德主張,史瑞伯的性別轉換與無性受孕象徵他對閹割的恐懼。他總結道,史瑞伯對其主治醫師傅萊契所表現出的固著(fixation)肯定與伊底帕斯情結有關。「別忘了,史瑞伯的父親也是醫師,」佛洛伊德洋洋得意地將所有線索串連起來,「他(史瑞伯)身上發生的那些荒誕神蹟,是對他父親醫術的尖酸諷刺。」
對於佛洛伊德的這番話,恐怕沒有人比榮格更覺得糾結。一九一一年三月,榮格在他位於瑞士波克羅次立(Burgholzli)的家中讀了該書初稿,立刻寫信給他的老師。他表示他覺得這本書「極其有趣,令人捧腹」,而且「文筆出色」。只有一個問題:榮格壓根不同意他的分析。榮格之所以反對,歸根究柢還是在於妄想性精神疾病的本質問題:思覺失調症是與生俱來的腦部疾患,還是生活的創傷造成?先天或後天?佛洛伊德在當時的精神醫學界獨樹一幟,堅信這項疾病完全出於「心因性」,或說是潛意識的傑作,而潛意識則很有可能由後天養成的童年經驗所形塑,或刻下了傷痕──大部分跟性有關。相較之下,榮格的看法比較傳統:思覺失調症至少有部分是器質性、生物性因素所致──很可能來自家族遺傳。
他們師徒倆經常為此爭執,多年來相持不下。不過對榮格來說,這只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他告訴佛洛伊德,不是所有事情都跟性有關──人們發瘋有時是因為別的原因,或許是某種先天因素。「在我看來,原欲(libido)的概念……必須靠遺傳因子補充其不足之處。」榮格寫道。
榮格寫了好幾封信,一再陳述同一論點。佛洛伊德從不接招;他來個相應不理,把榮格氣得半死。一九一二年,榮格發火了,開始摻雜個人情緒。「你把學生當成病人對待的作法是錯誤的,」榮格寫道,「這麼一來,你所製造的若非卑屈的兒子,就是無禮的學徒。與此同時,你始終是高高在上的父親。」
同年稍後,在紐約市福坦莫大學(Fordham University)的聽眾面前,榮格公開反對佛洛伊德,尤其強烈抨擊佛洛伊德對史瑞伯病例的解析。他表示,思覺失調「不能光靠喪失情慾來解釋」。
榮格知道佛洛伊德會把這番話視為異端。「他錯得離譜,」榮格後來省思「因為他根本不明白思覺失調的本質。」
佛洛伊德與榮格的決裂,大致在於兩人對瘋狂的本質所持的看法不同。早期精神分析中最偉大的夥伴關係就此結束,但有關思覺失調的根源與本質的爭論才剛剛開始。
一世紀後,估計全世界每一百人就有一人罹患思覺失調症──美國有超過三百萬人罹病,全球則有八千兩百萬名患者。根據一項統計數字,確診患者占據了全美精神病院的三分之一床位。而在另一項數據中,每年大約有四成的成年病患沒有接受任何治療。每二十個思覺失調症案例中就有一人以自殺告終。
如今,學術界充斥了數百篇以史瑞伯為主題的論文,每篇都遠遠跳出了佛洛伊德與榮格的範疇,以自己的角度探討這名患者以及他罹患的疾病。法國精神分析大師兼後結構主義教父賈克.拉岡(Jacques Lacan)表示,史瑞伯的問題源於挫折感,因為他無法成為他自己的母親所欠缺的陽具。到了一九七○年代,法國社會學家兼反文化運動代表人物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則認為史瑞伯是某種烈士,是社會力壓垮個人精神的犧牲者。直至今日,史瑞伯的回憶錄仍是一張完美的空白畫布,而史瑞伯本人則是理想的精神病患:一個無法還嘴的病人。與此同時,史瑞伯案例引發的思覺失調核心爭論──先天或後天?──已和我們對這項疾病的認知密不可分。
蓋爾文兄弟生於這個爭論年代。等到他們一一成年,醫界的看法已如不斷分裂的細胞,眾說紛紜。有人站在生物化學的角度,有人站在神經醫學的角度,有人則認為這項疾病跟遺傳有關,更有人持環境或病毒或細菌相關的說法。多倫多的精神病史學家愛德華.蕭爾特(Edward Shorter)曾說,「思覺失調症是一項有各種理論的疾病。」──而二十世紀輕而易舉便出現了數百種理論。至於思覺失調症的真相──病因為何、如何緩解──則依舊牢牢鎖在患者的內心深處。
試圖找出思覺失調生物之鑰的研究人員從未停止尋覓可以一舉平息先天與後天爭議的研究對象或實驗方法。但是,倘若有一大家子的史瑞伯──一群擁有相同遺傳基因、條件完備的研究對象──會怎麼樣?倘若有一組病例夠多的樣本,可以在其中某些或甚至全部病例中找到特定、可辨識的因子,會怎麼樣?
倘若有一個像唐和咪咪.蓋爾文這樣生了十二個小孩的家庭?事情會怎麼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