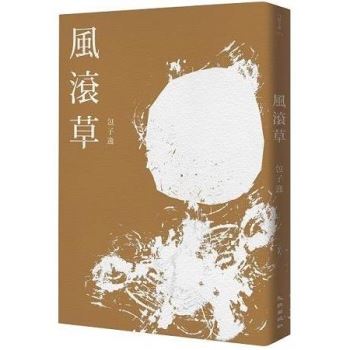節慶的樣子
每年感恩節過後,秋景都殘了,風偶爾颳起來枯枝一樣刺,此時紐約133街和Lenox大道街角賣耶誕樹的攤子總會準時出現。
來自羅德島的大鬍子D這時候總會趕來紐約賣耶誕樹。他是位年輕的木匠和音樂家,夏天當木匠、唱團彈琴謀生,冬天就到紐約街頭賣耶誕樹,負責大夜班。
值夜班不但寂寞,而且日夜顛倒,每天晚上上工的時候,南方34街閃亮的帝國大廈和他遙遙相望,尖筆一樣彩色的帝冠,就像明信片一樣好看,證明他確實來到了紐約,可是這些年來,他總是匆匆來去,趕在耶誕夜回家過節,一次都沒有造訪過那棟樓。他和帝國大廈就這樣保持著永恆而止乎禮的距離,像黑夜不斷錯過白晝。
大鬍子D的攤子架設在一家99分錢廉價商店門前空地,橫跨半條街,耶誕樹夾道,掛了許多燈泡和松枝花環,空氣中瀰漫著松香,根據攤子老板Ray(值白天班的人)的說法,因為是長期抗戰,所以儘量把路邊攤搞得溫馨一點,希望多多少少有點家的味道。
他們在路邊架了一座避寒的小亭子,裡面擺了一支吉他,亭外擺了一架用六大顆電池充電的陽春電子琴,三更半夜路上沒有人的時候,大鬍子D就會彈琴作樂,或者打開小筆電看電影。
小亭子裡有位固定班底:一隻拉布拉多和哈士奇混血狗。她有雙冰山一樣水藍的眼睛,乳牛一樣的毛色,名叫Tundra(苔原),讓人想起阿拉斯加秋天醉酒似的風景。
第一次碰到苔原的時候她四歲。苔原二十四小時幫忙顧攤,因為已經連續來了幾年,又性情溫和,和附近鄰居有了交情,有些養狗人家出門遛狗的時候都會來樹攤串串門子,順便也把苔原帶出去散步,也因此苔原莫名交了一堆紐約的犬友,也許對紐約的認識比主人更廣更遠。
我不太清楚耶誕樹的價格,但是肩膀高的小耶誕樹要價大概二十五美元,如果一棵樹要長五年才能長到那樣的高度,一年約莫值五元。兩倍高又兩倍胖的樹價也翻一倍,大概五十美金。想到一棵樹活了這麼多年,只為了榮耀幾個晚上的慶典,總是覺得不明所以。偶爾想起農夫巡邏修剪耶誕樹的樣子,會不會有種同時走在育嬰房和墳場的衝突感呢?年年和大鬍子D見面,有了些交情,偶爾特別天寒地凍,還會特地泡杯熱可可或熱咖啡去慰勞他。有一年他趁空檔用木匠技藝做了一隻可愛的麋鹿回送當作耶誕禮物,拿回家擺在冰箱上,麋鹿前腳長後腳短,脖子可以扭動,有種君臨天下的姿態,雄赳赳氣昂昂的。麋鹿的鹿角是插上去的兩根松枝,松綠撐了三季,到秋天才漸漸黃去。不久大鬍子D又來了,剛好可以換上一副新的鹿角。一年就這樣過了,隔年在路上看到苔原,她似乎身型也長了些,性格還是一樣,薄雪般溫柔沉靜。
客人來了,一棵樹被選上,擺在一個中空桶子內用網子包起,鋸掉一點樹幹底部,附上支架,最後被拖去某戶張燈結綵的人家盡最後的義務。
將這些記錄下來的那天深夜氣溫華氏三十八度左右,沒有風,可是感覺特別凍。我對這個攤子抱著複雜的情感,看到它好像看到一部分的自己,長出一圈年輪。
歲末,許多事連根截斷,又有許多事漸漸長成了節慶的樣子。
人不在國外,耶誕節就沒有了具體的感覺。想起往日耶誕節在紐約時街上的空寂,那些張燈結綵的裝飾、乾冰一樣無所不在的耶誕樂曲,以及唏囌囌包禮物和拆禮物的感覺和聲音,覺得很不真實,萬般皆過眼雲煙。
台北的耶誕節怎麼看都是虛的,現在無論如何都已經無法重新凝聚高中時期狂寫卡片分送同學的那種興致,至於和朋友擠在舞台前聽歌手排隊唱靡靡之音的熱情,經過了這麼多年工作和歷練的琢磨,早早剩下餘灰。不管如何,那三角柱的耶誕樹從來沒有感動過我,無論耶誕節在這些年來增添了多少個人的情感回憶,尤其在國外的那幾年,看過了那麼多的耶誕樹,還有那麼多載耶誕樹去回收廠絞爛的垃圾車,漸漸只想到一群生靈活了個那麼多年,只為了去裝飾那熱鬧,真是無比慘烈。也許是我畢竟不是個基督教派薰陶下長大的孩子,聖經永遠只會是我的文學讀本而不是精神指標,耶穌只是兩千多年前出生而胸懷若谷的歷史人物,這個節似乎欠缺臨場感和深刻烙印,只能落得像一層膩人的糖霜,讓人想隨手剝去。
至於近年流行的交換禮物,我們都常收到如惡夢一場的廉價品,許多人甚至趁機出清家中從沒被真心喜愛過的塵封廢物,虛與尾蛇的背叛感比忽然獲知耶誕老人不存在還沮喪。儘管這樣說,我雖然不特別過節,也不在意任何形式的慶祝,但我並不輕視過節,或者那些喜歡找各種名堂來慶祝、來展現驚喜的活動,如果可以,我也偶爾湊個熱鬧,在這熱鬧之中,感受人們的努力。
無論那表現的形式有多麼俗嗆,我總覺得,真誠地享受和營造那樣感覺的人,只要不是可悲地只是想抓住可以搪塞孤獨的浮木,毫無靈魂地因循習慣或為了面子而慶祝,他們都有種人性的可愛,只因為他們有一種想要點燃快樂的企圖。很多人如果不靠這些日子來團圓、熱鬧一下,他們就會因為生活的枯寂,而漸漸喪失了和人相聚與向上的活力,像繩子鬆脫的船,找不到港口,並且過於方便地忘記對他們所愛的人表達自己的愛,永遠地被一種幾乎沒有目標的平淡日子給綁架;所以有個什麼週年慶、某某節、生日和慶XX的名堂似乎是好的,它們就如同收費站,在年年月月的定點,等著向生命的過客收取做人應有的熱情。
我不特別過節,但我並不覺得這有任何超然之處,如同某些人誤解的那樣,或者某些人引以為豪的那樣。
不特別過節的人,如果日子就此過得意興闌珊,什麼都無所謂,我反而覺得他們需要好好找個生活中的某個重點來來慶祝慶祝,就算慶祝的名目和奈米一樣小也無所謂,那目的只是像重新尋找性感帶,或拿個槌子敲自己膝蓋檢查自己還有踢腳的靈活反應,替生活加點柴火,確定日子不會過凍,如此而已。
大嬸了沒
無論走到哪裡,城裡總會看見許多獨立經營的大嬸服飾專賣店,它們的特色是永恆地與潮流脫勾,屬於大嬸的小宇宙在那裡靜靜地運轉,年復一年複製使人安心的高遮蔽功能版型,一如婦女們集體在中短燙鬈的髮型中找到歸屬。
在店內浩瀚的保守陳列中,珠花與亮片,亮彩與荷葉邊替陳腔濫調的時裝爭取到許多小小突破,這些婉轉的個性展現與誇張的折扣聯合催情,使婦女們衝動(但自以為精明地)買下訂價過高的衣物,在狹窄的冷氣房裡感覺華貴,感覺獵捕到一種類似舶來品或獨立自主的情懷。這些永恆的大嬸服飾專賣店向來門可羅雀,儘管門口經常出現巨大的拍賣字眼。我從不明白它們如何能夠支付得起冷氣和租金,當四周的小吃店兵敗如山倒,小本經營的商家與翻漲的房租揮汗搏鬥,連街巷間的私人SPA護膚美甲會館也經營得如履薄冰之際,大嬸服飾店內雍容的毛領、神情高傲臉頰凹陷的塑膠洋模特兒,卻能熬過世事滄桑海枯石爛,處於時光凝結的不敗之地,永遠那樣好整以暇,好像隨便活一活也不講求養生,默默就活成了人瑞。
當然, 大嬸服飾店並不希罕像我這樣路過探頭探腦的無聊人士,後來我才明白,這些店家就像地方軍閥一樣,各自培訓了忠心耿耿的鄰里主顧部隊,靠著無邊無際的問候、狀似姊妹情深的金蘭結盟,老鼠會一樣蒐集了一群定期來噓寒問暖 「捧場」的女人,有了忠貞澆灌,場子便像在沙漠中隆起的拉斯維加斯,被捧了起來。
這些大嬸不像市場買貨的那些人倉促,市場的客人扯下懸掛在青菜豬肉中間的二九九成衣殺價包一包付錢的過程特別有效率,主要是擔憂拖太久剛買的新鮮蛤蠣就要悶壞;他們也不像百貨公司亂槍打鳥夢遊型的貴婦,貴婦們蒐集的是響亮的品牌,還有一種質料在指尖摸起來「真的是好」的秘密觸感,那是經年累月的血拼換來的評鑑力,更何況百貨公司只能在商言商,那些說要幫你修眉型、送你防皺眼膜的人,利益輸送的意圖太明顯。大嬸服飾店是這兩種購物方式去蕪存菁的總合。
李渝精彩內斂的〈九重葛〉短篇故事中有一家雜貨店,最能呼應大嬸服飾店的奧義,其功能介於公私之間的灰色地帶,有點像塔台,專門接收聽眾爆料或call in點播憂傷情歌的那種,買醬油買線衫都不是重點,大嬸們攜手來到一地,相濡以沫互相較勁,為此感到巨大,汲取操控的力量,為了這種意義,大嬸服飾店很難倒閉。
大嬸特別享受「彼此交換秘密」的快感,彷彿秘密可以換得友情,我經常看到身邊明明交情不深的大嬸們,他們莫名在某種天時地利人和的時空下,突然像炸開的潘朵拉盒子,猛烈交換彼此深層的秘密,並且在過程當中獲得一種酣暢的、惺惺相惜的短暫幻覺。大嬸服飾店提供的就是那個平行世界的魔幻時空。然而離開了那個時空,他們或許很快就為了極其渺小的事情互相憎恨了起來。因為這些大嬸服飾店的存在, 我漸漸領悟到大嬸是一種形容詞,大嬸若大嬸得可愛並不討人厭,問題只出在於有更多大嬸大嬸得很陰沉。他們像多毛的海底軟體動物伸出觸角蠕蠕地刺探著,在看不見的時刻出沒在某些角落,成群結黨,在皺摺間藏了刺人碎語和過份的自負或天真。
有些人年紀輕輕就活成了大嬸,有些男人聲音低沉腳毛很多但還是徹徹底底的大嬸,你看我們現在的報章雜誌,絕大多數都是非比尋常之大嬸的了。
吸菸的拳擊手
傑瑞是某個夏日連續兩個禮拜幾乎天天來我住所後院修補後牆的愛爾蘭工人,和他搭檔的是一位來自英國威爾斯的工人戴夫。
傑瑞大概五十多歲,害羞而且不善言詞,有時候我甚至覺得他腦袋魯鈍,可是為了某些原因,這兩個工匠之中我特別喜歡他,因為他不是個聰明人,所以他的嘴從來不違背他的心,直率,而且難以說謊,我覺得他非常可愛。
美國的愛爾蘭移民崇尚拳擊運動,這個運動幾乎牽動著民族榮辱的敏感神經,因為愛爾蘭拳擊手曾經在美國長期立於不敗之地。傑瑞年輕的時候是中量級的拳擊手,每次看到他,老是會想到上個世紀的愛爾蘭裔拳擊明星,他們酷愛把看起來像衛生褲的緊身褲拉到肚臍眼上面,同手同腳擺出戰鬥姿勢,讓人不免想到《岸上風雲》(On The Waterfront)電影裡活得血跡斑斑的新移民。
從拳擊退休以後,傑瑞改行當建築工,專長是修砌磚石。他每天十點半上床睡覺,早上五點半起床,從八點半左右開始上工,下午約三點之前就會收工。和許多愛爾蘭人一樣,喜歡喝個一兩杯,甚至一早就喝。他抽很多菸,抽菸的手勢很特別,手掌向上,用中指和拇指捏住菸屁股,露出意味深長的表情。他這特別的抽菸手勢洩漏出他是愛爾蘭人的故事,因為愛爾蘭風大,手心向上拿菸的手勢,可以防風。他每次都抽到菸頭幾乎要從指尖消失才把菸丟掉。每回我探出窗口,通常只看見傑瑞在辛勤工作,至於那位相對油條,喜歡套交情,嘴巴比較厲害的戴夫,每次我探頭出去觀望的時候,十之有八九都是在休息。我因此不能不偏袒傑瑞,因為他竟然有這樣一位花拳繡腿的夥伴,我很替他抱不平。而且,顯然傑瑞的技術比戴夫高超許多──戴夫雖然說得一口好話,可是通常只是說得好聽而已,他上工的模樣只讓人感到他的心早已經下工,平常喜歡炫燿自己的積蓄(他說,我有積架你知道嗎?他還說自己有個度假的別墅,老婆在銀行是上層經理),然而一旦被發現自己的工作沒有做徹底,他又會把自己貶低,說:我們是工人,可不是藝術家。
我倒是覺得傑瑞的技術,已經是一種無庸置疑的藝術。每一種用經驗支撐起來的技藝,做到某種程度,就有讓人感動的魔力。
那天,傑瑞在後院替後牆補上一層染成梅子粉顏色的水泥,戴夫照例只是做些鏟水泥之類的小差。傑瑞努力了老半天,臉上都沾上了顏色,這個時候戴夫還要來碎嘴,說:「傑瑞,你今天晚上要紅得像印地安人了。」那個時候,我覺得戴夫很煩。
也許是因為種種讓我私心偏愛的原由,我覺得傑瑞一口厚重的愛爾蘭口音也非常可愛。他總是稱呼我dear,而我就突然覺得跟他親近了起來,儘管我們並不常對話,而且我每次要拿水給他,他總是習慣客套推辭,說:別擔心我。
我想,傑瑞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他自然散發出來的故事性,他從來不炫燿,但是從他口中聽來的瑣事,總讓人覺得他經常受人佔便宜,因而特別讓人想要保護他。然而,他可曾經是個不折不扣的拳擊手,一個必須在台上用拳頭把對手擊倒的拳擊手!
修牆之事過了兩年,傑瑞的身影早就像被愛爾蘭的風給吹到很遠的地方,還陰天起霧,早已不知去向。怎料到某日突然聽到一則悲傷的消息:傑瑞耶誕節前因為菸蒂引起的火災意外,葬身於窩居的公寓。
據說他住的地方是房東非法改建的地下室隔間客房,沒有逃生口。聽說傑瑞原本已經逃出現場,但是為了搶救一些現金,回頭進去,從此沒有出來。
我特別感到哀傷的是,他一生菸不離手,最後也是那指尖的一點火星送他離開世間,而他要挽救的現金金額照理說也不到賣命的程度──否則也不會住在那樣窘困的地下室了。
我說啊,傑瑞,傻人怎麼沒有傻福呢?
每年感恩節過後,秋景都殘了,風偶爾颳起來枯枝一樣刺,此時紐約133街和Lenox大道街角賣耶誕樹的攤子總會準時出現。
來自羅德島的大鬍子D這時候總會趕來紐約賣耶誕樹。他是位年輕的木匠和音樂家,夏天當木匠、唱團彈琴謀生,冬天就到紐約街頭賣耶誕樹,負責大夜班。
值夜班不但寂寞,而且日夜顛倒,每天晚上上工的時候,南方34街閃亮的帝國大廈和他遙遙相望,尖筆一樣彩色的帝冠,就像明信片一樣好看,證明他確實來到了紐約,可是這些年來,他總是匆匆來去,趕在耶誕夜回家過節,一次都沒有造訪過那棟樓。他和帝國大廈就這樣保持著永恆而止乎禮的距離,像黑夜不斷錯過白晝。
大鬍子D的攤子架設在一家99分錢廉價商店門前空地,橫跨半條街,耶誕樹夾道,掛了許多燈泡和松枝花環,空氣中瀰漫著松香,根據攤子老板Ray(值白天班的人)的說法,因為是長期抗戰,所以儘量把路邊攤搞得溫馨一點,希望多多少少有點家的味道。
他們在路邊架了一座避寒的小亭子,裡面擺了一支吉他,亭外擺了一架用六大顆電池充電的陽春電子琴,三更半夜路上沒有人的時候,大鬍子D就會彈琴作樂,或者打開小筆電看電影。
小亭子裡有位固定班底:一隻拉布拉多和哈士奇混血狗。她有雙冰山一樣水藍的眼睛,乳牛一樣的毛色,名叫Tundra(苔原),讓人想起阿拉斯加秋天醉酒似的風景。
第一次碰到苔原的時候她四歲。苔原二十四小時幫忙顧攤,因為已經連續來了幾年,又性情溫和,和附近鄰居有了交情,有些養狗人家出門遛狗的時候都會來樹攤串串門子,順便也把苔原帶出去散步,也因此苔原莫名交了一堆紐約的犬友,也許對紐約的認識比主人更廣更遠。
我不太清楚耶誕樹的價格,但是肩膀高的小耶誕樹要價大概二十五美元,如果一棵樹要長五年才能長到那樣的高度,一年約莫值五元。兩倍高又兩倍胖的樹價也翻一倍,大概五十美金。想到一棵樹活了這麼多年,只為了榮耀幾個晚上的慶典,總是覺得不明所以。偶爾想起農夫巡邏修剪耶誕樹的樣子,會不會有種同時走在育嬰房和墳場的衝突感呢?年年和大鬍子D見面,有了些交情,偶爾特別天寒地凍,還會特地泡杯熱可可或熱咖啡去慰勞他。有一年他趁空檔用木匠技藝做了一隻可愛的麋鹿回送當作耶誕禮物,拿回家擺在冰箱上,麋鹿前腳長後腳短,脖子可以扭動,有種君臨天下的姿態,雄赳赳氣昂昂的。麋鹿的鹿角是插上去的兩根松枝,松綠撐了三季,到秋天才漸漸黃去。不久大鬍子D又來了,剛好可以換上一副新的鹿角。一年就這樣過了,隔年在路上看到苔原,她似乎身型也長了些,性格還是一樣,薄雪般溫柔沉靜。
客人來了,一棵樹被選上,擺在一個中空桶子內用網子包起,鋸掉一點樹幹底部,附上支架,最後被拖去某戶張燈結綵的人家盡最後的義務。
將這些記錄下來的那天深夜氣溫華氏三十八度左右,沒有風,可是感覺特別凍。我對這個攤子抱著複雜的情感,看到它好像看到一部分的自己,長出一圈年輪。
歲末,許多事連根截斷,又有許多事漸漸長成了節慶的樣子。
人不在國外,耶誕節就沒有了具體的感覺。想起往日耶誕節在紐約時街上的空寂,那些張燈結綵的裝飾、乾冰一樣無所不在的耶誕樂曲,以及唏囌囌包禮物和拆禮物的感覺和聲音,覺得很不真實,萬般皆過眼雲煙。
台北的耶誕節怎麼看都是虛的,現在無論如何都已經無法重新凝聚高中時期狂寫卡片分送同學的那種興致,至於和朋友擠在舞台前聽歌手排隊唱靡靡之音的熱情,經過了這麼多年工作和歷練的琢磨,早早剩下餘灰。不管如何,那三角柱的耶誕樹從來沒有感動過我,無論耶誕節在這些年來增添了多少個人的情感回憶,尤其在國外的那幾年,看過了那麼多的耶誕樹,還有那麼多載耶誕樹去回收廠絞爛的垃圾車,漸漸只想到一群生靈活了個那麼多年,只為了去裝飾那熱鬧,真是無比慘烈。也許是我畢竟不是個基督教派薰陶下長大的孩子,聖經永遠只會是我的文學讀本而不是精神指標,耶穌只是兩千多年前出生而胸懷若谷的歷史人物,這個節似乎欠缺臨場感和深刻烙印,只能落得像一層膩人的糖霜,讓人想隨手剝去。
至於近年流行的交換禮物,我們都常收到如惡夢一場的廉價品,許多人甚至趁機出清家中從沒被真心喜愛過的塵封廢物,虛與尾蛇的背叛感比忽然獲知耶誕老人不存在還沮喪。儘管這樣說,我雖然不特別過節,也不在意任何形式的慶祝,但我並不輕視過節,或者那些喜歡找各種名堂來慶祝、來展現驚喜的活動,如果可以,我也偶爾湊個熱鬧,在這熱鬧之中,感受人們的努力。
無論那表現的形式有多麼俗嗆,我總覺得,真誠地享受和營造那樣感覺的人,只要不是可悲地只是想抓住可以搪塞孤獨的浮木,毫無靈魂地因循習慣或為了面子而慶祝,他們都有種人性的可愛,只因為他們有一種想要點燃快樂的企圖。很多人如果不靠這些日子來團圓、熱鬧一下,他們就會因為生活的枯寂,而漸漸喪失了和人相聚與向上的活力,像繩子鬆脫的船,找不到港口,並且過於方便地忘記對他們所愛的人表達自己的愛,永遠地被一種幾乎沒有目標的平淡日子給綁架;所以有個什麼週年慶、某某節、生日和慶XX的名堂似乎是好的,它們就如同收費站,在年年月月的定點,等著向生命的過客收取做人應有的熱情。
我不特別過節,但我並不覺得這有任何超然之處,如同某些人誤解的那樣,或者某些人引以為豪的那樣。
不特別過節的人,如果日子就此過得意興闌珊,什麼都無所謂,我反而覺得他們需要好好找個生活中的某個重點來來慶祝慶祝,就算慶祝的名目和奈米一樣小也無所謂,那目的只是像重新尋找性感帶,或拿個槌子敲自己膝蓋檢查自己還有踢腳的靈活反應,替生活加點柴火,確定日子不會過凍,如此而已。
大嬸了沒
無論走到哪裡,城裡總會看見許多獨立經營的大嬸服飾專賣店,它們的特色是永恆地與潮流脫勾,屬於大嬸的小宇宙在那裡靜靜地運轉,年復一年複製使人安心的高遮蔽功能版型,一如婦女們集體在中短燙鬈的髮型中找到歸屬。
在店內浩瀚的保守陳列中,珠花與亮片,亮彩與荷葉邊替陳腔濫調的時裝爭取到許多小小突破,這些婉轉的個性展現與誇張的折扣聯合催情,使婦女們衝動(但自以為精明地)買下訂價過高的衣物,在狹窄的冷氣房裡感覺華貴,感覺獵捕到一種類似舶來品或獨立自主的情懷。這些永恆的大嬸服飾專賣店向來門可羅雀,儘管門口經常出現巨大的拍賣字眼。我從不明白它們如何能夠支付得起冷氣和租金,當四周的小吃店兵敗如山倒,小本經營的商家與翻漲的房租揮汗搏鬥,連街巷間的私人SPA護膚美甲會館也經營得如履薄冰之際,大嬸服飾店內雍容的毛領、神情高傲臉頰凹陷的塑膠洋模特兒,卻能熬過世事滄桑海枯石爛,處於時光凝結的不敗之地,永遠那樣好整以暇,好像隨便活一活也不講求養生,默默就活成了人瑞。
當然, 大嬸服飾店並不希罕像我這樣路過探頭探腦的無聊人士,後來我才明白,這些店家就像地方軍閥一樣,各自培訓了忠心耿耿的鄰里主顧部隊,靠著無邊無際的問候、狀似姊妹情深的金蘭結盟,老鼠會一樣蒐集了一群定期來噓寒問暖 「捧場」的女人,有了忠貞澆灌,場子便像在沙漠中隆起的拉斯維加斯,被捧了起來。
這些大嬸不像市場買貨的那些人倉促,市場的客人扯下懸掛在青菜豬肉中間的二九九成衣殺價包一包付錢的過程特別有效率,主要是擔憂拖太久剛買的新鮮蛤蠣就要悶壞;他們也不像百貨公司亂槍打鳥夢遊型的貴婦,貴婦們蒐集的是響亮的品牌,還有一種質料在指尖摸起來「真的是好」的秘密觸感,那是經年累月的血拼換來的評鑑力,更何況百貨公司只能在商言商,那些說要幫你修眉型、送你防皺眼膜的人,利益輸送的意圖太明顯。大嬸服飾店是這兩種購物方式去蕪存菁的總合。
李渝精彩內斂的〈九重葛〉短篇故事中有一家雜貨店,最能呼應大嬸服飾店的奧義,其功能介於公私之間的灰色地帶,有點像塔台,專門接收聽眾爆料或call in點播憂傷情歌的那種,買醬油買線衫都不是重點,大嬸們攜手來到一地,相濡以沫互相較勁,為此感到巨大,汲取操控的力量,為了這種意義,大嬸服飾店很難倒閉。
大嬸特別享受「彼此交換秘密」的快感,彷彿秘密可以換得友情,我經常看到身邊明明交情不深的大嬸們,他們莫名在某種天時地利人和的時空下,突然像炸開的潘朵拉盒子,猛烈交換彼此深層的秘密,並且在過程當中獲得一種酣暢的、惺惺相惜的短暫幻覺。大嬸服飾店提供的就是那個平行世界的魔幻時空。然而離開了那個時空,他們或許很快就為了極其渺小的事情互相憎恨了起來。因為這些大嬸服飾店的存在, 我漸漸領悟到大嬸是一種形容詞,大嬸若大嬸得可愛並不討人厭,問題只出在於有更多大嬸大嬸得很陰沉。他們像多毛的海底軟體動物伸出觸角蠕蠕地刺探著,在看不見的時刻出沒在某些角落,成群結黨,在皺摺間藏了刺人碎語和過份的自負或天真。
有些人年紀輕輕就活成了大嬸,有些男人聲音低沉腳毛很多但還是徹徹底底的大嬸,你看我們現在的報章雜誌,絕大多數都是非比尋常之大嬸的了。
吸菸的拳擊手
傑瑞是某個夏日連續兩個禮拜幾乎天天來我住所後院修補後牆的愛爾蘭工人,和他搭檔的是一位來自英國威爾斯的工人戴夫。
傑瑞大概五十多歲,害羞而且不善言詞,有時候我甚至覺得他腦袋魯鈍,可是為了某些原因,這兩個工匠之中我特別喜歡他,因為他不是個聰明人,所以他的嘴從來不違背他的心,直率,而且難以說謊,我覺得他非常可愛。
美國的愛爾蘭移民崇尚拳擊運動,這個運動幾乎牽動著民族榮辱的敏感神經,因為愛爾蘭拳擊手曾經在美國長期立於不敗之地。傑瑞年輕的時候是中量級的拳擊手,每次看到他,老是會想到上個世紀的愛爾蘭裔拳擊明星,他們酷愛把看起來像衛生褲的緊身褲拉到肚臍眼上面,同手同腳擺出戰鬥姿勢,讓人不免想到《岸上風雲》(On The Waterfront)電影裡活得血跡斑斑的新移民。
從拳擊退休以後,傑瑞改行當建築工,專長是修砌磚石。他每天十點半上床睡覺,早上五點半起床,從八點半左右開始上工,下午約三點之前就會收工。和許多愛爾蘭人一樣,喜歡喝個一兩杯,甚至一早就喝。他抽很多菸,抽菸的手勢很特別,手掌向上,用中指和拇指捏住菸屁股,露出意味深長的表情。他這特別的抽菸手勢洩漏出他是愛爾蘭人的故事,因為愛爾蘭風大,手心向上拿菸的手勢,可以防風。他每次都抽到菸頭幾乎要從指尖消失才把菸丟掉。每回我探出窗口,通常只看見傑瑞在辛勤工作,至於那位相對油條,喜歡套交情,嘴巴比較厲害的戴夫,每次我探頭出去觀望的時候,十之有八九都是在休息。我因此不能不偏袒傑瑞,因為他竟然有這樣一位花拳繡腿的夥伴,我很替他抱不平。而且,顯然傑瑞的技術比戴夫高超許多──戴夫雖然說得一口好話,可是通常只是說得好聽而已,他上工的模樣只讓人感到他的心早已經下工,平常喜歡炫燿自己的積蓄(他說,我有積架你知道嗎?他還說自己有個度假的別墅,老婆在銀行是上層經理),然而一旦被發現自己的工作沒有做徹底,他又會把自己貶低,說:我們是工人,可不是藝術家。
我倒是覺得傑瑞的技術,已經是一種無庸置疑的藝術。每一種用經驗支撐起來的技藝,做到某種程度,就有讓人感動的魔力。
那天,傑瑞在後院替後牆補上一層染成梅子粉顏色的水泥,戴夫照例只是做些鏟水泥之類的小差。傑瑞努力了老半天,臉上都沾上了顏色,這個時候戴夫還要來碎嘴,說:「傑瑞,你今天晚上要紅得像印地安人了。」那個時候,我覺得戴夫很煩。
也許是因為種種讓我私心偏愛的原由,我覺得傑瑞一口厚重的愛爾蘭口音也非常可愛。他總是稱呼我dear,而我就突然覺得跟他親近了起來,儘管我們並不常對話,而且我每次要拿水給他,他總是習慣客套推辭,說:別擔心我。
我想,傑瑞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他自然散發出來的故事性,他從來不炫燿,但是從他口中聽來的瑣事,總讓人覺得他經常受人佔便宜,因而特別讓人想要保護他。然而,他可曾經是個不折不扣的拳擊手,一個必須在台上用拳頭把對手擊倒的拳擊手!
修牆之事過了兩年,傑瑞的身影早就像被愛爾蘭的風給吹到很遠的地方,還陰天起霧,早已不知去向。怎料到某日突然聽到一則悲傷的消息:傑瑞耶誕節前因為菸蒂引起的火災意外,葬身於窩居的公寓。
據說他住的地方是房東非法改建的地下室隔間客房,沒有逃生口。聽說傑瑞原本已經逃出現場,但是為了搶救一些現金,回頭進去,從此沒有出來。
我特別感到哀傷的是,他一生菸不離手,最後也是那指尖的一點火星送他離開世間,而他要挽救的現金金額照理說也不到賣命的程度──否則也不會住在那樣窘困的地下室了。
我說啊,傑瑞,傻人怎麼沒有傻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