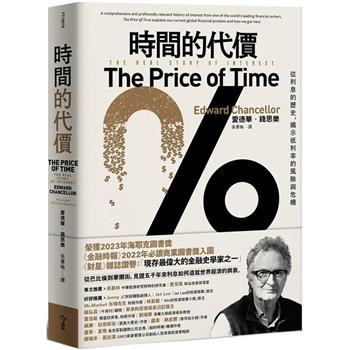引言 無政府主義者與資本主義者 [節錄]
1849年,法國國民議會(The French National Assembly)兩位議員在一份社會主義刊物《人民之聲》(La Voix du peuple)上掀起論戰。一邊是自稱無政府主義者、擔任《人民之聲》固定撰稿人的皮耶-約瑟夫.普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時至今日,他以名言「財產即是竊盜」(Property is theft)為人所知。站在論戰立場另一邊的,是自由貿易的擁護者與時事評論人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他以辛辣嘲諷的經濟寓言聞名。巴斯夏經常提出立論反對無益的政府干預,比方說,他就擬了一份「製燭人請願書」(Petition of the Candlemakers),請願書裡的製燭人要求立法規定人們要拉上百葉窗和遮陽簾以阻擋陽光,這樣才能賣出更多蠟燭。
這兩人辯駁的主題,是利率的合法性。普魯東以老派的觀點切入,宣稱收取利息是「高利剝削與劫掠之舉」。說高利剝削,是因為這是不平等的交易,理由是收息的人並未失去出借的資本,因此無權要求借款人返回更高的金額。利息是一種「給懶散的獎勵,(也是)引發不平等的根源,亦造成貧窮」。普魯東改編了他最膾炙人口的名言繼續說下去,「我要說,利息即是竊盜。」
他的評論還沒結束。普魯東控訴利息長期下來會讓債務利滾利,隨著時間過去貸款的金額會比地球的金環還大。他指稱,貸放收息會減緩貨幣流通的速度,導致「商業停滯,工業產業發生失業,抑制農業,而且各地會出現愈來愈多急迫的破產事件」。 利息助長階級之間的仇恨,拉高產品價格,從而限縮了消費。普魯東說,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勞工無力負擔他們用雙手製造出來的物品。「利息就像是雙面刃,」普魯東總結道,「不管是哪一邊砍在你身上都是殺戮。」
普魯東的惡言謾罵沒有任何原創概念,他的指控傳承自古代。他用希伯來語「neschek」來指稱利息,這個詞在詞源上是毒蛇噬咬的意思。普魯東的辯詞都在打高空,而且不斷重複,他的經濟分析沒什麼深度。喬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在《經濟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裡喟嘆普魯東完全沒有能力做分析。普魯東認為,調降利息「馬上就會在法蘭西共和國和全歐洲產生無可計量的成果」,債務不會增加,無力償還與破產的問題會減少,可提升消費,也可以確保勞工都能就業。一旦社會裡身為寄生蟲階級的放款人不能再收取利息,勞工的所得就會提高。
巴斯夏不同意。他力主利息是一種給互相交換服務的公平報酬。放款的人讓借錢的人有一段時間可以使用資本,時間是有價值的。巴斯夏引用1748年班哲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在《給年輕工匠的忠告》(Advice to a Young Tradesman)裡講過的名言:「時間很寶貴,時間就是金錢,時間構成了人生。」這番論調主張利息「自然、公平又合法,有益又有利,連對於支付利息的人來說都是這樣。」 資本才不會抑制經濟產出,反之,資本會讓勞動更有生產力。巴斯夏相信,資本也不會引燃階級仇恨,反之,資本對每個人都好,「尤其是長久以來受苦的階級」。
「獎勵」會提升借錢意願
巴斯夏預見,如果普魯東的計畫付諸實行,將會製造災難。如果借錢這件事沒有得到獎勵,就不會有人把錢拿出來借給他人。限制人們付錢取用資本,將會摧毀資本,儲蓄也會消失。普魯東的國民銀行貸放的前提是要求來借錢的勞工人民提供擔保,如果這些人提不出擔保,他們的處境也不會更好。取消利息只會讓富裕者得利。巴斯夏在寫給普魯東的信裡寫道:
在你的系統中,富有的人確實可以免費借到錢,但貧窮的人不管用什麼價格都借不到。
當有錢人來到銀行時,銀行行員會對他說:「你有償債能力,錢在這裡,我們不求回報借給你。」
但倘若勞動階級膽敢現身,銀行行員就會問他:「你的擔保呢?你是要用土地、房子還是產品來擔保?」
「我只有我的雙手和我的誠實誠信。」工人說。
「這樣我們不放心,我們秉持著明智嚴謹來經營銀行,我們不能免費借你錢。」
巴斯夏得出的結論是:「宣揚免息借款對勞動階級來說是一大災難。」到時候企業會減少,但勞工的人數還是跟之前一樣多,薪資會降低,資本則在全國流竄。如果銀行免息借錢,紙幣就會氾濫。國家失序,永遠都處在隨時可能陷入萬劫不復的邊緣。巴斯夏用以下的結論為兩人之間的書信往來畫上句點:「免息貸款在科學上很無稽,牽涉到的是對既得利益者的仇恨、階級之間的敵意和粗野暴行。」
但普魯東和巴斯夏至少在一件事上達成協議。普魯東相信,透過貨幣改革可以達成1848年革命的目標。他說,把利率訂在0.75%,可以達成七成五的革命目標。「免費借貸是社會主義的終極說詞、終極口號與終極努力。」巴斯夏反駁道,「創建一座用之不竭的紙幣工廠,這就是你的解決方案。」廢止資本可收取的利息,將會導致「借貸消失」與資本死亡。
普魯東和巴斯夏兩人的口角之爭各執一詞,雙方都不聽對方說了什麼。兩人之間的書信往來,調性愈來愈尖酸。普魯東在最後一封信裡斷言巴斯夏不用腦,擱筆前的最後一句話是:「巴斯夏先生,您死定了。」這倒也是實話。巴斯夏罹患了肺結核,一年後死於羅馬,享年49歲。
看得見的與看不見的後果
巴斯夏過世當年,他寫了最後一本小書。在《看得見的與看不見的》(What is Seen and What is Not Seen)這本小書裡,巴斯夏力促讀者好好想一想各種經濟行為造成的廣泛結果,而不只去思考對特定的受益人有何影響:
在經濟領域裡,一個習慣、一項機構或是一條法律不會只引發一次性的效果,而會是一系列的。這些效果一開始時隨即出現,一有原因馬上出現結果,這是看得見的;其他的效果會在之後才發生,那是看不見的。如果我們可以預見,那就太幸運了。
經濟學家的優劣就在這裡高下立判。糟糕的經濟學家看的是明顯的結果,出色的經濟學家則會考量看得見的與必須預見的效果。
巴斯夏說,糟糕的經濟學家追求目前的小惠,不去管接下來的大不利;出色的經濟學家則追求未來的大利,甘冒近期必須承受一些小小不利的風險。美國記者亨利.赫茲利特(Henry Hazlitt)1946年出版了暢銷書《一課經濟學》(Economics in One Lesson),就在書中闡述了巴斯夏的破窗寓言。赫茲特利和巴斯夏一樣,都喟嘆著:
人一直以來的傾向就是僅看得到特定政策的直接效果或是對於特定群體造成的影響,無力去探問政策長期會造成什麼結果,而且不僅限於特殊群體,更要從所有群體的角度來看。忽略次級結果是一大謬見。
赫茲利特批評的是當時的「新」經濟學,他認為,新經濟學僅考慮到政策對於特殊群體的短期效果,忽略了對整個社會的長期影響。他攻擊他稱之為「盲信」(fetish)的充分就業(full employment)。赫茲利特寫道,要讓熊彼得的「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概念實際動起來,不可打壓,因為這對經濟體的健全度來說極為重要,我們必須讓垂死的產業死亡,就像要壯大正在成長的產業一樣。赫茲利特把競爭性經濟中的價格體系比擬作蒸汽引擎的自動調節器。只要有人試著阻止價格下跌,結果只會是讓無效率的生產者留在產業裡。
赫茲利特主張,資本的供給由利率來調節,然而,一種「憂心利率『過高』的病態恐懼」使得政府祭出壓低貨幣價格的政策。赫茲利特寫道:
寬鬆的貨幣,引發經濟面的扭曲……它常會鼓動投機性極高的冒險行為,除非在催生出這些活動的人為條件之下,不然無以為繼。從供給面來說,人為調降利率有礙正常的節約、儲蓄與投資,減少資本累積,拖慢產能的成長,這是「積極人士」公開表示急於帶動的「經濟成長」。
赫茲利特引用威廉.葛拉罕.蘇納(William Graham Sumner)1883年的知名論文,當作結論。蘇納在這篇論文中寫到A和B設計了一套用來幫助X的計畫,但忽略了會對C造成的衝擊。C成為「被遺忘的人」,是一個「從來沒有人想到的人,是改革者、社會理論家和慈善家造成的受害者」。
普魯東的夢想成真
2008年9月雷曼兄弟銀行(Lehman Brothers)破產之後,新自由主義派(neoliberal)的經濟學家就著手執行無政府主義者普魯東設計的革命計畫。各國央行把利率推到五千年以來的新低點,在歐洲和日本,利率甚至為負值,這是前所未有的事。但,結果並不如普魯東所預測,巴斯夏對於免費借貸的殘酷預言反而顯然比較接近事實。
各國央行沾沾自喜,自認讓華爾街回復平靜,憂心出現通貨緊縮(deflation)的想法被斥為無稽,失業率大幅下滑,這些都是零利率「看得到」的效果;零利率的次級效果大部分都看不見,但只要認真去找就會發現。
2012年,加拿大經濟學家威廉.懷特(William White)發表一篇很短的報告,題為〈超寬鬆貨幣政策與意外結果法則〉(Ultra Easy Monetary Policy and the Law of Unintended Consequences)。懷特指出,大幅調降利率以鼓勵家庭多花錢、少存錢,事實上這只是把未來的消費提前,人們必須存更多錢,才能達成之前已經決定的目標;而且,由於利率普遍偏低,人要花更多時間,才能存夠讓他們覺得安心的儲備金。
有關當局相信,低利率會帶動企業投資,但懷特認為企業實際上會減少投資。此外,超寬鬆貨幣也會導致資本錯誤配置。創造性破壞受到壓抑。懷特總結道:「很有可能,寬鬆的貨幣實際上是阻礙,而無法帶動資本重新從生產力較低的資源,配置到較高的資源。」
調降借貸成本之後,超寬鬆貨幣變成一種誘因,鼓勵投資人去冒不該冒的風險。在此同時,保險公司和年金產品供應商則要辛辛苦苦面對低利時代。由於借錢的成本很低,政府恣意地提高國家債務。在最近期的分析中,認為寬鬆的貨幣效果只是把算總帳的日子延後。「在經濟走下坡時採行激進的貨幣寬鬆政策並非『免費的午餐』,」懷特總結,「在最好的情況下,能買到時間重新調整經濟體。但在現實中,這些機會都被浪費了。」華爾街的人講的就是「以拖待變」。
懷特也指出,貨幣政策決策者可能也得面對採行超低利率所製造出來的問題。懷特這篇論文於2012年問世,幾年之後,聯準會啟動暫時性的緊縮循環,但很快又放棄想要把利率帶回正常水準的企圖,反而重回印鈔票和降利率的老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政策利率直接調到零。懷特預測,各國央行將會被迫在提供信貸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這件事也成真了。在疫情嚴重的2020年,各國央行更進一步,直接為政府提供資金以因應相關支出,一如懷特的預測(請參見本書後記:天翻地覆時)。
巴斯夏主張免費借貸對勞工來說是一大災難,並未言過其實。次貸危機(subprime mortgage crisis)過後,各家銀行對信用分數低的個人與小企業提高了放款利率 ;另一方面,私募股權大亨以及和華爾街交好的人,則可以用極低廉的價格借資金。危機過後那十年,所得幾乎沒有成長,到處都只有低薪的工作,低薪的人被迫用高利率借錢,存下來的錢能賺得的實質報酬也是負值,富裕的投資客與企業則用便宜的代價借錢,大賺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