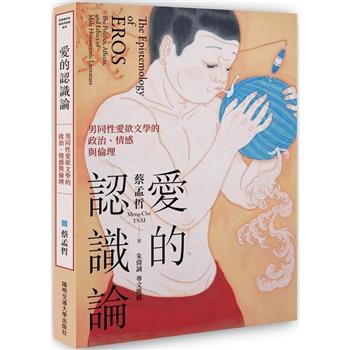│第一章│愛的認識論:民國時期社會主義視野的同性愛論述
本章主要是考察民國時期圍繞在「同性愛」並涉及婚姻家庭、政治經濟、社會國家,甚至是人類世界及宇宙的性/別論述。進一步分析當時受社會主義(Socialism)思潮影響的知識青年,如何思考性/親密關係議題與提出以友愛為基礎的社會連帶想像,並聚焦探討這些青年在不同社會主義脈絡中的性/別論述,回到歷史語境且分析他們如何將同性愛視為一種具有革新動能的社會力量,或一種導向更為自由與平等的生產關係和社會關係之實踐。他們在社會主義視野裡所設想的關於同性戀的「愛的認識論」——我稱之為「愛的關係模式」——把民國時期來自翻譯、議論、報導和文學創作等等的同性愛論述,區分為三種同性戀認識框架:以西方性科學來認識同性愛的醫學框架稱為「癖的病理化模式」,以媒體對同性愛軼事的獵奇報導及其衍生出的道德化批判稱為「窺的道德模式」,以及本章所要聚焦說明的「愛的關係模式」。
過去研究已顯示民國時期的社會思潮及知識形構受浪漫主義(Romanticism)、烏托邦主義(Utopianism)、達爾文主義(Darwinism)進化論以及戀愛至上主義(恋愛至上主義)等跨國思潮的影響,例如張灝(1937-)指出五四思想與文學的雙重傾向及兩歧特性:一方面重視科學理性主義(Rationalism),另一方面展現出浪漫主義和烏托邦主義的樣貌。(註1)而我將通過分析這些青年的性/別論述,來說明同性戀的認識論構作同時關乎個人與社會應如何變革之政治方案在意識形態上的根本差異;對他們來說,同性戀是在不同經濟條件和歷史過程生產出來的特定關係與情感樣態,或是推動、或是依隨著整體社會轉型的生命情境與關係實踐,而非單獨的、孤立出來的身分認同變項。
首先,我聚焦探討馬克思主義(Marxism)青年胡秋原的〈同性愛的研究〉一文中的「友愛與社會」一節,(註2) 透過分析胡的論述一方面肯認同性愛的生存價值及社會意義,另一方面則將這種個體的情感強度及特質透過友誼概念擴大到集體連帶,甚至轉化為一種思想基礎或宇宙觀,展現出社會主義獨特的政治思考與倫理視域。……
│第二章│愛的桃花源:民國時期同性愛欲與啟蒙救亡的辯證
民國時期的同性愛論述仍處在紛雜混沌、未定於一尊的歷史情境中,各類論述的形式及內容相互交錯影響,出現在大小報刊雜誌與各派文學作品之中;本章延續上一章關於「愛的認識論」的討論,聚焦「愛的關係模式」在轉型時期現代文學創作場域的構成樣態,討論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在文學範疇裡的男同性愛書寫。這些文學創作一方面是在一個歷史特定的、由社會文化組成的認識世界(也包含同性戀愛)的方式中所生產出來,另一方面這些文本論述也構成人們理解、判斷、評價、感知以及信仰的認識模式。本章主要討論郁達夫(1896-1945)和郭沫若(1892-1978)─二位都是當時主張「為藝術而藝術」的創造社作家─的文學創作與自傳回憶,其所再現的同性愛欲飽含了我稱為「愛的桃花源」的情感動能以及性/親密關係的想像。我將探問他們作品中所刻意描繪或不經意洩漏的同性愛欲書寫,如何既在文本內部拓展出敘事空間、也在文本之外撐開了不同於當時「文以載道」為主要文學典範的論述空間(如胡適〔1891-1962〕所說的「須言之有物」,或文學研究會的「為人生而藝術」),並藉以指出由文學創作所構成的「愛的認識論」,其實迂迴且含蓄地回應了當時以國家之愛、民族之情為核心的啟蒙與救亡雙重論述。本章亦旁及創造社同人葉鼎洛(1897-1958)、傾向自由主義的京派代表作家沈從文(1902-1988)和提倡左翼革命文學的太陽社作家蔣光慈(1901-1931)的小說,探討所謂「師生戀」在「愛的關係模式」之特色,間接體現與呼應了這個時期關於校園同性愛與情感教育議題的正反討論。如同上一章已指出的,這些文學作品所再現的同性戀,都無法指涉單獨個人的身分認同,而是在歷史過程與社會變化脈絡下的情感樣態、關係實踐與生命情境。
1921 年6 月,郁達夫和郭沫若在留學日本時與成仿吾(1897-1984)於東京成立創造社,其核心成員有田漢(1898-1968)、張資平(1893-1959)、鄭伯奇(1895-1979)和穆木天(1900-1971)等人,包括1925 年入社但於1928 年另組太陽社的蔣光慈,以及外圍同人葉鼎落等前後共有五十二人之多。在創社初期,郁達夫直言「文藝是天才的創造物,不可以規矩來測量的」;郭沫若也表示他對於藝術的見解「終覺不當是反射的(Reflective),應當是創造的(Creative)。〔中略〕真正的藝術品當然是由於純粹充實了的主觀產出」。(註3)伊藤虎丸(1927-2003)曾分析創造社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特色乃在於:它既是日本留學生的文學青年社團,因此受到大正時期文化主義思潮的影響;它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產物,所以反映中國知識青年的苦惱和奮鬥的軌跡。(註4)他還指出這些留學生作家透過學習仿效當時日本文學主流的短篇小說與私小說之形式,提出了新的文學理論和創造新的文體,是建設中國現代文學的新貢獻。(註5)早期創造社雖仍重視文學的時代責任並強調建設新文學的使命,然而它著重作家的內心情感和藝術個性,主張「文學是自我表現」的直覺、靈感和天才的創作觀點,在文學審美上樹立起獨特且鮮明的立場;特別是「強調情感的力量及其在文學中的本體性」,追求郭沫若稱為「主情主義」的文學觀。(註6)例如郁達夫的小說、郭沫若的詩歌與田漢的戲劇作品,都表現出文學應該忠於作家自我內心要求、表達個人情感與欲望的思想傾向和藝術風格;他們的創作講求人的自由與個性解放,側重主觀精神世界的刻畫,呈現近代歐洲浪漫主義思潮的影響,不僅對當時文壇吹入新的空氣,也擊中時代精神的內核,並吸引一部分的知識青年。(註7)在1925 年上海五卅慘案之後,創造社部分成員「向左轉」支持馬克思主義與共產黨,並與魯迅(1881-1936)於1930 年在上海成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推動五四以來的文學革命轉向為革命文學的風潮。知識分子與青年學子因現實上國民革命行動受挫(北伐與清黨),而改以文學創作與翻譯等方式進行革命實踐,「革命」內涵因此從反帝反封建反軍閥的理念轉由馬克思主義等左翼理論取代,影響革命時代的知識青年與創作者。(註8)……
註:
1. 張灝,〈重返五四:論五四思想的兩歧性〉,余英時等著:《五四新論:既非文藝復興,亦非啟蒙運動》(台北:聯經,1999),頁34-40。關於浪漫主義對於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參見:李歐梵著,王宏志譯,《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北京:新星,2005),第四部分;李海燕著,修佳明譯,《心靈革命:現代中國愛情的譜系(1900-1950)》(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第三章。關於演化論對於近現代中國進化思想的影響,參見:彭小妍,〈以美為尊:張競生「新女性中心」論與達爾文「性擇」說〉,《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44 期(2014 年3 月),頁57-77;王汎森,〈時間感、歷史觀、思想與社會:進化思想在近代中國〉,《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台北:聯經,2017),頁251-276。關於戀愛至上主義對於同性愛議題的影響,詳後分析。
2. 胡秋原寫於1929 年的〈同性愛的研究〉是要回應楊憂天(生卒年不詳)同年發表於《北新》雜誌第3 卷第2 期的〈同性愛的問題〉,胡表示要向人們介紹新的研究來重估同性愛的價值和意義,戮力為同性友誼辯解。二人的論戰文章於隔年由北新書局集結為《同性愛問題討論集》出版。參見:楊憂天,〈同性愛的問題〉,《同性愛問題討論集》(上海:北新書局,1930),頁1-47;胡秋原,〈同性愛的研究〉,《同性愛問題討論集》,頁49-222。
3. 郁達夫,〈文藝私見〉,《郁達夫全集.第十卷》(浙江: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頁22。郭沫若,〈論國內的評壇及我對於創作上的態度〉,饒鴻競等編:《創造社資料(上)》(北京:知識產權,2010),頁14。
4. 伊藤虎丸著,孫猛、徐江、李冬木等譯,《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中日近現代比較文學初探》(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1995]),頁143-144。
5. 伊藤虎丸,《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中日近現代比較文學初探》,頁154。
6. 程光煒等,《中國現代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頁45-47、84。
7. 咸立強,《尋找歸宿的流浪者:創造社研究》(上海:東方,2006),頁134-142。
8. 蘇敏逸,〈轉折年代知識青年的文學視界:以《紅黑》為考察對象〉,《清華中文學報》第19 期(2018 年6 月),頁265-313。
本章主要是考察民國時期圍繞在「同性愛」並涉及婚姻家庭、政治經濟、社會國家,甚至是人類世界及宇宙的性/別論述。進一步分析當時受社會主義(Socialism)思潮影響的知識青年,如何思考性/親密關係議題與提出以友愛為基礎的社會連帶想像,並聚焦探討這些青年在不同社會主義脈絡中的性/別論述,回到歷史語境且分析他們如何將同性愛視為一種具有革新動能的社會力量,或一種導向更為自由與平等的生產關係和社會關係之實踐。他們在社會主義視野裡所設想的關於同性戀的「愛的認識論」——我稱之為「愛的關係模式」——把民國時期來自翻譯、議論、報導和文學創作等等的同性愛論述,區分為三種同性戀認識框架:以西方性科學來認識同性愛的醫學框架稱為「癖的病理化模式」,以媒體對同性愛軼事的獵奇報導及其衍生出的道德化批判稱為「窺的道德模式」,以及本章所要聚焦說明的「愛的關係模式」。
過去研究已顯示民國時期的社會思潮及知識形構受浪漫主義(Romanticism)、烏托邦主義(Utopianism)、達爾文主義(Darwinism)進化論以及戀愛至上主義(恋愛至上主義)等跨國思潮的影響,例如張灝(1937-)指出五四思想與文學的雙重傾向及兩歧特性:一方面重視科學理性主義(Rationalism),另一方面展現出浪漫主義和烏托邦主義的樣貌。(註1)而我將通過分析這些青年的性/別論述,來說明同性戀的認識論構作同時關乎個人與社會應如何變革之政治方案在意識形態上的根本差異;對他們來說,同性戀是在不同經濟條件和歷史過程生產出來的特定關係與情感樣態,或是推動、或是依隨著整體社會轉型的生命情境與關係實踐,而非單獨的、孤立出來的身分認同變項。
首先,我聚焦探討馬克思主義(Marxism)青年胡秋原的〈同性愛的研究〉一文中的「友愛與社會」一節,(註2) 透過分析胡的論述一方面肯認同性愛的生存價值及社會意義,另一方面則將這種個體的情感強度及特質透過友誼概念擴大到集體連帶,甚至轉化為一種思想基礎或宇宙觀,展現出社會主義獨特的政治思考與倫理視域。……
│第二章│愛的桃花源:民國時期同性愛欲與啟蒙救亡的辯證
民國時期的同性愛論述仍處在紛雜混沌、未定於一尊的歷史情境中,各類論述的形式及內容相互交錯影響,出現在大小報刊雜誌與各派文學作品之中;本章延續上一章關於「愛的認識論」的討論,聚焦「愛的關係模式」在轉型時期現代文學創作場域的構成樣態,討論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在文學範疇裡的男同性愛書寫。這些文學創作一方面是在一個歷史特定的、由社會文化組成的認識世界(也包含同性戀愛)的方式中所生產出來,另一方面這些文本論述也構成人們理解、判斷、評價、感知以及信仰的認識模式。本章主要討論郁達夫(1896-1945)和郭沫若(1892-1978)─二位都是當時主張「為藝術而藝術」的創造社作家─的文學創作與自傳回憶,其所再現的同性愛欲飽含了我稱為「愛的桃花源」的情感動能以及性/親密關係的想像。我將探問他們作品中所刻意描繪或不經意洩漏的同性愛欲書寫,如何既在文本內部拓展出敘事空間、也在文本之外撐開了不同於當時「文以載道」為主要文學典範的論述空間(如胡適〔1891-1962〕所說的「須言之有物」,或文學研究會的「為人生而藝術」),並藉以指出由文學創作所構成的「愛的認識論」,其實迂迴且含蓄地回應了當時以國家之愛、民族之情為核心的啟蒙與救亡雙重論述。本章亦旁及創造社同人葉鼎洛(1897-1958)、傾向自由主義的京派代表作家沈從文(1902-1988)和提倡左翼革命文學的太陽社作家蔣光慈(1901-1931)的小說,探討所謂「師生戀」在「愛的關係模式」之特色,間接體現與呼應了這個時期關於校園同性愛與情感教育議題的正反討論。如同上一章已指出的,這些文學作品所再現的同性戀,都無法指涉單獨個人的身分認同,而是在歷史過程與社會變化脈絡下的情感樣態、關係實踐與生命情境。
1921 年6 月,郁達夫和郭沫若在留學日本時與成仿吾(1897-1984)於東京成立創造社,其核心成員有田漢(1898-1968)、張資平(1893-1959)、鄭伯奇(1895-1979)和穆木天(1900-1971)等人,包括1925 年入社但於1928 年另組太陽社的蔣光慈,以及外圍同人葉鼎落等前後共有五十二人之多。在創社初期,郁達夫直言「文藝是天才的創造物,不可以規矩來測量的」;郭沫若也表示他對於藝術的見解「終覺不當是反射的(Reflective),應當是創造的(Creative)。〔中略〕真正的藝術品當然是由於純粹充實了的主觀產出」。(註3)伊藤虎丸(1927-2003)曾分析創造社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特色乃在於:它既是日本留學生的文學青年社團,因此受到大正時期文化主義思潮的影響;它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產物,所以反映中國知識青年的苦惱和奮鬥的軌跡。(註4)他還指出這些留學生作家透過學習仿效當時日本文學主流的短篇小說與私小說之形式,提出了新的文學理論和創造新的文體,是建設中國現代文學的新貢獻。(註5)早期創造社雖仍重視文學的時代責任並強調建設新文學的使命,然而它著重作家的內心情感和藝術個性,主張「文學是自我表現」的直覺、靈感和天才的創作觀點,在文學審美上樹立起獨特且鮮明的立場;特別是「強調情感的力量及其在文學中的本體性」,追求郭沫若稱為「主情主義」的文學觀。(註6)例如郁達夫的小說、郭沫若的詩歌與田漢的戲劇作品,都表現出文學應該忠於作家自我內心要求、表達個人情感與欲望的思想傾向和藝術風格;他們的創作講求人的自由與個性解放,側重主觀精神世界的刻畫,呈現近代歐洲浪漫主義思潮的影響,不僅對當時文壇吹入新的空氣,也擊中時代精神的內核,並吸引一部分的知識青年。(註7)在1925 年上海五卅慘案之後,創造社部分成員「向左轉」支持馬克思主義與共產黨,並與魯迅(1881-1936)於1930 年在上海成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推動五四以來的文學革命轉向為革命文學的風潮。知識分子與青年學子因現實上國民革命行動受挫(北伐與清黨),而改以文學創作與翻譯等方式進行革命實踐,「革命」內涵因此從反帝反封建反軍閥的理念轉由馬克思主義等左翼理論取代,影響革命時代的知識青年與創作者。(註8)……
註:
1. 張灝,〈重返五四:論五四思想的兩歧性〉,余英時等著:《五四新論:既非文藝復興,亦非啟蒙運動》(台北:聯經,1999),頁34-40。關於浪漫主義對於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參見:李歐梵著,王宏志譯,《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北京:新星,2005),第四部分;李海燕著,修佳明譯,《心靈革命:現代中國愛情的譜系(1900-1950)》(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第三章。關於演化論對於近現代中國進化思想的影響,參見:彭小妍,〈以美為尊:張競生「新女性中心」論與達爾文「性擇」說〉,《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44 期(2014 年3 月),頁57-77;王汎森,〈時間感、歷史觀、思想與社會:進化思想在近代中國〉,《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台北:聯經,2017),頁251-276。關於戀愛至上主義對於同性愛議題的影響,詳後分析。
2. 胡秋原寫於1929 年的〈同性愛的研究〉是要回應楊憂天(生卒年不詳)同年發表於《北新》雜誌第3 卷第2 期的〈同性愛的問題〉,胡表示要向人們介紹新的研究來重估同性愛的價值和意義,戮力為同性友誼辯解。二人的論戰文章於隔年由北新書局集結為《同性愛問題討論集》出版。參見:楊憂天,〈同性愛的問題〉,《同性愛問題討論集》(上海:北新書局,1930),頁1-47;胡秋原,〈同性愛的研究〉,《同性愛問題討論集》,頁49-222。
3. 郁達夫,〈文藝私見〉,《郁達夫全集.第十卷》(浙江: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頁22。郭沫若,〈論國內的評壇及我對於創作上的態度〉,饒鴻競等編:《創造社資料(上)》(北京:知識產權,2010),頁14。
4. 伊藤虎丸著,孫猛、徐江、李冬木等譯,《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中日近現代比較文學初探》(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1995]),頁143-144。
5. 伊藤虎丸,《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中日近現代比較文學初探》,頁154。
6. 程光煒等,《中國現代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頁45-47、84。
7. 咸立強,《尋找歸宿的流浪者:創造社研究》(上海:東方,2006),頁134-142。
8. 蘇敏逸,〈轉折年代知識青年的文學視界:以《紅黑》為考察對象〉,《清華中文學報》第19 期(2018 年6 月),頁265-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