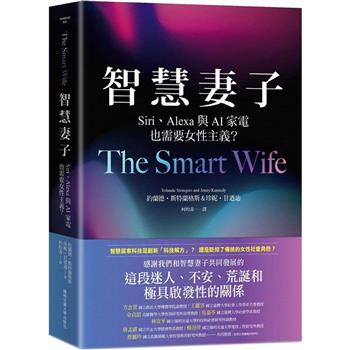第一章 認識智慧妻子
你忙了一整天。你很累、腰痠背痛,肚子又餓。你現在只想要翹起腳、點開你最愛的串流節目,然後幫自己倒一杯酒。但你還得要做晚餐、看小孩寫作業,明天的行程也還沒確認。應該要有人去洗那一大堆的衣服,然後你應該要把垃圾拿出去丟。如果一切都能安然進行,不出什麼亂子,而家裡所有人都能乖乖地去做家事,嗯⋯⋯那會有多好?你可能還希望有人能跟你講講話,問問你今天過得怎麼樣。你甚至可能渴望一些更特別的。會不會有什麼人,或者有什麼東西,可以做到這一切呢?
來認識你的智慧妻子(smart wife)吧!她性情開朗、樂於助人,而且價格越來越實惠。現在世界各地已有數百萬人開始使用智慧型設備,來提供過往現實生活中的真正妻子,所提供的家務、關懷和親密服務。
政論記者安娜貝爾•克拉布(Annabel Crabb)曾精準地使用「人妻荒」(wife drought)一詞來形容多數經濟與性別意識都發展成熟的國家所面臨的問題,而智慧妻子似乎是個相當巧妙的解方。畢竟,誰在家中不想要獲得更多幫助,或甚至,偶爾可以幫忙滿足更多的性慾?
2021年,已有產業觀察家預測,世界各地的網路型智慧語音裝置將會越來越多—其增長速度甚至將超越手機的普及程度。類似掃地機器人的智慧居家設備,目前已經是世界上大眾接受度最高的機器人。更廣泛的智慧居家市場也正快速發展,根據估計,2023年預計將發售十六億台不同的智慧型裝置,包括安全防護、照明、智慧音箱、電子恆溫器與影音娛樂產品。照護與性愛機器人的市場需求同樣也在成長,儘管速度相對緩慢。
智慧妻子顯然是個很吸引人的概念,對於許多有能力負擔智慧科技、網路與電力設備的人來說,也逐漸成為一種現實。然而,面對我們深知生活在二十一世紀所會面臨的各種困擾,她真的是個好的解方嗎?
在深入暸解我們迷人女主角的優、缺點之前,讓我們先稍微熟悉一下這位智慧妻子。克拉布所提到的人妻荒顯現,我們現正目睹當代社會中妻子的角色緩慢地走向死亡(至少是我們目前所知,長期擔任父權社會骨幹的妻子角色)。不過她開始強勢回歸,還出現了幾個關鍵的升級。現在被要求回到廚房裡的,並不是妻子本人,而是機器人、數位語音助理(又被稱為智慧音箱、對話代理人、虛擬助理、聊天機器人等)與其他智慧設備中內建的那些陰柔化的人工智慧(AI)。
智慧妻子有許多不同型態;事實上,你很可能早就已經和她一起生活了。最顯而易見的莫過於亞馬遜(Amazon)的Alexa、蘋果(Apple)的Siri,或者Google Home 等智慧助理,在多數的銷售市場裡它們的預設聲音都是女性。其他智慧妻子可能採擬人化、動物化或自動化的型態(例如家用電器或家用機器人)—多數時候它們所負擔的,都是傳統上由妻子承擔的家庭責任。有間印度公司甚至直接使用「智慧妻子」一語來宣傳他們出品的家電產品。在特別陰柔化,有時甚至是特別「情色化」的裝置中,例如性愛機器人或女性仿生人(gynoid),也可以看到智慧妻子的影子。
我們用「智慧」一語來代表有人工智慧、有連接網路,或有電子計算性質的東西。「妻子」一詞所指涉的,則是一種長期存於我們社會集體心理中的原型—可以一肩挑起家中所有的家務勞動。在過去與現在中,且在其最簡化的型態下,妻子既是社會建構的產物、是一種商品,還被視為是男人的財產。妻子的角色包括照顧者、管家、主婦、情緒勞動者、提供性愛服務的人,以及可以合法繁衍後代的人;在數千年的父權體制中,這些角色可說是根深蒂固的。
智慧妻子只是個比喻,並非字面上的意思(雖然我們在本書後面章節將會看到,確實有人真的和她們結婚)。我們用這個詞彙來描繪那些企圖擔起傳統上與妻子角色相關家務勞動的智慧科技,以及所有被使用者視為是智慧妻子的智慧科技。此詞也包括在科幻與大眾文化腳本中扮演妻子角色的那些陰柔化類人或仿人物體—也就是「現實生活」中智慧妻子的典範。
智慧妻子的原型,是1950 年的大西洋兩端的美國與英國家庭主婦。許多當代社會依然眷戀這位白人、中產階級、符合異性戀正統(heteronormative)的超完美嬌妻—在她井然有序的家中,有清新純白的床組、精心佈置的花飾、閃閃發光的廚具,還有精美的手作料理。看看她,不是很棒嗎?她在晚餐桌席的迷人發言、她的完美秀髮(看看那個捲度!)、她的孩子乾淨乖巧、她的丈夫心滿意足(而且事業成功),是所有追求此理想的妻子心中的最高標準—至少根據當年的廣告來看,確實是如此。這位令人依依不捨的神奇女子,通常婚後就不會出外從事有償的工作(除非是符合主婦職責的事情,譬如販售保鮮盒)。家,就是她的主要區域,負責照料家中的所有人。
這個被高度理想化的形象,依然可以在許多情境喜劇(sitcoms)或其他模仿智慧妻子概念的設定中看見。不過,這並不是本書女主角唯一的靈感來源。隨著智慧妻子在中國、印度、日本和韓國等亞洲國家的影響力持續擴大,她也開始展現這些地方對於理想女性的其他文化想像。中國目前已經占據了全球一半的數位語音助理市場,2019年的銷售量已經超過一千萬台,遠遠領先美國。儘管亞馬遜和Google Home 依然主宰中國市場,不過百度、阿里巴巴和小米已經緊隨其後。儘管文化各異,但各地所生產用來提供服務的智慧型裝置卻清一色,全都是一套以年輕、嫻靜、性化的女性(或女孩)形象作為特徵的技術,橫跨全球的智慧妻子市場皆然。
擁有一套無所不在的科技,就像是一名永遠不會累的妻子,某些人(包括我們自己)可能會覺得這個想法聽起來很有吸引力。但她真的要是這種刻板形象,才會讓人想回家嗎?她真的有助於提升性別平權嗎?除了陪伴我們、協助網購日常用品之外,她還如何維護了這個資本主義和父權體制的權力和壓迫?她體現了怎麼樣的未來?我們還能如何想像她和我們共同生活的其他樣貌?
我們不是第一個提出這些問題的人,也不是第一個點出智慧科技常常(很遺憾地)被標榜為主婦的人。本書選擇這位設定有些挑逗意味的虛構人物作為主角,並且明確將她定位為女性,主要參考了其他技術女性主義者(technofeminist)與數位媒體學者的作法;在這些學者中,最知名者莫過於唐娜•哈洛威(Donna Haraway)與凱莉•賈瑞特(Kylie Jarrett)兩人,前者曾經撰寫多篇文獻討論既是女性、又是機器的陰柔賽伯格意象,而後者則提出了「數位主婦」(digital housewife)的概念,探究人們在網路溝通平台上所進行的各種無償消費勞動。
以智慧妻子的形象來描繪智慧居家科技,是我們對家庭生活、AI與人類關係,以及當代女性主義的未來所提出的批判與干預。藉由探索這個有些戲謔的角色設定,我們認為,智慧居家科技的設計與行銷存在的根本問題在於,標榜這些裝置是有望終結人妻荒的創新「科技解方」(technofixes),同時體現、延續了女性在家庭中的陳舊刻板形象;不過,我們也會進一步提出一些建議,試圖解放、昇華現存於社會中的智慧妻子。
雖然我們筆下的智慧妻子似乎令人頗為憂心,但其實她的形象大可以更千變萬化,可能既是幻想,也很實際—甚至可能跟五○年代高度浪漫化的主婦有些類似。在《不只是克利佛太太》(Not June Cleaver)一書中,美國歷史研究學者瓊安•邁耶羅維茨(Joanne Meyerowitz)與其他論者就質疑,歷史看待這些主婦的方式帶有「固執的刻板印象」(tenacious stereotype),彷彿那些足不出戶、滿腹牢騷的郊區主婦總是「待在家中照顧孩子、打掃房子、烤餅乾」,但這種看法,就如同五○年代的主婦形象本身,都只是一種「充斥著對過往所謂更樸實、更快樂、更繁榮時代的懷舊想像」;該書作者於是舉出許多故事,展現戰後的美國女性在家庭中所扮演的多樣角色,作為對這套規範性假設的反證。
同樣地,隨著有越來越多的智慧妻子,用各種多元面貌走入我們的家庭,本書也希望能讓她們為自己發聲。本書將直指智慧妻子的大眾刻板印象,說明這些形象如何可能貶抑傳統的女性社會角色,並加劇對女性的暴力;但於此同時,我們也將討論關於性別困擾、不同文化形象的故事,以及其他有些古怪、但人們衷心接納的智慧妻子形象。本書將會彰顯,智慧妻子並不只扮演妻子的角色,她們也是有智慧的
朋友、僕人、女友、移工、秘書、母親、性工作者、親密伴侶、愛人、保姆、管家、寵物、人造物種,或者更多其他角色。藉由探索這些裝置所具有的多樣角色與外型形象,我們將能窺見一些足以讓智慧妻子超越自身侷限的可能性。
不過,現在先讓我們說明,這些形象各異的角色究竟是如何進入、填補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各種空白。
你忙了一整天。你很累、腰痠背痛,肚子又餓。你現在只想要翹起腳、點開你最愛的串流節目,然後幫自己倒一杯酒。但你還得要做晚餐、看小孩寫作業,明天的行程也還沒確認。應該要有人去洗那一大堆的衣服,然後你應該要把垃圾拿出去丟。如果一切都能安然進行,不出什麼亂子,而家裡所有人都能乖乖地去做家事,嗯⋯⋯那會有多好?你可能還希望有人能跟你講講話,問問你今天過得怎麼樣。你甚至可能渴望一些更特別的。會不會有什麼人,或者有什麼東西,可以做到這一切呢?
來認識你的智慧妻子(smart wife)吧!她性情開朗、樂於助人,而且價格越來越實惠。現在世界各地已有數百萬人開始使用智慧型設備,來提供過往現實生活中的真正妻子,所提供的家務、關懷和親密服務。
政論記者安娜貝爾•克拉布(Annabel Crabb)曾精準地使用「人妻荒」(wife drought)一詞來形容多數經濟與性別意識都發展成熟的國家所面臨的問題,而智慧妻子似乎是個相當巧妙的解方。畢竟,誰在家中不想要獲得更多幫助,或甚至,偶爾可以幫忙滿足更多的性慾?
2021年,已有產業觀察家預測,世界各地的網路型智慧語音裝置將會越來越多—其增長速度甚至將超越手機的普及程度。類似掃地機器人的智慧居家設備,目前已經是世界上大眾接受度最高的機器人。更廣泛的智慧居家市場也正快速發展,根據估計,2023年預計將發售十六億台不同的智慧型裝置,包括安全防護、照明、智慧音箱、電子恆溫器與影音娛樂產品。照護與性愛機器人的市場需求同樣也在成長,儘管速度相對緩慢。
智慧妻子顯然是個很吸引人的概念,對於許多有能力負擔智慧科技、網路與電力設備的人來說,也逐漸成為一種現實。然而,面對我們深知生活在二十一世紀所會面臨的各種困擾,她真的是個好的解方嗎?
在深入暸解我們迷人女主角的優、缺點之前,讓我們先稍微熟悉一下這位智慧妻子。克拉布所提到的人妻荒顯現,我們現正目睹當代社會中妻子的角色緩慢地走向死亡(至少是我們目前所知,長期擔任父權社會骨幹的妻子角色)。不過她開始強勢回歸,還出現了幾個關鍵的升級。現在被要求回到廚房裡的,並不是妻子本人,而是機器人、數位語音助理(又被稱為智慧音箱、對話代理人、虛擬助理、聊天機器人等)與其他智慧設備中內建的那些陰柔化的人工智慧(AI)。
智慧妻子有許多不同型態;事實上,你很可能早就已經和她一起生活了。最顯而易見的莫過於亞馬遜(Amazon)的Alexa、蘋果(Apple)的Siri,或者Google Home 等智慧助理,在多數的銷售市場裡它們的預設聲音都是女性。其他智慧妻子可能採擬人化、動物化或自動化的型態(例如家用電器或家用機器人)—多數時候它們所負擔的,都是傳統上由妻子承擔的家庭責任。有間印度公司甚至直接使用「智慧妻子」一語來宣傳他們出品的家電產品。在特別陰柔化,有時甚至是特別「情色化」的裝置中,例如性愛機器人或女性仿生人(gynoid),也可以看到智慧妻子的影子。
我們用「智慧」一語來代表有人工智慧、有連接網路,或有電子計算性質的東西。「妻子」一詞所指涉的,則是一種長期存於我們社會集體心理中的原型—可以一肩挑起家中所有的家務勞動。在過去與現在中,且在其最簡化的型態下,妻子既是社會建構的產物、是一種商品,還被視為是男人的財產。妻子的角色包括照顧者、管家、主婦、情緒勞動者、提供性愛服務的人,以及可以合法繁衍後代的人;在數千年的父權體制中,這些角色可說是根深蒂固的。
智慧妻子只是個比喻,並非字面上的意思(雖然我們在本書後面章節將會看到,確實有人真的和她們結婚)。我們用這個詞彙來描繪那些企圖擔起傳統上與妻子角色相關家務勞動的智慧科技,以及所有被使用者視為是智慧妻子的智慧科技。此詞也包括在科幻與大眾文化腳本中扮演妻子角色的那些陰柔化類人或仿人物體—也就是「現實生活」中智慧妻子的典範。
智慧妻子的原型,是1950 年的大西洋兩端的美國與英國家庭主婦。許多當代社會依然眷戀這位白人、中產階級、符合異性戀正統(heteronormative)的超完美嬌妻—在她井然有序的家中,有清新純白的床組、精心佈置的花飾、閃閃發光的廚具,還有精美的手作料理。看看她,不是很棒嗎?她在晚餐桌席的迷人發言、她的完美秀髮(看看那個捲度!)、她的孩子乾淨乖巧、她的丈夫心滿意足(而且事業成功),是所有追求此理想的妻子心中的最高標準—至少根據當年的廣告來看,確實是如此。這位令人依依不捨的神奇女子,通常婚後就不會出外從事有償的工作(除非是符合主婦職責的事情,譬如販售保鮮盒)。家,就是她的主要區域,負責照料家中的所有人。
這個被高度理想化的形象,依然可以在許多情境喜劇(sitcoms)或其他模仿智慧妻子概念的設定中看見。不過,這並不是本書女主角唯一的靈感來源。隨著智慧妻子在中國、印度、日本和韓國等亞洲國家的影響力持續擴大,她也開始展現這些地方對於理想女性的其他文化想像。中國目前已經占據了全球一半的數位語音助理市場,2019年的銷售量已經超過一千萬台,遠遠領先美國。儘管亞馬遜和Google Home 依然主宰中國市場,不過百度、阿里巴巴和小米已經緊隨其後。儘管文化各異,但各地所生產用來提供服務的智慧型裝置卻清一色,全都是一套以年輕、嫻靜、性化的女性(或女孩)形象作為特徵的技術,橫跨全球的智慧妻子市場皆然。
擁有一套無所不在的科技,就像是一名永遠不會累的妻子,某些人(包括我們自己)可能會覺得這個想法聽起來很有吸引力。但她真的要是這種刻板形象,才會讓人想回家嗎?她真的有助於提升性別平權嗎?除了陪伴我們、協助網購日常用品之外,她還如何維護了這個資本主義和父權體制的權力和壓迫?她體現了怎麼樣的未來?我們還能如何想像她和我們共同生活的其他樣貌?
我們不是第一個提出這些問題的人,也不是第一個點出智慧科技常常(很遺憾地)被標榜為主婦的人。本書選擇這位設定有些挑逗意味的虛構人物作為主角,並且明確將她定位為女性,主要參考了其他技術女性主義者(technofeminist)與數位媒體學者的作法;在這些學者中,最知名者莫過於唐娜•哈洛威(Donna Haraway)與凱莉•賈瑞特(Kylie Jarrett)兩人,前者曾經撰寫多篇文獻討論既是女性、又是機器的陰柔賽伯格意象,而後者則提出了「數位主婦」(digital housewife)的概念,探究人們在網路溝通平台上所進行的各種無償消費勞動。
以智慧妻子的形象來描繪智慧居家科技,是我們對家庭生活、AI與人類關係,以及當代女性主義的未來所提出的批判與干預。藉由探索這個有些戲謔的角色設定,我們認為,智慧居家科技的設計與行銷存在的根本問題在於,標榜這些裝置是有望終結人妻荒的創新「科技解方」(technofixes),同時體現、延續了女性在家庭中的陳舊刻板形象;不過,我們也會進一步提出一些建議,試圖解放、昇華現存於社會中的智慧妻子。
雖然我們筆下的智慧妻子似乎令人頗為憂心,但其實她的形象大可以更千變萬化,可能既是幻想,也很實際—甚至可能跟五○年代高度浪漫化的主婦有些類似。在《不只是克利佛太太》(Not June Cleaver)一書中,美國歷史研究學者瓊安•邁耶羅維茨(Joanne Meyerowitz)與其他論者就質疑,歷史看待這些主婦的方式帶有「固執的刻板印象」(tenacious stereotype),彷彿那些足不出戶、滿腹牢騷的郊區主婦總是「待在家中照顧孩子、打掃房子、烤餅乾」,但這種看法,就如同五○年代的主婦形象本身,都只是一種「充斥著對過往所謂更樸實、更快樂、更繁榮時代的懷舊想像」;該書作者於是舉出許多故事,展現戰後的美國女性在家庭中所扮演的多樣角色,作為對這套規範性假設的反證。
同樣地,隨著有越來越多的智慧妻子,用各種多元面貌走入我們的家庭,本書也希望能讓她們為自己發聲。本書將直指智慧妻子的大眾刻板印象,說明這些形象如何可能貶抑傳統的女性社會角色,並加劇對女性的暴力;但於此同時,我們也將討論關於性別困擾、不同文化形象的故事,以及其他有些古怪、但人們衷心接納的智慧妻子形象。本書將會彰顯,智慧妻子並不只扮演妻子的角色,她們也是有智慧的
朋友、僕人、女友、移工、秘書、母親、性工作者、親密伴侶、愛人、保姆、管家、寵物、人造物種,或者更多其他角色。藉由探索這些裝置所具有的多樣角色與外型形象,我們將能窺見一些足以讓智慧妻子超越自身侷限的可能性。
不過,現在先讓我們說明,這些形象各異的角色究竟是如何進入、填補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各種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