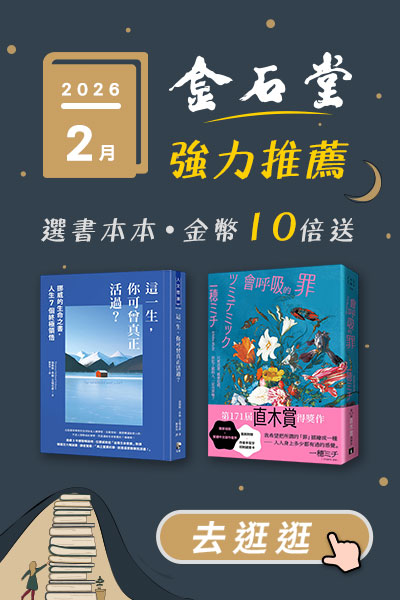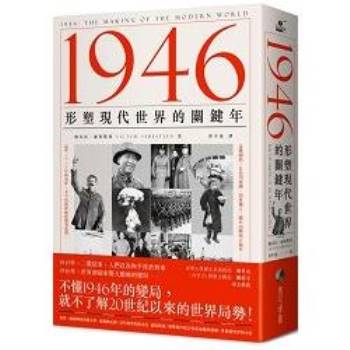6.古琴科事件
二月三日星期日晚上,美國記者德魯.皮爾森(Drew Pearson)在其NBC電台廣播節目上,播出一則轟動的獨家新聞。他說,有個蘇聯間諜已向渥太華的皇家加拿大騎警自首,並揭露「美國和加拿大境內一龐大的俄羅斯間諜網」。皮爾森是美國最受敬重與歡迎的廣播人之一,他每週一播的節目「德魯.皮爾森評論」,常吸引超過兩千五百萬人聆聽。這個晚上,他說:「這個俄羅斯人告訴加拿大當局,有多位為蘇聯做事的特務,安插在美加政府內部。」這整件事極為複雜,皮爾森只知道其中一部分。他不知道這人在將近六個月前就已變節投誠,不知道美英加三國政府一直壓著此事不曝光。但皮爾森的確說到加拿大總理麥肯錫.金恩(Mackenzie King),不久前「特地去了華府一趟」,以讓杜魯門總統了解全部詳情。
這個消息的播送,標誌著古琴科事件(Gouzenko affair)的開端。該事件是戰後第一樁重大間諜醜聞,其中複雜的密謀和反制活動,將催生出無數諜報小說和電影。一如皮爾森的主要消息來源所希望的,這樁醜聞激起一波對間諜活動的歇斯底里心態,深深改變了美英兩國和西方許多地區民眾對蘇聯的看法。
聯邦調查局長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給了皮爾森整件事的梗概。他估算那將有助於刺激杜魯門政府,以更強硬手段對付國內外的「顛覆活動」和共產主義。多年以後,胡佛和皮爾森都死了許久以後,世人才知道胡佛本人就是那個「深喉嚨」,在播出這個消息之前的幾個星期裡,與皮爾森通過多次電話,透露了局部細節。在播出那天的早上,兩人甚至還談過。
伊格爾.古琴科(Igor Guzenko)是蘇聯軍情局低階的密碼員,任職於蘇聯駐渥太華的大使館。二十六歲的他,已婚,育有一女,還有個小孩已在老婆肚子裡。他喜愛西方的生活,擔心因為一些安全上的小疏失受懲,被送回莫斯科,於是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五日晚間帶著一百零九份祕密文件離開大使館。他始終很想多賺點錢,於是先找報紙兜售。他來到《渥太華新聞報》(Ottawa Journal)報社,該報把他打發走,從而與一樁超級轟動的獨家新聞失之交臂。加拿大司法部官員認為他是個騙子,把他趕走。最後,他找上某個騎警局,該局警員把他的話當一回事。
古琴科所偷走的文件表明,蘇聯刺探原子機密和其他軍事機密已有數年,已在美加政府裡安插了特工(「暫不活動的潛伏間諜」[sleeper]),而且那些特工已爬上高位。那些文件證明,蘇聯首要的情報機關,內務人民委員部,轄有自成體系的一批間諜和探員,其運作規模遠比西方情報機關所以為的還要大、還要有系統。內務人民委員部後來改為國家安全部(MGB),即人稱格別烏的國家安全委員會(KGB)前身。
加拿大人盤問了古琴科好幾個月,然後給他一個新身分。他們給了他一個極富新意的新名字喬治.布朗,敲定每個月給他五百美元的工作費,外加一大筆現給的十萬美元。他們把大部分資料交給美國人和英國人。誠如後來某些間諜、政治人物和驚悚小說作家所間接表示的,那些資料並未透露蘇聯竊取曼哈頓計畫之機密的詳情。透過其他投誠者和另一個與他不相干的間諜網,美國才得知這方面的詳細情況。不過古琴科偷出的珍貴文件的確指出,北美境內具影響力的蘇聯特工的名字,而且為如何揪出其他特工提供了有用的線索。
值得注意的是,三國政府未在這一情報上大作文章,原因除了惰性,除了想將計就計搞反情報戰,以設下陷阱抓到其他間諜,主要因為他們擔心重大間諜醜聞可能在外交、政治上產生不樂見的影響。蘇聯仍是盟國,在現階段,不管是英國還是美國,都覺得與俄羅斯人清楚決裂沒什麼好處。
皮爾森揭露此事件後,不管詳情如何諱莫如深,西方報紙廣為報導,使加拿大人必須有所行動的壓力隨之變大。下個星期日,二月十日,皮爾森在節目裡大部分在談其他事,卻離題插入一段話,說那樁轟動的加拿大間諜案,「逮捕在即」。就那時候的情況,此話並非事實,但二月十五日拂曉,十六人遭逮捕,被控以間諜活動罪,其中包括十二名加拿大公務員。
五天後,在英國,軍情五處(MI5)逮捕英國物理學家艾倫.努恩.梅(Alan Nunn May),倫敦國王學院的一名講師。他坦承戰時暫調到加拿大國家研究院(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任職期間,曾把原子機密交給蘇聯人。該研究院當時正在蒙特婁附近建造一座核子反應爐。他說他不覺得自己犯了叛國罪,反倒覺得「做對了」。他唯一遺憾的事,乃是他把一小塊經處理過具高度放射性的鈾25透過信差交給俄羅斯人,那個信差經手時未穿防護衣,因而此後將在重病中度過餘生。在加拿大,有九人於這樁間諜醜聞後入獄,其中包括一名國會議員。
在美國,短期內未有人被捕,但在間諜就在你身邊的猜疑氣氛中,有些高階政府官員被當成蘇聯特務疑犯調查。他們包括財政部官員哈里.德克斯特.懷特(Harry Dexter White)和國務院的阿爾傑.希斯(Alger Hiss)。懷特曾代表美國出席一九四四年的布雷頓森林會議(Bretton Woods conference)。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就是在那場會議所創立。希斯則是美國駐聯合國辦公室的第一任主管。兩人都名譽掃地;懷特於作證後不久死於心臟病;身為蘇聯特務的希斯,因偽證罪關了三年。
古琴科事件對美國和美國總統影響深遠。杜魯門的民意支持度本就不高,因此事件更進一步下滑,不支持他的比例達到將近七成,創下新高。就連水門醜聞鬧得最沸沸揚揚時,尼克森(Richard Nixon)的不支持度都沒這麼低。杜魯門向心腹坦承,這種懷疑間諜無所不在的恐慌心態使他受到更大壓力,且或許不可避免的,使美國對「赤色威脅」反應過度。接下來產生的社會氣氛,不能只歸咎於伊格爾.古琴科一人。在德魯.皮爾森於電台披露該事件後九個月選上參議員的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McCarthy),發覺操控此一氣氛非常容易。沒幾個月,杜魯門就發布一項行政命令,要所有政府雇員「宣誓忠誠」,數千名共黨嫌疑人或同路人遭聯邦調查局和稅務機關調查。就連民間公司都根據政治理由要員工走路。
在英國,恐懼共黨入侵的心理從未達到美國那種瘋狂、歇斯底里的程度,但艾德禮主持一「內閣顛覆活動委員會」(Cabinet Committee on Subversion),數十名公務員遭軍情五處調查,有些學界人士失去在牛津、劍橋大學的教職,約翰路易斯(John Lewis Partnership)百貨公司的員工被迫簽署反共誓言。但英國人一如以往在意識形態上很隨和。誠如小說家帕梅拉.漢斯福德.約翰遜(Pamela Hansford Johnson)所憶道,大部分人「忙到沒心思去憂心」:「一般人忙著處理日常問題..看到自己身邊的種種戰爭廢墟──在上班途中的鐵軌沿線上,在公車所行經的路上──看到原本座落著酒館的地方,看到位在清理過之場地上的兒童遊戲區,心裡還在想著要花多久才能把它們都收拾好。一般人沒時間去操心新的廢墟..報紙上偶爾喧嚷著俄羅斯的威脅,但他們..不覺得俄羅斯威脅到自己。」
但對俄羅斯人來說,影響是立即而直接。劍橋間諜之一,後來投誠莫斯科以免被揭露叛徒身分的唐納德.麥克林(Donald Maclean),當時是派駐華府的英國高階外交官。他於一九八三年去世前不久告訴一名採訪他的俄國人,古琴科事件的後果,就是蘇聯先前取得的有價值情報來源,大部分「在此後遭堵住..(他們)幾乎是一夜之間就凍結..美國境內所有情報活動」。到了一九四六年二月底,蘇聯多年來千辛萬苦建立的間諜網已被完全封住。
二月三日星期日晚上,美國記者德魯.皮爾森(Drew Pearson)在其NBC電台廣播節目上,播出一則轟動的獨家新聞。他說,有個蘇聯間諜已向渥太華的皇家加拿大騎警自首,並揭露「美國和加拿大境內一龐大的俄羅斯間諜網」。皮爾森是美國最受敬重與歡迎的廣播人之一,他每週一播的節目「德魯.皮爾森評論」,常吸引超過兩千五百萬人聆聽。這個晚上,他說:「這個俄羅斯人告訴加拿大當局,有多位為蘇聯做事的特務,安插在美加政府內部。」這整件事極為複雜,皮爾森只知道其中一部分。他不知道這人在將近六個月前就已變節投誠,不知道美英加三國政府一直壓著此事不曝光。但皮爾森的確說到加拿大總理麥肯錫.金恩(Mackenzie King),不久前「特地去了華府一趟」,以讓杜魯門總統了解全部詳情。
這個消息的播送,標誌著古琴科事件(Gouzenko affair)的開端。該事件是戰後第一樁重大間諜醜聞,其中複雜的密謀和反制活動,將催生出無數諜報小說和電影。一如皮爾森的主要消息來源所希望的,這樁醜聞激起一波對間諜活動的歇斯底里心態,深深改變了美英兩國和西方許多地區民眾對蘇聯的看法。
聯邦調查局長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給了皮爾森整件事的梗概。他估算那將有助於刺激杜魯門政府,以更強硬手段對付國內外的「顛覆活動」和共產主義。多年以後,胡佛和皮爾森都死了許久以後,世人才知道胡佛本人就是那個「深喉嚨」,在播出這個消息之前的幾個星期裡,與皮爾森通過多次電話,透露了局部細節。在播出那天的早上,兩人甚至還談過。
伊格爾.古琴科(Igor Guzenko)是蘇聯軍情局低階的密碼員,任職於蘇聯駐渥太華的大使館。二十六歲的他,已婚,育有一女,還有個小孩已在老婆肚子裡。他喜愛西方的生活,擔心因為一些安全上的小疏失受懲,被送回莫斯科,於是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五日晚間帶著一百零九份祕密文件離開大使館。他始終很想多賺點錢,於是先找報紙兜售。他來到《渥太華新聞報》(Ottawa Journal)報社,該報把他打發走,從而與一樁超級轟動的獨家新聞失之交臂。加拿大司法部官員認為他是個騙子,把他趕走。最後,他找上某個騎警局,該局警員把他的話當一回事。
古琴科所偷走的文件表明,蘇聯刺探原子機密和其他軍事機密已有數年,已在美加政府裡安插了特工(「暫不活動的潛伏間諜」[sleeper]),而且那些特工已爬上高位。那些文件證明,蘇聯首要的情報機關,內務人民委員部,轄有自成體系的一批間諜和探員,其運作規模遠比西方情報機關所以為的還要大、還要有系統。內務人民委員部後來改為國家安全部(MGB),即人稱格別烏的國家安全委員會(KGB)前身。
加拿大人盤問了古琴科好幾個月,然後給他一個新身分。他們給了他一個極富新意的新名字喬治.布朗,敲定每個月給他五百美元的工作費,外加一大筆現給的十萬美元。他們把大部分資料交給美國人和英國人。誠如後來某些間諜、政治人物和驚悚小說作家所間接表示的,那些資料並未透露蘇聯竊取曼哈頓計畫之機密的詳情。透過其他投誠者和另一個與他不相干的間諜網,美國才得知這方面的詳細情況。不過古琴科偷出的珍貴文件的確指出,北美境內具影響力的蘇聯特工的名字,而且為如何揪出其他特工提供了有用的線索。
值得注意的是,三國政府未在這一情報上大作文章,原因除了惰性,除了想將計就計搞反情報戰,以設下陷阱抓到其他間諜,主要因為他們擔心重大間諜醜聞可能在外交、政治上產生不樂見的影響。蘇聯仍是盟國,在現階段,不管是英國還是美國,都覺得與俄羅斯人清楚決裂沒什麼好處。
皮爾森揭露此事件後,不管詳情如何諱莫如深,西方報紙廣為報導,使加拿大人必須有所行動的壓力隨之變大。下個星期日,二月十日,皮爾森在節目裡大部分在談其他事,卻離題插入一段話,說那樁轟動的加拿大間諜案,「逮捕在即」。就那時候的情況,此話並非事實,但二月十五日拂曉,十六人遭逮捕,被控以間諜活動罪,其中包括十二名加拿大公務員。
五天後,在英國,軍情五處(MI5)逮捕英國物理學家艾倫.努恩.梅(Alan Nunn May),倫敦國王學院的一名講師。他坦承戰時暫調到加拿大國家研究院(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任職期間,曾把原子機密交給蘇聯人。該研究院當時正在蒙特婁附近建造一座核子反應爐。他說他不覺得自己犯了叛國罪,反倒覺得「做對了」。他唯一遺憾的事,乃是他把一小塊經處理過具高度放射性的鈾25透過信差交給俄羅斯人,那個信差經手時未穿防護衣,因而此後將在重病中度過餘生。在加拿大,有九人於這樁間諜醜聞後入獄,其中包括一名國會議員。
在美國,短期內未有人被捕,但在間諜就在你身邊的猜疑氣氛中,有些高階政府官員被當成蘇聯特務疑犯調查。他們包括財政部官員哈里.德克斯特.懷特(Harry Dexter White)和國務院的阿爾傑.希斯(Alger Hiss)。懷特曾代表美國出席一九四四年的布雷頓森林會議(Bretton Woods conference)。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就是在那場會議所創立。希斯則是美國駐聯合國辦公室的第一任主管。兩人都名譽掃地;懷特於作證後不久死於心臟病;身為蘇聯特務的希斯,因偽證罪關了三年。
古琴科事件對美國和美國總統影響深遠。杜魯門的民意支持度本就不高,因此事件更進一步下滑,不支持他的比例達到將近七成,創下新高。就連水門醜聞鬧得最沸沸揚揚時,尼克森(Richard Nixon)的不支持度都沒這麼低。杜魯門向心腹坦承,這種懷疑間諜無所不在的恐慌心態使他受到更大壓力,且或許不可避免的,使美國對「赤色威脅」反應過度。接下來產生的社會氣氛,不能只歸咎於伊格爾.古琴科一人。在德魯.皮爾森於電台披露該事件後九個月選上參議員的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McCarthy),發覺操控此一氣氛非常容易。沒幾個月,杜魯門就發布一項行政命令,要所有政府雇員「宣誓忠誠」,數千名共黨嫌疑人或同路人遭聯邦調查局和稅務機關調查。就連民間公司都根據政治理由要員工走路。
在英國,恐懼共黨入侵的心理從未達到美國那種瘋狂、歇斯底里的程度,但艾德禮主持一「內閣顛覆活動委員會」(Cabinet Committee on Subversion),數十名公務員遭軍情五處調查,有些學界人士失去在牛津、劍橋大學的教職,約翰路易斯(John Lewis Partnership)百貨公司的員工被迫簽署反共誓言。但英國人一如以往在意識形態上很隨和。誠如小說家帕梅拉.漢斯福德.約翰遜(Pamela Hansford Johnson)所憶道,大部分人「忙到沒心思去憂心」:「一般人忙著處理日常問題..看到自己身邊的種種戰爭廢墟──在上班途中的鐵軌沿線上,在公車所行經的路上──看到原本座落著酒館的地方,看到位在清理過之場地上的兒童遊戲區,心裡還在想著要花多久才能把它們都收拾好。一般人沒時間去操心新的廢墟..報紙上偶爾喧嚷著俄羅斯的威脅,但他們..不覺得俄羅斯威脅到自己。」
但對俄羅斯人來說,影響是立即而直接。劍橋間諜之一,後來投誠莫斯科以免被揭露叛徒身分的唐納德.麥克林(Donald Maclean),當時是派駐華府的英國高階外交官。他於一九八三年去世前不久告訴一名採訪他的俄國人,古琴科事件的後果,就是蘇聯先前取得的有價值情報來源,大部分「在此後遭堵住..(他們)幾乎是一夜之間就凍結..美國境內所有情報活動」。到了一九四六年二月底,蘇聯多年來千辛萬苦建立的間諜網已被完全封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