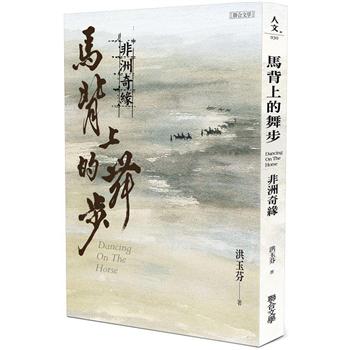雨,傾下奈及利亞北漠
沙漠的雨季,雨,如水柱,急遽而來,傾盆倒下。瞬間,雨停了,陽光普照。沙漠的雨季,雨水愈多,秋收愈豐,攸關這年的好過與否。
雨一下,路面積水一漥漥,日曬,變成了坑坑洞洞。坐在車內,不停的抖動,五臟六腑有如跳曼波舞。深感居住此地的人,如坑疤不平的馬路,秋收沒到,雨季過不完。
會議完,回飯店,過午。朋友說這時出發去釣魚已晚,因釣魚需大河遠在城外百餘里,不如城郊外的小河,有田野和原始部落,相信我會喜歡。
出發。
車後座,一個大冰桶裝了各式清涼冷飲,這國度來去超過三十年,盡是工作,頭一回郊遊去,雀躍之心,加了翅膀,飛翔而去。
雨季的陽光,溫馴。茅草穀倉,泥土房屋,粗糙簡陋,一間間,如風景畫般,與專心低頭吃草的牛羊,散落在畫布般的原野上。農作種植,全是半人高的梗葉,飽滿的翠綠植物,是玉米或黍穀?兩者長相類似,難以分辨差異。屬於撒哈拉沙漠裙襬的西非鄉村景致,隨著車速,節節後退,連日來的沉鬱心情,舒展開來。這裡,不是名勝古蹟,也不是遊樂場所,一草一木都風景,吸引我的目光。
朋友的車子,忽地停在一處烤肉攤前。這裡,約莫是部落的中心點,假日,人群一簇簇,或坐或站,一種無所事事的氛圍。長長鐵叉串起肉塊,烈焰紅炭,炊煙屢起,鐵架上的肉塊,慢慢轉成漂亮的金黃,香味撲鼻。朋友與他們嘰哩呱啦一陣後,車子再度發動。
我忍不住好奇他們的對話。原來,他最近得知地瓜葉營養豐富,部落不吃此菜,這裡是農業帶,他猜測應該有種植。果然,河流的對岸,一畝畝的玉米田,穿插少許菜園,就有種植。我順便告訴他,地瓜葉在台灣是家常健康菜,十分受歡迎。
澄淨的藍天,如天真無邪的孩童;柔軟的白雲,像荳蔻年華的少女,空氣甜軟得浮出音符。午後的陽光,耀眼。粗壯的老樹,頂天立地,枝幹綠蔭繁密如巨傘,吱喳的孩童,遮陽樹下;吵雜的群鳥,盤旋樹上,兩種風景,相映成趣。我不敵驕陽曝曬,也走避樹蔭下。怎知孩童一看我靠近,轟然鳥獸散,一雙雙骨碌碌的眼睛,澄澈晶亮,掛在黝黑的臉龐上,齊盯著我。我佯裝若無其事地坐在餘溫猶存的樹幹,眼角餘光覷著他們。
時光凝止,我似乎也變成小孩,好奇的追逐他們的身影。
他們,大揹小,小牽幼,赤足貼著黃泥土,嬉戲玩耍,彷彿這裡是一座遺世獨立的海角世界。小男孩,衣衫襤褸,頭頂一圓盤,花生塑膠袋包成小包,尖攏堆疊如小山丘,逢人兜售。我緩緩靠近,蹲下,與他同高度,輕輕地拿起花生,無聲的嘴型問他一包多少錢,打開錢包,他羞怯得噤言。朋友遠遠看到走來,一連串我聽不懂的豪薩語,付了錢,解惑似的對我說,他把花生全買了,且付錢超過其價值,要我放心。
無意中闖入這陌生的社會,我似乎扮演著觀光客,內心卻莫名如熱水翻滾。
朋友說,這個部落,無水無電,人們多世居務農。「很多人終其一生,不曾踏出這裡一步。」他喜歡釣魚,初次來有如陶淵明溯河循桃花源,那是很久以前了,後來成為他的假日休閒之地。他是第一位闖入這個封閉世界的白人,那時外人的足跡,微乎其微。首次來,人人目不轉睛地盯著他看,有如觀賞稀有動物。
河流兩岸,咫尺之近,靠舢舨船舶渡河,是部落生活的縮影。
不遠處,舢舨噠噠聲靠近,河水因雨季變得黃濁、暴漲,下船來的人群,莫不小心翼翼。瘦弱的小女孩,肩上荷著乾柴枝,稚氣的臉龐,讀不到屬於孩童的輕盈與歡笑,唯身上花布衫的色彩,是沉重沙洲的一抹亮點。瘦骨嶙峋的莊稼漢,一襲白袍飄飄,手持皮鞭,傍著牛羊群,緩緩走過,黃昏來臨。
風,樹梢間輕輕的吹,像一首無言的歌。雲彩,高空上靜靜地注視。泥土地,紅塵滾滾,人間的悲喜劇,上演著。
回程路上,朋友為我補習這部落的歷史與生活背景。
這個地區有三大農作物:玉米,黍,小米。可惜沒有灌溉系統,道地的看天田,雨水若下得少,農作物枯乾,收成少了,秋穫短缺,生活便拮据。
豪薩族是西非的其中一個最大族群,分布地方多,影響甚廣。奈及利亞北部、尼日南部、查德湖沿岸、喀麥隆北部、加納北部以及西非其它各國,都有為數不少的豪薩人。約八世紀起,豪薩人在現今尼日利亞北部建立多個城邦。至十九世紀,豪薩族經歷了數百年移民和征服的歷史發展,故它源於不同民族的融合,發展至有共同語言和共同宗教的族群。
這個部落,正是豪薩族群中的原始居民。穹蒼下,圓拱形帶尖的穀倉,絕美的景觀,令人好奇它的作用。朋友說那稱作「 Rumbu」〈豪薩語茅草屋之意〉。我公司有一個老客戶,公司名就叫「 Rumbu」。二十年來,Rumbu、Rumbu直叫,不解其意。他公司的商標就是傳統的茅草屋。現在,謎底揭曉,主其事的CEO,曾貴為國會的發言人之一,後來轉戰商場,不忘本,以傳統茅草屋為公司名。瞬間,恍然明白,原始圖騰,也可以是時尚的標誌,舊與新不是鴻溝,以傳統加上創新,便是橋了。
當我對著茅草屋升起肅然起敬之心時,主人一襲傳統的白袍,悄悄的出現了。我為茅草屋照相,與主人攀談,互動的情節,沒劇本,卻自然演出,好像我們是旅居的都市人,趁周末走訪了鄉下親戚的他們。
主人掀起穀倉的尖頂大蓋,只見滿滿曬乾的黍物,長長的稉柄,尾端纍纍、飽滿顆粒。為滿足我的好奇,他遞給我一支端詳,邊善意提醒勿沾到手,以免搔癢紅腫不止。
我們的談笑,劃破四周的靜謐,高大的木瓜樹也醒了,青綠的木瓜一顆顆垂吊枝頭,肥碩青翠,像在凝聽。女主人悄悄的出現,揹著沉睡的小嬰兒。年輕的母親,削瘦修長。一襲亮橘的傳統長裙,隨風擺動,細看,嘴唇上著色鮮豔的紅,沒對準嘴唇的線條,可能就地取材於傳統的化妝品吧。哦!愛美不分國界,各有姿態,令人稱奇。
央得同意,入內參觀他們的住屋。朋友說按傳統是不許外人進入,因我而開例。二道迷魂陣似的迴旋土牆進入,真是別有洞天。正中央一個泥土空地,周圍散布著茅草屋,泥土地上埋鍋造飯。柴薪粗塊,炭火燒紅,圓鍋外燻黑,煮熟的小米,一盤盤盛上,澆著疑是番茄醬汁,日常吃食,僅此而已。
角落裡,雞鴨群隊,咕咕咕、啄啄啄,奔走追逐,覓食去。孩童,大揹小,或爬行學步,或嬉戲玩耍。我偷窺茅草屋,狹小空間僅容一張榻舖,顯然只是夜寢用,作息全與日出同步。這塊泥土地,多功能用途:是廚房、餐廳、是活動的客廳,也是畜養家禽或孩子活動的院子。我看得目瞪口呆,刀耕火種的原始生活,在此淋漓盡致演出。我暗想,不只一戶人家居住吧,果然是兄弟妯娌集居,還有難得一見高齡祖母,典型的重視家族的伊斯蘭教文化。
男主人抱幼兒,來到我身旁。瘦巴巴、身輕如燕的孩子在父親的手中,絲毫不費力,我看在眼裡,心裡莫名的沉重起來。我朋友究竟長年在此,一看不對勁,轉頭對父親說,趕快帶孩子去看醫生吧。父親點頭稱是,母親微微頷首,剎那間,我讀出她眼眸中的一抹憂傷。懷中的孩子,過輕的身軀,卻是她心頭的最重。
夕陽西下,晚霞滿天,我們要離去。茅草屋的生活,如此的簡單與粗礪,
瘦弱孩子的影像,如淅瀝淅瀝的雨,流淌在沙漠裡,瞬間,又乾了。
沙漠的雨季,過了嗎?
沙漠的雨季,雨,如水柱,急遽而來,傾盆倒下。瞬間,雨停了,陽光普照。沙漠的雨季,雨水愈多,秋收愈豐,攸關這年的好過與否。
雨一下,路面積水一漥漥,日曬,變成了坑坑洞洞。坐在車內,不停的抖動,五臟六腑有如跳曼波舞。深感居住此地的人,如坑疤不平的馬路,秋收沒到,雨季過不完。
會議完,回飯店,過午。朋友說這時出發去釣魚已晚,因釣魚需大河遠在城外百餘里,不如城郊外的小河,有田野和原始部落,相信我會喜歡。
出發。
車後座,一個大冰桶裝了各式清涼冷飲,這國度來去超過三十年,盡是工作,頭一回郊遊去,雀躍之心,加了翅膀,飛翔而去。
雨季的陽光,溫馴。茅草穀倉,泥土房屋,粗糙簡陋,一間間,如風景畫般,與專心低頭吃草的牛羊,散落在畫布般的原野上。農作種植,全是半人高的梗葉,飽滿的翠綠植物,是玉米或黍穀?兩者長相類似,難以分辨差異。屬於撒哈拉沙漠裙襬的西非鄉村景致,隨著車速,節節後退,連日來的沉鬱心情,舒展開來。這裡,不是名勝古蹟,也不是遊樂場所,一草一木都風景,吸引我的目光。
朋友的車子,忽地停在一處烤肉攤前。這裡,約莫是部落的中心點,假日,人群一簇簇,或坐或站,一種無所事事的氛圍。長長鐵叉串起肉塊,烈焰紅炭,炊煙屢起,鐵架上的肉塊,慢慢轉成漂亮的金黃,香味撲鼻。朋友與他們嘰哩呱啦一陣後,車子再度發動。
我忍不住好奇他們的對話。原來,他最近得知地瓜葉營養豐富,部落不吃此菜,這裡是農業帶,他猜測應該有種植。果然,河流的對岸,一畝畝的玉米田,穿插少許菜園,就有種植。我順便告訴他,地瓜葉在台灣是家常健康菜,十分受歡迎。
澄淨的藍天,如天真無邪的孩童;柔軟的白雲,像荳蔻年華的少女,空氣甜軟得浮出音符。午後的陽光,耀眼。粗壯的老樹,頂天立地,枝幹綠蔭繁密如巨傘,吱喳的孩童,遮陽樹下;吵雜的群鳥,盤旋樹上,兩種風景,相映成趣。我不敵驕陽曝曬,也走避樹蔭下。怎知孩童一看我靠近,轟然鳥獸散,一雙雙骨碌碌的眼睛,澄澈晶亮,掛在黝黑的臉龐上,齊盯著我。我佯裝若無其事地坐在餘溫猶存的樹幹,眼角餘光覷著他們。
時光凝止,我似乎也變成小孩,好奇的追逐他們的身影。
他們,大揹小,小牽幼,赤足貼著黃泥土,嬉戲玩耍,彷彿這裡是一座遺世獨立的海角世界。小男孩,衣衫襤褸,頭頂一圓盤,花生塑膠袋包成小包,尖攏堆疊如小山丘,逢人兜售。我緩緩靠近,蹲下,與他同高度,輕輕地拿起花生,無聲的嘴型問他一包多少錢,打開錢包,他羞怯得噤言。朋友遠遠看到走來,一連串我聽不懂的豪薩語,付了錢,解惑似的對我說,他把花生全買了,且付錢超過其價值,要我放心。
無意中闖入這陌生的社會,我似乎扮演著觀光客,內心卻莫名如熱水翻滾。
朋友說,這個部落,無水無電,人們多世居務農。「很多人終其一生,不曾踏出這裡一步。」他喜歡釣魚,初次來有如陶淵明溯河循桃花源,那是很久以前了,後來成為他的假日休閒之地。他是第一位闖入這個封閉世界的白人,那時外人的足跡,微乎其微。首次來,人人目不轉睛地盯著他看,有如觀賞稀有動物。
河流兩岸,咫尺之近,靠舢舨船舶渡河,是部落生活的縮影。
不遠處,舢舨噠噠聲靠近,河水因雨季變得黃濁、暴漲,下船來的人群,莫不小心翼翼。瘦弱的小女孩,肩上荷著乾柴枝,稚氣的臉龐,讀不到屬於孩童的輕盈與歡笑,唯身上花布衫的色彩,是沉重沙洲的一抹亮點。瘦骨嶙峋的莊稼漢,一襲白袍飄飄,手持皮鞭,傍著牛羊群,緩緩走過,黃昏來臨。
風,樹梢間輕輕的吹,像一首無言的歌。雲彩,高空上靜靜地注視。泥土地,紅塵滾滾,人間的悲喜劇,上演著。
回程路上,朋友為我補習這部落的歷史與生活背景。
這個地區有三大農作物:玉米,黍,小米。可惜沒有灌溉系統,道地的看天田,雨水若下得少,農作物枯乾,收成少了,秋穫短缺,生活便拮据。
豪薩族是西非的其中一個最大族群,分布地方多,影響甚廣。奈及利亞北部、尼日南部、查德湖沿岸、喀麥隆北部、加納北部以及西非其它各國,都有為數不少的豪薩人。約八世紀起,豪薩人在現今尼日利亞北部建立多個城邦。至十九世紀,豪薩族經歷了數百年移民和征服的歷史發展,故它源於不同民族的融合,發展至有共同語言和共同宗教的族群。
這個部落,正是豪薩族群中的原始居民。穹蒼下,圓拱形帶尖的穀倉,絕美的景觀,令人好奇它的作用。朋友說那稱作「 Rumbu」〈豪薩語茅草屋之意〉。我公司有一個老客戶,公司名就叫「 Rumbu」。二十年來,Rumbu、Rumbu直叫,不解其意。他公司的商標就是傳統的茅草屋。現在,謎底揭曉,主其事的CEO,曾貴為國會的發言人之一,後來轉戰商場,不忘本,以傳統茅草屋為公司名。瞬間,恍然明白,原始圖騰,也可以是時尚的標誌,舊與新不是鴻溝,以傳統加上創新,便是橋了。
當我對著茅草屋升起肅然起敬之心時,主人一襲傳統的白袍,悄悄的出現了。我為茅草屋照相,與主人攀談,互動的情節,沒劇本,卻自然演出,好像我們是旅居的都市人,趁周末走訪了鄉下親戚的他們。
主人掀起穀倉的尖頂大蓋,只見滿滿曬乾的黍物,長長的稉柄,尾端纍纍、飽滿顆粒。為滿足我的好奇,他遞給我一支端詳,邊善意提醒勿沾到手,以免搔癢紅腫不止。
我們的談笑,劃破四周的靜謐,高大的木瓜樹也醒了,青綠的木瓜一顆顆垂吊枝頭,肥碩青翠,像在凝聽。女主人悄悄的出現,揹著沉睡的小嬰兒。年輕的母親,削瘦修長。一襲亮橘的傳統長裙,隨風擺動,細看,嘴唇上著色鮮豔的紅,沒對準嘴唇的線條,可能就地取材於傳統的化妝品吧。哦!愛美不分國界,各有姿態,令人稱奇。
央得同意,入內參觀他們的住屋。朋友說按傳統是不許外人進入,因我而開例。二道迷魂陣似的迴旋土牆進入,真是別有洞天。正中央一個泥土空地,周圍散布著茅草屋,泥土地上埋鍋造飯。柴薪粗塊,炭火燒紅,圓鍋外燻黑,煮熟的小米,一盤盤盛上,澆著疑是番茄醬汁,日常吃食,僅此而已。
角落裡,雞鴨群隊,咕咕咕、啄啄啄,奔走追逐,覓食去。孩童,大揹小,或爬行學步,或嬉戲玩耍。我偷窺茅草屋,狹小空間僅容一張榻舖,顯然只是夜寢用,作息全與日出同步。這塊泥土地,多功能用途:是廚房、餐廳、是活動的客廳,也是畜養家禽或孩子活動的院子。我看得目瞪口呆,刀耕火種的原始生活,在此淋漓盡致演出。我暗想,不只一戶人家居住吧,果然是兄弟妯娌集居,還有難得一見高齡祖母,典型的重視家族的伊斯蘭教文化。
男主人抱幼兒,來到我身旁。瘦巴巴、身輕如燕的孩子在父親的手中,絲毫不費力,我看在眼裡,心裡莫名的沉重起來。我朋友究竟長年在此,一看不對勁,轉頭對父親說,趕快帶孩子去看醫生吧。父親點頭稱是,母親微微頷首,剎那間,我讀出她眼眸中的一抹憂傷。懷中的孩子,過輕的身軀,卻是她心頭的最重。
夕陽西下,晚霞滿天,我們要離去。茅草屋的生活,如此的簡單與粗礪,
瘦弱孩子的影像,如淅瀝淅瀝的雨,流淌在沙漠裡,瞬間,又乾了。
沙漠的雨季,過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