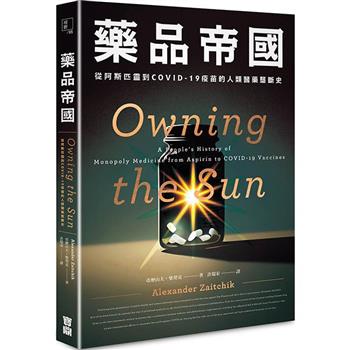Chapter 13
藥廠最好的朋友:比爾.蓋茲與COVID-19
2019年9月底,也就是武漢發生首宗未通報的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人傳人案例的數週前,串流媒體Netflix推出關於比爾.蓋茲的紀錄片《蓋茲之道》(Inside Bill’s Brain)。這部獲蓋茲認可的紀錄片讚美蓋茲,對蓋茲的刻畫採用過去20年間常見的一種套路:蓋茲曾是傲慢、躁動和可能過度雄心勃勃的天才,但如今已變成被謙遜感動的慈善家暨哲學家,英勇地利用他的天才和財富致力修復陷入危機的世界。這部紀錄片呈現了蓋茲如何鑽研各種重要問題,冷靜估算,敏銳觀察,善用他功能強大、高瞻遠矚的頭腦。蓋茲總結道,如果我們要克服氣候變遷、能源轉型和傳染病帶來的嚴峻挑戰,「我們有必要以快得不自然的速度開始部署解決方案。」
《蓋茲之道》推出幾個月後,蓋茲得到一個機會來證明他對採用空前快速的解決方案的決心。
如上一章所述,COVID-19引發緊急的規劃會議和國際辯論,著眼於打敗一個世紀以來第一種空氣傳播的大流行病毒的最有效策略。在WHO,公共衛生專家於2月開會,勾勒出一個合作研究、開發、測試、製造和部署藥品與疫苗的計畫。生產和分發數十億劑疫苗是艱鉅的任務,但因為病毒適應和突變的機會主義性質,這也是急迫的任務。這些討論可以參考愛滋病、伊波拉病毒(Ebola)和禽流感(avian flu)危機的慘痛教訓——這些危機每一次都展示了智慧財產權和利潤動機如何導致人為的匱乏和不平等。
在2020年初,沒有一個人比蓋茲更有條件推動「以快得不自然的速度」擴大抗疫方面的研發生產。在川普的白宮製造反科學無能奇觀之際,蓋茲是事實上的全球公共衛生政策沙皇。他的這個身分,是他在2000年卸任微軟執行長後,透過蓋茲基金會花了數十億美元買來的。蓋茲對全球公共衛生政策的影響力是獨一無二的:一方面是他可以影響的政策範圍非常廣,另一方面是他有能力在不同的權力層級以不同的形式影響政策,包括主導資金緊絀的非洲國家政府的預算抉擇,以至為國際衛生和開發機構設定長期議程。他帶著權威和影響力進入出版商、政府首長、非營利組織和製藥業高層的辦公室。
蓋茲沒有利用他的這種權威支持全球南方的專家和領袖,甚至不與他們接觸;這些人警告世人,將COVID-19科研成果留在囤積智慧財產權的公司手中是很危險的。蓋茲選擇支持另一陣營,致力確保抗疫措施與對知識壟斷的深刻意識形態支持保持一致;這種意識形態是貫穿蓋茲人生每一個階段和每一項事業的一個特徵。
在與製藥公司高層、政府官員和國際衛生機構高層的私下會面中,蓋茲和他的代表確認了他們支持企業控制抗疫科研成果,並試圖阻止任何關於集合智慧財產權或擱置TRIPS制度的討論。他們提出集合疫苗採購訂單的構想。與蓋茲並肩作戰的是理查.懷爾德(Richard Wilder),他曾是微軟的智慧財產權總監,如今在蓋茲的傳染病研究旗艦組織「流行病預防創新聯盟」(Coalition for Epidemic Preparedness Innovations,CEPI)擔任法務長和業務發展總監。CEPI是蓋茲在2017年達沃斯(Davos)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投入種子資金發起的一個公私合作計畫,體現了支持現行智慧財產權制度的一種慈善模式,而蓋茲的組織將在他試圖協調全球對抗COVID-19的過程中複製這種模式。
無國界醫生的政策顧問曼紐爾.馬丁(Manuel Martin)說:「在病毒大流行的初期,當一些政府和公司大談全球公共財時,蓋茲有機會發揮重大作用,支持開放模式,例如集合相關技術。當時他大可站出來說:『我們要求你們這麼做,因為我們有道德義務將一場競賽變成一場合作,大家都將跨平臺和跨領域交換資訊。』但蓋茲的人很早就說智慧財產權不是取得疫苗的障礙,因此打擊了人們對開放模式的熱情。他們的說法顯然是錯誤的。智慧財產權不是取得疫苗的唯一障礙,但從來沒有人說它是唯一的障礙。」
蓋茲的行動波及他在公共衛生領域所能影響的範圍,也就是這個領域沒有東西不受影響。
非政府組織知識生態國際(Knowledge Ecology International)的詹姆斯.洛夫說:「他有龐大的權力。他可以使你失去你在聯合國的工作。他知道,如果你想在全球公共衛生領域工作,最好不要因為質疑蓋茲基金會在智慧財產權和壟斷方面的立場而成為它的敵人。」
*******
2020年3月10日,比爾與梅琳達蓋茲基金會宣布與英國惠康基金會(Wellcome Trust)和萬事達卡(Mastercard)合作,帶頭啟動一個名為「治療加速」(Therapeutics Accelerator)的新機制,為新型冠狀病毒尋找治療方法。第二天,WHO宣布這種病毒已進入全球大流行狀態。
這項倡議的另一個重要作用,是為一家金融服務公司樹立良好的社會形象,這符合蓋茲在企業慈善方面的標誌性管理諮詢方法,是蓋茲將以同樣的老套路處理迫在眉睫的全球危機的一個早期跡象。當時關於如何組織全球研究工作的辯論開始令產業界感到不安,而瞭解這些辯論的人表示,蓋茲選擇在那時候推動「治療加速」並非巧合。
詹姆斯.洛夫說:「蓋茲希望維持專利壟斷模式,他先發制人,搶在WHO宣布研發合作計畫之前宣布他的『治療加速』計畫,釋出智慧財產權規則將如常運作的訊號。當時事情是有可能往另一方向發展的,但蓋茲利用他的影響力阻止了爭取分享製造抗疫產品所需知識的努力,包括分享技術訣竅、數據、細胞株(cell line),以及促進相關技術移轉。C-TAP本來可以包含所有這些內容。蓋茲透過加速計畫與產業界簽訂的合約對廠商沒什麼要求,包括不要求廠商揭露重要資訊,而資訊透明在約20個方面至關重要。自1990年代末以來,蓋茲一直在告訴所有人:即使你們保持自私自利,只要口頭表示將為窮國提供折扣優惠,就可以上天堂。」
4月24日,蓋茲推出加速計畫的擴大版「獲取COVID-19工具加速計畫」(Access to COVID-19 Tools Accelerator,ACT-A),宣稱它是一套全方位的方案,可以解決許多人預料的抗疫產品供應和取得的雙重危機。ACT-A由四大「支柱」組成,涵蓋衛生系統、診斷、治療和疫苗四方面。當中的疫苗支柱「COVID-19疫苗全球取得機制」(COVAX)始終是核心。COVAX在6月由GAVI正式啟動,其構想是一個疫苗採購和交易中心,同時服務富國和窮國,而GAVI是蓋茲主導的致力於全球南方兒童疫苗接種的公私合作組織。COVAX要求CEPI尋找並投資於足夠多的有望成功的疫苗,以建立一個有效疫苗組合。然後GAVI將利用預先市場承諾(Advance Market Commitment,AMC)這種融資機制組織疫苗採購和分配——基本上就是一種買方俱樂部,將補貼疫苗以滿足WHO所講的「優先五分之一」,或最弱勢的20%人口,也就是世上最貧窮的92個國家的需求。至於達到群體免疫所需要的餘下50%人口的需求,就要靠各國在全球市場上競爭來滿足。
產業界和GAVI的媒體關係部門大張旗鼓宣傳COVAX,但該計畫是基於這個信念:我們可以誘導市場,使它在全球的公共衛生和安全需求,與掌握WHO核准的第一批疫苗、重視專利壟斷的公司的利潤動機之間取得平衡。此外,COVAX要有效運作,還有賴富裕國家——COVAX稱之為「自籌資金的國家」(self-financing country)——的政府保持克制,避免競相與製造商達成雙邊協議,導致其他國家面臨疫苗缺貨的現實。事實證明這兩個前提都不成立,而後果是災難性的。
「蓋茲模式假定生產將追上需求的變化,完全不考慮企業沒有興趣解決的供應問題,」倡議組織PrEP4All的主任詹姆斯.克雷倫斯坦(James Krellenstein)說。「這是個非常危險的無能計畫,它注定了病毒將在傳播過程中產生更多變種。」
在COVAX推出後的頭幾個月裡,美國政府簽了七份雙邊預購協議,數量接近10億劑疫苗;英國簽署了五份協議,獲得2億7000萬劑,是該國總需求的兩倍有餘。G7的其他國家則占了餘下的大部分疫苗供給。
如果蓋茲的組織只是沒有預料到供應危機,又或者因為出於善意嘗試以技術手段解決政治問題而犯了錯,那麼COVAX可說是某人在行使權力時犯了大錯。但是,COVAX比單純的規劃失誤或想像力不足問題嚴重得多。事實上,有些人看到了供應危機的根源,也預料到問題的嚴重程度,但蓋茲親自嘗試破壞這些人的努力,而且他在做這件事的同時,動用一切可用的手段,包括利用直接的所有權,積極限制壟斷模式以外的技術授權和生產。
牛津大學詹納研究所(Jenner Institute)的所長宣布他希望將CEPI資助的一款候選疫苗的權利置於公有領域後,蓋茲介入此事。如凱薩健康新聞(Kaiser Health News)所報導:「數週後,在比爾與梅琳達蓋茲基金會敦促下,牛津大學改變了決定,與阿斯特捷利康簽訂獨家協議,將該疫苗的全部權利獨家授予這家製藥巨頭,但不要求該公司保證低價供應疫苗。」在CureVac的例子中,該公司從CEPI那裡獲得超過2000萬美元用於開發mRNA疫苗,但合約刪除了「取得義務」(access obligation)條款,而且完全不解釋原因。「這令人困惑,」非政府組織公共公民(Public Citizen)的黎茲維(Zain Rizvi)對《國家》雜誌(The Nation)表示。「CEPI幫助啟動了CureVac的疫苗研發工作,但隨後似乎放棄了它可以用來在世界各地擴大疫苗生產的籌碼。」
CureVac合約刪除取得義務條款,使人想起CEPI最初與合作藥廠所簽的合約。蓋茲2017年在達沃斯宣布啟動CEPI時,宣傳重點之一是該倡議的定價承諾,它要求合作廠商貫徹該倡議的社會價值和使命。但隨著媒體的關注減少,相關公司認為那些言語講過頭了。CEPI於是盡職地淡化相關說法,解除合作廠商受到的束縛。
蓋茲利用合約條款這種把戲掩護他維護專利壟斷的決心,使人想到以下問題:這是在維護誰的利益?如何維護?產業界很清楚,這些取得承諾的細節和結果,遠不如這種承諾存在這個事實那麼受關注。只要這種承諾存在,而且有組織加以宣傳,它們就能幫助產業界擾人耳目;若非如此,產業界面對要求推動根本改革的呼聲將會啞口無言,而之所以必須進行根本改革,是因為產業界存在系統失靈問題,而這正是取得承諾有其必要的原因。
蓋茲慈善事業的這一方面在2020年4月的ACT-A啟動儀式上展現了出來,出席儀式的包括來自產業界的若干「創始夥伴」。國際製藥生產聯盟主席湯瑪斯.庫尼稱讚該倡議是「具里程碑意義的全球合作計畫」(他將在接下來數週和數個月裡一再提到這一點),而既然有了它,就不必考慮其他框架了。全靠這個倡議,輝瑞執行長艾伯特.博爾拉才可以在該聯盟舉辦的媒體活動上迴避那麼多關於智慧財產權的問題,並且宣稱:「我們已經有了所需要的平臺,產業界已經在做所有該做的事。」
如果蓋茲利用他的影響力支持要求集合抗疫技術、擱置相關智慧財產權和組織全球技術移轉的呼籲,他數十年來堅決支持知識壟斷的歷史將戛然而止。他的這段歷史,可以追溯到他青少年時代對1970年代電腦程式開源文化的報復性討伐。在1980和1990年代,正是智慧財產權的一種創新應用——電腦程式碼獲得版權保護——使蓋茲在1995年起20年裡的大部分時間成為全球首富。正是在這一年,在包括微軟在內的產業界聯盟耗費巨資從事遊說之後,TRIPS開始生效。四年之後,蓋茲手持支票簿出現在公共衛生領域,此時他在TRIPS聯盟裡的夥伴處境艱難,面對爭取打破他們對救命愛滋病藥的壟斷的全球運動,顯得左支右絀。
藥廠最好的朋友:比爾.蓋茲與COVID-19
2019年9月底,也就是武漢發生首宗未通報的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人傳人案例的數週前,串流媒體Netflix推出關於比爾.蓋茲的紀錄片《蓋茲之道》(Inside Bill’s Brain)。這部獲蓋茲認可的紀錄片讚美蓋茲,對蓋茲的刻畫採用過去20年間常見的一種套路:蓋茲曾是傲慢、躁動和可能過度雄心勃勃的天才,但如今已變成被謙遜感動的慈善家暨哲學家,英勇地利用他的天才和財富致力修復陷入危機的世界。這部紀錄片呈現了蓋茲如何鑽研各種重要問題,冷靜估算,敏銳觀察,善用他功能強大、高瞻遠矚的頭腦。蓋茲總結道,如果我們要克服氣候變遷、能源轉型和傳染病帶來的嚴峻挑戰,「我們有必要以快得不自然的速度開始部署解決方案。」
《蓋茲之道》推出幾個月後,蓋茲得到一個機會來證明他對採用空前快速的解決方案的決心。
如上一章所述,COVID-19引發緊急的規劃會議和國際辯論,著眼於打敗一個世紀以來第一種空氣傳播的大流行病毒的最有效策略。在WHO,公共衛生專家於2月開會,勾勒出一個合作研究、開發、測試、製造和部署藥品與疫苗的計畫。生產和分發數十億劑疫苗是艱鉅的任務,但因為病毒適應和突變的機會主義性質,這也是急迫的任務。這些討論可以參考愛滋病、伊波拉病毒(Ebola)和禽流感(avian flu)危機的慘痛教訓——這些危機每一次都展示了智慧財產權和利潤動機如何導致人為的匱乏和不平等。
在2020年初,沒有一個人比蓋茲更有條件推動「以快得不自然的速度」擴大抗疫方面的研發生產。在川普的白宮製造反科學無能奇觀之際,蓋茲是事實上的全球公共衛生政策沙皇。他的這個身分,是他在2000年卸任微軟執行長後,透過蓋茲基金會花了數十億美元買來的。蓋茲對全球公共衛生政策的影響力是獨一無二的:一方面是他可以影響的政策範圍非常廣,另一方面是他有能力在不同的權力層級以不同的形式影響政策,包括主導資金緊絀的非洲國家政府的預算抉擇,以至為國際衛生和開發機構設定長期議程。他帶著權威和影響力進入出版商、政府首長、非營利組織和製藥業高層的辦公室。
蓋茲沒有利用他的這種權威支持全球南方的專家和領袖,甚至不與他們接觸;這些人警告世人,將COVID-19科研成果留在囤積智慧財產權的公司手中是很危險的。蓋茲選擇支持另一陣營,致力確保抗疫措施與對知識壟斷的深刻意識形態支持保持一致;這種意識形態是貫穿蓋茲人生每一個階段和每一項事業的一個特徵。
在與製藥公司高層、政府官員和國際衛生機構高層的私下會面中,蓋茲和他的代表確認了他們支持企業控制抗疫科研成果,並試圖阻止任何關於集合智慧財產權或擱置TRIPS制度的討論。他們提出集合疫苗採購訂單的構想。與蓋茲並肩作戰的是理查.懷爾德(Richard Wilder),他曾是微軟的智慧財產權總監,如今在蓋茲的傳染病研究旗艦組織「流行病預防創新聯盟」(Coalition for Epidemic Preparedness Innovations,CEPI)擔任法務長和業務發展總監。CEPI是蓋茲在2017年達沃斯(Davos)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投入種子資金發起的一個公私合作計畫,體現了支持現行智慧財產權制度的一種慈善模式,而蓋茲的組織將在他試圖協調全球對抗COVID-19的過程中複製這種模式。
無國界醫生的政策顧問曼紐爾.馬丁(Manuel Martin)說:「在病毒大流行的初期,當一些政府和公司大談全球公共財時,蓋茲有機會發揮重大作用,支持開放模式,例如集合相關技術。當時他大可站出來說:『我們要求你們這麼做,因為我們有道德義務將一場競賽變成一場合作,大家都將跨平臺和跨領域交換資訊。』但蓋茲的人很早就說智慧財產權不是取得疫苗的障礙,因此打擊了人們對開放模式的熱情。他們的說法顯然是錯誤的。智慧財產權不是取得疫苗的唯一障礙,但從來沒有人說它是唯一的障礙。」
蓋茲的行動波及他在公共衛生領域所能影響的範圍,也就是這個領域沒有東西不受影響。
非政府組織知識生態國際(Knowledge Ecology International)的詹姆斯.洛夫說:「他有龐大的權力。他可以使你失去你在聯合國的工作。他知道,如果你想在全球公共衛生領域工作,最好不要因為質疑蓋茲基金會在智慧財產權和壟斷方面的立場而成為它的敵人。」
*******
2020年3月10日,比爾與梅琳達蓋茲基金會宣布與英國惠康基金會(Wellcome Trust)和萬事達卡(Mastercard)合作,帶頭啟動一個名為「治療加速」(Therapeutics Accelerator)的新機制,為新型冠狀病毒尋找治療方法。第二天,WHO宣布這種病毒已進入全球大流行狀態。
這項倡議的另一個重要作用,是為一家金融服務公司樹立良好的社會形象,這符合蓋茲在企業慈善方面的標誌性管理諮詢方法,是蓋茲將以同樣的老套路處理迫在眉睫的全球危機的一個早期跡象。當時關於如何組織全球研究工作的辯論開始令產業界感到不安,而瞭解這些辯論的人表示,蓋茲選擇在那時候推動「治療加速」並非巧合。
詹姆斯.洛夫說:「蓋茲希望維持專利壟斷模式,他先發制人,搶在WHO宣布研發合作計畫之前宣布他的『治療加速』計畫,釋出智慧財產權規則將如常運作的訊號。當時事情是有可能往另一方向發展的,但蓋茲利用他的影響力阻止了爭取分享製造抗疫產品所需知識的努力,包括分享技術訣竅、數據、細胞株(cell line),以及促進相關技術移轉。C-TAP本來可以包含所有這些內容。蓋茲透過加速計畫與產業界簽訂的合約對廠商沒什麼要求,包括不要求廠商揭露重要資訊,而資訊透明在約20個方面至關重要。自1990年代末以來,蓋茲一直在告訴所有人:即使你們保持自私自利,只要口頭表示將為窮國提供折扣優惠,就可以上天堂。」
4月24日,蓋茲推出加速計畫的擴大版「獲取COVID-19工具加速計畫」(Access to COVID-19 Tools Accelerator,ACT-A),宣稱它是一套全方位的方案,可以解決許多人預料的抗疫產品供應和取得的雙重危機。ACT-A由四大「支柱」組成,涵蓋衛生系統、診斷、治療和疫苗四方面。當中的疫苗支柱「COVID-19疫苗全球取得機制」(COVAX)始終是核心。COVAX在6月由GAVI正式啟動,其構想是一個疫苗採購和交易中心,同時服務富國和窮國,而GAVI是蓋茲主導的致力於全球南方兒童疫苗接種的公私合作組織。COVAX要求CEPI尋找並投資於足夠多的有望成功的疫苗,以建立一個有效疫苗組合。然後GAVI將利用預先市場承諾(Advance Market Commitment,AMC)這種融資機制組織疫苗採購和分配——基本上就是一種買方俱樂部,將補貼疫苗以滿足WHO所講的「優先五分之一」,或最弱勢的20%人口,也就是世上最貧窮的92個國家的需求。至於達到群體免疫所需要的餘下50%人口的需求,就要靠各國在全球市場上競爭來滿足。
產業界和GAVI的媒體關係部門大張旗鼓宣傳COVAX,但該計畫是基於這個信念:我們可以誘導市場,使它在全球的公共衛生和安全需求,與掌握WHO核准的第一批疫苗、重視專利壟斷的公司的利潤動機之間取得平衡。此外,COVAX要有效運作,還有賴富裕國家——COVAX稱之為「自籌資金的國家」(self-financing country)——的政府保持克制,避免競相與製造商達成雙邊協議,導致其他國家面臨疫苗缺貨的現實。事實證明這兩個前提都不成立,而後果是災難性的。
「蓋茲模式假定生產將追上需求的變化,完全不考慮企業沒有興趣解決的供應問題,」倡議組織PrEP4All的主任詹姆斯.克雷倫斯坦(James Krellenstein)說。「這是個非常危險的無能計畫,它注定了病毒將在傳播過程中產生更多變種。」
在COVAX推出後的頭幾個月裡,美國政府簽了七份雙邊預購協議,數量接近10億劑疫苗;英國簽署了五份協議,獲得2億7000萬劑,是該國總需求的兩倍有餘。G7的其他國家則占了餘下的大部分疫苗供給。
如果蓋茲的組織只是沒有預料到供應危機,又或者因為出於善意嘗試以技術手段解決政治問題而犯了錯,那麼COVAX可說是某人在行使權力時犯了大錯。但是,COVAX比單純的規劃失誤或想像力不足問題嚴重得多。事實上,有些人看到了供應危機的根源,也預料到問題的嚴重程度,但蓋茲親自嘗試破壞這些人的努力,而且他在做這件事的同時,動用一切可用的手段,包括利用直接的所有權,積極限制壟斷模式以外的技術授權和生產。
牛津大學詹納研究所(Jenner Institute)的所長宣布他希望將CEPI資助的一款候選疫苗的權利置於公有領域後,蓋茲介入此事。如凱薩健康新聞(Kaiser Health News)所報導:「數週後,在比爾與梅琳達蓋茲基金會敦促下,牛津大學改變了決定,與阿斯特捷利康簽訂獨家協議,將該疫苗的全部權利獨家授予這家製藥巨頭,但不要求該公司保證低價供應疫苗。」在CureVac的例子中,該公司從CEPI那裡獲得超過2000萬美元用於開發mRNA疫苗,但合約刪除了「取得義務」(access obligation)條款,而且完全不解釋原因。「這令人困惑,」非政府組織公共公民(Public Citizen)的黎茲維(Zain Rizvi)對《國家》雜誌(The Nation)表示。「CEPI幫助啟動了CureVac的疫苗研發工作,但隨後似乎放棄了它可以用來在世界各地擴大疫苗生產的籌碼。」
CureVac合約刪除取得義務條款,使人想起CEPI最初與合作藥廠所簽的合約。蓋茲2017年在達沃斯宣布啟動CEPI時,宣傳重點之一是該倡議的定價承諾,它要求合作廠商貫徹該倡議的社會價值和使命。但隨著媒體的關注減少,相關公司認為那些言語講過頭了。CEPI於是盡職地淡化相關說法,解除合作廠商受到的束縛。
蓋茲利用合約條款這種把戲掩護他維護專利壟斷的決心,使人想到以下問題:這是在維護誰的利益?如何維護?產業界很清楚,這些取得承諾的細節和結果,遠不如這種承諾存在這個事實那麼受關注。只要這種承諾存在,而且有組織加以宣傳,它們就能幫助產業界擾人耳目;若非如此,產業界面對要求推動根本改革的呼聲將會啞口無言,而之所以必須進行根本改革,是因為產業界存在系統失靈問題,而這正是取得承諾有其必要的原因。
蓋茲慈善事業的這一方面在2020年4月的ACT-A啟動儀式上展現了出來,出席儀式的包括來自產業界的若干「創始夥伴」。國際製藥生產聯盟主席湯瑪斯.庫尼稱讚該倡議是「具里程碑意義的全球合作計畫」(他將在接下來數週和數個月裡一再提到這一點),而既然有了它,就不必考慮其他框架了。全靠這個倡議,輝瑞執行長艾伯特.博爾拉才可以在該聯盟舉辦的媒體活動上迴避那麼多關於智慧財產權的問題,並且宣稱:「我們已經有了所需要的平臺,產業界已經在做所有該做的事。」
如果蓋茲利用他的影響力支持要求集合抗疫技術、擱置相關智慧財產權和組織全球技術移轉的呼籲,他數十年來堅決支持知識壟斷的歷史將戛然而止。他的這段歷史,可以追溯到他青少年時代對1970年代電腦程式開源文化的報復性討伐。在1980和1990年代,正是智慧財產權的一種創新應用——電腦程式碼獲得版權保護——使蓋茲在1995年起20年裡的大部分時間成為全球首富。正是在這一年,在包括微軟在內的產業界聯盟耗費巨資從事遊說之後,TRIPS開始生效。四年之後,蓋茲手持支票簿出現在公共衛生領域,此時他在TRIPS聯盟裡的夥伴處境艱難,面對爭取打破他們對救命愛滋病藥的壟斷的全球運動,顯得左支右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