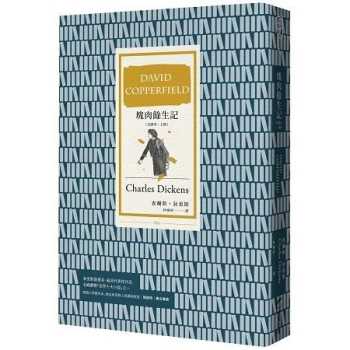〈導讀〉
閱讀一個年輕人的狂野心性:十九世紀狄更斯與二十一世紀讀者的相遇
實踐大學應外系、創意產業博士班講座教授 陳超明
For I knew, now, that my own heart was undisciplined when it first loved Dora; and that if it had been disciplined, it never could have felt, when we were married, what it had felt in its secret experience. (因為我現在知道,當我第一次愛上朵拉那時,我的心性是狂野的。如果那時我心已馴服,就不可能,在我們結婚時候,感受那種神祕經驗。)
這是《塊肉餘生記》主人翁大衛(David Copperfield),在小說中,最深刻的吶喊。唯有狂野的心性,才能體會情與慾間的神祕滋味,但也由於這「未經馴服」的心性,挑戰英國維多利亞時期婚姻的道德基礎。結婚到底為了什麼?夫妻倆如何在婚姻的鏈結中,發掘自己無法宣洩的自我與肉體的誘惑呢?這些問題,一直困擾著十九世紀的小說家狄更斯,也是我們二十一世記讀者在閱讀這本小說時,不斷問自己的問題。
這本《塊肉餘生記》,敘述年輕男子的成長,是一部傳統的教育與成長小說(bildungsroman),在字裡行間中,也透露出英國最偉大的小說家狄更斯個人的創傷歷程。將個人小時候受屈辱的經驗寫入小說,狄更斯模糊了小說與事實的界線。而在其自序中,他稱《塊肉餘生記》是他最喜愛的小孩 (“favorite child” ),無疑的,這是一部從他內心、從自身經驗中,所勾劃出最深刻的作品。
從衝突中成長,從掙扎中站起來
成長需要衝突,成長需要掙扎,這部小說也是狄更斯描寫衝突、描寫傷痕最直接的作品。從小時候戀母與喪父的創傷,到長大後情慾衝動,都赤裸裸地呈現在讀者面前,誠如敘述者大衛所說的:「我回首這一切,內心充滿刺痛。」
然而成長的動力為何呢?刺痛如何療傷?一個沒有自覺的人、一個不會犯錯的人、一個循規蹈矩的人,是不會體認自我錯誤,也永遠不會成長。急遽醒悟與反省,來自主角的心性與自覺。這不僅是一種道德的自覺,更是一種情慾的告白。
這是一部情慾告白的小說
傳統閱讀這本小說,大抵從主人翁的年輕衝動到成年後的成熟,如何在自我錯誤中,找到人生最終的靈魂伴侶(soul mate),道德論述及婚姻真諦,在閱讀中不斷被強化。然而,對我來說,這樣的閱讀,似乎忽略了小說家隱藏在道德論述下面的不安與焦慮:一個十九世紀年輕人的性心理與性成長。這部小說,不僅是如何教育年輕人面對家庭與社會,更是如何面對自我身體、情慾與性衝動的真實寫照。即使,小說家受限於維多利亞時期道德規範與出版限制,無法呈現性愛場景,然而,主角不自覺受到肉體牽引,在在看出這是維多利亞社會的集體焦慮:如何在性道德論述中,找到個人情慾的出口。
小說的主人翁,以第一人稱的觀點切入,告訴自己,他這一生命運來自他「狂野心性的第一個錯誤衝動」(“the first mistaken impulse of an undisciplined heart” ),也就是不受道德傳統與教化馴服的野性,從情慾衝動下,經常做出錯誤的判斷與行為。這個野性衝動,驅使主角從對母親的迷戀,歷經青少年同伴的同性(或同性戀)依賴,到後來與象徵青春肉體的朵拉(Dora)結婚,都是一連串創傷的過程,但也是深刻且令人陶醉的片刻。
「衝動的錯誤」,當然是從道德與教育的觀點來看。然而,也就是這種「錯誤」,才凸顯年輕人自我覺醒的可貴。大衛的第一個性覺醒,來自於年輕的同伴艾蜜莉(Emily)與史帝福斯(Steerforth)。這一女、一男,開啟了大衛內心對男女情慾的渴望,這種渴望是純潔的、是淨化的。但也就是這種情慾渴望,導致後來對於朵拉肉體的沉迷。然而,感性與理性並存的大衛,卻能從情慾沉迷中甦醒,認識他生命中的真愛。與其說,這是大衛個人的情慾歷程,不如說這是狄更斯對於年輕人成長最重要的記錄:從迷戀到情慾,從情慾到真情。
十九世紀與二十一世紀的相遇:情慾當道或道德戰勝?
小說的結局無疑是非常有啟發性的,到底年輕的你我,情歸何處?到底處於情慾漩渦的男女,如何自救?到底婚姻的情慾何在?遠在十九世紀的狄更斯,似乎冥冥之中,為二十一世紀,提供了複雜且多元的思考空間。
二十一世紀的讀者,在這本充滿道德教育與情慾衝突的小說中,不僅可以偷窺年輕男子的心性與情慾發展,更可以思索在這個充滿情慾的二十一世紀社會中,我們如何從錯誤中成長?如何在衝動中走出來?
經典作品中,這是一部刻劃年輕人情慾最深刻的小說,述說著幾百年來,任何人曾經年輕過的深刻體會,實在不容錯過。細讀或重讀這本經典,絕對不要錯過這些細膩情感,也不要輕忽狄更斯文字所帶來的道德與文化衝擊!
作者序(一八五〇年版)
書稿剛完成,我備感興奮,因此要脫離這種心情,沉著地完成這篇正式序言並非易事。我對本書的關心仍未退卻、依舊強烈;我的心分裂成愉悅與惋惜兩部分:愉悅是因構思已久的作品終於完成,但同時也為得和眾多老朋友道別而惋惜。不過再說下去,我的個人心事與私人情感恐怕會讓我最親愛的讀者厭煩。
除此之外,關於這本書我所能說的,在書中都努力說盡了。
要說在兩年的天馬行空之後把筆放下有多麼令人難過,或是作者眼見創造出的人物將永遠離開他時,是怎麼感覺像把一部分的自己留在那陰暗的世界裡,這些讀者大概都覺得無關緊要。然而我也沒有什麼好說的了,除非,真要我坦承的話(這更加不重要),我認為讀者在閱讀本書時,不會比我撰寫時對書中的每一件事更加深信不疑。
因此我想,與其陷在過去的回憶中,不如展望未來。我覺得自己闔上這本書最好的方式,莫過於期盼未來再次發表連載月刊的日子,以及細數曾落在《塊肉餘生記》書頁上的宜人陽光和細雨,這樣我就心滿意足了。
寫於倫敦,一八五〇年十月
* * * *
作者序(查爾斯.狄更斯版)
我在本書的原序中曾寫道:
書稿剛完成,我備感興奮,因此要脫離這種心情,沉著地完成這篇正式序言並非易事。我對本書的關心仍未退卻、依舊強烈;我的心分裂成愉悅與惋惜兩部分:愉悅是因構思已久的作品終於完成,但同時也為得和眾多老朋友道別而惋惜。不過再說下去,我的個人心事與私人情感恐怕會讓我最親愛的讀者厭煩。
除此之外,關於這本書我所能說的,在書中都努力說盡了。
要說在兩年的天馬行空之後把筆放下有多麼令人難過,或是作者眼見創造出的人物將永遠離開他時,是怎麼感覺像把一部分的自己留在那陰暗的世界裡,這些讀者大概都覺得無關緊要。然而我也沒有什麼好說的了,除非,真要我坦承的話(這更加不重要),我認為讀者在閱讀本書時,不會比我撰寫時對書中的每一件事更加深信不疑。
這些聲明至今仍千真萬確,因此我只能再告訴讀者一句知心話:在我所有的著作中,我最喜愛的就是這本。大家或許能夠輕易相信,我是個溺愛子女的父親,疼愛我想像出來的每個小孩,真的也沒有人比我更愛這個家庭了。但就像很多溺愛子女的父母一樣,我的內心深處也有個最偏愛的小孩,他就是大衛.考柏菲爾德。
寫於一八六九年
閱讀一個年輕人的狂野心性:十九世紀狄更斯與二十一世紀讀者的相遇
實踐大學應外系、創意產業博士班講座教授 陳超明
For I knew, now, that my own heart was undisciplined when it first loved Dora; and that if it had been disciplined, it never could have felt, when we were married, what it had felt in its secret experience. (因為我現在知道,當我第一次愛上朵拉那時,我的心性是狂野的。如果那時我心已馴服,就不可能,在我們結婚時候,感受那種神祕經驗。)
這是《塊肉餘生記》主人翁大衛(David Copperfield),在小說中,最深刻的吶喊。唯有狂野的心性,才能體會情與慾間的神祕滋味,但也由於這「未經馴服」的心性,挑戰英國維多利亞時期婚姻的道德基礎。結婚到底為了什麼?夫妻倆如何在婚姻的鏈結中,發掘自己無法宣洩的自我與肉體的誘惑呢?這些問題,一直困擾著十九世紀的小說家狄更斯,也是我們二十一世記讀者在閱讀這本小說時,不斷問自己的問題。
這本《塊肉餘生記》,敘述年輕男子的成長,是一部傳統的教育與成長小說(bildungsroman),在字裡行間中,也透露出英國最偉大的小說家狄更斯個人的創傷歷程。將個人小時候受屈辱的經驗寫入小說,狄更斯模糊了小說與事實的界線。而在其自序中,他稱《塊肉餘生記》是他最喜愛的小孩 (“favorite child” ),無疑的,這是一部從他內心、從自身經驗中,所勾劃出最深刻的作品。
從衝突中成長,從掙扎中站起來
成長需要衝突,成長需要掙扎,這部小說也是狄更斯描寫衝突、描寫傷痕最直接的作品。從小時候戀母與喪父的創傷,到長大後情慾衝動,都赤裸裸地呈現在讀者面前,誠如敘述者大衛所說的:「我回首這一切,內心充滿刺痛。」
然而成長的動力為何呢?刺痛如何療傷?一個沒有自覺的人、一個不會犯錯的人、一個循規蹈矩的人,是不會體認自我錯誤,也永遠不會成長。急遽醒悟與反省,來自主角的心性與自覺。這不僅是一種道德的自覺,更是一種情慾的告白。
這是一部情慾告白的小說
傳統閱讀這本小說,大抵從主人翁的年輕衝動到成年後的成熟,如何在自我錯誤中,找到人生最終的靈魂伴侶(soul mate),道德論述及婚姻真諦,在閱讀中不斷被強化。然而,對我來說,這樣的閱讀,似乎忽略了小說家隱藏在道德論述下面的不安與焦慮:一個十九世紀年輕人的性心理與性成長。這部小說,不僅是如何教育年輕人面對家庭與社會,更是如何面對自我身體、情慾與性衝動的真實寫照。即使,小說家受限於維多利亞時期道德規範與出版限制,無法呈現性愛場景,然而,主角不自覺受到肉體牽引,在在看出這是維多利亞社會的集體焦慮:如何在性道德論述中,找到個人情慾的出口。
小說的主人翁,以第一人稱的觀點切入,告訴自己,他這一生命運來自他「狂野心性的第一個錯誤衝動」(“the first mistaken impulse of an undisciplined heart” ),也就是不受道德傳統與教化馴服的野性,從情慾衝動下,經常做出錯誤的判斷與行為。這個野性衝動,驅使主角從對母親的迷戀,歷經青少年同伴的同性(或同性戀)依賴,到後來與象徵青春肉體的朵拉(Dora)結婚,都是一連串創傷的過程,但也是深刻且令人陶醉的片刻。
「衝動的錯誤」,當然是從道德與教育的觀點來看。然而,也就是這種「錯誤」,才凸顯年輕人自我覺醒的可貴。大衛的第一個性覺醒,來自於年輕的同伴艾蜜莉(Emily)與史帝福斯(Steerforth)。這一女、一男,開啟了大衛內心對男女情慾的渴望,這種渴望是純潔的、是淨化的。但也就是這種情慾渴望,導致後來對於朵拉肉體的沉迷。然而,感性與理性並存的大衛,卻能從情慾沉迷中甦醒,認識他生命中的真愛。與其說,這是大衛個人的情慾歷程,不如說這是狄更斯對於年輕人成長最重要的記錄:從迷戀到情慾,從情慾到真情。
十九世紀與二十一世紀的相遇:情慾當道或道德戰勝?
小說的結局無疑是非常有啟發性的,到底年輕的你我,情歸何處?到底處於情慾漩渦的男女,如何自救?到底婚姻的情慾何在?遠在十九世紀的狄更斯,似乎冥冥之中,為二十一世紀,提供了複雜且多元的思考空間。
二十一世紀的讀者,在這本充滿道德教育與情慾衝突的小說中,不僅可以偷窺年輕男子的心性與情慾發展,更可以思索在這個充滿情慾的二十一世紀社會中,我們如何從錯誤中成長?如何在衝動中走出來?
經典作品中,這是一部刻劃年輕人情慾最深刻的小說,述說著幾百年來,任何人曾經年輕過的深刻體會,實在不容錯過。細讀或重讀這本經典,絕對不要錯過這些細膩情感,也不要輕忽狄更斯文字所帶來的道德與文化衝擊!
作者序(一八五〇年版)
書稿剛完成,我備感興奮,因此要脫離這種心情,沉著地完成這篇正式序言並非易事。我對本書的關心仍未退卻、依舊強烈;我的心分裂成愉悅與惋惜兩部分:愉悅是因構思已久的作品終於完成,但同時也為得和眾多老朋友道別而惋惜。不過再說下去,我的個人心事與私人情感恐怕會讓我最親愛的讀者厭煩。
除此之外,關於這本書我所能說的,在書中都努力說盡了。
要說在兩年的天馬行空之後把筆放下有多麼令人難過,或是作者眼見創造出的人物將永遠離開他時,是怎麼感覺像把一部分的自己留在那陰暗的世界裡,這些讀者大概都覺得無關緊要。然而我也沒有什麼好說的了,除非,真要我坦承的話(這更加不重要),我認為讀者在閱讀本書時,不會比我撰寫時對書中的每一件事更加深信不疑。
因此我想,與其陷在過去的回憶中,不如展望未來。我覺得自己闔上這本書最好的方式,莫過於期盼未來再次發表連載月刊的日子,以及細數曾落在《塊肉餘生記》書頁上的宜人陽光和細雨,這樣我就心滿意足了。
寫於倫敦,一八五〇年十月
* * * *
作者序(查爾斯.狄更斯版)
我在本書的原序中曾寫道:
書稿剛完成,我備感興奮,因此要脫離這種心情,沉著地完成這篇正式序言並非易事。我對本書的關心仍未退卻、依舊強烈;我的心分裂成愉悅與惋惜兩部分:愉悅是因構思已久的作品終於完成,但同時也為得和眾多老朋友道別而惋惜。不過再說下去,我的個人心事與私人情感恐怕會讓我最親愛的讀者厭煩。
除此之外,關於這本書我所能說的,在書中都努力說盡了。
要說在兩年的天馬行空之後把筆放下有多麼令人難過,或是作者眼見創造出的人物將永遠離開他時,是怎麼感覺像把一部分的自己留在那陰暗的世界裡,這些讀者大概都覺得無關緊要。然而我也沒有什麼好說的了,除非,真要我坦承的話(這更加不重要),我認為讀者在閱讀本書時,不會比我撰寫時對書中的每一件事更加深信不疑。
這些聲明至今仍千真萬確,因此我只能再告訴讀者一句知心話:在我所有的著作中,我最喜愛的就是這本。大家或許能夠輕易相信,我是個溺愛子女的父親,疼愛我想像出來的每個小孩,真的也沒有人比我更愛這個家庭了。但就像很多溺愛子女的父母一樣,我的內心深處也有個最偏愛的小孩,他就是大衛.考柏菲爾德。
寫於一八六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