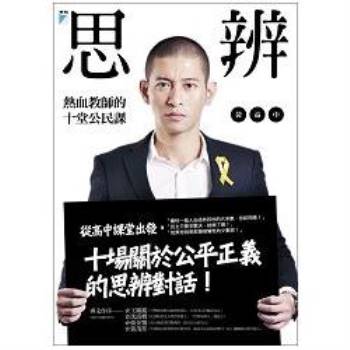第一堂
要成就多數人的利益,就要犧牲小我?◎公共利益
「所謂的正義與不正義,是體制處理這些事實的方式。」
──羅爾斯(John Rawls)
摘要
1課程
功利主義/自由至上主義/正義論
2新聞
樂生療養院事件/大埔事件
3搭配閱讀
《正義:一場思辨之旅》,邁可.桑德爾(Michael Sandel)著,樂為良譯,雅言
《錢買不到的東西:金錢與正義的攻防》,邁可.桑德爾(Michael Sandel)著,吳四明、姬健梅譯,先覺
課堂
今天是這個學期第X堂公民課,我們要上的是關於「公共利益」,什麼是「公共利益」?我想從一個遙遠的真實故事來談起。
十九世紀的大西洋上,發生了一起船難。英國的木犀草號(Mignonette)倖存的四個船員搭了一艘救生艇逃生,在大海上漂流了二十天以後,船上的補給品全都消耗殆盡,沒有飲用水,將是他們生存的最極限。最年輕的十七歲船員帕克不聽勸阻喝了海水,結果身體狀況衰弱,已經瀕臨死亡。
死神在虎視眈眈,而帕克已經陷入昏迷。這時,另外三個船員開始商議:再拖下去,四個人都會死,但犧牲一人,且在自然死亡之前,有新鮮的血液可供飲用,還有足以維生的食物,其他人就有機會得以生存。
一陣激辯之後,他們下了決定。
四天,終於等到了救援船,三人得以倖存。後來其中一位船員迫於良心不安,向警方自首,這件事當然在英國引發喧然大波,負面批評聲浪不斷。
什麼是「公共利益」?這個常常出現在報章雜誌與你我生活當中的名詞,我們最常聽到的解釋大概就是指「一般大眾的福利或福祉」。如果這個定義可以接受的話,那麼什麼叫做大眾福祉呢?英國哲學家邊沁(Jeremy Bentham)提出「功利主義(或稱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他主張欲追求社會的最大幸福,應考量行為的結果是否能帶來最多的快樂。從這個角度來看,所謂公共利益評斷的標準就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福祉」。
不過最大多數人的幸福要如何認定呢?功利主義認為公共利益是可以計算的,將一件事務對於社會上每個人可能產生的幸福與痛苦加以衡量計算,最後可以得到整體社會的幸福淨值總和。當個人對於事件結果滿意時,則此行為對個人來說具有正效益;相反的,若此事件使個人不滿意,則具有負效益。
由此看來,公共利益是一個可以加總的概念,政府為了實現大眾的公益,難免、或者不得已,只好犧牲極少數人的權益。
在這些前提之下,我開口問了學生第一個問題:
「請問各位同學,殺一人救三個人,符合公益標準嗎?」
「當然不行,這是殺人欸。」同學異口同聲地說。
我接著問:「就算他們不殺他,他自己也會死啊。而且帕克沒有家人,其他三位船員都有家庭,為了他們的家庭,這樣算符合效益原則吧?」
「殺人就是不對,沒有人有權力決定他人的死活!這不是公共利益。」說話的是班長小華,在班上很有正義感,也很有主見。
「所以……」我看著小華,「你們寧可四個人都一起死嗎?」
他們開始面有難色,我決定讓同學自由討論三分鐘,整間教室瞬間進入熱鬧的氣氛,你一言、我一語,彼此討論非常熱烈。
「如果你是法官,你會判決這是緊急避難情況,所以符合『阻卻違法事由』給予免刑嗎?」我結束討論,先問了這個問題。大多數同學都舉手表示反對。
「那如果其他船員拜託年輕船員帕克,比如說給帕克的朋友或親屬一大筆錢作為交換,而當事人自己同意呢?」
「這樣就可以,因為是他自己同意的。」小周邊說邊點頭,坐在他旁邊的男同學們,大家都贊同的點點頭。
「不行,吃人肉就是不對。」小華還是堅持。
「反正他本來就會死……這樣子至少還可以救活另外三個船員啊。」小周說。
在有當事人同意的前提下,我再進行一次表决,明顯發現,大多數同學都認為這樣就符合公共利益。
我拿出桑德爾(Michael Sandel)這本暢銷書《錢買不到的東西:金錢與正義的攻防》來說明自由至上主義(Libertarianism)的觀點。
「自由至上主義」主張市場放任機制,反對政府管制,出發點不是經濟效率,而是人的自由。自由是一種基本人權,人人對自有財物皆享有支配權,前提是必須尊重他人的相同權利。
「既然生命都可以賣了,所以假設一個有錢人需要器官移植,卻苦等不到,那麼他或他的家人直接去買活人的器官也是可以的囉?」
有部分同學點點頭。
「很好,既然有人點頭,那就表示奴隸制度是可以接受的囉?因為這是雙方合意交易的契約,屬於市場機制的範圍,只要不是強迫對方接受,你們也同意人類可以如同商品般在市場自由買賣囉?」看著他們又開始面有難色,我再次給了同學三分鐘討論。
「不行啦……奴隸制度是不對的,人類不是商品啊。」富有同情心的小美怯生生地說出自己的想法。
小周立刻反駁,「可是老師說雙方都是自願的啊,應該沒關係吧?」
「人家二十四孝的故事都還有賣身葬父呢。」也有同學這麼說。
「各位同學,大家都聽過人權吧,人權是普世價值,我們應該都認同。其實,按照德國著名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的說法,人權的根本在於『人性尊嚴』,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人本身就是目的、而非手段。如果把人當成商品來販售,就是剝奪了人性尊嚴,這不但侵犯了人權,也不是一個文明社會該有的價值。」
看著同學們睜得大大的眼睛,我等於用力地給同學們打了一巴掌,駁回他們剛才的回答,順帶給了一場機會教育。
其實不只是學生,有時候連大人們自己都忽略了很多價值:自由主義的市場機制帶給人們富裕與自由,但是它卻讓我們遠離了美好生活的想像。
過去三十年來,市場和市場價值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掌控了我們的生活。特別是冷戰結束後,市場經濟似乎證明了它是唯一可以創造富足與繁榮的正確道路。但是桑德爾教授特別點出,並非所有東西都能用價格機能進行合理的衡量,比如奴隸制度,比如買賣兒童,又比如你擔任陪審團成員,你不能雇用別人代替你去,或者有人急著收購選票,我們也不會准許公民販賣選票。
以上這些例子,用桑德爾的話來說,都指出一個重點:「生命中某些美好的事物,一旦被轉化為商品,就會淪於腐化或墮落。」人類社會中有感情、有道德、有對公平正義的期待,如果什麼都可以用金錢來衡量,身為人的基本價值是不是就因此被剝奪了呢?
樂生療養院事件
從一九三○年代就在新莊地區建立的樂生療養院,是台灣專門收容與隔離痲瘋病患的病院。由於該院院區被規劃為捷運機廠用地,在機廠開工前,文史團體就曾要求進行古蹟審查,呼籲捷運機廠另覓地點或變更設計。二○○四年開始,「青年樂生聯盟」、「樂生保留自救會」等團體開始以積極行動來促成院區保留。然而,台北市捷運局與台北縣政府以會增加工程預算及延宕通車為由,反對保存團體的訴求。
為了讓學生了解少數人的聲音,我播放一段新莊樂生療養院的故事《中天的夢想驛站/被世界遺棄 痲瘋病人徐周富子的故事》:
這是一位老阿嬤徐周富子的故事,她小時候家裡很窮,得了痲瘋病,人人害怕被傳染,把她送進樂生療養院。過年時,阿嬤也不能回家團圓,阿嬤只能「以院為家」。但是阿嬤很樂觀,即使有諸多歧視,她還是儘量活得樂觀,甚至還與痲瘋病友結婚,生下正常的女兒。阿嬤很自豪地說:「我們家的女兒不但很正常,而且比親戚家的女兒還漂亮呢!」
從十七歲入院,如今已過了半個世紀,這一次,她不向命運低頭,她生在這裡,死也要葬在這裡,這裡就是她的故鄉。
諷刺的是,政府當初是因為要隔離痲瘋病友,就把這些人關進療養院。當病友自立自強,做到「以院為家」地步時,我們的政府突然大筆一揮,說是因為要蓋新莊捷運機廠,必須要拆掉樂生療養院。當然政府也說要照顧病友的權益,所以在旁邊迴龍醫院蓋了新的病房要請病友搬過去。政府的說法是,不能因為五十位病患,卻耽誤了一百五十萬大台北通車族的權益,何況新病房都幫你蓋好了。
乍聽之下的確很有道理,五十對一百五十萬,從邊沁功利主義的效益原則來看,這絕對符合公共利益。
於是我問學生:「如果徐周富子阿嬤是你自己的阿嬤,你還會支持這件事嗎?」
「把你家拆了,然後跟你說我幫你蓋了一個全新的台大醫院,請你住進去,你願意嗎?」幾乎全班同學都頻頻搖頭。
「假設你家是舊公寓又沒電梯,我現在換一間全新的電梯醫院給你,冷氣很涼喔,如果你要看病還可以直接到樓下掛號!」這樣的福利,引起同學哄堂大笑。
小美默默地舉起手,我用眼神示意她說話。
「房子再怎麼破舊,那畢竟是我家啊。」教室陷入一陣寂靜,此刻,孩子們的腦袋陷入了更深一層的思考。
這時我引用美國當代自由主義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在《正義論》裡提出的「無知之幕」(the veil ignorance)觀點:假設大家來寫一份社會契約,或是制定一個決策,你會怎麼做呢?
所謂「無知之幕」,就是假設訂約者在原初立場中不知道某些特殊事實:不知道自己的社會地位、階級或社會身分;也不知道自己的自然資源、稟賦、能力和體力;也無人知道自己的價值觀。除此之外,立約者也不知道自己社會的政治和經濟情勢,也不知道自己社會的文明水準和文化成就;也不知道自己是屬於哪一個世代。
我們假設大家都是在一片無知之幕之後做選擇,一切都一無所知,回歸到平等的原始狀態來做選擇。
羅爾斯要我們想想,身為一個理性的自利者,你會怎麼選擇?
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夫妻離婚時要分財產,雙方財產包括存款、房子、車子等。請各位同學想想:怎麼樣分最公平?
小周不假思索地回答:「把房子車子都賣掉換得現金,再把所有現金加起來除以二啊。」從他臉上的表情來看,他並不覺得這是什麼困難的事。
「聽起來很有道理喔,不過我剛剛漏講一些,他們的財產還有沙發、電視、冰箱、抱枕等等一大堆。而且房子車子也不見得馬上賣得掉。有沒有更好的方法呢?」我還沒說完,就看見同學面面相覷。
「其實一個最簡單的方法,就像切蛋糕一樣,只要指定夫妻其中一方將所有財產分成兩部分,但是卻由另一方優先選擇一部分,這樣分出來的財產絕對是最公平的!」
「咦!真的耶!」「剛剛怎麼沒想到這個方法?」同學們像發現新大陸一樣興奮。
「這樣分的確最公平,」小周點點頭,「沒有人會害到自己。」
從羅爾斯的角度來看,他認為透過「無知之幕」,大家不會選擇功利主義,道理很簡單:「如果我是那個要被犧牲掉的少數呢?」
由於民主政治過分強調多數決的原則,社會上的弱勢團體,往往由於人數較少,也未掌握政治社會的資源,使得這些真正需要社會關懷的人,反而得不到政府的照顧。因此,羅爾斯在此提出一個公共利益的衡量標準,即「社會正義」。他的正義兩原則,第一是「平等原則」,每個人都有權利與他人享受同等的自由;第二是「差異原則」,允許財富分配、社會地位和職務的不平等。其中第一原則優先於第二原則。
由於社經背景與天賦條件不同,不可能要求每個人都相同地位、相同收入,假設允許某些不平等,卻可以為社會最底層帶來好處,這時羅爾斯同意可以有「差異原則」。
舉例來說,醫生是個很重要的行業,這關係到你我生命健康安全,如果沒有經過相當嚴格的專業訓練,是有可能危害到人體性命的。為了吸引社會菁英投入這個行業,我們給醫生比較高的薪水。但是這個給予高薪的前提是醫生能帶給偏遠鄉村或社會底層更多的醫療照顧。如果這位醫生只是服務社會頂端階級,則不能享有高薪。
我們常常聽到人要有「同理心」,可是同理心不能只是嘴巴說說,甚至表達同情眼光。那都是假的同理心。每個人如果都能在「無知之幕」之後思考,如果你我都有可能是那個被犧牲掉的少數時,你還會支持所謂的效益原則嗎?
在給同學們討論的時候,其實可以發現,同學們對所謂的功利主義的「公共利益」觀點開始產生了質疑。這代表同理心的觀點開始發酵了。
大埔事件
大埔事件,是一起發生在苗栗縣竹南鎮大埔里居民反對政府區段徵收與強制拆遷房屋的抗爭事件。苗栗縣政府為執行「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暨周邊地區特定區」都市計畫,進行區段徵收。然而並不是每位居民都同意被徵收,居民組成「大埔自救會」,加上「台灣農村陣線」等公民團體的協助,開始後續一連串抗爭與全國性的聲援。過程中有兩位被徵收戶因此自殺,包括二○一○年七十三歲的朱馮敏老太太與二○一三年張藥房老闆張森文。
二○一四年一月三日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更一審宣判,判決張藥房、朱樹、黃福記及柯成福四拆遷戶勝訴,其他駁回。二○一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內政部決定不上訴。
我播放一段苗栗大埔拆遷案的新聞《大埔案逆轉 徵收判違法需還地》, 這是二○一四年一月三日的判決,在台中高等行政法院的判決書裡,認為政府強拆大埔犯了兩個錯誤:其一是未遵行正當法律程序,其二是並沒有公益性、必要性,且違反比例原則。從《大埔農地徵收案說明圖》上來看,苗栗科學園區廠房閒置率高達百分之四十二,而大埔這四戶明顯未妨礙交通,結果因為苗栗縣政府「官方認定」的公共利益,死了兩條性命。
「房子拆了可以再建,」同學們從影片中回神,教室很安靜,大家都被渲染了一些哀傷的情緒,「但,人死了,誰賠得起?」
回到樂生療養院的案例,當初政府說不拆樂生,捷運無法通車,會耽誤到大新莊地區人民的權益。事實上捷運新莊線已於二○一二年一月五日通車,甚至一路通到迴龍站。想來也好笑,當初非拆樂生不可的捷運機廠到現在也沒有蓋啊!
最後我以樂生青年聯盟的《樂生戰鬥手冊》做總結:「抗爭有用嗎?常常遇到朋友這樣問。但是讓我們想一想,悲劇的發生既然是日夜累積的過程,要改變悲劇的運動怎麼可能在一夕之間就大功告成?北二高走山前夕,邊坡上方的土地必定也已經鬆垮、龜裂,如果當時就有人上去勘查、警告,甚至為之抗爭,幾位駕駛人的性命是不是就可以保全了呢?
所以,關於抗爭到底有沒有用,也許今天明天看不出有什麼用處,但總有一天我們會明白的,這些美好的風景,正是千千萬萬場看來無用的抗爭所換來的。
很多事我們都忽略了,就算是狀況如此,也不代表應該如此。用羅爾斯的話語來說:「所謂的正義與不正義,是體制處理這些事實的方式。」
這時我明顯感受到學生表情的嚴肅,在這些十七歲孩子的臉上,那些嘻笑的表情慢慢收斂了起來,原本理所當然認為的觀點,在此刻好像不再是那麼絕對。看著學生的眼神,我心中想著,這堂「公共利益」的一課,似乎有那麼一點成功呀!
課後作業
@這一課,值得你認識的公民團體NGO:
青年樂生聯盟/台灣農村陣線/台灣人權促進會
一、毀塘滅農航空城
(1)行政院目前為止僅核定了機場園區綱要計畫中的第三跑道(六百一十五公頃)和自貿港擴建區(一百三十公頃),僅七百四十五公頃土地核定通過,究竟為何最後會變成總計畫範圍四千七百九十一公頃,需要徵收三千七百零七公頃的土地,四萬六千名居民面臨迫遷?
(2)目前航空城規劃捨現成軍用跑道不用,反將該閒置軍用基地規劃作商場豪宅使用,以區段徵收方式辦理,大規模徵收民地。
(3)航空城計畫在第三跑道個案環評通過前,應立即停止徵收程序。政府應停止這個弊案重重、浮濫徵收的航空城計畫,就計畫全區召開行政聽證,開始真正的民眾參與程序,一同組成聽證籌備小組,重新檢視整個計畫的公益性與必要性。
二、公共電視《獨立特派員「無意上青天」》
台灣要國際化,因此被期許作為國際化跳板的「桃園航空城」看來勢在必行,是史上最大區段徵收案,當然有人不願意,認為審議過程不透明,發生不少抗議甚至自殺事件。為什麼一個願景美好的計畫卻仍然有人不贊同?為什麼原本不在計畫範圍內的住戶,結果還是要被遷走?獨立特派員帶您實地聽聽居民的心聲,看一看土地的真相。
一、請各組同學蒐集並分析桃園航空城計畫之正反方意見,用課堂上所學的理論為基礎,在下堂課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二、除了航空城的爭議,想想看,台灣還有沒有哪些地方正面臨這種「公共利益」的拆遷議題,也請各組同學至少選擇一個案例,進行比較分析,並於課堂上報告。
後記
這些年來,「公共利益」這詞其實已經被濫用過度了,不管是中央或地方政客,在「開發主義」的思維底下,伴隨著炒地皮的龐大利益,在公益的大旗下,浮濫徵收、強拆迫遷,成了這些政商金權結構獲得金錢與選票最好的方式。
從北到南,我們發現台灣真的病了:淡水有淡海二期新市鎮迫遷、桃園有航空城迫遷、新竹有璞玉計畫、苗栗是大埔竹科基地、台南有鐵路東移案件。由於被犧牲者一定是少數被徵收戶,相較於多數不受影響的市民,以及深信科學園區、生技園區可以帶動地方發展的神話,政府做出來的民調往往是贊成者佔多數。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政府聯合著房產開發商不斷壓迫那些弱勢民眾,加以輿論的推波助瀾,少數願意挺身捍衛弱勢權益的社運團體,就被打為妨礙城市開發、只會上街頭抗議的「暴民」。
從學生的反應,我相信人性是可以啟發的。關鍵在於有沒有方式引導他們思考:唯有親身體驗,才知箇中辛酸。當然我不可能還原事件現場,但是我可以試著用當事人現身說法的新聞畫面來使同學感同身受。影像有它的感染力,適度運用畫面來說故事,透過同學們的討論思辨,再搭配課堂理論說明,也許是一個比較容易處理相關議題的方法。
要成就多數人的利益,就要犧牲小我?◎公共利益
「所謂的正義與不正義,是體制處理這些事實的方式。」
──羅爾斯(John Rawls)
摘要
1課程
功利主義/自由至上主義/正義論
2新聞
樂生療養院事件/大埔事件
3搭配閱讀
《正義:一場思辨之旅》,邁可.桑德爾(Michael Sandel)著,樂為良譯,雅言
《錢買不到的東西:金錢與正義的攻防》,邁可.桑德爾(Michael Sandel)著,吳四明、姬健梅譯,先覺
課堂
今天是這個學期第X堂公民課,我們要上的是關於「公共利益」,什麼是「公共利益」?我想從一個遙遠的真實故事來談起。
十九世紀的大西洋上,發生了一起船難。英國的木犀草號(Mignonette)倖存的四個船員搭了一艘救生艇逃生,在大海上漂流了二十天以後,船上的補給品全都消耗殆盡,沒有飲用水,將是他們生存的最極限。最年輕的十七歲船員帕克不聽勸阻喝了海水,結果身體狀況衰弱,已經瀕臨死亡。
死神在虎視眈眈,而帕克已經陷入昏迷。這時,另外三個船員開始商議:再拖下去,四個人都會死,但犧牲一人,且在自然死亡之前,有新鮮的血液可供飲用,還有足以維生的食物,其他人就有機會得以生存。
一陣激辯之後,他們下了決定。
四天,終於等到了救援船,三人得以倖存。後來其中一位船員迫於良心不安,向警方自首,這件事當然在英國引發喧然大波,負面批評聲浪不斷。
什麼是「公共利益」?這個常常出現在報章雜誌與你我生活當中的名詞,我們最常聽到的解釋大概就是指「一般大眾的福利或福祉」。如果這個定義可以接受的話,那麼什麼叫做大眾福祉呢?英國哲學家邊沁(Jeremy Bentham)提出「功利主義(或稱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他主張欲追求社會的最大幸福,應考量行為的結果是否能帶來最多的快樂。從這個角度來看,所謂公共利益評斷的標準就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福祉」。
不過最大多數人的幸福要如何認定呢?功利主義認為公共利益是可以計算的,將一件事務對於社會上每個人可能產生的幸福與痛苦加以衡量計算,最後可以得到整體社會的幸福淨值總和。當個人對於事件結果滿意時,則此行為對個人來說具有正效益;相反的,若此事件使個人不滿意,則具有負效益。
由此看來,公共利益是一個可以加總的概念,政府為了實現大眾的公益,難免、或者不得已,只好犧牲極少數人的權益。
在這些前提之下,我開口問了學生第一個問題:
「請問各位同學,殺一人救三個人,符合公益標準嗎?」
「當然不行,這是殺人欸。」同學異口同聲地說。
我接著問:「就算他們不殺他,他自己也會死啊。而且帕克沒有家人,其他三位船員都有家庭,為了他們的家庭,這樣算符合效益原則吧?」
「殺人就是不對,沒有人有權力決定他人的死活!這不是公共利益。」說話的是班長小華,在班上很有正義感,也很有主見。
「所以……」我看著小華,「你們寧可四個人都一起死嗎?」
他們開始面有難色,我決定讓同學自由討論三分鐘,整間教室瞬間進入熱鬧的氣氛,你一言、我一語,彼此討論非常熱烈。
「如果你是法官,你會判決這是緊急避難情況,所以符合『阻卻違法事由』給予免刑嗎?」我結束討論,先問了這個問題。大多數同學都舉手表示反對。
「那如果其他船員拜託年輕船員帕克,比如說給帕克的朋友或親屬一大筆錢作為交換,而當事人自己同意呢?」
「這樣就可以,因為是他自己同意的。」小周邊說邊點頭,坐在他旁邊的男同學們,大家都贊同的點點頭。
「不行,吃人肉就是不對。」小華還是堅持。
「反正他本來就會死……這樣子至少還可以救活另外三個船員啊。」小周說。
在有當事人同意的前提下,我再進行一次表决,明顯發現,大多數同學都認為這樣就符合公共利益。
我拿出桑德爾(Michael Sandel)這本暢銷書《錢買不到的東西:金錢與正義的攻防》來說明自由至上主義(Libertarianism)的觀點。
「自由至上主義」主張市場放任機制,反對政府管制,出發點不是經濟效率,而是人的自由。自由是一種基本人權,人人對自有財物皆享有支配權,前提是必須尊重他人的相同權利。
「既然生命都可以賣了,所以假設一個有錢人需要器官移植,卻苦等不到,那麼他或他的家人直接去買活人的器官也是可以的囉?」
有部分同學點點頭。
「很好,既然有人點頭,那就表示奴隸制度是可以接受的囉?因為這是雙方合意交易的契約,屬於市場機制的範圍,只要不是強迫對方接受,你們也同意人類可以如同商品般在市場自由買賣囉?」看著他們又開始面有難色,我再次給了同學三分鐘討論。
「不行啦……奴隸制度是不對的,人類不是商品啊。」富有同情心的小美怯生生地說出自己的想法。
小周立刻反駁,「可是老師說雙方都是自願的啊,應該沒關係吧?」
「人家二十四孝的故事都還有賣身葬父呢。」也有同學這麼說。
「各位同學,大家都聽過人權吧,人權是普世價值,我們應該都認同。其實,按照德國著名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的說法,人權的根本在於『人性尊嚴』,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人本身就是目的、而非手段。如果把人當成商品來販售,就是剝奪了人性尊嚴,這不但侵犯了人權,也不是一個文明社會該有的價值。」
看著同學們睜得大大的眼睛,我等於用力地給同學們打了一巴掌,駁回他們剛才的回答,順帶給了一場機會教育。
其實不只是學生,有時候連大人們自己都忽略了很多價值:自由主義的市場機制帶給人們富裕與自由,但是它卻讓我們遠離了美好生活的想像。
過去三十年來,市場和市場價值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掌控了我們的生活。特別是冷戰結束後,市場經濟似乎證明了它是唯一可以創造富足與繁榮的正確道路。但是桑德爾教授特別點出,並非所有東西都能用價格機能進行合理的衡量,比如奴隸制度,比如買賣兒童,又比如你擔任陪審團成員,你不能雇用別人代替你去,或者有人急著收購選票,我們也不會准許公民販賣選票。
以上這些例子,用桑德爾的話來說,都指出一個重點:「生命中某些美好的事物,一旦被轉化為商品,就會淪於腐化或墮落。」人類社會中有感情、有道德、有對公平正義的期待,如果什麼都可以用金錢來衡量,身為人的基本價值是不是就因此被剝奪了呢?
樂生療養院事件
從一九三○年代就在新莊地區建立的樂生療養院,是台灣專門收容與隔離痲瘋病患的病院。由於該院院區被規劃為捷運機廠用地,在機廠開工前,文史團體就曾要求進行古蹟審查,呼籲捷運機廠另覓地點或變更設計。二○○四年開始,「青年樂生聯盟」、「樂生保留自救會」等團體開始以積極行動來促成院區保留。然而,台北市捷運局與台北縣政府以會增加工程預算及延宕通車為由,反對保存團體的訴求。
為了讓學生了解少數人的聲音,我播放一段新莊樂生療養院的故事《中天的夢想驛站/被世界遺棄 痲瘋病人徐周富子的故事》:
這是一位老阿嬤徐周富子的故事,她小時候家裡很窮,得了痲瘋病,人人害怕被傳染,把她送進樂生療養院。過年時,阿嬤也不能回家團圓,阿嬤只能「以院為家」。但是阿嬤很樂觀,即使有諸多歧視,她還是儘量活得樂觀,甚至還與痲瘋病友結婚,生下正常的女兒。阿嬤很自豪地說:「我們家的女兒不但很正常,而且比親戚家的女兒還漂亮呢!」
從十七歲入院,如今已過了半個世紀,這一次,她不向命運低頭,她生在這裡,死也要葬在這裡,這裡就是她的故鄉。
諷刺的是,政府當初是因為要隔離痲瘋病友,就把這些人關進療養院。當病友自立自強,做到「以院為家」地步時,我們的政府突然大筆一揮,說是因為要蓋新莊捷運機廠,必須要拆掉樂生療養院。當然政府也說要照顧病友的權益,所以在旁邊迴龍醫院蓋了新的病房要請病友搬過去。政府的說法是,不能因為五十位病患,卻耽誤了一百五十萬大台北通車族的權益,何況新病房都幫你蓋好了。
乍聽之下的確很有道理,五十對一百五十萬,從邊沁功利主義的效益原則來看,這絕對符合公共利益。
於是我問學生:「如果徐周富子阿嬤是你自己的阿嬤,你還會支持這件事嗎?」
「把你家拆了,然後跟你說我幫你蓋了一個全新的台大醫院,請你住進去,你願意嗎?」幾乎全班同學都頻頻搖頭。
「假設你家是舊公寓又沒電梯,我現在換一間全新的電梯醫院給你,冷氣很涼喔,如果你要看病還可以直接到樓下掛號!」這樣的福利,引起同學哄堂大笑。
小美默默地舉起手,我用眼神示意她說話。
「房子再怎麼破舊,那畢竟是我家啊。」教室陷入一陣寂靜,此刻,孩子們的腦袋陷入了更深一層的思考。
這時我引用美國當代自由主義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在《正義論》裡提出的「無知之幕」(the veil ignorance)觀點:假設大家來寫一份社會契約,或是制定一個決策,你會怎麼做呢?
所謂「無知之幕」,就是假設訂約者在原初立場中不知道某些特殊事實:不知道自己的社會地位、階級或社會身分;也不知道自己的自然資源、稟賦、能力和體力;也無人知道自己的價值觀。除此之外,立約者也不知道自己社會的政治和經濟情勢,也不知道自己社會的文明水準和文化成就;也不知道自己是屬於哪一個世代。
我們假設大家都是在一片無知之幕之後做選擇,一切都一無所知,回歸到平等的原始狀態來做選擇。
羅爾斯要我們想想,身為一個理性的自利者,你會怎麼選擇?
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夫妻離婚時要分財產,雙方財產包括存款、房子、車子等。請各位同學想想:怎麼樣分最公平?
小周不假思索地回答:「把房子車子都賣掉換得現金,再把所有現金加起來除以二啊。」從他臉上的表情來看,他並不覺得這是什麼困難的事。
「聽起來很有道理喔,不過我剛剛漏講一些,他們的財產還有沙發、電視、冰箱、抱枕等等一大堆。而且房子車子也不見得馬上賣得掉。有沒有更好的方法呢?」我還沒說完,就看見同學面面相覷。
「其實一個最簡單的方法,就像切蛋糕一樣,只要指定夫妻其中一方將所有財產分成兩部分,但是卻由另一方優先選擇一部分,這樣分出來的財產絕對是最公平的!」
「咦!真的耶!」「剛剛怎麼沒想到這個方法?」同學們像發現新大陸一樣興奮。
「這樣分的確最公平,」小周點點頭,「沒有人會害到自己。」
從羅爾斯的角度來看,他認為透過「無知之幕」,大家不會選擇功利主義,道理很簡單:「如果我是那個要被犧牲掉的少數呢?」
由於民主政治過分強調多數決的原則,社會上的弱勢團體,往往由於人數較少,也未掌握政治社會的資源,使得這些真正需要社會關懷的人,反而得不到政府的照顧。因此,羅爾斯在此提出一個公共利益的衡量標準,即「社會正義」。他的正義兩原則,第一是「平等原則」,每個人都有權利與他人享受同等的自由;第二是「差異原則」,允許財富分配、社會地位和職務的不平等。其中第一原則優先於第二原則。
由於社經背景與天賦條件不同,不可能要求每個人都相同地位、相同收入,假設允許某些不平等,卻可以為社會最底層帶來好處,這時羅爾斯同意可以有「差異原則」。
舉例來說,醫生是個很重要的行業,這關係到你我生命健康安全,如果沒有經過相當嚴格的專業訓練,是有可能危害到人體性命的。為了吸引社會菁英投入這個行業,我們給醫生比較高的薪水。但是這個給予高薪的前提是醫生能帶給偏遠鄉村或社會底層更多的醫療照顧。如果這位醫生只是服務社會頂端階級,則不能享有高薪。
我們常常聽到人要有「同理心」,可是同理心不能只是嘴巴說說,甚至表達同情眼光。那都是假的同理心。每個人如果都能在「無知之幕」之後思考,如果你我都有可能是那個被犧牲掉的少數時,你還會支持所謂的效益原則嗎?
在給同學們討論的時候,其實可以發現,同學們對所謂的功利主義的「公共利益」觀點開始產生了質疑。這代表同理心的觀點開始發酵了。
大埔事件
大埔事件,是一起發生在苗栗縣竹南鎮大埔里居民反對政府區段徵收與強制拆遷房屋的抗爭事件。苗栗縣政府為執行「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暨周邊地區特定區」都市計畫,進行區段徵收。然而並不是每位居民都同意被徵收,居民組成「大埔自救會」,加上「台灣農村陣線」等公民團體的協助,開始後續一連串抗爭與全國性的聲援。過程中有兩位被徵收戶因此自殺,包括二○一○年七十三歲的朱馮敏老太太與二○一三年張藥房老闆張森文。
二○一四年一月三日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更一審宣判,判決張藥房、朱樹、黃福記及柯成福四拆遷戶勝訴,其他駁回。二○一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內政部決定不上訴。
我播放一段苗栗大埔拆遷案的新聞《大埔案逆轉 徵收判違法需還地》, 這是二○一四年一月三日的判決,在台中高等行政法院的判決書裡,認為政府強拆大埔犯了兩個錯誤:其一是未遵行正當法律程序,其二是並沒有公益性、必要性,且違反比例原則。從《大埔農地徵收案說明圖》上來看,苗栗科學園區廠房閒置率高達百分之四十二,而大埔這四戶明顯未妨礙交通,結果因為苗栗縣政府「官方認定」的公共利益,死了兩條性命。
「房子拆了可以再建,」同學們從影片中回神,教室很安靜,大家都被渲染了一些哀傷的情緒,「但,人死了,誰賠得起?」
回到樂生療養院的案例,當初政府說不拆樂生,捷運無法通車,會耽誤到大新莊地區人民的權益。事實上捷運新莊線已於二○一二年一月五日通車,甚至一路通到迴龍站。想來也好笑,當初非拆樂生不可的捷運機廠到現在也沒有蓋啊!
最後我以樂生青年聯盟的《樂生戰鬥手冊》做總結:「抗爭有用嗎?常常遇到朋友這樣問。但是讓我們想一想,悲劇的發生既然是日夜累積的過程,要改變悲劇的運動怎麼可能在一夕之間就大功告成?北二高走山前夕,邊坡上方的土地必定也已經鬆垮、龜裂,如果當時就有人上去勘查、警告,甚至為之抗爭,幾位駕駛人的性命是不是就可以保全了呢?
所以,關於抗爭到底有沒有用,也許今天明天看不出有什麼用處,但總有一天我們會明白的,這些美好的風景,正是千千萬萬場看來無用的抗爭所換來的。
很多事我們都忽略了,就算是狀況如此,也不代表應該如此。用羅爾斯的話語來說:「所謂的正義與不正義,是體制處理這些事實的方式。」
這時我明顯感受到學生表情的嚴肅,在這些十七歲孩子的臉上,那些嘻笑的表情慢慢收斂了起來,原本理所當然認為的觀點,在此刻好像不再是那麼絕對。看著學生的眼神,我心中想著,這堂「公共利益」的一課,似乎有那麼一點成功呀!
課後作業
@這一課,值得你認識的公民團體NGO:
青年樂生聯盟/台灣農村陣線/台灣人權促進會
一、毀塘滅農航空城
(1)行政院目前為止僅核定了機場園區綱要計畫中的第三跑道(六百一十五公頃)和自貿港擴建區(一百三十公頃),僅七百四十五公頃土地核定通過,究竟為何最後會變成總計畫範圍四千七百九十一公頃,需要徵收三千七百零七公頃的土地,四萬六千名居民面臨迫遷?
(2)目前航空城規劃捨現成軍用跑道不用,反將該閒置軍用基地規劃作商場豪宅使用,以區段徵收方式辦理,大規模徵收民地。
(3)航空城計畫在第三跑道個案環評通過前,應立即停止徵收程序。政府應停止這個弊案重重、浮濫徵收的航空城計畫,就計畫全區召開行政聽證,開始真正的民眾參與程序,一同組成聽證籌備小組,重新檢視整個計畫的公益性與必要性。
二、公共電視《獨立特派員「無意上青天」》
台灣要國際化,因此被期許作為國際化跳板的「桃園航空城」看來勢在必行,是史上最大區段徵收案,當然有人不願意,認為審議過程不透明,發生不少抗議甚至自殺事件。為什麼一個願景美好的計畫卻仍然有人不贊同?為什麼原本不在計畫範圍內的住戶,結果還是要被遷走?獨立特派員帶您實地聽聽居民的心聲,看一看土地的真相。
一、請各組同學蒐集並分析桃園航空城計畫之正反方意見,用課堂上所學的理論為基礎,在下堂課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二、除了航空城的爭議,想想看,台灣還有沒有哪些地方正面臨這種「公共利益」的拆遷議題,也請各組同學至少選擇一個案例,進行比較分析,並於課堂上報告。
後記
這些年來,「公共利益」這詞其實已經被濫用過度了,不管是中央或地方政客,在「開發主義」的思維底下,伴隨著炒地皮的龐大利益,在公益的大旗下,浮濫徵收、強拆迫遷,成了這些政商金權結構獲得金錢與選票最好的方式。
從北到南,我們發現台灣真的病了:淡水有淡海二期新市鎮迫遷、桃園有航空城迫遷、新竹有璞玉計畫、苗栗是大埔竹科基地、台南有鐵路東移案件。由於被犧牲者一定是少數被徵收戶,相較於多數不受影響的市民,以及深信科學園區、生技園區可以帶動地方發展的神話,政府做出來的民調往往是贊成者佔多數。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政府聯合著房產開發商不斷壓迫那些弱勢民眾,加以輿論的推波助瀾,少數願意挺身捍衛弱勢權益的社運團體,就被打為妨礙城市開發、只會上街頭抗議的「暴民」。
從學生的反應,我相信人性是可以啟發的。關鍵在於有沒有方式引導他們思考:唯有親身體驗,才知箇中辛酸。當然我不可能還原事件現場,但是我可以試著用當事人現身說法的新聞畫面來使同學感同身受。影像有它的感染力,適度運用畫面來說故事,透過同學們的討論思辨,再搭配課堂理論說明,也許是一個比較容易處理相關議題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