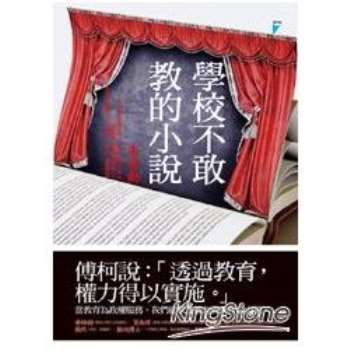課本不教的小說(1)
翹課才能學會的事:郭箏〈好個翹課天〉
世界上充滿了各種小框框,小得悶死人。有一次我沒上朝會,躲在廁所裡燻草,我忽然從窗口望出去,那副景象可真把我嚇呆了。我是說,你忽然看見一千多個一模一樣的齪蛋排列得整整齊齊的擠在一個小到不能再小的操場上,而你知道你也是其中之一,那種感覺真可怕,真叫人想吐。我想看看小虎他們,但找來找去就是找不著。我想如果我自己也排在那隊伍裡,我恐怕也會找不著我自己。
──郭箏〈好個翹課天〉(一九八四)
我是從高中開始學會翹課的。當然,遠不能和郭箏筆下的「海山七俠」相較。相對於他們的硬漢風格,我們這類是嬌慣的少年──人家是砸天砸地,拳頭與汗水,我們則是維特的憂鬱,撕扯著考卷和(自己寫的)情書。但我猜,我們都不是從小就立志要翹課的孩子。雖然〈好個翹課天〉發表的一九八四年,距離我第一次偽造假單,窩到附近咖啡店趕校刊要用的稿子已有整整二十年──如果考慮生於一九五五年的作者郭箏,這個高中故事發生的年代甚至能再推前十年──;雖然我們早就不再用「齪蛋」和「馬子」這些詞了,我們的年代網咖比彈子房多十幾倍。但毫無疑問,我覺得我完全能讀懂〈好個翹課天〉。我覺得就算再過五十年、一百年,一個高中生也能讀懂它。
只要這個島,還沒打算改變它那總是在碾碎少年理想、情感的傳統慣性。
我們學會翹課的歷程,也許非常的相像。在七歲或更早的年紀,我們第一次被帶到一個叫做教室的地方,和一群叫做同學的人坐在一起,台上有一個叫做老師的人。這裡面你只認識在窗外的爸爸或媽媽,而就在某一次轉頭,你發現他或她不見了。關於學校,我們學會的第一件事情是遺棄,第二件事情是隔離;你不能做你本能想做的事,因為你現在身在一個特區,在這裡你的天職就是被管束。沒有人告訴我們為什麼,久了我們也就忘了問。有的是因為我們也的確很適應被管束,有的是因為光是讓自己平安度過八個小時,不要受罰,就已經占去我們全部的心神。
我們,以及〈好個翹課天〉裡面的小郭、小虎等人,就是這樣過了十年的人。如果在法律上,十年的徒刑是重罪,那在當代台灣學校教育體系長大的每一個人都是命定的罪犯。於是,總會有人想著要逃獄的──我曾經就讀過一所四面由鐵窗包圍、進出由教官帶隊如押解的學校,因此「逃獄」二字對我來說,並不只是抽象的隱喻。十六、七歲正是最適合逃的年紀,這篇小說的角色都是高中生,並非偶然。我們都是在這個年紀擁有了前所未有的體力和知識,有了長期應付學校體制的經驗,深知它的虛榮與弱點。郭箏描寫了一群世俗眼光中的「壞學生」,師長們認為他們虛度青春、鬧事狎玩,沒有辦法跟上功課,一點也看不到未來。但透過這七個人翹課一天的故事,我們發現,發表這篇小說時正好滿三十歲的作者──一個標準的「大人」的年紀──,似乎全然不同意其他大人的看法。他給予敘事者小郭一個超然的位置,他看著一切,既明白所謂道德規則是怎麼回事(只是他選擇不遵守),又察覺到那些規則底下流動的欲望、敗德與虛偽(好友小虎為什麼選不上校隊?美麗的音樂老師和清純的夢中情人馬綿綿為什麼會……?)。在小說裡,他滿口髒話,卻是唯一清醒(也就因而受苦)的智者。
郭箏要說的故事,遠比「好學生vs.壞學生」或者「道德vs.不道德」複雜。它不是一個單純反抗的故事。他的思考是:我知道以「學校」為代表的成人社會是一團糟的,所以我想要逃獄。但問題是,逃出來之後呢?我們在最前面引用的一個段落,非常精采地演繹了這種思考。「我」首先必須是個翹課者,是個不守規則的人,才有機會暫時離開框框,目擊這個框框的可怖、虛無。人在框框裡面的時候,是不會有任何感覺的,因為「我想如果我自己也排在那隊伍裡,我恐怕也會找不著我自己。」某種形式的「翹課」是抵抗成為「大人」的必經之路。但這句話的另外一層深意是,「我」有些悲哀地體認到,自己和排列在隊伍裡面的人並無本質上的不同。如果「我」進入了隊伍,也不可能鶴立雞群,而是會被整個體制給碾碎、融化、取消掉。整篇〈好個翹課天〉因此就是灰心的調子,它不是一篇提倡反抗的故事,而是一篇反抗過的人的唏噓。
因此,不管我們是否翹過課、是否為了一樣的理由翹課,讀到他們總像是讀到自己。
沒有一人會甘心永遠待在教室裡。但也沒有一人敢說,我已經永遠不必回來上課了。
我想起高二那年,一個總是縱容我翹課、不把我當掉的老師。他從來不責罵我,但我從來也不覺得他是親近我、了解我的。因為他說過:「等到高三,你就會自己回來了。」於是每一次,當又有師長告訴我文學沒有用、寫小說會讓我餓死的時候,我就會想起這句話,還有〈好個翹課天〉。
讀更多的小說,寫更多的小說。——這是我翹課的方式,而且就像小郭在結尾那沒有目標的奔跑一樣,我知道翹課是沒完沒了的,只有繼續逃亡,才能免於被框框俘虜。
就從這裡開始吧。至今,我還沒有讓那位高二老師的預言成真,而這些課本不教的小說,都是這段漫長的跑路過程中攜行的食糧。我現在就把它們放在這裡,如果你和當時的我是同一類人,或許你也會需要它們的。放心取用吧,不像世俗的任何財富或權力,它們是永不枯竭的,可以在永無止盡的翹課之路給你力量和渴盼,助你指認出每一個想把你擄回教室的、埋伏在暗處的那些精神教條。
郭箏(一九五五-),另一個筆名應天魚,小說家、編劇。一九八四年,在中國時報副刊發表〈好個翹課天〉,造成一股風潮,四年後發表〈彈子王〉。曾為電視劇《施公》編寫劇本,也曾為導演吳宇森的《赤壁》編劇。
課本不教的小說(20)
含著碎石的心──邱妙津《蒙馬特遺書》
我日日夜夜止不住地悲傷,不是為了世間的錯誤,不是為了身體的殘敗病痛,而是為了心靈的脆弱性及它所承受的傷害,我悲傷它承受了那麼多的傷害,我疼惜自己能給予別人,給予世界那麼多,卻沒辦法使自己活得好過一點。世界總是沒有錯的,錯的是心靈的脆弱性,我們不能免除於世界的傷害,於是我們就要長期生著靈魂的病。
──邱妙津《蒙馬特遺書》(一九九六/二○○六)
想像一顆心臟,含著一小塊銳利的碎石。每一次心臟跳動,每一次肌體收縮,都在別人看不見之處劃出傷口,撕裂復撕裂,咬牙復咬牙。想像這顆心臟比常人更加強悍,它每一次搏動都是加倍劇烈、認真的,也因而帶來比常人更甚的痛楚。
對我而言,這就是邱妙津的《蒙馬特遺書》所寫出來的感覺,讀完之後,那顆碎石就轉而鑲在我們的心底了。
就跟每一個十六、七歲初讀邱妙津的人一樣,在接下來的好幾年內,我們或許會讀到很多寫得更優美、更精巧、更大器……或簡而言之,寫得更好的作品。但幾乎沒有任何一本書能取代《蒙馬特遺書》的地位,就算是邱妙津自己成就更耀眼的長篇小說《鱷魚手記》都沒有辦法。在每一個情感傷痛的時刻,我們抄寫它的句子:「我已獻身給一個人,但世界並不接受這件事,這件事之於世界根本微不足道,甚至是被嘲笑的……」許諾的時候,我們也抄:「找到一個人,然後對他絕對。」最寂寞的一刻,心底冒起的句子是:「之於你,我真的還不夠美嗎?你的生命沒有我來跟你說話真的不會有點寂寞嗎?」很奇怪的是,從進入學校到我們第一次翻開它之前,我們在教室裡讀過的書也不在少數了,卻沒有一本書能像它一樣在生命低點的時候貼隨著我們。
一九九六年初版的《蒙馬特遺書》由一系列書信組成,內容是女同志Zoë在女友絮離開她之後寫的信,少部分是寫給另一密友詠的。在這些書信裡,Zoë以質樸到接近粗礪的筆法,檢證兩人的情感關係、思考自己的生命與藝術本質。嚴格說起來,這並不像一本小說,某些段落的文字甚至趨近於哲學思辨。然而或許正是這種「不像小說」的特質,使得整本書充滿了直接面對傷痛的撞擊力道。直白的作品往往流於膚淺,深刻的作品難以避免晦澀,但直白且深刻地去面對自己的心,就鑲進其他作品沒辦法抵達的位置。到了二○○六年的新版,補上了初版僅有標題而無內容的第十五書和第十九書,這兩章卻都是以此前未見的,從絮的觀點寫給Zoë的。雖然在腔調上明顯有所區隔,較為甜膩且幼兒化,但Zoë一向就將絮描述為一個不夠成熟到足以擔當愛情的人。所以,從那幾章裡面絮的自我認知與Zoë對絮的描述幾無落差來看,我仍傾向把它們當作是邱妙津自己從不同角色的觀點模擬而成,而不是真實書信的收錄。既有模擬,那這些章節確實有小說手法無疑了;既有若干章節呈現出小說手法,整本小說也就不應當作完全紀實的書寫了。
這種「真實與虛構」的討論看似多餘,但對於被它深深撼動的讀者如我而言,卻是非常重要的分別;它實在痛得太真切,所有小說研究者對虛構事物的戒心與敏銳度,都會被襲擊到無法運作的程度。
在這本書裡,幾乎與邱妙津本人經歷貼合的面對絮的離去,陷入了情感的混亂、自毀之中。這一系列書信,可以讀作Zoë挽救情感、挽救自己生命的最後一系列嘗試,也可以如標題一般,直接讀作走向無可挽回之境的遺書。它是一批充滿矛盾的書信,時而堅定許諾時而脆弱毀傷,所有看似理性的文字都包藏著強大的情感風暴。用世俗的標準來看,我們甚至可以從Zoë在感情上的專斷、蠻橫、獨占與暴力裡,理解絮的叛離之必然;同時我們卻又知道這是Zoë人格特質上的必然。她很難是一個好情人,因為她生命的幅度是我們不能也不敢去容納的,但在文學的世界裡,她卻成為一種難以磨滅的,愛情的絕對典型。很少人將邱妙津與施明正相提並論,但我覺得台灣文學史上,這兩位作家是唯一與彼此相像的類型。他們受傷得喘不過氣的心靈,使他們用粗獷的文字取代了精工細雕;他們極端自覺因而自傲,然而穿越自傲的表象,我們卻又會看見低落到足以取消自己的自卑。
《蒙馬特遺書》的最後一封信的日期是一九九五年六月十七日,最後一段引用了安哲‧羅浦洛斯《鸛鳥踟躕》:
我們同樣沒有名字。
必須去借一個,有時候。
您供給我一個地方可以眺望。
將我遺忘在海邊吧。
我祝福您幸福健康。
然後,在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邱妙津如同卷首預言(「即將死去的我自己」)那樣在巴黎自殺,震動了台灣的文壇,直到二十年後的現在仍未完全靜止下來。一代一代年輕而被壓抑的靈魂,像是生來註定要遇見她一樣翻開了《蒙馬特遺書》,在那裡看見了被學校以及社會壓制住的某部分自己的投影,並且從此在心口上搋了一顆銳利的碎石。從此他們會知道傷痛是怎麼一回事,也會知道不要看輕傷痛的可能性,不要看輕任何一個身邊的人的情感。課本沒有教這些,因為大人們擔心,覺得自己的孩子們「不夠成熟」。只有如同祕密結社般讀過同樣的小說的人們知道,那是真正未曾成熟的大人所無法想像的;課本上自以為是保護的一切隱瞞,正好就是造成傷害、造成欺瞞的根源。
直視傷口或許會感覺到痛,但是痛正是心臟還在搏動的證據。
邱妙津(一九六九-一九九五)畢業於台大心理系。一九九二年前往法國,留學巴黎第八大學心理系臨床組,一九九五年在巴黎自殺身亡,得年僅二十六歲。著有《鬼的狂歡》、《寂寞的群眾》、《鱷魚手記》、《蒙馬特遺書》等。曾獲聯合文學中篇小說新人獎、時報文學獎推薦獎等。
翹課才能學會的事:郭箏〈好個翹課天〉
世界上充滿了各種小框框,小得悶死人。有一次我沒上朝會,躲在廁所裡燻草,我忽然從窗口望出去,那副景象可真把我嚇呆了。我是說,你忽然看見一千多個一模一樣的齪蛋排列得整整齊齊的擠在一個小到不能再小的操場上,而你知道你也是其中之一,那種感覺真可怕,真叫人想吐。我想看看小虎他們,但找來找去就是找不著。我想如果我自己也排在那隊伍裡,我恐怕也會找不著我自己。
──郭箏〈好個翹課天〉(一九八四)
我是從高中開始學會翹課的。當然,遠不能和郭箏筆下的「海山七俠」相較。相對於他們的硬漢風格,我們這類是嬌慣的少年──人家是砸天砸地,拳頭與汗水,我們則是維特的憂鬱,撕扯著考卷和(自己寫的)情書。但我猜,我們都不是從小就立志要翹課的孩子。雖然〈好個翹課天〉發表的一九八四年,距離我第一次偽造假單,窩到附近咖啡店趕校刊要用的稿子已有整整二十年──如果考慮生於一九五五年的作者郭箏,這個高中故事發生的年代甚至能再推前十年──;雖然我們早就不再用「齪蛋」和「馬子」這些詞了,我們的年代網咖比彈子房多十幾倍。但毫無疑問,我覺得我完全能讀懂〈好個翹課天〉。我覺得就算再過五十年、一百年,一個高中生也能讀懂它。
只要這個島,還沒打算改變它那總是在碾碎少年理想、情感的傳統慣性。
我們學會翹課的歷程,也許非常的相像。在七歲或更早的年紀,我們第一次被帶到一個叫做教室的地方,和一群叫做同學的人坐在一起,台上有一個叫做老師的人。這裡面你只認識在窗外的爸爸或媽媽,而就在某一次轉頭,你發現他或她不見了。關於學校,我們學會的第一件事情是遺棄,第二件事情是隔離;你不能做你本能想做的事,因為你現在身在一個特區,在這裡你的天職就是被管束。沒有人告訴我們為什麼,久了我們也就忘了問。有的是因為我們也的確很適應被管束,有的是因為光是讓自己平安度過八個小時,不要受罰,就已經占去我們全部的心神。
我們,以及〈好個翹課天〉裡面的小郭、小虎等人,就是這樣過了十年的人。如果在法律上,十年的徒刑是重罪,那在當代台灣學校教育體系長大的每一個人都是命定的罪犯。於是,總會有人想著要逃獄的──我曾經就讀過一所四面由鐵窗包圍、進出由教官帶隊如押解的學校,因此「逃獄」二字對我來說,並不只是抽象的隱喻。十六、七歲正是最適合逃的年紀,這篇小說的角色都是高中生,並非偶然。我們都是在這個年紀擁有了前所未有的體力和知識,有了長期應付學校體制的經驗,深知它的虛榮與弱點。郭箏描寫了一群世俗眼光中的「壞學生」,師長們認為他們虛度青春、鬧事狎玩,沒有辦法跟上功課,一點也看不到未來。但透過這七個人翹課一天的故事,我們發現,發表這篇小說時正好滿三十歲的作者──一個標準的「大人」的年紀──,似乎全然不同意其他大人的看法。他給予敘事者小郭一個超然的位置,他看著一切,既明白所謂道德規則是怎麼回事(只是他選擇不遵守),又察覺到那些規則底下流動的欲望、敗德與虛偽(好友小虎為什麼選不上校隊?美麗的音樂老師和清純的夢中情人馬綿綿為什麼會……?)。在小說裡,他滿口髒話,卻是唯一清醒(也就因而受苦)的智者。
郭箏要說的故事,遠比「好學生vs.壞學生」或者「道德vs.不道德」複雜。它不是一個單純反抗的故事。他的思考是:我知道以「學校」為代表的成人社會是一團糟的,所以我想要逃獄。但問題是,逃出來之後呢?我們在最前面引用的一個段落,非常精采地演繹了這種思考。「我」首先必須是個翹課者,是個不守規則的人,才有機會暫時離開框框,目擊這個框框的可怖、虛無。人在框框裡面的時候,是不會有任何感覺的,因為「我想如果我自己也排在那隊伍裡,我恐怕也會找不著我自己。」某種形式的「翹課」是抵抗成為「大人」的必經之路。但這句話的另外一層深意是,「我」有些悲哀地體認到,自己和排列在隊伍裡面的人並無本質上的不同。如果「我」進入了隊伍,也不可能鶴立雞群,而是會被整個體制給碾碎、融化、取消掉。整篇〈好個翹課天〉因此就是灰心的調子,它不是一篇提倡反抗的故事,而是一篇反抗過的人的唏噓。
因此,不管我們是否翹過課、是否為了一樣的理由翹課,讀到他們總像是讀到自己。
沒有一人會甘心永遠待在教室裡。但也沒有一人敢說,我已經永遠不必回來上課了。
我想起高二那年,一個總是縱容我翹課、不把我當掉的老師。他從來不責罵我,但我從來也不覺得他是親近我、了解我的。因為他說過:「等到高三,你就會自己回來了。」於是每一次,當又有師長告訴我文學沒有用、寫小說會讓我餓死的時候,我就會想起這句話,還有〈好個翹課天〉。
讀更多的小說,寫更多的小說。——這是我翹課的方式,而且就像小郭在結尾那沒有目標的奔跑一樣,我知道翹課是沒完沒了的,只有繼續逃亡,才能免於被框框俘虜。
就從這裡開始吧。至今,我還沒有讓那位高二老師的預言成真,而這些課本不教的小說,都是這段漫長的跑路過程中攜行的食糧。我現在就把它們放在這裡,如果你和當時的我是同一類人,或許你也會需要它們的。放心取用吧,不像世俗的任何財富或權力,它們是永不枯竭的,可以在永無止盡的翹課之路給你力量和渴盼,助你指認出每一個想把你擄回教室的、埋伏在暗處的那些精神教條。
郭箏(一九五五-),另一個筆名應天魚,小說家、編劇。一九八四年,在中國時報副刊發表〈好個翹課天〉,造成一股風潮,四年後發表〈彈子王〉。曾為電視劇《施公》編寫劇本,也曾為導演吳宇森的《赤壁》編劇。
課本不教的小說(20)
含著碎石的心──邱妙津《蒙馬特遺書》
我日日夜夜止不住地悲傷,不是為了世間的錯誤,不是為了身體的殘敗病痛,而是為了心靈的脆弱性及它所承受的傷害,我悲傷它承受了那麼多的傷害,我疼惜自己能給予別人,給予世界那麼多,卻沒辦法使自己活得好過一點。世界總是沒有錯的,錯的是心靈的脆弱性,我們不能免除於世界的傷害,於是我們就要長期生著靈魂的病。
──邱妙津《蒙馬特遺書》(一九九六/二○○六)
想像一顆心臟,含著一小塊銳利的碎石。每一次心臟跳動,每一次肌體收縮,都在別人看不見之處劃出傷口,撕裂復撕裂,咬牙復咬牙。想像這顆心臟比常人更加強悍,它每一次搏動都是加倍劇烈、認真的,也因而帶來比常人更甚的痛楚。
對我而言,這就是邱妙津的《蒙馬特遺書》所寫出來的感覺,讀完之後,那顆碎石就轉而鑲在我們的心底了。
就跟每一個十六、七歲初讀邱妙津的人一樣,在接下來的好幾年內,我們或許會讀到很多寫得更優美、更精巧、更大器……或簡而言之,寫得更好的作品。但幾乎沒有任何一本書能取代《蒙馬特遺書》的地位,就算是邱妙津自己成就更耀眼的長篇小說《鱷魚手記》都沒有辦法。在每一個情感傷痛的時刻,我們抄寫它的句子:「我已獻身給一個人,但世界並不接受這件事,這件事之於世界根本微不足道,甚至是被嘲笑的……」許諾的時候,我們也抄:「找到一個人,然後對他絕對。」最寂寞的一刻,心底冒起的句子是:「之於你,我真的還不夠美嗎?你的生命沒有我來跟你說話真的不會有點寂寞嗎?」很奇怪的是,從進入學校到我們第一次翻開它之前,我們在教室裡讀過的書也不在少數了,卻沒有一本書能像它一樣在生命低點的時候貼隨著我們。
一九九六年初版的《蒙馬特遺書》由一系列書信組成,內容是女同志Zoë在女友絮離開她之後寫的信,少部分是寫給另一密友詠的。在這些書信裡,Zoë以質樸到接近粗礪的筆法,檢證兩人的情感關係、思考自己的生命與藝術本質。嚴格說起來,這並不像一本小說,某些段落的文字甚至趨近於哲學思辨。然而或許正是這種「不像小說」的特質,使得整本書充滿了直接面對傷痛的撞擊力道。直白的作品往往流於膚淺,深刻的作品難以避免晦澀,但直白且深刻地去面對自己的心,就鑲進其他作品沒辦法抵達的位置。到了二○○六年的新版,補上了初版僅有標題而無內容的第十五書和第十九書,這兩章卻都是以此前未見的,從絮的觀點寫給Zoë的。雖然在腔調上明顯有所區隔,較為甜膩且幼兒化,但Zoë一向就將絮描述為一個不夠成熟到足以擔當愛情的人。所以,從那幾章裡面絮的自我認知與Zoë對絮的描述幾無落差來看,我仍傾向把它們當作是邱妙津自己從不同角色的觀點模擬而成,而不是真實書信的收錄。既有模擬,那這些章節確實有小說手法無疑了;既有若干章節呈現出小說手法,整本小說也就不應當作完全紀實的書寫了。
這種「真實與虛構」的討論看似多餘,但對於被它深深撼動的讀者如我而言,卻是非常重要的分別;它實在痛得太真切,所有小說研究者對虛構事物的戒心與敏銳度,都會被襲擊到無法運作的程度。
在這本書裡,幾乎與邱妙津本人經歷貼合的面對絮的離去,陷入了情感的混亂、自毀之中。這一系列書信,可以讀作Zoë挽救情感、挽救自己生命的最後一系列嘗試,也可以如標題一般,直接讀作走向無可挽回之境的遺書。它是一批充滿矛盾的書信,時而堅定許諾時而脆弱毀傷,所有看似理性的文字都包藏著強大的情感風暴。用世俗的標準來看,我們甚至可以從Zoë在感情上的專斷、蠻橫、獨占與暴力裡,理解絮的叛離之必然;同時我們卻又知道這是Zoë人格特質上的必然。她很難是一個好情人,因為她生命的幅度是我們不能也不敢去容納的,但在文學的世界裡,她卻成為一種難以磨滅的,愛情的絕對典型。很少人將邱妙津與施明正相提並論,但我覺得台灣文學史上,這兩位作家是唯一與彼此相像的類型。他們受傷得喘不過氣的心靈,使他們用粗獷的文字取代了精工細雕;他們極端自覺因而自傲,然而穿越自傲的表象,我們卻又會看見低落到足以取消自己的自卑。
《蒙馬特遺書》的最後一封信的日期是一九九五年六月十七日,最後一段引用了安哲‧羅浦洛斯《鸛鳥踟躕》:
我們同樣沒有名字。
必須去借一個,有時候。
您供給我一個地方可以眺望。
將我遺忘在海邊吧。
我祝福您幸福健康。
然後,在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邱妙津如同卷首預言(「即將死去的我自己」)那樣在巴黎自殺,震動了台灣的文壇,直到二十年後的現在仍未完全靜止下來。一代一代年輕而被壓抑的靈魂,像是生來註定要遇見她一樣翻開了《蒙馬特遺書》,在那裡看見了被學校以及社會壓制住的某部分自己的投影,並且從此在心口上搋了一顆銳利的碎石。從此他們會知道傷痛是怎麼一回事,也會知道不要看輕傷痛的可能性,不要看輕任何一個身邊的人的情感。課本沒有教這些,因為大人們擔心,覺得自己的孩子們「不夠成熟」。只有如同祕密結社般讀過同樣的小說的人們知道,那是真正未曾成熟的大人所無法想像的;課本上自以為是保護的一切隱瞞,正好就是造成傷害、造成欺瞞的根源。
直視傷口或許會感覺到痛,但是痛正是心臟還在搏動的證據。
邱妙津(一九六九-一九九五)畢業於台大心理系。一九九二年前往法國,留學巴黎第八大學心理系臨床組,一九九五年在巴黎自殺身亡,得年僅二十六歲。著有《鬼的狂歡》、《寂寞的群眾》、《鱷魚手記》、《蒙馬特遺書》等。曾獲聯合文學中篇小說新人獎、時報文學獎推薦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