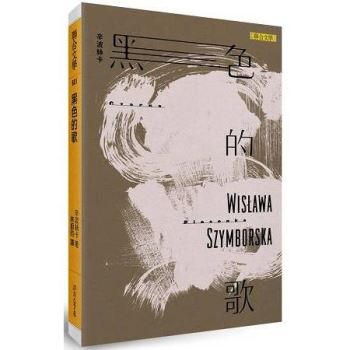Prolog/〈笑聲〉
那個我曾經是的女孩──
我認識她,當然。
我有幾張照片,
記錄她短暫的一生。
看到她那幾首小詩
我感到憐憫又好笑。
我記得幾個事件。
但是,
為了讓我身邊的那人
大笑,並且擁抱我,
我只會提起一個小故事:
那個小醜八怪
孩子氣的愛情。
我說,
她是如何愛上一個學生,
我的意思是她想要
他看她一眼。
我說,
她是如何把繃帶綁在
健康完好的頭上然後跑向他,
就為了,喔,讓他問一聲,
發生了什麼事。
好笑的小女孩。
她怎會知道,
即使絕望也會帶來好處,
如果幸運地
活得更久。
我會給她錢讓她去吃餅乾。
我會給她錢讓她去看電影。
離開吧,我沒有時間。
妳沒看到嗎,
燈已經熄了。
也許妳明白,
門也關起來了。
不要用力扯門把──
那個大笑的人,
那個擁抱我的人,
不是妳的學生。
最好是,如果妳能回到
妳來的地方。
我沒有虧欠妳什麼,
我只是個普通女人,
只知道,
在何時,
背叛陌生人的秘密。
不要這樣用那雙眼睛
看我們,那雙
張得太大的眼睛,
就像死人的眼睛一樣。
選自(《開心果》, 1967)
獻給詩 /《黑色的歌》
1
日子的顏色是從天空和葉片來的,
所以我們在蠟筆盒裡找不到它。
在花園遁入陰影之前,
我必須把我的眼睛換成文字。
在太陽底下慵懶的詩人們
與在枝葉上慢吞吞爬行的蒼蠅們有著不同的智慧,
蒼蠅不知道自己精確的拉丁名稱,
也不知道自己翅膀在陽光下的戲謔。
你們比詩還要脆弱。
你在飛行時就會忘了自己。
2
思緒──就像是空屋裡的風。
城市的一刻:牆上的陽光。
一扇窗戶打開自己的黑暗。
一點都不崇高。在牆的陷阱中。
有誰會需要關於死亡的知識。
因為它桌上的茶都涼了。
一點都沒有氣氛。肥皂般的文字。
世界的一刻:寂靜不會等。
噪音有如沙塵灑進窗戶。
一點都沒有詩意。給石頭和夢。
3
嬉戲的人散去,院子變得空洞。
我看著它,彷彿一個陌生的地方。
一個孩子留下的鐵圈──
沒有赤道的地球。
這是訴說自己請求的好時機:
我想要在你張得大大的眼中
看到一個更好的明天,
像你一樣
把手在火焰中交叉。
院子變暗了。
鐵圈會在那裡等到清晨。
不可以玩火。
我不能見到你更多。
有一粒沙的景色
我們叫它一粒沙。
但它不會叫它自己顆粒,或是沙。
沒有一般、特別、
暫時、永久、
錯誤或正確的名字,
它依然悠然自得。
我們的視線和觸摸對它不起作用。
它感覺不到我們的目光和觸摸。
而它掉落到窗台上,
只是我們的冒險,不是它的。
對它來說,掉到什麼地方都一樣,
不管是否確定已經掉落,
還是在掉落的途中。
從窗戶望出去可以看到一座美麗的湖,
但這景色看不到自己。
在這世上它以無色、無形、
無聲、無味、
而且無痛的姿態存在。
湖底意識不到底,
湖岸察覺不到岸。
湖水不會感覺到自己是濕還是乾。
對浪潮來說,單數或複數沒有差別,
它們聽不見自己嘩啦啦的拍擊聲,
拍在不大也不小的石頭上。
而這一切都在沒有天空的天空下發生,
日落時太陽完全沒有落下,
而當太陽躲在一朵無心的雲朵後方時,它並沒有在躲藏。
風把雲吹散,不為了任何其他理由,
只是因為它在吹。
一秒鐘過去。
兩秒鐘過去。
三秒鐘過去。
但那只是我們的三秒鐘。
時間流逝像是身負緊急訊息的信使。
但這只是我們的比喻。
這是個幻想的角色,它的緊急是虛構的,
而它的訊息是非人的。
/選自《橋上的人們》, 1986
對照筆記:看世界的人──林蔚昀
讀詩或寫詩的人,應該對這樣的情境很熟悉:看到雲,詩人說這代表偶然。看到高山瀑布,詩人說這讓我們感到人類渺小。看到玫瑰,詩人歌頌愛情。看到浪花,詩人頓悟生命無常。看到沙、小孩拿來玩耍的鐵圈、陽光、蒼蠅、花園…詩人都可以說出一個所以然,賦予這些事物意義和象徵,讓它們營造出氛圍和意象。或者,就算詩人沒說,評論家和讀者也會解釋出一個所以然。似乎,寫作和閱讀就是一場尋找意義的競賽。
在這萬物皆有所指、萬物充滿意義的宇宙中,辛波絲卡的〈有一粒沙的景色〉像是一種反問:「你真的有想到沙在想什麼嗎?還是你只想到你自己?搞不好它什麼都沒想,什麼都不想代表/象徵/比喻,只是簡簡單單地存在,即使沒有我們,它也可以過得很好?」
「宇宙萬物存在,不管我們是否存在,不論我們對宇宙萬物有什麼看法」的命題,其實一直在辛波絲卡的作品中反覆出現。除了〈有一粒沙的景色〉,在早期的〈獻給詩〉中,辛波絲卡也提到:「蒼蠅不知道自己精確的拉丁名稱,也不知道自己翅膀在陽光下的戲謔。」而在〈評論一首沒被寫下的詩〉中,詩人則用評論家的角度和自己對話,批評詩人「也許在太陽底下,或是在世界所有的太陽底下我們真的是孤獨的?」的論點完全不顧機率論和今日普遍被接受的信念。
但是問題來了:辛波絲卡和我們一樣沒有讀心術,沒有和宇宙萬物溝通的能力。她又怎麼知道,沙、湖、天空對我們怎麼看待它們無動於衷呢?搞不好它們會很開心,或者覺得「唉,人類都不懂我,解讀能力太差」?也許,這又會是另一個「子非魚,安知魚之樂?」的辯論?
如果不能寄情於外在事物(因為外在事物根本不在乎我們),表達內在的情感是困難的。畢竟,內在的感覺很抽象而且看不見,最能讓人理解的溝通方式還是透過看得見的外在事物來表達。所以,雖然辛波絲卡對沙是否願意代表我們有疑慮,她還是寫下了〈奇蹟市集〉,透過雲、倒影、母牛、日出日落來表達她對日常奇蹟的看法──雖然這些奇蹟可能不會自認為是奇蹟。
那個我曾經是的女孩──
我認識她,當然。
我有幾張照片,
記錄她短暫的一生。
看到她那幾首小詩
我感到憐憫又好笑。
我記得幾個事件。
但是,
為了讓我身邊的那人
大笑,並且擁抱我,
我只會提起一個小故事:
那個小醜八怪
孩子氣的愛情。
我說,
她是如何愛上一個學生,
我的意思是她想要
他看她一眼。
我說,
她是如何把繃帶綁在
健康完好的頭上然後跑向他,
就為了,喔,讓他問一聲,
發生了什麼事。
好笑的小女孩。
她怎會知道,
即使絕望也會帶來好處,
如果幸運地
活得更久。
我會給她錢讓她去吃餅乾。
我會給她錢讓她去看電影。
離開吧,我沒有時間。
妳沒看到嗎,
燈已經熄了。
也許妳明白,
門也關起來了。
不要用力扯門把──
那個大笑的人,
那個擁抱我的人,
不是妳的學生。
最好是,如果妳能回到
妳來的地方。
我沒有虧欠妳什麼,
我只是個普通女人,
只知道,
在何時,
背叛陌生人的秘密。
不要這樣用那雙眼睛
看我們,那雙
張得太大的眼睛,
就像死人的眼睛一樣。
選自(《開心果》, 1967)
獻給詩 /《黑色的歌》
1
日子的顏色是從天空和葉片來的,
所以我們在蠟筆盒裡找不到它。
在花園遁入陰影之前,
我必須把我的眼睛換成文字。
在太陽底下慵懶的詩人們
與在枝葉上慢吞吞爬行的蒼蠅們有著不同的智慧,
蒼蠅不知道自己精確的拉丁名稱,
也不知道自己翅膀在陽光下的戲謔。
你們比詩還要脆弱。
你在飛行時就會忘了自己。
2
思緒──就像是空屋裡的風。
城市的一刻:牆上的陽光。
一扇窗戶打開自己的黑暗。
一點都不崇高。在牆的陷阱中。
有誰會需要關於死亡的知識。
因為它桌上的茶都涼了。
一點都沒有氣氛。肥皂般的文字。
世界的一刻:寂靜不會等。
噪音有如沙塵灑進窗戶。
一點都沒有詩意。給石頭和夢。
3
嬉戲的人散去,院子變得空洞。
我看著它,彷彿一個陌生的地方。
一個孩子留下的鐵圈──
沒有赤道的地球。
這是訴說自己請求的好時機:
我想要在你張得大大的眼中
看到一個更好的明天,
像你一樣
把手在火焰中交叉。
院子變暗了。
鐵圈會在那裡等到清晨。
不可以玩火。
我不能見到你更多。
有一粒沙的景色
我們叫它一粒沙。
但它不會叫它自己顆粒,或是沙。
沒有一般、特別、
暫時、永久、
錯誤或正確的名字,
它依然悠然自得。
我們的視線和觸摸對它不起作用。
它感覺不到我們的目光和觸摸。
而它掉落到窗台上,
只是我們的冒險,不是它的。
對它來說,掉到什麼地方都一樣,
不管是否確定已經掉落,
還是在掉落的途中。
從窗戶望出去可以看到一座美麗的湖,
但這景色看不到自己。
在這世上它以無色、無形、
無聲、無味、
而且無痛的姿態存在。
湖底意識不到底,
湖岸察覺不到岸。
湖水不會感覺到自己是濕還是乾。
對浪潮來說,單數或複數沒有差別,
它們聽不見自己嘩啦啦的拍擊聲,
拍在不大也不小的石頭上。
而這一切都在沒有天空的天空下發生,
日落時太陽完全沒有落下,
而當太陽躲在一朵無心的雲朵後方時,它並沒有在躲藏。
風把雲吹散,不為了任何其他理由,
只是因為它在吹。
一秒鐘過去。
兩秒鐘過去。
三秒鐘過去。
但那只是我們的三秒鐘。
時間流逝像是身負緊急訊息的信使。
但這只是我們的比喻。
這是個幻想的角色,它的緊急是虛構的,
而它的訊息是非人的。
/選自《橋上的人們》, 1986
對照筆記:看世界的人──林蔚昀
讀詩或寫詩的人,應該對這樣的情境很熟悉:看到雲,詩人說這代表偶然。看到高山瀑布,詩人說這讓我們感到人類渺小。看到玫瑰,詩人歌頌愛情。看到浪花,詩人頓悟生命無常。看到沙、小孩拿來玩耍的鐵圈、陽光、蒼蠅、花園…詩人都可以說出一個所以然,賦予這些事物意義和象徵,讓它們營造出氛圍和意象。或者,就算詩人沒說,評論家和讀者也會解釋出一個所以然。似乎,寫作和閱讀就是一場尋找意義的競賽。
在這萬物皆有所指、萬物充滿意義的宇宙中,辛波絲卡的〈有一粒沙的景色〉像是一種反問:「你真的有想到沙在想什麼嗎?還是你只想到你自己?搞不好它什麼都沒想,什麼都不想代表/象徵/比喻,只是簡簡單單地存在,即使沒有我們,它也可以過得很好?」
「宇宙萬物存在,不管我們是否存在,不論我們對宇宙萬物有什麼看法」的命題,其實一直在辛波絲卡的作品中反覆出現。除了〈有一粒沙的景色〉,在早期的〈獻給詩〉中,辛波絲卡也提到:「蒼蠅不知道自己精確的拉丁名稱,也不知道自己翅膀在陽光下的戲謔。」而在〈評論一首沒被寫下的詩〉中,詩人則用評論家的角度和自己對話,批評詩人「也許在太陽底下,或是在世界所有的太陽底下我們真的是孤獨的?」的論點完全不顧機率論和今日普遍被接受的信念。
但是問題來了:辛波絲卡和我們一樣沒有讀心術,沒有和宇宙萬物溝通的能力。她又怎麼知道,沙、湖、天空對我們怎麼看待它們無動於衷呢?搞不好它們會很開心,或者覺得「唉,人類都不懂我,解讀能力太差」?也許,這又會是另一個「子非魚,安知魚之樂?」的辯論?
如果不能寄情於外在事物(因為外在事物根本不在乎我們),表達內在的情感是困難的。畢竟,內在的感覺很抽象而且看不見,最能讓人理解的溝通方式還是透過看得見的外在事物來表達。所以,雖然辛波絲卡對沙是否願意代表我們有疑慮,她還是寫下了〈奇蹟市集〉,透過雲、倒影、母牛、日出日落來表達她對日常奇蹟的看法──雖然這些奇蹟可能不會自認為是奇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