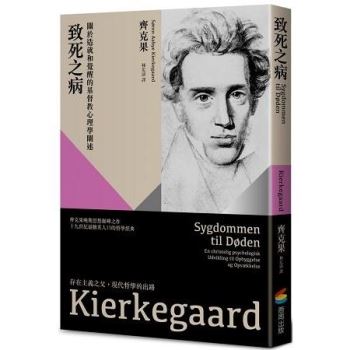王鏡玲 真理大學宗教文化與組織管理學系副教授
李麗娟 聖光神學院助理教授
汪文聖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教授
專文推薦(按姓氏筆畫排序)
【推薦序】
審視內在心靈的透視鏡
王鏡玲
齊克果在不同的時代都對那個時代的讀者,散發出思想的切身性和存在感的魅力。齊克果的思想影響二十世紀迄今當代宗教哲學、神學、心理學、文化研究等領域,本書雖然寫在十九世紀中期齊克果所生活的丹麥基督教的社會,但是這本書所提出對於「絕望」的人性透徹剖析,具有射向未來的跨文化啟發。齊克果對於人性絕望、憂懼、孤獨、傲慢、偽善、墨守教義、渾渾噩噩、醉生夢死的探究,正是一面透視鏡,不只是針對基督宗教的信徒,也同時提醒非基督宗教以及沒有特定宗教的信仰者,去審視自我內在心靈。
本書有很多精彩段落,有的宛如格言、有的宛如詩篇、有的宛如劇場主角的獨白。即使讀者在閱讀時無法一氣呵成,也可以藉由那些充滿辯證思路的段落,看齊克果如何以犀利的筆調,展現從死蔭幽谷,到曲境通幽的信仰冒險。此外,本書迂迴、內斂中有激情的寫作風格,更是對現今墨守僵化「學術」論文格式的當頭棒喝。以下僅舉幾段精彩段落。
一、對於絕望的辯證詩意:
在「第二部:絕望是罪」的開頭處,我們可以看到齊克果透過自身既是詩人又是基督徒的處境,剖析「罪(Synd)是:在神面前或是心裡想著神而在絕望中不想做自己,或是在絕望中想要做自己。」:
詩人可能有相當深邃的宗教渴望,而且會在絕望中心裡想著神。他愛神甚於一切,神是他內心深處的苦悶唯一的慰藉,然而他愛這個苦悶,始終不肯放手。他很想要在神面前做自己,除了讓自我受苦的定點(faste Punkt)以外;在那個定點上,他在絕望中不想做自己。他希望永恆可以拿走它,而在這個世間,不管他感到多麼絕望,他都沒辦法下定決心在信仰裡對它低聲下氣。
可是他始終和神保持著關係,那是他唯一的救恩;對他而言,沒有了神是最難以忍受的事,「他會因而陷入絕望」,然而事實上,他在寫作時會不自覺地對神有一點扭曲,讓人以為神更像一個對孩子們的願望百依百順的慈父。就像失戀的人變成了詩人,終日歌頌愛情的美好,他也成了虔誠的詩人。(頁一四三)
二、對於空洞思辨理論的警覺
齊克果不僅對於當時社會上基督宗教價值觀鞭辟入裡,也以其獨到的基督徒存在體驗,批判那些置身事外、對生命沒有參與感、夸夸其言的知識體系。齊克果以其個人面對上帝的獨特性,與存在處境的合體,與當時主流思辨哲學與神學激烈交鋒。齊克果認為思辨哲學與神學忽略了知識最關鍵的生命冒險、戒慎恐懼的生命現場。「倫理的問題不曾自現實抽離開來,而是深入現實當中,」知識不是思辨體系裡概念操弄的紙上談兵。以下我們看到齊克果以嘲諷的筆調,提醒知行合一的重要:
一個思想家建造了一座龐大的建築,一個體系,一個涵攝整個存在的體系,一套世界歷史等等,可是究其個人生活,我們會很詫異地發現一個令人咋舌而發噱的事實:他自己並沒有住在這棟宏偉的、有拱頂的宮殿裡,而是住在旁邊的棚子裡,或者是在狗屋裡,最多只肯住在門房的小屋子裡。只要有人多說兩句,提醒他這個矛盾,他就會勃然大怒。(頁九十九)
三、對於宗教徒的提醒
最後,在現今屬於宗教多元的社會裡,齊克果對於宗教徒的提醒,也很值得參考:
在外邦人的世界,人們因為害怕或畏懼窈窈冥冥的事物而畢恭畢敬地呼喚神的名字,相反的,在基督教世界裡,神的名字往往出現在街談巷議當中,人們總是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因為那可悲的、對世人顯現的神(他沒有像躲在深宮高苑裡的貴族一樣隱藏起來,反而輕率而不聰明地顯現自己)在所有人當中只是個家喻戶曉的角色,人們偶爾上教堂,就算是幫神一個大忙,當然也得到牧師的讚美,他代表神感謝他們大駕光臨,推崇他們都是虔誠的信徒,並且揶揄那些從來不上教堂榮耀神的人。(頁一九九)
儘管齊克果還有當時基督徒對於「外邦人」(異教徒)的時代限制,但他也精準地看出,宗教徒自以為掌握所信仰的「神」,卻也因此執著傲慢、反而遠離「神」。甚至在現今世界很多宗教「以神之名」互相攻擊殘殺,都提醒我們重新探索內在靈性,去認識「神聖」的無限與廣闊。
最後,譯者林宏濤先生,將中國哲人的文采融入翻譯的意境,讓本書在閱讀時擺脫外文譯著的語言隔閡,氣韻生動,實屬難得。
本文作者為真理大學宗教文化與組織管理學系副教授
【推薦序】
一窺齊克果的哲學辯證與溝通方法、倫理學立場、基督宗教的心理學分析
汪文聖
《致死之病》是部頗具結構性,但內容不失詼諧且處處充滿機鋒的一部書。開始時提出的問題是自我(Self)是什麼?齊克果的回答是先確立人是有限者與無限者、瞬息與永恆、自由與必然、身體與心靈的四組兩重因素的綜合,但誰來決定這個綜合呢?齊克果基於基督宗教的立場,將這個決定者歸為上帝。
《致死之病》主要的論題是「絕望是致死的病」,絕望的來源根本在於上述的綜合關係失去了由上帝來決定的關係。齊克果在開始問自我是什麼之後回答了:「自我是讓自身關連到那個定立了整個關係的關係」。這個句子有兩個「關係」的概念,前者是上述的綜合關係,後者是第三者決定這綜合關係的關係。在本書的不同脈絡中,我們發現,真正的自我是被上帝決定的人自己,或是被上帝決定的關係本身,甚或是上帝自身。
既然絕望才是致死的病,那麼肉體的死亡就不是真正的致死;既然對於人的決定是上帝,那麼人的生命也由上帝來決定。因此在「導論」的起頭即有耶穌針對拉撒路的肉體死亡而說:「這病不至於死」;反之,基督徒所領會的更可怕的事卻是絕望所引起的致死之病。
在失去上帝來決定人的綜合關係之前提下,絕望有著不同的種類與強弱層級。齊克果是循序漸進對於絕望從不自覺到自覺,從對個別事物到對普遍事物,進而對自我的絕望來解析的。從第一部到第二部,絕望程度的升級更基於:從本來沒有面對上帝轉為承認有個上帝,但尚未對祂產生信仰;絕望因此提高到有罪,並在持續加深中有著不同罪的層級。
我們綜觀一下《致死之病》,看看它除了在探討人從絕望深處轉而信仰上帝之外,還給予了我們哪些啟示?
第一、齊克果和黑格爾的關係。在本書討論從意識方面去看絕望的第一節,齊克果說到一個思想家建造一座大建築,包括整個存在與世界歷史體系,但自己卻住在大樓旁的棚子或是狗屋裡。這顯然在批評黑格爾。但齊克果在此書的構思卻有著黑格爾辯證法的影子。例如前述的人之綜合關係再受之於第三者的關係,但這是否是一種黑格爾式的「思辨辯證」(speculative dialectic),也就是從「在己」(in itself) 發展到「為己」(for itself),最後再到「在己為己」(in and for itself)呢?其實當例如有限者與無限者做綜合時,先是無限者對有限者的否定後,再建構了一個包涵這兩者元素的綜合體,但這個建構不是人的精神發展所成就的,卻是否定了人的精神而訴諸於上帝作為決定這綜合的第三者。故它可稱為一種「否定辯證」(negative dialectic),是對於人以及世俗的否定,相對於黑格爾對於人的精神與歷史行程的肯定。
第二、齊克果與蘇格拉底的關係。在第二部論「絕望是罪」的一節中討論了蘇格拉底對罪的定義。齊克果反對蘇格拉底以為罪是無知,因為齊克果強調罪是一種意識,人是知道自己的罪的。雖然一方面齊克果批評蘇格拉底定義罪時缺少了意志的元素,但另一方面他又同意蘇格拉底所區分的了解與真了解,贊同他以為若真了解就會受感動而去實踐。然而齊克果以為若沒有從上帝那裡得到真了解的啟示,甚至不願意從上帝那裡獲得真知,以致於有著這種對於違抗命令之意志自覺的罪,才能出現從知到行過渡的辯證動機,這點則是在蘇格拉底那裡仍然付諸闕如的。
李麗娟 聖光神學院助理教授
汪文聖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教授
專文推薦(按姓氏筆畫排序)
【推薦序】
審視內在心靈的透視鏡
王鏡玲
齊克果在不同的時代都對那個時代的讀者,散發出思想的切身性和存在感的魅力。齊克果的思想影響二十世紀迄今當代宗教哲學、神學、心理學、文化研究等領域,本書雖然寫在十九世紀中期齊克果所生活的丹麥基督教的社會,但是這本書所提出對於「絕望」的人性透徹剖析,具有射向未來的跨文化啟發。齊克果對於人性絕望、憂懼、孤獨、傲慢、偽善、墨守教義、渾渾噩噩、醉生夢死的探究,正是一面透視鏡,不只是針對基督宗教的信徒,也同時提醒非基督宗教以及沒有特定宗教的信仰者,去審視自我內在心靈。
本書有很多精彩段落,有的宛如格言、有的宛如詩篇、有的宛如劇場主角的獨白。即使讀者在閱讀時無法一氣呵成,也可以藉由那些充滿辯證思路的段落,看齊克果如何以犀利的筆調,展現從死蔭幽谷,到曲境通幽的信仰冒險。此外,本書迂迴、內斂中有激情的寫作風格,更是對現今墨守僵化「學術」論文格式的當頭棒喝。以下僅舉幾段精彩段落。
一、對於絕望的辯證詩意:
在「第二部:絕望是罪」的開頭處,我們可以看到齊克果透過自身既是詩人又是基督徒的處境,剖析「罪(Synd)是:在神面前或是心裡想著神而在絕望中不想做自己,或是在絕望中想要做自己。」:
詩人可能有相當深邃的宗教渴望,而且會在絕望中心裡想著神。他愛神甚於一切,神是他內心深處的苦悶唯一的慰藉,然而他愛這個苦悶,始終不肯放手。他很想要在神面前做自己,除了讓自我受苦的定點(faste Punkt)以外;在那個定點上,他在絕望中不想做自己。他希望永恆可以拿走它,而在這個世間,不管他感到多麼絕望,他都沒辦法下定決心在信仰裡對它低聲下氣。
可是他始終和神保持著關係,那是他唯一的救恩;對他而言,沒有了神是最難以忍受的事,「他會因而陷入絕望」,然而事實上,他在寫作時會不自覺地對神有一點扭曲,讓人以為神更像一個對孩子們的願望百依百順的慈父。就像失戀的人變成了詩人,終日歌頌愛情的美好,他也成了虔誠的詩人。(頁一四三)
二、對於空洞思辨理論的警覺
齊克果不僅對於當時社會上基督宗教價值觀鞭辟入裡,也以其獨到的基督徒存在體驗,批判那些置身事外、對生命沒有參與感、夸夸其言的知識體系。齊克果以其個人面對上帝的獨特性,與存在處境的合體,與當時主流思辨哲學與神學激烈交鋒。齊克果認為思辨哲學與神學忽略了知識最關鍵的生命冒險、戒慎恐懼的生命現場。「倫理的問題不曾自現實抽離開來,而是深入現實當中,」知識不是思辨體系裡概念操弄的紙上談兵。以下我們看到齊克果以嘲諷的筆調,提醒知行合一的重要:
一個思想家建造了一座龐大的建築,一個體系,一個涵攝整個存在的體系,一套世界歷史等等,可是究其個人生活,我們會很詫異地發現一個令人咋舌而發噱的事實:他自己並沒有住在這棟宏偉的、有拱頂的宮殿裡,而是住在旁邊的棚子裡,或者是在狗屋裡,最多只肯住在門房的小屋子裡。只要有人多說兩句,提醒他這個矛盾,他就會勃然大怒。(頁九十九)
三、對於宗教徒的提醒
最後,在現今屬於宗教多元的社會裡,齊克果對於宗教徒的提醒,也很值得參考:
在外邦人的世界,人們因為害怕或畏懼窈窈冥冥的事物而畢恭畢敬地呼喚神的名字,相反的,在基督教世界裡,神的名字往往出現在街談巷議當中,人們總是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因為那可悲的、對世人顯現的神(他沒有像躲在深宮高苑裡的貴族一樣隱藏起來,反而輕率而不聰明地顯現自己)在所有人當中只是個家喻戶曉的角色,人們偶爾上教堂,就算是幫神一個大忙,當然也得到牧師的讚美,他代表神感謝他們大駕光臨,推崇他們都是虔誠的信徒,並且揶揄那些從來不上教堂榮耀神的人。(頁一九九)
儘管齊克果還有當時基督徒對於「外邦人」(異教徒)的時代限制,但他也精準地看出,宗教徒自以為掌握所信仰的「神」,卻也因此執著傲慢、反而遠離「神」。甚至在現今世界很多宗教「以神之名」互相攻擊殘殺,都提醒我們重新探索內在靈性,去認識「神聖」的無限與廣闊。
最後,譯者林宏濤先生,將中國哲人的文采融入翻譯的意境,讓本書在閱讀時擺脫外文譯著的語言隔閡,氣韻生動,實屬難得。
本文作者為真理大學宗教文化與組織管理學系副教授
【推薦序】
一窺齊克果的哲學辯證與溝通方法、倫理學立場、基督宗教的心理學分析
汪文聖
《致死之病》是部頗具結構性,但內容不失詼諧且處處充滿機鋒的一部書。開始時提出的問題是自我(Self)是什麼?齊克果的回答是先確立人是有限者與無限者、瞬息與永恆、自由與必然、身體與心靈的四組兩重因素的綜合,但誰來決定這個綜合呢?齊克果基於基督宗教的立場,將這個決定者歸為上帝。
《致死之病》主要的論題是「絕望是致死的病」,絕望的來源根本在於上述的綜合關係失去了由上帝來決定的關係。齊克果在開始問自我是什麼之後回答了:「自我是讓自身關連到那個定立了整個關係的關係」。這個句子有兩個「關係」的概念,前者是上述的綜合關係,後者是第三者決定這綜合關係的關係。在本書的不同脈絡中,我們發現,真正的自我是被上帝決定的人自己,或是被上帝決定的關係本身,甚或是上帝自身。
既然絕望才是致死的病,那麼肉體的死亡就不是真正的致死;既然對於人的決定是上帝,那麼人的生命也由上帝來決定。因此在「導論」的起頭即有耶穌針對拉撒路的肉體死亡而說:「這病不至於死」;反之,基督徒所領會的更可怕的事卻是絕望所引起的致死之病。
在失去上帝來決定人的綜合關係之前提下,絕望有著不同的種類與強弱層級。齊克果是循序漸進對於絕望從不自覺到自覺,從對個別事物到對普遍事物,進而對自我的絕望來解析的。從第一部到第二部,絕望程度的升級更基於:從本來沒有面對上帝轉為承認有個上帝,但尚未對祂產生信仰;絕望因此提高到有罪,並在持續加深中有著不同罪的層級。
我們綜觀一下《致死之病》,看看它除了在探討人從絕望深處轉而信仰上帝之外,還給予了我們哪些啟示?
第一、齊克果和黑格爾的關係。在本書討論從意識方面去看絕望的第一節,齊克果說到一個思想家建造一座大建築,包括整個存在與世界歷史體系,但自己卻住在大樓旁的棚子或是狗屋裡。這顯然在批評黑格爾。但齊克果在此書的構思卻有著黑格爾辯證法的影子。例如前述的人之綜合關係再受之於第三者的關係,但這是否是一種黑格爾式的「思辨辯證」(speculative dialectic),也就是從「在己」(in itself) 發展到「為己」(for itself),最後再到「在己為己」(in and for itself)呢?其實當例如有限者與無限者做綜合時,先是無限者對有限者的否定後,再建構了一個包涵這兩者元素的綜合體,但這個建構不是人的精神發展所成就的,卻是否定了人的精神而訴諸於上帝作為決定這綜合的第三者。故它可稱為一種「否定辯證」(negative dialectic),是對於人以及世俗的否定,相對於黑格爾對於人的精神與歷史行程的肯定。
第二、齊克果與蘇格拉底的關係。在第二部論「絕望是罪」的一節中討論了蘇格拉底對罪的定義。齊克果反對蘇格拉底以為罪是無知,因為齊克果強調罪是一種意識,人是知道自己的罪的。雖然一方面齊克果批評蘇格拉底定義罪時缺少了意志的元素,但另一方面他又同意蘇格拉底所區分的了解與真了解,贊同他以為若真了解就會受感動而去實踐。然而齊克果以為若沒有從上帝那裡得到真了解的啟示,甚至不願意從上帝那裡獲得真知,以致於有著這種對於違抗命令之意志自覺的罪,才能出現從知到行過渡的辯證動機,這點則是在蘇格拉底那裡仍然付諸闕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