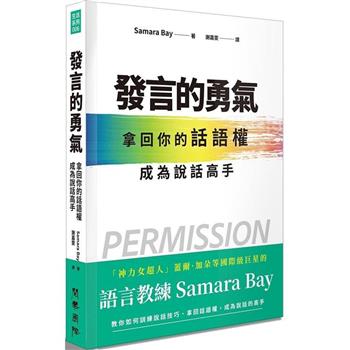第一章
呼吸(Breath):好好呼吸才能好好說話
我願意被看見。
我願意發聲。
我願意繼續前進。
我願意傾聽別人怎麼說。
即使感到孤獨,我也願意繼續前進。
我願意在每晚上床睡覺時,與自己和解。
我願意成為最大、最好、最有力量的自己。
我被這七句話給嚇壞了。
但我知道,這些話是一切的關鍵。
──艾瑪.華特森(Emma Watson)
暫停片刻,就只深呼吸。有時是,在我們睡覺或處理日常事務時,規律進出的節奏;有時是伴隨著生活中的驚喜時刻所出現的──溫暖的身體接觸、美妙的話語、突然現身的朋友。節奏改變了,我們吸入比平時更多的空氣,這個動作是對新鮮事物的本能反應。那一刻,我對丈夫大聲讀出驗孕手冊上的說明,想弄清楚驗孕棒的標記代表的意思──但讀到一半就停下來喘了口氣。緊接而來的是充滿無限可能和全然脆弱的嘆息。呼吸,是進行中的生命。
不過,呼吸同時也代表另外一件事。近十年來,「我不能呼吸」一直是黑人控訴警察不當執法的口號,提醒了大家脆弱的氣管──或人類──多麼容易遭受不當對待。當新冠疫情來襲,「我不能呼吸」的哭訴聲,透過人類使用的各種語言,在世界各地的醫院中迴盪。為了避免生病,我們把自己與他人隔離開來,手住鼻子和嘴巴,避免自己的氣息擴散。聚集在公共場所,讓彼此的願望和靈感相互融合,成為一件危險的事。在美國封城的第一個週末,我記得自己坐在床上,拚命閱讀新聞,換氣過度,腦中想著,上帝啊,如今分享呼吸竟然可能代表死亡。
在這樣的脈絡下,無論是在稀鬆平常的時刻,或在令人驚訝的時刻,留意自己的呼吸不再是件小事。原本呼吸是件再簡單不過的事,有點像眨眼,會自動發生。但在風險變高時,呼吸卻變成最困難的事,因為透過呼吸,你會釋放出內在的感覺或想法,但卻不知道後果是甚麼。
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在公共場合分享自己的呼吸,向來都是危險的。對於我們這些看法前衛,忍不住質疑傳統的人來說,群眾從來都不曾無條件歡迎我們的感受或想法。我們一直受到威脅、毀謗和忽視,我們失去工作,像女巫般被公開審判,不被信任。對傳統掌權者以外的所有人而言,想要深吸一口氣,發表自己的看法,得先刪除數千年來「誰有資格公開發言、應該如何發言」的教條,打破由來已久的迷思。
大口呼吸,釋放自己
因為事實是這樣的:當你真實而完整的吸一口氣,這外來的空氣被吸在幾分之一秒後變成你的一部分──你的希望和夢想,你的憤怒和快樂,你所有的想望。當然,每個人都需要空氣來維持生命,但也都需要空氣來啟動自己的憤怒和喜悅,如果我們想改寫傳統,就得啟動這些情緒──來重塑「誰有資格公開發言、該如何發言」的迷思,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成為自己的英雄。我對你的期待是,在風險很高的情境下,你已經準備妥當,可以勇敢面對,大口深呼吸,釋放真實的自己。
不過,有時我們會察覺自己在所處場合中形單影隻──我們是唯一特定種族或酷兒群體的人,唯一的女人,唯一坐輪椅的人,唯一衣著鮮豔、穿二手衣,或明顯有孕在身的人,唯一說話有不同口音,或願意花錢做對的事的人。就像「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活動領袖塔米卡·馬洛里(Tamika Mallory)所說,有時候我們發現自己置身於不屬於自己的競技場,在那個時刻,我們會深深渴望縮小自己或隱藏差異,而讓自己消失的方法之一,就是屏住呼吸。
可是有時候,我們身處的場合的確需要整修──也許你躍躍欲試,想用重新設計的藍圖大展身手。我一次又一次目睹這樣的情景,在我指導過的客戶身上,在講台下隨處可見的局外人身上:我們帶著雄心壯志、過人膽識,宏大願景、堅定使命,準備好要征服全世界;可是後來,當我們站在想對抗的人面前時…我們屏住呼吸,把空氣擠進又擠出緊縮的喉嚨,用壓抑的姿態說話,聲音沙啞單調,聽起來無精打采。我們準備好要改寫這個迷思,但我們的聲音卻並未處於最佳狀態。也許長久以來,我們一直要求自己為應對這種窘境做足準備──缺乏歸屬感、不夠好、被誤解、被貶低或在噓聲中逃下台──以至於如今因為習慣而出現這種反應。結果,掌權者依然穩若泰山,屹立不搖。
我可以幫助你改掉這個習慣,目的是讓你獲得許可和勇氣,同時讓你重新熟悉自己的呼吸。你必須相信,真正相信你的身體屬於那裡,並且用真心誠意邀請自己走進讓你害怕的空間。這種信任需要練習,而我會提供一些技巧,協助你做到。
同時我也會提供一些看法,因為你並不孤單。你不是唯一一個感覺沒有歸屬感,而且一想到要分享自己真心相信的事,呼吸就會變急促的人。我們對於公開發言的不安全感,真正的根源其實在於「公開」這個詞,這是許多人共享的故事,屬於我們的母親、祖母以及所有特立獨行、格格不入的傢伙和夢想家的故事。億萬年前人們起草社會公約時,我們這些人沒有受邀參與,所以此刻互相關照,留意其他「落單者」,讓他們覺得受歡迎,讓他們更輕鬆地呼吸,是會有幫助的。允許自己想像我們都屬於同樣的群體,讓友情在你的臉頰上躍動,當你們目光交會時,或許你會看到自己的倒影,讓自己可以更輕鬆地呼吸。沒有任何力量比團結一心更能改寫過時傳統,讓我們為了彼此,鼓起勇氣去做。
節奏:為想傳遞的想法而呼吸
當美國副總統賀錦麗在2020年夏天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接受提名時,她的表現時而熱情,時而調皮。她很健談,有親和力,但在言談間同時兼具儀式感和使命感,她的演講很適合在「呼吸進階班」的課堂裡再次播放。她用「美國,你好!」來開場,在沒有嘈雜群眾的會議室裡,少了許多政治家在疫情前習慣仰賴的現場即時回饋。但在進一步發言之前,她還是深吸了一口氣──彷彿吸進了所有支持她走到今天這一步的人,彷彿吸進了屬於她的歸屬感。她大可以欺騙自己,在沒有呼吸支持的情況下繼續前進,但她沒有這樣做。「今晚有機會在這裡說話,我深感榮幸」她繼續說,到這裡又再重新深吸一口氣。她用停頓幫助自己回到中心,用呼吸提示一個又一個想法。
你可以稱之為節奏──但我不太關心計算過的節奏,我關心的是你能為想傳遞的想法而呼吸,為需要聽到這個想法的人而呼吸 這代表你必須用夠多時間活在當下,才能不斷觀察會場、觀察自己。有些語句必須在結束時保持沉默,好在你環視充滿期待的群眾時留白,讓意義在會場間迴盪、沉澱,甚至可能會需要一整輪的呼吸循環,吸氣,呼氣,說下一句話之前,再吸入一口氣。除了呼吸聲之外一片寂靜的會場,會營造出驚人的力量。但有些語句需要加快速度,因為速度本身就能賦予語句意義 通常是在演講即將結束,或論述即將告一段落,在你高奏凱歌、走向結論時。你可以透過更快、更有律動感的吸氣來達成這項目標。賀錦麗做到了以上一切:她有強烈存在感,配合每個想法的強度調節呼吸,賦予訊息應有的份量,她深刻而敏銳地活在當下。
如果我們能見賢思齊,為呼吸負起全責,就有機會完全展現自己,創造真正驚喜的時刻,擁有不斷前進的人生。反叛份子會深深吸氣;事實上,我相信我們必須在呼吸的支持下,才有力量反叛。深呼吸給我們力量,展現最好的自己,讓別人聽見、看見;深呼吸給我們力量,在可能尚未準備好接受我們的場合,完整展現人性,讓與會者看見自己缺少了什麼。而這種力量,就是改寫故事的力量。
因此,在探討聲音的本書第一章,我想探討的其實是聲音出現前的那個靜默時刻,是你即將步上舞台,告訴自己「呼吸!」的那一刻,卻發現自己聳肩或挺胸,結果不但沒有放鬆,反而更緊張;是在你拿起麥克風、環視會場的那一刻,你嘗試呼吸,身體卻因為慣性壓力或習慣,無法順暢呼吸的那一刻,或者是你憧憬不已、屏息以待,卻忘記要放鬆的那一刻。這一章會探討所有可能出錯之處,不過只要藉由小小的技巧,就能迅速修正調整。
用呼吸為自己打氣
「如果你不幫自己,誰會幫你?」我清楚記得當高中合唱團老師說這句話時,我有多想翻白眼,老師警告我們要吸進足夠的空氣,才能順利唱完樂曲。聽起來很俗氣,用呼吸為自己加油,用士氣為自己打氣,酔嗎?不過現在,我正式收回那個白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允許自己呼吸的程度,
與我們允許自己「相信我是值得的」之間,
存在著不同凡響的身心連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們允許自己呼吸的程度,與我們允許自己「相信我是值得的」之間,存在著不同凡響的身心連結,我的意思是值得擁有任何東西:更高的薪水、注意力、同情心、權力,正反兩面皆然。我們越能完整呼吸,就越有力量;我們感覺越有力量,就越能完整呼吸。如果我們能用呼吸和信念為自己打氣,我們就能改變世界。
有趣的是,在你和我呱呱墜地那一刻,我們完全清楚自己必須知道的,關於呼吸的一切,呼吸是嬰兒離開子宮後,第一件為自己做的有用的事。如果我們做得夠好,呼吸此刻仍是我們每天為自己所做的事之中最有用的。關於做得好,我的意思是像嬰兒一樣輕鬆自在地呼吸,在我們被世界規定應該怎麼做之前──說話音量應該多大,應該多輕柔,應該有多少存在感,應該隱藏多少力量。
在開口說話前好好呼吸,是我們每個人顯示為自己站起來(反之則是削弱自己)的最基本方式,透過這個動作,我們會對別人發出訊號,要他們也這樣做。如果賀錦麗副總統的呼吸短淺或Š 氣,讓自己的聲音卡喉嚨裡,那天晚上我們從她的演講收到的訊息,將會南轅北轍。如果那天晚上之前的幾年,她養成了呼吸短淺或Š 氣的習慣,我敢打賭,她根本就不會走上那座講台。如果你覺得我在說你,這不是你的錯,但是你有能力,而且必須要,掌控自己的呼吸。
表面上看起來,呼吸再簡單不過,畢竟,我們每天呼吸兩萬多次。事實上,在我們睡覺、跑步,或與朋友開懷大笑時,呼吸會平順流暢,身體會自然擴張,讓活動順利進行。但在更重要的時刻,當言語足以改變人生時──簡報、宣傳、提案、推銷,甚至在試著與伴侶或父母劃清界線時──所有一切都變得極不自然。從生物學的角度來說,我們的身體仍然像幾十萬年前祖先的身體一樣運作:當我們感到焦慮或察覺危險時,身體會釋放出大量荷爾蒙,促使呼吸變得既短淺又急促,以迅速把氧氣輸送到大腦,進而應對威脅。但這會削弱其他所有功能,我們專注對付威脅,腎上腺素和血流量大增,心臟怦怦作響到自己都聽得見,隨時準備好暴衝或逃跑。
公開說話會啟動原始「戰或逃」的本能
而在公開演講時,我們受到的威脅不再是針對我們身體的,而是來自那些來聽演講人,他們盯著我們,評判我們。即使在身體走完這個應對威脅的流程以後,那些人還在,只不過如今他們看到的,是一個越來越不像我們的版本;我們變成一個驚慌失措、面紅耳赤的冒牌貨,能做的只是勉強峅在台上,遑論達成目標。身體知道如何調動所有「戰或逃」的功能,來應對類似「眼前向我們撲來那隻熊」這種挑戰。做得好,身體!但是,如果我們想超越自己,在別人面前成為最大、最好、最強大的自己,就必須教會自己的身體完整地調動其他能力,與其說這是生物學上的要求,不如說是習慣上的。比方說,我們看待鎂光燈下的自己的方式,我們與聽眾建立的關係,我們為聽眾帶來的價值,以及我們在發言時常有的行為模式。
呼吸(Breath):好好呼吸才能好好說話
我願意被看見。
我願意發聲。
我願意繼續前進。
我願意傾聽別人怎麼說。
即使感到孤獨,我也願意繼續前進。
我願意在每晚上床睡覺時,與自己和解。
我願意成為最大、最好、最有力量的自己。
我被這七句話給嚇壞了。
但我知道,這些話是一切的關鍵。
──艾瑪.華特森(Emma Watson)
暫停片刻,就只深呼吸。有時是,在我們睡覺或處理日常事務時,規律進出的節奏;有時是伴隨著生活中的驚喜時刻所出現的──溫暖的身體接觸、美妙的話語、突然現身的朋友。節奏改變了,我們吸入比平時更多的空氣,這個動作是對新鮮事物的本能反應。那一刻,我對丈夫大聲讀出驗孕手冊上的說明,想弄清楚驗孕棒的標記代表的意思──但讀到一半就停下來喘了口氣。緊接而來的是充滿無限可能和全然脆弱的嘆息。呼吸,是進行中的生命。
不過,呼吸同時也代表另外一件事。近十年來,「我不能呼吸」一直是黑人控訴警察不當執法的口號,提醒了大家脆弱的氣管──或人類──多麼容易遭受不當對待。當新冠疫情來襲,「我不能呼吸」的哭訴聲,透過人類使用的各種語言,在世界各地的醫院中迴盪。為了避免生病,我們把自己與他人隔離開來,手住鼻子和嘴巴,避免自己的氣息擴散。聚集在公共場所,讓彼此的願望和靈感相互融合,成為一件危險的事。在美國封城的第一個週末,我記得自己坐在床上,拚命閱讀新聞,換氣過度,腦中想著,上帝啊,如今分享呼吸竟然可能代表死亡。
在這樣的脈絡下,無論是在稀鬆平常的時刻,或在令人驚訝的時刻,留意自己的呼吸不再是件小事。原本呼吸是件再簡單不過的事,有點像眨眼,會自動發生。但在風險變高時,呼吸卻變成最困難的事,因為透過呼吸,你會釋放出內在的感覺或想法,但卻不知道後果是甚麼。
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在公共場合分享自己的呼吸,向來都是危險的。對於我們這些看法前衛,忍不住質疑傳統的人來說,群眾從來都不曾無條件歡迎我們的感受或想法。我們一直受到威脅、毀謗和忽視,我們失去工作,像女巫般被公開審判,不被信任。對傳統掌權者以外的所有人而言,想要深吸一口氣,發表自己的看法,得先刪除數千年來「誰有資格公開發言、應該如何發言」的教條,打破由來已久的迷思。
大口呼吸,釋放自己
因為事實是這樣的:當你真實而完整的吸一口氣,這外來的空氣被吸在幾分之一秒後變成你的一部分──你的希望和夢想,你的憤怒和快樂,你所有的想望。當然,每個人都需要空氣來維持生命,但也都需要空氣來啟動自己的憤怒和喜悅,如果我們想改寫傳統,就得啟動這些情緒──來重塑「誰有資格公開發言、該如何發言」的迷思,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成為自己的英雄。我對你的期待是,在風險很高的情境下,你已經準備妥當,可以勇敢面對,大口深呼吸,釋放真實的自己。
不過,有時我們會察覺自己在所處場合中形單影隻──我們是唯一特定種族或酷兒群體的人,唯一的女人,唯一坐輪椅的人,唯一衣著鮮豔、穿二手衣,或明顯有孕在身的人,唯一說話有不同口音,或願意花錢做對的事的人。就像「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活動領袖塔米卡·馬洛里(Tamika Mallory)所說,有時候我們發現自己置身於不屬於自己的競技場,在那個時刻,我們會深深渴望縮小自己或隱藏差異,而讓自己消失的方法之一,就是屏住呼吸。
可是有時候,我們身處的場合的確需要整修──也許你躍躍欲試,想用重新設計的藍圖大展身手。我一次又一次目睹這樣的情景,在我指導過的客戶身上,在講台下隨處可見的局外人身上:我們帶著雄心壯志、過人膽識,宏大願景、堅定使命,準備好要征服全世界;可是後來,當我們站在想對抗的人面前時…我們屏住呼吸,把空氣擠進又擠出緊縮的喉嚨,用壓抑的姿態說話,聲音沙啞單調,聽起來無精打采。我們準備好要改寫這個迷思,但我們的聲音卻並未處於最佳狀態。也許長久以來,我們一直要求自己為應對這種窘境做足準備──缺乏歸屬感、不夠好、被誤解、被貶低或在噓聲中逃下台──以至於如今因為習慣而出現這種反應。結果,掌權者依然穩若泰山,屹立不搖。
我可以幫助你改掉這個習慣,目的是讓你獲得許可和勇氣,同時讓你重新熟悉自己的呼吸。你必須相信,真正相信你的身體屬於那裡,並且用真心誠意邀請自己走進讓你害怕的空間。這種信任需要練習,而我會提供一些技巧,協助你做到。
同時我也會提供一些看法,因為你並不孤單。你不是唯一一個感覺沒有歸屬感,而且一想到要分享自己真心相信的事,呼吸就會變急促的人。我們對於公開發言的不安全感,真正的根源其實在於「公開」這個詞,這是許多人共享的故事,屬於我們的母親、祖母以及所有特立獨行、格格不入的傢伙和夢想家的故事。億萬年前人們起草社會公約時,我們這些人沒有受邀參與,所以此刻互相關照,留意其他「落單者」,讓他們覺得受歡迎,讓他們更輕鬆地呼吸,是會有幫助的。允許自己想像我們都屬於同樣的群體,讓友情在你的臉頰上躍動,當你們目光交會時,或許你會看到自己的倒影,讓自己可以更輕鬆地呼吸。沒有任何力量比團結一心更能改寫過時傳統,讓我們為了彼此,鼓起勇氣去做。
節奏:為想傳遞的想法而呼吸
當美國副總統賀錦麗在2020年夏天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接受提名時,她的表現時而熱情,時而調皮。她很健談,有親和力,但在言談間同時兼具儀式感和使命感,她的演講很適合在「呼吸進階班」的課堂裡再次播放。她用「美國,你好!」來開場,在沒有嘈雜群眾的會議室裡,少了許多政治家在疫情前習慣仰賴的現場即時回饋。但在進一步發言之前,她還是深吸了一口氣──彷彿吸進了所有支持她走到今天這一步的人,彷彿吸進了屬於她的歸屬感。她大可以欺騙自己,在沒有呼吸支持的情況下繼續前進,但她沒有這樣做。「今晚有機會在這裡說話,我深感榮幸」她繼續說,到這裡又再重新深吸一口氣。她用停頓幫助自己回到中心,用呼吸提示一個又一個想法。
你可以稱之為節奏──但我不太關心計算過的節奏,我關心的是你能為想傳遞的想法而呼吸,為需要聽到這個想法的人而呼吸 這代表你必須用夠多時間活在當下,才能不斷觀察會場、觀察自己。有些語句必須在結束時保持沉默,好在你環視充滿期待的群眾時留白,讓意義在會場間迴盪、沉澱,甚至可能會需要一整輪的呼吸循環,吸氣,呼氣,說下一句話之前,再吸入一口氣。除了呼吸聲之外一片寂靜的會場,會營造出驚人的力量。但有些語句需要加快速度,因為速度本身就能賦予語句意義 通常是在演講即將結束,或論述即將告一段落,在你高奏凱歌、走向結論時。你可以透過更快、更有律動感的吸氣來達成這項目標。賀錦麗做到了以上一切:她有強烈存在感,配合每個想法的強度調節呼吸,賦予訊息應有的份量,她深刻而敏銳地活在當下。
如果我們能見賢思齊,為呼吸負起全責,就有機會完全展現自己,創造真正驚喜的時刻,擁有不斷前進的人生。反叛份子會深深吸氣;事實上,我相信我們必須在呼吸的支持下,才有力量反叛。深呼吸給我們力量,展現最好的自己,讓別人聽見、看見;深呼吸給我們力量,在可能尚未準備好接受我們的場合,完整展現人性,讓與會者看見自己缺少了什麼。而這種力量,就是改寫故事的力量。
因此,在探討聲音的本書第一章,我想探討的其實是聲音出現前的那個靜默時刻,是你即將步上舞台,告訴自己「呼吸!」的那一刻,卻發現自己聳肩或挺胸,結果不但沒有放鬆,反而更緊張;是在你拿起麥克風、環視會場的那一刻,你嘗試呼吸,身體卻因為慣性壓力或習慣,無法順暢呼吸的那一刻,或者是你憧憬不已、屏息以待,卻忘記要放鬆的那一刻。這一章會探討所有可能出錯之處,不過只要藉由小小的技巧,就能迅速修正調整。
用呼吸為自己打氣
「如果你不幫自己,誰會幫你?」我清楚記得當高中合唱團老師說這句話時,我有多想翻白眼,老師警告我們要吸進足夠的空氣,才能順利唱完樂曲。聽起來很俗氣,用呼吸為自己加油,用士氣為自己打氣,酔嗎?不過現在,我正式收回那個白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允許自己呼吸的程度,
與我們允許自己「相信我是值得的」之間,
存在著不同凡響的身心連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們允許自己呼吸的程度,與我們允許自己「相信我是值得的」之間,存在著不同凡響的身心連結,我的意思是值得擁有任何東西:更高的薪水、注意力、同情心、權力,正反兩面皆然。我們越能完整呼吸,就越有力量;我們感覺越有力量,就越能完整呼吸。如果我們能用呼吸和信念為自己打氣,我們就能改變世界。
有趣的是,在你和我呱呱墜地那一刻,我們完全清楚自己必須知道的,關於呼吸的一切,呼吸是嬰兒離開子宮後,第一件為自己做的有用的事。如果我們做得夠好,呼吸此刻仍是我們每天為自己所做的事之中最有用的。關於做得好,我的意思是像嬰兒一樣輕鬆自在地呼吸,在我們被世界規定應該怎麼做之前──說話音量應該多大,應該多輕柔,應該有多少存在感,應該隱藏多少力量。
在開口說話前好好呼吸,是我們每個人顯示為自己站起來(反之則是削弱自己)的最基本方式,透過這個動作,我們會對別人發出訊號,要他們也這樣做。如果賀錦麗副總統的呼吸短淺或Š 氣,讓自己的聲音卡喉嚨裡,那天晚上我們從她的演講收到的訊息,將會南轅北轍。如果那天晚上之前的幾年,她養成了呼吸短淺或Š 氣的習慣,我敢打賭,她根本就不會走上那座講台。如果你覺得我在說你,這不是你的錯,但是你有能力,而且必須要,掌控自己的呼吸。
表面上看起來,呼吸再簡單不過,畢竟,我們每天呼吸兩萬多次。事實上,在我們睡覺、跑步,或與朋友開懷大笑時,呼吸會平順流暢,身體會自然擴張,讓活動順利進行。但在更重要的時刻,當言語足以改變人生時──簡報、宣傳、提案、推銷,甚至在試著與伴侶或父母劃清界線時──所有一切都變得極不自然。從生物學的角度來說,我們的身體仍然像幾十萬年前祖先的身體一樣運作:當我們感到焦慮或察覺危險時,身體會釋放出大量荷爾蒙,促使呼吸變得既短淺又急促,以迅速把氧氣輸送到大腦,進而應對威脅。但這會削弱其他所有功能,我們專注對付威脅,腎上腺素和血流量大增,心臟怦怦作響到自己都聽得見,隨時準備好暴衝或逃跑。
公開說話會啟動原始「戰或逃」的本能
而在公開演講時,我們受到的威脅不再是針對我們身體的,而是來自那些來聽演講人,他們盯著我們,評判我們。即使在身體走完這個應對威脅的流程以後,那些人還在,只不過如今他們看到的,是一個越來越不像我們的版本;我們變成一個驚慌失措、面紅耳赤的冒牌貨,能做的只是勉強峅在台上,遑論達成目標。身體知道如何調動所有「戰或逃」的功能,來應對類似「眼前向我們撲來那隻熊」這種挑戰。做得好,身體!但是,如果我們想超越自己,在別人面前成為最大、最好、最強大的自己,就必須教會自己的身體完整地調動其他能力,與其說這是生物學上的要求,不如說是習慣上的。比方說,我們看待鎂光燈下的自己的方式,我們與聽眾建立的關係,我們為聽眾帶來的價值,以及我們在發言時常有的行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