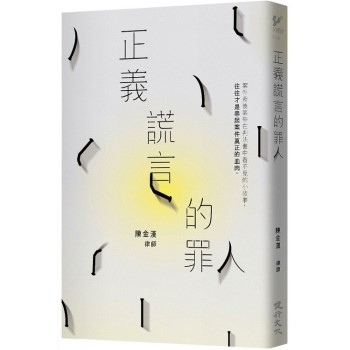空號
盛夏的午後,赤辣凶惡的豔陽高掛,馬路上熱氣蒸騰,路邊一攤攤的酸梅汁和愛玉冰也冰鎮不了這城市的燥熱,連呼吸的空氣都暗藏著一股令人窒息的憂鬱。
──
「警察局嗎?我叫魯平,我家住在板橋區金門街X巷X號X樓,我剛剛殺了人,請你們派人來處理。」
是個老人家的聲音。
「先生,請你講慢點,我們要詳細的記錄你……」
「嘟-嘟-嘟-」
沒等線上的女警把話說完,電話早已掛了。
女警覺得很奇怪,但還是按例通報附近警網前往察看究竟。
警方的報案專線,每天都會有幾通惡作劇的電話,但通常是小孩、醉漢或是精神病患,只要值班人員多問兩句,很容易就能分辨。
但這年頭,警察實在難為,不論是否謊報,警方可以瞎忙一場,但卻不容許有掛萬漏一的閃失,否則一經揭露,媒體絕不輕饒,他們總有本事把螞蟻浮誇成大象。立委諸公也會把芝麻綠豆的小事搬上國會殿堂,利用權力分立和免責權,點名署長和部長,藉質詢監督之名,行惡棍流氓之實,頤指氣使的掀桌、潑水和謾罵,竭盡所能的羞辱責難一番。
立委和媒體,始終都是這片土地上最有權力的亂源。
這會不會又是一次惡作劇?
兩位員警開著巡邏車,在路上各從口袋裡掏出了一百元當賭注。
老警員斬釘截鐵的斷定,這只是一件烏龍案。開車的菜鳥警員認為老人家報案,應該不會是開玩笑。這是他所能說服自己的合理推論,也是唯一的選項,因為資深員警享有猜賭的優先權,這是警界不成文的習慣。
──一進門,看見屋內景象,兩員警嚇出一身冷汗。
即使是資深老警員,看到眼前這一幕,心裡也直發毛,趕緊用無線電請求勤務中心調派附近警網及鑑識小組前來支援。
一屋明亮的燈火,把眼前這一幕照得更加驚悚慘白。
老人全身濺滿了鮮血,石像般地呆坐在餐桌旁,臉上染著疲憊,雙眼突白失魂,直盯著屍體。
老人一直沒說話,沒驚慌,沒理會員警,看不見情緒,安靜得令人毛骨悚然。
一旁沙發椅上,仰躺著早已氣絕身亡的老婦人,鐵釘鎚就掛在她正中的腦門上,頭額凹陷成一個大洞,帶髮的頭皮掀到一旁,將落未落地垂掛著,頭髮黑得有點不自然,顯然是染過的。髮間沾有幾點狀似麻婆豆腐的腦漿,鮮血順著髮端向後汲滴而下,像個滴漏的水龍頭。凹陷的臉使得五官嚴重形變模糊,前額的血順著左眼及凹陷的臉頰漫向整個左肩膀,再沿著還掛著點滴的左手臂,慢慢的滴落在地板上。
白磁磚把鮮血映得更加透明鮮紅。
命案現場,除了幾個鮮明的血腳印外,包括屋內客廳、房間、廚房、餐廳、陽台及花圃,所有擺設都相當整齊,並無凌亂打鬥的痕跡,門窗亦無破壞入侵的跡象。腦門上的大鐵鎚應就是凶器。研判客廳就是命案第一現場。
警方立刻封鎖現場,由鑑識小組進行仔細地採證,並以現行犯逮捕老人,將他押銬回板橋分局。
──
魯平,祖籍山東臨淄,民國十八年三月二十三日生,案發時已高齡八十三歲。
死者是魯老先生七十八歲的髮妻張季薇。
魯老先生在分局偵查隊待了快五個小時,沒吃沒喝也沒反應。
分局派出最資深的員警來訊問,老先生依然沉默,從頭到尾一語未發。
筆錄內容除了從老先生身分證上抄下來的個資外,其他一片空白,分局上下全都一籌莫展,案情毫無進展。
警方自我安慰,研判老先生可能驚魂未定,最後決定將他暫先拘留,隔天再續行調查。
第二天一早,警方再次前往魯家搜索,進一步細查其他所有相關的資料,尤其是保險單。
警方搜得魯平夫妻銀行的兩本帳戶,驚見帳戶中夫妻倆各有七百萬的鉅額定存,另有一份登記在魯先生名下的房產權狀,初步排除財殺。
警方同時也查出,老先生曾是國小教師,民國八十一年退休。
戶籍資料顯示,老夫妻育有一子,目前行方不明。
除此之外,並無任何其他突破性的進展。
老夫妻沒有手機,也查無任何往來的鄰居和親友,但有件事令警方驚奇不解。
根據魯老先生家用電話最近半年內的通聯記錄,總共撥出一百二十七通電話,但卻沒有任何一通電話撥入的記錄。更奇的是,撥出的電話都是相同的一個國際碼,依國碼可以判定,一百二十七通電話全都是打到美國。資料也顯示,所有一百二十七通電話的通話時間是零,其中最特別的是,有高達八十七通的電話是在案發前兩天所密集撥出。
警方覺得驚奇,試著重撥那個國際電話號碼,結果是――空號。
為何打了一百二十七通?誰撥打的?又是打給誰?為何是空號?
──
如果報案的老先生就是兇手,那他可能是台灣治安史上最高齡的殺人犯。
警方抱持懷疑的態度,他們甚至不排除行方不明的兒子或其他人涉案的可能性,但初判本案應是熟人所為。
警方請來里長,希望獲得更多的資訊,或者能讓老先生開口配合調查。但顯然沒有太大幫助,老先生依然不肯開口,里長對老先生也幾乎一無所知。
通常,時間越逼近法定移送時間二十四小時,警方就會越失耐性,某些極端的黑白臉戲碼就會在偵訊室裡開始上演,特別是一樁殺人重案。但,本案例外,因為他們面對的嫌犯,是個八十三歲的老人家。
──
里長聯絡我,要我到分局跟魯老先生談一談,希望對案情進展有幫助。
一開始,我有些為難,因為除非老先生當場同意委任,否則依法只有犯嫌的法代、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旁系血親、家長或家屬,可以獨立為犯嫌委任辯護人。但案件的膠著離奇,引發我潛在的興趣,於是我填好委任狀,趕往分局。
就一個老律師而言,要對案件保持高度熱誠和好奇心,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到達時,警方問魯老先生是否要委任律師?
魯老先生用眼角瞟了我一眼,表情不惡不善,隨即一語不發的低了頭。
員警無奈的對我搖搖頭,靜默的氣氛讓我感到有些尷尬。
我透過關係,找了分局裡一位有點熟的員警,概略的了解一下狀況。
我婉請警方法外施恩,考慮讓我和老先生私聊幾分鐘。
其實,除非魯先生願意立即委任我成為他的辯護律師,否則本案已進入偵查階段,在偵查不公開的原則下,私聊情況在實務上是絕對不被允許的,尤其是律師,常被警方視為麻煩的製造者。
──
「魯先生您好,我是陳律師。」
「很遺憾,發生了這種事,這只是一樁意外對吧?」
老先生依然不動如山,連看我一眼也沒有,詢問室壓迫而安靜,我幾乎能聽聞到老先生有點急促的呼吸聲。
「這是重大案件,雖然依法你享有緘默權,但你的沉默可能會讓事情越變越糟,最後還可能會被法院裁押禁見,關進看守所。」
「既然你是自己報案自首,顯然你已有面對法律的心理準備,你並不忌諱讓警方知道這件事,甚至希望警方能幫忙處理,我希望能為你提供一點法律上的意見和幫助,你願意和我談談嗎?」
任憑我唱足了獨腳戲,老先生依然沉默不語,像座哀愁的雕像。
「好吧!既然你甚麼都不願說,我也不勉強。但我必須強調,我雖然是律師,我們彼此也不認識,但我不是來賺錢的,甚至可以說,我也不是專程來為你辯護的,我只是對這樁案件感到十分的好奇,好奇它背後的故事。我的經驗清楚的告訴我,每滴眼淚都有它的故事,我只是想來這裡聆聽,聆聽一個老人家說說屬於他的故事和心酸而已。一切隨緣,不勉強。」
再一陣的沉默。
「這是我的名片,如果你改天需要的話。」
看來我是無計可施,只好將名片放在他面前,悄然起身。
離去時,我瞥見老人家眼角掛著淚花。
──
後來,檢察官的所有訊問,老先生唯一回答的問題就是他坦承殺死他的妻子,其他一律緘默,不做任何回答。當然也包括犯罪動機。
檢方懷疑老人家是否替人頂罪?也高度懷疑本案應有共犯?
毫無意外,本案檢方聲押獲准,但考量到老先生是自首和他的年紀,法院並未裁定禁見。
犯案動機,是檢察官在謀殺案中所必須徹查和了解的一部分,即使逮捕到兇手,兇手也坦承殺人,但如果沒查明真正的犯案動機,就一樁謀殺重案而言,也不能算是真正的破案。
然而,在實務上,縱使在欠缺動機情況下,檢察官依然可以依法起訴。通常檢察官都能從相關的證物資料中,合理的自推被告的犯案動機。但如果在一樁謀殺案中無法真正究明犯案動機或推斷錯誤,這對負責偵查起訴的檢察官而言,是莫大的打擊和恥辱,他們甚至會被標籤為不及格的檢察官。
一件刑案的犯案動機,密切牽繫著刑罰的罪責與人性善惡根源的判斷,是法官量刑最重要的依據之一。
──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魯老先生從看守所寄來的一封信,甚感意外。
他表示希望委任我當他的辯護人,但要求我必須遵照他所開出的條件,其中第一條就是:每周至少要到看守所律見兩次。
執業二十幾年,第一次碰到如此奇特的當事人,被告比辯護律師還強勢。
「魯先生,為何改變心意?」
律見時,不待獄警解開他的手銬我就開口急問著。
「律師,你不是說想聆聽一位老人家說說他的故事嗎?」
這是第一次聽到老先生開口,是相當流利而宏亮的山東腔,讓我微驚,他說話的語調帶有溫暖的感覺。
「喔!你願意告訴我?」
我故做質疑。
「只要你遵守我的條件,我願意詳詳細細地告訴你。」
「除了每周至少來這裡律見兩次外,還有甚麼別的條件嗎?」
我很好奇。
「首先,請律師把每次律見時我所口述的內容整理好,下次律見時讓我過目刪修,然後我再口述,你再整理,直到我把故事說完為止,就這麼簡單。」
老先生口吻傲然而肯定,似乎忘了他現在是個殺妻嫌犯。
「就這麼簡單嗎?既然是你自己的故事,為什麼你不自己寫?」
「我老了,視力差了,手也不太聽話,最重要的是,我思緒亂,需要有人陪我慢慢回憶。」
老先生思索了一下,口氣變得溫潤。
「你的回憶和本案有關嗎?」
「有關也無關。」
「這又怎麼說?如果是有關,為何不在法庭上說?」
「檢察官和法官會那麼耐心嗎?我曾當過證人,上過幾次法院,我很清楚,他們官大權力大,只挑他們結案想要的內容問,也只允許記錄和他們提問有關的內容而已,被告其餘的回答都被視為無關本案的廢話。有時他們不耐煩時,甚至還會疾言厲色的斥責制止,展示著他們莫大的官威。這你們當律師的應該比我還清楚。」
「言下之意,你是根本不相信司法?」
「當然不信。我一直搞不懂,一個連基本耐心都沒有的人,怎麼有資格配當檢察官和法官?」
「不相信司法的人又怎可能會相信律師?」
「當然也不相信。」
「為什麼?」
「因為律師往往會為了贏為了錢而不擇手段。」
個性直又白,讓我驚訝。
雖然他講的大多是實話,但身為一個律師,我還是不太喜歡當事人對司法和律師做些過度自以為是的批判。
「律師,我八十幾歲了,我是否罪該當死?不必等法官最後的判決,我心裡早已為我自己的人生下了最後的審判。我只需要有人陪我回憶,不需要別人來替我辯護,你可以接受我的委託,也可以拒絕,若你接受,請依照我的意思,可以嗎?」
老人家明知已挑起我的好奇心,語氣卻偽裝不耐。
我們對眼互視半晌,各自猜忖著對方的心思。
「我答應你,但我必須聲明在先,我也有權利隨時無條件解除我們之間的委任。」
「當然可以,沒問題。」
我原籍是大陸山東省臨淄人。
臨淄是春秋戰國時代的齊都,著名古城。
我懷念我的故鄉,但故鄉已遙遠。
當年,我就讀山東濟南市立第一師範學院二年級,某天半夜,突然被國民政府抓去充軍。從此,再也沒見過爹娘親友。那年,我只是一個才剛滿十八歲的小毛頭。
我本姓毛,在當年軍隊裡,這是一個很礙眼的姓,所以我一直謊稱自己姓魯。民國三十九年,我隨國民政府迫遷來台,在一次戶籍重整時,我就直接謊報姓魯。魯是山東省的簡稱,是想念也紀念我那回不去的故鄉。
來台第三年,我憑著師範肄業的學歷,在某國小謀得教職,同年也結婚了。
今年,我和我太太結婚剛好滿六十年,在鑽石婚紀念日當天,我決定殺了我太太。
其實,這幾十年來,我一直深愛我太太,因為深愛,所以選擇親手結束她的人生。這是我對她最後一次的好,卻只能好得這麼讓人心痛。
因為經濟上的因素,我們直到婚後第三年才敢生小孩。我們唯一的獨生子,名叫魯銘城,自幼聰穎絕倫,從小學到台大醫學院,都十分資優,特別是數理科目,更是出類拔萃,高中和大學聯考都是全國榜首。就我所知,這在台灣的聯考史上,這種雙榜首還是絕無僅有。至今我都還保留著當年大學聯考放榜時各大報紙的特刊剪報,特刊中有我兒子和我們夫妻倆三人的合照和簡介。
那照片,寫盡我們夫妻畢生的榮耀。
都已是四十幾年前的往事了,但從那早已泛黃的剪報中,我依然可以感受得到,當年的我是多麼地驕傲。
因為不能錄音,我只能埋首振筆疾書,深怕掛漏,但才一開場,老先生口述的內容,就深深吸引我,某些疑團在心中不斷的堆積和蔓延。
──我太太是苗栗南庄客家人。
當年,台灣社會對於我們這一輩的外省人,不論老少,你們都慣稱我們為「老芋仔」,這是一種語言文化差異下自然的歧視和隔閡。台灣女孩子會嫁給我們這種「老芋仔」,大多是非殘即貧的鄉下人。結婚後,她們也都會和我們一樣,或多或少同受某種程度的歧視或隔閡。
冷漠如牆,歧視是罪。
我太太嫁給我之後,就和老家的親友鮮少往來了。其實,除了學校少數同事外,我們夫妻幾乎沒有任何來往的親友。
從十八歲那年起,我就成了一個孤獨的流浪者。國民政府讓我有所依靠,但也讓我失去了原本所有心裡看不見的依靠。他們所給的,都不是我們想要的,而我們想要的,他們也已全都無法給。
我不喜歡這樣,奈何,時勢比人強。
很欣慰,在那顛沛的年代,在我人生孤寂的流浪路上,有我太太一路相陪。
盛夏的午後,赤辣凶惡的豔陽高掛,馬路上熱氣蒸騰,路邊一攤攤的酸梅汁和愛玉冰也冰鎮不了這城市的燥熱,連呼吸的空氣都暗藏著一股令人窒息的憂鬱。
──
「警察局嗎?我叫魯平,我家住在板橋區金門街X巷X號X樓,我剛剛殺了人,請你們派人來處理。」
是個老人家的聲音。
「先生,請你講慢點,我們要詳細的記錄你……」
「嘟-嘟-嘟-」
沒等線上的女警把話說完,電話早已掛了。
女警覺得很奇怪,但還是按例通報附近警網前往察看究竟。
警方的報案專線,每天都會有幾通惡作劇的電話,但通常是小孩、醉漢或是精神病患,只要值班人員多問兩句,很容易就能分辨。
但這年頭,警察實在難為,不論是否謊報,警方可以瞎忙一場,但卻不容許有掛萬漏一的閃失,否則一經揭露,媒體絕不輕饒,他們總有本事把螞蟻浮誇成大象。立委諸公也會把芝麻綠豆的小事搬上國會殿堂,利用權力分立和免責權,點名署長和部長,藉質詢監督之名,行惡棍流氓之實,頤指氣使的掀桌、潑水和謾罵,竭盡所能的羞辱責難一番。
立委和媒體,始終都是這片土地上最有權力的亂源。
這會不會又是一次惡作劇?
兩位員警開著巡邏車,在路上各從口袋裡掏出了一百元當賭注。
老警員斬釘截鐵的斷定,這只是一件烏龍案。開車的菜鳥警員認為老人家報案,應該不會是開玩笑。這是他所能說服自己的合理推論,也是唯一的選項,因為資深員警享有猜賭的優先權,這是警界不成文的習慣。
──一進門,看見屋內景象,兩員警嚇出一身冷汗。
即使是資深老警員,看到眼前這一幕,心裡也直發毛,趕緊用無線電請求勤務中心調派附近警網及鑑識小組前來支援。
一屋明亮的燈火,把眼前這一幕照得更加驚悚慘白。
老人全身濺滿了鮮血,石像般地呆坐在餐桌旁,臉上染著疲憊,雙眼突白失魂,直盯著屍體。
老人一直沒說話,沒驚慌,沒理會員警,看不見情緒,安靜得令人毛骨悚然。
一旁沙發椅上,仰躺著早已氣絕身亡的老婦人,鐵釘鎚就掛在她正中的腦門上,頭額凹陷成一個大洞,帶髮的頭皮掀到一旁,將落未落地垂掛著,頭髮黑得有點不自然,顯然是染過的。髮間沾有幾點狀似麻婆豆腐的腦漿,鮮血順著髮端向後汲滴而下,像個滴漏的水龍頭。凹陷的臉使得五官嚴重形變模糊,前額的血順著左眼及凹陷的臉頰漫向整個左肩膀,再沿著還掛著點滴的左手臂,慢慢的滴落在地板上。
白磁磚把鮮血映得更加透明鮮紅。
命案現場,除了幾個鮮明的血腳印外,包括屋內客廳、房間、廚房、餐廳、陽台及花圃,所有擺設都相當整齊,並無凌亂打鬥的痕跡,門窗亦無破壞入侵的跡象。腦門上的大鐵鎚應就是凶器。研判客廳就是命案第一現場。
警方立刻封鎖現場,由鑑識小組進行仔細地採證,並以現行犯逮捕老人,將他押銬回板橋分局。
──
魯平,祖籍山東臨淄,民國十八年三月二十三日生,案發時已高齡八十三歲。
死者是魯老先生七十八歲的髮妻張季薇。
魯老先生在分局偵查隊待了快五個小時,沒吃沒喝也沒反應。
分局派出最資深的員警來訊問,老先生依然沉默,從頭到尾一語未發。
筆錄內容除了從老先生身分證上抄下來的個資外,其他一片空白,分局上下全都一籌莫展,案情毫無進展。
警方自我安慰,研判老先生可能驚魂未定,最後決定將他暫先拘留,隔天再續行調查。
第二天一早,警方再次前往魯家搜索,進一步細查其他所有相關的資料,尤其是保險單。
警方搜得魯平夫妻銀行的兩本帳戶,驚見帳戶中夫妻倆各有七百萬的鉅額定存,另有一份登記在魯先生名下的房產權狀,初步排除財殺。
警方同時也查出,老先生曾是國小教師,民國八十一年退休。
戶籍資料顯示,老夫妻育有一子,目前行方不明。
除此之外,並無任何其他突破性的進展。
老夫妻沒有手機,也查無任何往來的鄰居和親友,但有件事令警方驚奇不解。
根據魯老先生家用電話最近半年內的通聯記錄,總共撥出一百二十七通電話,但卻沒有任何一通電話撥入的記錄。更奇的是,撥出的電話都是相同的一個國際碼,依國碼可以判定,一百二十七通電話全都是打到美國。資料也顯示,所有一百二十七通電話的通話時間是零,其中最特別的是,有高達八十七通的電話是在案發前兩天所密集撥出。
警方覺得驚奇,試著重撥那個國際電話號碼,結果是――空號。
為何打了一百二十七通?誰撥打的?又是打給誰?為何是空號?
──
如果報案的老先生就是兇手,那他可能是台灣治安史上最高齡的殺人犯。
警方抱持懷疑的態度,他們甚至不排除行方不明的兒子或其他人涉案的可能性,但初判本案應是熟人所為。
警方請來里長,希望獲得更多的資訊,或者能讓老先生開口配合調查。但顯然沒有太大幫助,老先生依然不肯開口,里長對老先生也幾乎一無所知。
通常,時間越逼近法定移送時間二十四小時,警方就會越失耐性,某些極端的黑白臉戲碼就會在偵訊室裡開始上演,特別是一樁殺人重案。但,本案例外,因為他們面對的嫌犯,是個八十三歲的老人家。
──
里長聯絡我,要我到分局跟魯老先生談一談,希望對案情進展有幫助。
一開始,我有些為難,因為除非老先生當場同意委任,否則依法只有犯嫌的法代、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旁系血親、家長或家屬,可以獨立為犯嫌委任辯護人。但案件的膠著離奇,引發我潛在的興趣,於是我填好委任狀,趕往分局。
就一個老律師而言,要對案件保持高度熱誠和好奇心,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到達時,警方問魯老先生是否要委任律師?
魯老先生用眼角瞟了我一眼,表情不惡不善,隨即一語不發的低了頭。
員警無奈的對我搖搖頭,靜默的氣氛讓我感到有些尷尬。
我透過關係,找了分局裡一位有點熟的員警,概略的了解一下狀況。
我婉請警方法外施恩,考慮讓我和老先生私聊幾分鐘。
其實,除非魯先生願意立即委任我成為他的辯護律師,否則本案已進入偵查階段,在偵查不公開的原則下,私聊情況在實務上是絕對不被允許的,尤其是律師,常被警方視為麻煩的製造者。
──
「魯先生您好,我是陳律師。」
「很遺憾,發生了這種事,這只是一樁意外對吧?」
老先生依然不動如山,連看我一眼也沒有,詢問室壓迫而安靜,我幾乎能聽聞到老先生有點急促的呼吸聲。
「這是重大案件,雖然依法你享有緘默權,但你的沉默可能會讓事情越變越糟,最後還可能會被法院裁押禁見,關進看守所。」
「既然你是自己報案自首,顯然你已有面對法律的心理準備,你並不忌諱讓警方知道這件事,甚至希望警方能幫忙處理,我希望能為你提供一點法律上的意見和幫助,你願意和我談談嗎?」
任憑我唱足了獨腳戲,老先生依然沉默不語,像座哀愁的雕像。
「好吧!既然你甚麼都不願說,我也不勉強。但我必須強調,我雖然是律師,我們彼此也不認識,但我不是來賺錢的,甚至可以說,我也不是專程來為你辯護的,我只是對這樁案件感到十分的好奇,好奇它背後的故事。我的經驗清楚的告訴我,每滴眼淚都有它的故事,我只是想來這裡聆聽,聆聽一個老人家說說屬於他的故事和心酸而已。一切隨緣,不勉強。」
再一陣的沉默。
「這是我的名片,如果你改天需要的話。」
看來我是無計可施,只好將名片放在他面前,悄然起身。
離去時,我瞥見老人家眼角掛著淚花。
──
後來,檢察官的所有訊問,老先生唯一回答的問題就是他坦承殺死他的妻子,其他一律緘默,不做任何回答。當然也包括犯罪動機。
檢方懷疑老人家是否替人頂罪?也高度懷疑本案應有共犯?
毫無意外,本案檢方聲押獲准,但考量到老先生是自首和他的年紀,法院並未裁定禁見。
犯案動機,是檢察官在謀殺案中所必須徹查和了解的一部分,即使逮捕到兇手,兇手也坦承殺人,但如果沒查明真正的犯案動機,就一樁謀殺重案而言,也不能算是真正的破案。
然而,在實務上,縱使在欠缺動機情況下,檢察官依然可以依法起訴。通常檢察官都能從相關的證物資料中,合理的自推被告的犯案動機。但如果在一樁謀殺案中無法真正究明犯案動機或推斷錯誤,這對負責偵查起訴的檢察官而言,是莫大的打擊和恥辱,他們甚至會被標籤為不及格的檢察官。
一件刑案的犯案動機,密切牽繫著刑罰的罪責與人性善惡根源的判斷,是法官量刑最重要的依據之一。
──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魯老先生從看守所寄來的一封信,甚感意外。
他表示希望委任我當他的辯護人,但要求我必須遵照他所開出的條件,其中第一條就是:每周至少要到看守所律見兩次。
執業二十幾年,第一次碰到如此奇特的當事人,被告比辯護律師還強勢。
「魯先生,為何改變心意?」
律見時,不待獄警解開他的手銬我就開口急問著。
「律師,你不是說想聆聽一位老人家說說他的故事嗎?」
這是第一次聽到老先生開口,是相當流利而宏亮的山東腔,讓我微驚,他說話的語調帶有溫暖的感覺。
「喔!你願意告訴我?」
我故做質疑。
「只要你遵守我的條件,我願意詳詳細細地告訴你。」
「除了每周至少來這裡律見兩次外,還有甚麼別的條件嗎?」
我很好奇。
「首先,請律師把每次律見時我所口述的內容整理好,下次律見時讓我過目刪修,然後我再口述,你再整理,直到我把故事說完為止,就這麼簡單。」
老先生口吻傲然而肯定,似乎忘了他現在是個殺妻嫌犯。
「就這麼簡單嗎?既然是你自己的故事,為什麼你不自己寫?」
「我老了,視力差了,手也不太聽話,最重要的是,我思緒亂,需要有人陪我慢慢回憶。」
老先生思索了一下,口氣變得溫潤。
「你的回憶和本案有關嗎?」
「有關也無關。」
「這又怎麼說?如果是有關,為何不在法庭上說?」
「檢察官和法官會那麼耐心嗎?我曾當過證人,上過幾次法院,我很清楚,他們官大權力大,只挑他們結案想要的內容問,也只允許記錄和他們提問有關的內容而已,被告其餘的回答都被視為無關本案的廢話。有時他們不耐煩時,甚至還會疾言厲色的斥責制止,展示著他們莫大的官威。這你們當律師的應該比我還清楚。」
「言下之意,你是根本不相信司法?」
「當然不信。我一直搞不懂,一個連基本耐心都沒有的人,怎麼有資格配當檢察官和法官?」
「不相信司法的人又怎可能會相信律師?」
「當然也不相信。」
「為什麼?」
「因為律師往往會為了贏為了錢而不擇手段。」
個性直又白,讓我驚訝。
雖然他講的大多是實話,但身為一個律師,我還是不太喜歡當事人對司法和律師做些過度自以為是的批判。
「律師,我八十幾歲了,我是否罪該當死?不必等法官最後的判決,我心裡早已為我自己的人生下了最後的審判。我只需要有人陪我回憶,不需要別人來替我辯護,你可以接受我的委託,也可以拒絕,若你接受,請依照我的意思,可以嗎?」
老人家明知已挑起我的好奇心,語氣卻偽裝不耐。
我們對眼互視半晌,各自猜忖著對方的心思。
「我答應你,但我必須聲明在先,我也有權利隨時無條件解除我們之間的委任。」
「當然可以,沒問題。」
我原籍是大陸山東省臨淄人。
臨淄是春秋戰國時代的齊都,著名古城。
我懷念我的故鄉,但故鄉已遙遠。
當年,我就讀山東濟南市立第一師範學院二年級,某天半夜,突然被國民政府抓去充軍。從此,再也沒見過爹娘親友。那年,我只是一個才剛滿十八歲的小毛頭。
我本姓毛,在當年軍隊裡,這是一個很礙眼的姓,所以我一直謊稱自己姓魯。民國三十九年,我隨國民政府迫遷來台,在一次戶籍重整時,我就直接謊報姓魯。魯是山東省的簡稱,是想念也紀念我那回不去的故鄉。
來台第三年,我憑著師範肄業的學歷,在某國小謀得教職,同年也結婚了。
今年,我和我太太結婚剛好滿六十年,在鑽石婚紀念日當天,我決定殺了我太太。
其實,這幾十年來,我一直深愛我太太,因為深愛,所以選擇親手結束她的人生。這是我對她最後一次的好,卻只能好得這麼讓人心痛。
因為經濟上的因素,我們直到婚後第三年才敢生小孩。我們唯一的獨生子,名叫魯銘城,自幼聰穎絕倫,從小學到台大醫學院,都十分資優,特別是數理科目,更是出類拔萃,高中和大學聯考都是全國榜首。就我所知,這在台灣的聯考史上,這種雙榜首還是絕無僅有。至今我都還保留著當年大學聯考放榜時各大報紙的特刊剪報,特刊中有我兒子和我們夫妻倆三人的合照和簡介。
那照片,寫盡我們夫妻畢生的榮耀。
都已是四十幾年前的往事了,但從那早已泛黃的剪報中,我依然可以感受得到,當年的我是多麼地驕傲。
因為不能錄音,我只能埋首振筆疾書,深怕掛漏,但才一開場,老先生口述的內容,就深深吸引我,某些疑團在心中不斷的堆積和蔓延。
──我太太是苗栗南庄客家人。
當年,台灣社會對於我們這一輩的外省人,不論老少,你們都慣稱我們為「老芋仔」,這是一種語言文化差異下自然的歧視和隔閡。台灣女孩子會嫁給我們這種「老芋仔」,大多是非殘即貧的鄉下人。結婚後,她們也都會和我們一樣,或多或少同受某種程度的歧視或隔閡。
冷漠如牆,歧視是罪。
我太太嫁給我之後,就和老家的親友鮮少往來了。其實,除了學校少數同事外,我們夫妻幾乎沒有任何來往的親友。
從十八歲那年起,我就成了一個孤獨的流浪者。國民政府讓我有所依靠,但也讓我失去了原本所有心裡看不見的依靠。他們所給的,都不是我們想要的,而我們想要的,他們也已全都無法給。
我不喜歡這樣,奈何,時勢比人強。
很欣慰,在那顛沛的年代,在我人生孤寂的流浪路上,有我太太一路相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