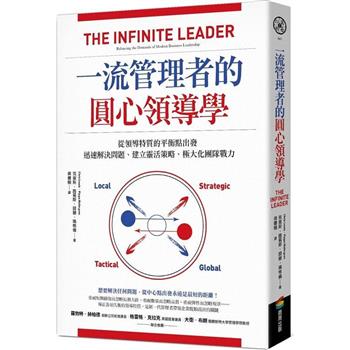▎體認到問題
我們都認識一些好的領導者,甚至有些是偉大的領導者,他們都正直誠實、有勇氣且有智慧,他們廣納百川,他們改變了很多人的生活,他們認真思考,他們連點成線。現代最出色的領袖之所以出色,是因為他們研究過表現最差的那一群。研究失敗案例可能會讓某些人很意外,認為在這方面耗時間很奇怪,但多數的領導者會告訴你,他們從失敗當中學到的比成功更多。事實上,很多進步都是因為失敗讓人產生了改變的動機。
我們之前列出的災難性事件有哪些共同之處?是因為缺少了符合專業資格、受過大學教育的領導者嗎?不是。那,為什麼他們的領導者沒有注意到發生什麼事?是資訊太多還是太少導致他們分心了?他們知道自己正在做錯的事嗎?他們沒有想像力,才看不到相關的效果嗎?他們覺得自己無法大聲把話說出來嗎?他們覺得自己能逃得過後果嗎?這些組織的規模有造成部分影響嗎?領導這些組織的主要是中年男子,這一點重要嗎?如果資深職位上有更多女性,這些女性會不會同樣落入男性文化,開始有同樣的行徑?科技扮演什麼角色?有明顯的模式嗎?
領導人都有明確的動機和決心,但是重點是他們用來做錯的事,或者說,至少是刻意忽略對的事。這些現象並非偶然,起因也並非什麼單一事件。無論這些人是不是故意,無論在日後重構時來看是不是很明顯,這都是很糟糕的領導,幾乎每一個方面都失衡。我們要研究的,就是這些失衡的地方。且讓我們來看看其中一些。
▎變動速度快──沒有能力平衡過去與未來
就算在最好的情況下,變動的速度都比領導更快。從文化面、技術面以及地緣政治面來看,領導者和他們領導的機構已經無力招架變化。
這使得「經濟理性主義」(economic rationalism)大行其道,體現經濟理性被視為領導的單一目標,就算要犧牲符合道德的行為也在所不惜。回過頭來,這給了我們「最高級的」(而不是「更好的」)經濟。最大的就最好。如果領導限於經濟理性主義的架構,永遠都只能達成次佳狀態,因為領導者永遠會選擇追求量化標準,放棄質化標準。
▎資訊過度負載──沒有能力平衡資訊
在一個執著於當下的時代,過去不受尊重,被人隨意打發,只有當前才重要。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變化?這可以直接追溯到智慧型手機,以及大量的干擾和數據引發的嚴重分心與資訊過度負載。一般人一天會收到四十封郵件,假設每天的工作時數是八小時、或者說四百八十分鐘,那麼,我們每十二分鐘就會被人打擾一次。
除了前述的失調之外,我們還要接收數量比以往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資訊,而這也很可能是造成失調的原因之一。資訊太多了,讓我們變得盲目,看不到眼前核心的明顯事實。在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及時娛樂的吸引力遠高於事實。即便事實就擺在眼前,我們的眼睛就像蒙上一層霧一樣,看不到大局的奧祕。
我們還要來談談知識加倍曲線(knowledge doubling curve)。知名的工程師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發現,到了二十世紀,資訊與人類知識的數量以指數成長。他注意到,二十世紀之前,人類的知識大約每二百五十年就會倍增,一九○○年之後,開始變成每一百年便會倍增。到了二次大戰末期,知識每二十五年便會倍增。到了一九八二年,富勒估計,人類知識每年就增加一倍(見圖1.2)。IBM說, 現在,知識每十二小時就增加一倍。
加入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裝置之後,本來已經快到非比尋常的資訊流速度會更快。知識倍增曲線有助於解釋為何人們會覺得焦慮:因為追不上。沒有人閱讀的速度快到能接收所有新資訊,更別說要弄明白當中的意義了。
用誰說的來決定哪些資訊有用、哪些沒有,不用去查核資訊的原出處,這樣簡單多了。有些人認為,如果消息出自民主黨或CNN,那就很可信,有些人則把目標放在共和黨和福斯新聞網(Fox News) 。回到一九六○年代末期,媒體理論宗師馬素.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就預見到了這股資訊潮,預言資訊過度負載會讓我們更往同溫層靠攏。
現今的領導人必須理解,人們愈來愈少真正去理解什麼事。現代人愈來愈不在意事實,也不再講究要整理出周延的意見。信念是更重要的形塑意見因素,超越邏輯。資訊應是流動的,像過程一樣,如果不是,資訊就變成單一的事件。我們需要分析與平衡資訊流,讓資訊流照亮前路,而不是讓視野變得模糊。
▎不用承擔後果— 做錯事的人不用受懲罰
通常代表正義的符號是天秤。結果要公平,要能平衡兩邊。
就算在最好的情況下,我們也只能說目前的領導顯然失衡,而且不只在地層級是這樣,連在全球舞台上的最高階之處也是如此。領導者犯罪不用下獄,表現不佳顯然也不用受到任何制裁。在二○○九年的金融危機中,沒有任何銀行家因為職務而入獄,多數銀行就是從之前停下來的地方再出發就是了。
這種事本身就很奇怪。政治領袖一定明白,新的溝通環境條件幫了他們大忙,提供了協助;在新環境中,人們喜歡煽情鼓動勝過溫和謙恭,喜歡大聲勝過安靜,喜歡騙子勝過說實話的人。政治領導者為何不想讓引發這麼多困境的人接受大眾檢核?是因為懲戒要花太多時間嗎?是因為顯然無法讓這些人洗心革面了嗎?是因為與魔鬼做了交易,考量長期的經濟益處勝過短期的政治利得嗎?
銀行家自我開脫,把信貸危機說成「信貸海嘯」(credit tsunami),說得好像這是老天爺做的,不在他們控制的範圍內。除非有人負責掌控全球的經濟流動,不然要央行體系有何用?這能歸咎於缺乏想像力嗎?事實一直都在眼前,比方說吧,倒掛的殖利率曲線與房貸違約率。某些企業家倒是解讀的很正確。
或許就像美國作家厄普頓.辛克萊(Upton Sinclair)所說:「如果一個人要靠著不理解才能領到薪水,那就很難要他去理解。」
有些人可能會說,檢驗一套系統是否有道德,最好的辦法就是讓系統受制於相反的行為,然後看看系統會不會自行修正。法國已故的政治學家亞歷西斯.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將會樂見在他的作品問世一百五十年後還有人會去討論與驗證。
如果不考慮領導失敗會嚴重衝擊我們生活的每一個面向,包括政治委任與國會民主,這種實驗在學術上還蠻有意思的。當全世界愈來愈緊繃,政治上卻又沒有相關經驗,領導在此時失敗,時機可謂糟到不能再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