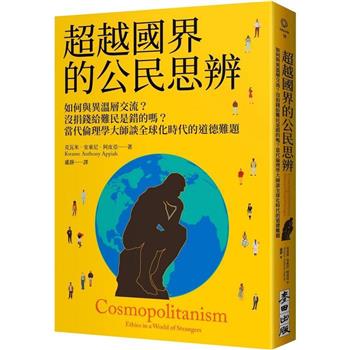第四章
道德分歧
穿越厚重,搜索輕薄
想見識價值分歧,你不需要離家千萬里。在散場的電影院外面,就有觀眾覺得《登峰造擊》拍得比《尋找新方向》好,但她的朋友卻嗤之以鼻:「這部片說四肢癱瘓的人活著毫無價值,如果她想要,你就應該殺了她欸,你怎麼會覺得這種電影比較好?」另一邊的酒吧剛發生一場鬥毆,人們熱烈討論著剛才的事,有人說勸架的旁觀者很勇敢,也有人說他太魯莽了,應該報警才對。在討論墮胎的課堂上,一名學生表示,懷孕初期墮胎對母親和胎兒都不好,但墮胎應該要成為母親的合法選擇。有個學生則認為,殺死胎兒的嚴重性,甚至比不上殺掉成年的貓。第三個同學卻說墮胎就是謀殺。如果我們希望鼓勵世界性的交流,開啟不同社會的之間的道德對話,我們就該預期到會有這些分歧──畢竟就連社會內部都免不了這類分歧。
但道德衝突有很多種形式。首先,我們的評價語彙非常繁多,而且就像哲學家常說的一樣,有些評價用詞,比如「好」或「應該」,都十分輕薄(thin)。這些字眼代表贊同,但用法卻有點過於靈活:好土壤、好狗狗、好論證、好主意、好人。知道這些詞的意思,並不會讓你知道該怎麼使用。當然,有些行為無論如何都跟好扯不上關係。這不僅是因為「好」這個詞的涵義中,原本就沒有內建這種行為,也是因為你無法理解要怎麼贊同這些事;比如說,搶飢餓孩童的食物就絕不是好事。
不過,大部分的評價語詞都比這「厚重」(thick)得多。如果要使用「粗魯」的概念,你一定是先認為要批評的行為欠缺良好的行止儀表,或是沒有適當關心他人的感受。比方說如果你是不小心踩到我的腳,我卻諷刺地對你說「謝謝」,暗示你是故意的。這樣就很粗魯。但如果我絲毫沒有諷刺的意思,只是單純感謝另一個人為我做的事,這樣就不粗魯。另一個例子是「勇敢」,這通常是用來稱讚人的詞彙。但它的意義比「對」或是「好」等輕薄的詞彙更具體:要表現出勇敢,你需要做一些我們會覺得有危險的事,這種行為很可能讓你會失去某些東西。當然,如果你有廣場恐懼症,或是知道按門鈴的是祕密警察,那光是打開家門就非常勇敢了。
輕薄的概念就像占位用的包包。正確、錯誤這些觀念,只有與特定社會環境的複雜性層層交織,才會真正發揮作用。正如美國政治理論大師麥可‧瓦哲(Michael Walzer)所言,道德從一開始就是厚重的。或者也可以說,當你想要找出跟別人的共識,就是準備從層層的厚重概念底下,抽出隱藏的輕薄概念。
輕薄的概念似乎都是普世性的;世界上有對與錯、好與壞等概念的不只有我們,每個社會都有和輕薄概念相對應的字眼。就連粗魯和勇敢這些厚重的概念,也幾乎普遍見於世界上每一個地方。但還有一些更厚重的概念,確實是專屬於特定社會的。當討論中有一方援用了另一方根本沒有的概念時,就會出現根本性的分歧。但是在這種分歧中,爭吵並不是為了達成共識,而是為了理解彼此。
家庭的重要性
不過有時候,我們熟悉的價值,也會以我們不熟悉的風俗習慣表現出來。好比說,全世界的人都認為應該對自己的子女負責。但誰是自己的子女?我同時成長於迦納的阿肯社會和我母親那邊的英語世界,兩邊對家庭的看法就很不一樣。雖然由於幾百年來的接觸,兩個社會的差異或多或少一直在不斷縮小。但還是有些重大的差異沒有消失。
阿肯人的「母族」是指一群有共同祖先的人,我們彼此之間有愛、也有義務;大致上來說,人與人之間的共同祖先愈近,彼此的牽絆就愈強烈,也就是愈接近一個家庭。然而,母族和西方家庭之間有一個關鍵的差別:是不是母族成員,取決於你的母親是誰,跟父親完全無關。如果妳是女性,那妳的子女就是母族的一員,而妳女兒的後代也是,她們女兒的後代也是,直到時間終結都是。母族的成員資格就像粒線體DNA一樣,只透過女性傳遞。所以我和我姊姊的孩子們處於同一個母族,但跟我哥哥的孩子們不在同一個母族。而且,由於我跟父親的血緣沒有透過女性連結,他也不是我的母族成員。
簡單來說,阿肯文化中的家庭,就是人類學家所說的母系。一百年前,英國人期待父親扮演的角色,在大多數阿肯人的生活中,都是由年紀較長的舅舅(wɔfa)來扮演。他要負責確保姊妹的孩子(wɔfase)能夠吃飽穿好並接受教育。許多已婚婦女會跟自己的兄弟住在一起,並定期拜訪她們的丈夫。當然,男人也會想接近自己的孩子,但他對孩子的義務相對沒有那麼高──或者說,就跟英國人的舅舅一樣。
如果你是外地人,到迦納應該會很驚訝,因為人們最習慣用來稱呼兄弟姊妹的字眼「nua」,同時也可以用來稱呼母親姊妹的孩子。人們有時會用迦納英語跟你說,某某某是「我同父同母的妹妹」,而你可能會覺得這說明也太多餘了(如果有人告訴你,某個女性是他的「小媽」,那麼他指的是他母親的妹妹)。
但是到了我小時候,這一切都開始變了。愈來愈多男人和自己的妻子兒女住在一起,沒有養育姊妹的孩子。但我父親還是會收到他姊妹小孩們的學校報告,要寄零用錢給他們,跟他們母親討論他們的學業,並支付母族家裡的帳單。他也常和他最親的姊妹一起吃飯,而他的妻子兒女(也就是我們)則自己在家一起吃飯。
這就是家庭組織的差異。哪一種對你來說比較合理,很大程度是取決於你在成長過程中接受了哪些觀念。在我看來,一個社會只要能夠有效分配養育兒童的責任,並且講得出一番道理就夠了;至於要說誰是正確的,其他方式都是錯的,那實在很奇怪。西方人認為父親不扶養子女是錯的。但阿散蒂人,特別是過去的阿散蒂人,卻會覺得如果有小孩沒有得到撫養,那錯的人應該是舅舅。一旦你了解這個制度,就很可能會承認它,而且這不是需要你放棄任何基本的道德認知。因為這兩者都符合良好養育的價值,而良好養育雖然輕薄,卻是普世性的價值,只不過這些價值觀在每個社會,都有相當特殊、符合當地習俗和期望,並與社會安排緊密交織的呈現方式。
週三的紅辣椒
但還有其他一些在地價值觀可能會違反你心目中重要的觀念。例如,我的父親不會吃「叢林肉」(bush meat),也就是叢林裡獵來的動物。這其中也包括鹿肉,他曾經告訴我們,有一次他在英國不小心吃到鹿肉,第二天皮膚上就長了疹子。不過,如果你問他為什麼不吃叢林肉,他不會說不喜歡,也不會說是因為過敏。如果他認為有必要,他會跟你說這是他的「akyiwadeε」,因為他屬於叢林水牛(Ekuona)氏族。從詞源學上來說,「akyiwadeε」的意思是「你應背向的東西」,如果一定要翻譯的話,或許可以說是「禁忌」。話說回來,禁忌的英語「taboo」也是從玻里尼西亞語傳進來的,原本是指某些群體中的人應極力避免的一類事物。
就像在玻里尼西亞一樣,在阿散蒂如果做了這些應背向的事,就會讓人「受到污染」,但也有各種補救措施和「淨化」自己的方式。西方人雖然也有厭惡感和淨化自己的欲望,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真的有「akyiwadeε」的概念。因為這是一個厚重的概念,如果要有這種概念,首先必須先認為某些事情不該做,是因為你屬於某個氏族,或是順服於某個神明,因此必須遵守這個禁忌。這樣,你才會說叢林水牛氏族的成員不吃叢林肉是有某種道理的。因為從象徵意義上來說,氏族動物是你的親戚,因此對你來說,吃牠(和牠的親戚)就有點像吃人。不過,氏族成員也只能成為不吃叢林肉的理由,而在傳統的阿散蒂社會裡,無法以這種方式理解的akyiwadeε實在太多了。一九二○年代,殖民地政府的人類學家拉特雷上尉(Captain Rattray)曾提到一個叫「埃丁喀拉」(Edinkra)的地方神祇;這位第一個大量書寫阿散蒂傳統的學者提到,埃丁喀拉的禁忌之一,是週三不能接觸紅辣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