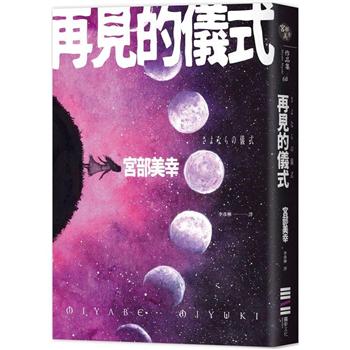母親的法律
咲子媽媽去世的時候,我並沒有哭泣。三個月前,主治醫師告訴憲一爸爸「繼續治療只會增添媽媽的痛苦」,爸爸決定停止對媽媽施打「希克羅辛」。我和一美兩人哭了整晚,心裡早有覺悟。
媽媽在人生走到盡頭前的大約八十天,都住在一棟名為「Cosmos」的安寧中心裡。這裡的外觀雖然是帶有昭和時期復古風格的西式紅磚建築,內部卻有著最新設備,看護人員也都相當優秀。我想媽媽應該走得平靜安詳。庭院裡種滿了當季的繽紛花朵,從每一間房間的窗戶都欣賞得到。每天的清晨及傍晚,都有各式各樣的野鳥聚集在小水池邊。運氣好的話,還可以看見可愛的野生松鼠。
舉行守靈夜儀式的那天晚上,當時媽媽所住的那個樓層的主任也到場了。閒聊的時候,他告訴我們「Cosmos」這個詞有兩個意思。一個是花名,也就是「大波斯菊」,另一個意思則是「宇宙」,安寧中心取這個名字是基於後者的意思。即將啟程前往天國的病患,以及圍繞在身邊的親友們,在那裡形成了一個小小的宇宙。
「咲子小姐就像是劃過了宇宙的美麗彗星。」主任這麼說。
我也這麼覺得。咲子媽媽真的很美。不只人美,心也美。
我是在四歲又七個月的時候,成為咲子媽媽的女兒。媽媽當時三十四歲,和憲一爸爸結婚第十年,家裡已經有了九歲十個月的翔,以及五歲半的一美。我加入之後,家裡變成了五個人。爸爸及媽媽擁有第一級的收養資格,可以收養新生兒,他們卻收養了配對名單裡排在較後面的我。
「我一看見妳的臉,聽見妳的聲音,就決定不再考慮其他孩子了。」
根據憲一爸爸的說法,當初領養翔及一美的時候,也是靠著媽媽的這種「一見鍾情」而決定的。
「媽媽的眼光很好,絕對不會看錯,所以爸爸很安心。事實證明媽媽果然沒有看錯,對吧?」
正如同爸爸所說的,在我加入後的十二年之間,我們一家人相處得和樂融融。正因為如此,即便我早已知道這個家會因為失去咲子媽媽而瓦解,我還是無法阻止自己感到悲傷。
當養父母因為離婚或喪偶而恢復單身時,必須將未成年的養子、養女送回「大家庭」。這是《受虐兒保護及養育特別措施法》(俗稱《母親法》)中明定的基本原則。在我出生的二十多年之前,這套法律剛實施沒多久的時候,就算養父母因為離婚或喪偶而只剩下一人,只要當事人提出訴願並獲得「母親制度管理委員會」核可,養子女就可以繼續住在寄養家庭裡。但後來發生了好幾起醜聞,因此這個「網開一面」的做法被取消了。
咲子媽媽生前對於委員會這種不通人情的做法感到相當不滿。她認為從前導致單親寄養家庭遭拆散的那幾起醜聞裡,有一些根本是冤枉了當事人,甚至是有人刻意捏造了假新聞。
「每個養父母都通過嚴謹的心理測驗,而且受過長時間的教育,怎麼可能一失去伴侶,就對養子女犯下性虐待的惡行?」媽媽常這麼說。
不管是政府還是母親委員會,都對養父母太不信任了。為什麼他們不能對自己訂下的制度抱持更大的自信?很少口出怨言的媽媽,曾經這麼向憲一爸爸抱怨。當時是三更半夜,而且他們正在喝葡萄酒,或許媽媽有點醉了。
面對媽媽的義憤填膺,憲一爸爸只能面露苦笑。
「我認為妳說得很有道理,但這世間有很多人並不這麼認為。委員會堅持拆散單親寄養家庭,主要的原因或許不是防止虐待,而是化解這社會上對養父母的偏見。說起來,這也是保護我們身為養父母的人。」
爸爸與媽媽郎才女貌,他們一起喝葡萄酒的模樣,美得有如一幅畫。那天晚上我沒有睡覺,躲在暗處偷偷看著他們,內心不禁為身為他們的女兒而感到驕傲。
沒想到四年後,媽媽舊疾復發。糾纏著媽媽的惡性新生物,在媽媽年輕時奪去了她的子宮,卻還意猶未足,不肯放過媽媽。媽媽最後敗給病魔,我們一家人也注定拆散。
《母親法》號稱是足以拯救全國受虐兒於水深火熱的奇蹟之法。在科學家已研究出惡性新生物的發生機制之後問世的分子標靶藥物「希克羅辛」,也號稱是能夠全面遏止惡性新生物繼續蔓延的奇蹟之藥。但不管是《母親法》還是「希克羅辛」,都還沒有辦法解決所有問題。
或許以後會更加完美吧。我只能這麼說服自己。
媽媽的喪禮結束後,一美與我便打包了行李,在一個月的緩衝期間結束前,搬進了當地的「大家庭」。基於憲一爸爸及我們的個人意願,我們保留了憲一爸爸的姓氏。但是以社會的角度來看,我們的戶籍已歸屬於母親委員會。
一美十七歲,二葉(就是我)十六歲。雖然我們是只差一歲的姊妹,但根據「大家庭」的規定,十三歲以上的兒童皆是住在單人房裡。「大家庭」是委員會專門提供給無寄養家庭的養子女居住的生活據點,而我們姊妹所入住的「大家庭」是由附近的數個地方政府共同經營,所以收容的兒童相當多(根據「大家庭」的規定,養子女在擁有正當職業且能獨力生活之前,都會被視為「兒童」,這也是讓我很不滿的一點)。建築物本身是老舊的公營住宅改建,方便性及安全性都不錯,唯一缺點是天花板太低。即使內部裝潢及家具再怎麼漂亮,過低的天花板也會給人舊時代的感覺。
翔由於已經成年了,所以並沒有與我們同住,而是住進了遠方某大學的學生宿舍。搬家的那天,他特地犧牲了假日,來幫我們整理房間。
「根本沒有什麼行李,何必大老遠跑來?」
「我就是放心不下妳們。」
哥哥很像媽媽,我們姊妹則是像爸爸。從小常有人對我們這麼說。當然那僅限於不知道我們是根據《母親法》住進寄養家庭的養子女。然而翔長大後,變得跟憲一爸爸愈來愈像。像的不是五官,而是動作、習慣及說話的用字遣詞。
至於一美及我,則是既不像爸爸也不像媽媽。我們跟翔也不像,甚至我們姊妹之間也不像。即使如此,在外人的眼裡,我們還是像親子,像兄妹,像姊妹。據說雖然我們的臉孔完全不同,但散發出的氛圍及一些小動作有幾分神似。
當人與人生活在一起,互相包容、互相幫助及互相體諒,自然而然會開始出現相似之處。受到細心照顧的孩子,會吸收細心照顧自己的雙親的各種優點,變得愈來愈像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因此親子之間到底有沒有血緣關係,其實影響不大……不,應該說是幾乎毫無影響。
翔的眼神中流露出了些許的寂寞,他對我們說道:
「我們永遠都是兄妹。」
「當然。」我回答。
咲子媽媽去世的時候,我並沒有哭泣。三個月前,主治醫師告訴憲一爸爸「繼續治療只會增添媽媽的痛苦」,爸爸決定停止對媽媽施打「希克羅辛」。我和一美兩人哭了整晚,心裡早有覺悟。
媽媽在人生走到盡頭前的大約八十天,都住在一棟名為「Cosmos」的安寧中心裡。這裡的外觀雖然是帶有昭和時期復古風格的西式紅磚建築,內部卻有著最新設備,看護人員也都相當優秀。我想媽媽應該走得平靜安詳。庭院裡種滿了當季的繽紛花朵,從每一間房間的窗戶都欣賞得到。每天的清晨及傍晚,都有各式各樣的野鳥聚集在小水池邊。運氣好的話,還可以看見可愛的野生松鼠。
舉行守靈夜儀式的那天晚上,當時媽媽所住的那個樓層的主任也到場了。閒聊的時候,他告訴我們「Cosmos」這個詞有兩個意思。一個是花名,也就是「大波斯菊」,另一個意思則是「宇宙」,安寧中心取這個名字是基於後者的意思。即將啟程前往天國的病患,以及圍繞在身邊的親友們,在那裡形成了一個小小的宇宙。
「咲子小姐就像是劃過了宇宙的美麗彗星。」主任這麼說。
我也這麼覺得。咲子媽媽真的很美。不只人美,心也美。
我是在四歲又七個月的時候,成為咲子媽媽的女兒。媽媽當時三十四歲,和憲一爸爸結婚第十年,家裡已經有了九歲十個月的翔,以及五歲半的一美。我加入之後,家裡變成了五個人。爸爸及媽媽擁有第一級的收養資格,可以收養新生兒,他們卻收養了配對名單裡排在較後面的我。
「我一看見妳的臉,聽見妳的聲音,就決定不再考慮其他孩子了。」
根據憲一爸爸的說法,當初領養翔及一美的時候,也是靠著媽媽的這種「一見鍾情」而決定的。
「媽媽的眼光很好,絕對不會看錯,所以爸爸很安心。事實證明媽媽果然沒有看錯,對吧?」
正如同爸爸所說的,在我加入後的十二年之間,我們一家人相處得和樂融融。正因為如此,即便我早已知道這個家會因為失去咲子媽媽而瓦解,我還是無法阻止自己感到悲傷。
當養父母因為離婚或喪偶而恢復單身時,必須將未成年的養子、養女送回「大家庭」。這是《受虐兒保護及養育特別措施法》(俗稱《母親法》)中明定的基本原則。在我出生的二十多年之前,這套法律剛實施沒多久的時候,就算養父母因為離婚或喪偶而只剩下一人,只要當事人提出訴願並獲得「母親制度管理委員會」核可,養子女就可以繼續住在寄養家庭裡。但後來發生了好幾起醜聞,因此這個「網開一面」的做法被取消了。
咲子媽媽生前對於委員會這種不通人情的做法感到相當不滿。她認為從前導致單親寄養家庭遭拆散的那幾起醜聞裡,有一些根本是冤枉了當事人,甚至是有人刻意捏造了假新聞。
「每個養父母都通過嚴謹的心理測驗,而且受過長時間的教育,怎麼可能一失去伴侶,就對養子女犯下性虐待的惡行?」媽媽常這麼說。
不管是政府還是母親委員會,都對養父母太不信任了。為什麼他們不能對自己訂下的制度抱持更大的自信?很少口出怨言的媽媽,曾經這麼向憲一爸爸抱怨。當時是三更半夜,而且他們正在喝葡萄酒,或許媽媽有點醉了。
面對媽媽的義憤填膺,憲一爸爸只能面露苦笑。
「我認為妳說得很有道理,但這世間有很多人並不這麼認為。委員會堅持拆散單親寄養家庭,主要的原因或許不是防止虐待,而是化解這社會上對養父母的偏見。說起來,這也是保護我們身為養父母的人。」
爸爸與媽媽郎才女貌,他們一起喝葡萄酒的模樣,美得有如一幅畫。那天晚上我沒有睡覺,躲在暗處偷偷看著他們,內心不禁為身為他們的女兒而感到驕傲。
沒想到四年後,媽媽舊疾復發。糾纏著媽媽的惡性新生物,在媽媽年輕時奪去了她的子宮,卻還意猶未足,不肯放過媽媽。媽媽最後敗給病魔,我們一家人也注定拆散。
《母親法》號稱是足以拯救全國受虐兒於水深火熱的奇蹟之法。在科學家已研究出惡性新生物的發生機制之後問世的分子標靶藥物「希克羅辛」,也號稱是能夠全面遏止惡性新生物繼續蔓延的奇蹟之藥。但不管是《母親法》還是「希克羅辛」,都還沒有辦法解決所有問題。
或許以後會更加完美吧。我只能這麼說服自己。
媽媽的喪禮結束後,一美與我便打包了行李,在一個月的緩衝期間結束前,搬進了當地的「大家庭」。基於憲一爸爸及我們的個人意願,我們保留了憲一爸爸的姓氏。但是以社會的角度來看,我們的戶籍已歸屬於母親委員會。
一美十七歲,二葉(就是我)十六歲。雖然我們是只差一歲的姊妹,但根據「大家庭」的規定,十三歲以上的兒童皆是住在單人房裡。「大家庭」是委員會專門提供給無寄養家庭的養子女居住的生活據點,而我們姊妹所入住的「大家庭」是由附近的數個地方政府共同經營,所以收容的兒童相當多(根據「大家庭」的規定,養子女在擁有正當職業且能獨力生活之前,都會被視為「兒童」,這也是讓我很不滿的一點)。建築物本身是老舊的公營住宅改建,方便性及安全性都不錯,唯一缺點是天花板太低。即使內部裝潢及家具再怎麼漂亮,過低的天花板也會給人舊時代的感覺。
翔由於已經成年了,所以並沒有與我們同住,而是住進了遠方某大學的學生宿舍。搬家的那天,他特地犧牲了假日,來幫我們整理房間。
「根本沒有什麼行李,何必大老遠跑來?」
「我就是放心不下妳們。」
哥哥很像媽媽,我們姊妹則是像爸爸。從小常有人對我們這麼說。當然那僅限於不知道我們是根據《母親法》住進寄養家庭的養子女。然而翔長大後,變得跟憲一爸爸愈來愈像。像的不是五官,而是動作、習慣及說話的用字遣詞。
至於一美及我,則是既不像爸爸也不像媽媽。我們跟翔也不像,甚至我們姊妹之間也不像。即使如此,在外人的眼裡,我們還是像親子,像兄妹,像姊妹。據說雖然我們的臉孔完全不同,但散發出的氛圍及一些小動作有幾分神似。
當人與人生活在一起,互相包容、互相幫助及互相體諒,自然而然會開始出現相似之處。受到細心照顧的孩子,會吸收細心照顧自己的雙親的各種優點,變得愈來愈像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因此親子之間到底有沒有血緣關係,其實影響不大……不,應該說是幾乎毫無影響。
翔的眼神中流露出了些許的寂寞,他對我們說道:
「我們永遠都是兄妹。」
「當然。」我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