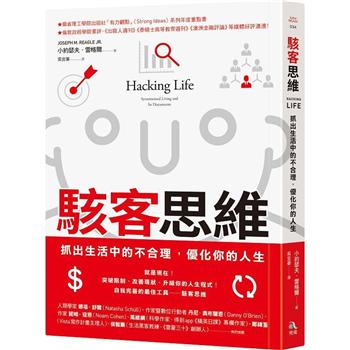【內文連載】
〈1 序章〉
馬克.里特曼的家是個由感測器和控制器組成的網絡,大量數據在他的房子、身體和車庫的伺服器之間傳輸。門、動作和溫度感測器監測著周圍環境,iPhone和健康手環則時時窺伺著他,一切都被記錄下來以便分析;只要簡單對Siri提出要求,就能控制燈光、溫度和音樂。
里特曼最新入手的小玩意是智慧水壺iKettle,他希望Siri能幫他泡杯茶,甚至還想把泡茶加入早晨的自動化行程:戴在手上的健康手環一旦發現里特曼醒了,就會提醒房子打開暖氣和樓下的燈,還能在他洗完澡前把水燒開。但里特曼一直沒辦法設定好水壺,他在推特與成千上萬名追蹤者分享這段歷程:
「三個小時過去了,我還是沒喝到茶。強制再校正導致無線基地臺重置。」好不容易設定好了,水壺卻無法與其他設備相容:「為了讓Siri控制水壺,我只好駭進系統,把這些功能整合起來。」他繼續在推特上分享這個過程,等到終於成功時,這個故事已經傳遍了全球—首先是《衛報》的一篇報導:「一名英國人花了十一個小時,試圖用智慧水壺泡一杯茶。」
這個案例完全展現出所謂的駭客心態,也就是對系統工作的熱情(偶爾會過度迷戀)。不過且讓我們想像堅守在科技以外的另一種駭客:
哈柏在打折時買了同樣的智慧水壺,花了幾個週末對它進行一番整頓,但最後得出一個結論:這東西沒救了;更糟的是收據不見了。幸好,還有另一種駭客手段。哈柏記得「生活駭客」網站上的一篇文章〈沒收據也能退貨—幾乎所有商品都適用〉。哈柏選擇做最後一次努力:再放幾個星期,等聖誕節過後再去退貨。儘管可能要排很久的隊,但此時商店通常會比較寬容。
里特曼是個大數據分析師與自我追蹤者,他之所以能成功解決問題,是因為他了解智慧家電背後的技術系統。而哈柏之所以能成功地在沒有收據的情況下退貨,是因為他了解另一個不同的系統,也就是購物季的動態系統。
我們可以從這兩種駭客技巧中看出,過去十年裡,駭客思維已擴及生活各層面,並廣泛應用於各種技術系統,以快速巧妙地解決問題。生活駭客追蹤或分析自己的飲食、財務、睡眠、工作,甚至包括頭痛。他們分享如何有效率地綁鞋帶、打包行李、尋找約會對象,以及學習語言的各項技巧。
提到「駭客」,許多人馬上會聯想到穿著帽T、埋首電腦前的犯罪者,這或許會讓人們對以上所描述的一切感到驚訝,但這些行為確實符合「駭客」一詞的原義。六十年前,麻省理工學院的鐵路模型愛好者用「hack」一字來形容快速修復「此系統」(火車月臺底下的電線和繼電器網路)的方法。駭客們熱衷於探索、構建和操縱這些系統。
今天,生活駭客涉及的領域除了科技、文化,還包括工作、財富、健康、人際關係,以及其他意義更廣的範圍。這是駭客思維的展現,是具系統化與實驗性的個人主義和理性方法。舉例來說,某些自稱「生物駭客」的人正在嘗試「消弭老化工程策略」,從這個名稱看得出來,這些人確實信心滿滿。 隨著科技不斷發展(尤其是各種能串連感測器的應用程式),這種駭客思維陸續出現在生活中許多從未「駭」過的領域。除了延長壽命,還有提高生產力、獲得物質滿足、達到最佳健康狀態、尋找戀愛對象與性伴侶……等系統。
生活駭客是一種生活方式,也是一種自我成長的途徑。考慮到自身的「怪癖」,我對它的優點確實很能感同身受,但也對它的缺點感到憂心。然而,這些擔憂並非源於生活駭客是外星人或邪教成員。之所以會出現生活駭客,是因為有其天時地利:當生活變得越來越像一個可以管理與建構的系統時,所有人都能藉此獲得一些幫助。
*二十一世紀的勵志新潮流
芸芸眾生中的你,只要擁有正確的態度和行動,就能躋身成功人士。至於該如何做到,只需要從四萬五千多本已出版的勵志書中挑一些來看就行了。大多數人就是這麼做的,如果把影音媒體、電視購物和個人教練算在內,這類市場總值約在五億到一百億美元之間。
生活駭客是自我成長史上最新的一頁,隨著成功的定義改變,人們給出的建議也隨之不同。我們是否仍像一八九○年代那樣,認為神能幫助我們成功?還是像一九三○年代的經典勵志書一樣,只要效法那些成功致富的人就行了?或是在當今資訊過剩的世界中,採納那些占一席之地的頂尖極客所分享的祕訣?史蒂芬.史塔克(Steven Starker)在《超市裡的甲骨文:美國人對勵志書的癡迷》一書寫到,勵志書反映了它們的社會文化背景,揭示了該時代的個人需求、願望和恐懼。正如《紐約客》雜誌在一篇有關費里斯的專訪中提到,每個世代都有專屬於它的勵志大師。
生活駭客是最新的勵志典範,且兩者都是所謂「實踐哲學」的延續。與學院派的哲學不同,實踐哲學關注生活中哪些是有價值的,以及如何認知它,是生活的哲學。若說斯多噶主義和儒學是古代的實踐哲學,那麼生活駭客就是當代的。例如,你可以透過控制自己每天花在回覆電子郵件上的時間(方法),來提高工作效率(目的)。
在美國文化中,勵志是一種很普遍的實踐哲學。正如史塔克所寫的:「我認為,美國的個人主義幾乎是所有勵志素材的泉源。」他也認為,勵志/自我成長是美國機會主義、自力更生和成功決心的一種表現。一位為《紐約》雜誌撰寫文章的文化評論家指出,「自《窮理查年鑑》出版以來,勵志文化—企業家精神、實用主義、強烈的自力更生、淡薄的靈性……已深深根植於美國人的DNA中」。
雖然「勵志」這個詞首見於蘇格蘭作家塞繆爾.斯邁爾斯(Samuel Smiles)那本獲利豐厚的同名書籍(一八五九年出版),但這個詞就跟蘋果派一樣,一開始雖是從歐洲輸入的詞語,如今卻已和美國文化密不可分;而生活駭客已然成為這塊「勵志派」的一部分。
在開始新的冒險之前,吉娜.特拉帕尼出版了三本取材於生活駭客的書;費里斯編纂了五本暢銷書、經營一個受歡迎的部落格,並主持一個有大量聽眾的播客,且都是以「一週工作四小時」這個品牌進行的。另外還有六位作者出版了關於極簡主義的書籍,包括《極簡富足:我靠一百樣東西過一年》和《會留下來的一切》。
當然還有更多關於生活駭客的書籍並未得到主流讀者的青睞,但儘管它們是獨立出版或只發行電子書,在網路書店上還是有數十則評論。我甚至曾在附近雜貨店的收銀處看過一本生活駭客雜誌,也看過國家地理頻道的節目《駭客智多星》。 生活駭客是極客們勵志成長的一種延續,現已成為主流。個人主義、務實、創業精神……等價值觀,以及克服障礙的無窮能力,都是這種精神的核心。生活駭客還加入了系統化思維、樂於實驗、喜愛科技,這些都很適合數位網路世界──一個充斥著系統和小工具的世界。
有些人可能覺得生活駭客就像勵志書一樣,很難視為正經嚴肅的事情;各種小技巧可被視為瑣碎小事;而生活方式的重新設計,則可以被當成《騙術》一書的老調重彈。但這種特色正是生活駭客的魅力所在:系統化精神的背後,既接納了世俗的駭客行為,也包含對人生更高遠的追求。
企業家保羅.布赫海特(Paul Buchheit),谷歌員工編號第二十三、Gmail的首席開發者,也是谷歌早期座右銘「不作惡」的創造者,他相信駭客是生活的「應用哲學」。他曾表示,有系統的地方,就有遭駭客入侵的可能,而到處都是系統。整個現實世界就是個有系統的系統,延伸到各個角落。
當然,並不是每個人都有駭客心態,畢竟社會需要各種不同的個性,但擁有這種心態的人,就是那些能跨越業種、統治權,甚至宗教來「改變世界」的人。對布赫海特來說,駭客行為比電腦中那些聰明的代碼更重要,也更偉大──這是我們創造未來的方式。
布赫海特的信念具有煽動、簡化和集大成的特性,就如同許多勵志方法所採用的前提。而正如史塔克所觀察到的,這些信念很容易讓批評者表現出不屑,以搖頭、瞬間冷笑、高傲的微笑和善意的忽視為回應。然而勵志書是我們文化結構的重要組成,它無所不在且影響深遠,以致無法忽視也不容輕忽,當然值得研究,生活駭客也是如此。
*生活駭客的五十道陰影
對布赫海特來說,任何系統都受制於兩套規則:覺得事物該如何運作的感知規則,以及現實中的實際規則,這正是駭客的力量所在。他認為,在大多數複雜系統中,這兩套規則的差距非常大。有時我們得以瞥見真相,發現某個系統的實際規則;一旦知道實際規則,就有可能發揮「奇蹟」──做出違反感知規則的事。例如,一名電腦駭客可以利用程式正常預期行為與現實中緩衝區溢位(簡單來說,就是指針對程式設計缺陷,塞入超過緩衝區所能容納的資料,破壞程式執行、趁機取得程式甚至是系統的控制權)之間的差距上下其手(例如針對目標電腦輸入惡意程式碼)。當然,駭客攻擊不只限於電腦。
在討論電腦駭客時,人們經常使用老電影裡的一個比喻:針對同樣的系統弱點,白帽駭客會修復它,黑帽駭客會惡意地利用它,灰帽駭客則介於兩者之間:他們可能會在未經允許的情況下進入系統,卻幾乎不會造成傷害。哈柏決定在聖誕假期結束後將智慧水壺退貨,就是種淺灰色駭客的行為。如同里特曼和其他人發現的,想讓智慧水壺透過無線網路正常運作並不容易,因此,在沒有收據的情況下退貨雖然違反了規定,倒似乎沒那麼惡質。
但如果哈柏使用同樣的技巧,卻選擇把東西退給另一家商店,好拿到未折扣價的退費呢?這等於哈柏詐欺了第二家商店,比起當初購入的特價,他能拿到更多現金,這下子他的帽子顏色變得更深了。
生活駭客網站〈沒收據也能退貨──幾乎所有商品都適用〉一文出現在萬聖節前的「邪惡週」主題底下。該網站的編輯們寫道,這樣的貼文雖然有點半開玩笑,卻反映出知識就是力量,至於用這種力量行善或作惡,取決於你自己。邪惡有時情有可原,甚至可以幫助你對抗邪惡:學習如何破解密碼,可以教你強化安全措施;更加了解謊言和操縱,讓你有能力看穿這類策略──或在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情況下使用它們。
這種理由聽起來幾乎可說是權術至上,還顯露出某種技術傾向和個人主義的心態。但一件事究竟是好是壞,不僅取決於個人。要理解這一點,我們可以用另一個問題代替道德的絕對性:要到什麼程度,才能分辨一名生活駭客有害或有益?又是對誰而言?接下來,我們會經常回到這個問題。
沒有收據就退貨的駭客行為顯然是出於對個人利益的關注,但如果哈柏把智慧水壺拿到他當初購買的商店去退、拿回與當時同樣的金額,並沒有所謂的傷害可言。只是如果每個人都使用這個方法,會變得怎樣呢?
這個問題就是康德所謂「定言令式」的一個例子:只做你希望每個人都做的事。第一種情況是,把一只無法使用的智慧水壺退回原購買商店、拿到跟當初購買時同樣的金額,這是無害的;但如果每個人都這麼做,世界將因此變得更糟。這種行為本身就帶有詐欺的意味,店家也會因此採取更加嚴格的退貨政策,反而會傷害到其他消費者。
康德的定言令式將道德考慮的範圍擴展到個人之外。我們可以問,如果一項駭客技巧是普遍的,也就是如果每個人都這麼做,這方法還能持續有效嗎?它有益嗎?這世界會因此變得更好嗎?
讓我們看看現實生活中的案例。鮑伯,萬宙商信(Verizon)的一名開發人員,被發現把自己的工作外包給一家中國公司。包括軟體開發人員在內,許多美國員工都對公司把業務發包給海外公司感到焦慮,覺得這可能導致自己遭到裁員。鮑伯也把工作外包出去,但仍保住自己的飯碗。他把兩成工資付給別人,換來每天上網看貓咪影片的日子。他把公司業務變成自己的優勢,駭進了這個系統。
很顯然,鮑伯的駭客行為是出於自身利益,也並非普遍。它之所以有用,因為這是暗中進行的單一案例。這項行為有可能傷害他人,鮑伯的不誠實使雇主身處風險之中;它無法通過康德的檢視,因為我們不會希望這種不誠實的行為是普遍的。
還有一些生活駭客技巧可能在無意中傷害使用者和他人。想想高生產力駭客技巧與整型手術的相似之處吧。在個人層面上,整型手術是一種能提高生活品質的自我提升法。它可能會出錯,使事情變得更糟;而且表面的強化,只能暫時緩解深層需求,形成一個不斷干預卻永遠無法獲得滿足的惡性循環。 普遍來說,我們很難斷言整型手術對所有人是好還是壞,生活駭客也是如此,尤其論及自我提升的社會涵義時,情況又會變得更加複雜。增強的動力通常是社會性的,也就是說,一旦開始推動,標準就會不斷提高,反而使得滿足感越來越遙不可及。一個人變美後,會讓其他人覺得自己更醜。
有些提高生產力的技巧相當有效:提高產能的關鍵,是排定工作的優先順序,而不是把行程表塞爆。有些技巧是行不通的:喝大量的水然後憋尿,應該可以讓你更專注,事實上卻有可能讓你更分心。而且就像某些手術一樣,有些會讓情況變得更糟,有些則永遠無法讓人滿意。塞爆行程表是一項錯誤,而且生產力再怎麼提升都永遠嫌不夠。到最後,生產力的提高反而讓每個人都被迫面對更多要求,包括生產力的再提升。
這些都是數位時代的陰影。在這個時代裡,人們進行廣泛的互動、各種設備無所不在,並有許多科學問題等待解決;此外,我們可以遠端工作、家事外包、追蹤和測試生活中的每一項指標(從心率到發送出去的電子郵件)。藉由思考鮑伯這樣的案例,我們可以確定人們認為值得的事物中蘊含著哪些固有價值,以及這麼做的有效性及後果。
〈3 時間駭客〉
*把我的生產力變四倍
二○一二年,曼尼什.塞提(Maneesh Sethi)終於成功變身網路名人。這位部落格格主請人在他工作效率不高時打他巴掌。當然,很多人之所以追蹤他,是因為難以置信,但這個噱頭發揮了支點的作用。這是他努力行銷自己的巔峰,就像費里斯一樣,成為一名生活方式設計企業家。這讓他開啟了自己的未來,決心開發一款令人驚嚇的小玩意。而他的故事也成為一個案例研究──關於對剝削的注意。
四年前,也就是二○○八年,塞提還是史丹佛大學的學生,當時他讀了費里斯的《一週工作四小時》,覺得它實在太振奮人心,不但只花了幾個小時就讀完全書,還買了前往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機票。正如他所說的:「我意識到,只要遵循費里斯的想法,自己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他離開學校,開始創立沒有辦公室的事業、環遊世界、接受非凡挑戰,並教其他人如何做同樣的事情,成為「一週工作四小時」的大師。
當然,和費里斯一樣,塞提並不是一個星期只工作四(或零)個小時,甚至連「半」退休也算不上。再說,就算有費里斯的粉絲參加你的派對,難道就能讓你成為有名的DJ嗎?塞提不斷旅行、四處享樂,卻也為了成為生活方式和行銷大師忙碌不已。塞提正努力獲得與費里斯和哥哥拉米特(Ramit Sethi)一樣的成功──塞提的哥哥是《我教你變成有錢人》一書的作者。
塞提致力於推銷暢銷勵志書,包括費里斯的《廚藝解構聖經》(這本書有提到塞提),以及一些關於飲食和女性「荷爾蒙治療」的書籍。最著名的是二○一二年,他從分類廣告網站上僱用了一名女性,當他被臉書分散注意力時,她就會打他巴掌。
「我要徵求一個人,到特定的地點(我家或咖啡館)在我身旁工作,要確定能看到我的電腦螢幕。只要我浪費時間,就吼我一下;必要的話,甚至打我巴掌都可以。可同時做自己的工作。徵求助手,越快越好。地點鄰近灣區捷運第十六街站。時薪八美元,期間可用自己的電腦做自己的事。」
塞提聲稱這個噱頭讓他的生產力變成四倍,並在部落格上分析記錄了這項進步。然而,即使意志力外包的成本低於最低工資,難道不能使用某種小工具達到同樣目的、讓成本更低嗎?
二○一四年,塞提推出了「帕夫洛夫」手環,概念來自於帕夫洛夫的制約理論,手環會產生微小電流,幫助使用者克服壞習慣。這個想法大受歡迎,在募資平臺上募到了超過二十八萬美元,是最初目標的五○八%。以前的做法是在手腕套個橡皮筋,然後彈自己一下,好擺脫不想要的想法或習慣。一條橡皮筋,拉起來再鬆開就會弄痛你,手環則是會電你一下。雖然相較之下橡皮筋是免費的,但塞提相信這個兩百美元的小玩意物有所值。「帕夫洛夫」結合了感應器、朋友和GPS,能讓你好好走在邁向目標的軌道上。比方說,不論當你把手伸到嘴邊(咬指甲或吃零食)、去最喜歡的速食店,或是在臉書花太多時間,它都會電你。此外,塞提還開了一門有關改掉壞習慣的線上課程,宣稱想馬上徹底戒掉某個習慣的人當中,成功率大約是五%;使用橡皮筋的,成功率是二五%;至於使用「帕夫洛夫」的人,大約有五五到六○%的人都成功了。
塞提用盡一切可能的方法,透過報紙、播客和部落格,向費里斯所謂的「新富」企業家推銷帕夫洛夫手環,這個小玩意甚至被美國深夜檔政治諷刺節目《柯柏報告》拿來嘲諷──這個節目可說是衡量大眾關注度的實用量表。還有一次非常珍貴的機會,是他在二○一六年時參加美國廣播公司的創業實境秀節目《創智贏家》,但他的提案並沒有被接受。其中一名評審說他是個靠花招行騙的人,而在塞提拒絕對他最具好感的投資者提出的交易後,又發生了更糟糕的事:有人說他去上節目只是為了推銷自己的產品,不是為了獲得額外的資金。對於費里斯和塞提這樣的生活駭客騙子,批評他們自私自利的聲音並不少見。
我們將在下一章繼續認真研究動機駭客。但對塞提行為的評論,讓我們回到這一章開始時,對富蘭克林的高生產力所提出的問題。當生活駭客試著充分利用時間時,他們究竟視什麼為理所當然?說得更準確一點,生活駭客的行為何時會變成剝削?
*特權和剝削
二○一二年,塞提寫了一篇〈性醜聞技巧〉,內容有關如何立刻實現各種目標(並與費里斯開派對),他指責其他人自以為擁有某些權利:如果你覺得,只因自己上了大學、努力讀書、拿到好成績和學位,就表示自己應該得到一份工作,那就錯了。有成千上萬的人都是這樣。所以他問:是什麼讓你與眾不同?更何況,與任何美國大學畢業生相比,還有其他國家的人會為了更少的錢更努力工作。
「告訴你們一個故事,是我一位菲律賓員工的故事。我僱用克拉克來幫我養成一個習慣:每天早上十點,他要打電話提醒我用牙線潔牙。
「有一天,我在十點三十二分時收到了一則訊息。『抱歉,曼尼什先生(克拉克總是叫我『先生』,就算我告訴他別這樣叫我),我遲到了,真的很抱歉。我們這裡被颶風襲擊,整個村子都沒有電!我得跑十幾公里到隔壁村子,才有辦法打電話給你!』
「你會只為了提醒我用牙線而跑十幾公里嗎?我給克拉克的薪水是每小時兩美元(但在此事之後,我給了他一大筆獎金),但你呢?你做了什麼來提升自己的價值,讓雇主願意付十到二十倍的薪水給你?」
想當然耳,塞提的回答是「侵入系統」:「達到目標的最短路徑,不是透過做其他人正在做的事情,反而多半是要做完全相反的事情。」為了在柏林成為DJ,他舉辦了許多派對;為了提高知名度,他建立了自己的播客,採訪其他更有名的生活駭客。
然而,在塞提教導別人「權利謬論」的同一篇文章中,他提到自己花錢請一名菲律賓人提醒他使用牙線。追求效率是值得稱讚的,就算做過頭,也還有機會重新評估目標和優先順序的有效性。然而正如富蘭克林的生產力端賴於妻子和奴隸等被忽視的勞動,外包也同樣依賴其他人的勞動成果。若是本地的工作,勞動將由零工經濟來完成,例如優步司機。這些人的工作靈活度高,獲利卻很少,其中更有許多人很快就會被自動化取代。至於那些可以遠端完成的工作,則會由迫切需要收入的外國人來執行。
儘管業主所提供的工作可能是低階的,但以誠實的態度來回應這種需求或許是一種美德。費里斯指出:「我把工作外包給印度人,有些人又會把部分工作再外包給菲律賓人。這是資本的有效利用,如果你想要自由市場的回報、想要享受資本主義制度的回報,這些就是必須遵守的規則。」但這什麼時候會變成剝削呢?什麼時候規則是不公平的?這正是自動化和全球化的雙面刃。
有效、自由且靈活,具備這些前提和承諾的系統,才會被生活駭客接納。將大企業的外包方法用在個人身上,確實是一種駭客技巧,卻也承繼了企業的道德過失。儘管塞提善良又隨和,但在颶風過後,克拉克是否能放一天假,先幫助家人、保留自己的時間,而不是把時間拿來換兩美元?還是因為他的家庭非常依賴這份薪水,所以他別無選擇,只能跑十幾公里,好提醒塞提用牙線?
同樣的,人們假設勞工可以選擇要做穩定的正職或富有彈性的計時工作,但零工經濟的從事者中,已處於邊緣、別無選擇的人卻越來越多。這樣看來,生產力駭客有時似乎在為那些會遭企業制度濫用的東西喝采。塞提推出了據說能糾正壞習慣的手環,四年後,亞馬遜為類似的東西申請了專利──針對拿錯貨品的倉庫員工。值得慶幸的是,亞馬遜的提案裡並沒有包括電擊裝置。但在那些能自己選擇制度與能要求他人實施該制度的人之間,存在著一種令人不安(即使是巧合)的互惠關係。
〈5 物品駭客〉
*從太多到極簡
關於自己與家當的關係,生活駭客會講的故事有兩種,第一種是關於他們認為不可或缺的裝備和工具,第二種則是他們如何擺脫其他的一切。約書亞.密爾本(Joshua Millburn)和萊恩.尼克迪穆(Ryan Nicodemus)是朋友,他們後來成了第二種故事的傳道者。三十歲之前,他們雖然事業成功,卻深受某種「揮之不去的不滿」所困擾。
我們得到了所有應該能讓我們快樂的東西:六位數年薪的好工作、豪華汽車、超大房子,還有在這種消費導向的生活方式中,塞爆所有生活角落的各種東西。但即使擁有這麼多,我們對自己的生活還是很不滿意。我們不快樂,那是一種巨大的空虛。每週工作七十到八十個小時,然後買更多的東西,並不能填補它;它只會帶來更多債務、壓力、焦慮、恐懼、孤獨、內疚、不知所措和憂鬱。
更糟糕的是,我們無法控制自己的時間,所以不能控制自己的生活。因此,二○一○年,我們以極簡主義原則重新奪回控制權,把注意力集中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
每個世代的人都會有新的見解,對那些跟網路一起成長的人來說,密爾本和尼克迪穆發現了一個近敵:如果你的目標是滿足,那麼物質財富無法達成它。
密爾本和尼克迪穆並不是他們這個世代第一個表示不滿、架設部落格,並試圖以此開展勵志寫作職涯的人。就像李奧.巴伯塔(Leo Babauta),他在二○○七年初建立了部落格「禪習慣」,專注於提高生產力。到了年底,他又推出了電子書《禪:極致的簡單生產力系統》。
二○○九年,就在禪習慣開始流行時,他開了一個新部落格,名為「極簡清單」,之後還寫了一本相關主題的書。幾年後,他談論的主題從提高生產力轉向極簡主義,他建議禪習慣的讀者「把生產力扔掉」:在一艘沉沒中的船上整理躺椅,是毫無意義的事—把事情簡化,直接把躺椅丟掉吧。他從未停止在禪習慣發表文章,但關注的重點改變了,從二○○九年到二○一一年,極簡清單上的許多貼文都反映出人們對極簡主義的強烈興趣。
同一時期,科林.萊特(Colin Wright)把每週工作一百個小時的日常,換成少於一百件東西的生活,並開始在部落格「流放生活」上發表文章,後來也在亞馬遜出版了關於極簡主義和旅行的暢銷書。二○一○年,戴夫.布魯諾(Dave Bruno)成功將自己的部落格寫成了《極簡富足:我靠一百樣東西過一年》一書,書中講述「我如何擺脫幾乎所有東西、重新塑造生活,並找回我的靈魂」。
這種關於危機、重獲靈魂、致力於改革的故事並不罕見。麗塔.霍特(Rita Holt)寫了一本關於極簡主義的電子書,講述她在崩潰痛哭後,如何擺脫自己討厭的生活方式。當她終於意識到「此時不做就沒有機會」時,她辭去了工作,投身於極簡主義革命,並邀請讀者在推特上追蹤她的旅行。
*計數遊牧者與近藤麻理惠
二○一一年,近藤麻理惠出版了一本有關居家整理的書,建議數百萬日本人丟掉那些不會讓他們怦然心動的東西。這本書於二○一四年出版了英文版,雖然近藤不會說英語,但比起密爾本和尼克迪穆,她獲得了更多媒體關注。很顯然的,極簡主義者和近藤都有整理的概念,也都回應了人們對物質主義和雜亂的普遍不滿,但毫無疑問的,極簡主義者就是比較像極客。他們喜歡計數、挑戰和旅行。
極簡主義者故事中有項顯著的特徵,即是列出他們的所有物。戴夫.布魯諾和《極簡富足》提出的挑戰,就是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寫《動機駭客》的溫特有九十九項物品。《極簡主義的藝術》一書作者艾弗雷特.柏格(Everett Bogue)則更精簡到剩下五十樣東西,後來才又承認自己需要的東西比那些更多。凱利.薩頓(Kelly Sutton)是部落格「少的崇拜」格主,他改變了這個公式:他的目標是把自己的生活濃縮成兩個盒子和兩只袋子。
極簡主義並非一成不變,但它確實由男性和那些清點自己物品的人所主導。
近藤麻理惠並不在乎你擁有多少東西,只要它們能讓你怦然心動,並整齊地收納好就行。極簡主義者將家當視為一種挑戰,必須計算數量並丟棄;近藤則以萬物有靈的態度謹慎對待它們。物品渴望服務人類,並滿足於好好告別。除了她與物品的關係變得更加親密,近藤的吸引力或許也在於,她那精疲力盡與充滿洞察力的故事非常戲劇化。
近藤從小就熱衷於整理,但這讓她付出了代價。有一天,她彷彿精神崩潰般昏倒了。兩小時後,「當我醒來時,聽到一個神祕的聲音,就像是某位整理之神在告訴我,要我仔細看看自己的東西。」祂告訴近藤,要關注那些應保留的東西,而不是要扔掉的東西。近藤式收納術於是誕生。近藤和其他大師之間的其他差異,還包括最明顯的性別:極簡主義者通常是男性,但近藤的粉絲女性居多;許多極簡主義者熱愛旅行,這一點也和近藤不同。
簡而言之,從過多到極簡的故事,是一種以狂喜為基調的解放之旅。設置了「物質性成功」陷阱的傳統路線引發了一場危機,緊跟著不滿和崩潰而來的則是覺醒。丟掉你的職業和家當,到世界各地寫作和旅行,成為極簡主義的傳教士吧。
〈1 序章〉
馬克.里特曼的家是個由感測器和控制器組成的網絡,大量數據在他的房子、身體和車庫的伺服器之間傳輸。門、動作和溫度感測器監測著周圍環境,iPhone和健康手環則時時窺伺著他,一切都被記錄下來以便分析;只要簡單對Siri提出要求,就能控制燈光、溫度和音樂。
里特曼最新入手的小玩意是智慧水壺iKettle,他希望Siri能幫他泡杯茶,甚至還想把泡茶加入早晨的自動化行程:戴在手上的健康手環一旦發現里特曼醒了,就會提醒房子打開暖氣和樓下的燈,還能在他洗完澡前把水燒開。但里特曼一直沒辦法設定好水壺,他在推特與成千上萬名追蹤者分享這段歷程:
「三個小時過去了,我還是沒喝到茶。強制再校正導致無線基地臺重置。」好不容易設定好了,水壺卻無法與其他設備相容:「為了讓Siri控制水壺,我只好駭進系統,把這些功能整合起來。」他繼續在推特上分享這個過程,等到終於成功時,這個故事已經傳遍了全球—首先是《衛報》的一篇報導:「一名英國人花了十一個小時,試圖用智慧水壺泡一杯茶。」
這個案例完全展現出所謂的駭客心態,也就是對系統工作的熱情(偶爾會過度迷戀)。不過且讓我們想像堅守在科技以外的另一種駭客:
哈柏在打折時買了同樣的智慧水壺,花了幾個週末對它進行一番整頓,但最後得出一個結論:這東西沒救了;更糟的是收據不見了。幸好,還有另一種駭客手段。哈柏記得「生活駭客」網站上的一篇文章〈沒收據也能退貨—幾乎所有商品都適用〉。哈柏選擇做最後一次努力:再放幾個星期,等聖誕節過後再去退貨。儘管可能要排很久的隊,但此時商店通常會比較寬容。
里特曼是個大數據分析師與自我追蹤者,他之所以能成功解決問題,是因為他了解智慧家電背後的技術系統。而哈柏之所以能成功地在沒有收據的情況下退貨,是因為他了解另一個不同的系統,也就是購物季的動態系統。
我們可以從這兩種駭客技巧中看出,過去十年裡,駭客思維已擴及生活各層面,並廣泛應用於各種技術系統,以快速巧妙地解決問題。生活駭客追蹤或分析自己的飲食、財務、睡眠、工作,甚至包括頭痛。他們分享如何有效率地綁鞋帶、打包行李、尋找約會對象,以及學習語言的各項技巧。
提到「駭客」,許多人馬上會聯想到穿著帽T、埋首電腦前的犯罪者,這或許會讓人們對以上所描述的一切感到驚訝,但這些行為確實符合「駭客」一詞的原義。六十年前,麻省理工學院的鐵路模型愛好者用「hack」一字來形容快速修復「此系統」(火車月臺底下的電線和繼電器網路)的方法。駭客們熱衷於探索、構建和操縱這些系統。
今天,生活駭客涉及的領域除了科技、文化,還包括工作、財富、健康、人際關係,以及其他意義更廣的範圍。這是駭客思維的展現,是具系統化與實驗性的個人主義和理性方法。舉例來說,某些自稱「生物駭客」的人正在嘗試「消弭老化工程策略」,從這個名稱看得出來,這些人確實信心滿滿。 隨著科技不斷發展(尤其是各種能串連感測器的應用程式),這種駭客思維陸續出現在生活中許多從未「駭」過的領域。除了延長壽命,還有提高生產力、獲得物質滿足、達到最佳健康狀態、尋找戀愛對象與性伴侶……等系統。
生活駭客是一種生活方式,也是一種自我成長的途徑。考慮到自身的「怪癖」,我對它的優點確實很能感同身受,但也對它的缺點感到憂心。然而,這些擔憂並非源於生活駭客是外星人或邪教成員。之所以會出現生活駭客,是因為有其天時地利:當生活變得越來越像一個可以管理與建構的系統時,所有人都能藉此獲得一些幫助。
*二十一世紀的勵志新潮流
芸芸眾生中的你,只要擁有正確的態度和行動,就能躋身成功人士。至於該如何做到,只需要從四萬五千多本已出版的勵志書中挑一些來看就行了。大多數人就是這麼做的,如果把影音媒體、電視購物和個人教練算在內,這類市場總值約在五億到一百億美元之間。
生活駭客是自我成長史上最新的一頁,隨著成功的定義改變,人們給出的建議也隨之不同。我們是否仍像一八九○年代那樣,認為神能幫助我們成功?還是像一九三○年代的經典勵志書一樣,只要效法那些成功致富的人就行了?或是在當今資訊過剩的世界中,採納那些占一席之地的頂尖極客所分享的祕訣?史蒂芬.史塔克(Steven Starker)在《超市裡的甲骨文:美國人對勵志書的癡迷》一書寫到,勵志書反映了它們的社會文化背景,揭示了該時代的個人需求、願望和恐懼。正如《紐約客》雜誌在一篇有關費里斯的專訪中提到,每個世代都有專屬於它的勵志大師。
生活駭客是最新的勵志典範,且兩者都是所謂「實踐哲學」的延續。與學院派的哲學不同,實踐哲學關注生活中哪些是有價值的,以及如何認知它,是生活的哲學。若說斯多噶主義和儒學是古代的實踐哲學,那麼生活駭客就是當代的。例如,你可以透過控制自己每天花在回覆電子郵件上的時間(方法),來提高工作效率(目的)。
在美國文化中,勵志是一種很普遍的實踐哲學。正如史塔克所寫的:「我認為,美國的個人主義幾乎是所有勵志素材的泉源。」他也認為,勵志/自我成長是美國機會主義、自力更生和成功決心的一種表現。一位為《紐約》雜誌撰寫文章的文化評論家指出,「自《窮理查年鑑》出版以來,勵志文化—企業家精神、實用主義、強烈的自力更生、淡薄的靈性……已深深根植於美國人的DNA中」。
雖然「勵志」這個詞首見於蘇格蘭作家塞繆爾.斯邁爾斯(Samuel Smiles)那本獲利豐厚的同名書籍(一八五九年出版),但這個詞就跟蘋果派一樣,一開始雖是從歐洲輸入的詞語,如今卻已和美國文化密不可分;而生活駭客已然成為這塊「勵志派」的一部分。
在開始新的冒險之前,吉娜.特拉帕尼出版了三本取材於生活駭客的書;費里斯編纂了五本暢銷書、經營一個受歡迎的部落格,並主持一個有大量聽眾的播客,且都是以「一週工作四小時」這個品牌進行的。另外還有六位作者出版了關於極簡主義的書籍,包括《極簡富足:我靠一百樣東西過一年》和《會留下來的一切》。
當然還有更多關於生活駭客的書籍並未得到主流讀者的青睞,但儘管它們是獨立出版或只發行電子書,在網路書店上還是有數十則評論。我甚至曾在附近雜貨店的收銀處看過一本生活駭客雜誌,也看過國家地理頻道的節目《駭客智多星》。 生活駭客是極客們勵志成長的一種延續,現已成為主流。個人主義、務實、創業精神……等價值觀,以及克服障礙的無窮能力,都是這種精神的核心。生活駭客還加入了系統化思維、樂於實驗、喜愛科技,這些都很適合數位網路世界──一個充斥著系統和小工具的世界。
有些人可能覺得生活駭客就像勵志書一樣,很難視為正經嚴肅的事情;各種小技巧可被視為瑣碎小事;而生活方式的重新設計,則可以被當成《騙術》一書的老調重彈。但這種特色正是生活駭客的魅力所在:系統化精神的背後,既接納了世俗的駭客行為,也包含對人生更高遠的追求。
企業家保羅.布赫海特(Paul Buchheit),谷歌員工編號第二十三、Gmail的首席開發者,也是谷歌早期座右銘「不作惡」的創造者,他相信駭客是生活的「應用哲學」。他曾表示,有系統的地方,就有遭駭客入侵的可能,而到處都是系統。整個現實世界就是個有系統的系統,延伸到各個角落。
當然,並不是每個人都有駭客心態,畢竟社會需要各種不同的個性,但擁有這種心態的人,就是那些能跨越業種、統治權,甚至宗教來「改變世界」的人。對布赫海特來說,駭客行為比電腦中那些聰明的代碼更重要,也更偉大──這是我們創造未來的方式。
布赫海特的信念具有煽動、簡化和集大成的特性,就如同許多勵志方法所採用的前提。而正如史塔克所觀察到的,這些信念很容易讓批評者表現出不屑,以搖頭、瞬間冷笑、高傲的微笑和善意的忽視為回應。然而勵志書是我們文化結構的重要組成,它無所不在且影響深遠,以致無法忽視也不容輕忽,當然值得研究,生活駭客也是如此。
*生活駭客的五十道陰影
對布赫海特來說,任何系統都受制於兩套規則:覺得事物該如何運作的感知規則,以及現實中的實際規則,這正是駭客的力量所在。他認為,在大多數複雜系統中,這兩套規則的差距非常大。有時我們得以瞥見真相,發現某個系統的實際規則;一旦知道實際規則,就有可能發揮「奇蹟」──做出違反感知規則的事。例如,一名電腦駭客可以利用程式正常預期行為與現實中緩衝區溢位(簡單來說,就是指針對程式設計缺陷,塞入超過緩衝區所能容納的資料,破壞程式執行、趁機取得程式甚至是系統的控制權)之間的差距上下其手(例如針對目標電腦輸入惡意程式碼)。當然,駭客攻擊不只限於電腦。
在討論電腦駭客時,人們經常使用老電影裡的一個比喻:針對同樣的系統弱點,白帽駭客會修復它,黑帽駭客會惡意地利用它,灰帽駭客則介於兩者之間:他們可能會在未經允許的情況下進入系統,卻幾乎不會造成傷害。哈柏決定在聖誕假期結束後將智慧水壺退貨,就是種淺灰色駭客的行為。如同里特曼和其他人發現的,想讓智慧水壺透過無線網路正常運作並不容易,因此,在沒有收據的情況下退貨雖然違反了規定,倒似乎沒那麼惡質。
但如果哈柏使用同樣的技巧,卻選擇把東西退給另一家商店,好拿到未折扣價的退費呢?這等於哈柏詐欺了第二家商店,比起當初購入的特價,他能拿到更多現金,這下子他的帽子顏色變得更深了。
生活駭客網站〈沒收據也能退貨──幾乎所有商品都適用〉一文出現在萬聖節前的「邪惡週」主題底下。該網站的編輯們寫道,這樣的貼文雖然有點半開玩笑,卻反映出知識就是力量,至於用這種力量行善或作惡,取決於你自己。邪惡有時情有可原,甚至可以幫助你對抗邪惡:學習如何破解密碼,可以教你強化安全措施;更加了解謊言和操縱,讓你有能力看穿這類策略──或在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情況下使用它們。
這種理由聽起來幾乎可說是權術至上,還顯露出某種技術傾向和個人主義的心態。但一件事究竟是好是壞,不僅取決於個人。要理解這一點,我們可以用另一個問題代替道德的絕對性:要到什麼程度,才能分辨一名生活駭客有害或有益?又是對誰而言?接下來,我們會經常回到這個問題。
沒有收據就退貨的駭客行為顯然是出於對個人利益的關注,但如果哈柏把智慧水壺拿到他當初購買的商店去退、拿回與當時同樣的金額,並沒有所謂的傷害可言。只是如果每個人都使用這個方法,會變得怎樣呢?
這個問題就是康德所謂「定言令式」的一個例子:只做你希望每個人都做的事。第一種情況是,把一只無法使用的智慧水壺退回原購買商店、拿到跟當初購買時同樣的金額,這是無害的;但如果每個人都這麼做,世界將因此變得更糟。這種行為本身就帶有詐欺的意味,店家也會因此採取更加嚴格的退貨政策,反而會傷害到其他消費者。
康德的定言令式將道德考慮的範圍擴展到個人之外。我們可以問,如果一項駭客技巧是普遍的,也就是如果每個人都這麼做,這方法還能持續有效嗎?它有益嗎?這世界會因此變得更好嗎?
讓我們看看現實生活中的案例。鮑伯,萬宙商信(Verizon)的一名開發人員,被發現把自己的工作外包給一家中國公司。包括軟體開發人員在內,許多美國員工都對公司把業務發包給海外公司感到焦慮,覺得這可能導致自己遭到裁員。鮑伯也把工作外包出去,但仍保住自己的飯碗。他把兩成工資付給別人,換來每天上網看貓咪影片的日子。他把公司業務變成自己的優勢,駭進了這個系統。
很顯然,鮑伯的駭客行為是出於自身利益,也並非普遍。它之所以有用,因為這是暗中進行的單一案例。這項行為有可能傷害他人,鮑伯的不誠實使雇主身處風險之中;它無法通過康德的檢視,因為我們不會希望這種不誠實的行為是普遍的。
還有一些生活駭客技巧可能在無意中傷害使用者和他人。想想高生產力駭客技巧與整型手術的相似之處吧。在個人層面上,整型手術是一種能提高生活品質的自我提升法。它可能會出錯,使事情變得更糟;而且表面的強化,只能暫時緩解深層需求,形成一個不斷干預卻永遠無法獲得滿足的惡性循環。 普遍來說,我們很難斷言整型手術對所有人是好還是壞,生活駭客也是如此,尤其論及自我提升的社會涵義時,情況又會變得更加複雜。增強的動力通常是社會性的,也就是說,一旦開始推動,標準就會不斷提高,反而使得滿足感越來越遙不可及。一個人變美後,會讓其他人覺得自己更醜。
有些提高生產力的技巧相當有效:提高產能的關鍵,是排定工作的優先順序,而不是把行程表塞爆。有些技巧是行不通的:喝大量的水然後憋尿,應該可以讓你更專注,事實上卻有可能讓你更分心。而且就像某些手術一樣,有些會讓情況變得更糟,有些則永遠無法讓人滿意。塞爆行程表是一項錯誤,而且生產力再怎麼提升都永遠嫌不夠。到最後,生產力的提高反而讓每個人都被迫面對更多要求,包括生產力的再提升。
這些都是數位時代的陰影。在這個時代裡,人們進行廣泛的互動、各種設備無所不在,並有許多科學問題等待解決;此外,我們可以遠端工作、家事外包、追蹤和測試生活中的每一項指標(從心率到發送出去的電子郵件)。藉由思考鮑伯這樣的案例,我們可以確定人們認為值得的事物中蘊含著哪些固有價值,以及這麼做的有效性及後果。
〈3 時間駭客〉
*把我的生產力變四倍
二○一二年,曼尼什.塞提(Maneesh Sethi)終於成功變身網路名人。這位部落格格主請人在他工作效率不高時打他巴掌。當然,很多人之所以追蹤他,是因為難以置信,但這個噱頭發揮了支點的作用。這是他努力行銷自己的巔峰,就像費里斯一樣,成為一名生活方式設計企業家。這讓他開啟了自己的未來,決心開發一款令人驚嚇的小玩意。而他的故事也成為一個案例研究──關於對剝削的注意。
四年前,也就是二○○八年,塞提還是史丹佛大學的學生,當時他讀了費里斯的《一週工作四小時》,覺得它實在太振奮人心,不但只花了幾個小時就讀完全書,還買了前往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機票。正如他所說的:「我意識到,只要遵循費里斯的想法,自己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他離開學校,開始創立沒有辦公室的事業、環遊世界、接受非凡挑戰,並教其他人如何做同樣的事情,成為「一週工作四小時」的大師。
當然,和費里斯一樣,塞提並不是一個星期只工作四(或零)個小時,甚至連「半」退休也算不上。再說,就算有費里斯的粉絲參加你的派對,難道就能讓你成為有名的DJ嗎?塞提不斷旅行、四處享樂,卻也為了成為生活方式和行銷大師忙碌不已。塞提正努力獲得與費里斯和哥哥拉米特(Ramit Sethi)一樣的成功──塞提的哥哥是《我教你變成有錢人》一書的作者。
塞提致力於推銷暢銷勵志書,包括費里斯的《廚藝解構聖經》(這本書有提到塞提),以及一些關於飲食和女性「荷爾蒙治療」的書籍。最著名的是二○一二年,他從分類廣告網站上僱用了一名女性,當他被臉書分散注意力時,她就會打他巴掌。
「我要徵求一個人,到特定的地點(我家或咖啡館)在我身旁工作,要確定能看到我的電腦螢幕。只要我浪費時間,就吼我一下;必要的話,甚至打我巴掌都可以。可同時做自己的工作。徵求助手,越快越好。地點鄰近灣區捷運第十六街站。時薪八美元,期間可用自己的電腦做自己的事。」
塞提聲稱這個噱頭讓他的生產力變成四倍,並在部落格上分析記錄了這項進步。然而,即使意志力外包的成本低於最低工資,難道不能使用某種小工具達到同樣目的、讓成本更低嗎?
二○一四年,塞提推出了「帕夫洛夫」手環,概念來自於帕夫洛夫的制約理論,手環會產生微小電流,幫助使用者克服壞習慣。這個想法大受歡迎,在募資平臺上募到了超過二十八萬美元,是最初目標的五○八%。以前的做法是在手腕套個橡皮筋,然後彈自己一下,好擺脫不想要的想法或習慣。一條橡皮筋,拉起來再鬆開就會弄痛你,手環則是會電你一下。雖然相較之下橡皮筋是免費的,但塞提相信這個兩百美元的小玩意物有所值。「帕夫洛夫」結合了感應器、朋友和GPS,能讓你好好走在邁向目標的軌道上。比方說,不論當你把手伸到嘴邊(咬指甲或吃零食)、去最喜歡的速食店,或是在臉書花太多時間,它都會電你。此外,塞提還開了一門有關改掉壞習慣的線上課程,宣稱想馬上徹底戒掉某個習慣的人當中,成功率大約是五%;使用橡皮筋的,成功率是二五%;至於使用「帕夫洛夫」的人,大約有五五到六○%的人都成功了。
塞提用盡一切可能的方法,透過報紙、播客和部落格,向費里斯所謂的「新富」企業家推銷帕夫洛夫手環,這個小玩意甚至被美國深夜檔政治諷刺節目《柯柏報告》拿來嘲諷──這個節目可說是衡量大眾關注度的實用量表。還有一次非常珍貴的機會,是他在二○一六年時參加美國廣播公司的創業實境秀節目《創智贏家》,但他的提案並沒有被接受。其中一名評審說他是個靠花招行騙的人,而在塞提拒絕對他最具好感的投資者提出的交易後,又發生了更糟糕的事:有人說他去上節目只是為了推銷自己的產品,不是為了獲得額外的資金。對於費里斯和塞提這樣的生活駭客騙子,批評他們自私自利的聲音並不少見。
我們將在下一章繼續認真研究動機駭客。但對塞提行為的評論,讓我們回到這一章開始時,對富蘭克林的高生產力所提出的問題。當生活駭客試著充分利用時間時,他們究竟視什麼為理所當然?說得更準確一點,生活駭客的行為何時會變成剝削?
*特權和剝削
二○一二年,塞提寫了一篇〈性醜聞技巧〉,內容有關如何立刻實現各種目標(並與費里斯開派對),他指責其他人自以為擁有某些權利:如果你覺得,只因自己上了大學、努力讀書、拿到好成績和學位,就表示自己應該得到一份工作,那就錯了。有成千上萬的人都是這樣。所以他問:是什麼讓你與眾不同?更何況,與任何美國大學畢業生相比,還有其他國家的人會為了更少的錢更努力工作。
「告訴你們一個故事,是我一位菲律賓員工的故事。我僱用克拉克來幫我養成一個習慣:每天早上十點,他要打電話提醒我用牙線潔牙。
「有一天,我在十點三十二分時收到了一則訊息。『抱歉,曼尼什先生(克拉克總是叫我『先生』,就算我告訴他別這樣叫我),我遲到了,真的很抱歉。我們這裡被颶風襲擊,整個村子都沒有電!我得跑十幾公里到隔壁村子,才有辦法打電話給你!』
「你會只為了提醒我用牙線而跑十幾公里嗎?我給克拉克的薪水是每小時兩美元(但在此事之後,我給了他一大筆獎金),但你呢?你做了什麼來提升自己的價值,讓雇主願意付十到二十倍的薪水給你?」
想當然耳,塞提的回答是「侵入系統」:「達到目標的最短路徑,不是透過做其他人正在做的事情,反而多半是要做完全相反的事情。」為了在柏林成為DJ,他舉辦了許多派對;為了提高知名度,他建立了自己的播客,採訪其他更有名的生活駭客。
然而,在塞提教導別人「權利謬論」的同一篇文章中,他提到自己花錢請一名菲律賓人提醒他使用牙線。追求效率是值得稱讚的,就算做過頭,也還有機會重新評估目標和優先順序的有效性。然而正如富蘭克林的生產力端賴於妻子和奴隸等被忽視的勞動,外包也同樣依賴其他人的勞動成果。若是本地的工作,勞動將由零工經濟來完成,例如優步司機。這些人的工作靈活度高,獲利卻很少,其中更有許多人很快就會被自動化取代。至於那些可以遠端完成的工作,則會由迫切需要收入的外國人來執行。
儘管業主所提供的工作可能是低階的,但以誠實的態度來回應這種需求或許是一種美德。費里斯指出:「我把工作外包給印度人,有些人又會把部分工作再外包給菲律賓人。這是資本的有效利用,如果你想要自由市場的回報、想要享受資本主義制度的回報,這些就是必須遵守的規則。」但這什麼時候會變成剝削呢?什麼時候規則是不公平的?這正是自動化和全球化的雙面刃。
有效、自由且靈活,具備這些前提和承諾的系統,才會被生活駭客接納。將大企業的外包方法用在個人身上,確實是一種駭客技巧,卻也承繼了企業的道德過失。儘管塞提善良又隨和,但在颶風過後,克拉克是否能放一天假,先幫助家人、保留自己的時間,而不是把時間拿來換兩美元?還是因為他的家庭非常依賴這份薪水,所以他別無選擇,只能跑十幾公里,好提醒塞提用牙線?
同樣的,人們假設勞工可以選擇要做穩定的正職或富有彈性的計時工作,但零工經濟的從事者中,已處於邊緣、別無選擇的人卻越來越多。這樣看來,生產力駭客有時似乎在為那些會遭企業制度濫用的東西喝采。塞提推出了據說能糾正壞習慣的手環,四年後,亞馬遜為類似的東西申請了專利──針對拿錯貨品的倉庫員工。值得慶幸的是,亞馬遜的提案裡並沒有包括電擊裝置。但在那些能自己選擇制度與能要求他人實施該制度的人之間,存在著一種令人不安(即使是巧合)的互惠關係。
〈5 物品駭客〉
*從太多到極簡
關於自己與家當的關係,生活駭客會講的故事有兩種,第一種是關於他們認為不可或缺的裝備和工具,第二種則是他們如何擺脫其他的一切。約書亞.密爾本(Joshua Millburn)和萊恩.尼克迪穆(Ryan Nicodemus)是朋友,他們後來成了第二種故事的傳道者。三十歲之前,他們雖然事業成功,卻深受某種「揮之不去的不滿」所困擾。
我們得到了所有應該能讓我們快樂的東西:六位數年薪的好工作、豪華汽車、超大房子,還有在這種消費導向的生活方式中,塞爆所有生活角落的各種東西。但即使擁有這麼多,我們對自己的生活還是很不滿意。我們不快樂,那是一種巨大的空虛。每週工作七十到八十個小時,然後買更多的東西,並不能填補它;它只會帶來更多債務、壓力、焦慮、恐懼、孤獨、內疚、不知所措和憂鬱。
更糟糕的是,我們無法控制自己的時間,所以不能控制自己的生活。因此,二○一○年,我們以極簡主義原則重新奪回控制權,把注意力集中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
每個世代的人都會有新的見解,對那些跟網路一起成長的人來說,密爾本和尼克迪穆發現了一個近敵:如果你的目標是滿足,那麼物質財富無法達成它。
密爾本和尼克迪穆並不是他們這個世代第一個表示不滿、架設部落格,並試圖以此開展勵志寫作職涯的人。就像李奧.巴伯塔(Leo Babauta),他在二○○七年初建立了部落格「禪習慣」,專注於提高生產力。到了年底,他又推出了電子書《禪:極致的簡單生產力系統》。
二○○九年,就在禪習慣開始流行時,他開了一個新部落格,名為「極簡清單」,之後還寫了一本相關主題的書。幾年後,他談論的主題從提高生產力轉向極簡主義,他建議禪習慣的讀者「把生產力扔掉」:在一艘沉沒中的船上整理躺椅,是毫無意義的事—把事情簡化,直接把躺椅丟掉吧。他從未停止在禪習慣發表文章,但關注的重點改變了,從二○○九年到二○一一年,極簡清單上的許多貼文都反映出人們對極簡主義的強烈興趣。
同一時期,科林.萊特(Colin Wright)把每週工作一百個小時的日常,換成少於一百件東西的生活,並開始在部落格「流放生活」上發表文章,後來也在亞馬遜出版了關於極簡主義和旅行的暢銷書。二○一○年,戴夫.布魯諾(Dave Bruno)成功將自己的部落格寫成了《極簡富足:我靠一百樣東西過一年》一書,書中講述「我如何擺脫幾乎所有東西、重新塑造生活,並找回我的靈魂」。
這種關於危機、重獲靈魂、致力於改革的故事並不罕見。麗塔.霍特(Rita Holt)寫了一本關於極簡主義的電子書,講述她在崩潰痛哭後,如何擺脫自己討厭的生活方式。當她終於意識到「此時不做就沒有機會」時,她辭去了工作,投身於極簡主義革命,並邀請讀者在推特上追蹤她的旅行。
*計數遊牧者與近藤麻理惠
二○一一年,近藤麻理惠出版了一本有關居家整理的書,建議數百萬日本人丟掉那些不會讓他們怦然心動的東西。這本書於二○一四年出版了英文版,雖然近藤不會說英語,但比起密爾本和尼克迪穆,她獲得了更多媒體關注。很顯然的,極簡主義者和近藤都有整理的概念,也都回應了人們對物質主義和雜亂的普遍不滿,但毫無疑問的,極簡主義者就是比較像極客。他們喜歡計數、挑戰和旅行。
極簡主義者故事中有項顯著的特徵,即是列出他們的所有物。戴夫.布魯諾和《極簡富足》提出的挑戰,就是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寫《動機駭客》的溫特有九十九項物品。《極簡主義的藝術》一書作者艾弗雷特.柏格(Everett Bogue)則更精簡到剩下五十樣東西,後來才又承認自己需要的東西比那些更多。凱利.薩頓(Kelly Sutton)是部落格「少的崇拜」格主,他改變了這個公式:他的目標是把自己的生活濃縮成兩個盒子和兩只袋子。
極簡主義並非一成不變,但它確實由男性和那些清點自己物品的人所主導。
近藤麻理惠並不在乎你擁有多少東西,只要它們能讓你怦然心動,並整齊地收納好就行。極簡主義者將家當視為一種挑戰,必須計算數量並丟棄;近藤則以萬物有靈的態度謹慎對待它們。物品渴望服務人類,並滿足於好好告別。除了她與物品的關係變得更加親密,近藤的吸引力或許也在於,她那精疲力盡與充滿洞察力的故事非常戲劇化。
近藤從小就熱衷於整理,但這讓她付出了代價。有一天,她彷彿精神崩潰般昏倒了。兩小時後,「當我醒來時,聽到一個神祕的聲音,就像是某位整理之神在告訴我,要我仔細看看自己的東西。」祂告訴近藤,要關注那些應保留的東西,而不是要扔掉的東西。近藤式收納術於是誕生。近藤和其他大師之間的其他差異,還包括最明顯的性別:極簡主義者通常是男性,但近藤的粉絲女性居多;許多極簡主義者熱愛旅行,這一點也和近藤不同。
簡而言之,從過多到極簡的故事,是一種以狂喜為基調的解放之旅。設置了「物質性成功」陷阱的傳統路線引發了一場危機,緊跟著不滿和崩潰而來的則是覺醒。丟掉你的職業和家當,到世界各地寫作和旅行,成為極簡主義的傳教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