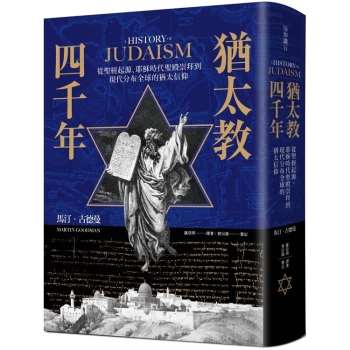導論:猶太教歷史研究的蹊徑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後,第三個月的初一,就在那一天他們來到了西奈的曠野。……摩西到上帝那裡,主從山上呼喚他說:「你要這樣告訴雅各家,對以色列人說:『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們都看見了,我如鷹將你們背在翅膀上,帶你們來歸我。如今你們若真的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約,就要在萬民中作屬我的子民,因為全地都是我的。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為神聖的國民。』這些話你要告訴以色列人。」……到了第三天早晨,山上有雷轟、閃電和密雲,並且角聲非常響亮,營中的百姓盡都戰抖顫抖。摩西率領百姓出營迎見上帝,都站在山下。西奈山全山冒煙,因為主在火中降臨山上。山的煙霧上騰,彷彿燒窯,整座山劇烈震動。角聲越來越響,摩西說話,上帝以聲音回答他。……
這段描寫摩西在西奈山接受天啟的戲劇化敘事,被保存在《出埃及記》裡。三千多年以來,人們對於上帝與「神聖的國民」締結的這個約持續做出各種不同的解讀,而猶太教的歷史實際上就是這些詮釋的演變史。
傳說摩西被賜予天啟的一千年之後,耶路撒冷的祭司兼歷史學家約瑟夫斯(Josephus)將現存最早的針對非猶太讀者所寫的猶太神學思想放進他的著作《駁斥阿比安》(Against Apion),以維護猶太傳統,反駁外邦作家的毀謗。約瑟夫斯筆下的摩西創造了一種非常適合人類的新體制,和當時所知的君主制、民主制和寡頭制等其他體制都相當不同,唯有發明一個新詞「神權制」(希臘文為theokratia)方能貼切表達此概念,因為摩西堅稱上帝應掌管一切:「他不把虔誠視為德行的一部分,而是看出並規定其他的德行皆屬虔誠的一部分。……所有的行為和職業,所有的言語,都和我們對上帝的虔誠有關聯。」
待到約瑟夫斯的時代,也就是西元一世紀晚期,摩西已成為一位英雄人物,籠罩在神話之中。約瑟夫斯推測,摩西的生存年代其實早了他兩千年左右,堅持宣稱:「我認為我們的立法者生存的年代超越了他處提及的立法者。」約瑟夫斯是為了非猶太人撰寫神學,但這些非猶太人對摩西的看法很明顯沒有這麼滿腔熱情。希臘人和羅馬人普遍知道猶太人把摩西視為他們的立法者,而在西元前四世紀晚期,阿布德拉的赫卡塔埃烏斯(Hecataeus of Abdera)也認為他「智慧與勇氣非凡」。然而,很多人也說他是江湖術士或騙子。和約瑟夫斯同年代的羅馬雄辯家昆體良(Quintilian)甚至還拿摩西為例,在闡述「城市的創建者受憎惡,因他們專注在一個對他人而言是詛咒的民族」時,連他指稱的那位「猶太迷信的創建者」不需明講都知道說的是誰。外人越是抨擊猶太教,像約瑟夫斯這樣的虔誠猶太人就越是擁護自身的優良傳統,宣稱這項傳統「讓上帝成為宇宙主宰」。正如約瑟夫斯提出的這句激問:「還有什麼政體比這更加神聖?當整個團體都為虔誠信神做好萬全準備…整個體制的組織就像某種祝聖儀式,還有什麼榮耀比這更適合上帝?」
與其他民族之間的反差,也是讓約瑟夫斯堅稱猶太人在面對與宗教有關的一切時,彼此從不產生歧見的原因。那是由於,每一位猶太人都被教導決定了他們生活方式的律法,因此「這些律法就彷彿是刻在我們的靈魂上」:
這是我們如此和睦的主要原因。因為對上帝抱持著相同的概念,生活方式和習慣完全沒有差異,使人的性格出現非常美麗的和諧。在我們這民族之間,絕對聽不到關於上帝的矛盾說法,而這在其他民族中十分常見,不只尋常百姓在情緒突然激動時會說的那些言詞,就連某些哲人也大膽地說出一些言論,有些企圖藉由辯論的方式消弭上帝的存在,有些則試圖代表人類消抹天命。我們的生活習慣也絕對看不出有任何差異:我們全都實踐相同的做法,全都與律法和諧共處,認同上帝看顧一切。
頁數 3/9
在本書後面的敘述中將清楚看見,把猶太人與希臘人和古代世界其他多神教民族的眾多神祇、教派、神話和習俗區別開來的,這種行為和信仰的「一致」與「統一」,在猶太教內部其實仍保留不少多元變化的空間,且不僅當時如此,而是整個猶太教歷史皆然。
猶太教的歷史並不是猶太人的歷史,但猶太教是猶太人的宗教,因此,只要猶太人的政治文化歷史與他們的宗教概念和實踐有所衝撞,本書必定也得追本溯源。此外,猶太教是個世界宗教,特別是因為猶太人遭現實所迫,數千年來廣泛分散各地,因此他們的宗教思想時常藉由吸收或排斥的方式,反映出自己生活的那個廣大的非猶太世界。雖然猶太教與民族性之間的關聯不像基督教、伊斯蘭教或佛教等其他世界宗教那樣薄弱(雖然,在這些宗教裡,宗教認同有時也是辨識某一民族或文化的標誌),早在約瑟夫斯寫下摩西所創造的特殊體制是多麼卓越以前,猶太人的身分認同就不是只以宗教定義,也由血統定義。最遲在西元前二世紀,幾乎所有的猶太人都已接納了那些希望遵循猶太習俗、將自己定義為猶太人的改宗者。在本書所探討的大部分歷史中,猶太教一直都有潛力成為一個普世宗教,而猶太人也一向相信他們的宗教具有普世的重要意義,雖然他們(不像某些基督徒)從不進行世界性的傳教活動,以改變他人信仰、皈依自己的宗教。
抽出三千年來猶太文化中的宗教元素,並加以描述和解釋,是一件令人卻步的任務,那是因為材料的分量和學術的重擔都是如此龐大。過去兩千年以來,猶太教出現非常多樣的表現形式。觀察今日各猶太教分支所著重的特點,進而定義猶太教的本質,並回溯這些特點在數世紀以來的發展歷程,是很直截了當的研究方式,而這種史書在過去幾世紀以來確實也有人寫過。然而,若假定現今被視為本質的東西從古至今一直都如此被看重,顯然是無法令人滿意的。無論如何,我們切勿理所當然地以為猶太教內部一直都有主流教派,或這個宗教的其他變化在過去都被當成支流看待,而現在也應該這麼看待。將傳統喻為一條大江或是一棵擁有許多樹枝的大樹,是很吸引人卻非常危險的做法。因為,現今猶太教最重要的那些層面,和古代的猶太教可能根本沒什麼關聯。例如,在耶路撒冷聖殿舉行獻祭儀式,是兩千年前禮拜儀式的核心,但今天猶太教大多數的教派顯然不會這麼做。
要避免把杜撰的敘事強加在猶太教的歷史中,以合理化現今所關注的層面,其中一個方式便是盡可能客觀描述在特定時期興起的各種猶太教形式,展現出不同表現形式之間的相似處,方能使欲在單部史書中探討所有猶太教派的做法顯得合情合理。這種多元主義的研究途徑固然有它的優點,但就其本身來說可能不太令人滿意,因為無論從內部看來多麼多元,外人向來把猶太教視為單一宗教,且自聖經問世以來,猶太族群內部和諧一致的說法便是猶太宗教文獻裡的常客。倘若史家能做的,就只是描述猶太教數世紀以來出現的一大堆奇異的表現形式,而未能闡述這些不同形式之間的關聯,那麼成果會是個陳列珍奇事物的展示櫃,能做的只是消遣、困惑讀者,但卻少了故事解釋猶太教為什麼演變成現在的樣貌,至今仍是影響數百萬人生命的宗教。
因此,本書的研究途徑結合了前幾代的線性歷史敘事,以及那些對各種傳統保持開放心胸的當代學者所偏好的「多元」敘事。本書將回溯目前已知在某個時間點同時發展興盛的各種猶太教表現形式,接著在證據許可的情況下,檢視這些變化形式之間的關係。本書力圖確立猶太教的不同分支在何時何地互相競爭合法地位或擁護者,又在何時何地寬容忍受彼此,無論是秉持開放接納的精神,或是懷有敵意勉強接受。 猶太教內部的紛爭史相當豐富,有時爭執的事物在外人眼中看起來可能只是雞毛蒜皮的小事。然而,在猶太人之間,宗教狂熱份子雖會以言語駁斥對手,卻不常出現宗教動機的暴力行為。聖經中講述非尼哈(Pinchas)的故事,說他自行執法,當場殺死淫亂的以色列男子和該男子帶回家族的偶像崇拜女子。然而,這雖然是對上帝狂熱的模範,但卻極少發生。猶太教完全沒有出現過如歐洲近世的基督教聖戰那樣的東西,也沒有如伊斯蘭教遜尼派和什葉派之間存在的那種不時撕裂彼此關係的深沉敵意。猶太教內部的寬容程度是本書探討的主題之一。
同時,史書也一定要追溯猶太教內部從一個時期到另一個時期的發展變遷,因此只要情況許可,我都盡力展現猶太教的各分支與前面幾代的關聯,並且點出這些分支選擇強調前幾代傳統中的哪些特定元素。猶太教大多數的教派都聲稱自己忠於過去的傳統,那麼,會出現如此多元的變化似乎又顯得奇怪了。原來,保守的說詞背後往往藏有改變和革新。這部史書將會指出,有哪一些革新會影響後世猶太人的宗教生活,又有哪一些最後將銷聲匿跡。
無論在哪一個時期,要給猶太人下一個明確的定義都是很不容易的。若以為在複雜的現代世界來臨前,猶太人的身分認同都是安全穩當、沒有問題的,那可就錯了。在任何時期,那些認為自己是猶太人的人,其自我認知與他人的認知可能並不一致:雙親之中只有一位是猶太人,這樣的人身分地位難以確定,這個問題早在約瑟夫斯寫書的年代就已受到關注,因為猶太人是在西元一世紀左右才開始把母親的身分視為決定性的因素,而非父親的身分;當時和現在一樣,對於外幫人改信猶太教可能只有一部分的猶太人認可,另一部分則不承認。本書採取的實際解決辦法就是,只要任何個人或團體準備好要跟猶太人一樣,使用從古至今指涉自我的三個主要名稱來稱呼自己,便都當成猶太人看待。「以色列人」、「希伯來人」和「猶太人」起初都有各自的特定指涉對象,但後來猶太人對於這三個詞的用法幾乎沒有區分。某些和猶太教分離的團體(如撒馬利亞人和部分的早期基督徒)決定稱自己為「以色列人」,而非「猶太人」,以示明確的區隔。
就連那些仍留在猶太教團體裡的猶太人,對於這些名稱的意涵可能也各自有不同的看法。在英文裡,「希伯來人」這個詞在十九世紀時用來指涉猶太人,是蠻有禮貌的用語,但是現今卻帶有些許的冒犯意味;在法國,十九世紀的猶太人叫自己「以色列人」,而「猶太人」這個詞直到最近才喪失了貶低的意涵。西元一世紀遭逢政治壓力時,猶太人在希伯來語和希臘語當中轉換指稱自己的用詞,顯示上述現象不是近代才出現的。這一切都與歷史背景有關,而歷史背景又能說明猶太教內部的發展,因此本書會觸及許多近東和歐洲以及(到更晚近的時期)美洲和其他地區的歷史,以便解釋本書主要關注的宗教變遷課題。 因此,發生在廣大世界的事件及其對猶太人所造成的影響,形成了本書劃分猶太教歷史各時期的依據,從近東地區的帝國、希臘羅馬文明到基督化的歐洲,再到伊斯蘭教的巨大影響,以及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所形塑出來的現代,一直到今天複雜的猶太世界(許多外地猶太人的命運和以色列這個國家密不可分)。劃分這些時期的歷史事件當中,只有一件是與猶太人的歷史有關,那就是西元七〇年耶路撒冷第二聖殿被毀。這起事件讓猶太教的發展進入全新時期,對於現存的各種猶太教表現形式都具有深遠的影響。當時的猶太人不太可能體認到失去聖殿後他們的宗教會出現多大的改變,但將西元七〇年當作猶太教歷史的一個轉捩點之所以很合理,其中一個特別重要的原因是,這麼做能糾正基督教對於猶太教神學觀念的謬誤,認為猶太教是舊約的宗教,在基督教出現之後就被取代,並被視為是多餘的。在現代世界形塑了所有猶太人宗教信仰的拉比猶太教,其實是在西元第一個千年之間演變出來的,和基督教會並行發展。拉比猶太教的基礎建立在一套文本集成上,基督徒稱這些文本為舊約聖經,猶太人則稱之為希伯來聖經。拉比特別將希伯來聖經的前五本書「摩西五經」指定為妥拉(原意為「教導」),他們也用這個詞來指涉更通泛的典籍,凡是透過天啟傳授給猶太人的指導教誨,都可稱作妥拉。但,拉比不是只有逐字逐句研讀聖經。他們發展米大示(midrash,原意為「教誨的闡述」)的技巧,將對聖經文本的詮釋納入《哈拉卡》(halakhah,原意為「律法」)中,與經由習俗和口述傳統傳遞的律法規則相符。在拉比猶太教裡,《哈拉卡》(尤其是保存在《巴比倫塔木德》﹝Babylonian Talmud﹞)裡的版本,實際上就和聖經一樣重要。
數世紀以來,猶太教以許多不同的語言表達,反映了這些周遭的文化。猶太人的官方語言是希伯來語,但聖經裡也找得到亞蘭語,亦即西元前一千年近東地區使用的方言。西元一世紀保存下來的猶太著作大部分是以希臘文寫成,而中世紀的猶太哲學重要著作則是以阿拉伯文寫成。在一本用英文寫成的書裡,很難確切傳達這些著作所處的多樣語言和文化世界中,必然會存在的細微差異,也很難傳達字源相當不同的詞語,在猶太人的認知裡為何可能指涉的是同一件事。例如,聖經裡說到位於地中海東岸的那片應許給猶太人的土地,在聖經最前面的敘述稱為迦南,但在聖經他處卻稱為以色列地;波斯帝國的耶胡德省(Yehud)以及希臘統治下的猶地亞(Judaea),在西元一三五年被羅馬政府命名為敘利亞-巴勒斯坦省(Syria Palaestina)。這樣的結果可能會讓現今的讀者十分困惑,但是措辭的選用常常具有其重要性,因此我會盡量讓參考來源本身表達出這點。
有些讀者可能會覺得,想客觀呈現猶太教歷史是相當天真的。十九世紀的歐洲出現了「猶太學研究」(Wissenschaft des Judentums),開啟猶太歷史的科學研究,當中有許多偉大的學者寫書,目的是要在沒有傳統拉比詮釋的包袱下,以批判的眼光評估古代猶太文獻,藉此強化當時猶太教內部某些趨勢的真實性。猶太研究確定成為西方大學所認可的學術領域後,特別是從一九六〇年代起,這種與時下宗教爭議產生關聯的現象已十分少見。在歐洲,許多猶太研究的教授並不是猶太人,因此他們聲稱能不受感情左右地鑽研自己的學科,是具有一定的可信度的,雖說基督教或無神論的預設立場當然也必會導致偏見。這不是我的立場。我生在一個英國猶太人的家庭,我們對自己的猶太認同非常認真看待。家父的圖書室擺滿了從祖父那兒繼承下來的猶太教書籍;我的祖父在倫敦的西葡猶太會堂擔任幹事多年,自己也寫過書,包括一本猶太人歷史。我們家實踐猶太教禮儀的方式通常只有週五晚上、安息日前夕的晚餐和每年的逾越節晚宴,並偶爾參加貝維斯馬克斯猶太會堂(Bevis Marks synagogue)的禮拜。青年時期的我有點叛逆,決定依循一種比較嚴守猶太教規範的生活方式(我的家人對此展現了令人欽佩的耐性)。我在牛津猶太會堂(Oxford Jewish Congregation)找到了歸屬,這意義應該十分重大,因為這是英國十分特別的一個會堂,在單一團體中同時包容了進步派、保守派與正統派的禮拜儀式。這樣的背景讓我對於猶太教發展史當中有關核心與邊緣的認知產生多大的影響,就由讀者來評斷吧。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後,第三個月的初一,就在那一天他們來到了西奈的曠野。……摩西到上帝那裡,主從山上呼喚他說:「你要這樣告訴雅各家,對以色列人說:『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們都看見了,我如鷹將你們背在翅膀上,帶你們來歸我。如今你們若真的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約,就要在萬民中作屬我的子民,因為全地都是我的。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為神聖的國民。』這些話你要告訴以色列人。」……到了第三天早晨,山上有雷轟、閃電和密雲,並且角聲非常響亮,營中的百姓盡都戰抖顫抖。摩西率領百姓出營迎見上帝,都站在山下。西奈山全山冒煙,因為主在火中降臨山上。山的煙霧上騰,彷彿燒窯,整座山劇烈震動。角聲越來越響,摩西說話,上帝以聲音回答他。……
這段描寫摩西在西奈山接受天啟的戲劇化敘事,被保存在《出埃及記》裡。三千多年以來,人們對於上帝與「神聖的國民」締結的這個約持續做出各種不同的解讀,而猶太教的歷史實際上就是這些詮釋的演變史。
傳說摩西被賜予天啟的一千年之後,耶路撒冷的祭司兼歷史學家約瑟夫斯(Josephus)將現存最早的針對非猶太讀者所寫的猶太神學思想放進他的著作《駁斥阿比安》(Against Apion),以維護猶太傳統,反駁外邦作家的毀謗。約瑟夫斯筆下的摩西創造了一種非常適合人類的新體制,和當時所知的君主制、民主制和寡頭制等其他體制都相當不同,唯有發明一個新詞「神權制」(希臘文為theokratia)方能貼切表達此概念,因為摩西堅稱上帝應掌管一切:「他不把虔誠視為德行的一部分,而是看出並規定其他的德行皆屬虔誠的一部分。……所有的行為和職業,所有的言語,都和我們對上帝的虔誠有關聯。」
待到約瑟夫斯的時代,也就是西元一世紀晚期,摩西已成為一位英雄人物,籠罩在神話之中。約瑟夫斯推測,摩西的生存年代其實早了他兩千年左右,堅持宣稱:「我認為我們的立法者生存的年代超越了他處提及的立法者。」約瑟夫斯是為了非猶太人撰寫神學,但這些非猶太人對摩西的看法很明顯沒有這麼滿腔熱情。希臘人和羅馬人普遍知道猶太人把摩西視為他們的立法者,而在西元前四世紀晚期,阿布德拉的赫卡塔埃烏斯(Hecataeus of Abdera)也認為他「智慧與勇氣非凡」。然而,很多人也說他是江湖術士或騙子。和約瑟夫斯同年代的羅馬雄辯家昆體良(Quintilian)甚至還拿摩西為例,在闡述「城市的創建者受憎惡,因他們專注在一個對他人而言是詛咒的民族」時,連他指稱的那位「猶太迷信的創建者」不需明講都知道說的是誰。外人越是抨擊猶太教,像約瑟夫斯這樣的虔誠猶太人就越是擁護自身的優良傳統,宣稱這項傳統「讓上帝成為宇宙主宰」。正如約瑟夫斯提出的這句激問:「還有什麼政體比這更加神聖?當整個團體都為虔誠信神做好萬全準備…整個體制的組織就像某種祝聖儀式,還有什麼榮耀比這更適合上帝?」
與其他民族之間的反差,也是讓約瑟夫斯堅稱猶太人在面對與宗教有關的一切時,彼此從不產生歧見的原因。那是由於,每一位猶太人都被教導決定了他們生活方式的律法,因此「這些律法就彷彿是刻在我們的靈魂上」:
這是我們如此和睦的主要原因。因為對上帝抱持著相同的概念,生活方式和習慣完全沒有差異,使人的性格出現非常美麗的和諧。在我們這民族之間,絕對聽不到關於上帝的矛盾說法,而這在其他民族中十分常見,不只尋常百姓在情緒突然激動時會說的那些言詞,就連某些哲人也大膽地說出一些言論,有些企圖藉由辯論的方式消弭上帝的存在,有些則試圖代表人類消抹天命。我們的生活習慣也絕對看不出有任何差異:我們全都實踐相同的做法,全都與律法和諧共處,認同上帝看顧一切。
頁數 3/9
在本書後面的敘述中將清楚看見,把猶太人與希臘人和古代世界其他多神教民族的眾多神祇、教派、神話和習俗區別開來的,這種行為和信仰的「一致」與「統一」,在猶太教內部其實仍保留不少多元變化的空間,且不僅當時如此,而是整個猶太教歷史皆然。
猶太教的歷史並不是猶太人的歷史,但猶太教是猶太人的宗教,因此,只要猶太人的政治文化歷史與他們的宗教概念和實踐有所衝撞,本書必定也得追本溯源。此外,猶太教是個世界宗教,特別是因為猶太人遭現實所迫,數千年來廣泛分散各地,因此他們的宗教思想時常藉由吸收或排斥的方式,反映出自己生活的那個廣大的非猶太世界。雖然猶太教與民族性之間的關聯不像基督教、伊斯蘭教或佛教等其他世界宗教那樣薄弱(雖然,在這些宗教裡,宗教認同有時也是辨識某一民族或文化的標誌),早在約瑟夫斯寫下摩西所創造的特殊體制是多麼卓越以前,猶太人的身分認同就不是只以宗教定義,也由血統定義。最遲在西元前二世紀,幾乎所有的猶太人都已接納了那些希望遵循猶太習俗、將自己定義為猶太人的改宗者。在本書所探討的大部分歷史中,猶太教一直都有潛力成為一個普世宗教,而猶太人也一向相信他們的宗教具有普世的重要意義,雖然他們(不像某些基督徒)從不進行世界性的傳教活動,以改變他人信仰、皈依自己的宗教。
抽出三千年來猶太文化中的宗教元素,並加以描述和解釋,是一件令人卻步的任務,那是因為材料的分量和學術的重擔都是如此龐大。過去兩千年以來,猶太教出現非常多樣的表現形式。觀察今日各猶太教分支所著重的特點,進而定義猶太教的本質,並回溯這些特點在數世紀以來的發展歷程,是很直截了當的研究方式,而這種史書在過去幾世紀以來確實也有人寫過。然而,若假定現今被視為本質的東西從古至今一直都如此被看重,顯然是無法令人滿意的。無論如何,我們切勿理所當然地以為猶太教內部一直都有主流教派,或這個宗教的其他變化在過去都被當成支流看待,而現在也應該這麼看待。將傳統喻為一條大江或是一棵擁有許多樹枝的大樹,是很吸引人卻非常危險的做法。因為,現今猶太教最重要的那些層面,和古代的猶太教可能根本沒什麼關聯。例如,在耶路撒冷聖殿舉行獻祭儀式,是兩千年前禮拜儀式的核心,但今天猶太教大多數的教派顯然不會這麼做。
要避免把杜撰的敘事強加在猶太教的歷史中,以合理化現今所關注的層面,其中一個方式便是盡可能客觀描述在特定時期興起的各種猶太教形式,展現出不同表現形式之間的相似處,方能使欲在單部史書中探討所有猶太教派的做法顯得合情合理。這種多元主義的研究途徑固然有它的優點,但就其本身來說可能不太令人滿意,因為無論從內部看來多麼多元,外人向來把猶太教視為單一宗教,且自聖經問世以來,猶太族群內部和諧一致的說法便是猶太宗教文獻裡的常客。倘若史家能做的,就只是描述猶太教數世紀以來出現的一大堆奇異的表現形式,而未能闡述這些不同形式之間的關聯,那麼成果會是個陳列珍奇事物的展示櫃,能做的只是消遣、困惑讀者,但卻少了故事解釋猶太教為什麼演變成現在的樣貌,至今仍是影響數百萬人生命的宗教。
因此,本書的研究途徑結合了前幾代的線性歷史敘事,以及那些對各種傳統保持開放心胸的當代學者所偏好的「多元」敘事。本書將回溯目前已知在某個時間點同時發展興盛的各種猶太教表現形式,接著在證據許可的情況下,檢視這些變化形式之間的關係。本書力圖確立猶太教的不同分支在何時何地互相競爭合法地位或擁護者,又在何時何地寬容忍受彼此,無論是秉持開放接納的精神,或是懷有敵意勉強接受。 猶太教內部的紛爭史相當豐富,有時爭執的事物在外人眼中看起來可能只是雞毛蒜皮的小事。然而,在猶太人之間,宗教狂熱份子雖會以言語駁斥對手,卻不常出現宗教動機的暴力行為。聖經中講述非尼哈(Pinchas)的故事,說他自行執法,當場殺死淫亂的以色列男子和該男子帶回家族的偶像崇拜女子。然而,這雖然是對上帝狂熱的模範,但卻極少發生。猶太教完全沒有出現過如歐洲近世的基督教聖戰那樣的東西,也沒有如伊斯蘭教遜尼派和什葉派之間存在的那種不時撕裂彼此關係的深沉敵意。猶太教內部的寬容程度是本書探討的主題之一。
同時,史書也一定要追溯猶太教內部從一個時期到另一個時期的發展變遷,因此只要情況許可,我都盡力展現猶太教的各分支與前面幾代的關聯,並且點出這些分支選擇強調前幾代傳統中的哪些特定元素。猶太教大多數的教派都聲稱自己忠於過去的傳統,那麼,會出現如此多元的變化似乎又顯得奇怪了。原來,保守的說詞背後往往藏有改變和革新。這部史書將會指出,有哪一些革新會影響後世猶太人的宗教生活,又有哪一些最後將銷聲匿跡。
無論在哪一個時期,要給猶太人下一個明確的定義都是很不容易的。若以為在複雜的現代世界來臨前,猶太人的身分認同都是安全穩當、沒有問題的,那可就錯了。在任何時期,那些認為自己是猶太人的人,其自我認知與他人的認知可能並不一致:雙親之中只有一位是猶太人,這樣的人身分地位難以確定,這個問題早在約瑟夫斯寫書的年代就已受到關注,因為猶太人是在西元一世紀左右才開始把母親的身分視為決定性的因素,而非父親的身分;當時和現在一樣,對於外幫人改信猶太教可能只有一部分的猶太人認可,另一部分則不承認。本書採取的實際解決辦法就是,只要任何個人或團體準備好要跟猶太人一樣,使用從古至今指涉自我的三個主要名稱來稱呼自己,便都當成猶太人看待。「以色列人」、「希伯來人」和「猶太人」起初都有各自的特定指涉對象,但後來猶太人對於這三個詞的用法幾乎沒有區分。某些和猶太教分離的團體(如撒馬利亞人和部分的早期基督徒)決定稱自己為「以色列人」,而非「猶太人」,以示明確的區隔。
就連那些仍留在猶太教團體裡的猶太人,對於這些名稱的意涵可能也各自有不同的看法。在英文裡,「希伯來人」這個詞在十九世紀時用來指涉猶太人,是蠻有禮貌的用語,但是現今卻帶有些許的冒犯意味;在法國,十九世紀的猶太人叫自己「以色列人」,而「猶太人」這個詞直到最近才喪失了貶低的意涵。西元一世紀遭逢政治壓力時,猶太人在希伯來語和希臘語當中轉換指稱自己的用詞,顯示上述現象不是近代才出現的。這一切都與歷史背景有關,而歷史背景又能說明猶太教內部的發展,因此本書會觸及許多近東和歐洲以及(到更晚近的時期)美洲和其他地區的歷史,以便解釋本書主要關注的宗教變遷課題。 因此,發生在廣大世界的事件及其對猶太人所造成的影響,形成了本書劃分猶太教歷史各時期的依據,從近東地區的帝國、希臘羅馬文明到基督化的歐洲,再到伊斯蘭教的巨大影響,以及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所形塑出來的現代,一直到今天複雜的猶太世界(許多外地猶太人的命運和以色列這個國家密不可分)。劃分這些時期的歷史事件當中,只有一件是與猶太人的歷史有關,那就是西元七〇年耶路撒冷第二聖殿被毀。這起事件讓猶太教的發展進入全新時期,對於現存的各種猶太教表現形式都具有深遠的影響。當時的猶太人不太可能體認到失去聖殿後他們的宗教會出現多大的改變,但將西元七〇年當作猶太教歷史的一個轉捩點之所以很合理,其中一個特別重要的原因是,這麼做能糾正基督教對於猶太教神學觀念的謬誤,認為猶太教是舊約的宗教,在基督教出現之後就被取代,並被視為是多餘的。在現代世界形塑了所有猶太人宗教信仰的拉比猶太教,其實是在西元第一個千年之間演變出來的,和基督教會並行發展。拉比猶太教的基礎建立在一套文本集成上,基督徒稱這些文本為舊約聖經,猶太人則稱之為希伯來聖經。拉比特別將希伯來聖經的前五本書「摩西五經」指定為妥拉(原意為「教導」),他們也用這個詞來指涉更通泛的典籍,凡是透過天啟傳授給猶太人的指導教誨,都可稱作妥拉。但,拉比不是只有逐字逐句研讀聖經。他們發展米大示(midrash,原意為「教誨的闡述」)的技巧,將對聖經文本的詮釋納入《哈拉卡》(halakhah,原意為「律法」)中,與經由習俗和口述傳統傳遞的律法規則相符。在拉比猶太教裡,《哈拉卡》(尤其是保存在《巴比倫塔木德》﹝Babylonian Talmud﹞)裡的版本,實際上就和聖經一樣重要。
數世紀以來,猶太教以許多不同的語言表達,反映了這些周遭的文化。猶太人的官方語言是希伯來語,但聖經裡也找得到亞蘭語,亦即西元前一千年近東地區使用的方言。西元一世紀保存下來的猶太著作大部分是以希臘文寫成,而中世紀的猶太哲學重要著作則是以阿拉伯文寫成。在一本用英文寫成的書裡,很難確切傳達這些著作所處的多樣語言和文化世界中,必然會存在的細微差異,也很難傳達字源相當不同的詞語,在猶太人的認知裡為何可能指涉的是同一件事。例如,聖經裡說到位於地中海東岸的那片應許給猶太人的土地,在聖經最前面的敘述稱為迦南,但在聖經他處卻稱為以色列地;波斯帝國的耶胡德省(Yehud)以及希臘統治下的猶地亞(Judaea),在西元一三五年被羅馬政府命名為敘利亞-巴勒斯坦省(Syria Palaestina)。這樣的結果可能會讓現今的讀者十分困惑,但是措辭的選用常常具有其重要性,因此我會盡量讓參考來源本身表達出這點。
有些讀者可能會覺得,想客觀呈現猶太教歷史是相當天真的。十九世紀的歐洲出現了「猶太學研究」(Wissenschaft des Judentums),開啟猶太歷史的科學研究,當中有許多偉大的學者寫書,目的是要在沒有傳統拉比詮釋的包袱下,以批判的眼光評估古代猶太文獻,藉此強化當時猶太教內部某些趨勢的真實性。猶太研究確定成為西方大學所認可的學術領域後,特別是從一九六〇年代起,這種與時下宗教爭議產生關聯的現象已十分少見。在歐洲,許多猶太研究的教授並不是猶太人,因此他們聲稱能不受感情左右地鑽研自己的學科,是具有一定的可信度的,雖說基督教或無神論的預設立場當然也必會導致偏見。這不是我的立場。我生在一個英國猶太人的家庭,我們對自己的猶太認同非常認真看待。家父的圖書室擺滿了從祖父那兒繼承下來的猶太教書籍;我的祖父在倫敦的西葡猶太會堂擔任幹事多年,自己也寫過書,包括一本猶太人歷史。我們家實踐猶太教禮儀的方式通常只有週五晚上、安息日前夕的晚餐和每年的逾越節晚宴,並偶爾參加貝維斯馬克斯猶太會堂(Bevis Marks synagogue)的禮拜。青年時期的我有點叛逆,決定依循一種比較嚴守猶太教規範的生活方式(我的家人對此展現了令人欽佩的耐性)。我在牛津猶太會堂(Oxford Jewish Congregation)找到了歸屬,這意義應該十分重大,因為這是英國十分特別的一個會堂,在單一團體中同時包容了進步派、保守派與正統派的禮拜儀式。這樣的背景讓我對於猶太教發展史當中有關核心與邊緣的認知產生多大的影響,就由讀者來評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