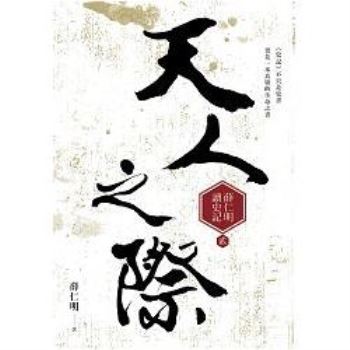第一堂(節錄)
愛「狎侮」人的劉邦——不正經反而有能量
關於這點,我們先不管,再來看劉邦的「狎侮」。狎侮不等於霸凌,劉邦會鬧別人,但不會霸凌。霸凌跟鬧很不一樣,霸凌是會傷到對方的,可是鬧最多只是把對方搞到哭笑不得而已。劉邦會跟你鬧、跟你玩,捉弄你,可是不會真的霸凌你。一個大氣的人不會霸凌別人。會霸凌別人的人,基本上都小咖。沒有一個大咖會霸凌別人,所以絕對沒有一個霸凌別人的人最後打得了天下。除了劉邦,項羽也不會霸凌人。不過,項羽會直接把人殺了。
狎侮就是跟你玩、跟你鬧,弄到快發脾氣了,再搓一搓你的頭,說道,沒關係,好玩嘛!對他而言,什麼事都好玩,因此可以在極短的時間內,把人跟人之間的隔閡全部消除掉,所以這種人打得了天下。我在西安有個學生,也算是這種會狎侮人的。他狎侮到什麼程度呢?記得我第一本簡體書《孔子隨喜》在大陸出版後,在上海季風書店辦了一個新書會,有一群朋友,分別從浙江、南京、天津,還有一個從日本過來。他看到人多,就勾著我的肩膀,說:咱們師徒拍一張照片吧!講完之後,拍拍我的肩膀,說:這是我的得意門生!像這種話,正常的師生關係中當然不可能聽見,可他做這種事,就做得很天經地義。我了解他,所以也覺得好玩。可我南京的朋友就因為有些事被他差點惹毛了,因為他什麼事情都沒大沒小、沒要沒緊,什麼時候都馬馬虎虎、隨隨便便,有人看他這種無賴的樣子,當然會很抓狂。可是,他的能耐就在於,當你快抓狂的那一剎那,他會啥事都沒發生過地岔開,跟你鬧鬧,好像也真的就沒事了。這種人,就是會狎侮人。會狎侮的人,外表看來,常常沒半點正經,可當他嚴肅起來,卻比誰都更正經。我西安這個學生,當初在山東讀物理系,讀到大四,受不了學院體系,覺得讀那些東西根本就糟蹋人,於是就辦了退學。大四退學之後,跑回西安住。我問他:你在西安靠什麼過生活?他毫無遮掩、直接就說:在色情場所工作。西安有一種色情場所,叫黑舞廳,大眾化消費,花些錢就可以進去,摟著舞女跳,跳一段時間之後,燈光全暗,然後,大家就不妨自行想像。他就是在那種地方工作,還一直跟我說,有機會到西安,一定要帶我去黑舞廳。我笑著說:你會被師母打死喲!有趣的是,他在這種地方上班,平常下班後,逛的又是些什麼地方?他說,下了班,就逛兩種地方,一是佛寺,二是道觀。平常讀什麼書?讀十三經。這就有意思了。
像這種人,在不正經的背後,某些關鍵時候,反而會有一種異常的能量。他平常的狀態,有點類似莊子所講的「渾沌」。反過來說,平時一板正經的人,真遇到要緊的事情,反而常常比較沒能量。平日老狎侮的人,他的生命就好像一個渾沌的狀態,整個能量就這樣含著、蓄著,真遇到關鍵時刻,就源源不絕似地湧現出來。所以遇到這種人,我們得稍微分辨一下,他到底是真正的混混?還是內有丘壑呢?
《史記》的閒筆,中國人的好玩與自由
下一小段要特別說一下: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時時冠之。高祖當亭長的時候,會用竹皮編冠。剛剛講過,亭長底下有兩個手下,其中一個就叫「求盜」,專門負責抓盜賊之類的。「之薛」的「之」,就是「到」,到薛地去製冠,然後常常拿起來戴。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等到他有地位之後,就常常戴這個冠,這就是後來人們所說的「劉氏冠」。司馬遷寫這段,看似無關宏旨。如果〈高祖本紀〉把這小段抽掉,也不影響任何情節,對於後來的歷史發展,更沒甚麼妨礙。但是,《史記》類似無甚相干的段落,卻四處可見。我們把這樣的段落,叫作「閒筆」。《史記》常有閒筆。大家如果讀《資治通鑑》,《資治通鑑》絕對不會有閒筆,因為儒者都一刻不能閒,從不做「無益」之事。哈哈!閒筆是中國著作中常見的特色,最好的例子,就是章回小說。章回小說每個要角登場之前,裡裡外外,總要先鋪排一段,鋪排之餘,常常還再寫一、兩首詩,歌詠一番。如果把這些詩拿掉,會不會影響情節?當然不會。可是,在古典小說裡面,類似無關緊要的篇幅,卻多得不得了。為什麼?因為古人知道,關心一件事,不能只關心情節,更該關心的是事情後頭那個人的性情。寫這些「無關緊要」的閒筆,都是為了描寫人物的性情。只有掌握得了性情,對於情節的演變,才可能有一種更接近核心的體會。
換句話說,中國人的敘述並不是直線邏輯、一環扣一環的目的論,所有的鋪陳也不必然指向一個最終的目標。中國的敘述方式當然有個大方向,可時刻也都能圓滿自足,準確地說,中國的東西都有一個「當下性」。大家如果懂這點,看傳統戲曲才會看得開心;否則以西方的角度來看,就會覺得傳統戲曲怎麼都如此拖沓?故事推展怎麼都如此緩慢?譬如《四郎探母》的第一折《坐宮》,五十分鐘只講一件事情,就是楊四郎心事重重、吞吞吐吐,最後終於跟鐵鏡公主說:「我想見我媽。」以故事而言,平淡、瑣碎、情節幾乎停頓,可大家知道,《四郎探母》的《坐宮》是一折多好的傳統老戲呀!
戲曲的特色是戲愈老、愈熟,大家愈愛看,真所謂百看不厭。看熟戲與情節幾乎無關,反正情節早知道了,大家根本就不在意。所以中國人看戲,與其說是關心故事的發展,更不如說是在「涵泳玩味」故事中的生命意味。「涵泳玩味」就牽涉到中國文明兩個關鍵字的其中一個:「樂」。「禮樂」、「禮樂」,樂是幹嘛的?樂就是涵詠、就是玩味,藉著這樣的「涵泳玩味」,進而再滋養人的生命。《史記》的文章就有「樂」的境界,可以有閒筆,可以蕩出去,不會只追著一條線索,讓讀者只關心:再來呢、再來呢?不會,司馬遷不會把文章寫到這麼緊繃、這麼令人喘不過氣來。他寫到一件事情,可以當下蕩開,大家隨著他游蕩了一回,回頭再看,不僅遊蕩得好玩,更突然胸襟一開、氣息綿長了。這其實是《史記》作為經典非常重要的特色。我們讀《史記》,有兩個關鍵的切入點:第一是「詩情」,第二是「修行」。司馬遷寫《史記》是有詩情的,《資治通鑑》沒有。所有中國的好作品,一定得先有詩情。
墨子在先秦時代那麼興盛,孟子不是說了,「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可秦漢之後,墨家卻一下子就衰落了。箇中原因,當然很多,可其中一條,實在是因為墨子的文章寫得太差,毫無詩情可言。最好的反例,則是孟子。孟子最大的優勢就是文章寫得極好,有種氣場,有股感染力,讓別人即使不贊成他都忍不住要一直讀下去。這是中國的特色,任何東西要有文采,要能讓人涵詠玩味;所有可以傳下來的東西,必定是文學的、必定有詩情,這是很重要的關鍵。
中國的東西,只要是純說理,即使說得再好,也沒用。包括佛經。當年玄奘不辭辛勞,游學印度十七載,可他翻譯的版本,為什麼沒有鳩摩羅什那麼通行呢?我想,就是因為他的文筆比不上鳩摩羅什吧!玄奘在中國的名聲那麼大,得到皇家的資助,又出了幾個極突出的弟子,可是他創的法相宗卻三代而衰,為什麼?因為法相宗那種重視邏輯、推理,思辨性的東西,不符合中國人的性情。換言之,玄奘的譯本也好,創立的法相宗也罷,都少了中國人很在意的那份詩情。
這樣的詩情,就決定了中國人看事情的角度。一方面虛實相生,一方面若有似無。因此,中國人不在意情節緊湊,也不在意邏輯緊密,更不在意直線發展。這和西方人看事情的視角大不相同。西方人看事情,兩個點之間,很習慣從A點到B點直接拉一條直線;就像西方的大公園,門口總有一條很大的路,兩側花草,整齊對稱;從頭到尾,一覽無遺。中國人從來不是這樣看事情的。A跟B這兩個點之間,中國人非得要弄得彎彎曲曲不可,A點總是看不到B點,否則,就不好看,也沒意思。所以中國的庭院有個照壁,不讓人一覽無遺,最好就像蘇州庭園那樣,曲徑通幽,移步換景,走一步就一個景,走一步又另一個景。這樣的曲曲折折,正是中國的特色。這樣的特色,也反映在中國語言的強烈詩性。因此,中國人的語言特別豐富,特別具有彈性;也因此,中國人擅長說反話、講假話。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我以前沒開竅,一直到年紀不小了,才終於懂得一件簡單的事兒。懂什麼呢?相較於男人,女人其實更懂得語言虛實的詩性。我後來才知道,原來女人稱讚男人有一種方式,是跟男人說:你好壞!原來,她說「你好壞!」的意思,其實就是「你好好哦!」。當我們使用這種語言時,一向都使用得如此自然而心照不宣,絕對不會有一個男人在聽到「你好壞」的時候,很嚴肅地轉過頭來問:我壞在哪裡?如果有這麼問的男人,我們只好拜託他:您去撞牆,好不好?
正因為中國人的曲折反復、虛實相生,所以章回小說的故事每回發展到大家急著要看結果時,常常隨即轉了個彎,說時遲、那時快,然後便蕩開來,另外又寫了一、兩萬字。岔出去寫了半天,好,終於又一句「言歸正傳」,才悠悠緩緩回到剛剛的情節。這就是中國的特色。中國人不管在多麼緊張、多麼關鍵的時刻,都有辦法從那個節骨眼跳脫出來。這正是中國人的解脫境界。換句話說,在中國人的眼裡,沒有什麼事情緊要到可以把人給真正束縛住;再要緊的事情,我們也都可以當下解脫。因此,章回小說裡,尤其是在戲曲裡,常常故事停頓,沒劇情發展,純粹就在情感或細節中鋪衍,大家卻覺得很好看,似乎也不關心故事情節發展到哪兒了。為什麼?因為情節對大家而言,固然重要;但再怎麼重要,仍須能從情節解脫開來。所有中國的東西,背後都有同樣的這個原理。
這樣的隨處解脫,就是中國人的「自由」。中國人的「自由」,跟西方人講的不太一樣。中國人講「自由」,不強調西方式外在的無拘無束,而是再多的牽絆都能無礙於內心的解脫。反之,只要被一個東西壓住、掙脫不了,那都不是自由。無論這東西看來再好、再動人、甚至再神聖,總之都是不祥之物。
所以,為什麼孟子文章那麼好,可我還是要批評他呢?畢竟,即使你是對的,只要堅持自己是正義化身,對別人可以那麼義正辭嚴、毫不留情,你都已經被心裡的正義給鎮魘住了,那就是不祥之物。換句話說,縱使你心裡有個真理,那真理也必須能呼吸吞吐,這才是中國人最高層次的自由。從這個角度看,如果你讀歷史,從頭到尾只關心整個發展的情節,最後就會變得無趣。最後不僅是無趣,還因為你太關心這些貌似重要的東西,反而失去最重要的自由。正因如此,我才會寫〈消散迷失已久的魂魄,久違了!──我讀史記〉那篇文章,談《史記》與《資治通鑑》的比較。司馬光因為是個儒者,很關心「資治」,很關心實際的事情,結果就因為太「實」了,便把《史記》裡許多閒筆、看來與「資治」沒那麼直接關聯的東西,統統都刪掉了。可一旦把這些東西刪掉之後,反而失去了呼吸吞吐的能力。一個人能否「治」得了天下,並不是靠著直線思維,其實更多是曲線思考,老子說的「曲則全」,得要有呼吸吞吐的能耐,才成得了大事。所以看事情不能只直線地看因果關係,那樣反而做不成事。有些人愈急著把事情做好,常常愈做不好,原因就在這裡。相反地,你看一些能成事的人,常常就是吊兒郎當的,生命寬鬆,沒太強烈的目的性,遇到關鍵時刻,反而容易轉身、找到出口,因此可以把事情弄好。這裡面都有類似的原理在。所以大家看到司馬遷寫這種閒筆的時候,別小看它。
那麼,司馬遷為什麼寫「劉氏冠」呢?第一個,劉邦是個閒人,有閒情逸致;第二個,劉邦花樣多,凡事好玩。這個「好玩」,最重要。正因為好玩,所以劉邦跟項羽爭到你死我活之時,依然可以遊刃有餘,再怎麼艱難,都不為所困。如果在垓下被圍的,換成是劉邦,當他殺出重圍,最後逃到烏江,又會怎麼樣?顯然劉邦絕對不會「無顏見江東父老」,他沒這種問題嘛!對不對?他逃到烏江,回頭一想,想到自己逃得這麼狼狽,可能還覺得好好玩!好玩,事情就困不住他;你那麼認真、凡事那麼較真,最後就可能把自己給逼死。
愛「狎侮」人的劉邦——不正經反而有能量
關於這點,我們先不管,再來看劉邦的「狎侮」。狎侮不等於霸凌,劉邦會鬧別人,但不會霸凌。霸凌跟鬧很不一樣,霸凌是會傷到對方的,可是鬧最多只是把對方搞到哭笑不得而已。劉邦會跟你鬧、跟你玩,捉弄你,可是不會真的霸凌你。一個大氣的人不會霸凌別人。會霸凌別人的人,基本上都小咖。沒有一個大咖會霸凌別人,所以絕對沒有一個霸凌別人的人最後打得了天下。除了劉邦,項羽也不會霸凌人。不過,項羽會直接把人殺了。
狎侮就是跟你玩、跟你鬧,弄到快發脾氣了,再搓一搓你的頭,說道,沒關係,好玩嘛!對他而言,什麼事都好玩,因此可以在極短的時間內,把人跟人之間的隔閡全部消除掉,所以這種人打得了天下。我在西安有個學生,也算是這種會狎侮人的。他狎侮到什麼程度呢?記得我第一本簡體書《孔子隨喜》在大陸出版後,在上海季風書店辦了一個新書會,有一群朋友,分別從浙江、南京、天津,還有一個從日本過來。他看到人多,就勾著我的肩膀,說:咱們師徒拍一張照片吧!講完之後,拍拍我的肩膀,說:這是我的得意門生!像這種話,正常的師生關係中當然不可能聽見,可他做這種事,就做得很天經地義。我了解他,所以也覺得好玩。可我南京的朋友就因為有些事被他差點惹毛了,因為他什麼事情都沒大沒小、沒要沒緊,什麼時候都馬馬虎虎、隨隨便便,有人看他這種無賴的樣子,當然會很抓狂。可是,他的能耐就在於,當你快抓狂的那一剎那,他會啥事都沒發生過地岔開,跟你鬧鬧,好像也真的就沒事了。這種人,就是會狎侮人。會狎侮的人,外表看來,常常沒半點正經,可當他嚴肅起來,卻比誰都更正經。我西安這個學生,當初在山東讀物理系,讀到大四,受不了學院體系,覺得讀那些東西根本就糟蹋人,於是就辦了退學。大四退學之後,跑回西安住。我問他:你在西安靠什麼過生活?他毫無遮掩、直接就說:在色情場所工作。西安有一種色情場所,叫黑舞廳,大眾化消費,花些錢就可以進去,摟著舞女跳,跳一段時間之後,燈光全暗,然後,大家就不妨自行想像。他就是在那種地方工作,還一直跟我說,有機會到西安,一定要帶我去黑舞廳。我笑著說:你會被師母打死喲!有趣的是,他在這種地方上班,平常下班後,逛的又是些什麼地方?他說,下了班,就逛兩種地方,一是佛寺,二是道觀。平常讀什麼書?讀十三經。這就有意思了。
像這種人,在不正經的背後,某些關鍵時候,反而會有一種異常的能量。他平常的狀態,有點類似莊子所講的「渾沌」。反過來說,平時一板正經的人,真遇到要緊的事情,反而常常比較沒能量。平日老狎侮的人,他的生命就好像一個渾沌的狀態,整個能量就這樣含著、蓄著,真遇到關鍵時刻,就源源不絕似地湧現出來。所以遇到這種人,我們得稍微分辨一下,他到底是真正的混混?還是內有丘壑呢?
《史記》的閒筆,中國人的好玩與自由
下一小段要特別說一下: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時時冠之。高祖當亭長的時候,會用竹皮編冠。剛剛講過,亭長底下有兩個手下,其中一個就叫「求盜」,專門負責抓盜賊之類的。「之薛」的「之」,就是「到」,到薛地去製冠,然後常常拿起來戴。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等到他有地位之後,就常常戴這個冠,這就是後來人們所說的「劉氏冠」。司馬遷寫這段,看似無關宏旨。如果〈高祖本紀〉把這小段抽掉,也不影響任何情節,對於後來的歷史發展,更沒甚麼妨礙。但是,《史記》類似無甚相干的段落,卻四處可見。我們把這樣的段落,叫作「閒筆」。《史記》常有閒筆。大家如果讀《資治通鑑》,《資治通鑑》絕對不會有閒筆,因為儒者都一刻不能閒,從不做「無益」之事。哈哈!閒筆是中國著作中常見的特色,最好的例子,就是章回小說。章回小說每個要角登場之前,裡裡外外,總要先鋪排一段,鋪排之餘,常常還再寫一、兩首詩,歌詠一番。如果把這些詩拿掉,會不會影響情節?當然不會。可是,在古典小說裡面,類似無關緊要的篇幅,卻多得不得了。為什麼?因為古人知道,關心一件事,不能只關心情節,更該關心的是事情後頭那個人的性情。寫這些「無關緊要」的閒筆,都是為了描寫人物的性情。只有掌握得了性情,對於情節的演變,才可能有一種更接近核心的體會。
換句話說,中國人的敘述並不是直線邏輯、一環扣一環的目的論,所有的鋪陳也不必然指向一個最終的目標。中國的敘述方式當然有個大方向,可時刻也都能圓滿自足,準確地說,中國的東西都有一個「當下性」。大家如果懂這點,看傳統戲曲才會看得開心;否則以西方的角度來看,就會覺得傳統戲曲怎麼都如此拖沓?故事推展怎麼都如此緩慢?譬如《四郎探母》的第一折《坐宮》,五十分鐘只講一件事情,就是楊四郎心事重重、吞吞吐吐,最後終於跟鐵鏡公主說:「我想見我媽。」以故事而言,平淡、瑣碎、情節幾乎停頓,可大家知道,《四郎探母》的《坐宮》是一折多好的傳統老戲呀!
戲曲的特色是戲愈老、愈熟,大家愈愛看,真所謂百看不厭。看熟戲與情節幾乎無關,反正情節早知道了,大家根本就不在意。所以中國人看戲,與其說是關心故事的發展,更不如說是在「涵泳玩味」故事中的生命意味。「涵泳玩味」就牽涉到中國文明兩個關鍵字的其中一個:「樂」。「禮樂」、「禮樂」,樂是幹嘛的?樂就是涵詠、就是玩味,藉著這樣的「涵泳玩味」,進而再滋養人的生命。《史記》的文章就有「樂」的境界,可以有閒筆,可以蕩出去,不會只追著一條線索,讓讀者只關心:再來呢、再來呢?不會,司馬遷不會把文章寫到這麼緊繃、這麼令人喘不過氣來。他寫到一件事情,可以當下蕩開,大家隨著他游蕩了一回,回頭再看,不僅遊蕩得好玩,更突然胸襟一開、氣息綿長了。這其實是《史記》作為經典非常重要的特色。我們讀《史記》,有兩個關鍵的切入點:第一是「詩情」,第二是「修行」。司馬遷寫《史記》是有詩情的,《資治通鑑》沒有。所有中國的好作品,一定得先有詩情。
墨子在先秦時代那麼興盛,孟子不是說了,「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可秦漢之後,墨家卻一下子就衰落了。箇中原因,當然很多,可其中一條,實在是因為墨子的文章寫得太差,毫無詩情可言。最好的反例,則是孟子。孟子最大的優勢就是文章寫得極好,有種氣場,有股感染力,讓別人即使不贊成他都忍不住要一直讀下去。這是中國的特色,任何東西要有文采,要能讓人涵詠玩味;所有可以傳下來的東西,必定是文學的、必定有詩情,這是很重要的關鍵。
中國的東西,只要是純說理,即使說得再好,也沒用。包括佛經。當年玄奘不辭辛勞,游學印度十七載,可他翻譯的版本,為什麼沒有鳩摩羅什那麼通行呢?我想,就是因為他的文筆比不上鳩摩羅什吧!玄奘在中國的名聲那麼大,得到皇家的資助,又出了幾個極突出的弟子,可是他創的法相宗卻三代而衰,為什麼?因為法相宗那種重視邏輯、推理,思辨性的東西,不符合中國人的性情。換言之,玄奘的譯本也好,創立的法相宗也罷,都少了中國人很在意的那份詩情。
這樣的詩情,就決定了中國人看事情的角度。一方面虛實相生,一方面若有似無。因此,中國人不在意情節緊湊,也不在意邏輯緊密,更不在意直線發展。這和西方人看事情的視角大不相同。西方人看事情,兩個點之間,很習慣從A點到B點直接拉一條直線;就像西方的大公園,門口總有一條很大的路,兩側花草,整齊對稱;從頭到尾,一覽無遺。中國人從來不是這樣看事情的。A跟B這兩個點之間,中國人非得要弄得彎彎曲曲不可,A點總是看不到B點,否則,就不好看,也沒意思。所以中國的庭院有個照壁,不讓人一覽無遺,最好就像蘇州庭園那樣,曲徑通幽,移步換景,走一步就一個景,走一步又另一個景。這樣的曲曲折折,正是中國的特色。這樣的特色,也反映在中國語言的強烈詩性。因此,中國人的語言特別豐富,特別具有彈性;也因此,中國人擅長說反話、講假話。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我以前沒開竅,一直到年紀不小了,才終於懂得一件簡單的事兒。懂什麼呢?相較於男人,女人其實更懂得語言虛實的詩性。我後來才知道,原來女人稱讚男人有一種方式,是跟男人說:你好壞!原來,她說「你好壞!」的意思,其實就是「你好好哦!」。當我們使用這種語言時,一向都使用得如此自然而心照不宣,絕對不會有一個男人在聽到「你好壞」的時候,很嚴肅地轉過頭來問:我壞在哪裡?如果有這麼問的男人,我們只好拜託他:您去撞牆,好不好?
正因為中國人的曲折反復、虛實相生,所以章回小說的故事每回發展到大家急著要看結果時,常常隨即轉了個彎,說時遲、那時快,然後便蕩開來,另外又寫了一、兩萬字。岔出去寫了半天,好,終於又一句「言歸正傳」,才悠悠緩緩回到剛剛的情節。這就是中國的特色。中國人不管在多麼緊張、多麼關鍵的時刻,都有辦法從那個節骨眼跳脫出來。這正是中國人的解脫境界。換句話說,在中國人的眼裡,沒有什麼事情緊要到可以把人給真正束縛住;再要緊的事情,我們也都可以當下解脫。因此,章回小說裡,尤其是在戲曲裡,常常故事停頓,沒劇情發展,純粹就在情感或細節中鋪衍,大家卻覺得很好看,似乎也不關心故事情節發展到哪兒了。為什麼?因為情節對大家而言,固然重要;但再怎麼重要,仍須能從情節解脫開來。所有中國的東西,背後都有同樣的這個原理。
這樣的隨處解脫,就是中國人的「自由」。中國人的「自由」,跟西方人講的不太一樣。中國人講「自由」,不強調西方式外在的無拘無束,而是再多的牽絆都能無礙於內心的解脫。反之,只要被一個東西壓住、掙脫不了,那都不是自由。無論這東西看來再好、再動人、甚至再神聖,總之都是不祥之物。
所以,為什麼孟子文章那麼好,可我還是要批評他呢?畢竟,即使你是對的,只要堅持自己是正義化身,對別人可以那麼義正辭嚴、毫不留情,你都已經被心裡的正義給鎮魘住了,那就是不祥之物。換句話說,縱使你心裡有個真理,那真理也必須能呼吸吞吐,這才是中國人最高層次的自由。從這個角度看,如果你讀歷史,從頭到尾只關心整個發展的情節,最後就會變得無趣。最後不僅是無趣,還因為你太關心這些貌似重要的東西,反而失去最重要的自由。正因如此,我才會寫〈消散迷失已久的魂魄,久違了!──我讀史記〉那篇文章,談《史記》與《資治通鑑》的比較。司馬光因為是個儒者,很關心「資治」,很關心實際的事情,結果就因為太「實」了,便把《史記》裡許多閒筆、看來與「資治」沒那麼直接關聯的東西,統統都刪掉了。可一旦把這些東西刪掉之後,反而失去了呼吸吞吐的能力。一個人能否「治」得了天下,並不是靠著直線思維,其實更多是曲線思考,老子說的「曲則全」,得要有呼吸吞吐的能耐,才成得了大事。所以看事情不能只直線地看因果關係,那樣反而做不成事。有些人愈急著把事情做好,常常愈做不好,原因就在這裡。相反地,你看一些能成事的人,常常就是吊兒郎當的,生命寬鬆,沒太強烈的目的性,遇到關鍵時刻,反而容易轉身、找到出口,因此可以把事情弄好。這裡面都有類似的原理在。所以大家看到司馬遷寫這種閒筆的時候,別小看它。
那麼,司馬遷為什麼寫「劉氏冠」呢?第一個,劉邦是個閒人,有閒情逸致;第二個,劉邦花樣多,凡事好玩。這個「好玩」,最重要。正因為好玩,所以劉邦跟項羽爭到你死我活之時,依然可以遊刃有餘,再怎麼艱難,都不為所困。如果在垓下被圍的,換成是劉邦,當他殺出重圍,最後逃到烏江,又會怎麼樣?顯然劉邦絕對不會「無顏見江東父老」,他沒這種問題嘛!對不對?他逃到烏江,回頭一想,想到自己逃得這麼狼狽,可能還覺得好好玩!好玩,事情就困不住他;你那麼認真、凡事那麼較真,最後就可能把自己給逼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