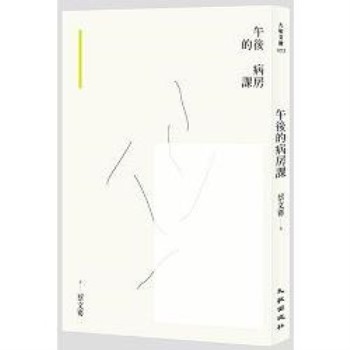午後的病房課
拉開百葉窗簾,夏日午後強盛的熱度穿透了密閉的玻璃窗,讓長年由中央空調控制、病人總是抱怨太冷的病房慢慢溫暖了起來。雖然大半的天光被對面高聳的醫療大樓遮蔽了,照射進入的陽光不如原先想像的那般耀眼,但淡黃色的流金光澤從窗邊的地板開始,逐漸擴散暈染了整個房間,現在映入眼底的,不再只有強調整齊乾淨卻單調冷漠的白色日光燈管、潔白床單和亮白色牆面。
轉身我看見同學們身上的白袍,在陽光下反射出來的,除了當初廠商為求純白的視覺效果而加入的大量螢光劑,還有某種小小而溫柔的光輝。
三個多小時過去了,我們好不容易完成初步的病史詢問,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幾乎放棄和老先生對談,除了帕金森氏症造成說話緩慢、結巴;輕微的失智情形讓他連上星期發生的事情也無法清楚交代,遑論數十年來複雜紛亂的病情;以及肺部的嚴重感染迫使他不斷急促地喘氣,再加上放置鼻胃管的不適感,往往老先生辛苦地由喉嚨發出一串斷斷續續的聲音,我們卻完全無法理解。
老先生也許是獨居老人或由安養機構收容,他身邊並沒有其他親友可供我們探詢病況或幫忙翻譯老先生的意思,只有醫院的社工在旁幫忙他處理文件等雜事,不得已我們決定嘗試筆談的方法,我們用幾乎是吼叫的音量,將問題盡量精簡並且反覆詢問數次,患有重聽的老先生終於聽懂之後,會用不斷顫抖的左手扶著同樣不斷顫抖的右手腕,企圖努力將筆平穩的握緊,在紙上寫下他那歪斜扭曲同時又小又擠的字跡,我們像在進行某種填字遊戲,從幾個比劃較少、結構簡單的字開始辨識,然後集思廣益揣摩著老先生的意思,一個字一個字仔細比對確定字型和字數符合我們猜想的句子之後,再慢而清楚的念出來給老先生聽,老先生會吃力的點點頭或搖搖頭來做出裁判。
踏入病房之前,學長警告過我們,老先生並不是一個配合度很高的病人,但筆談進行了一陣子以後,雙方都漸漸卸下對彼此的戒心和不信任,甚至建立起了某種默契,我們解讀字跡所需的時間越來越短,正確率亦有所提升,老先生也努力集中精神聽我們講話所以理解程度越來越好,我們就這樣一點一點拼湊出他的病史,嘗試去探索老先生老舊殘破卻珍貴的生命輿圖。雖然記憶的輕微錯亂導致有時他的回答反反覆覆不合邏輯,我們還是可以隱約體會感受,那些遷徙顛沛的生命歷程和不斷打擊他的生理病痛,是如何讓一個垂暮之年的老人備受折磨。老先生其實比我們想像的來得健談,但當我們幾經猶豫,仍然決定詢問他的家族病史時,老先生用力咬著微微顫抖的唇,雙眼浸在淚水裡看起來有點失焦,不像在望著我們,而是凝視著很遙遠的時空。
也許只是我的錯覺。老先生的情緒由一開始的害怕、焦躁,到晤談中段時的略顯激動努力噙淚,進行至後半段他終於慢慢放鬆下來,呼吸好像不那麼急促,全身的肌肉也不再那麼僵硬,我們就這樣的以各自的表達方式,平靜的交談著。令我驚訝的是我忽然發現這樣的溝通方式其實並不造成障礙,對我這樣剛剛進入臨床見習的醫學生而言,和病人的接觸常有意想不到的困難,我曾經遇過幾位只講方言或母語的病人,雞同鴨講一陣之後,情況往往變得十分尷尬,這時我通常放棄直接與他們溝通,轉而向陪病的親友詢問細節,抑或請學長、同學來幫忙。但老先生讓我體會懂得,溝通的本質也許不在語言文字,那些固然是工具,但同理心的感受讓我們能對彼此做更深層的認識,那是再長時間的對話、再精采的修辭和說話技巧也不確保能達成的。
「以-前-沒-有-人-這-樣-問-過-我-生-病-的-事-情,謝-謝-你-們」
聽到我們很快地正確解讀出最後這行字,老先生似乎笑了,他臉部的皺紋線條因消瘦而深陷分明,加上光線和陰影將之刻劃的更為立體,所以雖然肌肉只是微微的抽動,看上去卻像是一個深邃的笑容。我們了解對於患有帕金森氏症的老先生來說這是多麼困難且費力,顏面表情肌肉失去彈性的木然「面具臉」症狀,是帕金森氏症最常見的臨床表現之一,卻讓許多人誤以為老先生的個性既古怪又冷淡。
以嚴謹的學術角度來說,因為老先生的意識認知狀態並非理想,我們努力詢問獲得的病例,參考價值其實不高,但他教授給我們的,超越了那些我們早已從課本上讀得非常熟悉的複雜繁瑣的症狀、診斷標準。我第一次真正了解到所謂醫療的基礎,原來並不在於我們平日信仰、奉為權威甚至引以為傲的最新科技和知識,而是從最單純卻必要的理解和支持開始。
離開老先生的病房之後,接下來幾個禮拜我們按照排定的班表,輪流到其他科別的病房見習,日子過得非常忙碌,每天遇見形形色色的病人,難免也有不那麼順利的時候,每次心情沮喪我會拉開病房的窗簾看看陽光,然後想起那天老先生金黃色的笑容,再重新帶著微笑回到病床前。
教學部的助教通知有指名寄給我們的病友來信時我非常驚訝,一度擔心是不是最近做錯了甚麼事情被投訴。
那是個樸實簡單的信封,封口方式和信紙的摺法也不算仔細。
信紙上有幾行很小而且歪歪斜斜的字,老先生大概是怕害羞沒有屬名,但我一眼就認出那是他的筆跡。
可惜他沒有留下地址,我很想回信告訴他:「感謝您教了我那麼多。」
黑雨
「現在還下黑雨嗎?」,我在電話中問阿公。
那是老家特有的景象。
小型的煤雨以滲漏的方式不斷落下,源自輸煤碼頭橫跨頭頂的自動輸煤帶,雖然為了偽裝融入背景而漆成亮藍色,仍然粗魯刺眼地將天空分成了兩截,上層乾淨明澈的晴空、白雲通常與我們無關,漂浮的煤灰遮蔽了天光,漁港就這樣長年被淡淡的陰霾籠罩著,像是一個隔離孤立的灰色空間,和四周的風景都不連續。
有時強勁的季風從海上呼嘯而來,夾帶著大量露天煤場堆置的礦砂,以風暴般鋪天蓋地的氣勢,把整個漁村襲捲進暗黑的漩渦之中,走在路上的人一面咳嗽,一面忍著刺痛和眼淚,勉強比對眼前模糊的景物影像,尋找可辨識的輪廓,然後趕緊躲到屋裡緊閉所有的門窗,習以為常地等待黑雨遠去。
阿公愣了一會兒,只說現在一切都變得很不一樣:「你大概不認得了。」
1.
這是通往紅毛港的唯一道路,柏油路面其實尚算寬廣,只是兩旁工業區高聳矗立著巨大的成排高爐和船塢,被重重包圍的漁鄉顯得更為低矮。進入村落前最顯眼的地標建築是火力發電廠的煙囪群,偌大的廠區占據了半面海岸,同時綿延出一道紅白相間的天際線。發電廠是經濟建設計畫的重要成果,裝置容量甚至比核電廠還要來得大,驅動著城市的日夜運轉以及無止盡的膨脹擴張。發電廠高效率地燃燒煤炭,同時也以極快的速度將港灣的舊日光輝焚掠殆盡,而漫天吐放的塵埃餘燼,沉降在歲月裡逐漸改變了小漁村的顏色。
得先穿過那些灰濛濛的畫面和記憶,然後才可以回家。
我把車子停在新開闢的廣闊停車場,這是龐大填海造陸計畫的第一階段,前身是垃圾場,而工程使用的正是大煉鋼廠的副產品爐石,和火力發電廠的廢棄物飛灰,這些廢土就地傾倒,加上長串的廢輪胎重塑出色彩造型怪異的海岸線,他們填塞了漁村原本賴以為生的海洋,淤積了住民曾經寧靜湛藍的童年回憶和海上夢想,然後為新填的土地取了個閃耀的名字「南星」,從自由貿易區到國際機場等用途眾說紛紜,只是二十年過去,舊的希望被掩埋了,新的希望仍是荒蕪一片。
很久沒有回老家,除了固執的阿公,已經沒有人願意住在破落的老房子老漁村裡,「等到這裡沒有半個人,我就走。」,阿公並不是唯一堅持的人,我們的老鄰居,開柑仔店的豐叔就理直氣壯的在電視螢光幕上宣告:「等到沒人買了,我自然就關店。」。
真的還有人在嗎。雖然中午往往是街道上最安靜的時刻,但我面前整座漁港卻連一點聲音都沒有發出,聲音是生命力的直接表現也最能顯示地域特色,可是現在這裡沒有人聲、沒有拆船廠的噪音,連以往隨處可見的養殖魚塭馬達也不再轟轟作響,沉寂的像是時間被偷偷凝結固定了,所有的動作都暫停下來,不知道甚麼時候才能重新啟動時光流轉的開關。
繞過恢偉的齊天大聖廟,我向印象中迷宮般的小巷弄行進,嚴格的限建政策執行了超過四十年,許多的房子都是以傳統街屋、合院為基礎加蓋的鐵皮屋,易建易拆的「鐵厝」不講求美觀,哪裡有空隙可利用就往哪裡搭起,房屋前後高低參差錯落,構造層次複雜,一眼望去時常看不到那條蜿蜒其間的小路,而對孩子來說,穿堂入院常是最方便的捷徑,循著微弱的入射光線在陌生的黑暗中摸索前進,也是種有趣的探險遊戲。
這麼多年之後我又回到原處,面對著廟埕旁的大榕樹,思索著該選擇哪一條路回家,儘管已經憑著印象演練過許多次,我依然沒有把握。如果走錯路,我是不是應該為了記憶的消逝感到愧疚;如果還認得路,我可不可以仍舊理所當然地直接穿越過別家的後門。
衛星導航在這裡大概沒有用,就算有詳盡確實的地圖,又要怎樣保證在記憶龐雜擁擠的迷路之間我不會走失。
結果我很快找到了阿公的家,意外地容易。整條街上只剩下一棟完整的房子,其餘的都成了斷垣殘壁或者看上去危顫欲墜,真正的困難之處,其實在於我要怎麼安全通過這些遷村工程留下的遍地瓦礫廢墟。
原來時間不只是靜止而已,早已風化崩解而不可逆轉了。
而我得通過它,才能回家。
2.
「你敢是真的欲出國讀冊喔?」
阿公的聲調聽起來並不像真的問句,和方才下午大多數的時間一樣,他好像只是自言自語著,我們兩個看起來聊了很久,其實卻鮮少交集,往往是以沉默回答了彼此的問題,然後再重新由無關緊要的小事說起。
這次不等我回答,說完這句話阿公就起身去拿擱在進屋處角落的釣竿和冰箱然後急忙地出門了,甚至連門扉也沒有闔上。或許阿公真的是怕耽擱錯過魚群活躍的時刻,又或者他不希望我看見他那時的表情,事實上,記憶裡在這座低矮陰濕的老合院內,我從來看不清楚誰的表情,不論是阿公的,父親的,或叔伯鄰人的,每個人的眉眼鼻口,都像是被強勁鹹澀的海風吹皺成了一團,糾結複雜難以理解是哭或是笑。
從小阿公總是栩栩如生地描繪,每值出海季節的盛況,淺淺而清澈的瀉湖內萬魚竄動翻騰,數百艘漁船從早到晚來回穿梭,雖然已經是數十年前的記憶了,但阿公仍堅持,這兩天適逢作大潮,加上季風正盛魚群入港避風浪,指給我看連那整排老木麻黃都給吹的搖搖晃晃,正是再好不過的釣魚時機。
由黃轉紅的夕陽持續變大,向海面迫近,陣陣晚風吹送火燒雲鑲金邊的烈焰向陸地襲來,阿公沿海岸線走去,黝黑乾瘦的身影越拉越長,海邊鹽分地帶土壤貧瘠且風勢凌厲,樹形不高但大多堅毅挺拔,生於斯長於斯的阿公,自然也有類似的特質。
猜想此時阿公已經熟練地越過防風林和堤防,隱身在消波塊的空隙間垂釣他的美好回憶。我坐在屋裡,看著老舊的門櫺框出一幅畫面,我記得那同樣也是一個悶熱的黃昏,在搬家前最後一次我坐在這裡像這樣看著,看父親忙著將大箱小箱打包好的東西運上發財小貨車,母親像是迫不及待的早早坐上了右前方的座位,我沒有哭鬧只是靜靜坐著不肯離開,父親強行把我拉上車之後總算是帶齊了行李,長鏡頭裡我們在一小段的顛簸晃動之後,很快駛離了那個畫面。
那時阿公也是什麼話都沒說,只是安靜地拿起他的釣具反方向往海港口慢慢走去。
十年逝去,門框外的風景推移的很慢,港口對岸高樓鱗次櫛比的建起,這方的海岸線卻仍然蕭索,畫面裡流動的幾乎總是離開的背影,而那些生了根的只好在原地老去。
這裡是台灣南方最大城市的西南隅,向海峽長長伸出的孤立半島,有一個富於歷史和地域的想像空間的名字,但很少人聽過或想起過它的名字。
甚至原屬於它的人也忙著拋棄這個名字。
像是我們。
3.
在上小學以前,據說我只會講專屬這座漁村的、在句尾帶有獨特口音的閩南話,而父親堅持,要把我的戶口寄在遠房親戚家,讓我可以搭每小時一班的渡輪跨區到「真正」的都會學校念書,雖然我們和他們的戶籍確確實實坐落在同一座城市裡,但大家都相信:留在這裡,不會有出路。直到升上國中搬家以前,我以寄居的名義度過了六年嘗試融入、偽裝為都市人的日子,渡輪接送我在兩岸的港口,日夜擺盪在五顏六色的高樓霓虹和低矮散落的漁家燈火之間。
現在渡輪停駛了,我也成為真正的都市人、外來者。也許基於某種防禦心理,對於大部分的小學同學我都沒有留下什麼印象了,看畢業紀念冊的團體合照上,我置身於一群擁擠的陌生人中,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小縫隙,對鏡頭擠出一絲僵硬的微笑。
除了紅毛以外。她是柑仔店豐叔的姪女,和我一齊每天從渡船頭搭船通勤上學,很自然地變成我孤獨的小學生涯中最要好的同學,因為天生髮色和膚色較淡,加上家住紅毛港,所以得到了這個她一直不喜歡的外號。紅毛同樣國小畢業後就舉家搬遷了,我們也幾乎沒有再聯絡過,只是聽說幾年以前她的雙親因意外亡故,所以紅毛又回到漁港來和豐叔同住。沒有想到後來紅毛這個外號變成我的記憶裡和這座漁村最強的連結,當我聽到有人提起紅毛港,就反射似的馬上想起她。
天已經黑得和海面再也分不清邊界,阿公還沒有回來,無事可做的我決定碰碰運氣,去柑仔店看看紅毛在不在。小店面內沒有人看顧生意,而其實也沒有必要,我向裡頭喊了一聲豐叔,回應我的是一個似乎熟悉又陌生的女聲,我知道那是紅毛。
原來豐叔也釣魚去了,紅毛邀請我到雜貨店深處昏暗窄小的客廳坐下,一陣不知道該講什麼才合宜的尷尬沉默之後,我決定請她帶我去海邊新鋪設的觀光腳踏車道和景觀咖啡店走走。
我們坐在仿歐式的露天咖啡座,看著岬角尾端四十年來從未真正啟用作導引信號塔的高字塔,在暗夜中孤獨地向四面的海發出淡藍色的光,據說它將是拆遷工程完成後,半島上唯一被保存的地標建築。
光線的顏色和角度都被設計的非常完美,創造出一種孤島上的人從未見過的,幸福和希望的氛圍。
有雨開始落下來。
起先我注意到的是那一滴一滴懸掛在紅毛髮稍、睫毛上的水珠,點點折射出咖啡座燈光的浪漫淡黃色調;然後雨勢慢慢轉強,高字塔燈火通明的窗戶把夜空中的細細雨絲照成一座自塔頂垂落的藍色瀑布。
我和紅毛隨意聊著,其他童年玩伴們是怎樣陸陸續續離開這座小漁村,而留下來的人又過得如何,真的如同媒體的報導,為了表示抗議,懷抱著炸船封港的決心嗎?
她問我回來之後有沒有到處看看。在地藝術家在舊碼頭倉庫以破碎的磁磚鑲嵌創作,企圖拼貼紅毛港充滿裂痕的圖像;居民們搬遷前留下的老照片,還滿貼在那些殘立的房屋牆面上看守家園;以及廢棄的渡輪站,不知道哪時被用鮮豔的油漆噴了一個大大的、充滿憤怒的英文單字。
時光在我們面前如此大規模且急遽的衰頹敗壞,我們能夠或者應該嘗試保存、追憶還是生氣?「至少比甚麼都不做來得好吧。」紅毛說。
雨點拍打在身上,好像被種種複雜的感覺和什麼沉重的東西給紛紛擊中,令人難以承受。
這場雨並沒有要停歇的樣子,我們終於決定離開海邊。壓低身體飛快地踩著腳踏車,正沿海岸線奔馳逃離時,忽然隱約聽見細微的「啪」一聲,像是某條細線斷裂的聲音,回頭我看見岬角盡頭的那座光亮方塔正逐層暗去,防風林旁兩列蒼白的路燈也由遠而近一一斷電,倏忽之間似乎又回到印象中總是黯淡的紅毛港夜晚。
雨仍然下著,且變得越來越大。
在完全漆黑的雨中,一路上我們穿過許多記憶,去尋找遠方想像中的光。
拉開百葉窗簾,夏日午後強盛的熱度穿透了密閉的玻璃窗,讓長年由中央空調控制、病人總是抱怨太冷的病房慢慢溫暖了起來。雖然大半的天光被對面高聳的醫療大樓遮蔽了,照射進入的陽光不如原先想像的那般耀眼,但淡黃色的流金光澤從窗邊的地板開始,逐漸擴散暈染了整個房間,現在映入眼底的,不再只有強調整齊乾淨卻單調冷漠的白色日光燈管、潔白床單和亮白色牆面。
轉身我看見同學們身上的白袍,在陽光下反射出來的,除了當初廠商為求純白的視覺效果而加入的大量螢光劑,還有某種小小而溫柔的光輝。
三個多小時過去了,我們好不容易完成初步的病史詢問,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幾乎放棄和老先生對談,除了帕金森氏症造成說話緩慢、結巴;輕微的失智情形讓他連上星期發生的事情也無法清楚交代,遑論數十年來複雜紛亂的病情;以及肺部的嚴重感染迫使他不斷急促地喘氣,再加上放置鼻胃管的不適感,往往老先生辛苦地由喉嚨發出一串斷斷續續的聲音,我們卻完全無法理解。
老先生也許是獨居老人或由安養機構收容,他身邊並沒有其他親友可供我們探詢病況或幫忙翻譯老先生的意思,只有醫院的社工在旁幫忙他處理文件等雜事,不得已我們決定嘗試筆談的方法,我們用幾乎是吼叫的音量,將問題盡量精簡並且反覆詢問數次,患有重聽的老先生終於聽懂之後,會用不斷顫抖的左手扶著同樣不斷顫抖的右手腕,企圖努力將筆平穩的握緊,在紙上寫下他那歪斜扭曲同時又小又擠的字跡,我們像在進行某種填字遊戲,從幾個比劃較少、結構簡單的字開始辨識,然後集思廣益揣摩著老先生的意思,一個字一個字仔細比對確定字型和字數符合我們猜想的句子之後,再慢而清楚的念出來給老先生聽,老先生會吃力的點點頭或搖搖頭來做出裁判。
踏入病房之前,學長警告過我們,老先生並不是一個配合度很高的病人,但筆談進行了一陣子以後,雙方都漸漸卸下對彼此的戒心和不信任,甚至建立起了某種默契,我們解讀字跡所需的時間越來越短,正確率亦有所提升,老先生也努力集中精神聽我們講話所以理解程度越來越好,我們就這樣一點一點拼湊出他的病史,嘗試去探索老先生老舊殘破卻珍貴的生命輿圖。雖然記憶的輕微錯亂導致有時他的回答反反覆覆不合邏輯,我們還是可以隱約體會感受,那些遷徙顛沛的生命歷程和不斷打擊他的生理病痛,是如何讓一個垂暮之年的老人備受折磨。老先生其實比我們想像的來得健談,但當我們幾經猶豫,仍然決定詢問他的家族病史時,老先生用力咬著微微顫抖的唇,雙眼浸在淚水裡看起來有點失焦,不像在望著我們,而是凝視著很遙遠的時空。
也許只是我的錯覺。老先生的情緒由一開始的害怕、焦躁,到晤談中段時的略顯激動努力噙淚,進行至後半段他終於慢慢放鬆下來,呼吸好像不那麼急促,全身的肌肉也不再那麼僵硬,我們就這樣的以各自的表達方式,平靜的交談著。令我驚訝的是我忽然發現這樣的溝通方式其實並不造成障礙,對我這樣剛剛進入臨床見習的醫學生而言,和病人的接觸常有意想不到的困難,我曾經遇過幾位只講方言或母語的病人,雞同鴨講一陣之後,情況往往變得十分尷尬,這時我通常放棄直接與他們溝通,轉而向陪病的親友詢問細節,抑或請學長、同學來幫忙。但老先生讓我體會懂得,溝通的本質也許不在語言文字,那些固然是工具,但同理心的感受讓我們能對彼此做更深層的認識,那是再長時間的對話、再精采的修辭和說話技巧也不確保能達成的。
「以-前-沒-有-人-這-樣-問-過-我-生-病-的-事-情,謝-謝-你-們」
聽到我們很快地正確解讀出最後這行字,老先生似乎笑了,他臉部的皺紋線條因消瘦而深陷分明,加上光線和陰影將之刻劃的更為立體,所以雖然肌肉只是微微的抽動,看上去卻像是一個深邃的笑容。我們了解對於患有帕金森氏症的老先生來說這是多麼困難且費力,顏面表情肌肉失去彈性的木然「面具臉」症狀,是帕金森氏症最常見的臨床表現之一,卻讓許多人誤以為老先生的個性既古怪又冷淡。
以嚴謹的學術角度來說,因為老先生的意識認知狀態並非理想,我們努力詢問獲得的病例,參考價值其實不高,但他教授給我們的,超越了那些我們早已從課本上讀得非常熟悉的複雜繁瑣的症狀、診斷標準。我第一次真正了解到所謂醫療的基礎,原來並不在於我們平日信仰、奉為權威甚至引以為傲的最新科技和知識,而是從最單純卻必要的理解和支持開始。
離開老先生的病房之後,接下來幾個禮拜我們按照排定的班表,輪流到其他科別的病房見習,日子過得非常忙碌,每天遇見形形色色的病人,難免也有不那麼順利的時候,每次心情沮喪我會拉開病房的窗簾看看陽光,然後想起那天老先生金黃色的笑容,再重新帶著微笑回到病床前。
教學部的助教通知有指名寄給我們的病友來信時我非常驚訝,一度擔心是不是最近做錯了甚麼事情被投訴。
那是個樸實簡單的信封,封口方式和信紙的摺法也不算仔細。
信紙上有幾行很小而且歪歪斜斜的字,老先生大概是怕害羞沒有屬名,但我一眼就認出那是他的筆跡。
可惜他沒有留下地址,我很想回信告訴他:「感謝您教了我那麼多。」
黑雨
「現在還下黑雨嗎?」,我在電話中問阿公。
那是老家特有的景象。
小型的煤雨以滲漏的方式不斷落下,源自輸煤碼頭橫跨頭頂的自動輸煤帶,雖然為了偽裝融入背景而漆成亮藍色,仍然粗魯刺眼地將天空分成了兩截,上層乾淨明澈的晴空、白雲通常與我們無關,漂浮的煤灰遮蔽了天光,漁港就這樣長年被淡淡的陰霾籠罩著,像是一個隔離孤立的灰色空間,和四周的風景都不連續。
有時強勁的季風從海上呼嘯而來,夾帶著大量露天煤場堆置的礦砂,以風暴般鋪天蓋地的氣勢,把整個漁村襲捲進暗黑的漩渦之中,走在路上的人一面咳嗽,一面忍著刺痛和眼淚,勉強比對眼前模糊的景物影像,尋找可辨識的輪廓,然後趕緊躲到屋裡緊閉所有的門窗,習以為常地等待黑雨遠去。
阿公愣了一會兒,只說現在一切都變得很不一樣:「你大概不認得了。」
1.
這是通往紅毛港的唯一道路,柏油路面其實尚算寬廣,只是兩旁工業區高聳矗立著巨大的成排高爐和船塢,被重重包圍的漁鄉顯得更為低矮。進入村落前最顯眼的地標建築是火力發電廠的煙囪群,偌大的廠區占據了半面海岸,同時綿延出一道紅白相間的天際線。發電廠是經濟建設計畫的重要成果,裝置容量甚至比核電廠還要來得大,驅動著城市的日夜運轉以及無止盡的膨脹擴張。發電廠高效率地燃燒煤炭,同時也以極快的速度將港灣的舊日光輝焚掠殆盡,而漫天吐放的塵埃餘燼,沉降在歲月裡逐漸改變了小漁村的顏色。
得先穿過那些灰濛濛的畫面和記憶,然後才可以回家。
我把車子停在新開闢的廣闊停車場,這是龐大填海造陸計畫的第一階段,前身是垃圾場,而工程使用的正是大煉鋼廠的副產品爐石,和火力發電廠的廢棄物飛灰,這些廢土就地傾倒,加上長串的廢輪胎重塑出色彩造型怪異的海岸線,他們填塞了漁村原本賴以為生的海洋,淤積了住民曾經寧靜湛藍的童年回憶和海上夢想,然後為新填的土地取了個閃耀的名字「南星」,從自由貿易區到國際機場等用途眾說紛紜,只是二十年過去,舊的希望被掩埋了,新的希望仍是荒蕪一片。
很久沒有回老家,除了固執的阿公,已經沒有人願意住在破落的老房子老漁村裡,「等到這裡沒有半個人,我就走。」,阿公並不是唯一堅持的人,我們的老鄰居,開柑仔店的豐叔就理直氣壯的在電視螢光幕上宣告:「等到沒人買了,我自然就關店。」。
真的還有人在嗎。雖然中午往往是街道上最安靜的時刻,但我面前整座漁港卻連一點聲音都沒有發出,聲音是生命力的直接表現也最能顯示地域特色,可是現在這裡沒有人聲、沒有拆船廠的噪音,連以往隨處可見的養殖魚塭馬達也不再轟轟作響,沉寂的像是時間被偷偷凝結固定了,所有的動作都暫停下來,不知道甚麼時候才能重新啟動時光流轉的開關。
繞過恢偉的齊天大聖廟,我向印象中迷宮般的小巷弄行進,嚴格的限建政策執行了超過四十年,許多的房子都是以傳統街屋、合院為基礎加蓋的鐵皮屋,易建易拆的「鐵厝」不講求美觀,哪裡有空隙可利用就往哪裡搭起,房屋前後高低參差錯落,構造層次複雜,一眼望去時常看不到那條蜿蜒其間的小路,而對孩子來說,穿堂入院常是最方便的捷徑,循著微弱的入射光線在陌生的黑暗中摸索前進,也是種有趣的探險遊戲。
這麼多年之後我又回到原處,面對著廟埕旁的大榕樹,思索著該選擇哪一條路回家,儘管已經憑著印象演練過許多次,我依然沒有把握。如果走錯路,我是不是應該為了記憶的消逝感到愧疚;如果還認得路,我可不可以仍舊理所當然地直接穿越過別家的後門。
衛星導航在這裡大概沒有用,就算有詳盡確實的地圖,又要怎樣保證在記憶龐雜擁擠的迷路之間我不會走失。
結果我很快找到了阿公的家,意外地容易。整條街上只剩下一棟完整的房子,其餘的都成了斷垣殘壁或者看上去危顫欲墜,真正的困難之處,其實在於我要怎麼安全通過這些遷村工程留下的遍地瓦礫廢墟。
原來時間不只是靜止而已,早已風化崩解而不可逆轉了。
而我得通過它,才能回家。
2.
「你敢是真的欲出國讀冊喔?」
阿公的聲調聽起來並不像真的問句,和方才下午大多數的時間一樣,他好像只是自言自語著,我們兩個看起來聊了很久,其實卻鮮少交集,往往是以沉默回答了彼此的問題,然後再重新由無關緊要的小事說起。
這次不等我回答,說完這句話阿公就起身去拿擱在進屋處角落的釣竿和冰箱然後急忙地出門了,甚至連門扉也沒有闔上。或許阿公真的是怕耽擱錯過魚群活躍的時刻,又或者他不希望我看見他那時的表情,事實上,記憶裡在這座低矮陰濕的老合院內,我從來看不清楚誰的表情,不論是阿公的,父親的,或叔伯鄰人的,每個人的眉眼鼻口,都像是被強勁鹹澀的海風吹皺成了一團,糾結複雜難以理解是哭或是笑。
從小阿公總是栩栩如生地描繪,每值出海季節的盛況,淺淺而清澈的瀉湖內萬魚竄動翻騰,數百艘漁船從早到晚來回穿梭,雖然已經是數十年前的記憶了,但阿公仍堅持,這兩天適逢作大潮,加上季風正盛魚群入港避風浪,指給我看連那整排老木麻黃都給吹的搖搖晃晃,正是再好不過的釣魚時機。
由黃轉紅的夕陽持續變大,向海面迫近,陣陣晚風吹送火燒雲鑲金邊的烈焰向陸地襲來,阿公沿海岸線走去,黝黑乾瘦的身影越拉越長,海邊鹽分地帶土壤貧瘠且風勢凌厲,樹形不高但大多堅毅挺拔,生於斯長於斯的阿公,自然也有類似的特質。
猜想此時阿公已經熟練地越過防風林和堤防,隱身在消波塊的空隙間垂釣他的美好回憶。我坐在屋裡,看著老舊的門櫺框出一幅畫面,我記得那同樣也是一個悶熱的黃昏,在搬家前最後一次我坐在這裡像這樣看著,看父親忙著將大箱小箱打包好的東西運上發財小貨車,母親像是迫不及待的早早坐上了右前方的座位,我沒有哭鬧只是靜靜坐著不肯離開,父親強行把我拉上車之後總算是帶齊了行李,長鏡頭裡我們在一小段的顛簸晃動之後,很快駛離了那個畫面。
那時阿公也是什麼話都沒說,只是安靜地拿起他的釣具反方向往海港口慢慢走去。
十年逝去,門框外的風景推移的很慢,港口對岸高樓鱗次櫛比的建起,這方的海岸線卻仍然蕭索,畫面裡流動的幾乎總是離開的背影,而那些生了根的只好在原地老去。
這裡是台灣南方最大城市的西南隅,向海峽長長伸出的孤立半島,有一個富於歷史和地域的想像空間的名字,但很少人聽過或想起過它的名字。
甚至原屬於它的人也忙著拋棄這個名字。
像是我們。
3.
在上小學以前,據說我只會講專屬這座漁村的、在句尾帶有獨特口音的閩南話,而父親堅持,要把我的戶口寄在遠房親戚家,讓我可以搭每小時一班的渡輪跨區到「真正」的都會學校念書,雖然我們和他們的戶籍確確實實坐落在同一座城市裡,但大家都相信:留在這裡,不會有出路。直到升上國中搬家以前,我以寄居的名義度過了六年嘗試融入、偽裝為都市人的日子,渡輪接送我在兩岸的港口,日夜擺盪在五顏六色的高樓霓虹和低矮散落的漁家燈火之間。
現在渡輪停駛了,我也成為真正的都市人、外來者。也許基於某種防禦心理,對於大部分的小學同學我都沒有留下什麼印象了,看畢業紀念冊的團體合照上,我置身於一群擁擠的陌生人中,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小縫隙,對鏡頭擠出一絲僵硬的微笑。
除了紅毛以外。她是柑仔店豐叔的姪女,和我一齊每天從渡船頭搭船通勤上學,很自然地變成我孤獨的小學生涯中最要好的同學,因為天生髮色和膚色較淡,加上家住紅毛港,所以得到了這個她一直不喜歡的外號。紅毛同樣國小畢業後就舉家搬遷了,我們也幾乎沒有再聯絡過,只是聽說幾年以前她的雙親因意外亡故,所以紅毛又回到漁港來和豐叔同住。沒有想到後來紅毛這個外號變成我的記憶裡和這座漁村最強的連結,當我聽到有人提起紅毛港,就反射似的馬上想起她。
天已經黑得和海面再也分不清邊界,阿公還沒有回來,無事可做的我決定碰碰運氣,去柑仔店看看紅毛在不在。小店面內沒有人看顧生意,而其實也沒有必要,我向裡頭喊了一聲豐叔,回應我的是一個似乎熟悉又陌生的女聲,我知道那是紅毛。
原來豐叔也釣魚去了,紅毛邀請我到雜貨店深處昏暗窄小的客廳坐下,一陣不知道該講什麼才合宜的尷尬沉默之後,我決定請她帶我去海邊新鋪設的觀光腳踏車道和景觀咖啡店走走。
我們坐在仿歐式的露天咖啡座,看著岬角尾端四十年來從未真正啟用作導引信號塔的高字塔,在暗夜中孤獨地向四面的海發出淡藍色的光,據說它將是拆遷工程完成後,半島上唯一被保存的地標建築。
光線的顏色和角度都被設計的非常完美,創造出一種孤島上的人從未見過的,幸福和希望的氛圍。
有雨開始落下來。
起先我注意到的是那一滴一滴懸掛在紅毛髮稍、睫毛上的水珠,點點折射出咖啡座燈光的浪漫淡黃色調;然後雨勢慢慢轉強,高字塔燈火通明的窗戶把夜空中的細細雨絲照成一座自塔頂垂落的藍色瀑布。
我和紅毛隨意聊著,其他童年玩伴們是怎樣陸陸續續離開這座小漁村,而留下來的人又過得如何,真的如同媒體的報導,為了表示抗議,懷抱著炸船封港的決心嗎?
她問我回來之後有沒有到處看看。在地藝術家在舊碼頭倉庫以破碎的磁磚鑲嵌創作,企圖拼貼紅毛港充滿裂痕的圖像;居民們搬遷前留下的老照片,還滿貼在那些殘立的房屋牆面上看守家園;以及廢棄的渡輪站,不知道哪時被用鮮豔的油漆噴了一個大大的、充滿憤怒的英文單字。
時光在我們面前如此大規模且急遽的衰頹敗壞,我們能夠或者應該嘗試保存、追憶還是生氣?「至少比甚麼都不做來得好吧。」紅毛說。
雨點拍打在身上,好像被種種複雜的感覺和什麼沉重的東西給紛紛擊中,令人難以承受。
這場雨並沒有要停歇的樣子,我們終於決定離開海邊。壓低身體飛快地踩著腳踏車,正沿海岸線奔馳逃離時,忽然隱約聽見細微的「啪」一聲,像是某條細線斷裂的聲音,回頭我看見岬角盡頭的那座光亮方塔正逐層暗去,防風林旁兩列蒼白的路燈也由遠而近一一斷電,倏忽之間似乎又回到印象中總是黯淡的紅毛港夜晚。
雨仍然下著,且變得越來越大。
在完全漆黑的雨中,一路上我們穿過許多記憶,去尋找遠方想像中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