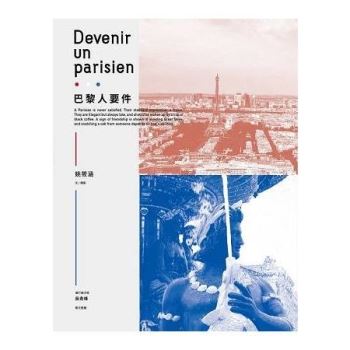阿薩斯街的日子(Les journées au rue d’Assas)
初抵巴黎的時候,我住在盧森堡公園附近阿薩斯街(Rue d’Assas)的一間小閣樓。這是一棟十九世紀建築而成的典型奧斯曼公寓,有著兩公尺高的大門,氣派的挑高大廳通往鋪有紅地毯的大理石階梯,以及一座古典黑鐵雕花電梯,然而那是給主棟的住戶使用,閣樓出入口是在大廳後方的破舊小門裡,踩著呀呀作響的木樓梯,費盡渾身力氣爬到六樓。
這種樓頂閣樓在從前作為貴族家裡傭人居住使用,沿著小樓梯能通往樓下主人的房間,結束一天於華麗宅邸打掃與保姆的工作後,再爬樓梯回到窄小冰冷的閣樓休息。如此想像似乎有些悲慘,但年輕的海明威在巴黎時何嘗不是住過這種冬冷夏熱的小閣樓,而離盧森堡公園三分鐘的步行距離,更是多少巴黎人夢寐以求的住宿地點。若決定在巴黎生活,就必須學會不去在意許多日常細節,聳聳肩說:「就是這樣!」,否則只會讓自己陷入困境。小閣樓有扇天窗,除了一根煙囪以外什麼也看不見,下雨天時若忘記關窗,雨水便會潑灑進來。我把遠離家鄉的一只行李箱在這不到六坪米的房間攤開來,將生活物品依序填入空格之中,就這樣開始在巴黎生活的第一天。
選擇何時作為巴黎的第一天是很重要的。巴黎在各個時節的面貌,將嚴重影響人們對她的印象。八月到巴黎的人,會誤以為這是座不算擁擠的城市,路人友好並能以英文溝通,然而那只是由於法國人都出城渡假,城裡只剩招攬觀光客的商人以及外國遊客所致。我抵達巴黎時,是一月底的冬季,溫度與亞熱帶家鄉相去甚遠,冷風彷彿無時無刻都能鑽進骨頭裡,暖氣永遠不夠,只能躲到商店內把身體充暖後,再進行步行。巴黎的冬天天黑得特別早,到銀行處理事情、在超市採購生活所需之後,一天好像很快就用完了。但或許那時我們都還年輕,不懂得倉促的意義,只單純的想在這座城市渡過一段時間,緩慢而奢侈的囤積一份只屬於自己的巴黎日曆。每個早晨,從阿薩斯街這一頭,穿過盧森堡公園到另一頭的索邦大學修習法文。這一個幾乎每位留學生都經歷過的語言學校時期,純粹裡帶有迷惘,卻永遠新鮮,回想起來是最珍貴的。法文課分為文法課以及聽力課,經過分級考試後,我被分配到中級班,一個班級裡大概有三十幾位學生,大多來自美國、澳洲或是歐洲其他國家,相較於他們的勇於發言,沉默內向的亞洲人只有不到五位左右。課堂上多半研讀一些艱澀的古典文學或時事文章,有時會無聊的讓人睡著,偶爾也因為作業忘了寫而擔心被老師點到焦慮著,望著窗外突然下起的大雨,才想起閣樓裡的天窗忘了關上。
每兩週一次的聽力課目的在訓練聽力與口語,戴上耳機,老師會一對一的糾正每個人特定字母的發音。日本同學向來對V和B,以及R和L的發音感到相當苦惱,我則對於法文有點曖昧的B和P以及D和T發音無法好好分辨,尤其在電話裡要記下對方郵件地址時,總是寫錯。
從阿薩斯街沿著女士街(Rue Madame)直走,到老鴿舍街(Rue du Vieux-Colombier)右轉便能走到聖許畢斯教堂(Église Saint-Sulpice),當時它仍在整修,半邊的鐘樓被施工的鷹架遮蓋住,看到全貌的那一天好像永遠等不到。教堂前有一處噴泉,偶有市集舉行,廣場上的市府咖啡館總是人聲鼎沸,即使是冬夜裡也從不顯得蕭條。為了考取設計學院,我在教堂附近的畫室修習晚間的裸女素描課程。課堂上大概只有五、六個學生,多半是附近的居民,豎起畫架、夾好半開的素描紙,拿出炭筆與軟橡皮,待模特兒擺好姿勢,便開始素描。十五分鐘三張速寫、五分鐘三張速寫,仔細觀察皮膚與肌肉的線條,如此重複的畫個幾圈,便能使人疲憊不堪。
提起多出幾分重量的背袋,從女士街往阿薩斯街的方向走回家。這條街上總是相當安靜,只有我一個人行走著,幾乎全是奧斯曼式公寓住宅群,住過一些名畫家,有幾間舊書店、鐘錶店,當然早已打烊。夜深得特別快,溫度下降之後非常寒冷,昏黃的路燈光下開始飄起了雪,湧起了適才被專注作畫忘卻的飢餓感,口袋裡給完模特兒小費後沒有多餘的硬幣,決定回家煮一盤卡波那拉麵。緩緩的走上階梯,木質地板上有些踩過雪地後濕漉漉的腳印。一個人在遠方,漂泊不定、茫然而迷惘,像在沒有路燈的黑夜裡,只能小心翼翼地往前面邁進。然而晨曦總會迎來的,多年後的早晨,當巴黎的日常變得如此熟稔,回想起阿薩斯街的日子,仍像一個原點,只要回到這條街,就彷彿能找回初抵巴黎的青春歲月,儘管大部分已經不著痕跡的遺失了。
時光廊巷(Passage du temps)
巴黎的陽光是有額度的。某個早晨醒來,發現窗外天色呈現一片灰濛,厚重的雲層似乎再也不允許一絲光線穿透,就曉得今年的陽光額度已然用盡,剩餘的將是永無止盡的冬日。
那樣的日子約莫發生在夏末秋初,一切周而復始的時刻。人們告別假期,回到這座城市裡各自的崗位上,大道兩側的梧桐樹開始落葉,小巷逐漸恢復過往的密度。然而這一切卻總像帶著幾許歎息:短暫的夏季宣告結束,漫長的寒冬即將來臨。
不如說這座城市永遠充滿著歎息的,處處瀰漫著懷舊的氣氛。十九世紀塞納省長奧斯曼男爵大改造下,開創了林蔭大道、下水道以及公園,並規定了建築物的密度與高度:四十五度斜角的灰藍色屋頂、米白牆面,二三樓有著鑄鐵雕花陽台的「奧斯曼式建築」,構成了巴黎市中心主要風景,這些法定不能輕易改造的房屋,讓人能輕而易舉想像上個世紀的風情。而為了連接羅浮宮至巴黎歌劇院一帶,從十八世紀末起建有許多以鐵鑄玻璃天棚覆蓋的「廊巷」,既是走廊也是巷道,眾多商店在其中開設,在尚未有水泥馬路的時代,穿著蓬蓬裙的貴婦們,雨天時便能無憂無慮的在裡面逛街,是現代百貨公司的前身。
巴黎的第一盞瓦斯燈便是在此點亮,輝煌時期曾多達數百條,至今僅存二十幾條的廊巷,是喚醒這座城市古老記憶的鑰匙,銜接在兩條大道之間,像是鮮為人知的祕密捷徑。對懷舊主義的人來說,它是通往上個世紀的時光機,在廊巷裡的老舊店鋪中找一本頁首有著手寫字跡的舊書、一張印有舊時艾菲爾鐵塔的明信片,一些不再使用的硬幣與泛黃的郵票,就等於找回一種過去。懷舊靈魂在巴黎就像回到原生地,無處不感到快活。我向來喜歡在這座城市裡,尋找飄渺的歷史痕跡,蕭邦居住過的公寓、巴爾札克喜愛造訪的餐廳,與書本中的文人無形之間交錯,總讓人觸電般的著迷。走入一間座椅稀少,有著木頭吧台的咖啡館,牆壁泛黃而斑駁,幾排金屬杆上掛著皮夾克與長版大衣,鄰座翻閱巴黎人日報(Parisien)空氣飄散而來的油墨味,與隔桌刀叉底下醃漬鯡魚之間的存在感,是我解讀為巴黎人懷舊的一種形貌,懷念並固執著數十年來的一些小習慣,樂此不疲。從每個區域街坊每月不定期舉行的古物拍賣,到每週末熱鬧的凡夫跳蚤市場(Marché des puces Vanves),可見到巴黎人對舊物的熱愛,幾個手繪的碗盤、六〇年代明星照片、一只洋娃娃,一臺仍可以用的老式相機,如果有點時間,老闆都很樂意訴說每件物品背後的長串來歷。
廊巷是我的獨家小徑,即使只作為一個下班回家的短暫過道,五分鐘的時間,都能讓我有搭乘時光機的美麗錯覺,走在馬賽克瓷磚走道上,真實感受巴黎的歷史就在腳下。廊巷也是一個城市裡祕密的集寶遊戲,每造訪一條廊巷就有不同的驚喜。
錨廊巷(Passage de l’Ancre),是這個陽光用完的秋天裡最後一抹繽紛。
不如薇薇安廊巷(Galerie Vivienne)或全景巷(Passage Panorama)至今依舊生氣蓬勃,也不像布拉迪廊巷(Passage Brady)被印度餐廳所佔據,完全變了樣,錨廊巷只是靜悄悄地存在了兩百多年,有如五線譜上一個拉長的休止符,提供繁忙的巴黎人一個稍事歇息的空間。
作為煤炭街(Rue Charbon)的延伸,錨廊巷連結了聖馬當街(Rue Saint-Martin)與托爾比勾街(Rue Turbigo)。這條小巷僅長不到兩百公尺,兩側亦十分狹隘,鮮少有路人經過,形成了它獨有的疏離氣氛,在聖馬當街的入口甚至是一道普通公寓的大門,不仔細注意便會錯過。未有玻璃天棚遮掩,少了一分廊巷的覆蓋感,取而代之的是直接落下的自然光線。一進到巷裡,就會瞭解它的魅力:有著綠色、紅色、黃色、橘色外牆,互相緊挨著的小公寓們,門口充滿綠意的植物、花朵茂盛的盆栽,散發著森林般的清香,並停靠著一輛顏色同樣鮮艷的單車。在巴黎統一的奧斯曼建築群中,它顯得格外獨特迷人。叫不出名字的藤蔓似乎已經攀爬了一段時間,看得出有人細心修剪過。巷中一間有著舊式招牌的雨傘店,還提供少見的傘類維修服務。轉身離開錨廊巷,巴黎的天色依舊灰白,而翻湧上來的現實也依舊沈重,這一段五分鐘的空白,就是都市裡最後的喘息。我們所在巴黎已不如海明威所在的巴黎,生活不再單純,卻也從未簡單過。但或許我們仍能找到一份值得密藏的小幸福,在某條巷弄。
初抵巴黎的時候,我住在盧森堡公園附近阿薩斯街(Rue d’Assas)的一間小閣樓。這是一棟十九世紀建築而成的典型奧斯曼公寓,有著兩公尺高的大門,氣派的挑高大廳通往鋪有紅地毯的大理石階梯,以及一座古典黑鐵雕花電梯,然而那是給主棟的住戶使用,閣樓出入口是在大廳後方的破舊小門裡,踩著呀呀作響的木樓梯,費盡渾身力氣爬到六樓。
這種樓頂閣樓在從前作為貴族家裡傭人居住使用,沿著小樓梯能通往樓下主人的房間,結束一天於華麗宅邸打掃與保姆的工作後,再爬樓梯回到窄小冰冷的閣樓休息。如此想像似乎有些悲慘,但年輕的海明威在巴黎時何嘗不是住過這種冬冷夏熱的小閣樓,而離盧森堡公園三分鐘的步行距離,更是多少巴黎人夢寐以求的住宿地點。若決定在巴黎生活,就必須學會不去在意許多日常細節,聳聳肩說:「就是這樣!」,否則只會讓自己陷入困境。小閣樓有扇天窗,除了一根煙囪以外什麼也看不見,下雨天時若忘記關窗,雨水便會潑灑進來。我把遠離家鄉的一只行李箱在這不到六坪米的房間攤開來,將生活物品依序填入空格之中,就這樣開始在巴黎生活的第一天。
選擇何時作為巴黎的第一天是很重要的。巴黎在各個時節的面貌,將嚴重影響人們對她的印象。八月到巴黎的人,會誤以為這是座不算擁擠的城市,路人友好並能以英文溝通,然而那只是由於法國人都出城渡假,城裡只剩招攬觀光客的商人以及外國遊客所致。我抵達巴黎時,是一月底的冬季,溫度與亞熱帶家鄉相去甚遠,冷風彷彿無時無刻都能鑽進骨頭裡,暖氣永遠不夠,只能躲到商店內把身體充暖後,再進行步行。巴黎的冬天天黑得特別早,到銀行處理事情、在超市採購生活所需之後,一天好像很快就用完了。但或許那時我們都還年輕,不懂得倉促的意義,只單純的想在這座城市渡過一段時間,緩慢而奢侈的囤積一份只屬於自己的巴黎日曆。每個早晨,從阿薩斯街這一頭,穿過盧森堡公園到另一頭的索邦大學修習法文。這一個幾乎每位留學生都經歷過的語言學校時期,純粹裡帶有迷惘,卻永遠新鮮,回想起來是最珍貴的。法文課分為文法課以及聽力課,經過分級考試後,我被分配到中級班,一個班級裡大概有三十幾位學生,大多來自美國、澳洲或是歐洲其他國家,相較於他們的勇於發言,沉默內向的亞洲人只有不到五位左右。課堂上多半研讀一些艱澀的古典文學或時事文章,有時會無聊的讓人睡著,偶爾也因為作業忘了寫而擔心被老師點到焦慮著,望著窗外突然下起的大雨,才想起閣樓裡的天窗忘了關上。
每兩週一次的聽力課目的在訓練聽力與口語,戴上耳機,老師會一對一的糾正每個人特定字母的發音。日本同學向來對V和B,以及R和L的發音感到相當苦惱,我則對於法文有點曖昧的B和P以及D和T發音無法好好分辨,尤其在電話裡要記下對方郵件地址時,總是寫錯。
從阿薩斯街沿著女士街(Rue Madame)直走,到老鴿舍街(Rue du Vieux-Colombier)右轉便能走到聖許畢斯教堂(Église Saint-Sulpice),當時它仍在整修,半邊的鐘樓被施工的鷹架遮蓋住,看到全貌的那一天好像永遠等不到。教堂前有一處噴泉,偶有市集舉行,廣場上的市府咖啡館總是人聲鼎沸,即使是冬夜裡也從不顯得蕭條。為了考取設計學院,我在教堂附近的畫室修習晚間的裸女素描課程。課堂上大概只有五、六個學生,多半是附近的居民,豎起畫架、夾好半開的素描紙,拿出炭筆與軟橡皮,待模特兒擺好姿勢,便開始素描。十五分鐘三張速寫、五分鐘三張速寫,仔細觀察皮膚與肌肉的線條,如此重複的畫個幾圈,便能使人疲憊不堪。
提起多出幾分重量的背袋,從女士街往阿薩斯街的方向走回家。這條街上總是相當安靜,只有我一個人行走著,幾乎全是奧斯曼式公寓住宅群,住過一些名畫家,有幾間舊書店、鐘錶店,當然早已打烊。夜深得特別快,溫度下降之後非常寒冷,昏黃的路燈光下開始飄起了雪,湧起了適才被專注作畫忘卻的飢餓感,口袋裡給完模特兒小費後沒有多餘的硬幣,決定回家煮一盤卡波那拉麵。緩緩的走上階梯,木質地板上有些踩過雪地後濕漉漉的腳印。一個人在遠方,漂泊不定、茫然而迷惘,像在沒有路燈的黑夜裡,只能小心翼翼地往前面邁進。然而晨曦總會迎來的,多年後的早晨,當巴黎的日常變得如此熟稔,回想起阿薩斯街的日子,仍像一個原點,只要回到這條街,就彷彿能找回初抵巴黎的青春歲月,儘管大部分已經不著痕跡的遺失了。
時光廊巷(Passage du temps)
巴黎的陽光是有額度的。某個早晨醒來,發現窗外天色呈現一片灰濛,厚重的雲層似乎再也不允許一絲光線穿透,就曉得今年的陽光額度已然用盡,剩餘的將是永無止盡的冬日。
那樣的日子約莫發生在夏末秋初,一切周而復始的時刻。人們告別假期,回到這座城市裡各自的崗位上,大道兩側的梧桐樹開始落葉,小巷逐漸恢復過往的密度。然而這一切卻總像帶著幾許歎息:短暫的夏季宣告結束,漫長的寒冬即將來臨。
不如說這座城市永遠充滿著歎息的,處處瀰漫著懷舊的氣氛。十九世紀塞納省長奧斯曼男爵大改造下,開創了林蔭大道、下水道以及公園,並規定了建築物的密度與高度:四十五度斜角的灰藍色屋頂、米白牆面,二三樓有著鑄鐵雕花陽台的「奧斯曼式建築」,構成了巴黎市中心主要風景,這些法定不能輕易改造的房屋,讓人能輕而易舉想像上個世紀的風情。而為了連接羅浮宮至巴黎歌劇院一帶,從十八世紀末起建有許多以鐵鑄玻璃天棚覆蓋的「廊巷」,既是走廊也是巷道,眾多商店在其中開設,在尚未有水泥馬路的時代,穿著蓬蓬裙的貴婦們,雨天時便能無憂無慮的在裡面逛街,是現代百貨公司的前身。
巴黎的第一盞瓦斯燈便是在此點亮,輝煌時期曾多達數百條,至今僅存二十幾條的廊巷,是喚醒這座城市古老記憶的鑰匙,銜接在兩條大道之間,像是鮮為人知的祕密捷徑。對懷舊主義的人來說,它是通往上個世紀的時光機,在廊巷裡的老舊店鋪中找一本頁首有著手寫字跡的舊書、一張印有舊時艾菲爾鐵塔的明信片,一些不再使用的硬幣與泛黃的郵票,就等於找回一種過去。懷舊靈魂在巴黎就像回到原生地,無處不感到快活。我向來喜歡在這座城市裡,尋找飄渺的歷史痕跡,蕭邦居住過的公寓、巴爾札克喜愛造訪的餐廳,與書本中的文人無形之間交錯,總讓人觸電般的著迷。走入一間座椅稀少,有著木頭吧台的咖啡館,牆壁泛黃而斑駁,幾排金屬杆上掛著皮夾克與長版大衣,鄰座翻閱巴黎人日報(Parisien)空氣飄散而來的油墨味,與隔桌刀叉底下醃漬鯡魚之間的存在感,是我解讀為巴黎人懷舊的一種形貌,懷念並固執著數十年來的一些小習慣,樂此不疲。從每個區域街坊每月不定期舉行的古物拍賣,到每週末熱鬧的凡夫跳蚤市場(Marché des puces Vanves),可見到巴黎人對舊物的熱愛,幾個手繪的碗盤、六〇年代明星照片、一只洋娃娃,一臺仍可以用的老式相機,如果有點時間,老闆都很樂意訴說每件物品背後的長串來歷。
廊巷是我的獨家小徑,即使只作為一個下班回家的短暫過道,五分鐘的時間,都能讓我有搭乘時光機的美麗錯覺,走在馬賽克瓷磚走道上,真實感受巴黎的歷史就在腳下。廊巷也是一個城市裡祕密的集寶遊戲,每造訪一條廊巷就有不同的驚喜。
錨廊巷(Passage de l’Ancre),是這個陽光用完的秋天裡最後一抹繽紛。
不如薇薇安廊巷(Galerie Vivienne)或全景巷(Passage Panorama)至今依舊生氣蓬勃,也不像布拉迪廊巷(Passage Brady)被印度餐廳所佔據,完全變了樣,錨廊巷只是靜悄悄地存在了兩百多年,有如五線譜上一個拉長的休止符,提供繁忙的巴黎人一個稍事歇息的空間。
作為煤炭街(Rue Charbon)的延伸,錨廊巷連結了聖馬當街(Rue Saint-Martin)與托爾比勾街(Rue Turbigo)。這條小巷僅長不到兩百公尺,兩側亦十分狹隘,鮮少有路人經過,形成了它獨有的疏離氣氛,在聖馬當街的入口甚至是一道普通公寓的大門,不仔細注意便會錯過。未有玻璃天棚遮掩,少了一分廊巷的覆蓋感,取而代之的是直接落下的自然光線。一進到巷裡,就會瞭解它的魅力:有著綠色、紅色、黃色、橘色外牆,互相緊挨著的小公寓們,門口充滿綠意的植物、花朵茂盛的盆栽,散發著森林般的清香,並停靠著一輛顏色同樣鮮艷的單車。在巴黎統一的奧斯曼建築群中,它顯得格外獨特迷人。叫不出名字的藤蔓似乎已經攀爬了一段時間,看得出有人細心修剪過。巷中一間有著舊式招牌的雨傘店,還提供少見的傘類維修服務。轉身離開錨廊巷,巴黎的天色依舊灰白,而翻湧上來的現實也依舊沈重,這一段五分鐘的空白,就是都市裡最後的喘息。我們所在巴黎已不如海明威所在的巴黎,生活不再單純,卻也從未簡單過。但或許我們仍能找到一份值得密藏的小幸福,在某條巷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