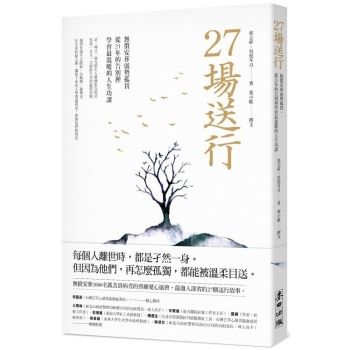第1場送行
二十年的漫長回家路
時間:1999 年
貝蒂在遇見我們之前,已經在醫院太平間的冷藏室裡「住」了超過一年的時間了。
不,或者更正確地說,其實是我們遇見了她。我一直認為,貝蒂是我的貴人,若不是因為她,我就不會成立協會,如今我們就無法幫助到這麼多家庭或迷失的旅人,送他們好好地、舒適地走上最後一程;如果不是她,接下來的這些故事,都不會開始了。
這位有著美國身軀、華人靈魂,始終渴望尋根返鄉的女子,看似藉由我們的幫助讓客死異鄉的她走上返鄉之路,但也是她,幫助我們開啟了之後這一趟趟,雖然漫長卻充滿溫暖的「最後一程」。
華人深信「死者為大」,一場普通的喪事,辦完往往十幾二十萬跑不掉,而且就習俗來說,好好送走至親最後一程,更是身為子女父母應盡的責任與義務。因此許多人就因為這最後的一程,成了被留下的親人最沉重的負擔,尤其假若家人原先就過著拮据的生活,又憑空多了數十萬的債務,在悲痛親人離世之際,更是一重大打擊。就因為如此,讓我在協助弱勢家庭多年後,也興起了免費協助辦理殮葬的念頭。
只可惜我這樁美意,頭半年,並不如我想像得順遂。主要是因為,在華人在保守的觀念中,要仰賴別人幫助完成喪事是不孝的、抬不起頭的。因此多數弱勢家庭寧可跟週遭親友或錢莊借錢,平添自己更多的負擔,也拉不下臉來接受我們的援手,多數人多是婉拒。
約過了半年的時間,或許上蒼有感受到我們的誠意跟決心,某天下午醫院的社工突然來電告訴我貝蒂的故事。我從來也都沒有想過,這件事的起點竟會是從一個外國人開始。
在我們接受這案件之前,貝蒂已經在醫院太平間的冷藏室住了超過一年。住在美國紐奧爾良、高齡七十九歲的貝蒂,她一直堅信自己的前世是中國人,也因如此,當她得知自己罹患乳癌並已多處轉移後,決心來亞洲開啟她的尋根之旅。可惜的是,才與旅伴雷諾從曼谷來到台灣的第三天,貝蒂就在中正紀念堂因氣喘發作昏迷而失去意識,被送去了醫院急救。
氣切搶救成功的她,恢復意識後,顫抖地寫下了她最後的願望「Go Home」,沒多久,便又再度失去意識。而她的旅伴雷諾,卻因為身上的盤纏已經花光,不得已只好返回美國,甚至連貝蒂在美國的家人,也未曾跟醫院聯繫過,在這段期間只有她一位住在菲律賓的義女,託人寄了個天使雕像過來而已。對於貝蒂,我們所知道的,最多就僅僅只有這樣了。
在貝蒂生病的期間,醫院和社工人員也想過要讓貝蒂搭飛機回美國,不過一來航空公司深怕在漫長的旅途中發生意外,二來醫療專機也所費不貲,只好作罷。無依無靠、因缺氧陷入昏迷的貝蒂,就這樣孤寂地在醫院昏迷了一年多,最後積欠了兩百五十多萬的醫藥費辭世。聯繫了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現「美國在台協會」︶,他們也僅表示:「我們無權處理在海外死亡之美國人民遺體,且無法洽商他人願意支付其喪葬費用,但會再努力尋找家屬。」在過世後,醫院保留了她的遺體一年多,希望有人來認領,不過,卻始終沒有任何一點消息。為了這件事,我們也得到了善心人的幫助,在美國登報三個月,並在登報啟事上承諾貝蒂的家人我們願意支付來回機票,希望他們不要感到有負擔,能夠主動來連繫我們。
大體留在醫院是小事,但貝蒂「Go Home」的心願無法了卻,才是我們心中最最不忍的。
基於同理,我們當然日夜期盼著她的家人能來接她回家,但就連她的旅伴雷諾也不再捎來任何消息。這幾年背包客盛行,許多年輕人常在網路上或同好圈中結伴出遊,也許貝蒂跟雷諾其實就只是兩個結伴出遊的銀髮背包客,彼此並無深交;也或者有可能是因信仰禮俗的不同,對多數不相信輪迴轉世的美國人而言,離世就代表了告別,不像我們華人對於最後一程如此看重。
始終想幫人走完最後一程卻無法達成的我們,以及想要回家卻始終回不了家的貝蒂,就在這機緣巧合下相遇了。
因此,當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發函告知希望能讓貝蒂以台灣居民身分辦理後事時,社工跟醫院也清楚,這樁憾事,確實該告一段落。因此,當社工致電給我時,即使根本就不熟悉殮葬事務,但我心裡頭「即使邊做邊學也一定要把這件事做完」的意念,卻很堅定。我們要讓相信輪迴轉世的貝蒂老太太,靈魂可以找到回家的路去轉世投胎。
不過答應要協助辦喪禮後,緊接著,難題就來了。貝蒂老太太是位基督徒,但又相信自己前世是中國人,既然信基督卻又相信輪迴轉世,該辦怎樣的葬禮,這可真是難倒我了。左思右想後,協會決定不如就幫她辦一場中西合併的喪禮。於是我們請來了有治喪經驗的朋友,號召各處的志工,大家開始有錢出錢、有力出力,設了靈堂、折了紙蓮花,最後在大體上多覆蓋了一件基督教特有的袍子。只要有誠心都是好的,無須拘泥於繁文縟節的規矩,爾後這也成了我們治喪的原則。
當然其中也有一些志工不能理解,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辦喪事這麼觸霉頭不吉利的事情,到底為什麼非做不可呢? 可對我而言,善心其實是沒有差別的,這不單單只是幫助貝蒂找到回家的路,更是讓許多弱勢家庭不要因為孝心而造成自身更大的負擔。
「看見大體怕不怕?」事後曾有人這樣問我。當時才三十九歲的我,幾乎沒有見過什麼屍體。說實話,並不是我膽子特別大,當天只是因為緊張到忘記害怕而已。我緊張到當醫護人員從冷藏櫃裡拉出貝蒂、屍袋的拉鍊「刷」地打開,看著她那灰色、鬆軟,幾乎無肌肉結締組織,就如同電影中常見到的屍體時,我完全無法產生任何不舒服或者奇異的感覺。
我手執銅板筊杯念念有詞,呼喊貝蒂回家。
擲出第一個允杯,然後接著兩個、三個,過程非常順利,我知道,貝蒂同意我們帶她走了。為了不讓她孤單,我還特地找來二十幾個親朋好友參加喪禮,只希望她這趟漫長的回家路能走得熱熱鬧鬧,一點也不孤單。
辦喪禮,一切儀式都以尊重死者為優先。無論他們的信仰是什麼,最重要的,都是讓他們安心好走。前後大概十天的時間,做完了頭、尾七,舉行完這場中西合併的喪禮後,我們的第一個案件完成了。
不過這個案件,即使到今日,在我心中都還感到尚未完結。葬禮結束後,我們將貝蒂火化,然後安奉在台北富德公墓的靈骨塔。至今我都仍然希望她能真正回到美國的家,可二十年過去了,始終沒有任何消息。
最後,我只能換個方向想,告訴自己,若不侷限於我們華人的傳統家庭觀念,那麼,堅信自己前世是中國人的貝蒂,某個程度上,也已經回家了。
一場送行的體悟:許多人忌諱喪禮、害怕死亡,但其實它不過只是人生裡頭,必經的一段過程而已。佛家說:「日日是好日,時時是好時。」也正是說明了心境的重要,他鄉也可轉換成故鄉。死者為大,只要懷抱著敬意與誠心,便無所懼。
第8場送行
徐上兵半世紀的歸路
時間:2017 年
──一九六八年,上兵徐坤湖死於馬祖,葬於北竿,軍方以自殺結案,再無下文。家屬接獲通報雖不信,亦無能翻案。
──二○一六年底,相隔近五十年後,退伍軍人吳香官在北竿的中興公園發現軍人公墓,以及其中的徐坤湖墓碑。
──二○一六年底,臉書社團「馬祖捍衛戰士」由在馬祖北竿服役退伍的吳政武貼出徐坤湖墓碑照,社團社員范植源向基隆市長請求協助。
──二○一七年,……經過五十年的寂靜等待、五十年的兩岸眺望,一縷忠魂曾執干戈以衛社稷卻有家歸不得的徐坤湖,終於踏上了返鄉路。
我是個很善於等待的人,有時那耐性都讓人感到不可思議。每次有媒體朋友來採訪,我告訴他們,我還在等待已經在靈骨塔安奉了近二十年的貝蒂家人來認領她的骨灰,別人都笑我異想天開。
但真的異想天開嗎? 若聽了徐上兵的故事,也許就不會覺得這件事不可能了。
徐上兵等了整整五十年,才終於回到家。
這五十年來,他的家人始終無法放下,只是找不到救濟管道。任誰也沒想過,會是用這樣的方式,讓他找到回家之路。
事情是從臉書「馬祖捍衛戰士」這個社群粉絲頁所開始的。
社群網路的興起,不僅僅只是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也徹底顛覆了人跟人的距離。社團的社員范植源,是一位曾在馬祖當過砲兵的復健師,他憑著對馬祖的熱情跟傻勁,一直對袍澤盡心盡力,讓一些退伍的同袍可以在此交流。某天,突然有人在社團轉貼了一張孤墳的照片,問了一句:「我們有可能幫他找到回家的路嗎?」
在海島當兵的孤寂,沒嘗過的人不會懂。想到自己那兩年天天思鄉的心情,再想想這些永遠都無法回家的孤墳,范植源、吳政武及吳香官對這件事上了心。或許就是因為這樣的感同身受,只要有機會能盡點棉薄之力,都是樂意。
而想家的煎熬,發現並拍照的空軍退役軍官吳香官更懂。於二○一六年底返鄉掃墓的他,在馬祖北竿中興公園無意中發現了孤零零的墓碑,荒煙蔓草,彷彿從來沒人探訪過,上面寫著「徐坤湖」三個字。想起了報效國家時對家人的思念,吳香官更覺得要盡一己之力幫助同袍,於是將照片轉給了曾在馬祖北竿服役的友人吳政武,希望他能一同協助,為這張照片的主人找到回家路。
套句范植源曾在媒體來採訪時說過的一句話:「以前部隊什麼都有教,就是沒教我放棄袍澤。」就可以明白這份深邃的心意。
國軍兄弟的決心,加上網路的無遠弗屆,成就了這樁美事。
由於孤墳上有照片,旁邊寫著「陸軍十師二十九團三營,上等列兵徐坤湖,基隆市人,卒於民國五十七年」,范植源憑著這個線索,將照片轉到基隆人的社團,然後消息慢慢擴散出去,遂聯繫到了基隆市政府。
只是,五十年的時光,很可能早已人事全非。徐坤湖的父母或已過世,後代或已離散,不要說是兄弟姊妹了,可能連遠親都找不到! 只是說來也真幸運,不如就稱之為命運的安排吧,徐坤湖的家人五十年來竟然從來都沒有搬離過原住處,也因為如此,才終於順利找到了他的家人。徐坤湖的死,對徐家來說,一直都是心裡的痛。
早在徐坤湖過世的一九六八年,家人便試著想要帶他回家。
徐家家境清貧,徐坤湖的父親是製冰工人,因機器爆炸導致雙目失明,卻肩負著扶養六個小孩的責任。徐坤湖排行老三,是個熱心、開朗的人,常跟家人說等他退伍了就可以回家負擔家中經濟,怎知徐家卻在他退伍前的一個多月收到區公所通知,說他自殺死了,軍方僅託區公所轉交一隻手錶跟幾百元的遺物,從此再無下文。
徐家負責聯繫的小弟徐慶元說,當時家人也急著想去馬祖辦後事,但一直等不到軍方船期,軍方總是以「沒船班」、「海象不好」等各種理由拖延,再追問與三哥同梯退伍的人,也一問三不知,甚至家中正在海軍擔任旗艦兵的老四也趁著去馬祖時打聽過,結果依然空手而歸。
雖然很想找到三哥,讓他回家,但當時家境很拮据,再怎麼不甘願也沒辦法。而且當年台灣還在戒嚴時期,軍方相當封閉,根本沒有管道可問。家人只能等,只能存著一個念想,日子就這樣一天又一天地過,這一等,就是五十年。
在這漫漫幾十年,徐家狀況一直都不好,老大、老二、大姊都相繼過世,只剩下年紀最小的徐慶元跟他四哥還在世上。也因為親人相繼故去,對於讓三哥回家的那一絲懸念也逐漸黯淡、漸漸不抱希望,直到接到市府的聯繫,那盞行將熄滅的火苗才又驀地燃起。
「我真的很想去接三哥回家,但沒有錢可以飛去馬祖完成心願,更別說接回來之後,遷墳也需要一筆龐大費用。」徐慶元無奈地說。
對他們這樣清貧的家庭來說,活著不容易,但即便想痛快死去,也仍舊擔心死後的軀體無處安葬、沒有落腳之處。這點,我們自然是可以感同身受的。
就因為這樣,范植源找上了我們。他說:「我答應了學長,一定要幫他返台回歸故里,無論如何一定要做到。」
由於被他的熱情感動、也希望徐家能夠放下那半世紀的遺憾跟包袱,繼續往前走,我們承擔下了這份差事,決定飛往馬祖一趟,幫徐家免費辦後事。
當時是二月底,冬天的馬祖陰雨綿綿、天候陰晴不定,氣溫平均只有一度到兩度左右。本來我們是打算二十三號要搭船過去,但天候實在太差,始終沒能開船,連一班航班也都沒有。眼看著一群人只能乾等,心急如焚卻莫可奈何。
一直到二月二十六日,終於有飛機要飛了,搭飛機的時候,與會的志工還是不免擔心地說:「雖然真的是等不及了,但若天候太不好,到時候可能還是要在馬祖多待幾天。」
說也奇怪,我們預備去馬祖帶徐上兵回家那幾天,天氣原本始終十分糟糕,誰知道就在近一個小時的飛程落地馬祖北竿後,突然天候轉而大好,之後也是連續兩日的好天氣。當地負責接待的人員說,這是馬祖多天來第一次放晴。一下飛機,在馬防部政戰主任余熙明少將暨軍方人員大力協助下,車子直接開往中興公園。
抵達墓碑所在之處前,要先經過一段雜草叢生的地帶,得拿鐮刀割草才能前行,可一找到墓碑,起掘工作便非常順利,連三次擲筊引魂,也是一擲就過。
在墓碑前,徐家小弟抱著墓碑痛哭。我們停下手上工作,讓他好好跟三哥敘了舊。
五十年的陰陽相隔,想必他內心也累積了許多無處可訴的心事吧? 如今,總算是可以好好地跟三哥傾吐了。在這之後,我們對徐上兵的墓碑行了軍式敬禮,接下來便正式開挖。
開挖的過程極為順利,一個多小時就完成。然而,在撿骨的時候,我們發現徐上兵的頭顱上竟有著彈道痕,眾人不禁相對愕然,彷彿目睹的是一顆未爆彈。這類事情,我們心照不宣,但也知道事情已經過了五十年,再怎麼追究,都很難找到源頭。而更讓我們心酸的一幕,是看到徐上兵腳上一雙有如全新的黑色襪子仍牢牢穿著──他,似乎也在期待能早一點踏上回家的路啊!
我們在馬祖待了兩個晚上,直至二十八號早上才離開。那兩天,馬祖的天氣都極為晴朗,萬里無雲,諸事順利。可一到台北,便收到了馬祖當地接待人員的訊息,說我們一走,馬祖又陷入了寒冷陰雨。
徐上兵的遺骨回到了基隆火化,我們善願協會志工在三月三日為其辦理告別式。魂歸故里,後來也經由基隆市政府的協助,讓他的骨骸回到基隆南榮公塔安奉。漂泊五十年的遊子,終於回家了!
一場送行的體悟:網路世界無遠弗屆,拉近了許多人的距離,不單讓很多上了年紀的人找到失聯已久的朋友,甚至,還能讓離家已久的遊子,找到回家之路。
而徐家人的不死心,也是重要力量。徐家這五十年來未曾遷移過戶籍,縱使物換星移,但家人思念三哥的心永遠都在,也是這樣的相信與等待,才換來圓滿的結局。
二十年的漫長回家路
時間:1999 年
貝蒂在遇見我們之前,已經在醫院太平間的冷藏室裡「住」了超過一年的時間了。
不,或者更正確地說,其實是我們遇見了她。我一直認為,貝蒂是我的貴人,若不是因為她,我就不會成立協會,如今我們就無法幫助到這麼多家庭或迷失的旅人,送他們好好地、舒適地走上最後一程;如果不是她,接下來的這些故事,都不會開始了。
這位有著美國身軀、華人靈魂,始終渴望尋根返鄉的女子,看似藉由我們的幫助讓客死異鄉的她走上返鄉之路,但也是她,幫助我們開啟了之後這一趟趟,雖然漫長卻充滿溫暖的「最後一程」。
華人深信「死者為大」,一場普通的喪事,辦完往往十幾二十萬跑不掉,而且就習俗來說,好好送走至親最後一程,更是身為子女父母應盡的責任與義務。因此許多人就因為這最後的一程,成了被留下的親人最沉重的負擔,尤其假若家人原先就過著拮据的生活,又憑空多了數十萬的債務,在悲痛親人離世之際,更是一重大打擊。就因為如此,讓我在協助弱勢家庭多年後,也興起了免費協助辦理殮葬的念頭。
只可惜我這樁美意,頭半年,並不如我想像得順遂。主要是因為,在華人在保守的觀念中,要仰賴別人幫助完成喪事是不孝的、抬不起頭的。因此多數弱勢家庭寧可跟週遭親友或錢莊借錢,平添自己更多的負擔,也拉不下臉來接受我們的援手,多數人多是婉拒。
約過了半年的時間,或許上蒼有感受到我們的誠意跟決心,某天下午醫院的社工突然來電告訴我貝蒂的故事。我從來也都沒有想過,這件事的起點竟會是從一個外國人開始。
在我們接受這案件之前,貝蒂已經在醫院太平間的冷藏室住了超過一年。住在美國紐奧爾良、高齡七十九歲的貝蒂,她一直堅信自己的前世是中國人,也因如此,當她得知自己罹患乳癌並已多處轉移後,決心來亞洲開啟她的尋根之旅。可惜的是,才與旅伴雷諾從曼谷來到台灣的第三天,貝蒂就在中正紀念堂因氣喘發作昏迷而失去意識,被送去了醫院急救。
氣切搶救成功的她,恢復意識後,顫抖地寫下了她最後的願望「Go Home」,沒多久,便又再度失去意識。而她的旅伴雷諾,卻因為身上的盤纏已經花光,不得已只好返回美國,甚至連貝蒂在美國的家人,也未曾跟醫院聯繫過,在這段期間只有她一位住在菲律賓的義女,託人寄了個天使雕像過來而已。對於貝蒂,我們所知道的,最多就僅僅只有這樣了。
在貝蒂生病的期間,醫院和社工人員也想過要讓貝蒂搭飛機回美國,不過一來航空公司深怕在漫長的旅途中發生意外,二來醫療專機也所費不貲,只好作罷。無依無靠、因缺氧陷入昏迷的貝蒂,就這樣孤寂地在醫院昏迷了一年多,最後積欠了兩百五十多萬的醫藥費辭世。聯繫了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現「美國在台協會」︶,他們也僅表示:「我們無權處理在海外死亡之美國人民遺體,且無法洽商他人願意支付其喪葬費用,但會再努力尋找家屬。」在過世後,醫院保留了她的遺體一年多,希望有人來認領,不過,卻始終沒有任何一點消息。為了這件事,我們也得到了善心人的幫助,在美國登報三個月,並在登報啟事上承諾貝蒂的家人我們願意支付來回機票,希望他們不要感到有負擔,能夠主動來連繫我們。
大體留在醫院是小事,但貝蒂「Go Home」的心願無法了卻,才是我們心中最最不忍的。
基於同理,我們當然日夜期盼著她的家人能來接她回家,但就連她的旅伴雷諾也不再捎來任何消息。這幾年背包客盛行,許多年輕人常在網路上或同好圈中結伴出遊,也許貝蒂跟雷諾其實就只是兩個結伴出遊的銀髮背包客,彼此並無深交;也或者有可能是因信仰禮俗的不同,對多數不相信輪迴轉世的美國人而言,離世就代表了告別,不像我們華人對於最後一程如此看重。
始終想幫人走完最後一程卻無法達成的我們,以及想要回家卻始終回不了家的貝蒂,就在這機緣巧合下相遇了。
因此,當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發函告知希望能讓貝蒂以台灣居民身分辦理後事時,社工跟醫院也清楚,這樁憾事,確實該告一段落。因此,當社工致電給我時,即使根本就不熟悉殮葬事務,但我心裡頭「即使邊做邊學也一定要把這件事做完」的意念,卻很堅定。我們要讓相信輪迴轉世的貝蒂老太太,靈魂可以找到回家的路去轉世投胎。
不過答應要協助辦喪禮後,緊接著,難題就來了。貝蒂老太太是位基督徒,但又相信自己前世是中國人,既然信基督卻又相信輪迴轉世,該辦怎樣的葬禮,這可真是難倒我了。左思右想後,協會決定不如就幫她辦一場中西合併的喪禮。於是我們請來了有治喪經驗的朋友,號召各處的志工,大家開始有錢出錢、有力出力,設了靈堂、折了紙蓮花,最後在大體上多覆蓋了一件基督教特有的袍子。只要有誠心都是好的,無須拘泥於繁文縟節的規矩,爾後這也成了我們治喪的原則。
當然其中也有一些志工不能理解,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辦喪事這麼觸霉頭不吉利的事情,到底為什麼非做不可呢? 可對我而言,善心其實是沒有差別的,這不單單只是幫助貝蒂找到回家的路,更是讓許多弱勢家庭不要因為孝心而造成自身更大的負擔。
「看見大體怕不怕?」事後曾有人這樣問我。當時才三十九歲的我,幾乎沒有見過什麼屍體。說實話,並不是我膽子特別大,當天只是因為緊張到忘記害怕而已。我緊張到當醫護人員從冷藏櫃裡拉出貝蒂、屍袋的拉鍊「刷」地打開,看著她那灰色、鬆軟,幾乎無肌肉結締組織,就如同電影中常見到的屍體時,我完全無法產生任何不舒服或者奇異的感覺。
我手執銅板筊杯念念有詞,呼喊貝蒂回家。
擲出第一個允杯,然後接著兩個、三個,過程非常順利,我知道,貝蒂同意我們帶她走了。為了不讓她孤單,我還特地找來二十幾個親朋好友參加喪禮,只希望她這趟漫長的回家路能走得熱熱鬧鬧,一點也不孤單。
辦喪禮,一切儀式都以尊重死者為優先。無論他們的信仰是什麼,最重要的,都是讓他們安心好走。前後大概十天的時間,做完了頭、尾七,舉行完這場中西合併的喪禮後,我們的第一個案件完成了。
不過這個案件,即使到今日,在我心中都還感到尚未完結。葬禮結束後,我們將貝蒂火化,然後安奉在台北富德公墓的靈骨塔。至今我都仍然希望她能真正回到美國的家,可二十年過去了,始終沒有任何消息。
最後,我只能換個方向想,告訴自己,若不侷限於我們華人的傳統家庭觀念,那麼,堅信自己前世是中國人的貝蒂,某個程度上,也已經回家了。
一場送行的體悟:許多人忌諱喪禮、害怕死亡,但其實它不過只是人生裡頭,必經的一段過程而已。佛家說:「日日是好日,時時是好時。」也正是說明了心境的重要,他鄉也可轉換成故鄉。死者為大,只要懷抱著敬意與誠心,便無所懼。
第8場送行
徐上兵半世紀的歸路
時間:2017 年
──一九六八年,上兵徐坤湖死於馬祖,葬於北竿,軍方以自殺結案,再無下文。家屬接獲通報雖不信,亦無能翻案。
──二○一六年底,相隔近五十年後,退伍軍人吳香官在北竿的中興公園發現軍人公墓,以及其中的徐坤湖墓碑。
──二○一六年底,臉書社團「馬祖捍衛戰士」由在馬祖北竿服役退伍的吳政武貼出徐坤湖墓碑照,社團社員范植源向基隆市長請求協助。
──二○一七年,……經過五十年的寂靜等待、五十年的兩岸眺望,一縷忠魂曾執干戈以衛社稷卻有家歸不得的徐坤湖,終於踏上了返鄉路。
我是個很善於等待的人,有時那耐性都讓人感到不可思議。每次有媒體朋友來採訪,我告訴他們,我還在等待已經在靈骨塔安奉了近二十年的貝蒂家人來認領她的骨灰,別人都笑我異想天開。
但真的異想天開嗎? 若聽了徐上兵的故事,也許就不會覺得這件事不可能了。
徐上兵等了整整五十年,才終於回到家。
這五十年來,他的家人始終無法放下,只是找不到救濟管道。任誰也沒想過,會是用這樣的方式,讓他找到回家之路。
事情是從臉書「馬祖捍衛戰士」這個社群粉絲頁所開始的。
社群網路的興起,不僅僅只是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也徹底顛覆了人跟人的距離。社團的社員范植源,是一位曾在馬祖當過砲兵的復健師,他憑著對馬祖的熱情跟傻勁,一直對袍澤盡心盡力,讓一些退伍的同袍可以在此交流。某天,突然有人在社團轉貼了一張孤墳的照片,問了一句:「我們有可能幫他找到回家的路嗎?」
在海島當兵的孤寂,沒嘗過的人不會懂。想到自己那兩年天天思鄉的心情,再想想這些永遠都無法回家的孤墳,范植源、吳政武及吳香官對這件事上了心。或許就是因為這樣的感同身受,只要有機會能盡點棉薄之力,都是樂意。
而想家的煎熬,發現並拍照的空軍退役軍官吳香官更懂。於二○一六年底返鄉掃墓的他,在馬祖北竿中興公園無意中發現了孤零零的墓碑,荒煙蔓草,彷彿從來沒人探訪過,上面寫著「徐坤湖」三個字。想起了報效國家時對家人的思念,吳香官更覺得要盡一己之力幫助同袍,於是將照片轉給了曾在馬祖北竿服役的友人吳政武,希望他能一同協助,為這張照片的主人找到回家路。
套句范植源曾在媒體來採訪時說過的一句話:「以前部隊什麼都有教,就是沒教我放棄袍澤。」就可以明白這份深邃的心意。
國軍兄弟的決心,加上網路的無遠弗屆,成就了這樁美事。
由於孤墳上有照片,旁邊寫著「陸軍十師二十九團三營,上等列兵徐坤湖,基隆市人,卒於民國五十七年」,范植源憑著這個線索,將照片轉到基隆人的社團,然後消息慢慢擴散出去,遂聯繫到了基隆市政府。
只是,五十年的時光,很可能早已人事全非。徐坤湖的父母或已過世,後代或已離散,不要說是兄弟姊妹了,可能連遠親都找不到! 只是說來也真幸運,不如就稱之為命運的安排吧,徐坤湖的家人五十年來竟然從來都沒有搬離過原住處,也因為如此,才終於順利找到了他的家人。徐坤湖的死,對徐家來說,一直都是心裡的痛。
早在徐坤湖過世的一九六八年,家人便試著想要帶他回家。
徐家家境清貧,徐坤湖的父親是製冰工人,因機器爆炸導致雙目失明,卻肩負著扶養六個小孩的責任。徐坤湖排行老三,是個熱心、開朗的人,常跟家人說等他退伍了就可以回家負擔家中經濟,怎知徐家卻在他退伍前的一個多月收到區公所通知,說他自殺死了,軍方僅託區公所轉交一隻手錶跟幾百元的遺物,從此再無下文。
徐家負責聯繫的小弟徐慶元說,當時家人也急著想去馬祖辦後事,但一直等不到軍方船期,軍方總是以「沒船班」、「海象不好」等各種理由拖延,再追問與三哥同梯退伍的人,也一問三不知,甚至家中正在海軍擔任旗艦兵的老四也趁著去馬祖時打聽過,結果依然空手而歸。
雖然很想找到三哥,讓他回家,但當時家境很拮据,再怎麼不甘願也沒辦法。而且當年台灣還在戒嚴時期,軍方相當封閉,根本沒有管道可問。家人只能等,只能存著一個念想,日子就這樣一天又一天地過,這一等,就是五十年。
在這漫漫幾十年,徐家狀況一直都不好,老大、老二、大姊都相繼過世,只剩下年紀最小的徐慶元跟他四哥還在世上。也因為親人相繼故去,對於讓三哥回家的那一絲懸念也逐漸黯淡、漸漸不抱希望,直到接到市府的聯繫,那盞行將熄滅的火苗才又驀地燃起。
「我真的很想去接三哥回家,但沒有錢可以飛去馬祖完成心願,更別說接回來之後,遷墳也需要一筆龐大費用。」徐慶元無奈地說。
對他們這樣清貧的家庭來說,活著不容易,但即便想痛快死去,也仍舊擔心死後的軀體無處安葬、沒有落腳之處。這點,我們自然是可以感同身受的。
就因為這樣,范植源找上了我們。他說:「我答應了學長,一定要幫他返台回歸故里,無論如何一定要做到。」
由於被他的熱情感動、也希望徐家能夠放下那半世紀的遺憾跟包袱,繼續往前走,我們承擔下了這份差事,決定飛往馬祖一趟,幫徐家免費辦後事。
當時是二月底,冬天的馬祖陰雨綿綿、天候陰晴不定,氣溫平均只有一度到兩度左右。本來我們是打算二十三號要搭船過去,但天候實在太差,始終沒能開船,連一班航班也都沒有。眼看著一群人只能乾等,心急如焚卻莫可奈何。
一直到二月二十六日,終於有飛機要飛了,搭飛機的時候,與會的志工還是不免擔心地說:「雖然真的是等不及了,但若天候太不好,到時候可能還是要在馬祖多待幾天。」
說也奇怪,我們預備去馬祖帶徐上兵回家那幾天,天氣原本始終十分糟糕,誰知道就在近一個小時的飛程落地馬祖北竿後,突然天候轉而大好,之後也是連續兩日的好天氣。當地負責接待的人員說,這是馬祖多天來第一次放晴。一下飛機,在馬防部政戰主任余熙明少將暨軍方人員大力協助下,車子直接開往中興公園。
抵達墓碑所在之處前,要先經過一段雜草叢生的地帶,得拿鐮刀割草才能前行,可一找到墓碑,起掘工作便非常順利,連三次擲筊引魂,也是一擲就過。
在墓碑前,徐家小弟抱著墓碑痛哭。我們停下手上工作,讓他好好跟三哥敘了舊。
五十年的陰陽相隔,想必他內心也累積了許多無處可訴的心事吧? 如今,總算是可以好好地跟三哥傾吐了。在這之後,我們對徐上兵的墓碑行了軍式敬禮,接下來便正式開挖。
開挖的過程極為順利,一個多小時就完成。然而,在撿骨的時候,我們發現徐上兵的頭顱上竟有著彈道痕,眾人不禁相對愕然,彷彿目睹的是一顆未爆彈。這類事情,我們心照不宣,但也知道事情已經過了五十年,再怎麼追究,都很難找到源頭。而更讓我們心酸的一幕,是看到徐上兵腳上一雙有如全新的黑色襪子仍牢牢穿著──他,似乎也在期待能早一點踏上回家的路啊!
我們在馬祖待了兩個晚上,直至二十八號早上才離開。那兩天,馬祖的天氣都極為晴朗,萬里無雲,諸事順利。可一到台北,便收到了馬祖當地接待人員的訊息,說我們一走,馬祖又陷入了寒冷陰雨。
徐上兵的遺骨回到了基隆火化,我們善願協會志工在三月三日為其辦理告別式。魂歸故里,後來也經由基隆市政府的協助,讓他的骨骸回到基隆南榮公塔安奉。漂泊五十年的遊子,終於回家了!
一場送行的體悟:網路世界無遠弗屆,拉近了許多人的距離,不單讓很多上了年紀的人找到失聯已久的朋友,甚至,還能讓離家已久的遊子,找到回家之路。
而徐家人的不死心,也是重要力量。徐家這五十年來未曾遷移過戶籍,縱使物換星移,但家人思念三哥的心永遠都在,也是這樣的相信與等待,才換來圓滿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