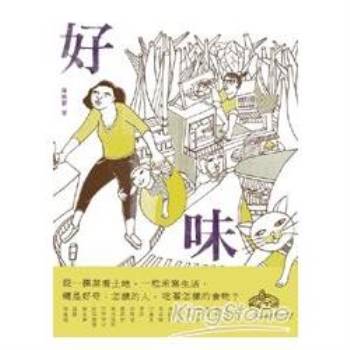張曼娟 最後的薄殼
那一年,台灣作家張曼娟獨個兒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書,人在異地,頗不適應,流言繪影繪聲,說她天天都打扮得漂漂亮亮去玩,實情可是日日和助理困在辦公室和舊電腦博鬥。很累很累,忽然看見門把上掛著一袋好吃的,有時候是剛出爐的蛋撻、有時候是新鮮的三文治,便知道好朋友Y來過又走了。Y曾經開書店,請過張曼娟出席講座。之前香港朋友大都盛宴招待,不是鮑魚,便是魚翅,Y卻會帶去各種各樣地道小館子,張曼娟還記得第一次去潮州店「打泠」。玻璃櫃子掛滿琳琳總總食物,感覺好誇張:「簡直就是走進《千與千尋》那大吃大喝的場面!」
Y通常都不大吃,只是喝啤酒,笑笑看著她開懷大嚼。
二零零三年一場瘟疫過去,張曼娟來到香港,自然少不得找Y。可以平安重逢,吃吃喝喝都分外開心,在離港前一夜,Y竟又帶著一盒便當去到酒店。「才開門,就嗅到一股鮮烈的香氣,忍不住咽下口水。」她依然記得好清楚,那是剛炒好的「薄殼」:蝴蝶花紋外殼,薄到近乎透明,嫩蜆肉滿滿都是湯汁,味道鮮甜得像是會發光。薄蜆只有短短一個月當造,難得可以吃到,她回台後記下當時的心情:「整片寧靜的海洋窗景,可以相交一輩子的好朋友,我被恩典的光芒籠罩,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只是好朋友,沒有跟她相交一輩子。二零零八年Y語調輕鬆地在部落格宣佈自己「is cancering」。他以最樂觀堅強的態度,面對翻覆不定的病情,一方面認真檢視自己對生命的態度,另一方面嘻笑幽默地,不斷讓孩子和太太作好心理準備,期間尚有餘閒翻看所有杜琪峰的電影,寫了一系列影評。張曼娟知道消息,非常著急:「我要來香港看你!」
Y說:「不用啦,等我好一點來看你好了。」
「不行,我一定要來,機票都訂好了。」正好九月教師節台灣放假,張曼娟決定早上飛過來香港,待三小時,當天回台北。
「那太好了,這是最後可以吃到『薄殼』的時候。」Y居然答。
這時還顧著吃?張曼娟氣炸了,趕到香港,Y非常瘦,她甚至認不出來。「你一定要好起來!」她嚴重地警告他。那天吃了什麼?不記得了。過了兩個月,Y稍稍好轉,便去台灣,張曼娟帶他去花蓮看太平洋,他一個人赤著腳在海灘跑,很開心,回台北的火車上,他累得睡著了。
這是她最後一次見到他。
翌年Y出殯,來了超過一千人,過了很久,他的部落格還有人繼續留言,談電影、說人生。
2011年張曼娟來香港出任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主任,Y的爸爸找她吃飯,問她想吃什麼。「我不曉得,從來都是Y決定去什麼地方、點什麼菜。」這些年來他們吃過的飯店,她從來沒有記下來,因為沒料到他會不在。
那鮮甜多汁的「薄殼」,熱騰騰裝在鋁盤裡的,到底要去哪找?
「我想,可能不會再吃『薄殼』了。」張曼娟說。
岑寧兒 傍身玉桂水
岑寧兒(Yoyo)第一次在北京見到李宗盛,他開口就問:「what’s music to you?」
「你是music lover?還是music player?」他說:「你可以只是喜歡音樂,不是一定要做音樂。」
Yoyo想了一會:「我想試試啊。」她本來也可以選擇電影,但在遇上李宗盛那一刻,答案就容易得多。
「那就試啊。」李宗盛繼續問:「你要當performer,還是musician?」Performer的訓練是要能唱不同的歌,彷彿演員,不同類型的歌都能駕馭。「musician呢,就選一個樂器,用一年時間看一個城市,看自己能寫出什麼。」李宗盛說,Yoyo也不明白為什麼是「城市」,當時她二十一歲大學剛畢業,聳聳肩,就留在北京。
她小時學什麼樂器都沒能堅持下來,唯有隨手挑了一把結他。接下來四年,她待在李宗盛的工作室,周末去Jazz Bar唱歌,並且開始寫歌:「每一天都會嘗試對自己的感覺敏感一些,記下來,隨便哼下來的音樂,也寫下來,時時刻刻都在想,如何能變成一首歌。」
第一首寫出來的歌,叫《明天開始》,每件事都是明天才做啦,那是Yoyo當時掛在口邊的說話,朋友們聽了,都笑說這歌真寫實。她甚至寫了一首歌懊惱《寫什麼?》:寫心情寫太陽寫月亮,沒有什麼大道理想講,不憤世嫉俗沒需要咆哮,腦裡只有一堆問題,想坦白,可是又怕暴露自己……到底還有什麼是人家沒寫過,寫什麼?!
直到後來寫了一首歌《Mask》:
讓我帶著對你對一切的期望
讓我為你的期望裝模作樣
不敢被你看穿
不能再讓你失望
一開口清唱,那美麗的嗓子,教人渾身起了雞皮疙瘩。Yoyo也是憑著這歌聲被人認識,那是在北京四年後回到香港,在陳奕迅演唱會和五個朋友一起當和音,清唱《The end of the world》太投入,哭了,全場人人動容,陳奕迅衝口而出:「天籟。」
這兩年Yoyo決定在台灣繼續創作音樂,到不同的音樂場合演奏她在北京時寫的歌。她自資出版一隻小小的唱片,只有三首歌。「我沒錢錄太多歌,能力也只足夠做好這十分鐘的音樂啊。」她笑著不斷向桌上的唱片點頭:「多謝陳奕迅!多謝陳奕迅!不過看來要再唱多二十場才夠結帳!」
一步一腳印,她用很大力氣推開家人幫忙,爸爸岑建勳在電影圈響噹噹,一出口便可以幫女兒打通人脈策劃定位;媽媽劉天蘭一出手,不費力便能觸目有型──「但那還是自己嗎?他們太強了,讓他們幫忙,我永遠不會知道自己是什麼。」Yoyo直到唱片發行,才送給爸媽。媽媽拿著不斷說:好靚啊好靚啊,爸爸感動如小影迷。
Yoyo唯一拿來「傍身」的,是玉桂水,這是岑家秘方:玉桂皮刨絲,放在暖杯裡用熱水焗一晚。「我伯父說玉桂是『藥王』,只剩一口氣的,喝了都能醒一會!」她誇張地睜圓雙眼,拍拍木桌子:「我以前一有流行感冒一定中招,現在明顯病少了。」每天早上,她都喝一杯。
葉漢華 街貓口中的雞頸
童畫裡的貓咪,喝牛奶,吃鮮魚,跳上主人大腿嬌嗲地喵~
街頭的貓,沒有主人,也就不識嬌嗲,要嘛很兇很兇,面對大狗都敢揮拳咆叫,要嘛極度機警,風一吹過亦急急躲起來,簷縫裡只剩一對閃閃眼睛。所有介乎兩者的,都好難活下去。
葉漢華不是第一個新聞攝影記者拍攝街貓。謝至德拍過一陣子老店的貓,懶洋洋地攤在藥房玻璃櫃瞇眼睛;符俊偉的貓,俏皮幽默,他甚至拍過像貓的雲,一幅是一朵貓雲,一幅是一堆雲中間,露出如貓的藍天。葉漢華鏡頭下的,卻是城市中的戰士,一臉兇狠。
「我最初只是覺得意:貓打呵欠的樣子好有趣。」那是二零零二年,葉漢華回家途中總會經過荃灣一座廟宇,那裡有二十多隻貓,玩貓,拍貓,正好輕鬆一下,然而一個寒冷雨夜,幾隻狗從山上下來,把四、五隻貓咬死了。他開始走進貓的世界:「街貓的生活充滿挑戰:野狗咬、漁護署捉、窩居被掃蕩,貓一直要適應環境。」
新聞攝影工作零碎割裂,任由上司指派,可是從一個記者會,趕到另一個記者會之間,時間就是自己的,葉漢華每天都把握機會與貓相遇,明明可以坐地鐵,他選擇走路,並且盡挑舊區後巷。
一看見貓,馬上悄悄停下,細細觀察,如果貓不介意,慢慢走近。「不拍照也沒所謂,有時我也會無所事事地和貓一同發呆,默默感受彼此的互動。」他是安靜的人,說話很輕。有一張相片裡的貓剛剛好在兩個屋頂間飛跳,原來他看見貓跳過去,心想可能會跳回來,就在站在兩個屋頂之間抬頭按著相機等,十分鐘後,貓果然跳回去,耐性少一點反應慢一點,都拍不到!
「有時愈想拍,愈是會錯失機會,那就平常心吧,因為這就是貓。」他溫和地說。十年來天天拍,晚晚放上Facebook群組「捕貓捉影」,幾乎踏遍港九新界,葉漢華明白街貓:一塊爛布、一堆紙皮,都可以是貓窩,比較好的地頭是高少少、隱蔽少少,例如簷縫頂、鋅鐵之間,可是這樣的舊區漸漸消失,有些貓選錯地方?在去水道,大雨一來,就被沖走。
肚子餓,後巷的垃圾堆有剩飯菜渣。有兩張相片令人印象深刻,一張是貓媽媽不知從那裡偷到一大塊牛扒,爬上水管,上面成堆小貓伸長脖子等著;另一張,那貓好兇地不知咬住什麼。
「是雞頸。」葉漢華聽附近的阿姐說,那貓是剛剛被人丟棄的,燒臘店賣剩有點肉的部位,都給其他街貓搶走了,這隻貓,只搶到最多骨頭的雞頸。葉漢華走得太近,貓於是死命咬實。不是所有的街貓都知道,最最最危險的,是整罐打開的貓罐頭──漁護署會在捕貓籠裡放罐頭,貓一走進去,閘門馬上落下,漁護署收走後四日沒人認領,便會處死。二零一零年,全港超過一萬五千頭貓和狗被漁護署捕獲,一萬三千多頭,都死了。
有些義工會把街貓帶回家,然而數量一多,?環便差,貓長期被困在籠裡,雖然安全,卻不見得好過在街頭。亦有好心街坊餵貓,然而如果事後沒清潔,隨時會被其他街坊投訴,招惹漁護署介入,再者街貓數量一直增加,亦不是辦法。
葉漢華支持「捕捉絕育回放」 (TNR Trap, Neuter, Return)):「台灣以前也像香港,但有好些攝影師關注街貓,作品出版很受歡迎,人們開始關注並且展開TNR,幾年下來,街貓的數目真的開始減少。」當地旅遊局甚至把街貓變成景點,例如「淡水貓散步」,在淡水地圖上加上不同的街貓。
香港何時也可這樣包容?葉漢華每天繼續拍攝。
石祐珊 守護家燕媽媽
石祐珊很小很小,便知道要守護媽媽。
薛家燕當年想得非常仔細才結婚,以前八歲便出來拍戲,根本不懂做家務,特地學足一年烹飪,還要和奶奶、丈夫的哥哥弟弟一起住,每天吃飯都一圍酒席似的,三十四歲趕緊生下大女兒祐珊,每隔兩年又生下兒子和小女兒。
可是丈夫還是丟下她和三個孩子。
「很小就知道媽媽和爸爸有問題,孩子很敏感,一早便曉得。」祐珊說但凡爸爸不在家,她都會跟媽媽一起睡,弟弟妹妹在隔壁的房間呼呼大睡,她卻緊張地陪著媽媽,擔心媽媽不開心。
丈夫離開家裡足足三年,家燕才決定離婚,奶奶馬上以業主的身份,要她和三個孩子都離開。無人無錢,薛家燕說那刻曾經想過由二十五樓的寓所跳下來,好在聽到孩子叫媽媽,她才打消自殺念頭。
從大屋搬到小房子,孩子都知道環境艱難。媽媽決定重回娛樂圈,十一歲的祐珊懂事地說:「媽媽你去拍劇吧,我會照顧弟弟妹妹!」媽媽聽了紅著眼,接下《真情》裡「好姨」的角色。
現在想起來,祐珊也發笑:「其實能做什麼?弟弟九歲妹妹七歲,我頂多就是煮公仔麵給他們吃。」當時也有工人照顧,祐珊便立志要努力讀書,為弟弟妹妹當好榜樣。
學校作文寫「我最難忘的一夜」,祐珊寫弟弟肚子痛,她餵他吃藥,仍然沒有好轉,只好整晚抱著弟弟不敢睡,後來老師把作文給媽媽看,媽媽當場哭了。小妹妹買鞋子也懂得選大一點的,由七歲可以一直穿到十歲,破破爛爛地。
當時全家人最開心,便是一起去快餐店。「明知家裡沒錢,難道還吵去迪士尼樂園?但最便宜的連鎖店雪糕,也吃得好開心,大家吃吃吃!」吃得弟弟妹妹都圓滾滾地,祐珊卻是最瘦的一個。
守護的角色,一直至今沒變。
二零零九年媽媽割膽手術後胃炎,一度陷入昏迷,祐珊馬上飛回香港。「弟弟妹妹都在美國唸書,我也在美國工作,有兩年時間沒有人在媽媽身邊,我很明白她太孤單了,所以拚命接工作也不願回家。」祐珊也閃過一絲猶豫,但很快便決定:「我要回來陪媽媽。」
祐珊原本刻意不靠媽媽的關係,考進MTV公司工作,後來又進到美國著名的經理人公司William Morris,這公司有過百年歷史,第一位藝人是差利卓別靈,全公司上千人,只有大約十個亞洲臉孔。祐珊在William Morris要由派信做起,才剛做了三年。
她坦言喜歡做照顧人的角色,不願走到幕前:「小時候也曾經有人邀約和媽媽一起拍戲,可是媽媽說一定要讀完大學,這是對的,現在我完全知道在背台詞,和為藝人策劃事業,我更有興趣後者。」她暫時是自由身,替不同的藝人接工作,因為美國公司的關係,很多機會作為中間人,把華人藝人帶到國際,有時,也幫忙媽媽接洽工作。「總是要有人當醜人吧。」她笑笑。
媽媽工作好忙,沒時間再做飯,祐珊想來想去,也想不到有什麼菜是媽媽煮過的,她只記得在很小的時候,曾經和媽媽一起做壽包。
那些年,薛家燕連壽包也自己做。
Ger媽 一個電話擺平親家
Ger在廣東話,指陽具,怎樣的女孩,會起這樣的名字?
數香港八十後社會運動青年,Ger(蔡芷筠)一定榜上有名,她甚至有份決定用「八十後」作為字頭。那是二零零九年她和幾個朋友一起發起「八十後六四文化祭」,同年又與更多的朋友一起組成「八十後反高鐵青年」,接著以「八十後文藝青年」名義參選藝術發展局的民選委員,成為藝展局史上最年輕的藝術教育小組主席。
大膽、叛逆、敢作敢為,這些普遍烙在「八十後」的標誌,似乎亦可以套用在Ger媽身上。
「以前不是有部電影叫《靚妹仔》?我阿媽覺得是自己的寫照,她甚至和戲中主角溫碧霞、麥德和等都是朋友,一齊跳舞、一齊『蒲』。」Ger說:「阿媽十八歲就生我,我是婆婆帶大的。」
媽媽只肯唸完小學,十八歲在髮型屋剪髮電髮,夠膽生孩子,但沒耐性當媽媽。Ger對媽媽最早的記憶,是媽媽不小心讓她撞傷頭,可是讀書期間,同學反而羡慕她的媽媽不管不罵。
家長日,媽媽會來,但亦坦白告訴老師:「我也不知道女兒怎樣的。」小學四年級Ger忘記在手冊寫日期,老師要求見家長,媽媽見過老師,走出學校門口就點煙:「你個班主任真的好串,但不理她。」中六班主任斷言:「你女兒很不行,沒救啦!」「關你什麼事?」媽媽一句衝過去。
Ger好感動:「阿媽不是傳統關愛照顧型的母親,但好撐我!」
她進到大學開始食煙,媽媽居然說:「你這也太遲了吧。」之後兩母女最「舒暢」的活動就是一起在騎樓抽煙,閒談。「爸爸那邊的親戚會因為媽媽抽煙有偏見,但其實這種判斷好表面,我阿媽,大方、有義氣,食煙不等於是壞人。」她說來眼睛閃閃,全是欣賞的神色。
去年Ger和曾經是她的大學老師曾德平結婚,曾媽媽不喜歡Ger又食煙又搞社運,好勉強才肯兩家人坐下來吃飯,談話間,兩位媽媽聊到原來二十年前都在同一間海鮮酒家工作過,曾媽媽談起一個失散了的舊同事,Ger媽馬上打電話找到對方,手機一遞,就讓曾媽媽和舊同事講電話。
這通電話後,整頓飯的氣氛突然一百八十度轉變。
沒有反駁,沒有申辯,行動勝於一切,會記住多年的朋友,一定是交得過的朋友,能夠馬上找到,可見也是義氣之人——曾媽媽終於接受這段婚姻。
婚後,Ger戒了煙,母女沒有一同抽煙,但不時相約去旅行,Ger非常落力照顧母親。她說起有次看到媽媽喜歡的monchichi公仔:「我買給你?!」「你就買啊。」媽媽答得好酷,可是一收到公仔,馬上放在褲袋,還特地露出公仔頭,去到餐廳還拿出手機替公仔拍照。
「媽媽心底裡是小女孩,你說怎可以不疼她!」Ger在旅途上變成照顧的角色,不時嘮叨:咳嗽還喝汽水?病了又不早點睡?三更半夜還要唱K?
媽媽有時聽,有時不。
那一年,台灣作家張曼娟獨個兒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書,人在異地,頗不適應,流言繪影繪聲,說她天天都打扮得漂漂亮亮去玩,實情可是日日和助理困在辦公室和舊電腦博鬥。很累很累,忽然看見門把上掛著一袋好吃的,有時候是剛出爐的蛋撻、有時候是新鮮的三文治,便知道好朋友Y來過又走了。Y曾經開書店,請過張曼娟出席講座。之前香港朋友大都盛宴招待,不是鮑魚,便是魚翅,Y卻會帶去各種各樣地道小館子,張曼娟還記得第一次去潮州店「打泠」。玻璃櫃子掛滿琳琳總總食物,感覺好誇張:「簡直就是走進《千與千尋》那大吃大喝的場面!」
Y通常都不大吃,只是喝啤酒,笑笑看著她開懷大嚼。
二零零三年一場瘟疫過去,張曼娟來到香港,自然少不得找Y。可以平安重逢,吃吃喝喝都分外開心,在離港前一夜,Y竟又帶著一盒便當去到酒店。「才開門,就嗅到一股鮮烈的香氣,忍不住咽下口水。」她依然記得好清楚,那是剛炒好的「薄殼」:蝴蝶花紋外殼,薄到近乎透明,嫩蜆肉滿滿都是湯汁,味道鮮甜得像是會發光。薄蜆只有短短一個月當造,難得可以吃到,她回台後記下當時的心情:「整片寧靜的海洋窗景,可以相交一輩子的好朋友,我被恩典的光芒籠罩,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只是好朋友,沒有跟她相交一輩子。二零零八年Y語調輕鬆地在部落格宣佈自己「is cancering」。他以最樂觀堅強的態度,面對翻覆不定的病情,一方面認真檢視自己對生命的態度,另一方面嘻笑幽默地,不斷讓孩子和太太作好心理準備,期間尚有餘閒翻看所有杜琪峰的電影,寫了一系列影評。張曼娟知道消息,非常著急:「我要來香港看你!」
Y說:「不用啦,等我好一點來看你好了。」
「不行,我一定要來,機票都訂好了。」正好九月教師節台灣放假,張曼娟決定早上飛過來香港,待三小時,當天回台北。
「那太好了,這是最後可以吃到『薄殼』的時候。」Y居然答。
這時還顧著吃?張曼娟氣炸了,趕到香港,Y非常瘦,她甚至認不出來。「你一定要好起來!」她嚴重地警告他。那天吃了什麼?不記得了。過了兩個月,Y稍稍好轉,便去台灣,張曼娟帶他去花蓮看太平洋,他一個人赤著腳在海灘跑,很開心,回台北的火車上,他累得睡著了。
這是她最後一次見到他。
翌年Y出殯,來了超過一千人,過了很久,他的部落格還有人繼續留言,談電影、說人生。
2011年張曼娟來香港出任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主任,Y的爸爸找她吃飯,問她想吃什麼。「我不曉得,從來都是Y決定去什麼地方、點什麼菜。」這些年來他們吃過的飯店,她從來沒有記下來,因為沒料到他會不在。
那鮮甜多汁的「薄殼」,熱騰騰裝在鋁盤裡的,到底要去哪找?
「我想,可能不會再吃『薄殼』了。」張曼娟說。
岑寧兒 傍身玉桂水
岑寧兒(Yoyo)第一次在北京見到李宗盛,他開口就問:「what’s music to you?」
「你是music lover?還是music player?」他說:「你可以只是喜歡音樂,不是一定要做音樂。」
Yoyo想了一會:「我想試試啊。」她本來也可以選擇電影,但在遇上李宗盛那一刻,答案就容易得多。
「那就試啊。」李宗盛繼續問:「你要當performer,還是musician?」Performer的訓練是要能唱不同的歌,彷彿演員,不同類型的歌都能駕馭。「musician呢,就選一個樂器,用一年時間看一個城市,看自己能寫出什麼。」李宗盛說,Yoyo也不明白為什麼是「城市」,當時她二十一歲大學剛畢業,聳聳肩,就留在北京。
她小時學什麼樂器都沒能堅持下來,唯有隨手挑了一把結他。接下來四年,她待在李宗盛的工作室,周末去Jazz Bar唱歌,並且開始寫歌:「每一天都會嘗試對自己的感覺敏感一些,記下來,隨便哼下來的音樂,也寫下來,時時刻刻都在想,如何能變成一首歌。」
第一首寫出來的歌,叫《明天開始》,每件事都是明天才做啦,那是Yoyo當時掛在口邊的說話,朋友們聽了,都笑說這歌真寫實。她甚至寫了一首歌懊惱《寫什麼?》:寫心情寫太陽寫月亮,沒有什麼大道理想講,不憤世嫉俗沒需要咆哮,腦裡只有一堆問題,想坦白,可是又怕暴露自己……到底還有什麼是人家沒寫過,寫什麼?!
直到後來寫了一首歌《Mask》:
讓我帶著對你對一切的期望
讓我為你的期望裝模作樣
不敢被你看穿
不能再讓你失望
一開口清唱,那美麗的嗓子,教人渾身起了雞皮疙瘩。Yoyo也是憑著這歌聲被人認識,那是在北京四年後回到香港,在陳奕迅演唱會和五個朋友一起當和音,清唱《The end of the world》太投入,哭了,全場人人動容,陳奕迅衝口而出:「天籟。」
這兩年Yoyo決定在台灣繼續創作音樂,到不同的音樂場合演奏她在北京時寫的歌。她自資出版一隻小小的唱片,只有三首歌。「我沒錢錄太多歌,能力也只足夠做好這十分鐘的音樂啊。」她笑著不斷向桌上的唱片點頭:「多謝陳奕迅!多謝陳奕迅!不過看來要再唱多二十場才夠結帳!」
一步一腳印,她用很大力氣推開家人幫忙,爸爸岑建勳在電影圈響噹噹,一出口便可以幫女兒打通人脈策劃定位;媽媽劉天蘭一出手,不費力便能觸目有型──「但那還是自己嗎?他們太強了,讓他們幫忙,我永遠不會知道自己是什麼。」Yoyo直到唱片發行,才送給爸媽。媽媽拿著不斷說:好靚啊好靚啊,爸爸感動如小影迷。
Yoyo唯一拿來「傍身」的,是玉桂水,這是岑家秘方:玉桂皮刨絲,放在暖杯裡用熱水焗一晚。「我伯父說玉桂是『藥王』,只剩一口氣的,喝了都能醒一會!」她誇張地睜圓雙眼,拍拍木桌子:「我以前一有流行感冒一定中招,現在明顯病少了。」每天早上,她都喝一杯。
葉漢華 街貓口中的雞頸
童畫裡的貓咪,喝牛奶,吃鮮魚,跳上主人大腿嬌嗲地喵~
街頭的貓,沒有主人,也就不識嬌嗲,要嘛很兇很兇,面對大狗都敢揮拳咆叫,要嘛極度機警,風一吹過亦急急躲起來,簷縫裡只剩一對閃閃眼睛。所有介乎兩者的,都好難活下去。
葉漢華不是第一個新聞攝影記者拍攝街貓。謝至德拍過一陣子老店的貓,懶洋洋地攤在藥房玻璃櫃瞇眼睛;符俊偉的貓,俏皮幽默,他甚至拍過像貓的雲,一幅是一朵貓雲,一幅是一堆雲中間,露出如貓的藍天。葉漢華鏡頭下的,卻是城市中的戰士,一臉兇狠。
「我最初只是覺得意:貓打呵欠的樣子好有趣。」那是二零零二年,葉漢華回家途中總會經過荃灣一座廟宇,那裡有二十多隻貓,玩貓,拍貓,正好輕鬆一下,然而一個寒冷雨夜,幾隻狗從山上下來,把四、五隻貓咬死了。他開始走進貓的世界:「街貓的生活充滿挑戰:野狗咬、漁護署捉、窩居被掃蕩,貓一直要適應環境。」
新聞攝影工作零碎割裂,任由上司指派,可是從一個記者會,趕到另一個記者會之間,時間就是自己的,葉漢華每天都把握機會與貓相遇,明明可以坐地鐵,他選擇走路,並且盡挑舊區後巷。
一看見貓,馬上悄悄停下,細細觀察,如果貓不介意,慢慢走近。「不拍照也沒所謂,有時我也會無所事事地和貓一同發呆,默默感受彼此的互動。」他是安靜的人,說話很輕。有一張相片裡的貓剛剛好在兩個屋頂間飛跳,原來他看見貓跳過去,心想可能會跳回來,就在站在兩個屋頂之間抬頭按著相機等,十分鐘後,貓果然跳回去,耐性少一點反應慢一點,都拍不到!
「有時愈想拍,愈是會錯失機會,那就平常心吧,因為這就是貓。」他溫和地說。十年來天天拍,晚晚放上Facebook群組「捕貓捉影」,幾乎踏遍港九新界,葉漢華明白街貓:一塊爛布、一堆紙皮,都可以是貓窩,比較好的地頭是高少少、隱蔽少少,例如簷縫頂、鋅鐵之間,可是這樣的舊區漸漸消失,有些貓選錯地方?在去水道,大雨一來,就被沖走。
肚子餓,後巷的垃圾堆有剩飯菜渣。有兩張相片令人印象深刻,一張是貓媽媽不知從那裡偷到一大塊牛扒,爬上水管,上面成堆小貓伸長脖子等著;另一張,那貓好兇地不知咬住什麼。
「是雞頸。」葉漢華聽附近的阿姐說,那貓是剛剛被人丟棄的,燒臘店賣剩有點肉的部位,都給其他街貓搶走了,這隻貓,只搶到最多骨頭的雞頸。葉漢華走得太近,貓於是死命咬實。不是所有的街貓都知道,最最最危險的,是整罐打開的貓罐頭──漁護署會在捕貓籠裡放罐頭,貓一走進去,閘門馬上落下,漁護署收走後四日沒人認領,便會處死。二零一零年,全港超過一萬五千頭貓和狗被漁護署捕獲,一萬三千多頭,都死了。
有些義工會把街貓帶回家,然而數量一多,?環便差,貓長期被困在籠裡,雖然安全,卻不見得好過在街頭。亦有好心街坊餵貓,然而如果事後沒清潔,隨時會被其他街坊投訴,招惹漁護署介入,再者街貓數量一直增加,亦不是辦法。
葉漢華支持「捕捉絕育回放」 (TNR Trap, Neuter, Return)):「台灣以前也像香港,但有好些攝影師關注街貓,作品出版很受歡迎,人們開始關注並且展開TNR,幾年下來,街貓的數目真的開始減少。」當地旅遊局甚至把街貓變成景點,例如「淡水貓散步」,在淡水地圖上加上不同的街貓。
香港何時也可這樣包容?葉漢華每天繼續拍攝。
石祐珊 守護家燕媽媽
石祐珊很小很小,便知道要守護媽媽。
薛家燕當年想得非常仔細才結婚,以前八歲便出來拍戲,根本不懂做家務,特地學足一年烹飪,還要和奶奶、丈夫的哥哥弟弟一起住,每天吃飯都一圍酒席似的,三十四歲趕緊生下大女兒祐珊,每隔兩年又生下兒子和小女兒。
可是丈夫還是丟下她和三個孩子。
「很小就知道媽媽和爸爸有問題,孩子很敏感,一早便曉得。」祐珊說但凡爸爸不在家,她都會跟媽媽一起睡,弟弟妹妹在隔壁的房間呼呼大睡,她卻緊張地陪著媽媽,擔心媽媽不開心。
丈夫離開家裡足足三年,家燕才決定離婚,奶奶馬上以業主的身份,要她和三個孩子都離開。無人無錢,薛家燕說那刻曾經想過由二十五樓的寓所跳下來,好在聽到孩子叫媽媽,她才打消自殺念頭。
從大屋搬到小房子,孩子都知道環境艱難。媽媽決定重回娛樂圈,十一歲的祐珊懂事地說:「媽媽你去拍劇吧,我會照顧弟弟妹妹!」媽媽聽了紅著眼,接下《真情》裡「好姨」的角色。
現在想起來,祐珊也發笑:「其實能做什麼?弟弟九歲妹妹七歲,我頂多就是煮公仔麵給他們吃。」當時也有工人照顧,祐珊便立志要努力讀書,為弟弟妹妹當好榜樣。
學校作文寫「我最難忘的一夜」,祐珊寫弟弟肚子痛,她餵他吃藥,仍然沒有好轉,只好整晚抱著弟弟不敢睡,後來老師把作文給媽媽看,媽媽當場哭了。小妹妹買鞋子也懂得選大一點的,由七歲可以一直穿到十歲,破破爛爛地。
當時全家人最開心,便是一起去快餐店。「明知家裡沒錢,難道還吵去迪士尼樂園?但最便宜的連鎖店雪糕,也吃得好開心,大家吃吃吃!」吃得弟弟妹妹都圓滾滾地,祐珊卻是最瘦的一個。
守護的角色,一直至今沒變。
二零零九年媽媽割膽手術後胃炎,一度陷入昏迷,祐珊馬上飛回香港。「弟弟妹妹都在美國唸書,我也在美國工作,有兩年時間沒有人在媽媽身邊,我很明白她太孤單了,所以拚命接工作也不願回家。」祐珊也閃過一絲猶豫,但很快便決定:「我要回來陪媽媽。」
祐珊原本刻意不靠媽媽的關係,考進MTV公司工作,後來又進到美國著名的經理人公司William Morris,這公司有過百年歷史,第一位藝人是差利卓別靈,全公司上千人,只有大約十個亞洲臉孔。祐珊在William Morris要由派信做起,才剛做了三年。
她坦言喜歡做照顧人的角色,不願走到幕前:「小時候也曾經有人邀約和媽媽一起拍戲,可是媽媽說一定要讀完大學,這是對的,現在我完全知道在背台詞,和為藝人策劃事業,我更有興趣後者。」她暫時是自由身,替不同的藝人接工作,因為美國公司的關係,很多機會作為中間人,把華人藝人帶到國際,有時,也幫忙媽媽接洽工作。「總是要有人當醜人吧。」她笑笑。
媽媽工作好忙,沒時間再做飯,祐珊想來想去,也想不到有什麼菜是媽媽煮過的,她只記得在很小的時候,曾經和媽媽一起做壽包。
那些年,薛家燕連壽包也自己做。
Ger媽 一個電話擺平親家
Ger在廣東話,指陽具,怎樣的女孩,會起這樣的名字?
數香港八十後社會運動青年,Ger(蔡芷筠)一定榜上有名,她甚至有份決定用「八十後」作為字頭。那是二零零九年她和幾個朋友一起發起「八十後六四文化祭」,同年又與更多的朋友一起組成「八十後反高鐵青年」,接著以「八十後文藝青年」名義參選藝術發展局的民選委員,成為藝展局史上最年輕的藝術教育小組主席。
大膽、叛逆、敢作敢為,這些普遍烙在「八十後」的標誌,似乎亦可以套用在Ger媽身上。
「以前不是有部電影叫《靚妹仔》?我阿媽覺得是自己的寫照,她甚至和戲中主角溫碧霞、麥德和等都是朋友,一齊跳舞、一齊『蒲』。」Ger說:「阿媽十八歲就生我,我是婆婆帶大的。」
媽媽只肯唸完小學,十八歲在髮型屋剪髮電髮,夠膽生孩子,但沒耐性當媽媽。Ger對媽媽最早的記憶,是媽媽不小心讓她撞傷頭,可是讀書期間,同學反而羡慕她的媽媽不管不罵。
家長日,媽媽會來,但亦坦白告訴老師:「我也不知道女兒怎樣的。」小學四年級Ger忘記在手冊寫日期,老師要求見家長,媽媽見過老師,走出學校門口就點煙:「你個班主任真的好串,但不理她。」中六班主任斷言:「你女兒很不行,沒救啦!」「關你什麼事?」媽媽一句衝過去。
Ger好感動:「阿媽不是傳統關愛照顧型的母親,但好撐我!」
她進到大學開始食煙,媽媽居然說:「你這也太遲了吧。」之後兩母女最「舒暢」的活動就是一起在騎樓抽煙,閒談。「爸爸那邊的親戚會因為媽媽抽煙有偏見,但其實這種判斷好表面,我阿媽,大方、有義氣,食煙不等於是壞人。」她說來眼睛閃閃,全是欣賞的神色。
去年Ger和曾經是她的大學老師曾德平結婚,曾媽媽不喜歡Ger又食煙又搞社運,好勉強才肯兩家人坐下來吃飯,談話間,兩位媽媽聊到原來二十年前都在同一間海鮮酒家工作過,曾媽媽談起一個失散了的舊同事,Ger媽馬上打電話找到對方,手機一遞,就讓曾媽媽和舊同事講電話。
這通電話後,整頓飯的氣氛突然一百八十度轉變。
沒有反駁,沒有申辯,行動勝於一切,會記住多年的朋友,一定是交得過的朋友,能夠馬上找到,可見也是義氣之人——曾媽媽終於接受這段婚姻。
婚後,Ger戒了煙,母女沒有一同抽煙,但不時相約去旅行,Ger非常落力照顧母親。她說起有次看到媽媽喜歡的monchichi公仔:「我買給你?!」「你就買啊。」媽媽答得好酷,可是一收到公仔,馬上放在褲袋,還特地露出公仔頭,去到餐廳還拿出手機替公仔拍照。
「媽媽心底裡是小女孩,你說怎可以不疼她!」Ger在旅途上變成照顧的角色,不時嘮叨:咳嗽還喝汽水?病了又不早點睡?三更半夜還要唱K?
媽媽有時聽,有時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