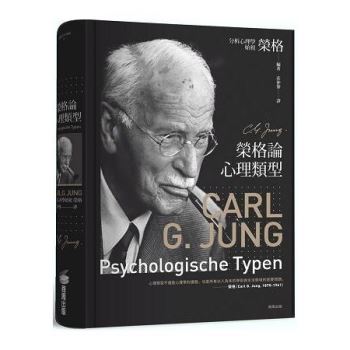心理類型學
(此篇論文Psychologische Typologie曾在一九三六年二月發表於《南德月刊》〔Süddeutsche Monatshefte〕)
在人類本質的絕對相似性和絕對差異性這兩極之間,人們還會插入幾個以規律性形式表達相似性和差異性的中間階段,也就是所謂的「類型」或—誠如人們從前所稱謂的—「性情」,這是人類學術研究史早期一個眾所周知的作法,也是人們好思考的理智所採取的行動。西元前五世紀的古希臘哲學家恩培多克勒(Empedokles, 495-430)曾以秩序原則處理自然事物的混亂。古希臘羅馬時期的醫生會把跟某些亦源於希臘自然哲學的屬性(諸如乾燥、溫暖、潮濕、寒冷)相連結的秩序原則—即風、火、水和土這四種元素—轉移到人類的本質上,並因此而試圖以有序的類別掌握人類本質紛亂的多種多樣。在這些醫生當中,主要是由古羅馬帝國時期的希臘裔醫學家蓋倫提出關於心理類型的學說,這套學說影響了歐洲對疾病和病人的學術研究長達一千八百年左右。此外,蓋倫所劃分的四種性情的舊稱還透露了本身的「體液病理學」(Humoralpathologie)的起源:憂鬱型的黑膽質(melancholisch)、冷靜型的黏液質(phlegmatisch)—希臘文的phlegma(黏液)是指燃燒和發炎,德文的Schleim(黏液)則被理解為發炎的結果—活潑型的多血質(sanguinisch),以及躁動型的黃膽質(cholerisch)。
我們現代對於「性情」的觀點當然遠比從前更富有心理學意涵,因為,「心靈」(Seele;或中譯為「靈魂」)這個概念經過兩千年的發展後,已大幅脫離了那種關於冷與熱、黏液與膽汁的觀念。現在的醫生甚至不認為,個體的性情—即某種心性狀態或易激動性(Erregbarkeit)—跟他本身的血液和體液的性質有何瓜葛,不過,他們的專業以及以身體疾病的視角所進行的醫療處理,卻會經常誘惑他們成為心理學的門外漢,而且還把心靈視為腺體生理學(Drüsen-Physiologie) 的一種具依賴性的、敏感的終端器官(Endorgan)。當然,現在的醫生所說的「體液」已不再是古希臘羅馬時期的醫生所謂的「體液」,而是仍令人難以捉摸的、能廣泛影響「心性」—作為性情方面的反應以及情緒性反應的化身—的賀爾蒙。整體的體質,也就是最廣義的體質,實際上和心靈的性情密切相關,由於它們的關係極其緊密,以致於當醫生們也把心靈現象主要視為一種對於身體的依賴時,都不該因此而受到責怪。不論在什麼地方,心靈就是充滿生命力的身體,而充滿生命力的身體則是富含心靈的形骸;不論在什麼地方或採取什麼方式,我們都可以輕易地發覺心靈和身體的一體性,而且既應該從身體、也應該從心靈層面探索這種一體性。換句話說,這種一體性在研究者看來,應該既依託於身體,也依託於心靈。唯物主義的觀點賦予了身體優先權,而讓心靈屈居於次等現象和伴隨現象的地位,而且還把它當作所謂的「附帶現象」(Epiphänomen),而不再給予實質性。心靈現象取決於生理作用的這個看法本身,雖是一個不錯的研究假設,但在唯物主義裡,它卻變成了一種哲學的侵犯。所有關於生命體的、嚴肅的學術研究都會拒絕這種侵犯,因為,學術研究一方面總是在面對有生命的軀殼包含著一個未解的奧祕這個事實,但另一方面卻也無法否認這個事實的客觀性:身體現象和心靈現象之間存在著我們完全無法調解的對立,而且心靈現象的奧祕並不亞於身體現象的奧祕。
當人們對於心靈的看法—較之古希臘羅馬時期的觀點—已往自主化和抽象化發展數百年之後,唯物主義的侵犯才在近代具有可能性。然而,在古希臘羅馬時期,人們仍然把身體和心靈(靈魂)當作無法分離的統一體而一起看待,因為,他們還是未接受基督教的異教徒,所以,比較接近原始的史前時代。在史前時代裡,人格還未受到道德的撕裂,人們還可以在童稚的純潔以及沒有責任感的狀態裡,體驗本身作為完整的、無法被切割的整體。根據現存的莎草紙文獻的描述,古埃及人在死後向陰府判官認罪時,還顯得相當天真單純,他們會表示:「我不曾讓別人挨餓,不曾使別人哭泣,也不曾殺害別人⋯⋯」,如是等等。古希臘荷馬史詩裡的英雄,在充滿合情合理的神性和人性的自然世界裡流淚涕泣、放聲大笑、發狂咆哮、以智取勝並殺害他人。至於那些住在奧林匹斯山的古希臘眾神的家族,則在非常沒有責任感的狀態裡玩得很開心。在這個哲學尚未出現的早期階段裡,人們過生活,也體驗生活,而且還受到本身的心性狀態的影響。只有激發心性的、讓心臟砰砰直跳的、讓呼吸急促或窘迫的、讓內臟受到干擾的東西,才會被當時的人們視為「與靈魂有關的東西」。因此,他們會優先把靈魂確定在橫膈膜—phrenes(橫膈膜)這個希臘字就相當於德語的Gemüt(心性)—和心臟的部位上。後來,一些哲學家才開始把理性定位在頭腦裡。非洲有些民族基本上認為,自身的「想法」就存在於肚腹裡;美國西南印地安人的培布羅族(Pueblo-Indianer)則認為,人們是在心裡「思考」(「因為,只有瘋狂的人才在頭腦裡思考」)。在這個發展階段裡,意識就是身體和心靈的統一體的體驗以及所受到的影響。不過,當既開朗又悲慘的培布羅族開始思考時,便構想出一種分裂—哲學家尼采則認為,古波斯的祆教先知查拉圖斯特拉應該為這種分裂負責—也就是產生了一些二元對立的觀念,諸如單數和雙數、上和下、好和壞的區分。
這些二元對立的觀念也是早期畢達哥拉斯學派的產物;該學派的學說強調人們的道德責任以及罪惡在形而上方面所造成的嚴重後果,而且這些主張還透過他們所推行的那些玄妙的祕密宗教儀式,而在數百年後普遍盛行於民間,並且廣泛地遍布各個社會階層。柏拉圖早就以白馬和黑馬的比喻說明人類心靈的矛盾和困境,不過,在更早之前,畢達哥拉斯學派的祕密宗教儀式便已在宣揚陰界對死人在世行徑的褒善懲惡的那套理論。這種祕密儀式絕對無關於身處「幕後隱蔽世界的」哲學家那種鑽牛角尖的心理,或位於隱僻之處的神祕主義。早在西元前六世紀便已存在於大希臘(Magna Graecia)的畢達哥拉斯主義,其實有些類似城邦的宗教信仰。後來,畢達哥拉斯主義的思想和祕密宗教儀式不僅沒有因為大希臘的沒落而完全消失,反而還在西元前二世紀經歷了本身的哲學思想的復興,而且當時還對亞歷山卓城—北非人文薈萃的港都—的知識界發揮了相當強烈的影響。畢達哥拉斯主義和猶太先知的預言在相互碰撞後所形成的產物,還可以被視為基督教—作為一種世界性宗教—的濫觴。從古希臘文化融合另一種信仰的綜攝現象(Synkretismus)裡,產生了一種對於人的分類,這種類型化完全不同於當時的醫生所遵奉的體液心理學(Humoralpsychologie),而是一些介於古希臘哲學家巴門尼德(Parmenides, ca.515-ca.450 B.C.)所指出的光明與黑暗、上與下這兩端的中間階段。這套分類把人區分為三種,即肉身的個體、靈魂的個體和心理的個體。這種劃分已不再是自然科學對於相似性和差異性的表述,而是一種批判的價值系統。這種價值系統並非依據自然的顯現方式,而是依據倫理、哲學和神祕主義性質的確定性。雖然,這不完全是「基督教式」的見解,但卻屬於使徒保羅傳道時期的早期基督教的觀點。這種觀點的存在已證明了只會體驗、且被情緒所擄獲的人們原本的一體性的分裂,因此,不該被低估。
在此之前,人們只是具有生命的存在者、被經驗者,以及未能深思地分析本身的過去和未來的經驗者,但後來卻突然具有某種能力,而被迫面對三種決定命運的、且負有道德責任的因素,也就是身體、靈魂和心理這三大因素。人們在出生時,大概就已經確定,本身是否以肉身、靈魂或未決定要偏向哪一方的中間狀態存在著。古希臘精神所具有的分裂已更形劇烈,而且還意味深長地強調靈魂和心理,靈魂和心理便因此而無可避免地脫離了自然的肉體,而獲得了自主性。因此,一切最高的終極目標便存在於道德的確定性以及心理的、超世俗的(überweltlich)最終狀態裡,心理跟肉身的分離便擴大為個體的心理和世俗世界的對立。畢達哥拉斯主義的二元對立原本所具有的那種寬容的智慧便轉變成強烈的道德衝突,挑起警覺性和意識性,就跟挑起自己與本身的衝突一樣,是再恰當不過的作法了!為了使所有的人類從原本不負責任的、天真無邪的精神狀態裡—也就是從半睡半醒的狀態裡—徹底清醒過來,並使他們轉入一種刻意地自我負責的狀態,人們已完全無法再想到其他更有效的方法。人們把以上的過程稱為文化發展,這無論如何都關乎區辨力和判斷力的發展,當然也關乎意識的發展。在智識能力的意義上,認識和批判的增加已為往後人類心理的發展創造了基礎。這種在各方面都已明確超越古希臘羅馬人民的能力表現的心理產物,就是學術研究。雖然,此時人已和自然區別開來,但卻得以因此而再度被適當地納入與自然的相互關係裡,因此,學術研究便消除了人與自然的隔閡。假如人們無法藉由傳統的宗教信仰而保住本身在形而上方面的特殊地位,大家所熟悉的「信仰和知識」的對立就會因此而產生,而人們原有的特殊地位也會隨之落空。無論如何,自然科學都意味著可以為肉體存在進行辯解的一個了不起的理由,在這個意義上,唯物主義甚至是一種具有歷史公正性的表達。人類的心靈本身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經驗領域。長久以來,它一直都屬於形上學範疇,不過,從十七、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時期開始,以學術研究的方法闡明心靈本質的嚴肅性嘗試便有增添的趨勢。人們當時以摸索的方式從感官感知著手,而後才逐漸敢於探入聯想的領域,聯想這個研究方向最後便發展成以馮特的「生理心理學」為頂峰的實驗心理學。在法國,許多醫生很快地認同了比較偏重描述的心理學,而這也是法國心理學所特有的發展。此外,法國心理學的奠基者特奧督.李波特(Théodule-Armand Ribot, 1839-1916)、心理學家暨哲學家皮耶.賈內,以及史學家伊波利特.泰因(Hippolyte Taine, 1828-1893)都在這方面貢獻卓著,而這些學術性嘗試的特徵就是心靈已消失在個別的心理機制或心理作用裡。除了這些努力之外,還零星出現了一些現今可能被人們稱為「全面式的研究方法」(Ganzheitsbetrachtung)的研究。這樣看來,似乎這個研究方向源自於傳記學,尤其是源自於從前有一段頗為美好的時期所出現的一些經常被稱為「喜於探知的」生涯敘說的作品。在這個脈絡裡,我想到了十九世紀德國醫生作家尤斯迪努斯.柯爾納(Justinus Kerner, 1786-1862)以及他撰寫的那部著名傳記《普雷佛斯特的女先知》(Die Seherin von Prevorst)、十九世紀德國知名的新教牧師約翰.布倫哈特(Johann Christoph Blumhardt,1805-1880)和他那份關於自己如何以基督教的信仰治癒女教友果特莉繽.狄圖絲(Gottliebin Dittus)的報導。此外,為了正確地看待歷史,我在這裡也不該忽略歐洲中世紀天主教會所編寫的那部《聖徒與殉道者言行錄集》(Acta Sanctorum)。一些當代的專家學者為了達到學術研究的目標,也會採用這條路線,例如維也納精神分析學家佛洛伊德、美國哲學家暨心理學家詹姆斯和日內瓦大學心理學教授弗洛諾依。詹姆斯和他的好友弗洛諾依曾試圖描述所有的心靈現象,並從整體來判斷心靈現象。佛洛伊德這位在維也納執業的精神科醫師也從個體人格的整體性與不可分割性出發,但卻局限於那個時代所主張的(驅力的)機制和個別心理作用的。此外,佛洛伊德還把人類圖像窄化成具有顯著「市民性的」、集體性的個人(Kollektivperson),而且還以片面的世界觀來進行意義的解釋。此外,令人感到可惜的是,這位精神分析學家後來屈服於醫學的誘惑,而以體液心理學的方式把心靈現象歸因於身體層面。他個人雖然感受到心靈的神聖不可侵犯性,而顯得有些膽怯,但卻也對長久以來屬於形上學領域的心靈採取了反抗的姿態。
相較於源自古希臘羅馬時期的那些關於體質的思想,佛洛伊德起初的心理學研究雖然是正確的,但後來在理論上卻想把一切再度歸因於被身體所制約的驅力,而讓自己也受制於從前的體質思想,至於我本人則是從心靈本身所固有的規律性這個看法出發。心靈和身體不論在任何地方都是無法切分的統一體,但它們在各自的本質上卻明顯地不同,以致於我們只能認為,心靈就跟身體一樣,都具有各自的本質性。只要我們無法了解心靈和身體的一體性,我們就只能分別地探討身體和心靈,而且首先似乎只能把這兩者當作互不依賴的獨立體—至少在它們的結構上—來處理。不過,我們卻日復一日地看到,身體和心靈之間並不是這種關係。因此,我們如果不想改變這種看法,就無法釐清任何關乎於心靈的東西。
我們就是認為,心靈具有本身所固有的規律性,因此,我們可以讓自己—暫時地—甩開把心靈的一切歸因於某些身體因素這個無法解決問題的任務,而把心靈的表現方式當作其自身本質的表達,並試著確定其中的規律性或類型。我所提出的心理類型學涉及了心靈結構要素的說明,但它卻不是在描述某種體質類型(Konstitutionstypus)的心靈作用,德國當代精神病理學家克雷奇默對於體格和性格的對應關係的研究,便屬於這條研究路線。我已在拙作《心理類型》裡,詳盡地呈現我個人對於純粹的心理類型化的嘗試。我在撰寫這本著作時,已行醫二十年,而且還因為診療的工作而有機會認識來自各個階層以及五湖四海的人們,而這些經驗就是我從事研究的基礎。年輕的醫生剛開始行醫時,總還想著臨床的病象和診斷,但隨著經驗的增加,就會逐漸獲得一些完全不同的印象,即人類個體驚人的多樣性,以及個案所顯示的大量而混亂的變異。個案特殊的性格和特殊的生活情況會導致病象的出現,如果人們對此還有興趣加以觀察,就會發現,這些病象或多或少會被強制套上某種臨床的診斷。所謂的臨床病象其實更是某些性格所偽裝的、或刻意表現的外顯,相較於這個事實所帶給我們的強烈印象,人們用哪個名稱來指謂這種失調的狀況,就顯得無關緊要了。
由於所謂的「情結」純粹是個體的某種性格傾向所造成的結果,因此,這些情結—作為精神官能症的「核心要素」—也是無足輕重的。這種情況最容易顯現在心理病患與原生家庭的關係裡。舉例來說,某個病患有四個兄弟姊妹,他在排行上既不是老大也不是老么,而且跟其他的手足一樣,接受相同的教育並擁有相同的生活條件,但是,其他的兄弟姊妹都健康無虞,而只有他生病。對他的個人狀況的檢查則顯示,他的兄弟姐妹也承受、甚至還忍受一連串相同的影響,但只有他因此而發病,至少看起來是這樣。實際上,這些影響並不是他生病的真正原因,而是後來出現的一些表面的、不實在的解釋。其實精神官能症真正的起因在於患者本身所固有的方式,比方說,患者接受和處理外在影響的方式。在比較過許多個案之後,我逐漸明白,顯然一定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普遍態度存在著,因此,由較為高度分化的個人所組成的全體人類,也可以被區分為兩種類別。不過,實際的情況顯然不是這樣,所以,我們只能說:如果我們觀察的對象是較為高度分化的個人,就可以清楚地觀察到這兩種普遍態度的差別,換句話說,這兩種態度的不同必須超過一定的分化程度,才能被觀察到,並有其實際的意義。上述的患者通常不屬於一般常見的類型,因此,無法在與生俱來的本能的基礎裡找到足夠的確定性。這種本能的不確定性是個體發展片面性態度的重要理由之一,個體的片面性態度與習慣有關,但最終卻是由遺傳所決定並促成的。
我把這兩種不同的基本態度稱為「內傾」和「外傾」。外傾的特徵就是對外在客體的關注,對外在事情的發展過程和要求抱持開明和熱忱的態度,因此,外傾者不僅影響它們,也讓自己接受它們的影響。他們對本身處於這種外傾狀態以及和他人的共同參與懷有樂趣和需求,而且能夠忍受忙碌和喧嚷,甚至本身還樂在其中。此外,他們也會持續關注本身與周遭的人的關係,並維持自己和朋友及熟人之間的情誼,但卻不會吹毛求疵地挑剔自己所結交的人。他們相當重視如何影響以及是否影響自己的周遭世界,因此,非常樂於讓自己在公開的場合有所表現。與此相應的是,他們通常會儘可能把集體性賦予本身的世界觀及倫理道德,並格外強調利他主義,至於他們的良知則高度取決於周遭人們的意見。當別人「知道什麼」時,他們主要的道德考量才會展開,而且他們的宗教信念在某種程度上也受制於多數人的決定。
只要有一丁點兒可能,外傾者本身的主體就會處於隱晦之中。外傾者會以無意識遮掩主體,而讓自己無法察覺到它的存在,而且他們特別厭惡對本身的動機進行批判性檢驗。他們的祕密往往藏不了多久,就會跟別人分享。不過,如果他們真的有什麼無法向別人吐露的事情,就寧可忘記它們。他們不僅會避開任何可能損及自己在群體面前所表現出的樂觀和積極精神的東西,而且還會以信念和熱情展現自己的所思所欲,以及處理事情的方式。
(此篇論文Psychologische Typologie曾在一九三六年二月發表於《南德月刊》〔Süddeutsche Monatshefte〕)
在人類本質的絕對相似性和絕對差異性這兩極之間,人們還會插入幾個以規律性形式表達相似性和差異性的中間階段,也就是所謂的「類型」或—誠如人們從前所稱謂的—「性情」,這是人類學術研究史早期一個眾所周知的作法,也是人們好思考的理智所採取的行動。西元前五世紀的古希臘哲學家恩培多克勒(Empedokles, 495-430)曾以秩序原則處理自然事物的混亂。古希臘羅馬時期的醫生會把跟某些亦源於希臘自然哲學的屬性(諸如乾燥、溫暖、潮濕、寒冷)相連結的秩序原則—即風、火、水和土這四種元素—轉移到人類的本質上,並因此而試圖以有序的類別掌握人類本質紛亂的多種多樣。在這些醫生當中,主要是由古羅馬帝國時期的希臘裔醫學家蓋倫提出關於心理類型的學說,這套學說影響了歐洲對疾病和病人的學術研究長達一千八百年左右。此外,蓋倫所劃分的四種性情的舊稱還透露了本身的「體液病理學」(Humoralpathologie)的起源:憂鬱型的黑膽質(melancholisch)、冷靜型的黏液質(phlegmatisch)—希臘文的phlegma(黏液)是指燃燒和發炎,德文的Schleim(黏液)則被理解為發炎的結果—活潑型的多血質(sanguinisch),以及躁動型的黃膽質(cholerisch)。
我們現代對於「性情」的觀點當然遠比從前更富有心理學意涵,因為,「心靈」(Seele;或中譯為「靈魂」)這個概念經過兩千年的發展後,已大幅脫離了那種關於冷與熱、黏液與膽汁的觀念。現在的醫生甚至不認為,個體的性情—即某種心性狀態或易激動性(Erregbarkeit)—跟他本身的血液和體液的性質有何瓜葛,不過,他們的專業以及以身體疾病的視角所進行的醫療處理,卻會經常誘惑他們成為心理學的門外漢,而且還把心靈視為腺體生理學(Drüsen-Physiologie) 的一種具依賴性的、敏感的終端器官(Endorgan)。當然,現在的醫生所說的「體液」已不再是古希臘羅馬時期的醫生所謂的「體液」,而是仍令人難以捉摸的、能廣泛影響「心性」—作為性情方面的反應以及情緒性反應的化身—的賀爾蒙。整體的體質,也就是最廣義的體質,實際上和心靈的性情密切相關,由於它們的關係極其緊密,以致於當醫生們也把心靈現象主要視為一種對於身體的依賴時,都不該因此而受到責怪。不論在什麼地方,心靈就是充滿生命力的身體,而充滿生命力的身體則是富含心靈的形骸;不論在什麼地方或採取什麼方式,我們都可以輕易地發覺心靈和身體的一體性,而且既應該從身體、也應該從心靈層面探索這種一體性。換句話說,這種一體性在研究者看來,應該既依託於身體,也依託於心靈。唯物主義的觀點賦予了身體優先權,而讓心靈屈居於次等現象和伴隨現象的地位,而且還把它當作所謂的「附帶現象」(Epiphänomen),而不再給予實質性。心靈現象取決於生理作用的這個看法本身,雖是一個不錯的研究假設,但在唯物主義裡,它卻變成了一種哲學的侵犯。所有關於生命體的、嚴肅的學術研究都會拒絕這種侵犯,因為,學術研究一方面總是在面對有生命的軀殼包含著一個未解的奧祕這個事實,但另一方面卻也無法否認這個事實的客觀性:身體現象和心靈現象之間存在著我們完全無法調解的對立,而且心靈現象的奧祕並不亞於身體現象的奧祕。
當人們對於心靈的看法—較之古希臘羅馬時期的觀點—已往自主化和抽象化發展數百年之後,唯物主義的侵犯才在近代具有可能性。然而,在古希臘羅馬時期,人們仍然把身體和心靈(靈魂)當作無法分離的統一體而一起看待,因為,他們還是未接受基督教的異教徒,所以,比較接近原始的史前時代。在史前時代裡,人格還未受到道德的撕裂,人們還可以在童稚的純潔以及沒有責任感的狀態裡,體驗本身作為完整的、無法被切割的整體。根據現存的莎草紙文獻的描述,古埃及人在死後向陰府判官認罪時,還顯得相當天真單純,他們會表示:「我不曾讓別人挨餓,不曾使別人哭泣,也不曾殺害別人⋯⋯」,如是等等。古希臘荷馬史詩裡的英雄,在充滿合情合理的神性和人性的自然世界裡流淚涕泣、放聲大笑、發狂咆哮、以智取勝並殺害他人。至於那些住在奧林匹斯山的古希臘眾神的家族,則在非常沒有責任感的狀態裡玩得很開心。在這個哲學尚未出現的早期階段裡,人們過生活,也體驗生活,而且還受到本身的心性狀態的影響。只有激發心性的、讓心臟砰砰直跳的、讓呼吸急促或窘迫的、讓內臟受到干擾的東西,才會被當時的人們視為「與靈魂有關的東西」。因此,他們會優先把靈魂確定在橫膈膜—phrenes(橫膈膜)這個希臘字就相當於德語的Gemüt(心性)—和心臟的部位上。後來,一些哲學家才開始把理性定位在頭腦裡。非洲有些民族基本上認為,自身的「想法」就存在於肚腹裡;美國西南印地安人的培布羅族(Pueblo-Indianer)則認為,人們是在心裡「思考」(「因為,只有瘋狂的人才在頭腦裡思考」)。在這個發展階段裡,意識就是身體和心靈的統一體的體驗以及所受到的影響。不過,當既開朗又悲慘的培布羅族開始思考時,便構想出一種分裂—哲學家尼采則認為,古波斯的祆教先知查拉圖斯特拉應該為這種分裂負責—也就是產生了一些二元對立的觀念,諸如單數和雙數、上和下、好和壞的區分。
這些二元對立的觀念也是早期畢達哥拉斯學派的產物;該學派的學說強調人們的道德責任以及罪惡在形而上方面所造成的嚴重後果,而且這些主張還透過他們所推行的那些玄妙的祕密宗教儀式,而在數百年後普遍盛行於民間,並且廣泛地遍布各個社會階層。柏拉圖早就以白馬和黑馬的比喻說明人類心靈的矛盾和困境,不過,在更早之前,畢達哥拉斯學派的祕密宗教儀式便已在宣揚陰界對死人在世行徑的褒善懲惡的那套理論。這種祕密儀式絕對無關於身處「幕後隱蔽世界的」哲學家那種鑽牛角尖的心理,或位於隱僻之處的神祕主義。早在西元前六世紀便已存在於大希臘(Magna Graecia)的畢達哥拉斯主義,其實有些類似城邦的宗教信仰。後來,畢達哥拉斯主義的思想和祕密宗教儀式不僅沒有因為大希臘的沒落而完全消失,反而還在西元前二世紀經歷了本身的哲學思想的復興,而且當時還對亞歷山卓城—北非人文薈萃的港都—的知識界發揮了相當強烈的影響。畢達哥拉斯主義和猶太先知的預言在相互碰撞後所形成的產物,還可以被視為基督教—作為一種世界性宗教—的濫觴。從古希臘文化融合另一種信仰的綜攝現象(Synkretismus)裡,產生了一種對於人的分類,這種類型化完全不同於當時的醫生所遵奉的體液心理學(Humoralpsychologie),而是一些介於古希臘哲學家巴門尼德(Parmenides, ca.515-ca.450 B.C.)所指出的光明與黑暗、上與下這兩端的中間階段。這套分類把人區分為三種,即肉身的個體、靈魂的個體和心理的個體。這種劃分已不再是自然科學對於相似性和差異性的表述,而是一種批判的價值系統。這種價值系統並非依據自然的顯現方式,而是依據倫理、哲學和神祕主義性質的確定性。雖然,這不完全是「基督教式」的見解,但卻屬於使徒保羅傳道時期的早期基督教的觀點。這種觀點的存在已證明了只會體驗、且被情緒所擄獲的人們原本的一體性的分裂,因此,不該被低估。
在此之前,人們只是具有生命的存在者、被經驗者,以及未能深思地分析本身的過去和未來的經驗者,但後來卻突然具有某種能力,而被迫面對三種決定命運的、且負有道德責任的因素,也就是身體、靈魂和心理這三大因素。人們在出生時,大概就已經確定,本身是否以肉身、靈魂或未決定要偏向哪一方的中間狀態存在著。古希臘精神所具有的分裂已更形劇烈,而且還意味深長地強調靈魂和心理,靈魂和心理便因此而無可避免地脫離了自然的肉體,而獲得了自主性。因此,一切最高的終極目標便存在於道德的確定性以及心理的、超世俗的(überweltlich)最終狀態裡,心理跟肉身的分離便擴大為個體的心理和世俗世界的對立。畢達哥拉斯主義的二元對立原本所具有的那種寬容的智慧便轉變成強烈的道德衝突,挑起警覺性和意識性,就跟挑起自己與本身的衝突一樣,是再恰當不過的作法了!為了使所有的人類從原本不負責任的、天真無邪的精神狀態裡—也就是從半睡半醒的狀態裡—徹底清醒過來,並使他們轉入一種刻意地自我負責的狀態,人們已完全無法再想到其他更有效的方法。人們把以上的過程稱為文化發展,這無論如何都關乎區辨力和判斷力的發展,當然也關乎意識的發展。在智識能力的意義上,認識和批判的增加已為往後人類心理的發展創造了基礎。這種在各方面都已明確超越古希臘羅馬人民的能力表現的心理產物,就是學術研究。雖然,此時人已和自然區別開來,但卻得以因此而再度被適當地納入與自然的相互關係裡,因此,學術研究便消除了人與自然的隔閡。假如人們無法藉由傳統的宗教信仰而保住本身在形而上方面的特殊地位,大家所熟悉的「信仰和知識」的對立就會因此而產生,而人們原有的特殊地位也會隨之落空。無論如何,自然科學都意味著可以為肉體存在進行辯解的一個了不起的理由,在這個意義上,唯物主義甚至是一種具有歷史公正性的表達。人類的心靈本身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經驗領域。長久以來,它一直都屬於形上學範疇,不過,從十七、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時期開始,以學術研究的方法闡明心靈本質的嚴肅性嘗試便有增添的趨勢。人們當時以摸索的方式從感官感知著手,而後才逐漸敢於探入聯想的領域,聯想這個研究方向最後便發展成以馮特的「生理心理學」為頂峰的實驗心理學。在法國,許多醫生很快地認同了比較偏重描述的心理學,而這也是法國心理學所特有的發展。此外,法國心理學的奠基者特奧督.李波特(Théodule-Armand Ribot, 1839-1916)、心理學家暨哲學家皮耶.賈內,以及史學家伊波利特.泰因(Hippolyte Taine, 1828-1893)都在這方面貢獻卓著,而這些學術性嘗試的特徵就是心靈已消失在個別的心理機制或心理作用裡。除了這些努力之外,還零星出現了一些現今可能被人們稱為「全面式的研究方法」(Ganzheitsbetrachtung)的研究。這樣看來,似乎這個研究方向源自於傳記學,尤其是源自於從前有一段頗為美好的時期所出現的一些經常被稱為「喜於探知的」生涯敘說的作品。在這個脈絡裡,我想到了十九世紀德國醫生作家尤斯迪努斯.柯爾納(Justinus Kerner, 1786-1862)以及他撰寫的那部著名傳記《普雷佛斯特的女先知》(Die Seherin von Prevorst)、十九世紀德國知名的新教牧師約翰.布倫哈特(Johann Christoph Blumhardt,1805-1880)和他那份關於自己如何以基督教的信仰治癒女教友果特莉繽.狄圖絲(Gottliebin Dittus)的報導。此外,為了正確地看待歷史,我在這裡也不該忽略歐洲中世紀天主教會所編寫的那部《聖徒與殉道者言行錄集》(Acta Sanctorum)。一些當代的專家學者為了達到學術研究的目標,也會採用這條路線,例如維也納精神分析學家佛洛伊德、美國哲學家暨心理學家詹姆斯和日內瓦大學心理學教授弗洛諾依。詹姆斯和他的好友弗洛諾依曾試圖描述所有的心靈現象,並從整體來判斷心靈現象。佛洛伊德這位在維也納執業的精神科醫師也從個體人格的整體性與不可分割性出發,但卻局限於那個時代所主張的(驅力的)機制和個別心理作用的。此外,佛洛伊德還把人類圖像窄化成具有顯著「市民性的」、集體性的個人(Kollektivperson),而且還以片面的世界觀來進行意義的解釋。此外,令人感到可惜的是,這位精神分析學家後來屈服於醫學的誘惑,而以體液心理學的方式把心靈現象歸因於身體層面。他個人雖然感受到心靈的神聖不可侵犯性,而顯得有些膽怯,但卻也對長久以來屬於形上學領域的心靈採取了反抗的姿態。
相較於源自古希臘羅馬時期的那些關於體質的思想,佛洛伊德起初的心理學研究雖然是正確的,但後來在理論上卻想把一切再度歸因於被身體所制約的驅力,而讓自己也受制於從前的體質思想,至於我本人則是從心靈本身所固有的規律性這個看法出發。心靈和身體不論在任何地方都是無法切分的統一體,但它們在各自的本質上卻明顯地不同,以致於我們只能認為,心靈就跟身體一樣,都具有各自的本質性。只要我們無法了解心靈和身體的一體性,我們就只能分別地探討身體和心靈,而且首先似乎只能把這兩者當作互不依賴的獨立體—至少在它們的結構上—來處理。不過,我們卻日復一日地看到,身體和心靈之間並不是這種關係。因此,我們如果不想改變這種看法,就無法釐清任何關乎於心靈的東西。
我們就是認為,心靈具有本身所固有的規律性,因此,我們可以讓自己—暫時地—甩開把心靈的一切歸因於某些身體因素這個無法解決問題的任務,而把心靈的表現方式當作其自身本質的表達,並試著確定其中的規律性或類型。我所提出的心理類型學涉及了心靈結構要素的說明,但它卻不是在描述某種體質類型(Konstitutionstypus)的心靈作用,德國當代精神病理學家克雷奇默對於體格和性格的對應關係的研究,便屬於這條研究路線。我已在拙作《心理類型》裡,詳盡地呈現我個人對於純粹的心理類型化的嘗試。我在撰寫這本著作時,已行醫二十年,而且還因為診療的工作而有機會認識來自各個階層以及五湖四海的人們,而這些經驗就是我從事研究的基礎。年輕的醫生剛開始行醫時,總還想著臨床的病象和診斷,但隨著經驗的增加,就會逐漸獲得一些完全不同的印象,即人類個體驚人的多樣性,以及個案所顯示的大量而混亂的變異。個案特殊的性格和特殊的生活情況會導致病象的出現,如果人們對此還有興趣加以觀察,就會發現,這些病象或多或少會被強制套上某種臨床的診斷。所謂的臨床病象其實更是某些性格所偽裝的、或刻意表現的外顯,相較於這個事實所帶給我們的強烈印象,人們用哪個名稱來指謂這種失調的狀況,就顯得無關緊要了。
由於所謂的「情結」純粹是個體的某種性格傾向所造成的結果,因此,這些情結—作為精神官能症的「核心要素」—也是無足輕重的。這種情況最容易顯現在心理病患與原生家庭的關係裡。舉例來說,某個病患有四個兄弟姊妹,他在排行上既不是老大也不是老么,而且跟其他的手足一樣,接受相同的教育並擁有相同的生活條件,但是,其他的兄弟姊妹都健康無虞,而只有他生病。對他的個人狀況的檢查則顯示,他的兄弟姐妹也承受、甚至還忍受一連串相同的影響,但只有他因此而發病,至少看起來是這樣。實際上,這些影響並不是他生病的真正原因,而是後來出現的一些表面的、不實在的解釋。其實精神官能症真正的起因在於患者本身所固有的方式,比方說,患者接受和處理外在影響的方式。在比較過許多個案之後,我逐漸明白,顯然一定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普遍態度存在著,因此,由較為高度分化的個人所組成的全體人類,也可以被區分為兩種類別。不過,實際的情況顯然不是這樣,所以,我們只能說:如果我們觀察的對象是較為高度分化的個人,就可以清楚地觀察到這兩種普遍態度的差別,換句話說,這兩種態度的不同必須超過一定的分化程度,才能被觀察到,並有其實際的意義。上述的患者通常不屬於一般常見的類型,因此,無法在與生俱來的本能的基礎裡找到足夠的確定性。這種本能的不確定性是個體發展片面性態度的重要理由之一,個體的片面性態度與習慣有關,但最終卻是由遺傳所決定並促成的。
我把這兩種不同的基本態度稱為「內傾」和「外傾」。外傾的特徵就是對外在客體的關注,對外在事情的發展過程和要求抱持開明和熱忱的態度,因此,外傾者不僅影響它們,也讓自己接受它們的影響。他們對本身處於這種外傾狀態以及和他人的共同參與懷有樂趣和需求,而且能夠忍受忙碌和喧嚷,甚至本身還樂在其中。此外,他們也會持續關注本身與周遭的人的關係,並維持自己和朋友及熟人之間的情誼,但卻不會吹毛求疵地挑剔自己所結交的人。他們相當重視如何影響以及是否影響自己的周遭世界,因此,非常樂於讓自己在公開的場合有所表現。與此相應的是,他們通常會儘可能把集體性賦予本身的世界觀及倫理道德,並格外強調利他主義,至於他們的良知則高度取決於周遭人們的意見。當別人「知道什麼」時,他們主要的道德考量才會展開,而且他們的宗教信念在某種程度上也受制於多數人的決定。
只要有一丁點兒可能,外傾者本身的主體就會處於隱晦之中。外傾者會以無意識遮掩主體,而讓自己無法察覺到它的存在,而且他們特別厭惡對本身的動機進行批判性檢驗。他們的祕密往往藏不了多久,就會跟別人分享。不過,如果他們真的有什麼無法向別人吐露的事情,就寧可忘記它們。他們不僅會避開任何可能損及自己在群體面前所表現出的樂觀和積極精神的東西,而且還會以信念和熱情展現自己的所思所欲,以及處理事情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