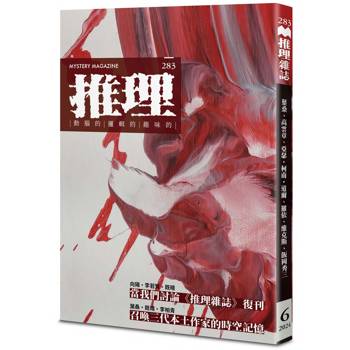召喚三代本土作家的時空記憶——小記《推理》雜誌的創作年代
洪敍銘:時隔 16年,《推理》雜誌即將復刊,「經典回歸」所召喚的不僅是世代讀者的記憶,透過這個載體,也能讓讀者們再次認識台灣犯罪推理小說的發展。其中,「創作」是《推理》雜誌的主體與重點,因此此次以以雜誌投稿時期的三位本土作家——「三代同堂」——的概念進行對談,既能呼應主軸,又相當別開生面。
三位作家在《推理》雜誌的首次刊登,分別是第42期的〈玻璃鞋〉(葉桑)、第128期的〈考前計劃〉(既晴)、第260期的〈赤雲迷情〉(李柏青),在合計282期的《推理》雜誌中橫跨了三個時代,各具代表性。由於時代不同,在第一次投稿並獲得刊登時,當下的環境背景都是截然不同的。此次對談亦能一窺三位作家在不同時代與《推理》雜誌的互動,也能藉此召喚回氛圍、替讀者們重述記憶。
首先,想先請作家們回憶第一次投稿的背景、想法,作為創作者與《推理》雜誌「互動初體驗」的過程,以及後續的感受與影響。
葉桑:我在與《推理》雜誌結緣之前,已經寫過很多小說、也出過書。當時我在想要靠寫作開闢財源的話,還需要更多能夠發表作品的舞台,偶然在圖書館裡閱讀到《推理》雜誌後,便打算自己來投投看。
第一次投稿獲得成功刊登的是1988年的〈玻璃鞋〉,故事文青、唯美的風格,收到了鄭秀媛編輯的肯定。她很喜歡且希望我多多投稿,開啟了我後續固定投稿《推理》雜誌的寫作生涯。由於《推理》雜誌收稿不限字數,稿費也給得相對優渥,給予我不少成為專職作家的信心。現在回想,非常感謝那個文學蓬勃發展的時代,讓我能夠一直寫小說與出版成冊,到現在累積了許多作品。
在我那個年代,投稿管道以報章雜誌為主,除非跟編輯有特別的交情,不然很難找到長篇連載的篇幅,也造就當時推理創作以「短篇」為主的風氣。
我的創作觀受兩本書影響很大:松本清張的《砂之器》、森村誠一的《人性的證明》,閱讀後深受感動。那時也讀了一系列好時年出版社的作品,後來又看了連城三紀彥的小說,發現原來犯罪推理小說也可以寫得這麼唯美,所以決定走這條路線。
由於《推理》雜誌上有很多名偵探的系列作品,也讓我設定了「葉威廉」這個系列在雜誌上連載。葉威廉是我心目中理想的人物形象,警察陳皓則來自我朋友的部分特質。寫系列角色的方便之處,就是可以不用一直架設新的人物,在故事中也可以延續到先前的發展。《推理》雜誌的存在孕育了葉威廉這位罕見的長、短篇作品兼具的台灣名偵探。
既晴:我是在國中時發現《推理》雜誌的,當時本來在書店買參考書。《推理》雜誌的封面都是找知名畫家來畫,在書局內擺飾相當吸睛。林佛兒用心地為《推理》雜誌包裝出藝術感,不希望讓其感覺廉價,這種有意識打造出的質感刊物,吸引了學生時期的我。而我翻閱雜誌時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有台灣人的創作」,它告訴了我們推理小說不是只有外國人才能寫。
《推理》雜誌的內容很豐富,除了小說故事也有很多專欄,景翔的錄影帶專欄就非常棒,那時適逢錄影帶出租娛樂爆發的時代,我國中時開始收看兩小時的火曜劇場(週二懸疑劇場),帶給我課業之外很重要的私人空間。
大學時期網際網路開始興起,我在網路上發現討論推理小說的論壇,影響我持續關注這一塊領域,後來也藉由經營BBS討論區,建立犯罪推理小說的發展系譜。
我第一次投稿《推理》雜誌是在大二,使用了國中課業壓力很重的回憶來寫。假如我是第二名,那把第一名的殺掉就變成第一名了。也可能對應到了當時的時代背景,這篇〈考前計劃〉對於社會意識的探討、對升學主義的批判也時常成為評論的焦點。
當時,刊登作品後主編會寄信給我,彙整讀者的意見給我。無論是批評或肯定,都會讓我感覺到被關心,產生寫作動力。《推理》雜誌提供了創作者與讀者的互動園地,作家可以依循讀者的回應來調整自己創作的方向,這個練習對於我後來成為作家的養成是很有幫助的。
洪敍銘:既晴身處的是大小文學獎最為興盛的時代,當時的背景讓你留下了什麼樣的記憶呢?對於李柏青來說,網路與資訊的世代來臨,又對你的創作有了什麼實質的改變或影響?
既晴:那個時候沒有大眾文學獎,可能是我自己在「台灣推理俱樂部~恐怖の人狼城」網站,決定與朋友合資舉辦「人狼城推理文學獎」的原因。我認為葉桑老師的時代作家們正在摸索「什麼是推理小說」,而我那時是一個正在摸索「什麼是台灣推理小說」的時代,所以來自純文學的嘗試是很常見的。
當時沒有短篇小說連載或者文學獎的目標,我們推理創作者追求的就是長篇單行本。我站在短篇移轉到長篇創作的轉折點上,皇冠大眾小說獎得獎的《請把門鎖好》被批評不是推理小說,正是大家那時在討論的「類型的邊界」。現在台灣對於犯罪推理類型的認知,也逐漸與國外的認知有了一致性。
李柏青:我是在國、高中時開始看推理小說,我媽媽收藏很多書,書櫃裡就有《推理》雜誌。而我是在2003年,大四那時開始認真追《推理》雜誌,時常在圖書館唸完書時去閱讀。
晚期《推理》雜誌所收錄的本土作品數量不多,且「612大限」的版權問題影響,歐美作品因版權問題無法被翻譯,也就只剩下了日本作品,所刊露的台灣作家也剩下魯子青、胡柏源。我利用大學上課時間默默地在寫小說,本來只發表在自己的BBS上,後來也嘗試投稿《推理》雜誌,第一篇被刊登出來的時間在2006年當完兵的時候,受到鼓勵的我就將舊作整理好一次投稿過去,並在接下來幾期陸續刊出。最後一次刊登的〈淡水河浮屍〉是在第273期,而不久後的282期就停刊了。
我所認識的《推理》雜誌與前兩位真的不太一樣,沒有稿費,追求的就是文字被刊登在雜誌上的感覺,已經是個不為錢而寫作的時代了吧。我也沒有收過主編寄來的讀者回饋或信件,回饋都是從網路上看到的。
《推理》雜誌對我母親那一輩的文青來說是個很重要的存在,幾乎人人都知道,這在現代是難以想像的,阿姨們會對我說:「你的小說被刊登出來很厲害!」
洪敍銘:關於文本中的世代對話,三位如何從不同世代的作品中,看見台灣社會環境的演進與改變?以及對另外兩位作者作品的評價,他們的影響性。
既晴:我可以說是看著葉桑作品長大、也看著柏青成長的「三明治世代」。在那時葉桑是創作量最龐大的前輩,除了刊登篇數外,出版單行本紀錄也是最多的。早期會創造出名偵探的台灣作家不多,余心樂與葉桑就是早期的代表人物。而且葉桑還在葉威廉之外,也創造了好幾位各具風格的偵探,創作面相既多且廣。除了本格,也發展出犯罪、懸疑、異色等實驗性手法,即便在那個時代大家還對「推理」的理解有限,葉桑仍舊做出很多創新,讓我們發現推理小說可以這樣寫,這是他對我最大的影響,也讓我在創作時會嘗試實驗,不僅止於本格。
在實驗時,有時候我也會擔心自己會不會距離讀者太遠,但是柏青在新人時就沒有包袱,他不是用類型限制創作,而是秉持自由,在類型的規則上做出更多花樣。我們三個都是在犯罪推理領域內嘗試各種實驗性作品的人,共同點便是沒有很特定的流派標籤。柏青的作品讓我看到未來的可能性,我們會被類型的定義拘束,而他展現出多元的可能。
李柏青:我是在2000年後開始讀本土的作品,讀最多的就是既晴和藍霄。我也參考了魯子青這位作家,他啟發我台灣推理可以這樣子來寫。在那個《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熱潮、本格極度流行的時代,可以去嘗試比較不一樣的,更鄉土與接地氣的寫作路線。
在投稿「人狼城推理文學獎」落選後,既晴曾經打電話給我長聊,建議我去讀卜洛克的「馬修.史卡德系列」,這算是改變我人生的一套書。我一向沒有特地為自己的寫作設定什麼目標,沒有刻意說想要開創什麼東西,人家說什麼好看我就去讀、有空我就來寫,感謝既晴給我的評價。
葉桑:我最喜歡兩位作家的作品分別是《修羅火》和《康堤紐斯大飯店》。台灣推理推廣部的版主楓雨也有說過他最喜歡《修羅火》。我覺得這部作品的影像畫面非常精彩,我自己的用字遣詞不那麼適合影視化,後來新寫的馬張系列就有受到這種影響,當然一個作家不能輕易被人影響,而是從作品中抓精髓去參考,例如畫面感的描述法。現在的葉威廉系列會保留我過去的特色,但新寫的系列就會嘗試把這些給我的影響放進去。另外柏青的《婚前一年》讓我感受到,推理小說可以寫得這麼日常真是不簡單,我之後也會想要參考這種型態。
洪敍銘:請三位以創作者的觀點為核心,分享您對於《推理》雜誌復刊後的期待。
葉桑:我的期待會是可以全部都放本土作家的作品,我身為本土作家,很在乎年輕作家有沒有發表的園地。不論寫得好不好,大家都是從不好開始寫的。
李柏青:停刊時我曾經在部落格上寫了一篇文章給林佛兒先生的遺孀李若鶯老師,她甚至有問我要不要來接手《推理》雜誌,但我那時候要當兵了,手上也沒錢。
雜誌要賺錢才能生存,我認為要把內容範圍放大一點,不要限縮在推理「小說」上,現在的推理文本包含各種電視、動畫、遊戲、密室逃脫等等,盡量廣泛地納入這些領域,提供智性挑戰愛好者一個資訊平台。
另外,除了刊登小說之外也要有評論,「暴雷」的評論。可以更吸引看過作品的讀者來閱讀雜誌文章,沒暴雷的評論會像是隔靴搔癢。
既晴:我對以前《推理》雜誌有句話印象深刻,林佛兒先生對《推理》雜誌的期望是,雜誌的內容要有超過一半的作品是來自台灣本土作者,可惜到停刊時還沒有成功。雜誌應該要表現犯罪推理這個文類的全貌,要讓讀者們看到大長篇以外的選擇、看到來自世界各地的作品風格。讓《推理》雜誌從復健開始,慢慢地邁向這個目標。
洪敍銘:時隔 16年,《推理》雜誌即將復刊,「經典回歸」所召喚的不僅是世代讀者的記憶,透過這個載體,也能讓讀者們再次認識台灣犯罪推理小說的發展。其中,「創作」是《推理》雜誌的主體與重點,因此此次以以雜誌投稿時期的三位本土作家——「三代同堂」——的概念進行對談,既能呼應主軸,又相當別開生面。
三位作家在《推理》雜誌的首次刊登,分別是第42期的〈玻璃鞋〉(葉桑)、第128期的〈考前計劃〉(既晴)、第260期的〈赤雲迷情〉(李柏青),在合計282期的《推理》雜誌中橫跨了三個時代,各具代表性。由於時代不同,在第一次投稿並獲得刊登時,當下的環境背景都是截然不同的。此次對談亦能一窺三位作家在不同時代與《推理》雜誌的互動,也能藉此召喚回氛圍、替讀者們重述記憶。
首先,想先請作家們回憶第一次投稿的背景、想法,作為創作者與《推理》雜誌「互動初體驗」的過程,以及後續的感受與影響。
葉桑:我在與《推理》雜誌結緣之前,已經寫過很多小說、也出過書。當時我在想要靠寫作開闢財源的話,還需要更多能夠發表作品的舞台,偶然在圖書館裡閱讀到《推理》雜誌後,便打算自己來投投看。
第一次投稿獲得成功刊登的是1988年的〈玻璃鞋〉,故事文青、唯美的風格,收到了鄭秀媛編輯的肯定。她很喜歡且希望我多多投稿,開啟了我後續固定投稿《推理》雜誌的寫作生涯。由於《推理》雜誌收稿不限字數,稿費也給得相對優渥,給予我不少成為專職作家的信心。現在回想,非常感謝那個文學蓬勃發展的時代,讓我能夠一直寫小說與出版成冊,到現在累積了許多作品。
在我那個年代,投稿管道以報章雜誌為主,除非跟編輯有特別的交情,不然很難找到長篇連載的篇幅,也造就當時推理創作以「短篇」為主的風氣。
我的創作觀受兩本書影響很大:松本清張的《砂之器》、森村誠一的《人性的證明》,閱讀後深受感動。那時也讀了一系列好時年出版社的作品,後來又看了連城三紀彥的小說,發現原來犯罪推理小說也可以寫得這麼唯美,所以決定走這條路線。
由於《推理》雜誌上有很多名偵探的系列作品,也讓我設定了「葉威廉」這個系列在雜誌上連載。葉威廉是我心目中理想的人物形象,警察陳皓則來自我朋友的部分特質。寫系列角色的方便之處,就是可以不用一直架設新的人物,在故事中也可以延續到先前的發展。《推理》雜誌的存在孕育了葉威廉這位罕見的長、短篇作品兼具的台灣名偵探。
既晴:我是在國中時發現《推理》雜誌的,當時本來在書店買參考書。《推理》雜誌的封面都是找知名畫家來畫,在書局內擺飾相當吸睛。林佛兒用心地為《推理》雜誌包裝出藝術感,不希望讓其感覺廉價,這種有意識打造出的質感刊物,吸引了學生時期的我。而我翻閱雜誌時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有台灣人的創作」,它告訴了我們推理小說不是只有外國人才能寫。
《推理》雜誌的內容很豐富,除了小說故事也有很多專欄,景翔的錄影帶專欄就非常棒,那時適逢錄影帶出租娛樂爆發的時代,我國中時開始收看兩小時的火曜劇場(週二懸疑劇場),帶給我課業之外很重要的私人空間。
大學時期網際網路開始興起,我在網路上發現討論推理小說的論壇,影響我持續關注這一塊領域,後來也藉由經營BBS討論區,建立犯罪推理小說的發展系譜。
我第一次投稿《推理》雜誌是在大二,使用了國中課業壓力很重的回憶來寫。假如我是第二名,那把第一名的殺掉就變成第一名了。也可能對應到了當時的時代背景,這篇〈考前計劃〉對於社會意識的探討、對升學主義的批判也時常成為評論的焦點。
當時,刊登作品後主編會寄信給我,彙整讀者的意見給我。無論是批評或肯定,都會讓我感覺到被關心,產生寫作動力。《推理》雜誌提供了創作者與讀者的互動園地,作家可以依循讀者的回應來調整自己創作的方向,這個練習對於我後來成為作家的養成是很有幫助的。
洪敍銘:既晴身處的是大小文學獎最為興盛的時代,當時的背景讓你留下了什麼樣的記憶呢?對於李柏青來說,網路與資訊的世代來臨,又對你的創作有了什麼實質的改變或影響?
既晴:那個時候沒有大眾文學獎,可能是我自己在「台灣推理俱樂部~恐怖の人狼城」網站,決定與朋友合資舉辦「人狼城推理文學獎」的原因。我認為葉桑老師的時代作家們正在摸索「什麼是推理小說」,而我那時是一個正在摸索「什麼是台灣推理小說」的時代,所以來自純文學的嘗試是很常見的。
當時沒有短篇小說連載或者文學獎的目標,我們推理創作者追求的就是長篇單行本。我站在短篇移轉到長篇創作的轉折點上,皇冠大眾小說獎得獎的《請把門鎖好》被批評不是推理小說,正是大家那時在討論的「類型的邊界」。現在台灣對於犯罪推理類型的認知,也逐漸與國外的認知有了一致性。
李柏青:我是在國、高中時開始看推理小說,我媽媽收藏很多書,書櫃裡就有《推理》雜誌。而我是在2003年,大四那時開始認真追《推理》雜誌,時常在圖書館唸完書時去閱讀。
晚期《推理》雜誌所收錄的本土作品數量不多,且「612大限」的版權問題影響,歐美作品因版權問題無法被翻譯,也就只剩下了日本作品,所刊露的台灣作家也剩下魯子青、胡柏源。我利用大學上課時間默默地在寫小說,本來只發表在自己的BBS上,後來也嘗試投稿《推理》雜誌,第一篇被刊登出來的時間在2006年當完兵的時候,受到鼓勵的我就將舊作整理好一次投稿過去,並在接下來幾期陸續刊出。最後一次刊登的〈淡水河浮屍〉是在第273期,而不久後的282期就停刊了。
我所認識的《推理》雜誌與前兩位真的不太一樣,沒有稿費,追求的就是文字被刊登在雜誌上的感覺,已經是個不為錢而寫作的時代了吧。我也沒有收過主編寄來的讀者回饋或信件,回饋都是從網路上看到的。
《推理》雜誌對我母親那一輩的文青來說是個很重要的存在,幾乎人人都知道,這在現代是難以想像的,阿姨們會對我說:「你的小說被刊登出來很厲害!」
洪敍銘:關於文本中的世代對話,三位如何從不同世代的作品中,看見台灣社會環境的演進與改變?以及對另外兩位作者作品的評價,他們的影響性。
既晴:我可以說是看著葉桑作品長大、也看著柏青成長的「三明治世代」。在那時葉桑是創作量最龐大的前輩,除了刊登篇數外,出版單行本紀錄也是最多的。早期會創造出名偵探的台灣作家不多,余心樂與葉桑就是早期的代表人物。而且葉桑還在葉威廉之外,也創造了好幾位各具風格的偵探,創作面相既多且廣。除了本格,也發展出犯罪、懸疑、異色等實驗性手法,即便在那個時代大家還對「推理」的理解有限,葉桑仍舊做出很多創新,讓我們發現推理小說可以這樣寫,這是他對我最大的影響,也讓我在創作時會嘗試實驗,不僅止於本格。
在實驗時,有時候我也會擔心自己會不會距離讀者太遠,但是柏青在新人時就沒有包袱,他不是用類型限制創作,而是秉持自由,在類型的規則上做出更多花樣。我們三個都是在犯罪推理領域內嘗試各種實驗性作品的人,共同點便是沒有很特定的流派標籤。柏青的作品讓我看到未來的可能性,我們會被類型的定義拘束,而他展現出多元的可能。
李柏青:我是在2000年後開始讀本土的作品,讀最多的就是既晴和藍霄。我也參考了魯子青這位作家,他啟發我台灣推理可以這樣子來寫。在那個《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熱潮、本格極度流行的時代,可以去嘗試比較不一樣的,更鄉土與接地氣的寫作路線。
在投稿「人狼城推理文學獎」落選後,既晴曾經打電話給我長聊,建議我去讀卜洛克的「馬修.史卡德系列」,這算是改變我人生的一套書。我一向沒有特地為自己的寫作設定什麼目標,沒有刻意說想要開創什麼東西,人家說什麼好看我就去讀、有空我就來寫,感謝既晴給我的評價。
葉桑:我最喜歡兩位作家的作品分別是《修羅火》和《康堤紐斯大飯店》。台灣推理推廣部的版主楓雨也有說過他最喜歡《修羅火》。我覺得這部作品的影像畫面非常精彩,我自己的用字遣詞不那麼適合影視化,後來新寫的馬張系列就有受到這種影響,當然一個作家不能輕易被人影響,而是從作品中抓精髓去參考,例如畫面感的描述法。現在的葉威廉系列會保留我過去的特色,但新寫的系列就會嘗試把這些給我的影響放進去。另外柏青的《婚前一年》讓我感受到,推理小說可以寫得這麼日常真是不簡單,我之後也會想要參考這種型態。
洪敍銘:請三位以創作者的觀點為核心,分享您對於《推理》雜誌復刊後的期待。
葉桑:我的期待會是可以全部都放本土作家的作品,我身為本土作家,很在乎年輕作家有沒有發表的園地。不論寫得好不好,大家都是從不好開始寫的。
李柏青:停刊時我曾經在部落格上寫了一篇文章給林佛兒先生的遺孀李若鶯老師,她甚至有問我要不要來接手《推理》雜誌,但我那時候要當兵了,手上也沒錢。
雜誌要賺錢才能生存,我認為要把內容範圍放大一點,不要限縮在推理「小說」上,現在的推理文本包含各種電視、動畫、遊戲、密室逃脫等等,盡量廣泛地納入這些領域,提供智性挑戰愛好者一個資訊平台。
另外,除了刊登小說之外也要有評論,「暴雷」的評論。可以更吸引看過作品的讀者來閱讀雜誌文章,沒暴雷的評論會像是隔靴搔癢。
既晴:我對以前《推理》雜誌有句話印象深刻,林佛兒先生對《推理》雜誌的期望是,雜誌的內容要有超過一半的作品是來自台灣本土作者,可惜到停刊時還沒有成功。雜誌應該要表現犯罪推理這個文類的全貌,要讓讀者們看到大長篇以外的選擇、看到來自世界各地的作品風格。讓《推理》雜誌從復健開始,慢慢地邁向這個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