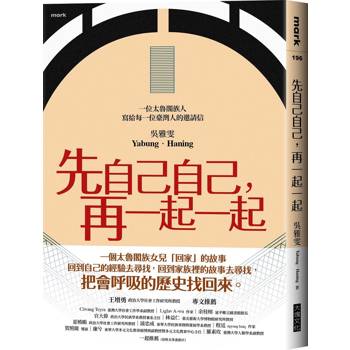第二章
我的成長與情緒
我是一九八七年在花蓮縣秀林鄉加灣部落出生,族名Yabung.Haning。太魯閣族是父子連名,Yabung 是我的名字,Haning 則是我爸的名字。
太魯閣族人叫人名時,總是會加上一些形象特徵或是故事方便記憶,簡單來說就是很愛幫人家取外號,我小時候總被隔壁部落的叔叔叫Yabung.Tuba,Tuba是太魯閣族語「魚藤」的意思,在溪裡抓魚時把藤汁搗出來放水裡,可以暫時麻痺附近的魚。聽說我出生時的加灣部落有個名字同樣也叫Yabung 的婦女試圖吃魚藤自殺而出名,所以隔壁部落的叔叔總是叫我加灣來的Yabung.Tuba。
我的阿公叫Jiru,大家都叫我阿公Jiru.Honda,因為他是我們部落第一個買下Honda(本田)摩托車的人。阿公阿嬤認真務農,以前家裡的客廳還有農會頒發的木製匾額,是阿公擔任農會代表時所贈。而聽說我出生時,阿公抱我沒有多久就去世了,爸爸總說那時候我剛出生,阿公第一次抱我,我叫了三聲阿公之後,他就因農藥中毒而死在田裡。
當時加灣部落主要經濟來源是種稻米,在沒有保護遮蔽的狀態下灑農藥,導致不少人因為農藥中毒或是肝臟方面的疾病而去世,我阿公Jiru就是肝病去世。
有關族人因肝病而去世這件事,不知道為什麼在我長大之後,總是被人說「原住民得肝病就是因為愛喝酒」的關係,而讓我一度以為會得肝病的原因只有喝酒,一直到我接觸長期照顧服務的工作才知道,原來會得肝病的原因有很多種,有喝酒、農藥及過勞等。
加灣部落的太魯閣族名叫Alang Qowgan, Qowgan 是一種大竹子的名字,祖先遷移至此看見許多這種竹子因此命名,而後來的加灣山相繼因為各種法律的規定,諸如獵人狩獵被抓、禁止游耕燒墾、禁伐補償的政策以及部落生活經濟的改變,導致缺乏族人上山整理而逐漸荒廢,竹林樹木被覆蓋著滿滿的小花蔓澤蘭。這種外來藤本植物會攀著植物往上爬,只要有陽光空隙它便會填滿,植物會因為缺乏光合作用而死亡,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就很少找到長者所說的Qowgan 這種竹子了。
鄰近我家後面的是一座陡直約六百五十公尺高的加灣山,我依稀記得小時候跟著阿嬤沿著景美國小旁邊的小路上山,在阿嬤刻意栽種的箭筍細竹間用繩子與帆布搭建的簡易工寮,並放置鍋碗瓢盆、寶特瓶水,阿嬤在那裡生火煮湯麵,我則會在放完火燒墾後的山坡,坐在紙箱上找地方滑下去,當然最後少不了被修理一頓。也記得小時候常常看到我們家後面的山頂上有人招手,或者將要製作竹筒飯的節慶日,往山的方向看去會有「竹子雨」──山上有人把竹子用投射的方式往下丟擲,聚集在某處,或者順著竹子的路往山下拖拉,那些往下移動的竹子就好像下雨一樣。
「部落很多規矩妳不知道!」
我的童年,常常聽到有人在部落的路上打架爭執,甚至刀光劍影、拿著電鋸在路上跑都不是奇怪的畫面。
只要半夜有人叫囂,部落的族人就會前去阻止、拉扯,就如同我爸和部落的叔叔在飲酒過後有些言論產生不愉快,就會扭打起來,甚至拿刀出來,好像很有默契地把手上的刀打在對方的刀上,鏗鏘產生火花,但不至於出人命,頂多扭到腳或是不小心劃到耳朵流血包紮,隔天腳一跛一跛地再到對方家道歉。我總不覺得在部落看到幾個男人打架是令人害怕的事情,某個部分還覺得有種湊熱鬧的興奮感,這是跟新聞上面播放的槍擊殺戮社會案件不一樣的情境。
在太魯閣族社群裡的衝突事件,有個潛規則,就是不太能叫警察,族人間可以打架,其他人會協助勸架阻止,但其中一方如果有人報警來處理,或是訴訟上法院,會被譴責說那樣做太超過了。我爸媽就指責過隔壁鄰居兄弟鬩牆鬧上警局,但他們譴責最多的不是打架行為本身,而是報警處理的這件事。
我又想起大學時期年輕氣盛做的蠢事。部落一個阿姨為人霸道,多數族人盡量不跟她有交集,我媽透過關係在部落買了一隻貴賓狗,那隻狗是那個阿姨的狗配種後的小孩。我媽養了一陣子很是喜愛,有一天那位阿姨就衝進我家直接把那隻狗給帶走說那是她的狗,我氣不過就跑去警察局準備要報案。
我媽得知後氣沖沖地衝去警察局當著大家的面把我給拖走,她嘴裡對我罵著:「部落很多規矩妳都不知道,妳以為妳讀書讀得高就可以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嗎?妳還早得很!部落的人是我每天都會見面的,妳這樣子一搞我要怎麼在部落裡生活?」
當時的我並不明白,為什麼部落的人寧願自己吃虧,也不要找警察處理。
彎彎曲曲的歷史殖民痕跡與我的小姆指
我就讀部落裡一間私立天主教安德幼稚園,那時候園長是一個外國人,園區的角落有個小教堂,幽幽靜靜,我們小孩總是說那裡有吸血鬼,不乖的話會被園長抓去裡面吃掉。
園內的孩子都是加灣部落的太魯閣族,因為私立的關係學費本來就很貴,但是安德幼稚園可以接受分期付款,或是同意以先欠費的方式照顧小孩,甚至付不出學費的家庭,園長也還是會收,依靠募款等方式來維持營運。我們家都有分期付款和欠費的情況,這是我後來才知道的事情。
即便是在太魯閣族部落裡的幼稚園,學生也都是太魯閣族,但園內並沒有讓我有任何學習太魯閣族文化、語言的印象,當然那時的年代忙著生存都來不及,更不可能談到族群文化,秉著慈愛與收容幫助我們偏鄉兒童的議題就很偉大了,所以我依稀記得幼稚園的畢業表演是跳著阿美族舞蹈和蚌殼精。
我是看著迪士尼和格林童話的卡通長大,小姑姑還送我《十萬個為什麼》的動畫卡帶給我,小姑姑很喜歡麥可.傑克森(Michael Jackson),她房間都是他的海報和音樂,當時部落甚至還有許多小朋友相繼模仿麥可.傑克森的月球漫步舞步。
每到星期日,就是要去加灣基督長老教會聽《聖經》故事,然後吃糖果,阿嬤通常給我二十元的奉獻金,我都會投十元給教會,剩下十元我會拿來買糖果。我最喜歡在星期日中午,部落十字路口中間,會有棉花糖阿伯,下午會有糖葫蘆阿伯,甚至有行動剪髮的阿伯在部落走動。那些阿伯們都是漢人,在固定的時間出現在部落固定的位置,持續至少有二十年以上,直到可能行動不便無法來為止。
每當到了夏天,我會和鄰居小朋友去景美國小的水圳游泳,摘水圳上母構樹的種子當糖果來吃,水圳是在臺美建交時期為了部落種植灌溉水稻時建設的。我們在半山腰有個祕密基地,我依稀記得是藤蔓圍繞著樹形成的天然樹洞,我們也不曾害怕會有蛇或是蟲之類的,自以為地把寶物藏在那裡。
部落正中間有個叫做「高山青」的廢棄酒店,它是我們部落孩子冒險的鬼屋,我們會在高山青前空地集合,拿著手電筒去闖,闖過了可怕幽暗的大廳,到二樓會看見破碎的玻璃落地窗,然後就是樓梯下樓直達酒店後的花園池塘。花園池畔上有一個一個小小的獨立小房子,很像蘑菇長在花園上。傍晚我跟鄰居的小朋友都在部落的馬路上賽跑。
部落的大人們都在忙,我們小孩每天在部落也忙著玩,但玩的時候切記不能讓自己受傷,或是遺失東西。比方今天手被割到了,自己很痛就算了,回去被大人發現受傷了,就是先一陣挨打;或是鞋子掉了一隻後,又是一陣挨打;被發現去了大人警告不能去的地方,比方溪河、水圳、海邊後,又會一陣挨打。
對這些處罰的因應方式就是,不要讓自己受傷,或是想辦法不被發現,我的右手小拇指彎彎的,因為小時候玩耍時折到,回家默默地藏起來不講,就是怕被打的關係,但也就這樣彎彎曲曲地長大了。
分離寄宿的國小生活
要上國小時,爸媽到雲林麥寮及桃園等地工作,我們跟著很多同樣是太魯閣族叔叔阿姨們一起同居生活。當時我一年級就讀桃園的國小,我的同學幾乎都是閩南人,我到同學家玩時第一次聽到他們家長說出「番仔」的稱呼,不懂這意思的我們還是玩在一起。
讀了半個學期,爸媽因為接工程常常要轉移陣地,不方便帶著我一起,於是我被送回花蓮給阿嬤照顧。我還記得當爸媽準備要騎車離去時,我手抱著我媽媽,然後阿嬤抓住我的腳,我騰空在半空中聲嘶竭力地哭喊著:「我不要!我要一起去!」
當然最後,我還是留在花蓮。但沒有多久,不太會中文的阿嬤因為不知道要怎麼教我,小學課本都是她看不懂的中文和注音,所以又把我交給隔壁佳民部落的大姑姑照顧,使我就讀佳民部落的國小。
佳民國小一個年級只有一班,每班大約只有十到十五位學生,我一進去期中考直接考第一名,因此被全班排擠過。全校學生都是太魯閣族,但任教的老師沒有一個是太魯閣族,印象中幾乎都是外省籍老師,因為我從來沒有聽過他們講過閩南語。
國小在學校除了學習中文、數學、自然等主科之外,老師還教我們打響板數來寶、做紙雕、念順口溜,以及唱童謠(童謠都是閩南語或是中文的歌謠)。
我常常會被推去比賽國語朗讀、演講、注音寫字與書法。老師為了要「糾正」我的口音,要求我每天上臺朗讀《國語日報》,教我拿著筆、順著注音的四聲畫在空中調整我的抑揚頓挫,所以我的中文咬字很標準,這也導致我在後來接觸自己的文化時,有一段時間總被誤認為「不在部落長大的孩子」。
由於我臺風很穩,便被加灣部落提倡母語推廣的田老師相中,要我去比賽母語演講。大約是在我三、四年級時,常常要到田老師家受訓,她先教我如何認羅馬拼音,再教我咬字發音,然後要我用中文寫一篇〈我的家〉,她翻譯成母語,再要求我背下來。我就以這篇〈Alang mu〉(我的家)拿下了全國第一名的母語演講冠軍,成為家喻戶曉的全國太魯閣族語冠軍的Yabung。
那時的我懵懵懂懂,只知道把背下來的音與手勢演繹出來,但其實對於母語並沒有很熟知。因為那時太魯閣族還沒有正名,使得我報名參加的族群名也總是在變化,一下子是泰雅族東賽德克族語、或是泰雅亞族德魯固族語,而年幼無知的我對於族別也不是很清楚,我只知道我在比賽母語演講。
而田老師鋼鐵般的教導,總讓我很害怕去她家學母語。我曾看過她在我面前打了跟我同年紀的小男孩耳光,只因為他一直念錯,巨大的壓力之下,我向阿嬤哭訴說不想再去比賽了,所以阿嬤就幫我擋下了田老師的比賽要求。也許是因為說母語的經驗讓我有陰影,自此之後我就再也不去碰母語了,即便在部落總是聽到長輩們都用母語交談。
我的成長與情緒
我是一九八七年在花蓮縣秀林鄉加灣部落出生,族名Yabung.Haning。太魯閣族是父子連名,Yabung 是我的名字,Haning 則是我爸的名字。
太魯閣族人叫人名時,總是會加上一些形象特徵或是故事方便記憶,簡單來說就是很愛幫人家取外號,我小時候總被隔壁部落的叔叔叫Yabung.Tuba,Tuba是太魯閣族語「魚藤」的意思,在溪裡抓魚時把藤汁搗出來放水裡,可以暫時麻痺附近的魚。聽說我出生時的加灣部落有個名字同樣也叫Yabung 的婦女試圖吃魚藤自殺而出名,所以隔壁部落的叔叔總是叫我加灣來的Yabung.Tuba。
我的阿公叫Jiru,大家都叫我阿公Jiru.Honda,因為他是我們部落第一個買下Honda(本田)摩托車的人。阿公阿嬤認真務農,以前家裡的客廳還有農會頒發的木製匾額,是阿公擔任農會代表時所贈。而聽說我出生時,阿公抱我沒有多久就去世了,爸爸總說那時候我剛出生,阿公第一次抱我,我叫了三聲阿公之後,他就因農藥中毒而死在田裡。
當時加灣部落主要經濟來源是種稻米,在沒有保護遮蔽的狀態下灑農藥,導致不少人因為農藥中毒或是肝臟方面的疾病而去世,我阿公Jiru就是肝病去世。
有關族人因肝病而去世這件事,不知道為什麼在我長大之後,總是被人說「原住民得肝病就是因為愛喝酒」的關係,而讓我一度以為會得肝病的原因只有喝酒,一直到我接觸長期照顧服務的工作才知道,原來會得肝病的原因有很多種,有喝酒、農藥及過勞等。
加灣部落的太魯閣族名叫Alang Qowgan, Qowgan 是一種大竹子的名字,祖先遷移至此看見許多這種竹子因此命名,而後來的加灣山相繼因為各種法律的規定,諸如獵人狩獵被抓、禁止游耕燒墾、禁伐補償的政策以及部落生活經濟的改變,導致缺乏族人上山整理而逐漸荒廢,竹林樹木被覆蓋著滿滿的小花蔓澤蘭。這種外來藤本植物會攀著植物往上爬,只要有陽光空隙它便會填滿,植物會因為缺乏光合作用而死亡,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就很少找到長者所說的Qowgan 這種竹子了。
鄰近我家後面的是一座陡直約六百五十公尺高的加灣山,我依稀記得小時候跟著阿嬤沿著景美國小旁邊的小路上山,在阿嬤刻意栽種的箭筍細竹間用繩子與帆布搭建的簡易工寮,並放置鍋碗瓢盆、寶特瓶水,阿嬤在那裡生火煮湯麵,我則會在放完火燒墾後的山坡,坐在紙箱上找地方滑下去,當然最後少不了被修理一頓。也記得小時候常常看到我們家後面的山頂上有人招手,或者將要製作竹筒飯的節慶日,往山的方向看去會有「竹子雨」──山上有人把竹子用投射的方式往下丟擲,聚集在某處,或者順著竹子的路往山下拖拉,那些往下移動的竹子就好像下雨一樣。
「部落很多規矩妳不知道!」
我的童年,常常聽到有人在部落的路上打架爭執,甚至刀光劍影、拿著電鋸在路上跑都不是奇怪的畫面。
只要半夜有人叫囂,部落的族人就會前去阻止、拉扯,就如同我爸和部落的叔叔在飲酒過後有些言論產生不愉快,就會扭打起來,甚至拿刀出來,好像很有默契地把手上的刀打在對方的刀上,鏗鏘產生火花,但不至於出人命,頂多扭到腳或是不小心劃到耳朵流血包紮,隔天腳一跛一跛地再到對方家道歉。我總不覺得在部落看到幾個男人打架是令人害怕的事情,某個部分還覺得有種湊熱鬧的興奮感,這是跟新聞上面播放的槍擊殺戮社會案件不一樣的情境。
在太魯閣族社群裡的衝突事件,有個潛規則,就是不太能叫警察,族人間可以打架,其他人會協助勸架阻止,但其中一方如果有人報警來處理,或是訴訟上法院,會被譴責說那樣做太超過了。我爸媽就指責過隔壁鄰居兄弟鬩牆鬧上警局,但他們譴責最多的不是打架行為本身,而是報警處理的這件事。
我又想起大學時期年輕氣盛做的蠢事。部落一個阿姨為人霸道,多數族人盡量不跟她有交集,我媽透過關係在部落買了一隻貴賓狗,那隻狗是那個阿姨的狗配種後的小孩。我媽養了一陣子很是喜愛,有一天那位阿姨就衝進我家直接把那隻狗給帶走說那是她的狗,我氣不過就跑去警察局準備要報案。
我媽得知後氣沖沖地衝去警察局當著大家的面把我給拖走,她嘴裡對我罵著:「部落很多規矩妳都不知道,妳以為妳讀書讀得高就可以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嗎?妳還早得很!部落的人是我每天都會見面的,妳這樣子一搞我要怎麼在部落裡生活?」
當時的我並不明白,為什麼部落的人寧願自己吃虧,也不要找警察處理。
彎彎曲曲的歷史殖民痕跡與我的小姆指
我就讀部落裡一間私立天主教安德幼稚園,那時候園長是一個外國人,園區的角落有個小教堂,幽幽靜靜,我們小孩總是說那裡有吸血鬼,不乖的話會被園長抓去裡面吃掉。
園內的孩子都是加灣部落的太魯閣族,因為私立的關係學費本來就很貴,但是安德幼稚園可以接受分期付款,或是同意以先欠費的方式照顧小孩,甚至付不出學費的家庭,園長也還是會收,依靠募款等方式來維持營運。我們家都有分期付款和欠費的情況,這是我後來才知道的事情。
即便是在太魯閣族部落裡的幼稚園,學生也都是太魯閣族,但園內並沒有讓我有任何學習太魯閣族文化、語言的印象,當然那時的年代忙著生存都來不及,更不可能談到族群文化,秉著慈愛與收容幫助我們偏鄉兒童的議題就很偉大了,所以我依稀記得幼稚園的畢業表演是跳著阿美族舞蹈和蚌殼精。
我是看著迪士尼和格林童話的卡通長大,小姑姑還送我《十萬個為什麼》的動畫卡帶給我,小姑姑很喜歡麥可.傑克森(Michael Jackson),她房間都是他的海報和音樂,當時部落甚至還有許多小朋友相繼模仿麥可.傑克森的月球漫步舞步。
每到星期日,就是要去加灣基督長老教會聽《聖經》故事,然後吃糖果,阿嬤通常給我二十元的奉獻金,我都會投十元給教會,剩下十元我會拿來買糖果。我最喜歡在星期日中午,部落十字路口中間,會有棉花糖阿伯,下午會有糖葫蘆阿伯,甚至有行動剪髮的阿伯在部落走動。那些阿伯們都是漢人,在固定的時間出現在部落固定的位置,持續至少有二十年以上,直到可能行動不便無法來為止。
每當到了夏天,我會和鄰居小朋友去景美國小的水圳游泳,摘水圳上母構樹的種子當糖果來吃,水圳是在臺美建交時期為了部落種植灌溉水稻時建設的。我們在半山腰有個祕密基地,我依稀記得是藤蔓圍繞著樹形成的天然樹洞,我們也不曾害怕會有蛇或是蟲之類的,自以為地把寶物藏在那裡。
部落正中間有個叫做「高山青」的廢棄酒店,它是我們部落孩子冒險的鬼屋,我們會在高山青前空地集合,拿著手電筒去闖,闖過了可怕幽暗的大廳,到二樓會看見破碎的玻璃落地窗,然後就是樓梯下樓直達酒店後的花園池塘。花園池畔上有一個一個小小的獨立小房子,很像蘑菇長在花園上。傍晚我跟鄰居的小朋友都在部落的馬路上賽跑。
部落的大人們都在忙,我們小孩每天在部落也忙著玩,但玩的時候切記不能讓自己受傷,或是遺失東西。比方今天手被割到了,自己很痛就算了,回去被大人發現受傷了,就是先一陣挨打;或是鞋子掉了一隻後,又是一陣挨打;被發現去了大人警告不能去的地方,比方溪河、水圳、海邊後,又會一陣挨打。
對這些處罰的因應方式就是,不要讓自己受傷,或是想辦法不被發現,我的右手小拇指彎彎的,因為小時候玩耍時折到,回家默默地藏起來不講,就是怕被打的關係,但也就這樣彎彎曲曲地長大了。
分離寄宿的國小生活
要上國小時,爸媽到雲林麥寮及桃園等地工作,我們跟著很多同樣是太魯閣族叔叔阿姨們一起同居生活。當時我一年級就讀桃園的國小,我的同學幾乎都是閩南人,我到同學家玩時第一次聽到他們家長說出「番仔」的稱呼,不懂這意思的我們還是玩在一起。
讀了半個學期,爸媽因為接工程常常要轉移陣地,不方便帶著我一起,於是我被送回花蓮給阿嬤照顧。我還記得當爸媽準備要騎車離去時,我手抱著我媽媽,然後阿嬤抓住我的腳,我騰空在半空中聲嘶竭力地哭喊著:「我不要!我要一起去!」
當然最後,我還是留在花蓮。但沒有多久,不太會中文的阿嬤因為不知道要怎麼教我,小學課本都是她看不懂的中文和注音,所以又把我交給隔壁佳民部落的大姑姑照顧,使我就讀佳民部落的國小。
佳民國小一個年級只有一班,每班大約只有十到十五位學生,我一進去期中考直接考第一名,因此被全班排擠過。全校學生都是太魯閣族,但任教的老師沒有一個是太魯閣族,印象中幾乎都是外省籍老師,因為我從來沒有聽過他們講過閩南語。
國小在學校除了學習中文、數學、自然等主科之外,老師還教我們打響板數來寶、做紙雕、念順口溜,以及唱童謠(童謠都是閩南語或是中文的歌謠)。
我常常會被推去比賽國語朗讀、演講、注音寫字與書法。老師為了要「糾正」我的口音,要求我每天上臺朗讀《國語日報》,教我拿著筆、順著注音的四聲畫在空中調整我的抑揚頓挫,所以我的中文咬字很標準,這也導致我在後來接觸自己的文化時,有一段時間總被誤認為「不在部落長大的孩子」。
由於我臺風很穩,便被加灣部落提倡母語推廣的田老師相中,要我去比賽母語演講。大約是在我三、四年級時,常常要到田老師家受訓,她先教我如何認羅馬拼音,再教我咬字發音,然後要我用中文寫一篇〈我的家〉,她翻譯成母語,再要求我背下來。我就以這篇〈Alang mu〉(我的家)拿下了全國第一名的母語演講冠軍,成為家喻戶曉的全國太魯閣族語冠軍的Yabung。
那時的我懵懵懂懂,只知道把背下來的音與手勢演繹出來,但其實對於母語並沒有很熟知。因為那時太魯閣族還沒有正名,使得我報名參加的族群名也總是在變化,一下子是泰雅族東賽德克族語、或是泰雅亞族德魯固族語,而年幼無知的我對於族別也不是很清楚,我只知道我在比賽母語演講。
而田老師鋼鐵般的教導,總讓我很害怕去她家學母語。我曾看過她在我面前打了跟我同年紀的小男孩耳光,只因為他一直念錯,巨大的壓力之下,我向阿嬤哭訴說不想再去比賽了,所以阿嬤就幫我擋下了田老師的比賽要求。也許是因為說母語的經驗讓我有陰影,自此之後我就再也不去碰母語了,即便在部落總是聽到長輩們都用母語交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