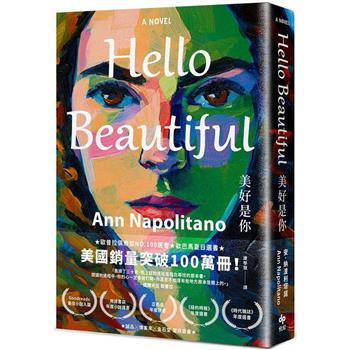威廉
一九六○年二月~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威廉・華特斯人生最初的六天,並非家中唯一的孩子。他有一個三歲大的姊姊,名叫卡洛琳的紅髮女孩。家裡有幾卷無聲錄影帶,主角是她;影片裡,威廉的爸爸笑得很開心,而威廉從來沒有在現實中看過他笑。其中一支影片裡,爸爸神情開朗,小小的紅髮女孩掀起裙子蒙住臉,嘻笑著不斷繞圈奔跑,看來這就是他笑的原因。威廉出生後,和媽媽一起住院的那幾天,卡洛琳發燒、咳嗽。他們出院回家時,卡洛琳似乎開始康復了,然而咳嗽還是很嚴重。一天早上,爸媽去她的房間準備抱她出去時,發現她躺在嬰兒床上,已經沒氣了。
威廉小時候,父母從不提起卡洛琳。客廳的邊桌擺著一張她的照片,威廉偶爾會特地去看,為了說服自己真的曾經有過姊姊。他們搬離了原本的住處,換了一棟位在牛頓市另一邊的房子,在那棟波士頓郊區的海軍藍屋瓦房子裡,威廉是唯一的孩子。他的父親是會計師,公司位於波士頓精華地帶,工作時間非常長。失去女兒之後,爸爸也失去了開朗的表情。威廉的媽媽總是在客廳抽菸、喝波旁威士忌,有時候一個人,偶爾有鄰居太太陪伴。她收藏著幾件荷葉邊圍裙,煮飯的時候會穿上,但只要一弄髒或變皺,她就會非常焦慮。
有一次,圍裙沾到深色的醬汁,媽媽急得滿臉通紅,就快哭出來了,威廉說:「不然妳煮飯的時候不要穿圍裙嘛。考內特家的媽媽都只在腰帶塞一條擦碗布,妳也那樣做吧。」
媽媽的表情彷彿他說的是希臘語。威廉繼續說:「隔壁考內特家的媽媽呀?她不是都用擦碗布嗎?」
從五歲開始,威廉幾乎每天下午都帶著籃球去附近的公園,因為棒球或足球不能一個人玩,但籃球可以。公園裡有個露天籃球場,很少有人去,通常都會有一邊的籃球架沒人用。他投球,一連好幾個小時,假裝自己是賽爾提克隊 的選手。他最喜歡的球員是比爾・羅素 ,但是扮演羅素需要有對手可以阻擋。山姆・瓊斯 是最厲害的射手,所以威廉通常扮演瓊斯。他努力模仿瓊斯完美的投籃姿勢,假裝球場旁邊的樹木是為他加油的球迷。
十歲那年,一天下午,他去籃球場時發現已經有人在打球了。一群男生,大約五、六個,年齡與威廉相仿,他們在球架之間追逐搶球。威廉正要後退,但其中一個孩子大聲說:「喂,要不要一起玩?」接著,他不等威廉回答就說:「你加入藍隊。」幾秒之後,威廉被捲進球賽,他的心臟跳得很猛烈。隊友傳球給他,他立刻回傳,他不敢投球,生怕萬一沒中會被罵球技很爛。幾分鐘後,比賽突然結束,因為有人要回家了,那群男生往不同方向離開。威廉走路回家,心跳依然劇烈。在那之後,當威廉帶球去公園,不時會遇到那群孩子。他們出現的時間不一定,但每次都會揮手要他加入,把他當作一份子。這讓威廉感到驚愕。通常人們的視線會直接略過他,無論大人或小孩,彷彿他是透明的;父母也幾乎從不正眼看他。威廉接受這一切,他可以理解,畢竟他無趣又不起眼。他最大的特色就是整個人缺乏色彩:沙色頭髮、淺藍眼睛,英格蘭與愛爾蘭後裔常見的極白膚色。威廉很清楚,他的內在同樣無趣寡淡。他在學校從不說話,也沒有人和他玩。籃球場上的那群男生讓威廉第一次有機會加入團體,而且不必說話。
五年級時,小學體育老師說:「我看到你下午都會去投籃。你爸爸多高?」
威廉茫然地望著老師。「不確定。一般身高?」
「好,那你大概可以打控球後衛的位置。你必須加強控球。你知道比爾・布拉德利 吧?尼克隊那個有點笨拙的人?他小時候會把厚紙板黏在眼鏡上,這樣就不能往下看腳。他戴著那副眼鏡運球在街上走來走去。可想而知,看起來很像神經病,但他的控球能力非常厲害。他光憑感覺就知道球會往哪裡跳,不用看也能找到。」
那天放學後威廉衝回家,整個人激動不已。這是第一次有大人正眼看他,注意到他這個人、注意到他做的事,那樣的關注令他渾身不自在。威廉翻找書桌抽屜,打了很多噴嚏之後,終於在很裡面的角落找到一副玩具眼鏡。他去了兩次洗手間,然後才小心翼翼將兩片長方形紙板黏在眼鏡下緣。
每當威廉生病或不舒服,他都覺得一定會死。一個月至少有一次,放學後他會爬進被窩,相信自己得了不治之症。他不會告訴父母,因為這個家裡不允許生病。咳嗽更是大忌,被視為惡劣的忤逆。威廉感冒的時候,只能躲在衣櫥裡關上門咳嗽,臉埋在一整排上學穿的襯衫中。他戴上那副眼鏡、帶著球出門時,肩膀與腦後感覺到熟悉的憂慮。但現在威廉沒有時間生病,沒有時間害怕。他感覺到這是關鍵時刻,他的身分認同終於完整了。球場上的那群男生看出來了,體育老師也看出來了。威廉或許不知道自己是什麼人,但世界告訴他了:他是籃球員。
體育老師教給威廉更多小訣竅,讓他加強技巧。「防守的時候,要用肩膀和屁股推開對手。裁判不會視為犯規。練習衝刺,這樣起步會比對手快,運球的時候才不會被追上。」威廉也努力練習傳球,在公園打球的時候,才能把球交給最強的隊友。他想繼續和他們打球,他知道如果能讓其他人表現更好,他就有價值了。他學會該往哪裡跑才能提供射手切入的空間。他做好掩護,讓射手能以喜歡的方式投球。每次贏了比賽,隊友都會拍拍威廉的背。他們的接納稍微平息了威廉內在的恐懼。在籃球場上,他知道自己該做什麼。
上高中後,威廉的實力已經足以擔任校隊先發。他身高五呎八吋 ,打控球後衛。他花了那麼多時間戴眼鏡練習果然沒有白費:他的運球功力全隊第一,中距離跳投也相當出色。他努力練習搶籃板球,挽救隊友的失誤。傳球依然是威廉最強的技能,他一出場,隊友都能表現得更加出色,他們非常感謝威廉。他是校隊裡唯一的一年級生,因此,即使學長的父母願意放任他們在地下室喝酒,他們也不會讓威廉加入。升高二的暑假,威廉突然抽長五吋,隊友非常驚訝──所有人都非常驚訝。他一旦開始抽高就停不下來,高中畢業時,他的身高已經到達六呎七吋 。因為抽高太快,吃再多也趕不上成長需求,因此他瘦得嚇人。每天早上他彎腰走進廚房時,媽媽都一臉驚恐,只要他經過身邊,她一定會給他東西吃。她似乎覺得他這麼瘦害她臉上無光,畢竟餵飽他是她的責任。父母偶爾會去看他比賽,但次數非常少,他們客客氣氣坐在看臺上,好像不認識球場上的任何人。
威廉受傷的那場比賽,父母沒有來。他在搶籃板球的時候被人在空中一推。他身體扭動,以很彆扭的姿勢右腿落地。右膝承受了所有衝擊力道加上他的體重。威廉聽見膝蓋發出怪聲,然後眼前籠罩濃霧。教練平常就只有兩種狀態:大吼和嘟囔,此時他在威廉耳邊大吼:「華特斯,你還好吧?」平常無論教練大吼或嘟囔,威廉都以同樣的方式回應:以問題回答問題。他缺乏自信,無法以篤定的語氣回應。此刻他清清嗓子。濃霧瀰漫外界與內在,伸手不見五指,夾雜著從膝蓋輻射而出的劇痛。他說:「不好。」
他的髕骨骨折,如此一來,十一年級剩下的七週他都不能上場。威廉的右腿打了石膏,完全動彈不得,整整兩個月的時間都得用拐杖。這也意味著,從五歲以來,他第一次無法打籃球。威廉坐在房間的書桌前,對著放在另一頭的垃圾桶扔紙團。受傷時瀰漫的雲霧一直沒有消散;他的皮膚感覺潮濕冰冷。醫生說傷勢會完全康復,十二年級可以繼續打球,儘管如此,威廉依然每天每分鐘都感到輕微恐慌。時間也變得很奇怪。他覺得自己將永遠困在房間中、椅子上、石膏裡。他也想到姊姊,想著卡洛琳逝去的經過。他思考她不復存在的事實,他無法理解,然而,隨著時鐘從這分鐘辛勤地爬向下一分鐘,他好希望自己也不存在。離開籃球場,他毫無用處。沒有人會因為少了他而難過。如果他消失,感覺會像是從不曾存在過。沒有人提起卡洛琳,自然也不會有人提起他。直到威廉的右腿終於擺脫石膏,重新可以奔跑投球,濃霧與企圖消失的念頭才逐漸散去。
威廉的學業成績不錯,加上籃球場上表現出色,幾家擁有NCAA一級籃球隊 的大學提出獎學金邀請他入學。他很慶幸有獎學金,因為父母從來沒有表示過願意供他上大學,他也將獎學金視為能夠繼續打籃球的保證。威廉想要離開波士頓──他從來沒有離開市中心超過九十英哩──不過,他擔心南方會太過溼熱,於是接受了芝加哥西北大學的獎學金。一九七八年八月底,威廉在火車站和母親吻別、和父親握手。當威廉握著爸爸的手,心中有種奇怪的感覺,他可能永遠不會再見到父母了──他們只有一個孩子,但不是他。
大學選課的時候,威廉的重心偏向歷史。他一直覺得對世界運作的方式知識不足,有如一個大洞,歷史似乎是解決這個問題的好答案。歷史能夠在迥異的事件中找到模式,他喜歡這種感覺。如果這件事發生了,接下來那件事就會跟著發生。沒有任何一件事毫無來由,因此,奧地利大公遇刺事件可以連結到世界大戰 。大學的生活太嶄新,完全無法預期,威廉走在喧鬧的宿舍走廊時,會有興奮的學生舉手和他擊掌。面對這樣的狀況,他奮力想找到一點平衡感。他將一天的時間分成三份:在圖書館讀書、在籃球場訓練、在教室上課。在這三個地方,他很清楚自己該做什麼。他走進教室、坐在位子上、翻開筆記本,當教授開始講課時,他因為安心而全身無力。
威廉很少留意課堂上的其他學生,但一起上歐洲史的茱莉雅・帕達瓦諾讓人不注意也難。因為她的臉上總是燃燒著義憤填膺,也因為她太愛發問,快把教授逼瘋了──他是英國人,年紀很大了,一隻手裡總是捏著一條大手帕。當她說話時,長鬈髮在明豔的臉龐周圍如簾幕般搖曳,她提出的問題類似這些:教授,我很想多瞭解克萊門汀 在這起事件中的角色。她不是邱吉爾最重要的顧問嗎?或者:請說明一下戰爭時期的密碼系統?我想知道運作的詳情。希望您能給個範例。
威廉從來不在課堂上發言,也從不去教授辦公室諮詢。他相信學生的角色就是要乖乖閉嘴,盡可能多吸收知識。對於那個鬈髮女同學,他的看法與教授一致:雖然她的問題很有意思,但經常打斷教授講課提問很不禮貌。學生應該認真聽講,教授則像鋪開地毯一樣傳授智慧,這樣才能交織出課堂肅穆的氛圍,就像織布一樣。然而,那個女同學卻在這塊布上戳了一堆洞,就好像她完全不知道有這塊布的存在。
一天下午下課後,那個女同學突然出現在他身邊說:「嗨,我是茱莉雅。」害威廉嚇了一大跳。
「嗨,我是威廉。」他必須清清嗓子,這很可能是他一整天第一次開口說話。女同學看著他,大大的眼睛很嚴肅。他發現,在陽光下,她的棕髮間會出現蜂蜜色調的線條。感覺她整個人在發亮,不只外在,內在也是。
「為什麼你這麼高?」
威廉的身高經常引人議論,這不是第一次了。他很清楚,每當走進一個地方,他的體型總會令人訝異,多數人都會忍不住想說點什麼。一個星期總會有好幾個人問他:上面的空氣新鮮嗎?
不過,茱莉雅發問時一臉猜忌的表情,讓他忍不住笑出聲。他在穿過中庭的小徑上停下腳步,於是她也跟著停。威廉很少大笑,他的雙手刺刺麻麻,彷彿剛從缺氧的夢境醒來。整體的感覺就是一種愉悅的酥癢。後來當威廉回想起這一刻,才意識到這就是他愛上她的瞬間。更正確地說,是他的身體愛上她。在中庭中央,來自一個特定女孩的關注,勾出他內在每個角落與縫隙發出的笑聲。威廉裹足不前的心靈早已讓身體感到厭煩透頂,此時,身體不得不在他的神經與肌肉大肆施放煙火,提醒他發生了重大事件。
「你笑什麼?」茱莉雅問。
他勉強壓抑住笑聲。「請不要生氣。」
她不耐煩地點一下頭。「我沒有生氣。」
「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這麼高。」不過其實他暗自認定,是意志力讓他長這麼高的。如果想認真投入籃球運動,身高至少要六呎三吋,威廉實在太在乎籃球,因此違抗了基因。「我是籃球校隊選手。」
「看來至少你把身高用在對的地方了。」她說。「改天我說不定會去看你比賽。我對運動沒有半點興趣,我來學校只是為了上課。」她停頓一下,然後說:「還有我為了省錢,所以住在家裡。」她說得很快,似乎覺得丟臉。
茱莉雅要他把她的電話號碼抄在歷史筆記本裡,她離開之前,他答應明天晚上會打電話給她。他喜不喜歡她這件事似乎並不重要,在中庭中央,那個女生已經決定了他們要當男女朋友。之後她會告訴他,她已經在課堂上觀察他好幾個星期了,她喜歡他認真嚴肅的態度。「男生都很傻,但你不一樣。」她說。
即使認識了茱莉雅,籃球依然佔據了威廉大部分的時間與思緒。高中時,他是隊上最優秀的球員,但來到西北大學之後,他沮喪地發現自己竟然吊車尾。在這支球隊中,他的身高並不特別,而且其他隊友體格更壯碩。他們多數人已經花了幾年的時間練舉重,威廉竟然不知道應該要練舉重,這件事令他驚慌。球隊訓練時,他很容易被推開或撞倒。他開始在訓練之前去舉重,訓練結束之後,留在球場繼續練習以不同的角度投球。他隨時都很餓,外套口袋裡總是塞著幾個三明治。他明白自己在球隊裡的角色,很可能是幫助隊友發光發熱。儘管他並非天才型運動員,但他的傳球、投球、防守能力都夠好到派上用場。他最重要的能力則是很少在場上犯錯。有一次教練團在談話,不知道他就在旁邊,他聽見一位教練說他「籃球智商很高,可惜跳不高」。
獎學金規定學生必須在校園工作,在職缺清單中,他選了在體育館裡的那個,因為這樣比較方便籃球訓練。他在指定的時間前往位在巨大體育館建築半地下室的洗衣房報到,主管是一位女性,非常瘦,頂著高聳的爆炸頭,戴眼鏡。她搖頭說:「你跑錯地方了。他們叫你來這裡?白人不會被派來洗衣房。你應該要去圖書館或學生育樂中心才對。快走吧。」
威廉往狹長的空間望去。一整排三十臺洗衣機佔據一邊的牆壁,三十臺烘乾機佔據另一邊。確實,一眼看去沒有其他白人。
「有差嗎?」他說。「我想要這份工作,拜託。」
她再次搖頭,眼鏡在鼻頭晃動,但她還來不及開口,有人拍拍威廉的背,低沉嗓音說出他的名字。他轉身看到籃球隊的另一名一年級球員,強壯的大前鋒,名叫肯特。肯特的籃球技巧與威廉恰恰相反:他的體能非常傑出,能夠大秀灌籃,搶籃板球又快又猛,在場上的每分鐘都高速衝刺,但他很不會判斷局勢,導致經常失球,也搞不清楚防守時該站在哪裡。教練每次看到肯特在場上的表現都會抱頭懊惱,想必是因為肯特明明有強大的體能潛力,打球時卻只會高速橫衝直撞,這樣的落差讓教練很頭痛。
「嘿,兄弟,」肯特說,「你也在這裡工作?領班,如果妳不介意,我來帶他就好。」肯特對嚴肅的領班露出大大的迷人笑容。
她的態度軟化。「好吧,那就這樣。既然我不用帶他,那我可以裝作他不存在。」
從那天開始,威廉與肯特都會特地選同一個值班時段,並肩在洗衣房工作。他們洗了千百條毛巾和各個運動校隊的制服。美式足球的制服最難洗,因為很臭,而且青草污漬深入纖維,必須用特殊漂白劑刷洗。威廉與肯特在洗衣的每個步驟都訓練出一套節奏;這份工作重視時機與效率,感覺很像籃球訓練的延伸。他們利用工作時間分析賽局,思考如何讓球隊表現更好。
一天下午,他們忙著摺疊有如小山的毛巾,威廉一邊說明:「順序是這樣:首先是後衛傳給另一個後衛,前鋒繞過底線掩護,一名後衛出來幫中鋒牽制對手。」威廉停頓一下,確定肯特有聽懂。「如果球傳給中鋒,那麼小前鋒就要去角落,另一個前鋒在那裡繞過掩護,另一個後衛掩護弱邊。」
「掩護再被掩護。」
「就是這樣!假使中鋒傳球給前鋒,那麼也是同樣的順序。」
「太容易被看穿了吧!教練老是要我們重複練同樣的跑位,一次又一次……」
「不過要是做得夠好,即使防守球員知道接下來的步驟,也很少有人能擋住,尤其是如果我們……」
「你們兩個,」站在旁邊那臺烘乾機前面的人說,「你們知道你們說的這些別人根本聽不懂嗎?我常看籃球,但我完全不知道你們在說什麼。」
肯特與威廉對他傻笑。下班之後,他們上樓去體育館練投球,那裡的氣溫比洗衣房低二十度。
肯特來自底特律市,對NBA的每個球員、每支球隊都有很多意見,經常大肆評論,更衣室裡總是低級笑話滿天飛,他常常話講到一半就大笑起來。訓練時,他經常因為炫技而遭到教練吼罵,肯特雖然會道歉,但五分鐘之後又會再犯。「練好基本功!」教練一次又一次怒吼。
肯特自稱是魔術強森 的親戚,強森是密西根州立大學的四年級生,各界都看好他將是NBA選秀狀元。肯特交遊廣闊,大家都喜歡他,威廉不懂為什麼肯特會想和他來往。他只看出肯特似乎喜歡威廉沉靜的個性,將此視為經營友誼的機會。多數時候都是肯特在說話,威廉後知後覺地發現,肯特經常分享自己的往事,是為了讓威廉也說出他的往事。肯特告訴他奶奶罹患白血症的事,全家都萬分錯愕──因為她總是說自己會長命百歲,因為她氣勢強大,所有人都相信真的會實現。威廉告訴肯特,他到現在只和父母通信過一次,聖誕假期也會留在學校。
一天晚上,結束漫長辛苦的訓練之後,他們慢慢走過靜謐的中庭,肌肉因為過度操勞而抽筋,肯特說:「有時候我必須提醒自己,即使教練讓我坐冷板凳,或是因為不喜歡我的華麗球風對我大吼,這些都無所謂。我要念醫學院。他無法阻擋我實現未來的計畫。」
威廉很驚訝。「你想當醫生?」
「百分之百。雖然我還不知道要怎麼負擔學費,但我一定會學醫。你大學畢業之後要做什麼?」
威廉察覺手指冰涼。十一月初已經很冷了,他呼吸時,肺裡的空氣感覺很冰。威廉從來沒想過大學畢業之後的人生,他知道自己故意忽視未來。他很想說打籃球,但他的實力不足以加入職業隊。肯特會這麼問,就表示他也認為威廉的實力不夠好。
「我不知道。」威廉說。
「那我們一起想吧。」肯特說。「你有很多天分,而我們也還有很多時間。」
我有天分嗎?威廉想。除了籃球之外,他不知道自己還有什麼天分。
十二月初,茱莉雅來看週五晚上的籃球賽,當威廉發現她在看臺上時,眼前突然一片模糊,把球傳給對手。肯特在球場上衝刺,經過威廉時大喊:「喂!你搞屁啊?」防守時威廉成功抄截兩次,讓西北大學野貓隊逆轉局勢。進攻時,威廉在罰球圈外傳地板球給角落無人防守的射手。快到中場休息的時候,肯特喜孜孜地說:「我懂了!有女生來看你打球!她在哪裡?」
比賽結束,西北大學獲勝,威廉有幾分鐘打出了球季初期最佳表現。他爬上看臺去找茱莉雅。接近時他才發現,她和三個女生坐在一起,每個都長得很像她。她們的髮型一模一樣,豐盈的及肩鬈髮。「我的三個妹妹。」茱莉雅說。「我帶她們來當球探偵察你。籃球術語是這麼說的吧?」
威廉點頭,在四個女生的注目下,他忽然非常在意球褲太短、無袖球衣太薄。
「我們看得很開心。」一個感覺年紀較小的女生說。「不過感覺好累喔。你流了好多汗,我這輩子應該還沒有流過這麼多汗。我是瑟西莉雅,她是愛茉琳,我們是雙胞胎,今年十四歲。」
愛茉琳與瑟西莉雅對他露出友善的笑容,他也報以微笑。茱莉雅和坐在另一邊的妹妹很仔細研究他,眼神有如鑑定師正評估寶石。就算其中一個從皮包拿出鐘錶匠用的放大鏡戴上,他也不覺得奇怪。茱莉雅說:「你在球場上的樣子……好有力量。」
威廉臉紅了,茱莉雅的臉頰上方也透出粉紅。他看得出這個漂亮女生想要他,他不敢相信自己竟然這麼好運。從來沒有人想要他。他多希望能將她擁入懷中,在她的三個妹妹面前、在全場所有人面前,但威廉的天性做不出那種放肆的行為。他滿身大汗,茱莉雅又開口了。
「這是我妹妹希薇。」她說。「我最大,但只比她大十個月。」
「很高興認識你。」希薇說。她的髮色比茱莉雅略深,體型更嬌小,身材曲線也沒有那麼明顯。她繼續研究威廉,茱莉雅燦爛微笑,有如完全開屏的孔雀。就在他眼前,茱莉雅的襯衫因為被豐滿胸口撐得太緊,一顆鈕釦蹦開。她急忙重新扣好,但他還是瞥見粉紅胸罩。
「你有幾個兄弟姊妹?」雙胞胎其中一個問,不確定是愛茉琳還是瑟西莉雅。她們不是同卵雙胞胎,但長相非常相似,威廉無法分辨。同樣的橄欖色肌膚、同樣的淺棕色頭髮。
「兄弟姊妹?沒有。」他說,不過他當然還是有想到爸媽家中,邊桌上那張照片裡的紅髮幼童。
茱莉雅已經知道他是獨生子──他們第一次通電話時,她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這個──但她的三個妹妹全都一臉驚愕,表情非常有喜感。
「太慘了。」雙胞胎其中一個說,他不知道是愛茉琳還是瑟西莉雅。
「一定要請他來家裡吃飯。」希薇說,其他姊妹一起點頭。「他感覺好寂寞。」
於是乎,大學開學四個月後,威廉有了女朋友,也有了新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