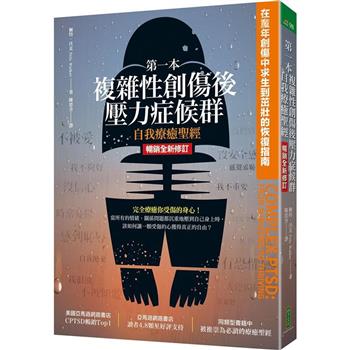◎一場奇特的經驗之旅
四十年前,我在印度搭乘從德里開往加爾各答的火車。當時,正是我在印度為期一年心靈探索的尾聲,但這趟探索之旅失敗了,我沒有得到啟悟,我的救贖幻想只為我帶來了絕望和阿米巴痢疾。這場疾病讓我少了十三公斤,看起來就像個憔悴瘦弱的和尚。
更糟的是,閱讀華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的《大道之歌》而燃起的希望,完全消失殆盡。那個希望,曾在我被突然逐出家門後,支撐了我長達五年的世界之旅……
回來談那趟火車之旅。我和平民、雞、羊為伍,坐在擁擠的二等座位上,閱讀著英文版的印度報紙。報紙說,我的目的地加爾各答,到處都是逃離孟加拉水災的十萬難民,他們顯然都睡在鬧區的騎樓下。
我在深夜抵達時,果然看到一個個身軀包裹在毯子裡,肩碰著肩,並且排滿了各條街道。我住進另一位旅人介紹的旅館,一晚二十分錢。
我睡得很差,畏懼著第二天早上即將看到的景象。我要如何面對滿滿的絕望人群,尤其當我什麼都給不了之
際?要是去澳洲,我有機會賺一點錢,但我懷疑自己連去澳洲的錢都不夠。
隔天早上,我好不容易擠下樓,卻被街頭景象的轉變給嚇呆了。那些難民把毯子攤開來,當成野餐墊,每張毯子上是一個快樂的家庭。小小的攜帶式爐子上煮了餐點和茶,人們帶著驚人的生命力與熱情,開著玩笑。還有小孩……孩子們(這個畫面深刻地印在我的記憶中)在父母身上爬著,尤其是父親們充滿感情地和孩子玩起體操,而且這些父親似乎和孩子一樣喜愛這個遊戲。
我被從未經歷過的混雜情緒給淹沒了─—一種陌生的雞尾酒式的放鬆、愉悅和焦慮。直到十年後,我才理解那個焦慮:原來那是從我的潛意識裡滲透出來的羨慕。
我深深地羨慕著這個豪華的親情大餐,那是我不曾經歷或目睹的。我在成長過程中所看過的家庭喜劇(甚至是甜膩膩的那種),都無法呈現出如此真誠有感的健康連結與依附。
多年後,我成為人類學及社會服務工作的學生,明白那是怎麼一回事。我回想起在其他尚未工業化的國家,也曾見到相似的情景,只是場面沒那麼大:摩洛哥、泰國、峇里島,還有澳洲的原住民保留區。
這些回憶使我發自內心地知道,無論是在我自己的家庭,或是朋友的家庭,我從沒見過這樣的感情。多年來,我消化著這個經驗,並用它來克服對自己童年失落的否認。我展開了數十年的追尋,引領我寫下這本書,以及《如果不能怪罪你,我要如何原諒你?》。
我希望透過這本書來努力創造一張地圖,使你可以依循著去療癒來自童年缺乏愛的傷口。如果我有時重複談論「縮小找碴鬼」、「哀悼童年失落」之類的話題,那是因為我一次又一次地試圖用不同的方式,來強調它們在療癒過程中的重要性。
如果你發現自己迷路了,不知道如何回到地圖上,那些話題永遠會是幫助你重回地圖的關鍵。
——佩特.沃克
◎從別人的身上獲得療癒
重新撫育的最佳狀態是一種陰陽動態,平衡著「受他人重新撫育」和「自己重新撫育」兩者相互提升的過程。重新撫育有時候需要由他人開始,並且由他人示範,像是由治療師、支持者、和善的朋友、支持性團體,來示範如何自己重新撫育。或者,有許多倖存者是透過我的某位案主所說的「書籍社群」,直覺、自發性地接受他人的重新撫育。那些作者鼓勵他們重視自己、支持自己,使倖存者得到重新撫育。
愛麗絲是個倖存者,她的家庭對她造成了全面性的童年創傷,使她很快地學到,向他人展現脆弱是危險的、愚蠢的、不經考慮的。然而,她依然渴望得到那些被不公平剝奪的支持與幫助,這種渴望在覺知層面的展現,使她被那些自助書籍強烈吸引。透過閱讀許多心理學知識,她終於得到了足夠的幫助,能去思考也許真的有和善、安全、樂於幫助的真人存在,並接受一些非常有助益的治療。
在我能夠克服恐懼與尷尬而投入治療之前,也花了很長一段時間慢慢閱讀和參加講座。如前所述,我很幸運地能夠找到夠好的治療師,幫我把關係療癒提升到另一個層次。
心理治療讓我能夠內化並模仿我的治療師,像她那樣一致且可靠地站在我自己這邊。然後,這導致我被更安全、更真正親密的友誼所吸引,而我在許多案主和朋友身上,也看到了同樣的結果。
後來,我達到了在治療關係以外首次「贏得的安全依附」,於是治療關係不再是我能得到有意義的深度連結的唯一來源。
我相信,從他人那裡得到父育和母育般的支持,這種需求是一輩子的,並不僅限於童年。很幸運地,我在多年後體驗到他人多重層次的重新撫育,我稱之為「代理團的重新撫育」,其概念是,擁有不同親密等級的一群朋友,而我自己的重新撫育委員內部小圈圈,包括了最親近的五位朋友。
我認為,這個內部小圈圈是我可以無話不談且卸下心防的人,包含了妻子、一位治療師友人、一位運動夥伴,以及我長期參與的男性團體中的兩位成員。在這個圈子的外圍還有一些人,如果我能夠多見到他們的話,他們也可能納入內部小圈圈裡。
在這個圈圈外,是各種關係,屬於比較沒那麼親密,但仍有意義的。再往外一圈,是過去很親密但現在不常見到的人,而我現在透過想像他們關心我,便可以得到慰藉。我已過世的祖母、三位前治療師、兩位陸軍夥伴、高中與大學的朋友、我待在澳洲十年的四位最要好朋友,都在這個圈子內。
再往外一圈,是我的醫護師、我偶爾造訪的身體工作者、一些治療師同僚,以及常幫我兒子選書的睿智老圖書館員。
往外再一圈,是我一起運動的朋友、我兒子朋友的父母,還有一些鄰居。和那些人接觸時,不會使我感到特別脆弱,而且我們之間有一種輕鬆的感覺,能幫助我在整體上有歸屬感。
最外圈是偶爾碰到的陌生人,有時候,在一些機緣下,我有幸能和他們產生自在舒服的互動。
我知道許多倖存者在有效的復原工作之下,從他人那裡得到了足夠的愛,於是他們心中對於幫助與支持的童年期飢渴,得到了顯著的滿足。像我一樣,他們的代理團從第一個夠親密的人開始,再把自己算進去,這代理團就有兩個人了,然後這代理團可以慢慢地,一次增加一段友誼地建立起來。
於是,透過可靠他人的幫助,我們的復原療癒會在各個層面提升。然而,再說一次,曾遭遇特別嚴重背叛的倖存者,可能需要先改善其他層面,才能夠承擔展現脆弱的風險,並願意接受關係性的幫助。
◎敘事的力量
有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CPTSD的復原程度,會反應在一個對自己人生故事的敘述中。倖存者復原得越多,他的故事就會越完整、協調、情緒一致,並且會以自我同情的角度訴說。
在我的經驗中,深層的復原通常反映在那些突顯情緒忽略的述說中,其中描述著一個人受了什麼苦、持續應付著什麼。
我的案主麥特,在母親節的兩天前剝了一大層否認與貶低的洋蔥。然後,他帶著糟糕的情緒重現來到會談中。「人生爛透了,而我甚至更爛!我甚至連挑選母親節卡片這麼簡單的事都做不到。」
幸運的是,從前一年的母親節起,麥特已經在「正視」方面有大幅的進展。一年前,他仍以為母親是個好媽媽,因為她從來沒有打過他。但當時,他因為花了一小時在卡片商店裡挑不出一張母親節卡片,而被嚴重地引發情緒重現。
隨著我們進一步探索後才發現,原來是每一張卡片中所印的詞句,都會使他覺得,如果他寄出這張卡片,就是背叛了自己的內在小孩。
「我跟你說,佩特,沒有一張卡片描述了我能感恩的事。我完全不記得她曾經為我做過或說過的任何好事!」不久,他開始深深地哀悼著母親給他的愛護如此稀少。他與母親的互動中充滿了母親輕蔑的表情和挖苦的語調,他為此哭泣、發怒。「為什麼我在母親牌卡中拿到這麼一手爛牌」如同健康的哀悼通常會發生的情況,在那次會談的尾聲,他覺得自己的情緒重現被化解了,並重新感覺到自己站在自己這一邊。脫離情緒重現後的紓解,也使他的健康幽默感回來了。他開始絮叨著:「我要創立一個卡片生意給我這樣的人。我要製作一系列的卡片給有失能母親的人。這個如何?『謝謝媽媽從不知道我讀幾年級』,或『謝謝媽媽給我的記憶,記得你在我痛苦的時候走開』,或是『謝謝媽媽教會我只注意到自己不對的地方』;又或是『謝謝媽媽教我如何厭惡地對自己皺眉』。」
◎如何讓自己大哭一場
在我成年早期的第一次突破性哭泣後,我曾經變得很難流淚。在不易流淚的那段期間,我經常渴望那令人難以置信的解脫,但是,不像發怒,我無法強迫自己哭泣。後來,我得知很多人也是這樣,我的朋友馬侃也遭受同樣的挫折,想哭到想把檸檬汁擠到自己的眼睛裡去,後來他能夠笑談這件事,但也嚴肅地警告我,絕對別嘗試這種行為。
我整理出一份清單,列出我們討論過如何讓自己大哭一場的方法。
如同本書中所有的忠告,請自由使用你覺得適合的項目,並且自由安排你覺得最好的順序。不同的組合,可能會提升哭泣或發怒能力,或者兩者同時出現。有時候怎麼做都沒用,但我鼓勵你,再多試試那些在直覺上覺得可能有用的技術。
1.找一個安全、舒適、不會被聽見的地方。
2.閉上眼睛,回憶你曾對某人感到慈悲憐憫的時候。這可以來自真實生活,或是讀過的一本書或一首詩,或是看過的電影或新聞。
3.藉由回憶某個人對你很仁慈,或是想像某個人應該會對你仁慈,來提取自我憐憫。像是我,我就會對你很仁慈。
4.進行言語抒發,談談困擾你的事。你可以寫下來,也可以對真實的朋友、想像的朋友,或是對我訴說。
5.想像自己受到更高的力量安慰。看見自己坐在這個仁慈的更高力量,或應該是仁慈的真實人物的腿上(我有一位案主覺得聖誕老人很好用)。
6.回憶你曾經在哭泣或發怒後覺得好多了的經驗,或看見別人在真實生活中或電影中哭泣。
7.回憶你曾經生氣,或別人的生氣,而使你免於傷害的經驗。
8.想像你的憤怒在周圍形成一個火紅的保護屏障。
9.想像你的眼淚或憤怒帶著恐懼、羞恥或憂鬱,升起並發散出來。
10. 想像自己慈愛地抱著你的內在小孩,告訴他,覺得不高興或受傷時,都可以感到悲傷或生氣,這是很正常的。
11.告訴你的內在小孩,你會保護他不受批判。
12.深深地、慢慢地、完全地呼吸。
13.播放可以感動你或是挑起情緒的音樂。
14.觀賞一部淒美的電影。
15.觀賞一部內容含有令你羨慕的憤怒發洩的電影。
關於第十五項,有好幾位案主表示,一九七六年的電影《螢光幕後》(Network),裡面有一幕是主角對著窗外大喊「我們再也不要忍受了」,能幫助帶出並抒發他們的憤怒。
最後,如果閱讀這本書之後,並沒有使你開始釋放找碴鬼對你哀悼能力的束縛,請考慮尋求心理治療師或支持團體來幫助你,去處理找碴鬼用以破壞你哀悼能力的那些羞恥。
四十年前,我在印度搭乘從德里開往加爾各答的火車。當時,正是我在印度為期一年心靈探索的尾聲,但這趟探索之旅失敗了,我沒有得到啟悟,我的救贖幻想只為我帶來了絕望和阿米巴痢疾。這場疾病讓我少了十三公斤,看起來就像個憔悴瘦弱的和尚。
更糟的是,閱讀華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的《大道之歌》而燃起的希望,完全消失殆盡。那個希望,曾在我被突然逐出家門後,支撐了我長達五年的世界之旅……
回來談那趟火車之旅。我和平民、雞、羊為伍,坐在擁擠的二等座位上,閱讀著英文版的印度報紙。報紙說,我的目的地加爾各答,到處都是逃離孟加拉水災的十萬難民,他們顯然都睡在鬧區的騎樓下。
我在深夜抵達時,果然看到一個個身軀包裹在毯子裡,肩碰著肩,並且排滿了各條街道。我住進另一位旅人介紹的旅館,一晚二十分錢。
我睡得很差,畏懼著第二天早上即將看到的景象。我要如何面對滿滿的絕望人群,尤其當我什麼都給不了之
際?要是去澳洲,我有機會賺一點錢,但我懷疑自己連去澳洲的錢都不夠。
隔天早上,我好不容易擠下樓,卻被街頭景象的轉變給嚇呆了。那些難民把毯子攤開來,當成野餐墊,每張毯子上是一個快樂的家庭。小小的攜帶式爐子上煮了餐點和茶,人們帶著驚人的生命力與熱情,開著玩笑。還有小孩……孩子們(這個畫面深刻地印在我的記憶中)在父母身上爬著,尤其是父親們充滿感情地和孩子玩起體操,而且這些父親似乎和孩子一樣喜愛這個遊戲。
我被從未經歷過的混雜情緒給淹沒了─—一種陌生的雞尾酒式的放鬆、愉悅和焦慮。直到十年後,我才理解那個焦慮:原來那是從我的潛意識裡滲透出來的羨慕。
我深深地羨慕著這個豪華的親情大餐,那是我不曾經歷或目睹的。我在成長過程中所看過的家庭喜劇(甚至是甜膩膩的那種),都無法呈現出如此真誠有感的健康連結與依附。
多年後,我成為人類學及社會服務工作的學生,明白那是怎麼一回事。我回想起在其他尚未工業化的國家,也曾見到相似的情景,只是場面沒那麼大:摩洛哥、泰國、峇里島,還有澳洲的原住民保留區。
這些回憶使我發自內心地知道,無論是在我自己的家庭,或是朋友的家庭,我從沒見過這樣的感情。多年來,我消化著這個經驗,並用它來克服對自己童年失落的否認。我展開了數十年的追尋,引領我寫下這本書,以及《如果不能怪罪你,我要如何原諒你?》。
我希望透過這本書來努力創造一張地圖,使你可以依循著去療癒來自童年缺乏愛的傷口。如果我有時重複談論「縮小找碴鬼」、「哀悼童年失落」之類的話題,那是因為我一次又一次地試圖用不同的方式,來強調它們在療癒過程中的重要性。
如果你發現自己迷路了,不知道如何回到地圖上,那些話題永遠會是幫助你重回地圖的關鍵。
——佩特.沃克
◎從別人的身上獲得療癒
重新撫育的最佳狀態是一種陰陽動態,平衡著「受他人重新撫育」和「自己重新撫育」兩者相互提升的過程。重新撫育有時候需要由他人開始,並且由他人示範,像是由治療師、支持者、和善的朋友、支持性團體,來示範如何自己重新撫育。或者,有許多倖存者是透過我的某位案主所說的「書籍社群」,直覺、自發性地接受他人的重新撫育。那些作者鼓勵他們重視自己、支持自己,使倖存者得到重新撫育。
愛麗絲是個倖存者,她的家庭對她造成了全面性的童年創傷,使她很快地學到,向他人展現脆弱是危險的、愚蠢的、不經考慮的。然而,她依然渴望得到那些被不公平剝奪的支持與幫助,這種渴望在覺知層面的展現,使她被那些自助書籍強烈吸引。透過閱讀許多心理學知識,她終於得到了足夠的幫助,能去思考也許真的有和善、安全、樂於幫助的真人存在,並接受一些非常有助益的治療。
在我能夠克服恐懼與尷尬而投入治療之前,也花了很長一段時間慢慢閱讀和參加講座。如前所述,我很幸運地能夠找到夠好的治療師,幫我把關係療癒提升到另一個層次。
心理治療讓我能夠內化並模仿我的治療師,像她那樣一致且可靠地站在我自己這邊。然後,這導致我被更安全、更真正親密的友誼所吸引,而我在許多案主和朋友身上,也看到了同樣的結果。
後來,我達到了在治療關係以外首次「贏得的安全依附」,於是治療關係不再是我能得到有意義的深度連結的唯一來源。
我相信,從他人那裡得到父育和母育般的支持,這種需求是一輩子的,並不僅限於童年。很幸運地,我在多年後體驗到他人多重層次的重新撫育,我稱之為「代理團的重新撫育」,其概念是,擁有不同親密等級的一群朋友,而我自己的重新撫育委員內部小圈圈,包括了最親近的五位朋友。
我認為,這個內部小圈圈是我可以無話不談且卸下心防的人,包含了妻子、一位治療師友人、一位運動夥伴,以及我長期參與的男性團體中的兩位成員。在這個圈子的外圍還有一些人,如果我能夠多見到他們的話,他們也可能納入內部小圈圈裡。
在這個圈圈外,是各種關係,屬於比較沒那麼親密,但仍有意義的。再往外一圈,是過去很親密但現在不常見到的人,而我現在透過想像他們關心我,便可以得到慰藉。我已過世的祖母、三位前治療師、兩位陸軍夥伴、高中與大學的朋友、我待在澳洲十年的四位最要好朋友,都在這個圈子內。
再往外一圈,是我的醫護師、我偶爾造訪的身體工作者、一些治療師同僚,以及常幫我兒子選書的睿智老圖書館員。
往外再一圈,是我一起運動的朋友、我兒子朋友的父母,還有一些鄰居。和那些人接觸時,不會使我感到特別脆弱,而且我們之間有一種輕鬆的感覺,能幫助我在整體上有歸屬感。
最外圈是偶爾碰到的陌生人,有時候,在一些機緣下,我有幸能和他們產生自在舒服的互動。
我知道許多倖存者在有效的復原工作之下,從他人那裡得到了足夠的愛,於是他們心中對於幫助與支持的童年期飢渴,得到了顯著的滿足。像我一樣,他們的代理團從第一個夠親密的人開始,再把自己算進去,這代理團就有兩個人了,然後這代理團可以慢慢地,一次增加一段友誼地建立起來。
於是,透過可靠他人的幫助,我們的復原療癒會在各個層面提升。然而,再說一次,曾遭遇特別嚴重背叛的倖存者,可能需要先改善其他層面,才能夠承擔展現脆弱的風險,並願意接受關係性的幫助。
◎敘事的力量
有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CPTSD的復原程度,會反應在一個對自己人生故事的敘述中。倖存者復原得越多,他的故事就會越完整、協調、情緒一致,並且會以自我同情的角度訴說。
在我的經驗中,深層的復原通常反映在那些突顯情緒忽略的述說中,其中描述著一個人受了什麼苦、持續應付著什麼。
我的案主麥特,在母親節的兩天前剝了一大層否認與貶低的洋蔥。然後,他帶著糟糕的情緒重現來到會談中。「人生爛透了,而我甚至更爛!我甚至連挑選母親節卡片這麼簡單的事都做不到。」
幸運的是,從前一年的母親節起,麥特已經在「正視」方面有大幅的進展。一年前,他仍以為母親是個好媽媽,因為她從來沒有打過他。但當時,他因為花了一小時在卡片商店裡挑不出一張母親節卡片,而被嚴重地引發情緒重現。
隨著我們進一步探索後才發現,原來是每一張卡片中所印的詞句,都會使他覺得,如果他寄出這張卡片,就是背叛了自己的內在小孩。
「我跟你說,佩特,沒有一張卡片描述了我能感恩的事。我完全不記得她曾經為我做過或說過的任何好事!」不久,他開始深深地哀悼著母親給他的愛護如此稀少。他與母親的互動中充滿了母親輕蔑的表情和挖苦的語調,他為此哭泣、發怒。「為什麼我在母親牌卡中拿到這麼一手爛牌」如同健康的哀悼通常會發生的情況,在那次會談的尾聲,他覺得自己的情緒重現被化解了,並重新感覺到自己站在自己這一邊。脫離情緒重現後的紓解,也使他的健康幽默感回來了。他開始絮叨著:「我要創立一個卡片生意給我這樣的人。我要製作一系列的卡片給有失能母親的人。這個如何?『謝謝媽媽從不知道我讀幾年級』,或『謝謝媽媽給我的記憶,記得你在我痛苦的時候走開』,或是『謝謝媽媽教會我只注意到自己不對的地方』;又或是『謝謝媽媽教我如何厭惡地對自己皺眉』。」
◎如何讓自己大哭一場
在我成年早期的第一次突破性哭泣後,我曾經變得很難流淚。在不易流淚的那段期間,我經常渴望那令人難以置信的解脫,但是,不像發怒,我無法強迫自己哭泣。後來,我得知很多人也是這樣,我的朋友馬侃也遭受同樣的挫折,想哭到想把檸檬汁擠到自己的眼睛裡去,後來他能夠笑談這件事,但也嚴肅地警告我,絕對別嘗試這種行為。
我整理出一份清單,列出我們討論過如何讓自己大哭一場的方法。
如同本書中所有的忠告,請自由使用你覺得適合的項目,並且自由安排你覺得最好的順序。不同的組合,可能會提升哭泣或發怒能力,或者兩者同時出現。有時候怎麼做都沒用,但我鼓勵你,再多試試那些在直覺上覺得可能有用的技術。
1.找一個安全、舒適、不會被聽見的地方。
2.閉上眼睛,回憶你曾對某人感到慈悲憐憫的時候。這可以來自真實生活,或是讀過的一本書或一首詩,或是看過的電影或新聞。
3.藉由回憶某個人對你很仁慈,或是想像某個人應該會對你仁慈,來提取自我憐憫。像是我,我就會對你很仁慈。
4.進行言語抒發,談談困擾你的事。你可以寫下來,也可以對真實的朋友、想像的朋友,或是對我訴說。
5.想像自己受到更高的力量安慰。看見自己坐在這個仁慈的更高力量,或應該是仁慈的真實人物的腿上(我有一位案主覺得聖誕老人很好用)。
6.回憶你曾經在哭泣或發怒後覺得好多了的經驗,或看見別人在真實生活中或電影中哭泣。
7.回憶你曾經生氣,或別人的生氣,而使你免於傷害的經驗。
8.想像你的憤怒在周圍形成一個火紅的保護屏障。
9.想像你的眼淚或憤怒帶著恐懼、羞恥或憂鬱,升起並發散出來。
10. 想像自己慈愛地抱著你的內在小孩,告訴他,覺得不高興或受傷時,都可以感到悲傷或生氣,這是很正常的。
11.告訴你的內在小孩,你會保護他不受批判。
12.深深地、慢慢地、完全地呼吸。
13.播放可以感動你或是挑起情緒的音樂。
14.觀賞一部淒美的電影。
15.觀賞一部內容含有令你羨慕的憤怒發洩的電影。
關於第十五項,有好幾位案主表示,一九七六年的電影《螢光幕後》(Network),裡面有一幕是主角對著窗外大喊「我們再也不要忍受了」,能幫助帶出並抒發他們的憤怒。
最後,如果閱讀這本書之後,並沒有使你開始釋放找碴鬼對你哀悼能力的束縛,請考慮尋求心理治療師或支持團體來幫助你,去處理找碴鬼用以破壞你哀悼能力的那些羞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