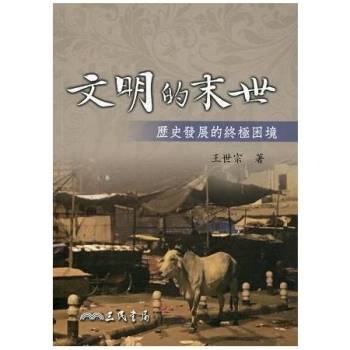第二節 文明的原罪與成就
文明是人上進的呈現,文明求真求善求美,若相對於野蠻,文明便是開化,但文明的目標不止於開化,因為「人為萬物之靈」僅為文明得以發展的基礎條件而非最終成果。人能上達,這表示人有先天的優點,但又不盡良善,亦即人活在一個不完美的世界,而圖加以改善或自我提升。人有此警覺,即是原罪感,蓋理想的期望反映不理想的現狀,而人具有良心,所以不符理想者即被視為「惡」而非「相當好」,可見原罪出於原善,人有天心才自認有罪。惡為善之不足,正如「壞」是「不夠好」,若世間一切皆完善,則人不可能有善惡觀,反之一切皆不完善,人乃有分別善惡的意識。然完善即是至善,而不完善不是至惡,因為惡僅為善之不足而非獨立於善之外的本質6,善已然存在,純粹或徹底的惡不可能出現,故有惡即有善、有善即有惡,此非相對主義或二元觀,而是求道所以可能的因素,也就是「文明的環境」7。總之,原罪是人求好心切之下的感受,此種感受是「不太妙的」,它暗示「可為」是程度的問題,即使「大有可為」也不可能心想事成。
原罪的存在使文明又有希望又有絕境,因為文明要求無限的進化,而進化實為有限。原罪固然是人的自省心得,但若人有原罪,則人之外的萬事萬物亦必有其缺陷,簡言之,一旦人發現其自身並非完美,便可知世界為不完美,這與其說是由「人為萬物之靈」一義推論而得,無寧說是由「人非宇宙主宰」一事斷定,因為人既不完美則人必是被造之物而非造物主,而上帝為完美即表示上帝之外一切均不完美。原罪之感唯人有之,此因萬物無此靈性,所以人自覺不良便知世上無完善之事物,由此可見所謂原罪乃是人在失望之餘追本溯源的說法,原罪的真諦或廣義其實是「無所不在的缺陷」。文明以人為主角,人有原罪所以文明的原罪是無法盡善盡美,尤不幸者大眾的無知是人類之原罪,以致文明的絕境發生於最樂觀的時代,不僅不為人所知且因此惡化。
不論人對於原罪是否有所察覺,原罪的作用隨時隨地呈現於人的行為中,省思歷史尤可發現顯著之例,因為關乎人類社會整體之事更易顯示圓滿為無望。常人不知原罪為何物,但大都對其所處的環境感到不滿,而深思文明的人亦不可能對文明滿意,烏托邦(utopia)的提出便是此種心情的反映,然文明若有缺陷則無法真正改正,因為文明是上進向化的活力,它既有善意且有能力,而猶有不足之處,這必是本來(先天性)的缺失,永不能克服。史上的烏托邦思想皆非完美國度的設想,而是因應現實所提出的局部改良意見,或是避世心態的自白,這是對於人間不可能化為淨土的承認,然則烏托邦式的改革建議即無可能成功,因為文明的缺陷既是原罪所致,一事可以改正則萬事皆可以改正,片面的改造只是聊表心意而非希望無窮,難怪烏托邦主張歷來不斷被提出,亦即不斷被放棄。天堂與地獄的觀念也是原罪感受的間接表達,蓋天堂與地獄之說暗示世間為「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之地,此域雖不盡善但也非至惡,也就是有缺陷的世界,於是天堂為人所期乃因理想,而地獄為人所畏則因邪念,因為沈淪墮落本是人可以防止的事,自我放縱者其實「放不開」。一般侈談天堂與地獄的人對於人世的改善實心力無多,這固然是因其缺乏盡力負責的精神,但也含有「事不可為」的無奈,而這確非無理,所以期望來世是自然的事,而好論此事者大約善多於惡,畢竟其說猶有善惡報應的道德意念。天堂與地獄的信徒大部分偏重天堂而忽略地獄,因為此輩必自信(自我暗示)能上天堂,無知與自私使其以地獄一說勸善的努力不強,何況對於現實的失望使人認為淑世的意義甚為有限。在社會改良的問題上,相對於教徒「悲觀之下的樂觀」,務實而不信神的人表現了「樂觀之中的悲觀」,功利主義者所號召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greatest number),顯然是棄「質」就「量」的建議,於此完美已非目標,社會性的正義取代公道,其說默認原罪,卻連帶否認「原善」,以致造成「多數暴力」,加速文明的滅亡。由此可見,文明的沒落雖本是文明的原罪,但對此缺乏正確認知而推展錯誤的政策者,須負毀滅文明的罪名。
人無法獨立,不僅個人無法獨立,人類亦無法獨立,因為人非創造者或主宰,真正獨立者為上帝,故人的存在必有所依賴8。生命是精神與物質的結合,儘管精神重於物質,但次要也是必要,人生不能沒有物質條件支撐,精神文明也需物質文明維持。人為萬物之靈,萬物之靈能支配萬物,但無法離開萬物,這不僅是因物質需求,也是由於精神寄託,即使人在精神上無所追求,也不能處於無神的狀態,因為使用物質便要費神,做事既有利益也有意義,否則人不可能在營生之外更有所為,可見人為萬物之靈實為一項任務,這即是文明發展的潛力。萬物在世均有其價值及定位,然無一具有絕對或全面的重要性,此即萬物皆依賴其他以生,唯一獨立而不可或缺者乃是上帝,所以萬物各自的角色決定其地位,有地位即有價值,但價值無不有窮,人為萬物之靈,這是崇高的地位,卻非自由之身。萬物皆為上帝設定,愈有靈性愈有不知所措之感,因為萬事亦為上帝注定,而萬物之靈也無法知曉神意,所以精神強盛卻乏追求便有苦惱,於是文明可謂是人「無聊」之作,也就是無法自主的企圖所致之成就。文明或許不能使人偉大,但無所事事必使人毀滅,文明是人自救的事業(沒有文明則人無法生存),雖然文明創建者並無此感。文明成就愈高愈顯文明成就有限,這便是因文明不是一種發明而是一種發現,人既不是獨立的生命,自無可能創造什麼,文明其實是人被設計的自助活動,不論其成就如何皆可稱成功,因為人類不僅藉文明而存活,且由此更覺自尊。然而全能者必自主,「完成任務」是能力的證明也是能力有限的證明,文明是人所執行的天命,當然有其極限,即使過程順利也不表示結果如意,文明止境兼有成敗二意象9。
文明始於求生而至於求道,求生是為安全,求道近乎自由,求生與求道可以並進但不能常兼,安全與自由未必相違但難以兩得,此非本質性矛盾而是技術性衝突,蓋求道可於求生中進行,然有時必須犧牲性命,而絕對的自由必定安全無虞,然自由與安全皆未徹底時只能相權抉擇,這是在不完美的世界中因條件有限所致的相互排斥性(例如專業只能挑選而不能全功),不是其道本不相容,正如義利兩全不易,然可盡力成全。安全與自由無法兼備,這是現實的問題,不是理想的錯誤,而文明由安全的確保出發,進而尋求自由的價值,這使安全與自由的緊張性有增無減,因為文明的成就必使安全提升,然文明的要求是上進,為求安全而放棄自由是退卻,為求自由而犧牲安全卻可能是自殺,於是冒險性隨文明進化愈來愈大。如此,文明末世可能出於人因不欲冒險所致之發展停滯,也可能由於冒險失敗造成滅亡,而實際上前者才是主因,因為文明的末世是精神性沈淪,不是物質性毀壞,文明的價值觀不以成敗論英雄,若人以理想冒險而斷送生命,此乃文明的極致表現,可歌可泣而非可悲可歎。具體而言,文明的末世是因大眾化而起,大眾的立場相對於菁英是偏重安全,於是物質享受成為文明主旨,精神冒險廣受忽略,文明的末世竟是歌舞昇平的時代,這確是「美麗的誤會」。「保險」(insurance)自十四世紀出現,近來愈為興盛,「探險」(exploration)自古有之,至十九世紀盛極而衰,如今竟成休閒消遣的遊戲,文明的末世一方面是能力高強,另一方面卻是心態低俗,此時問題顯然不是欲振乏力而是自甘墮落。在飲食上,人從致力於「維生」進步至「享受」,由此卻發現盡情吃喝頗為「害身」,於是轉而注重「節制」,常有「忌口」之情,然放縱者自得其樂,孤芳自賞者則偏執病態,以致現代人不是太胖就是太瘦,對此文明進步的用處竟是在自我扭曲之時加以治療(減肥或整容),可見安全與自由的輕重不能恰當拿捏便將兩失,而生活大致安穩後不追求生命意義便是慢性自殺。
文明是開化的表現,開化是上進的行動,上進是改善的行為,而改善不可能達成至善,因為至善即是完美,而完美不含不完美,也就未經改善的過程或不具改進的問題。由此可知,「最佳」並非「完美」,「極致」隱含「極限」,文明的成就暗示其失敗,最高的文明呈現文明的困境。文明的要求是「止於至善」,這是永無停息的努力,然「不斷」不是「永恆」,文明的精神是光明偉大的,但文明的性質是美中不足的,「太好了」是超出一般的期望,而非「過於美好」,「好不可能過分」(It cannot be too good to be better.),因為事實永不如理想,而做到更好是人永久的責任,這便是原罪的作用。具有缺陷便無法臻於完美,求道之事若在,得道乃無可能,文明的理想性已顯示文明不能化為真理,這固然是永遠的缺憾,但也造成文明發展的無限性,使人高貴而感永恆。於是文明意義上的大功告成是文明止境的到來,以及世人由此所體會的「盡力」意境,這包括維持人類的最佳狀況而任憑上帝處置,同時絕無求善不成轉而為惡的念頭。簡言之,文明的極致成就是文明極限的發覺,理想上這應是人類的共識,實際上這只是智者的獨見,因為人類的原罪包括無力盡知與智愚有差。
第三節 文明發展的極限
文明為唯一,易言之,文明具有普世性,然則東方落後於西方而非各有其途,故東方文化不是文明末世時的另一選擇或出路。文明的進步是憑提升而非累積,雖然累積可能是提升的基礎,但量變未必造成質變,提升是有所追求所致,累積是目標不高或目的不明的預備工夫,其結果不可奢望。進化是突破現狀,然其成就畢竟有限,累積是擴充現有,而其勢似為無窮,但世間終非無限,文明不能永恆,故人須於累積中提升,不能以累積提升。世界文明即是人類文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類量大質一,世界文明是單一文明,不是眾文化之集體。文明是精神含意,不能以形式定義,精神取向為唯一,所以文明不應為數眾多,而是放諸四海皆準,東西文明或古今文明之稱只為歷史討論之便,非謂文明多元。文明一說本是價值解釋,價值有高低,但其道一以貫之,無有衝突(大價值與小價值的關係不是矛盾),故本質上文明即是世界(性)文明,也就是人類文明,以文明為多數實是邏輯性的錯誤。如此,任何一地的文明發展皆對世人有利,而最高文明的困境是全人類的危機10,文明的末世不呈現於世界各地,但其無望卻是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誠如「古文明」的下場皆為滅亡而非發揚光大,西方的沒落象徵的是文明的絕命而非東方的生機。此說不意謂世人的生存是休戚與共,而是表示人的價值是在於君子之舉,古代文明所以散佈分立乃因君子殊途同歸,現代文明所以全面停滯實因小人同惡相濟,文化交流在促進文明提升之時,亦使「同化」變成舉世的大眾化,於是小人凌駕大人,一處有憂,無處不患,這是「德不孤必有鄰」的反相,它又顯示唯有菁英主義才不致「兵敗如山倒」。
文明既不能臻於至善,世界大同乃無可能,因此文化多元的現象必然存在,於是文明的末世呈現價值混亂之局,事實上多元主義正是造成文明衰微的要因。多元主義伴隨真理信仰的沒落而興盛,此理在文明初期已經顯現,但其情直到文明末期方才普遍,因為求道是傳統文化的主流精神。文明的性質與目的舉世皆同,所以文明進化促使人類同化,然而因為文明終究無法完全成功,下層文化不再受上層文化導引或限制之後,不僅突然活動繁盛並且地位大升,這是文明末世的「反淘汰」怪象。「萬法歸一」既然不是人間實情,「多采多姿」似乎亦有其存在的意義,易言之,崇高性與豐富性若不能兼得,在輕重抉擇之餘也不必將次要者消滅。如此,文明極限來臨時單一性(真理為唯一)未能出現—然單一化的程度卻為史上最高—而多元性又不應加以推崇,在進退失據的情形下文明的末世當然是迷惘的時代,雖然大眾在此時的感受絕非如此。功虧一簣儘管是未竟全功但也不是徹底失敗,當進一步成就已無希望時「守成」便成為要務,放棄或破壞現有成就乃是自甘墮落的病態行為,所以文化多元性若不能隨文明進化而自然消失,也不須刻意將之消滅,但加以維護乃至提倡的作法則為變態之舉,因為「不能做到最好便表現最壞」其實是出於懷憂喪志心情的意氣風發行動。真理通貫眾說,真相超越萬象,一元論不反對多元現象,而多元論不接受一元取向,因為一元論在事實之上立言,而多元論在現象之中打轉;文明末世雖仍處於多元世界中,但其同質性遠勝於過去,若不知這是接近真理而難以得道的原罪性困境,反而以多元為最高層次,則是最高級的迷失,因為此一誤入歧途是基礎雄厚的錯亂。
文明是人類開化的過程,而開化的進行一方面是出於人的內省,另一方面則是由於對外的探索,所以文明初期不可能對於文明的取向已有清楚完備的構想,文明的意義或方向須經一段摸索的歷程之後乃能確定。質言之,「上古」是文明初探的時期,「古典」是文明定型的時期,「中古」是文明自反的時期,「現代」是文明再造的時期;如此,上古文明的首務是安定生活,古典文明的成就是建立標準,中古文明的立場是質疑古典,現代文明的事業是重振古典。然而現代不是古典的復興而已,文明的永恆價值在現代獲得確認與發揚之時,也於此顯露其「不夠完美」的本質性缺陷,這個不盡理想的情況是文明極致所反映的極限,可見現代性一旦確立即有崩解的危機11。文明的內在困境遲至其高度發展時始呈現,這是文明的原罪表現,它不意味歷史是「白忙一場」,而是「覺悟」所必須付出的代價與連帶的(意外)發現,雖令人有些失望,卻使人更加有知。事實上人不可能在文明初興之時即正確認定文明的性質或目標,若然則人在當時已為全知,又何須求道,此義是「上進者必有缺失」,所以「從錯誤中學習」是人無法逃脫的厄運,同時可知文明與天道雖精神一致但不能合一。
真理為通貫一切之道,文明若臻於至善則世界大同,否則不論各方觀點如何接近,必仍存有歧見,蓋「諸善通同而諸惡扞格」,完美無分種類,次佳即有分別,文明既止於「高度」而已,衝突之下的協調乃為文明末世的「盛況」。萬事萬物為上帝所造,且其高下輕重的地位不同,於是獨立與平等並無可能,和諧既非宇宙的真相也非事物的關係,社會祥和其實不是「富而好禮」,而是人際妥協的最佳成果。事實上當文明已無力上達時,真理的認知隨即衰落,而專業化分工代之興起,通識的探索變成訊息的溝通,求道的事業讓步於組織的工作,位高權重者缺乏卓見而媚於俗念,所以調和不同的立場成為大才,雖然面面俱到未必皆大歡喜,但這已是今人唯一的「全盛」觀念。文明雖圖所有人的開化(得道),但因各人資質不一,文明的追求是人類的極致境界而非眾人的平均佳境,因此文明不是一般人的成就而是菁英的成功,菁英主義以領導為尚而不以服務為本,然則民主政治一行文明便開始淪落,人權平等之制罔顧天命而背棄道義,此所謂「人眾者勝天」,實為「退而求其次」,以「全失」替代「獨得」,卻自慰「雖不滿意但可接受」。現實主義可能是文明的發現,然文明的精神終究是理想主義,英雄所見「略同」是英雄的不幸而非英雄之喜,文明的探討方法歷來是批判,全面性的協調顯然是文明的絕境,而常人無此憂慮更是其事的明證。
至善不是相對於至惡,因為惡是善的不足,若至惡存在則至善無法存在,所以不佳的改良固然可能,但由此臻於至善乃不可能;完美之對為不完美,不論次佳者如何接近完美(愈接近完美愈有不完美之慨),畢竟完美與不完美實為兩個不同的境域,無法交通。文明始於善的追求,有改善之需者必不完善,亦即含有本質性的缺陷,然則文明可謂出於原罪而企圖超越原罪,這是可貴的努力,但必止於困局。正是因此,文明雖無大功告成之日,卻可於困頓來臨之時發覺其所以然,易言之,人生的真相雖不可知但答案非不可得,問題的解決或無希望但其解答仍為有用,因為人不僅可於錯誤中學習,並且超越人力的事不需人煩惱,而現實的問題皆可憑現實的條件處理得宜。文明的終極境界是大同,大同可望不可及,於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成為新案,這是文明的挫敗,然凡人不知其實,反而以為大同由此可達,不論如何此情所示確是人類的極限已至,而其況既是注定之事也是末世最佳之法,更有啟示真理之效。由此可見,文明在功用上雖不是全能,但這卻是促進人求知求道的必要設計,而精神較物質可貴,知道比實行更為重要,故文明的缺陷竟是一種好處,原罪原來是善緣。
文明是人上進的呈現,文明求真求善求美,若相對於野蠻,文明便是開化,但文明的目標不止於開化,因為「人為萬物之靈」僅為文明得以發展的基礎條件而非最終成果。人能上達,這表示人有先天的優點,但又不盡良善,亦即人活在一個不完美的世界,而圖加以改善或自我提升。人有此警覺,即是原罪感,蓋理想的期望反映不理想的現狀,而人具有良心,所以不符理想者即被視為「惡」而非「相當好」,可見原罪出於原善,人有天心才自認有罪。惡為善之不足,正如「壞」是「不夠好」,若世間一切皆完善,則人不可能有善惡觀,反之一切皆不完善,人乃有分別善惡的意識。然完善即是至善,而不完善不是至惡,因為惡僅為善之不足而非獨立於善之外的本質6,善已然存在,純粹或徹底的惡不可能出現,故有惡即有善、有善即有惡,此非相對主義或二元觀,而是求道所以可能的因素,也就是「文明的環境」7。總之,原罪是人求好心切之下的感受,此種感受是「不太妙的」,它暗示「可為」是程度的問題,即使「大有可為」也不可能心想事成。
原罪的存在使文明又有希望又有絕境,因為文明要求無限的進化,而進化實為有限。原罪固然是人的自省心得,但若人有原罪,則人之外的萬事萬物亦必有其缺陷,簡言之,一旦人發現其自身並非完美,便可知世界為不完美,這與其說是由「人為萬物之靈」一義推論而得,無寧說是由「人非宇宙主宰」一事斷定,因為人既不完美則人必是被造之物而非造物主,而上帝為完美即表示上帝之外一切均不完美。原罪之感唯人有之,此因萬物無此靈性,所以人自覺不良便知世上無完善之事物,由此可見所謂原罪乃是人在失望之餘追本溯源的說法,原罪的真諦或廣義其實是「無所不在的缺陷」。文明以人為主角,人有原罪所以文明的原罪是無法盡善盡美,尤不幸者大眾的無知是人類之原罪,以致文明的絕境發生於最樂觀的時代,不僅不為人所知且因此惡化。
不論人對於原罪是否有所察覺,原罪的作用隨時隨地呈現於人的行為中,省思歷史尤可發現顯著之例,因為關乎人類社會整體之事更易顯示圓滿為無望。常人不知原罪為何物,但大都對其所處的環境感到不滿,而深思文明的人亦不可能對文明滿意,烏托邦(utopia)的提出便是此種心情的反映,然文明若有缺陷則無法真正改正,因為文明是上進向化的活力,它既有善意且有能力,而猶有不足之處,這必是本來(先天性)的缺失,永不能克服。史上的烏托邦思想皆非完美國度的設想,而是因應現實所提出的局部改良意見,或是避世心態的自白,這是對於人間不可能化為淨土的承認,然則烏托邦式的改革建議即無可能成功,因為文明的缺陷既是原罪所致,一事可以改正則萬事皆可以改正,片面的改造只是聊表心意而非希望無窮,難怪烏托邦主張歷來不斷被提出,亦即不斷被放棄。天堂與地獄的觀念也是原罪感受的間接表達,蓋天堂與地獄之說暗示世間為「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之地,此域雖不盡善但也非至惡,也就是有缺陷的世界,於是天堂為人所期乃因理想,而地獄為人所畏則因邪念,因為沈淪墮落本是人可以防止的事,自我放縱者其實「放不開」。一般侈談天堂與地獄的人對於人世的改善實心力無多,這固然是因其缺乏盡力負責的精神,但也含有「事不可為」的無奈,而這確非無理,所以期望來世是自然的事,而好論此事者大約善多於惡,畢竟其說猶有善惡報應的道德意念。天堂與地獄的信徒大部分偏重天堂而忽略地獄,因為此輩必自信(自我暗示)能上天堂,無知與自私使其以地獄一說勸善的努力不強,何況對於現實的失望使人認為淑世的意義甚為有限。在社會改良的問題上,相對於教徒「悲觀之下的樂觀」,務實而不信神的人表現了「樂觀之中的悲觀」,功利主義者所號召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greatest number),顯然是棄「質」就「量」的建議,於此完美已非目標,社會性的正義取代公道,其說默認原罪,卻連帶否認「原善」,以致造成「多數暴力」,加速文明的滅亡。由此可見,文明的沒落雖本是文明的原罪,但對此缺乏正確認知而推展錯誤的政策者,須負毀滅文明的罪名。
人無法獨立,不僅個人無法獨立,人類亦無法獨立,因為人非創造者或主宰,真正獨立者為上帝,故人的存在必有所依賴8。生命是精神與物質的結合,儘管精神重於物質,但次要也是必要,人生不能沒有物質條件支撐,精神文明也需物質文明維持。人為萬物之靈,萬物之靈能支配萬物,但無法離開萬物,這不僅是因物質需求,也是由於精神寄託,即使人在精神上無所追求,也不能處於無神的狀態,因為使用物質便要費神,做事既有利益也有意義,否則人不可能在營生之外更有所為,可見人為萬物之靈實為一項任務,這即是文明發展的潛力。萬物在世均有其價值及定位,然無一具有絕對或全面的重要性,此即萬物皆依賴其他以生,唯一獨立而不可或缺者乃是上帝,所以萬物各自的角色決定其地位,有地位即有價值,但價值無不有窮,人為萬物之靈,這是崇高的地位,卻非自由之身。萬物皆為上帝設定,愈有靈性愈有不知所措之感,因為萬事亦為上帝注定,而萬物之靈也無法知曉神意,所以精神強盛卻乏追求便有苦惱,於是文明可謂是人「無聊」之作,也就是無法自主的企圖所致之成就。文明或許不能使人偉大,但無所事事必使人毀滅,文明是人自救的事業(沒有文明則人無法生存),雖然文明創建者並無此感。文明成就愈高愈顯文明成就有限,這便是因文明不是一種發明而是一種發現,人既不是獨立的生命,自無可能創造什麼,文明其實是人被設計的自助活動,不論其成就如何皆可稱成功,因為人類不僅藉文明而存活,且由此更覺自尊。然而全能者必自主,「完成任務」是能力的證明也是能力有限的證明,文明是人所執行的天命,當然有其極限,即使過程順利也不表示結果如意,文明止境兼有成敗二意象9。
文明始於求生而至於求道,求生是為安全,求道近乎自由,求生與求道可以並進但不能常兼,安全與自由未必相違但難以兩得,此非本質性矛盾而是技術性衝突,蓋求道可於求生中進行,然有時必須犧牲性命,而絕對的自由必定安全無虞,然自由與安全皆未徹底時只能相權抉擇,這是在不完美的世界中因條件有限所致的相互排斥性(例如專業只能挑選而不能全功),不是其道本不相容,正如義利兩全不易,然可盡力成全。安全與自由無法兼備,這是現實的問題,不是理想的錯誤,而文明由安全的確保出發,進而尋求自由的價值,這使安全與自由的緊張性有增無減,因為文明的成就必使安全提升,然文明的要求是上進,為求安全而放棄自由是退卻,為求自由而犧牲安全卻可能是自殺,於是冒險性隨文明進化愈來愈大。如此,文明末世可能出於人因不欲冒險所致之發展停滯,也可能由於冒險失敗造成滅亡,而實際上前者才是主因,因為文明的末世是精神性沈淪,不是物質性毀壞,文明的價值觀不以成敗論英雄,若人以理想冒險而斷送生命,此乃文明的極致表現,可歌可泣而非可悲可歎。具體而言,文明的末世是因大眾化而起,大眾的立場相對於菁英是偏重安全,於是物質享受成為文明主旨,精神冒險廣受忽略,文明的末世竟是歌舞昇平的時代,這確是「美麗的誤會」。「保險」(insurance)自十四世紀出現,近來愈為興盛,「探險」(exploration)自古有之,至十九世紀盛極而衰,如今竟成休閒消遣的遊戲,文明的末世一方面是能力高強,另一方面卻是心態低俗,此時問題顯然不是欲振乏力而是自甘墮落。在飲食上,人從致力於「維生」進步至「享受」,由此卻發現盡情吃喝頗為「害身」,於是轉而注重「節制」,常有「忌口」之情,然放縱者自得其樂,孤芳自賞者則偏執病態,以致現代人不是太胖就是太瘦,對此文明進步的用處竟是在自我扭曲之時加以治療(減肥或整容),可見安全與自由的輕重不能恰當拿捏便將兩失,而生活大致安穩後不追求生命意義便是慢性自殺。
文明是開化的表現,開化是上進的行動,上進是改善的行為,而改善不可能達成至善,因為至善即是完美,而完美不含不完美,也就未經改善的過程或不具改進的問題。由此可知,「最佳」並非「完美」,「極致」隱含「極限」,文明的成就暗示其失敗,最高的文明呈現文明的困境。文明的要求是「止於至善」,這是永無停息的努力,然「不斷」不是「永恆」,文明的精神是光明偉大的,但文明的性質是美中不足的,「太好了」是超出一般的期望,而非「過於美好」,「好不可能過分」(It cannot be too good to be better.),因為事實永不如理想,而做到更好是人永久的責任,這便是原罪的作用。具有缺陷便無法臻於完美,求道之事若在,得道乃無可能,文明的理想性已顯示文明不能化為真理,這固然是永遠的缺憾,但也造成文明發展的無限性,使人高貴而感永恆。於是文明意義上的大功告成是文明止境的到來,以及世人由此所體會的「盡力」意境,這包括維持人類的最佳狀況而任憑上帝處置,同時絕無求善不成轉而為惡的念頭。簡言之,文明的極致成就是文明極限的發覺,理想上這應是人類的共識,實際上這只是智者的獨見,因為人類的原罪包括無力盡知與智愚有差。
第三節 文明發展的極限
文明為唯一,易言之,文明具有普世性,然則東方落後於西方而非各有其途,故東方文化不是文明末世時的另一選擇或出路。文明的進步是憑提升而非累積,雖然累積可能是提升的基礎,但量變未必造成質變,提升是有所追求所致,累積是目標不高或目的不明的預備工夫,其結果不可奢望。進化是突破現狀,然其成就畢竟有限,累積是擴充現有,而其勢似為無窮,但世間終非無限,文明不能永恆,故人須於累積中提升,不能以累積提升。世界文明即是人類文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類量大質一,世界文明是單一文明,不是眾文化之集體。文明是精神含意,不能以形式定義,精神取向為唯一,所以文明不應為數眾多,而是放諸四海皆準,東西文明或古今文明之稱只為歷史討論之便,非謂文明多元。文明一說本是價值解釋,價值有高低,但其道一以貫之,無有衝突(大價值與小價值的關係不是矛盾),故本質上文明即是世界(性)文明,也就是人類文明,以文明為多數實是邏輯性的錯誤。如此,任何一地的文明發展皆對世人有利,而最高文明的困境是全人類的危機10,文明的末世不呈現於世界各地,但其無望卻是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誠如「古文明」的下場皆為滅亡而非發揚光大,西方的沒落象徵的是文明的絕命而非東方的生機。此說不意謂世人的生存是休戚與共,而是表示人的價值是在於君子之舉,古代文明所以散佈分立乃因君子殊途同歸,現代文明所以全面停滯實因小人同惡相濟,文化交流在促進文明提升之時,亦使「同化」變成舉世的大眾化,於是小人凌駕大人,一處有憂,無處不患,這是「德不孤必有鄰」的反相,它又顯示唯有菁英主義才不致「兵敗如山倒」。
文明既不能臻於至善,世界大同乃無可能,因此文化多元的現象必然存在,於是文明的末世呈現價值混亂之局,事實上多元主義正是造成文明衰微的要因。多元主義伴隨真理信仰的沒落而興盛,此理在文明初期已經顯現,但其情直到文明末期方才普遍,因為求道是傳統文化的主流精神。文明的性質與目的舉世皆同,所以文明進化促使人類同化,然而因為文明終究無法完全成功,下層文化不再受上層文化導引或限制之後,不僅突然活動繁盛並且地位大升,這是文明末世的「反淘汰」怪象。「萬法歸一」既然不是人間實情,「多采多姿」似乎亦有其存在的意義,易言之,崇高性與豐富性若不能兼得,在輕重抉擇之餘也不必將次要者消滅。如此,文明極限來臨時單一性(真理為唯一)未能出現—然單一化的程度卻為史上最高—而多元性又不應加以推崇,在進退失據的情形下文明的末世當然是迷惘的時代,雖然大眾在此時的感受絕非如此。功虧一簣儘管是未竟全功但也不是徹底失敗,當進一步成就已無希望時「守成」便成為要務,放棄或破壞現有成就乃是自甘墮落的病態行為,所以文化多元性若不能隨文明進化而自然消失,也不須刻意將之消滅,但加以維護乃至提倡的作法則為變態之舉,因為「不能做到最好便表現最壞」其實是出於懷憂喪志心情的意氣風發行動。真理通貫眾說,真相超越萬象,一元論不反對多元現象,而多元論不接受一元取向,因為一元論在事實之上立言,而多元論在現象之中打轉;文明末世雖仍處於多元世界中,但其同質性遠勝於過去,若不知這是接近真理而難以得道的原罪性困境,反而以多元為最高層次,則是最高級的迷失,因為此一誤入歧途是基礎雄厚的錯亂。
文明是人類開化的過程,而開化的進行一方面是出於人的內省,另一方面則是由於對外的探索,所以文明初期不可能對於文明的取向已有清楚完備的構想,文明的意義或方向須經一段摸索的歷程之後乃能確定。質言之,「上古」是文明初探的時期,「古典」是文明定型的時期,「中古」是文明自反的時期,「現代」是文明再造的時期;如此,上古文明的首務是安定生活,古典文明的成就是建立標準,中古文明的立場是質疑古典,現代文明的事業是重振古典。然而現代不是古典的復興而已,文明的永恆價值在現代獲得確認與發揚之時,也於此顯露其「不夠完美」的本質性缺陷,這個不盡理想的情況是文明極致所反映的極限,可見現代性一旦確立即有崩解的危機11。文明的內在困境遲至其高度發展時始呈現,這是文明的原罪表現,它不意味歷史是「白忙一場」,而是「覺悟」所必須付出的代價與連帶的(意外)發現,雖令人有些失望,卻使人更加有知。事實上人不可能在文明初興之時即正確認定文明的性質或目標,若然則人在當時已為全知,又何須求道,此義是「上進者必有缺失」,所以「從錯誤中學習」是人無法逃脫的厄運,同時可知文明與天道雖精神一致但不能合一。
真理為通貫一切之道,文明若臻於至善則世界大同,否則不論各方觀點如何接近,必仍存有歧見,蓋「諸善通同而諸惡扞格」,完美無分種類,次佳即有分別,文明既止於「高度」而已,衝突之下的協調乃為文明末世的「盛況」。萬事萬物為上帝所造,且其高下輕重的地位不同,於是獨立與平等並無可能,和諧既非宇宙的真相也非事物的關係,社會祥和其實不是「富而好禮」,而是人際妥協的最佳成果。事實上當文明已無力上達時,真理的認知隨即衰落,而專業化分工代之興起,通識的探索變成訊息的溝通,求道的事業讓步於組織的工作,位高權重者缺乏卓見而媚於俗念,所以調和不同的立場成為大才,雖然面面俱到未必皆大歡喜,但這已是今人唯一的「全盛」觀念。文明雖圖所有人的開化(得道),但因各人資質不一,文明的追求是人類的極致境界而非眾人的平均佳境,因此文明不是一般人的成就而是菁英的成功,菁英主義以領導為尚而不以服務為本,然則民主政治一行文明便開始淪落,人權平等之制罔顧天命而背棄道義,此所謂「人眾者勝天」,實為「退而求其次」,以「全失」替代「獨得」,卻自慰「雖不滿意但可接受」。現實主義可能是文明的發現,然文明的精神終究是理想主義,英雄所見「略同」是英雄的不幸而非英雄之喜,文明的探討方法歷來是批判,全面性的協調顯然是文明的絕境,而常人無此憂慮更是其事的明證。
至善不是相對於至惡,因為惡是善的不足,若至惡存在則至善無法存在,所以不佳的改良固然可能,但由此臻於至善乃不可能;完美之對為不完美,不論次佳者如何接近完美(愈接近完美愈有不完美之慨),畢竟完美與不完美實為兩個不同的境域,無法交通。文明始於善的追求,有改善之需者必不完善,亦即含有本質性的缺陷,然則文明可謂出於原罪而企圖超越原罪,這是可貴的努力,但必止於困局。正是因此,文明雖無大功告成之日,卻可於困頓來臨之時發覺其所以然,易言之,人生的真相雖不可知但答案非不可得,問題的解決或無希望但其解答仍為有用,因為人不僅可於錯誤中學習,並且超越人力的事不需人煩惱,而現實的問題皆可憑現實的條件處理得宜。文明的終極境界是大同,大同可望不可及,於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成為新案,這是文明的挫敗,然凡人不知其實,反而以為大同由此可達,不論如何此情所示確是人類的極限已至,而其況既是注定之事也是末世最佳之法,更有啟示真理之效。由此可見,文明在功用上雖不是全能,但這卻是促進人求知求道的必要設計,而精神較物質可貴,知道比實行更為重要,故文明的缺陷竟是一種好處,原罪原來是善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