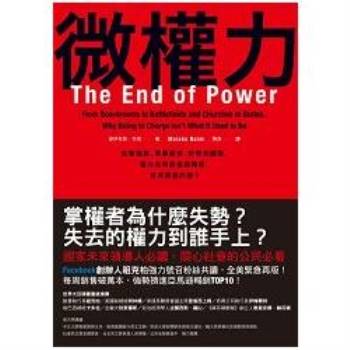這本書談的是權力。
更準確地說,此書講述權力——令他人做事或令其停止進行的能力——正在經歷的本質變化具有歷史意義,足以改變世界。
權力正在流散,掌權已久的大玩家正面對越來越多後起之秀與小型勢力的挑戰。掌權者在行使權力時也正面對更多的限制。
我們討論權力演變時卻常常誤解,甚至輕視其變化的幅度、性質以及其延伸的後果。我們很容易受誘導,只著眼於網際網路及新科技帶來的影響,只著眼於權力如何由一方流向另一方,或者只專注解答「文化軟實力」是否可以取代「軍事硬實力」等等問題。這些討論的觀點角度並不全面,甚至會妨礙我們明白真正導致現今權力取得、行使、維持及瓦解的基本驅動力。
我們知道權力正由勞動力轉移至腦力;由北轉向南,由西轉向東;從舊型企業巨獸轉向靈活變通的新創公司;從穩固的獨裁者轉向廣場上的人民、網路世界。單單只道出權力正由一個大陸或國家流向另一個,或者正傾瀉到新的參與者身上,都不足夠。權力正在經歷更為根本性的突變,這現象仍未受到廣泛關注更遑論理解。對立的國家、企業、政黨、社會運動、機構或獨立領袖縱然仍跟過去一樣你搶我鬥地爭奪和維持權力,但權力本身正在消散。
權力正在衰退。
簡單來說,權力可以換得的成果已日漸式微。在二十一世紀,權力更容易獲得,卻更難行使,並且更容易失去。無論在會議室、戰地抑或是網路空間,權力鬥爭一如往常激烈,可獲得的回報卻在遞減。這些殘酷的爭鬥掩蓋了權力本身正在加速衰敗的事實。若想要了解一個改造二十一世紀的最重要趨勢,關鍵就是去理解權力如何失去其價值,並且去面對這情況的艱鉅挑戰。
這並不是在說權力已經徹底消失,或是現在已經沒有人權傾天下。美國總統、中國國家主席、摩根大通或殼牌石油總裁、紐約時報執行主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首腦、教宗等人仍坐擁極大權力,可是卻都遜於上一任。上一代的領袖們不只面對的挑戰者及競爭者較少,行使權力時亦較少遇上限制,譬如公民運動、環球市場及媒體監督。是以,今天的當權者一旦做出錯誤決定,通常要較其上一任更立即地付出代價,而且代價更大。他們重新打造行使權力的方式以因應新現實,引發的連鎖效應觸及人際互動的每一層面。
權力的衰退正在改變世界。
這本書的目的就是要證明以上的大膽推論。
在今天,即使國家之間爆發戰爭,軍事大國進攻的力道也已大不如前。強弱懸殊的戰爭越來越常見,大型軍隊經常要面對小型非傳統的軍事力量,如叛亂分子、分離分子及民兵策動的攻勢。軍事力量較弱一方獲勝的次數也在增加。哈佛大學一項卓越的研究指出,一八〇〇年至一八四九年間發生的強弱懸殊戰爭裡,兵力及武器裝備較弱的一方實現戰略目標的比例只得百分之十二。情況在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九八年間出現轉變,弱勢一方報捷的比例急升至百分之五十五。受多種因素影響,敵對雙方的政治及軍事戰略角力成為左右勝負的主因,軍事實力的差距反而顯得沒那麼重要。因此,兵力強大、船堅砲利的國家無法確保軍事優勢。推動這轉變的主因是弱勢一方低成本重傷亡的攻擊能力大增,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中使用的簡陋爆炸裝置便是很好的例子。一名駐阿富汗的美國海軍將領估計,其小隊中百分之八十的人命傷亡都是由這些製作簡單的爆炸裝置導致的;在伊拉克戰爭中,這種裝置造成盟軍三分之二的死傷。就算美國國防部不惜斥鉅資採取應對措施,包括斥資一百七十億美元購置五萬台無線電頻率干擾器,以期干擾簡易爆炸裝置的遙控引爆設備(手機、車庫門開關器),這些裝置的殺傷力還是略勝一籌。
獨裁者及黨派領袖的權力亦開始衰落,他們的數目也在減少。在一九七七年,全球共有八十九個獨裁國家,到了二〇一一年,數字已銳減至二十二個。時至今日,世界上有超過一半的人口活在民主的土地上。「阿拉伯之春」的震盪傳揚至世界各個角落,包括清廉選舉尚未穩定之地,以及當權者或政權希望永久統治的區域。有些不民主地區也容許不同的黨派,今天少數黨派代表席位比一九八〇年代大幅增加了三倍。每一處的政黨領袖都曾遭遇挫敗,因為他們的競爭對手不再是密室內定的候選人。在成熟的民主體制中,約有半數的主要政黨在選舉黨內領導者時會採用黨內初選或其他代表性的選舉方式,希望可以讓一般黨員有更多選擇。各地的政治領袖都會告訴你,他們已經無法再像前人般理所當然地控制選舉及發號施令。
這趨勢也席捲商界。毋庸置疑,財富集中在一小撮人手中,富者越富,腰纏萬貫的富人會利用其財勢獲取政治權力。這趨勢令人擔憂,亦不為世俗接受,但並不是形塑企業領袖和富有投資者權力運作的唯一力量。
事實證明,即使美國最富有的百分之一人口亦無法躲開財富、權力和地位突如其來的變化。面對收入不平等,經濟大衰退發揮了矯正效應,尤其嚴重影響富人的收入。美國國稅局數據顯示,在二〇〇七年至二〇〇九年間,收入達一百萬美元或以上的美國人數急跌四成至二十三萬六千八百八十三人,整體收入也銳挫近五成;跌幅遠高於總收入為五萬美元或以下的美國人,後者同期跌幅不足百分之二。當然,這並不能說明在以美國為首的先進民主國家中,貧富差距沒有顯著加劇,事實恰好相反,收入不均的現象正在急速惡化。但這現況也不應阻礙我們了解不少富裕人士和家庭在經濟危機中遭受的打擊,他們的財富和經濟實力確實顯著下跌。個人收入與財富已不再是獲取權力的唯一途徑。率領大型企業的管理階層往往比那些「純粹」的富豪享有更多權力。這些企業領袖現在的收入亦遠較以往豐厚,惟其任期卻越來越短。一九九二年,美國財富五百強企業的董事長在下一個五年中連任的機會是百分之三十六,一九九八年下降至百分之二十五。二〇〇五年,美國企業董事長的平均任期已縮短至六年,而這趨勢是全球性的。二〇一一年,全球最大兩千五百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長離職率是百分之十四點四;即使以企業管理層穩定見稱的日本,大企業董事長的非自願離職人數在二〇〇八年也增加了三倍。
企業本身也遭逢同樣命運。一九八〇年,傲居行業前五名的美國企業在五年後跌出五強的可能性僅為百分之十,但是在二十年後可能性已上升到百分之二十五。環顧今天美國和全球五百強企業排行榜,最近十年才上榜的企業數量足證,相對的後起之秀正在取代傳統企業巨頭的位置。在金融領域,銀行正在喪失權力和影響力,被新興、靈活的對沖基金取代:在二〇一〇年下半年,全球經濟陷入嚴重危機,排名前十名的對沖基金(當中多數不為公眾所知)賺得的利潤比全球六大銀行的總盈利還要高。當中最大的對沖基金管理的資金達到天文數字,賺取豐厚利潤,但其員工總數不過幾百名。
與此同時,企業面對令名譽、收入和價值受創的「品牌災難」時也更脆弱。一項研究顯示,在過去二十年間,全球最知名品牌母公司在五年內經歷品牌災難的風險由百分之二十急升百分之八十二。英國石油公司、老虎伍茲及梅鐸新聞集團的財富都曾因不利傳聞在一夜之間大幅萎縮。
這些趨勢甚至已從傳統的權力舞台——戰場、政界和商界——進入慈善界、宗教界、文化界以及個人領域。
慈善事業不再是大型基金會、社會團體和國際組織的專利,已被各式小型基金會進軍,捐助方式也起了顯著變化,現在不少捐助者已繞過傳統的慈善機構,直接提供支援給受助者。一九九〇年代,美國個人及機構投進的國際捐助增加了三倍,該數字在一九九八年至二〇〇七年又再升一倍至三百九十六億美元──比世界銀行的年度捐助額多出一半。美國在一九七五年有四萬家基金會,到了二〇一二年數量已逾七萬六千家。演員、運動員及慈善活動知名常客,如歐普拉、柯林頓、安潔莉娜裘莉和波諾,都為慈善捐款注入了強大動力。當然,比爾蓋茲夫婦、巴菲特和索羅斯等人捐助成立的大型基金會,也在顛覆大型慈善業機構主導的傳統運作模式。數以千計的科技新貴及對沖基金經理人快速投身慈善事業,投入的金額更是過去難以想像。「公益創投」興起,催生了專門為公益資金用途提供建議、支援和集資管道的新產業。
我知道,要爭辯權力正在衰退實與當下普遍的認知相悖——我們仍生活在一個權力趨向更集中的時代,掌權者的權力比以往更強盛更牢不可破。很多人確實認為權力有如財富:錢能生錢,越有錢越多錢;權也能生權,越有權越多權。從這角度看,權力和財富集中的循環可視為人類歷史的主要驅動力。世上誠然仍有許多坐擁巨大權力的機構及人士,他們的權力相當穩固;但本書在稍後的章節會證明,以這稜鏡觀看世界無法看到一個非常重要的面貌:事物正在變化的法則。
我們將看到,權力不僅簡單從一部分具有影響力的當權者手中轉移到另一方手中,而是權力本質有了更徹底和複雜的轉變。權力變得更垂手可得,事實上,在當今世界擁有權力的人的確更多了;可是權力的使用範圍縮小了。即便奪得了權力,權力的行使卻越來越難。我們即將探討的改變造就了不同領域的創新者和新秀,但不幸的是,受惠者名單也包括海盜、恐怖分子、叛亂分子、駭客、走私販、偽造者以及網路罪犯。這些改變也給支持民主的社會行動者帶來機會——包括議題狹隘與極端的偏激政治團體——不論在民主或專制國家,他們都可以透過嶄新方式贏得政治影響力,繞過或打破現存政治體制的嚴謹內部結構。二〇一一年夏天,為數不多的馬來西亞社運人士決定仿效馬德里太陽門廣場的「憤怒者」運動,占領了吉隆坡獨立廣場。一石激起千層浪,當時幾乎無人能預料這行動會激發性質相近的「占領華爾街」運動,浪潮席捲過全球近兩千六百座城市。
即使一連串的「占領運動」並未引發任何實質上的政治變化,但其影響值得注目。誠如一九六〇年代編年史學者季特林指出:「公共話題轉向在那久遠的六〇年代需時三年才可體現,話題如殘酷的戰爭、貧困的生活、低劣的政治、被壓抑的民主諾言……但是在二〇一一年,這只需要三星期。」就速度、影響力、創新的橫向組織形式而言,「占領運動」的發展在在反映出,傳統政黨過去掌控了社會成員表達不滿、希望和訴求的管道,如今他們的壟斷地位遭到蠶食。在中東地區,始於二〇一〇年的阿拉伯之春不但沒有顯露疲態,反而繼續蔓延至全球——各個專制政權都感受到其引發的迴響。
在地緣政治方面,小腳色——小國或非國家——亦獲得新機遇,可以否決、干預、引導和阻礙強國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多國組織的共同決策。隨手舉些例子:波蘭否決了歐盟的低碳經濟路線圖;土耳其和巴西破壞了強國與伊朗就核問題的談判;維基解密泄露美國外交機密;蓋茲基金會挑戰世界衛生組織在打擊瘧疾的領導地位。類似例子在貿易、氣候變遷及許多其他議題的全球談判越來越常見。
這些新崛起而且漸露頭角的「小型參與者」每一個都不盡相同,它們所在的領域南轅北轍,但仍有共同處:它們都不再需要透過規模、範疇、歷史或固有傳統發揮作用。它們象徵一種新權力的崛起,我們不妨將其稱為「微權力」,而這種權力在過去並沒有多少發揮空間。本書想爭辯的就是在今時今日,改變世界的已越來越不是大型當權者之間的競爭,而是微權力的崛起,以及它們挑戰當權者的能力。
權力的衰退並不代表當權者就此消失,而是大型政府、大型軍隊、大型企業和大型學府將面對前所未有的束縛和限制,但是它們仍然會躋身權力階層,其一舉一動仍足以左右大局,只是影響力不如它們自身渴望的重大,也不如它們預期的多。儘管當權者弱化看起來純粹是件好事(畢竟權力衍生出腐敗,不是嗎?),它們被降級卻可能引起複雜的社會動盪、混亂和運作癱瘓的問題。
我會在接下來的章節告訴你權力如何加速衰退,儘管坊間看到的是相反的趨勢,像是「巨者回歸」,上一個十年末期出現的「大到不能倒」,中美兩國軍費穩步增加、全球收入和財富差距日益懸殊。相較起現時政策制定者及分析家所聚焦的表面趨勢及發展,權力衰退才是眼下更為重要及影響深遠的議題。權力衰退並不特別由互聯網驅使,亦不可概括地訴諸資訊科技進步。互聯網及其他科技毋庸置疑正在改變政治、社會運動、商業活動,當然也包括權力的本質,但是這個基本角色太常被誇大及誤解。嶄新的資訊科技只是工具,而工具要發揮影響力,需要的是使用者。相對的,使用者在操作工具時要有目標、方向及動力。臉書、推特及簡訊強化了阿拉伯之春示威者的力量,可是實際上驅動群眾走上街頭的卻是國內外的情勢,不是那些供人使用的資訊工具。參與推翻埃及總統穆巴拉克的示威者達數百萬人,但就算在運動最高峰,臉書上公認有助於鼓動示威者的專頁只有三十五萬名粉絲。最近一項研究顯示,在埃及與利比亞起義期間,在推特點擊相關資料連結的用戶,百分之七十五都不是來自阿拉伯國家。美國和平研究所也曾研究阿拉伯之春期間的推特用戶使用模式,該所總結:新媒體「不論在國內的集體行動或地區性的傳播,都不見其擔當重要角色。」
此外,我們亦不應將權力衰退與當下最「時興的」權力轉移混為一談:自從美國走疲、中國崛起不證自明地被視為這時代地緣政治變局的關鍵,分析家與評論家便熱衷於剖析。估算歐洲衰弱及金磚國家崛起會伴隨帶來什麼情況、「其餘」的國家又會如何,就成為專家與業餘指揮家最熱門的猜謎遊戲。但是國家間的競爭不斷在變(競爭一直以來都在變),只把目光釘死在哪個國家走下坡、哪個國家得勢,在根本上就失了焦,非常危險。因為每一批新贏家都會對一項發現傷透腦筋,那就是未來每個掌權者都會察覺,他們的自由度與行使權力的效力大抵會遭遇前人未遇過的限制。
權力的圍牆倒下,打通了新手通往權力世界的大門,改變了人類重要領域的競爭本質。
這些新手是我們早前提及的微權力——一種全新的權力:並不巨大,不具壓倒性;大型、專業機構的權力通常有強制性,但這股相對權力可以抗衡、限制大玩家的操控。
這種權力來自創新及進取,是,但也來自新延伸的技術領域如否決、拖延、牽制及干擾。這些在戰爭期間常被反動者使用的典型策略,如今已擴展至許多其他領域而且行之有效。不單只對積極進取的創新者打開新視野,也包括極端分子、分離分子、各種非以爭取整體社會進步為目標的人。這些新參與者的數量正在明顯地迅速增長,如果我們繼續無視權力衰退不做補救,後果將不堪設想。
我們迫切需要理解及正視權力衰退的本質和其種種後果。即使上述風險並未造成無政府狀態等混亂,顯然已干預了我們處理這時代重大問題的能力。從氣候變遷、核擴散、經濟危機、資源枯竭、疾病、全球「最底層十億人」的長期貧窮問題、恐怖主義、走私、網路犯罪等等,現今世界面臨的複雜問題與日俱增,都需要更多來自不同背景的各方人士攜手解決。權力的衰退在以下角度看是個令人鼓舞的趨勢,因為它為全球的新投機事業、新企業以及新聲音創造更多空間與機會,但會為穩定性帶來危險。我們如何在歡迎多元聲音、意見、新概念、創新之際,不讓情況嚴重癱瘓,導致累積的成果毁於一旦?理解權力的衰退將是我們身處在重生世界中找尋出路所邁出的第一步。
更準確地說,此書講述權力——令他人做事或令其停止進行的能力——正在經歷的本質變化具有歷史意義,足以改變世界。
權力正在流散,掌權已久的大玩家正面對越來越多後起之秀與小型勢力的挑戰。掌權者在行使權力時也正面對更多的限制。
我們討論權力演變時卻常常誤解,甚至輕視其變化的幅度、性質以及其延伸的後果。我們很容易受誘導,只著眼於網際網路及新科技帶來的影響,只著眼於權力如何由一方流向另一方,或者只專注解答「文化軟實力」是否可以取代「軍事硬實力」等等問題。這些討論的觀點角度並不全面,甚至會妨礙我們明白真正導致現今權力取得、行使、維持及瓦解的基本驅動力。
我們知道權力正由勞動力轉移至腦力;由北轉向南,由西轉向東;從舊型企業巨獸轉向靈活變通的新創公司;從穩固的獨裁者轉向廣場上的人民、網路世界。單單只道出權力正由一個大陸或國家流向另一個,或者正傾瀉到新的參與者身上,都不足夠。權力正在經歷更為根本性的突變,這現象仍未受到廣泛關注更遑論理解。對立的國家、企業、政黨、社會運動、機構或獨立領袖縱然仍跟過去一樣你搶我鬥地爭奪和維持權力,但權力本身正在消散。
權力正在衰退。
簡單來說,權力可以換得的成果已日漸式微。在二十一世紀,權力更容易獲得,卻更難行使,並且更容易失去。無論在會議室、戰地抑或是網路空間,權力鬥爭一如往常激烈,可獲得的回報卻在遞減。這些殘酷的爭鬥掩蓋了權力本身正在加速衰敗的事實。若想要了解一個改造二十一世紀的最重要趨勢,關鍵就是去理解權力如何失去其價值,並且去面對這情況的艱鉅挑戰。
這並不是在說權力已經徹底消失,或是現在已經沒有人權傾天下。美國總統、中國國家主席、摩根大通或殼牌石油總裁、紐約時報執行主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首腦、教宗等人仍坐擁極大權力,可是卻都遜於上一任。上一代的領袖們不只面對的挑戰者及競爭者較少,行使權力時亦較少遇上限制,譬如公民運動、環球市場及媒體監督。是以,今天的當權者一旦做出錯誤決定,通常要較其上一任更立即地付出代價,而且代價更大。他們重新打造行使權力的方式以因應新現實,引發的連鎖效應觸及人際互動的每一層面。
權力的衰退正在改變世界。
這本書的目的就是要證明以上的大膽推論。
在今天,即使國家之間爆發戰爭,軍事大國進攻的力道也已大不如前。強弱懸殊的戰爭越來越常見,大型軍隊經常要面對小型非傳統的軍事力量,如叛亂分子、分離分子及民兵策動的攻勢。軍事力量較弱一方獲勝的次數也在增加。哈佛大學一項卓越的研究指出,一八〇〇年至一八四九年間發生的強弱懸殊戰爭裡,兵力及武器裝備較弱的一方實現戰略目標的比例只得百分之十二。情況在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九八年間出現轉變,弱勢一方報捷的比例急升至百分之五十五。受多種因素影響,敵對雙方的政治及軍事戰略角力成為左右勝負的主因,軍事實力的差距反而顯得沒那麼重要。因此,兵力強大、船堅砲利的國家無法確保軍事優勢。推動這轉變的主因是弱勢一方低成本重傷亡的攻擊能力大增,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中使用的簡陋爆炸裝置便是很好的例子。一名駐阿富汗的美國海軍將領估計,其小隊中百分之八十的人命傷亡都是由這些製作簡單的爆炸裝置導致的;在伊拉克戰爭中,這種裝置造成盟軍三分之二的死傷。就算美國國防部不惜斥鉅資採取應對措施,包括斥資一百七十億美元購置五萬台無線電頻率干擾器,以期干擾簡易爆炸裝置的遙控引爆設備(手機、車庫門開關器),這些裝置的殺傷力還是略勝一籌。
獨裁者及黨派領袖的權力亦開始衰落,他們的數目也在減少。在一九七七年,全球共有八十九個獨裁國家,到了二〇一一年,數字已銳減至二十二個。時至今日,世界上有超過一半的人口活在民主的土地上。「阿拉伯之春」的震盪傳揚至世界各個角落,包括清廉選舉尚未穩定之地,以及當權者或政權希望永久統治的區域。有些不民主地區也容許不同的黨派,今天少數黨派代表席位比一九八〇年代大幅增加了三倍。每一處的政黨領袖都曾遭遇挫敗,因為他們的競爭對手不再是密室內定的候選人。在成熟的民主體制中,約有半數的主要政黨在選舉黨內領導者時會採用黨內初選或其他代表性的選舉方式,希望可以讓一般黨員有更多選擇。各地的政治領袖都會告訴你,他們已經無法再像前人般理所當然地控制選舉及發號施令。
這趨勢也席捲商界。毋庸置疑,財富集中在一小撮人手中,富者越富,腰纏萬貫的富人會利用其財勢獲取政治權力。這趨勢令人擔憂,亦不為世俗接受,但並不是形塑企業領袖和富有投資者權力運作的唯一力量。
事實證明,即使美國最富有的百分之一人口亦無法躲開財富、權力和地位突如其來的變化。面對收入不平等,經濟大衰退發揮了矯正效應,尤其嚴重影響富人的收入。美國國稅局數據顯示,在二〇〇七年至二〇〇九年間,收入達一百萬美元或以上的美國人數急跌四成至二十三萬六千八百八十三人,整體收入也銳挫近五成;跌幅遠高於總收入為五萬美元或以下的美國人,後者同期跌幅不足百分之二。當然,這並不能說明在以美國為首的先進民主國家中,貧富差距沒有顯著加劇,事實恰好相反,收入不均的現象正在急速惡化。但這現況也不應阻礙我們了解不少富裕人士和家庭在經濟危機中遭受的打擊,他們的財富和經濟實力確實顯著下跌。個人收入與財富已不再是獲取權力的唯一途徑。率領大型企業的管理階層往往比那些「純粹」的富豪享有更多權力。這些企業領袖現在的收入亦遠較以往豐厚,惟其任期卻越來越短。一九九二年,美國財富五百強企業的董事長在下一個五年中連任的機會是百分之三十六,一九九八年下降至百分之二十五。二〇〇五年,美國企業董事長的平均任期已縮短至六年,而這趨勢是全球性的。二〇一一年,全球最大兩千五百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長離職率是百分之十四點四;即使以企業管理層穩定見稱的日本,大企業董事長的非自願離職人數在二〇〇八年也增加了三倍。
企業本身也遭逢同樣命運。一九八〇年,傲居行業前五名的美國企業在五年後跌出五強的可能性僅為百分之十,但是在二十年後可能性已上升到百分之二十五。環顧今天美國和全球五百強企業排行榜,最近十年才上榜的企業數量足證,相對的後起之秀正在取代傳統企業巨頭的位置。在金融領域,銀行正在喪失權力和影響力,被新興、靈活的對沖基金取代:在二〇一〇年下半年,全球經濟陷入嚴重危機,排名前十名的對沖基金(當中多數不為公眾所知)賺得的利潤比全球六大銀行的總盈利還要高。當中最大的對沖基金管理的資金達到天文數字,賺取豐厚利潤,但其員工總數不過幾百名。
與此同時,企業面對令名譽、收入和價值受創的「品牌災難」時也更脆弱。一項研究顯示,在過去二十年間,全球最知名品牌母公司在五年內經歷品牌災難的風險由百分之二十急升百分之八十二。英國石油公司、老虎伍茲及梅鐸新聞集團的財富都曾因不利傳聞在一夜之間大幅萎縮。
這些趨勢甚至已從傳統的權力舞台——戰場、政界和商界——進入慈善界、宗教界、文化界以及個人領域。
慈善事業不再是大型基金會、社會團體和國際組織的專利,已被各式小型基金會進軍,捐助方式也起了顯著變化,現在不少捐助者已繞過傳統的慈善機構,直接提供支援給受助者。一九九〇年代,美國個人及機構投進的國際捐助增加了三倍,該數字在一九九八年至二〇〇七年又再升一倍至三百九十六億美元──比世界銀行的年度捐助額多出一半。美國在一九七五年有四萬家基金會,到了二〇一二年數量已逾七萬六千家。演員、運動員及慈善活動知名常客,如歐普拉、柯林頓、安潔莉娜裘莉和波諾,都為慈善捐款注入了強大動力。當然,比爾蓋茲夫婦、巴菲特和索羅斯等人捐助成立的大型基金會,也在顛覆大型慈善業機構主導的傳統運作模式。數以千計的科技新貴及對沖基金經理人快速投身慈善事業,投入的金額更是過去難以想像。「公益創投」興起,催生了專門為公益資金用途提供建議、支援和集資管道的新產業。
我知道,要爭辯權力正在衰退實與當下普遍的認知相悖——我們仍生活在一個權力趨向更集中的時代,掌權者的權力比以往更強盛更牢不可破。很多人確實認為權力有如財富:錢能生錢,越有錢越多錢;權也能生權,越有權越多權。從這角度看,權力和財富集中的循環可視為人類歷史的主要驅動力。世上誠然仍有許多坐擁巨大權力的機構及人士,他們的權力相當穩固;但本書在稍後的章節會證明,以這稜鏡觀看世界無法看到一個非常重要的面貌:事物正在變化的法則。
我們將看到,權力不僅簡單從一部分具有影響力的當權者手中轉移到另一方手中,而是權力本質有了更徹底和複雜的轉變。權力變得更垂手可得,事實上,在當今世界擁有權力的人的確更多了;可是權力的使用範圍縮小了。即便奪得了權力,權力的行使卻越來越難。我們即將探討的改變造就了不同領域的創新者和新秀,但不幸的是,受惠者名單也包括海盜、恐怖分子、叛亂分子、駭客、走私販、偽造者以及網路罪犯。這些改變也給支持民主的社會行動者帶來機會——包括議題狹隘與極端的偏激政治團體——不論在民主或專制國家,他們都可以透過嶄新方式贏得政治影響力,繞過或打破現存政治體制的嚴謹內部結構。二〇一一年夏天,為數不多的馬來西亞社運人士決定仿效馬德里太陽門廣場的「憤怒者」運動,占領了吉隆坡獨立廣場。一石激起千層浪,當時幾乎無人能預料這行動會激發性質相近的「占領華爾街」運動,浪潮席捲過全球近兩千六百座城市。
即使一連串的「占領運動」並未引發任何實質上的政治變化,但其影響值得注目。誠如一九六〇年代編年史學者季特林指出:「公共話題轉向在那久遠的六〇年代需時三年才可體現,話題如殘酷的戰爭、貧困的生活、低劣的政治、被壓抑的民主諾言……但是在二〇一一年,這只需要三星期。」就速度、影響力、創新的橫向組織形式而言,「占領運動」的發展在在反映出,傳統政黨過去掌控了社會成員表達不滿、希望和訴求的管道,如今他們的壟斷地位遭到蠶食。在中東地區,始於二〇一〇年的阿拉伯之春不但沒有顯露疲態,反而繼續蔓延至全球——各個專制政權都感受到其引發的迴響。
在地緣政治方面,小腳色——小國或非國家——亦獲得新機遇,可以否決、干預、引導和阻礙強國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多國組織的共同決策。隨手舉些例子:波蘭否決了歐盟的低碳經濟路線圖;土耳其和巴西破壞了強國與伊朗就核問題的談判;維基解密泄露美國外交機密;蓋茲基金會挑戰世界衛生組織在打擊瘧疾的領導地位。類似例子在貿易、氣候變遷及許多其他議題的全球談判越來越常見。
這些新崛起而且漸露頭角的「小型參與者」每一個都不盡相同,它們所在的領域南轅北轍,但仍有共同處:它們都不再需要透過規模、範疇、歷史或固有傳統發揮作用。它們象徵一種新權力的崛起,我們不妨將其稱為「微權力」,而這種權力在過去並沒有多少發揮空間。本書想爭辯的就是在今時今日,改變世界的已越來越不是大型當權者之間的競爭,而是微權力的崛起,以及它們挑戰當權者的能力。
權力的衰退並不代表當權者就此消失,而是大型政府、大型軍隊、大型企業和大型學府將面對前所未有的束縛和限制,但是它們仍然會躋身權力階層,其一舉一動仍足以左右大局,只是影響力不如它們自身渴望的重大,也不如它們預期的多。儘管當權者弱化看起來純粹是件好事(畢竟權力衍生出腐敗,不是嗎?),它們被降級卻可能引起複雜的社會動盪、混亂和運作癱瘓的問題。
我會在接下來的章節告訴你權力如何加速衰退,儘管坊間看到的是相反的趨勢,像是「巨者回歸」,上一個十年末期出現的「大到不能倒」,中美兩國軍費穩步增加、全球收入和財富差距日益懸殊。相較起現時政策制定者及分析家所聚焦的表面趨勢及發展,權力衰退才是眼下更為重要及影響深遠的議題。權力衰退並不特別由互聯網驅使,亦不可概括地訴諸資訊科技進步。互聯網及其他科技毋庸置疑正在改變政治、社會運動、商業活動,當然也包括權力的本質,但是這個基本角色太常被誇大及誤解。嶄新的資訊科技只是工具,而工具要發揮影響力,需要的是使用者。相對的,使用者在操作工具時要有目標、方向及動力。臉書、推特及簡訊強化了阿拉伯之春示威者的力量,可是實際上驅動群眾走上街頭的卻是國內外的情勢,不是那些供人使用的資訊工具。參與推翻埃及總統穆巴拉克的示威者達數百萬人,但就算在運動最高峰,臉書上公認有助於鼓動示威者的專頁只有三十五萬名粉絲。最近一項研究顯示,在埃及與利比亞起義期間,在推特點擊相關資料連結的用戶,百分之七十五都不是來自阿拉伯國家。美國和平研究所也曾研究阿拉伯之春期間的推特用戶使用模式,該所總結:新媒體「不論在國內的集體行動或地區性的傳播,都不見其擔當重要角色。」
此外,我們亦不應將權力衰退與當下最「時興的」權力轉移混為一談:自從美國走疲、中國崛起不證自明地被視為這時代地緣政治變局的關鍵,分析家與評論家便熱衷於剖析。估算歐洲衰弱及金磚國家崛起會伴隨帶來什麼情況、「其餘」的國家又會如何,就成為專家與業餘指揮家最熱門的猜謎遊戲。但是國家間的競爭不斷在變(競爭一直以來都在變),只把目光釘死在哪個國家走下坡、哪個國家得勢,在根本上就失了焦,非常危險。因為每一批新贏家都會對一項發現傷透腦筋,那就是未來每個掌權者都會察覺,他們的自由度與行使權力的效力大抵會遭遇前人未遇過的限制。
權力的圍牆倒下,打通了新手通往權力世界的大門,改變了人類重要領域的競爭本質。
這些新手是我們早前提及的微權力——一種全新的權力:並不巨大,不具壓倒性;大型、專業機構的權力通常有強制性,但這股相對權力可以抗衡、限制大玩家的操控。
這種權力來自創新及進取,是,但也來自新延伸的技術領域如否決、拖延、牽制及干擾。這些在戰爭期間常被反動者使用的典型策略,如今已擴展至許多其他領域而且行之有效。不單只對積極進取的創新者打開新視野,也包括極端分子、分離分子、各種非以爭取整體社會進步為目標的人。這些新參與者的數量正在明顯地迅速增長,如果我們繼續無視權力衰退不做補救,後果將不堪設想。
我們迫切需要理解及正視權力衰退的本質和其種種後果。即使上述風險並未造成無政府狀態等混亂,顯然已干預了我們處理這時代重大問題的能力。從氣候變遷、核擴散、經濟危機、資源枯竭、疾病、全球「最底層十億人」的長期貧窮問題、恐怖主義、走私、網路犯罪等等,現今世界面臨的複雜問題與日俱增,都需要更多來自不同背景的各方人士攜手解決。權力的衰退在以下角度看是個令人鼓舞的趨勢,因為它為全球的新投機事業、新企業以及新聲音創造更多空間與機會,但會為穩定性帶來危險。我們如何在歡迎多元聲音、意見、新概念、創新之際,不讓情況嚴重癱瘓,導致累積的成果毁於一旦?理解權力的衰退將是我們身處在重生世界中找尋出路所邁出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