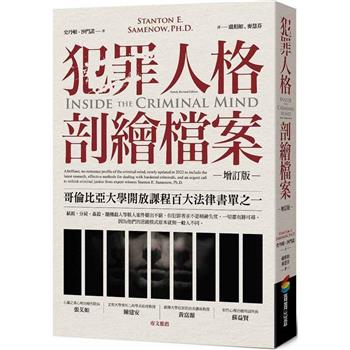賴瑞與崔佛:思維錯誤
缺乏會對他人造成傷害的概念
賴瑞對於那位從店裡走出來的無辜老人一無所知。賴瑞也沒興趣知道他是誰。漫無目的尋找刺激的賴瑞,有興趣的是「招惹」這名完全不相識的陌生人所帶來的期待。在殺死對方之前,把對方變成一個渾身顫抖、哀求一點點人性光輝的東西,是他極致的刺激。對他而言,這名受害者就像一隻腳下的螻蟻。我對賴瑞的幾次訪談中,他從來沒有對自己犯下的罪行表達後悔。他希望時光可以倒流,但不是出於殺人的悔意,而是這樣他就不用一輩子待在監獄裡。這是他唯一擔心的事。
崔佛殺了父親,也擺脫了他這輩子視為仇敵的那個人。他的受害者並非陌生人,但對他來說,是不是陌生人無關緊要。他並沒有把他的父親當成一個人。他曾多次想像要把溫特先生從地球上抹去,這樣自己才能自由自在地去做他想做的事。入監之後,崔佛幾乎從來沒有想過他的罪行對他的母親、弟弟、親戚、父親的同事、家人的朋友,抑或是他們社區的鄰居,會帶來什麼樣長久不去的衝擊。如同賴瑞一樣,崔佛的心思全擺在自己以及如何度過牢獄生活之上。被監禁在郡監獄時,他拒絕訪客,因為他不想有任何來自過去的人帶著一堆問題來打擾他,要求他做出一堆解釋。
目標受害者與其他非直接受害者,全都因為一項罪行的結果而飽受折磨。但像賴瑞與崔佛這樣的罪犯,對於他們的罪行所掀起的漣漪效應毫無知覺。
聲稱自己才是受害者,把過錯推給別人
在要求罪犯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時,他們會認為自己是受害的一方。若從他們的角度來看,因為其他人會干預他們想要做的事情,接著還會設法限制他們,所以他們一直都受到不公平的對待。賴瑞覺得他的受害者是一個剛好在錯誤的時間出現在錯誤地點的傢伙,就好像過錯全都在受害者,誰叫他要在那裡呢?
長久以來,崔佛一直自認是他父親「瘋狂惡劣情緒」下的被害者,而且憎恨他父親試圖將他的價值觀強加在自己身上。他對自己的母親也沒有什麼好話,他聲稱她正在「毀滅我的人生」。溫特夫婦的期望,與大多數的父母都一樣,不論來自什麼樣的社會階級,他們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得到教育、公正地對待他人,最後還能夠自己養活自己。
關閉良心譴責的能力
像賴瑞與崔佛這樣的罪犯,似乎無法與他人產生共鳴,因為他們不會展現出任何同理心,他們對於自己帶給其他人的痛苦漠不關心。崔佛的母親在試著與他談論家裡因他而導致的混亂時,因為他「冷淡的反應」或拒絕表現任何感情的態度而感到沮喪。崔佛從未表達懊悔之意。他的父親針對任何事情與他進行的溝通,都是困難重重。除了依照他的主張行事外,他不想跟自己的父母有任何瓜葛。對於自己的父母可能會有什麼反應,崔佛完全無感,他會說出令所有父母驚恐慌張的話,然後開心地看著他父母的愁苦。他平靜地說過:「我有時會脫口說出一些瘋狂的事情,不過我只是隨口說說,不會像我父母那樣認真對待。我媽對於激怒我這件事,還挺擅長的。我會用暴力威脅他們。」
當賴瑞堅持「我沒有良心」的時候,態度異常固執。但是他卻對鄰居的一位老奶奶和老奶奶的外孫產生了依戀。這位老太太指望著賴瑞幫她許多忙。賴瑞其實跟他的母親也很親,儘管他不斷地在抱怨她。 他從來沒有想過他的犯罪行為會讓在乎他的人千瘡百孔。當他攻擊那名從商店裡走出來的老人時,其他的一切都不再重要。就像賴瑞對我說的話:「事情發生了就是發生了。」不論他的良心是如何破碎,在他追逐當下那個目標時,他關閉了自己僅有的良心碎片。
罪犯短暫的感情用事,不該被誤解為良心。在罪犯意志消沉的時候,他們很可能會回到自己的母親那裡尋求慰藉。過去他們曾經多次依靠自己的母親,特別是靠著母親把他們保釋出來,遠離麻煩。然而不論他們對母親有多麼殷勤或多麼崇拜,他們都讓自己的母親活在地獄裡,他們在她反對他們想做的事情時破口大罵,他們偷她的錢、威脅她、讓她夜裡無法成眠。罪犯對自己母親的評論在聖人與魔鬼之間搖擺不定,一切都取決於他們的母親願意聽從他們命令的程度。然而不論罪犯讓自己的母親經歷過什麼樣的折磨,他們的母親依然會原諒他們,並給予支持,希望他們改過自新。
當崔佛描述自己是「情緒障礙」時,他指的是自己並沒有與任何人建立任何有意義的關係的事實。除了抽大麻或玩電玩時的那些膚淺之交外,他並沒有向任何人坦露過自己。對於自己對其他人造成的傷害,他似乎從來不會後悔。除了他自己,其他人的生命在他眼中也似乎沒有任何價值。
對於自己理所應得的堅定信念
儘管兩人家庭背景迥異,然而賴瑞和崔佛卻有許多相似之處,兩人都曾犯下侵犯財產罪、使用非法毒品,也都暴力對待過別人。兩個人都認定自己有權去做任何心裡閃過的事情。崔佛的父母因為看到兒子「持續而頑固地變壞」而心生恐懼,他們害怕這樣的情況可能是心理疾病之故。但是崔佛卻一點都不覺得自己每下愈況,他認為自己的行為全都只是在反制他那對不可理喻的父母而已。
像賴瑞與崔佛這樣的罪犯期待在任何情況中勝出。他們自認是輪軸的中心,永遠不會成為眾多輪輻之一。他們已經決定採取行動的事實,就已經賦予了這個行動應有的正當性。其他人對於隱藏在溫和外表之後的險惡意圖毫無所覺。罪犯期待占據上風。其他人要做的事情就只有別擋路、別成為他們的包袱。至於其他人想要的東西與期望,一點都不重要。賴瑞說:「如果我看到想要的東西,我就會拿走。」崔佛在未告知的情況下拿走屬於他父母的錢時,也是一樣的想法。他不需要對自己或其他人交代自己偷竊行為的正當性。在崔佛的心裡,這些錢早就屬於他,他要考慮的,只有這些錢該怎麼花。
認定自己獨一無二
罪犯持續努力強化自己的獨特感,這是他們人格的一道驅力。在他們的內心,他們認為自己就像一枚指紋一樣獨一無二。他們堅信自己與眾不同的想法,源於他們把其他人都關在他們的生命之外。除了私利的目的,崔佛與賴瑞都不會去尋求其他人的建議。
當崔佛的父親告訴他,他需要住進精神科醫院的時候,他震怒不已。他覺得如果有任何人需要治療,那也是他的父親。崔佛找不到任何應該順應大多數同儕的理由。在他眼裡,他的同儕全愚蠢地走在別人為他們鋪好的路上,他們不像自己有個自由的靈魂。
崔佛與賴瑞的人際關係都不好,部分是因為他們覺得沒有人跟自己一樣,所以不會有人瞭解自己。他們自認高人一等,他們確信適用於其他人的東西,與自己一點都不相關。他們會制訂出屬於他們自己的規矩。
缺乏責任的觀念
罪犯對於他人的態度反覆善變,完全視對方是否對自己有用而定。今天他可能把一個人當作至親至愛的盟友,明天就可能是非死不可的敵人。崔佛在享受父母富裕生活型態所提供的物質舒適的同時,也對他們因為自己的不合群與壞成績而一再打擾自己感到憤怒。他的母親發現與兒子周旋的過程非常痛苦,因為他總是「發脾氣、沮喪而自大」。崔佛對於家人想要伸出援手的所有提議,都會暴怒不已。甚至在父親或母親對他好的時候,他也會表現出一副不屑的態度。他回憶說:「我媽會幫我做一頓很豐盛的午餐。我直接丟掉。」他堅稱:「他們要我變成他們的複製人。」他對父母所累積的痛恨,遠遠超過了青少年叛逆期的表現。他不要他的父母出現在自己的生命中。
和所有的父母一樣,溫特夫婦也有缺點。但是他們另外兩個兒子卻設法容忍了這些缺點。崔佛在殺害他父親時,從未想過自己對家庭的責任,不過入獄後,他卻認為他母親有義務要幫他聘請一位頂尖的辯護律師。
賴瑞的父母、手足以及其他親戚都為他祈禱,希望他能有所改變。有一段時間,賴瑞的父親甚至說服了兒子與自己同住。不過對於他父親以一種管教的方式試圖安排他的生活,賴瑞感到極度惱火。就在他的父親以為兒子要安定下來時,賴瑞離開了,又回到母親的住處,他在那裡可以有更多的自由。不論犯案前後,賴瑞都沒有展現出任何跡象,顯示他意識到自己對那些關心他的人有責任。他只在乎自己想要的東西。
關閉恐懼感的能力
大眾普遍認為罪犯不會去考慮自己行為的後果。然而事實上,他們會去考慮後果。從經驗來看,罪犯很清楚自己的計畫如果出了差錯,大概會發生什麼事,以及遭到逮捕的可能性。他們在生活中,都曾經歷過父母的懲罰、親戚的規勸、在學校行為不端的懲處;在許多情況下,他們也有待在警察局、法庭、看守所、社區監獄或州立監禁機構的經驗。罪犯不但不會漠視這些可能的結果,也不會忘記這些經驗。但是罪犯在實際做出犯行的當下,這些後果全成了過去式。這一次,他們確信自己會成功。
從孩童時期開始,賴瑞與崔佛就已成功關閉了他們對於自己行為所可能引發後果的恐懼感。他們做壞事後成功逃脫的次數,比大家知道的還要多出不知多少倍。當這兩名年輕人在奪走另外一個人的生命時,就好像他們只是輕輕按下了一個開關,就消除了腦子裡所有關於後果與恐懼的考量。
無聊與思維錯誤
就像賴瑞與崔佛一樣,罪犯往往都會說自己無事可做,抱怨生活無聊。其實具強烈責任感的人也會這麼說,他們也許會覺得某次的演講很無聊、某次的死記硬背很無趣。在二○二○年新冠疫情期間,因為冠狀病毒傳播,大家的活動受到了限制,很多人都有極度無聊的體驗。但是一般人不會為了消除這樣的無聊而去犯罪。罪犯則不然,大家因為無聊而在家日復一日的上網,反而成了罪犯開心剝削大眾的豐收期。他們把假的產品賣給大眾、提出假的聘雇計畫,或承諾根本不可能實現的高投資報酬。
當罪犯說他們很無聊時,他們其實是很生氣,而且很危險,因為他們要找發洩的出口。崔佛曾描述過他所經歷的「生活中爆量的無聊」。他對學校開始感到無聊,或者如他自己的話,開始覺得「幻滅」。在他父母的眼裡,他非常抑鬱,因此他們很怕兒子會傷害自己。崔佛把他的抑鬱歸咎於「無趣」。他說完全是因為他父母堅持要他上大學,他才會出現「抑鬱」的情形。進入大學後,不到一年他就因為成績不及格,必須休學回家。再次感到無聊的崔佛,迫切地想要離家,所以他威脅父母,如果不讓他回到學校,他就要拿槍自盡,儘管他說的學校是另一所大學。
崔佛對我說,根本沒有工作的必要,生活的目的就是要開心。他說:「我覺得絕大多數人都是這樣想。不然呢?人類就是會感到無聊。自娛的方式多得不得了。我不喜歡我的家人。我也沒有朋友。」對他而言,開心就是吸毒以及一天玩六到八個小時的暴力電玩,他覺得這兩件事一點都不無聊。(電玩並沒有讓他變成一個暴力的人。早在他第一次玩電玩前,他就已經是個暴力的人了。)賴瑞與崔佛沒有朋友,拒絕接受家人,對工作也沒有宏圖大志,他們缺乏人生目的。兩人藉由毒品與犯罪來舒緩他們的「抑鬱」和無聊。崔佛說:「大麻就是我的抗抑鬱療法。」他完全不需要醫師開立的抗抑鬱藥物。
當一名罪犯說「無事可做」時,他指的是沒有令人興奮的事情。然而只要他們開始思考犯罪,這種挫敗的心態就會獲得緩解。賴瑞所處的環境很混亂,所以沒有人可以長期關注他的行徑,他能活動的舞台,要比生活在父母嚴格監督下的崔佛大得多。崔佛住進大學宿舍後,因為沒有父母的干預,也開始可以肆無忌憚地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賴瑞殺了一名完全不相識的陌生人,這件事解除了他的無聊感。崔佛殺他父親不是因為無事可做,而是因為怕被關進精神科治療醫院,他在那裡會感到無聊,而且無法掌控自己的日常生活。
罪犯對於無聊這件事的回應,是他們思維錯誤的直接結果。在追求刺激的過程中,他們只在乎自己想要的東西。如果要求罪犯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他們就會怪環境、怪其他人。一如賴瑞與崔佛,罪犯為了達到他們的目標,會關閉自己的良心運作。罪犯理所應得的感覺,反映出他們的認知:他們可以藉由任何自認必要的方式,得到任何自己想要的東西。罪犯認為自己獨一無二的這種觀念,強化了他們不論做什麼都必然會成功的自信。當罪犯試圖抒解無聊時,責任與義務完全無足輕重。在尋找「該做些什麼事」時,罪犯關閉了他們對可能後果的恐懼。因為這些思維錯誤,大家都可能成為失去生命的受害者。
缺乏會對他人造成傷害的概念
賴瑞對於那位從店裡走出來的無辜老人一無所知。賴瑞也沒興趣知道他是誰。漫無目的尋找刺激的賴瑞,有興趣的是「招惹」這名完全不相識的陌生人所帶來的期待。在殺死對方之前,把對方變成一個渾身顫抖、哀求一點點人性光輝的東西,是他極致的刺激。對他而言,這名受害者就像一隻腳下的螻蟻。我對賴瑞的幾次訪談中,他從來沒有對自己犯下的罪行表達後悔。他希望時光可以倒流,但不是出於殺人的悔意,而是這樣他就不用一輩子待在監獄裡。這是他唯一擔心的事。
崔佛殺了父親,也擺脫了他這輩子視為仇敵的那個人。他的受害者並非陌生人,但對他來說,是不是陌生人無關緊要。他並沒有把他的父親當成一個人。他曾多次想像要把溫特先生從地球上抹去,這樣自己才能自由自在地去做他想做的事。入監之後,崔佛幾乎從來沒有想過他的罪行對他的母親、弟弟、親戚、父親的同事、家人的朋友,抑或是他們社區的鄰居,會帶來什麼樣長久不去的衝擊。如同賴瑞一樣,崔佛的心思全擺在自己以及如何度過牢獄生活之上。被監禁在郡監獄時,他拒絕訪客,因為他不想有任何來自過去的人帶著一堆問題來打擾他,要求他做出一堆解釋。
目標受害者與其他非直接受害者,全都因為一項罪行的結果而飽受折磨。但像賴瑞與崔佛這樣的罪犯,對於他們的罪行所掀起的漣漪效應毫無知覺。
聲稱自己才是受害者,把過錯推給別人
在要求罪犯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時,他們會認為自己是受害的一方。若從他們的角度來看,因為其他人會干預他們想要做的事情,接著還會設法限制他們,所以他們一直都受到不公平的對待。賴瑞覺得他的受害者是一個剛好在錯誤的時間出現在錯誤地點的傢伙,就好像過錯全都在受害者,誰叫他要在那裡呢?
長久以來,崔佛一直自認是他父親「瘋狂惡劣情緒」下的被害者,而且憎恨他父親試圖將他的價值觀強加在自己身上。他對自己的母親也沒有什麼好話,他聲稱她正在「毀滅我的人生」。溫特夫婦的期望,與大多數的父母都一樣,不論來自什麼樣的社會階級,他們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得到教育、公正地對待他人,最後還能夠自己養活自己。
關閉良心譴責的能力
像賴瑞與崔佛這樣的罪犯,似乎無法與他人產生共鳴,因為他們不會展現出任何同理心,他們對於自己帶給其他人的痛苦漠不關心。崔佛的母親在試著與他談論家裡因他而導致的混亂時,因為他「冷淡的反應」或拒絕表現任何感情的態度而感到沮喪。崔佛從未表達懊悔之意。他的父親針對任何事情與他進行的溝通,都是困難重重。除了依照他的主張行事外,他不想跟自己的父母有任何瓜葛。對於自己的父母可能會有什麼反應,崔佛完全無感,他會說出令所有父母驚恐慌張的話,然後開心地看著他父母的愁苦。他平靜地說過:「我有時會脫口說出一些瘋狂的事情,不過我只是隨口說說,不會像我父母那樣認真對待。我媽對於激怒我這件事,還挺擅長的。我會用暴力威脅他們。」
當賴瑞堅持「我沒有良心」的時候,態度異常固執。但是他卻對鄰居的一位老奶奶和老奶奶的外孫產生了依戀。這位老太太指望著賴瑞幫她許多忙。賴瑞其實跟他的母親也很親,儘管他不斷地在抱怨她。 他從來沒有想過他的犯罪行為會讓在乎他的人千瘡百孔。當他攻擊那名從商店裡走出來的老人時,其他的一切都不再重要。就像賴瑞對我說的話:「事情發生了就是發生了。」不論他的良心是如何破碎,在他追逐當下那個目標時,他關閉了自己僅有的良心碎片。
罪犯短暫的感情用事,不該被誤解為良心。在罪犯意志消沉的時候,他們很可能會回到自己的母親那裡尋求慰藉。過去他們曾經多次依靠自己的母親,特別是靠著母親把他們保釋出來,遠離麻煩。然而不論他們對母親有多麼殷勤或多麼崇拜,他們都讓自己的母親活在地獄裡,他們在她反對他們想做的事情時破口大罵,他們偷她的錢、威脅她、讓她夜裡無法成眠。罪犯對自己母親的評論在聖人與魔鬼之間搖擺不定,一切都取決於他們的母親願意聽從他們命令的程度。然而不論罪犯讓自己的母親經歷過什麼樣的折磨,他們的母親依然會原諒他們,並給予支持,希望他們改過自新。
當崔佛描述自己是「情緒障礙」時,他指的是自己並沒有與任何人建立任何有意義的關係的事實。除了抽大麻或玩電玩時的那些膚淺之交外,他並沒有向任何人坦露過自己。對於自己對其他人造成的傷害,他似乎從來不會後悔。除了他自己,其他人的生命在他眼中也似乎沒有任何價值。
對於自己理所應得的堅定信念
儘管兩人家庭背景迥異,然而賴瑞和崔佛卻有許多相似之處,兩人都曾犯下侵犯財產罪、使用非法毒品,也都暴力對待過別人。兩個人都認定自己有權去做任何心裡閃過的事情。崔佛的父母因為看到兒子「持續而頑固地變壞」而心生恐懼,他們害怕這樣的情況可能是心理疾病之故。但是崔佛卻一點都不覺得自己每下愈況,他認為自己的行為全都只是在反制他那對不可理喻的父母而已。
像賴瑞與崔佛這樣的罪犯期待在任何情況中勝出。他們自認是輪軸的中心,永遠不會成為眾多輪輻之一。他們已經決定採取行動的事實,就已經賦予了這個行動應有的正當性。其他人對於隱藏在溫和外表之後的險惡意圖毫無所覺。罪犯期待占據上風。其他人要做的事情就只有別擋路、別成為他們的包袱。至於其他人想要的東西與期望,一點都不重要。賴瑞說:「如果我看到想要的東西,我就會拿走。」崔佛在未告知的情況下拿走屬於他父母的錢時,也是一樣的想法。他不需要對自己或其他人交代自己偷竊行為的正當性。在崔佛的心裡,這些錢早就屬於他,他要考慮的,只有這些錢該怎麼花。
認定自己獨一無二
罪犯持續努力強化自己的獨特感,這是他們人格的一道驅力。在他們的內心,他們認為自己就像一枚指紋一樣獨一無二。他們堅信自己與眾不同的想法,源於他們把其他人都關在他們的生命之外。除了私利的目的,崔佛與賴瑞都不會去尋求其他人的建議。
當崔佛的父親告訴他,他需要住進精神科醫院的時候,他震怒不已。他覺得如果有任何人需要治療,那也是他的父親。崔佛找不到任何應該順應大多數同儕的理由。在他眼裡,他的同儕全愚蠢地走在別人為他們鋪好的路上,他們不像自己有個自由的靈魂。
崔佛與賴瑞的人際關係都不好,部分是因為他們覺得沒有人跟自己一樣,所以不會有人瞭解自己。他們自認高人一等,他們確信適用於其他人的東西,與自己一點都不相關。他們會制訂出屬於他們自己的規矩。
缺乏責任的觀念
罪犯對於他人的態度反覆善變,完全視對方是否對自己有用而定。今天他可能把一個人當作至親至愛的盟友,明天就可能是非死不可的敵人。崔佛在享受父母富裕生活型態所提供的物質舒適的同時,也對他們因為自己的不合群與壞成績而一再打擾自己感到憤怒。他的母親發現與兒子周旋的過程非常痛苦,因為他總是「發脾氣、沮喪而自大」。崔佛對於家人想要伸出援手的所有提議,都會暴怒不已。甚至在父親或母親對他好的時候,他也會表現出一副不屑的態度。他回憶說:「我媽會幫我做一頓很豐盛的午餐。我直接丟掉。」他堅稱:「他們要我變成他們的複製人。」他對父母所累積的痛恨,遠遠超過了青少年叛逆期的表現。他不要他的父母出現在自己的生命中。
和所有的父母一樣,溫特夫婦也有缺點。但是他們另外兩個兒子卻設法容忍了這些缺點。崔佛在殺害他父親時,從未想過自己對家庭的責任,不過入獄後,他卻認為他母親有義務要幫他聘請一位頂尖的辯護律師。
賴瑞的父母、手足以及其他親戚都為他祈禱,希望他能有所改變。有一段時間,賴瑞的父親甚至說服了兒子與自己同住。不過對於他父親以一種管教的方式試圖安排他的生活,賴瑞感到極度惱火。就在他的父親以為兒子要安定下來時,賴瑞離開了,又回到母親的住處,他在那裡可以有更多的自由。不論犯案前後,賴瑞都沒有展現出任何跡象,顯示他意識到自己對那些關心他的人有責任。他只在乎自己想要的東西。
關閉恐懼感的能力
大眾普遍認為罪犯不會去考慮自己行為的後果。然而事實上,他們會去考慮後果。從經驗來看,罪犯很清楚自己的計畫如果出了差錯,大概會發生什麼事,以及遭到逮捕的可能性。他們在生活中,都曾經歷過父母的懲罰、親戚的規勸、在學校行為不端的懲處;在許多情況下,他們也有待在警察局、法庭、看守所、社區監獄或州立監禁機構的經驗。罪犯不但不會漠視這些可能的結果,也不會忘記這些經驗。但是罪犯在實際做出犯行的當下,這些後果全成了過去式。這一次,他們確信自己會成功。
從孩童時期開始,賴瑞與崔佛就已成功關閉了他們對於自己行為所可能引發後果的恐懼感。他們做壞事後成功逃脫的次數,比大家知道的還要多出不知多少倍。當這兩名年輕人在奪走另外一個人的生命時,就好像他們只是輕輕按下了一個開關,就消除了腦子裡所有關於後果與恐懼的考量。
無聊與思維錯誤
就像賴瑞與崔佛一樣,罪犯往往都會說自己無事可做,抱怨生活無聊。其實具強烈責任感的人也會這麼說,他們也許會覺得某次的演講很無聊、某次的死記硬背很無趣。在二○二○年新冠疫情期間,因為冠狀病毒傳播,大家的活動受到了限制,很多人都有極度無聊的體驗。但是一般人不會為了消除這樣的無聊而去犯罪。罪犯則不然,大家因為無聊而在家日復一日的上網,反而成了罪犯開心剝削大眾的豐收期。他們把假的產品賣給大眾、提出假的聘雇計畫,或承諾根本不可能實現的高投資報酬。
當罪犯說他們很無聊時,他們其實是很生氣,而且很危險,因為他們要找發洩的出口。崔佛曾描述過他所經歷的「生活中爆量的無聊」。他對學校開始感到無聊,或者如他自己的話,開始覺得「幻滅」。在他父母的眼裡,他非常抑鬱,因此他們很怕兒子會傷害自己。崔佛把他的抑鬱歸咎於「無趣」。他說完全是因為他父母堅持要他上大學,他才會出現「抑鬱」的情形。進入大學後,不到一年他就因為成績不及格,必須休學回家。再次感到無聊的崔佛,迫切地想要離家,所以他威脅父母,如果不讓他回到學校,他就要拿槍自盡,儘管他說的學校是另一所大學。
崔佛對我說,根本沒有工作的必要,生活的目的就是要開心。他說:「我覺得絕大多數人都是這樣想。不然呢?人類就是會感到無聊。自娛的方式多得不得了。我不喜歡我的家人。我也沒有朋友。」對他而言,開心就是吸毒以及一天玩六到八個小時的暴力電玩,他覺得這兩件事一點都不無聊。(電玩並沒有讓他變成一個暴力的人。早在他第一次玩電玩前,他就已經是個暴力的人了。)賴瑞與崔佛沒有朋友,拒絕接受家人,對工作也沒有宏圖大志,他們缺乏人生目的。兩人藉由毒品與犯罪來舒緩他們的「抑鬱」和無聊。崔佛說:「大麻就是我的抗抑鬱療法。」他完全不需要醫師開立的抗抑鬱藥物。
當一名罪犯說「無事可做」時,他指的是沒有令人興奮的事情。然而只要他們開始思考犯罪,這種挫敗的心態就會獲得緩解。賴瑞所處的環境很混亂,所以沒有人可以長期關注他的行徑,他能活動的舞台,要比生活在父母嚴格監督下的崔佛大得多。崔佛住進大學宿舍後,因為沒有父母的干預,也開始可以肆無忌憚地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賴瑞殺了一名完全不相識的陌生人,這件事解除了他的無聊感。崔佛殺他父親不是因為無事可做,而是因為怕被關進精神科治療醫院,他在那裡會感到無聊,而且無法掌控自己的日常生活。
罪犯對於無聊這件事的回應,是他們思維錯誤的直接結果。在追求刺激的過程中,他們只在乎自己想要的東西。如果要求罪犯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他們就會怪環境、怪其他人。一如賴瑞與崔佛,罪犯為了達到他們的目標,會關閉自己的良心運作。罪犯理所應得的感覺,反映出他們的認知:他們可以藉由任何自認必要的方式,得到任何自己想要的東西。罪犯認為自己獨一無二的這種觀念,強化了他們不論做什麼都必然會成功的自信。當罪犯試圖抒解無聊時,責任與義務完全無足輕重。在尋找「該做些什麼事」時,罪犯關閉了他們對可能後果的恐懼。因為這些思維錯誤,大家都可能成為失去生命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