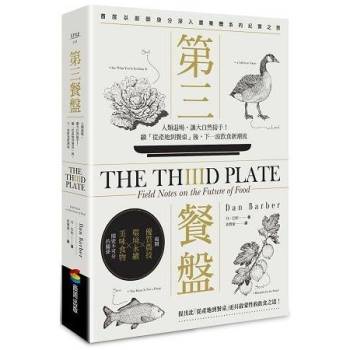第十二章
十月初,麗莎打電話給我,說艾杜瓦多想邀請我去看他宰殺鵝,時間是十一月十日,問我到時要不要去西班牙,親睹「用瓦斯獻祭。」
我記得艾杜瓦多曾強調,要成功產出好的鵝肝,宰殺的過程非常重要。萬一這個步驟沒做好,很可能就毀了一副鵝肝。他說,他下手俐落,一眨眼就可以殺死一隻鵝,接著,又以神秘的口吻補充:「牠們可是處於一種毫無壓力的狀態喔,就像人在浴缸裡割腕─舒服地死去。」我不確定該不該認同他這種比喻,不過,我確實被他這番話勾起興趣。
可是就在我出發的前幾天,麗莎打電話來,說宰殺鵝的日期有變動,但艾杜瓦多沒交代原因。不過,我來不及取消這趟行程,所以還是如期出發。我猜想,那些準備上場的成鵝,要不是脂肪囤積的程度還不足以宰殺,就是更值得留下來觀賞。
當我抵達艾杜瓦多的農場,他迎接我的態度竟出奇地親暱,彷彿見到童年好友。我猜想,他大概是因為更改了宰殺時間而對我不好意思吧。
「艾杜瓦多,鵝的事,沒關係。」我說,希望他放輕鬆。「我可以明年再來看你宰殺的過程。」
麗莎翻譯完我的話之後,他揚起眉說:「對,對。」但沒有道歉或解釋。接著,他忽然開始描述起宰殺的過程,大概以為我想感受一下無緣親睹的場面吧。「牠們睡覺。」他說,還閉起眼睛,頭微微側倚在右手,假裝睡在柔軟的枕頭上。
「一起睡?」我的語氣懷疑多於探詢。
「是,是真的。」他說:「他們一起睡覺,不會有感覺,什麼感覺都沒有。」
艾杜瓦多開始描述起他在一間偌大的密閉室前所架起的玻璃纖維圍籬,這個圍籬就像迷宮般。他說會撒些玉米,吸引鵝過來,還表演他怎麼出聲及拍手誘勸牠們。然後他仔細地模仿鵝搖搖擺擺走路的樣子,假裝正在穿越一座隱形迷宮。
「一隻進來後,其他隻發現吃了那些玉米之後不會有事,就會跟著進來。」他說:「必須讓牠們自己進到屠宰室。」他的鵝不會掙扎,不會驚慌失控。他耐心地告訴我,自由意志是他養的食物之所以甜美的關鍵因素。
他怎麼確定他的鵝沒受苦?
「味道啊!」他說:「你吃過我的食物了,嚐起來像是受苦的鵝嗎?」當然不像。嚐起來像被主人悉心照料,臨死前還享受按摩的鵝。可是,我怎麼知道受過苦的鵝吃起來不同呢?在遇到艾杜瓦多之前,我甚至不知道至少可以用不會讓鵝不舒服的方式來取得鵝肝呢。於是,我要他進一步說明。
他點點頭。「我兒子出生那年,我開始有點懷疑自己做得對不對。我希望自己不會良心不安,所以,把牠們關進毒氣室,放了毒氣之後,我又打開門,讓空氣循環,二十分鐘後,牠們醒來,昏沉沉⋯⋯」他把原本微側的頭放正,開始慢慢地左右搖晃,看起來真的像昏沉沉地。接著,他的頭往右偏,閉上眼,大半晌後睜開,興奮地看著我,說:「然後,牠們又開始大吃,彷彿什麼事都沒發生過。」
艾杜瓦多的作法或許聽起來誇張,可是有很多研究顯示,動物受苦而死,其肉質確實較差。正如艾杜瓦多所言,動物若在生前承受很大壓力,尤其在死亡前幾分鐘,這些壓力和痛苦會反映在肉的味道和質地上。
「石穀倉中心」的藍丘餐廳開幕時,我就親眼目睹過這種情況。某天克雷格把一隻盤克夏(Berkshire pig)品種的豬帶到屠宰場,結果宰殺後的豬肉非常難吃。我們的肉廚荷西指著肉上的紅色斑紋給我看,此外,我也發現這隻豬的肉吃起來乾澀、粗硬,跟我預期得差非常多。克雷格認為,應該是這隻豬單獨前往屠宰場的途中承受過大壓力,因此他決定做些改變。之後,要送豬去屠宰時,他讓兩隻豬結伴同行(一種邁向死亡的夥伴支持法),並給牠們充裕的飼料。此外,他還把農場蓊綠樹林的照片放大,掛在運豬貨車裡。到了屠宰場,只有一隻豬被宰殺,另一隻則運回農場,隔週,那隻上週被運回來的豬─牠已經熟悉這趟旅程─前往屠宰場時,會有另一隻豬陪著走完牠的最後一段路。採取這種作法後,豬肉的紅色斑紋消失了,盤克夏豬該有的美味出現了。
我問艾杜瓦多,他做這些的目的是為了確保鵝肝的優良品質,或者是為了鵝著想?他輕輕搖頭,笑了一下,意思是他不懂我這個問題。我不死心,再問一次:「你這麼做的動機是什麼?如果可以選擇,你最想要的是甜美的鵝肝,或者無痛苦地結束鵝的生命?」
艾杜瓦多很驚訝地揚起眉,說:「這有差別嗎?」
艾杜瓦多安排我們去吃午餐,但他建議我們先去看一下那些「差不多準備好要被宰殺」的鵝。
我們在不同的牧草地開進開出,大約二十分鐘後,遇見一群伊比利豬。牠們低著頭,行動一致地在地上尋找橡實。艾杜瓦多要我關掉汽車引擎。他說,那些鵝應該就在附近。我們站在一棵橡樹底下等著。附近地面上佈滿了裂開的橡實殼,看起來真像彈殼。
「豬就在這裡。」艾杜瓦多確認這個事實,並彎腰查看牠們吃剩的殘餘物。
我看見一顆沒被豬發現的完整橡實,撿起來握在手中。好大一顆。
「鵝會吃下一整顆橡實嗎?」我問。
他笑笑,指著遠處,我循著他的手指望過去,看見二十來隻鵝,排成一列,從長得頗高的牧草叢走出來,嘎嘎叫得好大聲。
「好大隻呀!」麗莎驚呼。
的確是:這些鵝宛如史前時代的動物─類似小型的恐龍。牠們的體積大約是我春天初見牠們時的三倍大。忽然,牠們大聲嘎啼,聚在一起,一邊拍翅,一邊靠近地上有著完整橡實的區域。
「牠們會為了橡實和豬起衝突嗎?」我問。
「如果豬太過分,鵝就會用翅膀摑牠的臉。」艾杜瓦多說,還把手肘往外伸,來回拍打身體,模仿鵝用翅膀摑豬。
「豬很怕被摑。」他彎腰喊道:「哈囉,我的姑娘們。」
鵝低頭覓食。「見到了嗎?牠們的脖子有大大的脂肪袋。」艾杜瓦多說,指著牠們脖子四周那明顯的一圈脂肪。「往下看。」他抓住我的手,要我們跪下,讓視線與鵝的視線等高。「看那肚子都垂到地面了。」
艾杜瓦多說,另一個判斷鵝是否準備好被宰殺的方法,就是觀察雨中的鵝。「鵝會滲出脂肪,」他開始解釋,並指著鵝的胸口。「就是那裡。牠們還會用嘴喙將脂肪撥散,蓋在羽毛上,類似穿雨衣的概念。所以,只要看看雨水從牠們身體散開的程度,就可以知道牠們的肝臟儲存了多少脂肪。」
不管是不是雨衣,我只想說,牠們看起來好肥美,真的像準備進屠宰場了─而這正是我飛了大半個地球來這裡,想要看的重頭戲。不過,我聽見艾杜瓦多嘆了一口氣,說:「今年的橡實長得不好,雖然不算最差。有時候,就是還不到可以宰殺的時候。」
艾杜瓦多說,幾年前,偶爾他會拿穀物餵鵝,替牠們補充營養,可是這時候真的很猶豫。
我不懂,他之所以餵牠們吃穀物,是為了確保自己有好鵝肝可以賣,還是為了取悅他的鵝肝經銷商,畢竟他們還是喜歡額外添加一些穀物當飼料。艾杜瓦多說,吃穀物的鵝,可以讓經銷商想到他們之前賣的法國鵝肝,他們覺得那種鵝肝的品質有保證。
「我告訴他們:你們知道我這輩子吃過最爛的食物是在哪裡嗎?巴黎!我在巴黎吃到最難吃的鵝肝,簡直是垃圾。」
艾杜瓦多把爛鵝肝歸咎於玉米飼料,而非灌食。他說這種飼料讓鵝肝變成預期中的滋味,但這種預期並不是正面的。
「鵝肝的構造都很類似,但最終每塊鵝肝的味道都會不同才是。吃起來應該每塊各有特色。」他說,語氣就像知名羊農約翰.賈米森稱讚他那些草飼羊的味道隻隻都不同。我告訴他,多數廚師想要的正好相反,他們希望每塊肉吃起來都一樣。艾杜瓦多又跪在地上,手握成空拳,放在眼睛上,當做望遠鏡,從空拳中望向他那些正遠去的鵝。「那些廚師搞錯了。」他說。
對火腿的虧欠
那天下午稍晚時,我們返回蒙納斯特里奧鎮,前往八個月前我品嚐艾杜瓦多的鵝肝的那家餐館。就在我吃完午餐,收拾外套和包包,準備離開時,我聽見艾杜瓦多跟麗莎說話。我轉身,看見他的右手伸得高高,拇指和食指夾著一片薄薄的火腿。午後的金黃燦陽穿透餐館的窗戶,像X光逆光映照著那片火腿。
這時,艾杜瓦多承認他對豬的虧欠。「我的人生目標就是讓我的鵝肝去提醒大家這東西的存在。」他說。那片火腿如蛛網般不可思議的條紋,在陽光下清晰歷歷。他用左手食指小心翼翼地來回輕撫紋路,沿著閃閃發亮的白色紋理繞彎迴旋,專注的態度彷彿正駕車駛在Dehesa的蜿蜒道路上。他這種動作太不可思議,部分是因為在這一刻之前,艾杜瓦多始終把他農場裡的豬當成附屬產物。
「你知道嗎?」他說,看著懸在半空中那片半透明的火腿。「伊比利火腿是全世界最棒的火腿,因為它完美地傳達出土地的精神。」
稍後麗莎告訴我,艾杜瓦多在使用土地這個詞彙時,應該是很有意識的。「土地」一詞的西班牙語是tierra,意思不只是在我們腳底下的地。tierra這個字是整體性的,包括土壤,還包括植物的根、水及太陽。
麗莎解釋,所以,伊比利火腿的重要性不只在美食層面,還有文化層面,因為它與西班牙人的自我認同緊緊相繫。在西班牙的過往歷史中,天主教徒就是藉由吃豬肉來強調自己有別於統治階級穆斯林與逐漸壯大的猶太社群。吃豬肉,就「證明」你不是猶太人或穆斯林(亦即異教徒),因為這兩種宗教都嚴禁吃豬肉。
我想起有次聽到一個年輕的西班牙廚師談起伊比利火腿對他的意義。「火腿?」他咧著大笑臉,說:「火腿就是上帝在說話。」
「你知道嗎?」麗莎告訴我:「跟艾杜瓦多和他的鵝相處的這些時間,我一直在想,他的鵝肝其實是靠著兩千年的火腿傳統所支撐起來的。所以,我好高興聽到他終於承認這個事實。」
西 班牙人對火腿的迷戀不只因為它是美食,還因為某種對西班牙人來說幾乎快被遺忘的古老意義。或許,以前艾杜瓦多之所以不願意承認豬的重要,是因為他不願意明 白說出麗莎所說的話─從某方面來看,他的鵝其實是搭豬的順風車。我知道,若想了解艾杜瓦多的鵝肝,我必須更充分了解伊比利火腿。為了了解火腿,我得知道更 多關於Dehesa的事。
十月初,麗莎打電話給我,說艾杜瓦多想邀請我去看他宰殺鵝,時間是十一月十日,問我到時要不要去西班牙,親睹「用瓦斯獻祭。」
我記得艾杜瓦多曾強調,要成功產出好的鵝肝,宰殺的過程非常重要。萬一這個步驟沒做好,很可能就毀了一副鵝肝。他說,他下手俐落,一眨眼就可以殺死一隻鵝,接著,又以神秘的口吻補充:「牠們可是處於一種毫無壓力的狀態喔,就像人在浴缸裡割腕─舒服地死去。」我不確定該不該認同他這種比喻,不過,我確實被他這番話勾起興趣。
可是就在我出發的前幾天,麗莎打電話來,說宰殺鵝的日期有變動,但艾杜瓦多沒交代原因。不過,我來不及取消這趟行程,所以還是如期出發。我猜想,那些準備上場的成鵝,要不是脂肪囤積的程度還不足以宰殺,就是更值得留下來觀賞。
當我抵達艾杜瓦多的農場,他迎接我的態度竟出奇地親暱,彷彿見到童年好友。我猜想,他大概是因為更改了宰殺時間而對我不好意思吧。
「艾杜瓦多,鵝的事,沒關係。」我說,希望他放輕鬆。「我可以明年再來看你宰殺的過程。」
麗莎翻譯完我的話之後,他揚起眉說:「對,對。」但沒有道歉或解釋。接著,他忽然開始描述起宰殺的過程,大概以為我想感受一下無緣親睹的場面吧。「牠們睡覺。」他說,還閉起眼睛,頭微微側倚在右手,假裝睡在柔軟的枕頭上。
「一起睡?」我的語氣懷疑多於探詢。
「是,是真的。」他說:「他們一起睡覺,不會有感覺,什麼感覺都沒有。」
艾杜瓦多開始描述起他在一間偌大的密閉室前所架起的玻璃纖維圍籬,這個圍籬就像迷宮般。他說會撒些玉米,吸引鵝過來,還表演他怎麼出聲及拍手誘勸牠們。然後他仔細地模仿鵝搖搖擺擺走路的樣子,假裝正在穿越一座隱形迷宮。
「一隻進來後,其他隻發現吃了那些玉米之後不會有事,就會跟著進來。」他說:「必須讓牠們自己進到屠宰室。」他的鵝不會掙扎,不會驚慌失控。他耐心地告訴我,自由意志是他養的食物之所以甜美的關鍵因素。
他怎麼確定他的鵝沒受苦?
「味道啊!」他說:「你吃過我的食物了,嚐起來像是受苦的鵝嗎?」當然不像。嚐起來像被主人悉心照料,臨死前還享受按摩的鵝。可是,我怎麼知道受過苦的鵝吃起來不同呢?在遇到艾杜瓦多之前,我甚至不知道至少可以用不會讓鵝不舒服的方式來取得鵝肝呢。於是,我要他進一步說明。
他點點頭。「我兒子出生那年,我開始有點懷疑自己做得對不對。我希望自己不會良心不安,所以,把牠們關進毒氣室,放了毒氣之後,我又打開門,讓空氣循環,二十分鐘後,牠們醒來,昏沉沉⋯⋯」他把原本微側的頭放正,開始慢慢地左右搖晃,看起來真的像昏沉沉地。接著,他的頭往右偏,閉上眼,大半晌後睜開,興奮地看著我,說:「然後,牠們又開始大吃,彷彿什麼事都沒發生過。」
艾杜瓦多的作法或許聽起來誇張,可是有很多研究顯示,動物受苦而死,其肉質確實較差。正如艾杜瓦多所言,動物若在生前承受很大壓力,尤其在死亡前幾分鐘,這些壓力和痛苦會反映在肉的味道和質地上。
「石穀倉中心」的藍丘餐廳開幕時,我就親眼目睹過這種情況。某天克雷格把一隻盤克夏(Berkshire pig)品種的豬帶到屠宰場,結果宰殺後的豬肉非常難吃。我們的肉廚荷西指著肉上的紅色斑紋給我看,此外,我也發現這隻豬的肉吃起來乾澀、粗硬,跟我預期得差非常多。克雷格認為,應該是這隻豬單獨前往屠宰場的途中承受過大壓力,因此他決定做些改變。之後,要送豬去屠宰時,他讓兩隻豬結伴同行(一種邁向死亡的夥伴支持法),並給牠們充裕的飼料。此外,他還把農場蓊綠樹林的照片放大,掛在運豬貨車裡。到了屠宰場,只有一隻豬被宰殺,另一隻則運回農場,隔週,那隻上週被運回來的豬─牠已經熟悉這趟旅程─前往屠宰場時,會有另一隻豬陪著走完牠的最後一段路。採取這種作法後,豬肉的紅色斑紋消失了,盤克夏豬該有的美味出現了。
我問艾杜瓦多,他做這些的目的是為了確保鵝肝的優良品質,或者是為了鵝著想?他輕輕搖頭,笑了一下,意思是他不懂我這個問題。我不死心,再問一次:「你這麼做的動機是什麼?如果可以選擇,你最想要的是甜美的鵝肝,或者無痛苦地結束鵝的生命?」
艾杜瓦多很驚訝地揚起眉,說:「這有差別嗎?」
艾杜瓦多安排我們去吃午餐,但他建議我們先去看一下那些「差不多準備好要被宰殺」的鵝。
我們在不同的牧草地開進開出,大約二十分鐘後,遇見一群伊比利豬。牠們低著頭,行動一致地在地上尋找橡實。艾杜瓦多要我關掉汽車引擎。他說,那些鵝應該就在附近。我們站在一棵橡樹底下等著。附近地面上佈滿了裂開的橡實殼,看起來真像彈殼。
「豬就在這裡。」艾杜瓦多確認這個事實,並彎腰查看牠們吃剩的殘餘物。
我看見一顆沒被豬發現的完整橡實,撿起來握在手中。好大一顆。
「鵝會吃下一整顆橡實嗎?」我問。
他笑笑,指著遠處,我循著他的手指望過去,看見二十來隻鵝,排成一列,從長得頗高的牧草叢走出來,嘎嘎叫得好大聲。
「好大隻呀!」麗莎驚呼。
的確是:這些鵝宛如史前時代的動物─類似小型的恐龍。牠們的體積大約是我春天初見牠們時的三倍大。忽然,牠們大聲嘎啼,聚在一起,一邊拍翅,一邊靠近地上有著完整橡實的區域。
「牠們會為了橡實和豬起衝突嗎?」我問。
「如果豬太過分,鵝就會用翅膀摑牠的臉。」艾杜瓦多說,還把手肘往外伸,來回拍打身體,模仿鵝用翅膀摑豬。
「豬很怕被摑。」他彎腰喊道:「哈囉,我的姑娘們。」
鵝低頭覓食。「見到了嗎?牠們的脖子有大大的脂肪袋。」艾杜瓦多說,指著牠們脖子四周那明顯的一圈脂肪。「往下看。」他抓住我的手,要我們跪下,讓視線與鵝的視線等高。「看那肚子都垂到地面了。」
艾杜瓦多說,另一個判斷鵝是否準備好被宰殺的方法,就是觀察雨中的鵝。「鵝會滲出脂肪,」他開始解釋,並指著鵝的胸口。「就是那裡。牠們還會用嘴喙將脂肪撥散,蓋在羽毛上,類似穿雨衣的概念。所以,只要看看雨水從牠們身體散開的程度,就可以知道牠們的肝臟儲存了多少脂肪。」
不管是不是雨衣,我只想說,牠們看起來好肥美,真的像準備進屠宰場了─而這正是我飛了大半個地球來這裡,想要看的重頭戲。不過,我聽見艾杜瓦多嘆了一口氣,說:「今年的橡實長得不好,雖然不算最差。有時候,就是還不到可以宰殺的時候。」
艾杜瓦多說,幾年前,偶爾他會拿穀物餵鵝,替牠們補充營養,可是這時候真的很猶豫。
我不懂,他之所以餵牠們吃穀物,是為了確保自己有好鵝肝可以賣,還是為了取悅他的鵝肝經銷商,畢竟他們還是喜歡額外添加一些穀物當飼料。艾杜瓦多說,吃穀物的鵝,可以讓經銷商想到他們之前賣的法國鵝肝,他們覺得那種鵝肝的品質有保證。
「我告訴他們:你們知道我這輩子吃過最爛的食物是在哪裡嗎?巴黎!我在巴黎吃到最難吃的鵝肝,簡直是垃圾。」
艾杜瓦多把爛鵝肝歸咎於玉米飼料,而非灌食。他說這種飼料讓鵝肝變成預期中的滋味,但這種預期並不是正面的。
「鵝肝的構造都很類似,但最終每塊鵝肝的味道都會不同才是。吃起來應該每塊各有特色。」他說,語氣就像知名羊農約翰.賈米森稱讚他那些草飼羊的味道隻隻都不同。我告訴他,多數廚師想要的正好相反,他們希望每塊肉吃起來都一樣。艾杜瓦多又跪在地上,手握成空拳,放在眼睛上,當做望遠鏡,從空拳中望向他那些正遠去的鵝。「那些廚師搞錯了。」他說。
對火腿的虧欠
那天下午稍晚時,我們返回蒙納斯特里奧鎮,前往八個月前我品嚐艾杜瓦多的鵝肝的那家餐館。就在我吃完午餐,收拾外套和包包,準備離開時,我聽見艾杜瓦多跟麗莎說話。我轉身,看見他的右手伸得高高,拇指和食指夾著一片薄薄的火腿。午後的金黃燦陽穿透餐館的窗戶,像X光逆光映照著那片火腿。
這時,艾杜瓦多承認他對豬的虧欠。「我的人生目標就是讓我的鵝肝去提醒大家這東西的存在。」他說。那片火腿如蛛網般不可思議的條紋,在陽光下清晰歷歷。他用左手食指小心翼翼地來回輕撫紋路,沿著閃閃發亮的白色紋理繞彎迴旋,專注的態度彷彿正駕車駛在Dehesa的蜿蜒道路上。他這種動作太不可思議,部分是因為在這一刻之前,艾杜瓦多始終把他農場裡的豬當成附屬產物。
「你知道嗎?」他說,看著懸在半空中那片半透明的火腿。「伊比利火腿是全世界最棒的火腿,因為它完美地傳達出土地的精神。」
稍後麗莎告訴我,艾杜瓦多在使用土地這個詞彙時,應該是很有意識的。「土地」一詞的西班牙語是tierra,意思不只是在我們腳底下的地。tierra這個字是整體性的,包括土壤,還包括植物的根、水及太陽。
麗莎解釋,所以,伊比利火腿的重要性不只在美食層面,還有文化層面,因為它與西班牙人的自我認同緊緊相繫。在西班牙的過往歷史中,天主教徒就是藉由吃豬肉來強調自己有別於統治階級穆斯林與逐漸壯大的猶太社群。吃豬肉,就「證明」你不是猶太人或穆斯林(亦即異教徒),因為這兩種宗教都嚴禁吃豬肉。
我想起有次聽到一個年輕的西班牙廚師談起伊比利火腿對他的意義。「火腿?」他咧著大笑臉,說:「火腿就是上帝在說話。」
「你知道嗎?」麗莎告訴我:「跟艾杜瓦多和他的鵝相處的這些時間,我一直在想,他的鵝肝其實是靠著兩千年的火腿傳統所支撐起來的。所以,我好高興聽到他終於承認這個事實。」
西 班牙人對火腿的迷戀不只因為它是美食,還因為某種對西班牙人來說幾乎快被遺忘的古老意義。或許,以前艾杜瓦多之所以不願意承認豬的重要,是因為他不願意明 白說出麗莎所說的話─從某方面來看,他的鵝其實是搭豬的順風車。我知道,若想了解艾杜瓦多的鵝肝,我必須更充分了解伊比利火腿。為了了解火腿,我得知道更 多關於Dehesa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