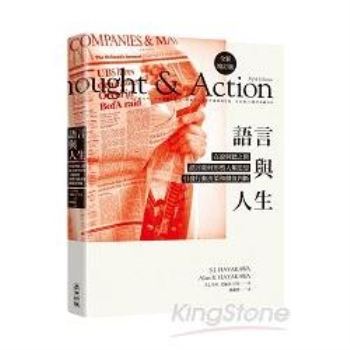我們該模仿什麼動物?
自認意志堅強且現實的人通常深信人類天性自私,生存即戰鬥,適者生存。根據此理論,即使表面上以文明妝點,人類必須遵從的基本法則仍是叢林戰鬥。所謂「適者」就是具有優越武力、卓越智謀和絕對無情進行爭鬥的人。
「適者生存」的哲學廣為傳布,使得那些在個人鬥爭、企業競爭或國際關係上行為無情自私的人可以安撫個人良心,說服自己不過是順從了自然法則。但公正的旁觀者可以用自身的人類經驗捫心自問,是否老虎的無情、狐狸的狡猾及遵從叢林法則,確實適於佐證人類的適者生存?如果人類非得從低等動物中尋找仿效對象,除了猛獸之外,是否還有能夠師法的對象?
舉例來說,我們可以效法兔子或小鹿,並將「適者生存」定義為快速逃離敵人的能力。我們也可以效法蚯蚓或鼴鼠,將「適者生存」視為躲藏及逃躲。我們還能參考牡蠣或家蠅並將其適者生存能力定義為大量繁衍以免被天敵吃光。在《美麗新世界》中,赫胥黎描摹了將人類當作群居螞蟻的世界。世界在菁英團隊的管理下,或許像蟻群一樣的團結、和諧、有效率,但就像赫胥黎所昭示的,那也沒有任何意義。若單純以動物為目標來定義所謂「適者生
存」,我們可以設計出無數不適合人類的行為系統:我們可以師法龍蝦、狗、麻雀、鸚鵡、長頸鹿、臭鼬或寄生蟲,因為牠們很明顯在各特定環境都生存得很好。然而我們也該問問,是否人類的「適者」真與低等動物的「適者」相同?
既然普遍認為競爭是世界運行的力量,那麼就該確認一下現今科學中所謂「適者生存」為何。生物學家將生存競爭分為兩類:其一,「種間競爭」(intraspecific struggle),即不同物種間的鬥爭,如狼與鹿或人類與細菌。其二,「種內競爭」(interspecific struggle),同一物種成員間的爭鬥,比如老鼠相鬥或人類相爭。現代生物學有大量證據顯示藉由種內競爭來進化的物種,往往使自己不利於種間競爭,因此那些物種要不已經絕種,就是瀕臨絕種。孔雀的尾巴雖然有利於和其他孔雀進行性競爭,但處於整個大環境或跟其他物種競爭時卻只會礙事而已。因此孔雀很可能因為突發的生態平衡變化而在一夜之間消失。也有其他證據顯示,無論種間或種內的競爭,動物之間暴烈而猛力的廝殺都對物種存續沒有幫助。許多備有強大防禦和攻擊能力的巨大爬蟲動物,早在數百萬年前就於地球絕跡。
雖然已認定人類必須爭鬥求生,但如果要探討人類求生,首先還是得區別哪些特質有益於對抗環境和其他物種(諸如洪水、暴風雨、野生動物、昆蟲或細菌等),而哪些素質(如侵略性)是用於對抗其他人類。也有一些對人類求生很重要的素質與爭鬥無關。
如果我們無法團結合作,就只能被各個擊破,這法則遠在被富蘭克林訴諸文字前就為人所知。對大多數生物來說,要求生存,物種內的合作(有時包括跨物種合作)至為重要。
人類是會說話的動物。任何關於人類生存的理論若無視此前提,就會像探討河狸生存理論之際卻無視河狸使用牙齒和扁尾的有趣習性一樣,不夠科學。讓我們看看「說話」,也就是「人類的溝通」意味著什麼。
知識之淵
除了發展語言,人類還借助黏土板、木材或石頭、獸皮、紙和晶片,製造出或多或少的永久記號和畫痕藉以「表記」語言。這些符號能讓我們與發聲所不能及的對象溝通,跨越空間與時間障礙。從刻畫在樹皮上的印地安人足跡直到現代都會報紙,演化過程如此漫長,然而其共同點是:為其他人的方便(廣義上或可說是為了引領他人),傳達個人所知資訊。今時今日,許多加拿大的木材上仍可找到印地安人多年前留下的痕跡。阿基米德已逝,我們仍擁有他的物理實驗觀察結果報告。濟慈已逝,他留下的詩句仍可以告訴我們他初次讀賈浦曼譯荷馬時如何感動。伊麗莎白.巴雷特已逝,但我們仍可得知她對羅伯特.白朗寧的情感。我們藉由書籍和雜誌獲知數以百計我們應無從得見的人們所思所感。而衛星將我們所居世界的種種藉由報紙、收音機及電視傳遞出去,這些資訊終有一日能用以解決我們的問題。
因此,從沒有人能夠只依賴自身的直接經驗過活。原始文化中的人也能透過語言溝通來利用鄰居、朋友、親戚或祖先的經驗。與其因為受限自身經驗和知識而徒留無助、發掘那些其他人早已發現的、重複別人已犯過的錯,不如根據別人留下的經驗繼續向前。也就是說,語言促成進步。
任何文字文化只要持續幾世紀,人類累積的知識,便會遠遠超過該文化中任何人一輩子可閱讀或記憶的量。透過印刷、電腦資料庫等機械手段,或經由如出版業、報社、雜誌社、圖書館系統,或電腦網路等傳播媒介,這些持續增加的知識能公開給那些求知若渴的人。我們只要有能力閱讀任何歐洲或亞洲的主要語言,就有機會接觸到數世紀以來文明世界各處人類所累積的智識資產。
語言是人類生活不可或缺的機制,以之塑造、引導、豐富並藉由累積我們族類的過去經驗形成今日的生活。我們從逝者身上無償獲贈歷代文化成就,包括關於烹飪、武器、書寫、印刷、建築工法、遊戲和娛樂、交通工具上的發明,人文與科學上所有發現。我們不勞而獲的贈禮不只讓我們有機會得到比先人更豐富的人生,也讓我們有機會對人類成就總和有所貢獻,就算貢獻十分渺小。
因此,學會讀寫就是學會使用這份龐大的人類成就並有所貢獻,同時也促成他人成就。
字詞巨瀑
這一切如何影響你我及「路人甲」,或曰「TC米特先生」呢?長島大學的莉莉安.李柏和休.李柏在他們的著作《TC米特先生的教育》中為米特先生命名。從早上米特先生扭開晨間新聞廣播的那一刻,到他閱讀一本小說或看著電視睡著為止,他就像現代社會中所有人一樣浸淫在字詞中。報紙編輯、政治家、推銷員、節目主持人、專欄作家、午餐會演講者和教士、同事、朋友、親人、老婆孩子、市場報告、郵寄廣告、圖書、廣告看板、脫口秀節目,這一切終日都以字詞對他窮追猛打。每當米特參與廣告宣傳活動、發表演說、寫信或和朋友聊天,他自己也持續對大量語言造成的字詞巨瀑(the Niagara of Words)有所貢獻。
當米特的生活中出了差錯,比如他感到擔憂、困惑、或緊張,或他的家庭、事業、國家大事有什麼發展不如他預期,他會抱怨若干事物:天氣、健康、神經狀態或他的工作同僚。如果事態較嚴重,他可能轉而責怪環境、經濟體系、其他國家或其他社會文化。
若他人遭遇困境,他也會歸責於前述原因或「人性」。但他絕少思及日常字詞巨瀑的本質或許是這些困境的源頭。
事實上,米特遇到某些狀況時也會認為語言是徵結所在。他時不時在某個語法點停頓下來。偶爾他留意到廣告所說「如何增進你的字詞力量」,並思考他是否該成為更有效率的發聲者。面對字詞巨瀑,比如他從沒時間追上進度的雜誌,或他知道他必得一讀的書,他也想知道速讀課程是否幫得上忙。偶爾他會被某些人(總有那麼些人)扭曲字詞意義所擾,尤其在爭論過程中,而這些字詞往往刁詭難懂。有時他惱怒地留意到某些字詞別有所指,此時他深覺,如果人們能遵從字典學習詞彙的「真正涵義」就能改正這一切。然而他也知道別人不會這樣做,因為連他自己也不太樂意,最後他會把這一切歸咎於人性弱點。
可惜米特的語言學思辯能力有限。而米特並不只是普羅大眾的典型代表,也是科學家、政論家和作家的典型代表。像大多數人一樣,他視字詞如同他所呼吸的空氣一般自然,對它的想法也與對待空氣沒什麼不同。
即使如此,米特其實也深刻涉入他日常吸收和使用的字詞。報紙上的字詞會讓他的拳頭落在餐桌上;主管吹捧他或敦促他的字詞會讓他工作更賣力;偷聽到別人私下對他的議論使他憂思成疾;幾年前他在牧師面前說的一席話讓他對一個女人承諾終生;寫在幾張紙上的字詞讓他保有工作,也月月帶來令他付了又付的帳單。字詞編織的綿密網絡幾乎涵蓋米特所有人生,但他對字詞的想法卻有限地驚人。
米特或許會留意到那群人(比如生活在極權制度下的人),他們只能聽見和閱讀經過刻意篩選的字詞,因之行徑古怪到他只能當他們是瘋子。然而,他有時也當某些和他受相同教育、同樣多樣化資訊的人是瘋子。聽著鄰居的觀點,他不禁納悶:「他們怎麼會這樣想?我都發現了他們沒發現嗎?他們一定瘋了!」「這種病態」,他自問,「是否再次顯示出『人性必然的脆弱』?」米特先生身為美國人,喜歡設想所有可能,而非以「無計可施」作結,但他實在不知道該如何自這狀況抽身。
米特對語言的思辯總無法深入並以失敗作結,原因之一是人們本就深信字詞並不重要,字詞所承載的「想法」才是重點。但腦中的騷動如果不化為詞語,要如何稱之為「想法」?米特幾乎不這麼想。事實上某組字詞或許無可避免會引人進入死胡同,但另一組字詞就不會。某些字詞容易引發歷史或感傷聯想因而難讓人冷靜討論。語言有多種不同使用方式,誤認使用方式會導致極大誤解。使用諸如日文、中文或土耳其語等結構和英文截然不同語言的人,或許他們思考的方式根本和說英語的人不同。前述概念對米特來說都十分陌生,他總認為重點在於讓人表達他的想法,至於字詞就順其自然。
無論米特是否有自覺,不只他聽見和使用的字詞,連他無意識間對語言預設的態度也影響他人生的每分每秒。比如說,如果他喜歡艾伯特這名字,且想用它幫孩子命名,但可能會因為認識一位曾企圖自殺的艾伯特而放棄這念頭。無論他是否有自覺,他都依照語言和現實之間的關係所形成的假想推論而行動。無論明智與否,這些無意識推論決定他的行動模式。字詞、他使用字詞的方式,及別人使用字詞時他如何判定,皆大幅形塑他的信仰、偏見、理想和抱負。字詞構築他所在之處的道德和學術氛圍,簡而言之,他的「語意環境」。
本書主要研究語言、思想和行為之間的相互關係。旨在檢證語言和人們的語言習慣如何透過思考(十之八九都關於自己)、說話、傾聽、閱讀和書寫來揭露自我。
本書的基本假設為人類生存的基礎機制乃透過語言進行的種內合作。同時也假設若語言使用引致或加深歧見或衝突,說者、聽者,或兩者身上必然有語言學上的錯誤。人類生存係仰賴語言書寫傾聽和閱讀能力,以之增近你和同類一起生存下去的機會。
自認意志堅強且現實的人通常深信人類天性自私,生存即戰鬥,適者生存。根據此理論,即使表面上以文明妝點,人類必須遵從的基本法則仍是叢林戰鬥。所謂「適者」就是具有優越武力、卓越智謀和絕對無情進行爭鬥的人。
「適者生存」的哲學廣為傳布,使得那些在個人鬥爭、企業競爭或國際關係上行為無情自私的人可以安撫個人良心,說服自己不過是順從了自然法則。但公正的旁觀者可以用自身的人類經驗捫心自問,是否老虎的無情、狐狸的狡猾及遵從叢林法則,確實適於佐證人類的適者生存?如果人類非得從低等動物中尋找仿效對象,除了猛獸之外,是否還有能夠師法的對象?
舉例來說,我們可以效法兔子或小鹿,並將「適者生存」定義為快速逃離敵人的能力。我們也可以效法蚯蚓或鼴鼠,將「適者生存」視為躲藏及逃躲。我們還能參考牡蠣或家蠅並將其適者生存能力定義為大量繁衍以免被天敵吃光。在《美麗新世界》中,赫胥黎描摹了將人類當作群居螞蟻的世界。世界在菁英團隊的管理下,或許像蟻群一樣的團結、和諧、有效率,但就像赫胥黎所昭示的,那也沒有任何意義。若單純以動物為目標來定義所謂「適者生
存」,我們可以設計出無數不適合人類的行為系統:我們可以師法龍蝦、狗、麻雀、鸚鵡、長頸鹿、臭鼬或寄生蟲,因為牠們很明顯在各特定環境都生存得很好。然而我們也該問問,是否人類的「適者」真與低等動物的「適者」相同?
既然普遍認為競爭是世界運行的力量,那麼就該確認一下現今科學中所謂「適者生存」為何。生物學家將生存競爭分為兩類:其一,「種間競爭」(intraspecific struggle),即不同物種間的鬥爭,如狼與鹿或人類與細菌。其二,「種內競爭」(interspecific struggle),同一物種成員間的爭鬥,比如老鼠相鬥或人類相爭。現代生物學有大量證據顯示藉由種內競爭來進化的物種,往往使自己不利於種間競爭,因此那些物種要不已經絕種,就是瀕臨絕種。孔雀的尾巴雖然有利於和其他孔雀進行性競爭,但處於整個大環境或跟其他物種競爭時卻只會礙事而已。因此孔雀很可能因為突發的生態平衡變化而在一夜之間消失。也有其他證據顯示,無論種間或種內的競爭,動物之間暴烈而猛力的廝殺都對物種存續沒有幫助。許多備有強大防禦和攻擊能力的巨大爬蟲動物,早在數百萬年前就於地球絕跡。
雖然已認定人類必須爭鬥求生,但如果要探討人類求生,首先還是得區別哪些特質有益於對抗環境和其他物種(諸如洪水、暴風雨、野生動物、昆蟲或細菌等),而哪些素質(如侵略性)是用於對抗其他人類。也有一些對人類求生很重要的素質與爭鬥無關。
如果我們無法團結合作,就只能被各個擊破,這法則遠在被富蘭克林訴諸文字前就為人所知。對大多數生物來說,要求生存,物種內的合作(有時包括跨物種合作)至為重要。
人類是會說話的動物。任何關於人類生存的理論若無視此前提,就會像探討河狸生存理論之際卻無視河狸使用牙齒和扁尾的有趣習性一樣,不夠科學。讓我們看看「說話」,也就是「人類的溝通」意味著什麼。
知識之淵
除了發展語言,人類還借助黏土板、木材或石頭、獸皮、紙和晶片,製造出或多或少的永久記號和畫痕藉以「表記」語言。這些符號能讓我們與發聲所不能及的對象溝通,跨越空間與時間障礙。從刻畫在樹皮上的印地安人足跡直到現代都會報紙,演化過程如此漫長,然而其共同點是:為其他人的方便(廣義上或可說是為了引領他人),傳達個人所知資訊。今時今日,許多加拿大的木材上仍可找到印地安人多年前留下的痕跡。阿基米德已逝,我們仍擁有他的物理實驗觀察結果報告。濟慈已逝,他留下的詩句仍可以告訴我們他初次讀賈浦曼譯荷馬時如何感動。伊麗莎白.巴雷特已逝,但我們仍可得知她對羅伯特.白朗寧的情感。我們藉由書籍和雜誌獲知數以百計我們應無從得見的人們所思所感。而衛星將我們所居世界的種種藉由報紙、收音機及電視傳遞出去,這些資訊終有一日能用以解決我們的問題。
因此,從沒有人能夠只依賴自身的直接經驗過活。原始文化中的人也能透過語言溝通來利用鄰居、朋友、親戚或祖先的經驗。與其因為受限自身經驗和知識而徒留無助、發掘那些其他人早已發現的、重複別人已犯過的錯,不如根據別人留下的經驗繼續向前。也就是說,語言促成進步。
任何文字文化只要持續幾世紀,人類累積的知識,便會遠遠超過該文化中任何人一輩子可閱讀或記憶的量。透過印刷、電腦資料庫等機械手段,或經由如出版業、報社、雜誌社、圖書館系統,或電腦網路等傳播媒介,這些持續增加的知識能公開給那些求知若渴的人。我們只要有能力閱讀任何歐洲或亞洲的主要語言,就有機會接觸到數世紀以來文明世界各處人類所累積的智識資產。
語言是人類生活不可或缺的機制,以之塑造、引導、豐富並藉由累積我們族類的過去經驗形成今日的生活。我們從逝者身上無償獲贈歷代文化成就,包括關於烹飪、武器、書寫、印刷、建築工法、遊戲和娛樂、交通工具上的發明,人文與科學上所有發現。我們不勞而獲的贈禮不只讓我們有機會得到比先人更豐富的人生,也讓我們有機會對人類成就總和有所貢獻,就算貢獻十分渺小。
因此,學會讀寫就是學會使用這份龐大的人類成就並有所貢獻,同時也促成他人成就。
字詞巨瀑
這一切如何影響你我及「路人甲」,或曰「TC米特先生」呢?長島大學的莉莉安.李柏和休.李柏在他們的著作《TC米特先生的教育》中為米特先生命名。從早上米特先生扭開晨間新聞廣播的那一刻,到他閱讀一本小說或看著電視睡著為止,他就像現代社會中所有人一樣浸淫在字詞中。報紙編輯、政治家、推銷員、節目主持人、專欄作家、午餐會演講者和教士、同事、朋友、親人、老婆孩子、市場報告、郵寄廣告、圖書、廣告看板、脫口秀節目,這一切終日都以字詞對他窮追猛打。每當米特參與廣告宣傳活動、發表演說、寫信或和朋友聊天,他自己也持續對大量語言造成的字詞巨瀑(the Niagara of Words)有所貢獻。
當米特的生活中出了差錯,比如他感到擔憂、困惑、或緊張,或他的家庭、事業、國家大事有什麼發展不如他預期,他會抱怨若干事物:天氣、健康、神經狀態或他的工作同僚。如果事態較嚴重,他可能轉而責怪環境、經濟體系、其他國家或其他社會文化。
若他人遭遇困境,他也會歸責於前述原因或「人性」。但他絕少思及日常字詞巨瀑的本質或許是這些困境的源頭。
事實上,米特遇到某些狀況時也會認為語言是徵結所在。他時不時在某個語法點停頓下來。偶爾他留意到廣告所說「如何增進你的字詞力量」,並思考他是否該成為更有效率的發聲者。面對字詞巨瀑,比如他從沒時間追上進度的雜誌,或他知道他必得一讀的書,他也想知道速讀課程是否幫得上忙。偶爾他會被某些人(總有那麼些人)扭曲字詞意義所擾,尤其在爭論過程中,而這些字詞往往刁詭難懂。有時他惱怒地留意到某些字詞別有所指,此時他深覺,如果人們能遵從字典學習詞彙的「真正涵義」就能改正這一切。然而他也知道別人不會這樣做,因為連他自己也不太樂意,最後他會把這一切歸咎於人性弱點。
可惜米特的語言學思辯能力有限。而米特並不只是普羅大眾的典型代表,也是科學家、政論家和作家的典型代表。像大多數人一樣,他視字詞如同他所呼吸的空氣一般自然,對它的想法也與對待空氣沒什麼不同。
即使如此,米特其實也深刻涉入他日常吸收和使用的字詞。報紙上的字詞會讓他的拳頭落在餐桌上;主管吹捧他或敦促他的字詞會讓他工作更賣力;偷聽到別人私下對他的議論使他憂思成疾;幾年前他在牧師面前說的一席話讓他對一個女人承諾終生;寫在幾張紙上的字詞讓他保有工作,也月月帶來令他付了又付的帳單。字詞編織的綿密網絡幾乎涵蓋米特所有人生,但他對字詞的想法卻有限地驚人。
米特或許會留意到那群人(比如生活在極權制度下的人),他們只能聽見和閱讀經過刻意篩選的字詞,因之行徑古怪到他只能當他們是瘋子。然而,他有時也當某些和他受相同教育、同樣多樣化資訊的人是瘋子。聽著鄰居的觀點,他不禁納悶:「他們怎麼會這樣想?我都發現了他們沒發現嗎?他們一定瘋了!」「這種病態」,他自問,「是否再次顯示出『人性必然的脆弱』?」米特先生身為美國人,喜歡設想所有可能,而非以「無計可施」作結,但他實在不知道該如何自這狀況抽身。
米特對語言的思辯總無法深入並以失敗作結,原因之一是人們本就深信字詞並不重要,字詞所承載的「想法」才是重點。但腦中的騷動如果不化為詞語,要如何稱之為「想法」?米特幾乎不這麼想。事實上某組字詞或許無可避免會引人進入死胡同,但另一組字詞就不會。某些字詞容易引發歷史或感傷聯想因而難讓人冷靜討論。語言有多種不同使用方式,誤認使用方式會導致極大誤解。使用諸如日文、中文或土耳其語等結構和英文截然不同語言的人,或許他們思考的方式根本和說英語的人不同。前述概念對米特來說都十分陌生,他總認為重點在於讓人表達他的想法,至於字詞就順其自然。
無論米特是否有自覺,不只他聽見和使用的字詞,連他無意識間對語言預設的態度也影響他人生的每分每秒。比如說,如果他喜歡艾伯特這名字,且想用它幫孩子命名,但可能會因為認識一位曾企圖自殺的艾伯特而放棄這念頭。無論他是否有自覺,他都依照語言和現實之間的關係所形成的假想推論而行動。無論明智與否,這些無意識推論決定他的行動模式。字詞、他使用字詞的方式,及別人使用字詞時他如何判定,皆大幅形塑他的信仰、偏見、理想和抱負。字詞構築他所在之處的道德和學術氛圍,簡而言之,他的「語意環境」。
本書主要研究語言、思想和行為之間的相互關係。旨在檢證語言和人們的語言習慣如何透過思考(十之八九都關於自己)、說話、傾聽、閱讀和書寫來揭露自我。
本書的基本假設為人類生存的基礎機制乃透過語言進行的種內合作。同時也假設若語言使用引致或加深歧見或衝突,說者、聽者,或兩者身上必然有語言學上的錯誤。人類生存係仰賴語言書寫傾聽和閱讀能力,以之增近你和同類一起生存下去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