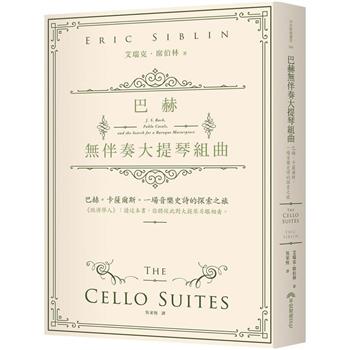第一號組曲(G大調)
前奏曲
我坐在西班牙一處濱海莊園的庭院,此地曾為卡薩爾斯(Pablo Casals)所有。一八九○年的一天下午,還是孩童的這位加泰隆尼亞大提琴家發現了這音樂。我戴著耳機,聽著音樂,花園草木繁茂,棕櫚與松樹遮去陽光,不遠處地中海粼粼的波光,與第一號《無伴奏大提琴組曲》前奏曲應和得絲絲入扣。沒有比這地方更適合聆賞這音樂了。雖然巴赫是在十八世紀初寫下《無伴奏大提琴組曲》,但還要過兩百年,卡薩爾斯才讓這部作品廣為世人所知。
我知道有這部作品,是在二○○○年一個秋天的晚上。那一年是「巴赫年」,紀念這位作曲家去世兩百五十年。我坐在多倫多皇家音樂院(Royal Conservatory of Music)的觀眾席,聆聽一位不認識的大提琴家演奏我一無所知的作品。
當地的報紙登了音樂會的訊息,而我閒來無事,住的旅館又在不遠,除此之外,我沒有理由去聽這場音樂會。但我說不定已經在不知不覺中尋找著什麼。當時,我才結束了為蒙特婁的《快報》(The Gazette)寫流行音樂樂評的工作,這份差事讓我的腦袋裝滿音樂,而大部分的音樂是我並不想去聽的。排行榜前四十名的歌曲在我掌管聽覺的大腦皮層占據了太久,而圍繞著搖滾樂的文化已經越來越讓我難以忍受。我還是想讓音樂在我的生活中占據重要位置,但是要以不同的方式。結果,《無伴奏大提琴組曲》提供了一個脫離窘境的方式。
那場獨奏會的大提琴家,是來自波士頓的羅倫斯.雷瑟,曲目解說寫道,「實在是匪夷所思,長久以來,」《無伴奏大提琴組曲》被當成練習曲集。但自從卡薩爾斯在二十世紀之初開始拉奏巴赫的《無伴奏大提琴組曲》,「我們知道自己何其幸運,能擁有這些絕世逸品。然而,大部分的愛樂者有所不知,這些作品的手稿並沒有留存下來……《無伴奏大提琴組曲》,並無真正可靠的來源。」
這讓我心中挖新聞的念頭開始轉:巴赫的手稿,究竟流落到哪去了?
巴赫的手稿流落何方?
據說這部《大提琴組曲》,是巴赫在一七二○年於日耳曼的小城柯騰(Cöthen)創作,並以渡鴉羽毛的墨水筆寫下。但是,原始手稿並無留存,我們要如何確定這點?大提琴在巴赫的時代地位不高,一般是被貶到背景拉著單調的低音,那麼他為何要為大提琴寫這樣一部畫時代的巨作?以巴赫經常把自己的作品改寫給其他樂器演奏,我們又如何能確定這音樂是寫給大提琴的?
我坐在皇家音樂學院音樂廳的聽眾席,看著這孤單的形影以如此節制之質,發出這般宏偉的音聲,似乎在挑戰著音樂的可能性。就只有單一樂器,而且是音域固定在那麼低的大提琴,與此重任似乎並不相稱,彷彿有個至高的作曲家構思了一部企圖心過大的作品,一個理想的文本,卻對於承載任務的樂器未經琢磨漠不關心。
看著羅倫斯.雷瑟熟練地演奏這些組曲,我對他的樂器如此龐大感到印象深刻。這樂器以前稱之為violoncello,簡稱cello,讓我聯想到來自中世紀弦樂王國的某個笨手笨腳的農夫,粗野而原始,與它發出的精練樂音相差十萬八千里。但靠近細看,可以看到精工雕刻的渦狀琴頭和線條優美的音孔,形似某些精緻的巴洛克時代簽名。從這些音孔中傳出的音樂,比我所聽過的都要來得粗獷而狂喜。我任由心緒漫溢。這音樂在一七二○年聽起來會是什麼模樣?不難想像大提琴在戴著撲粉假髮的貴族面前展現身手,吸引他們的注意。
但如果《大提琴組曲》是如此魅力獨具,為什麼在卡薩爾斯發現它們之前卻沒什麼人聽過?在這組作品完成之後近兩百年間,只有少數專業音樂家和研究巴赫的學者知道有這麼一部史詩般的音樂。他們認為這組作品更像是技巧練習,而不適合在音樂廳裡演奏。
這六首組曲的故事,不只關乎音樂而已。音樂由政治所形塑,從十八世紀普魯士的尚武精神,到百年之後宣揚著巴赫名聲的德國愛國運動都是如此。當歐洲的獨裁統治在二十世紀猖獗之際,卡薩爾斯卻把音符化為反抗法西斯的子彈。過了幾十年後,羅斯托波維奇(Mstislav Rostropovich)在柏林圍牆的斷垣前面演奏《大提琴組曲》。
在卡薩爾斯讓世人注意到大提琴組曲之後(這在他發現這音樂許久之後才發生),它的魅力就無可抵擋了。唱片目錄上已有超過五十個錄音版本,超過七十五個大提琴演出版本。其他如長笛、鋼琴、吉他、小號、低音號、薩克斯風、班究琴的演奏家發現他們可以改編《大提琴組曲》,還有更多人嘗試進行改編,結果大為成功。
對大提琴家來說,這六首組曲變成了一切,成了一場在時間中推移的儀式,一座演出曲目的聖母峰——或者說,是富士山。二○○七年,義大利大提琴家馬里歐.布魯奈洛(Mario Brunello)爬到標高接近海拔三七五○公尺的富士山頂,拉奏《大提琴組曲》的選曲,因為他認為「巴赫的音樂最接近絕對與完美」。
前奏曲
我坐在西班牙一處濱海莊園的庭院,此地曾為卡薩爾斯(Pablo Casals)所有。一八九○年的一天下午,還是孩童的這位加泰隆尼亞大提琴家發現了這音樂。我戴著耳機,聽著音樂,花園草木繁茂,棕櫚與松樹遮去陽光,不遠處地中海粼粼的波光,與第一號《無伴奏大提琴組曲》前奏曲應和得絲絲入扣。沒有比這地方更適合聆賞這音樂了。雖然巴赫是在十八世紀初寫下《無伴奏大提琴組曲》,但還要過兩百年,卡薩爾斯才讓這部作品廣為世人所知。
我知道有這部作品,是在二○○○年一個秋天的晚上。那一年是「巴赫年」,紀念這位作曲家去世兩百五十年。我坐在多倫多皇家音樂院(Royal Conservatory of Music)的觀眾席,聆聽一位不認識的大提琴家演奏我一無所知的作品。
當地的報紙登了音樂會的訊息,而我閒來無事,住的旅館又在不遠,除此之外,我沒有理由去聽這場音樂會。但我說不定已經在不知不覺中尋找著什麼。當時,我才結束了為蒙特婁的《快報》(The Gazette)寫流行音樂樂評的工作,這份差事讓我的腦袋裝滿音樂,而大部分的音樂是我並不想去聽的。排行榜前四十名的歌曲在我掌管聽覺的大腦皮層占據了太久,而圍繞著搖滾樂的文化已經越來越讓我難以忍受。我還是想讓音樂在我的生活中占據重要位置,但是要以不同的方式。結果,《無伴奏大提琴組曲》提供了一個脫離窘境的方式。
那場獨奏會的大提琴家,是來自波士頓的羅倫斯.雷瑟,曲目解說寫道,「實在是匪夷所思,長久以來,」《無伴奏大提琴組曲》被當成練習曲集。但自從卡薩爾斯在二十世紀之初開始拉奏巴赫的《無伴奏大提琴組曲》,「我們知道自己何其幸運,能擁有這些絕世逸品。然而,大部分的愛樂者有所不知,這些作品的手稿並沒有留存下來……《無伴奏大提琴組曲》,並無真正可靠的來源。」
這讓我心中挖新聞的念頭開始轉:巴赫的手稿,究竟流落到哪去了?
巴赫的手稿流落何方?
據說這部《大提琴組曲》,是巴赫在一七二○年於日耳曼的小城柯騰(Cöthen)創作,並以渡鴉羽毛的墨水筆寫下。但是,原始手稿並無留存,我們要如何確定這點?大提琴在巴赫的時代地位不高,一般是被貶到背景拉著單調的低音,那麼他為何要為大提琴寫這樣一部畫時代的巨作?以巴赫經常把自己的作品改寫給其他樂器演奏,我們又如何能確定這音樂是寫給大提琴的?
我坐在皇家音樂學院音樂廳的聽眾席,看著這孤單的形影以如此節制之質,發出這般宏偉的音聲,似乎在挑戰著音樂的可能性。就只有單一樂器,而且是音域固定在那麼低的大提琴,與此重任似乎並不相稱,彷彿有個至高的作曲家構思了一部企圖心過大的作品,一個理想的文本,卻對於承載任務的樂器未經琢磨漠不關心。
看著羅倫斯.雷瑟熟練地演奏這些組曲,我對他的樂器如此龐大感到印象深刻。這樂器以前稱之為violoncello,簡稱cello,讓我聯想到來自中世紀弦樂王國的某個笨手笨腳的農夫,粗野而原始,與它發出的精練樂音相差十萬八千里。但靠近細看,可以看到精工雕刻的渦狀琴頭和線條優美的音孔,形似某些精緻的巴洛克時代簽名。從這些音孔中傳出的音樂,比我所聽過的都要來得粗獷而狂喜。我任由心緒漫溢。這音樂在一七二○年聽起來會是什麼模樣?不難想像大提琴在戴著撲粉假髮的貴族面前展現身手,吸引他們的注意。
但如果《大提琴組曲》是如此魅力獨具,為什麼在卡薩爾斯發現它們之前卻沒什麼人聽過?在這組作品完成之後近兩百年間,只有少數專業音樂家和研究巴赫的學者知道有這麼一部史詩般的音樂。他們認為這組作品更像是技巧練習,而不適合在音樂廳裡演奏。
這六首組曲的故事,不只關乎音樂而已。音樂由政治所形塑,從十八世紀普魯士的尚武精神,到百年之後宣揚著巴赫名聲的德國愛國運動都是如此。當歐洲的獨裁統治在二十世紀猖獗之際,卡薩爾斯卻把音符化為反抗法西斯的子彈。過了幾十年後,羅斯托波維奇(Mstislav Rostropovich)在柏林圍牆的斷垣前面演奏《大提琴組曲》。
在卡薩爾斯讓世人注意到大提琴組曲之後(這在他發現這音樂許久之後才發生),它的魅力就無可抵擋了。唱片目錄上已有超過五十個錄音版本,超過七十五個大提琴演出版本。其他如長笛、鋼琴、吉他、小號、低音號、薩克斯風、班究琴的演奏家發現他們可以改編《大提琴組曲》,還有更多人嘗試進行改編,結果大為成功。
對大提琴家來說,這六首組曲變成了一切,成了一場在時間中推移的儀式,一座演出曲目的聖母峰——或者說,是富士山。二○○七年,義大利大提琴家馬里歐.布魯奈洛(Mario Brunello)爬到標高接近海拔三七五○公尺的富士山頂,拉奏《大提琴組曲》的選曲,因為他認為「巴赫的音樂最接近絕對與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