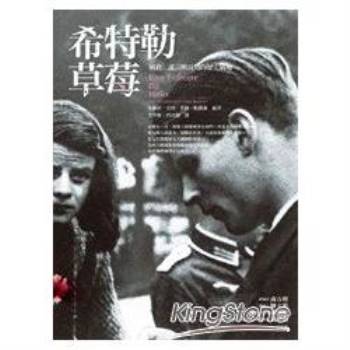1933年1月30日是個不尋常的日子,就連卡爾也感受到了。全家人都在等待這一天的來臨,等著年邁的總統興登堡任命國社黨領導人希特勒為國家總理。最起碼,對於那些懷著一顆熱切的心、全心全意相信「領袖」的人們而言,無不盼望從這天起,一切都會與從前大不相同,開始漸入佳境。而卡爾的家人便是如此。
家中的門鈴總是響個不停,親朋好友們不時來串門子,為的就是共同舉杯慶祝納粹運動的勝利。個個滿懷著歡度佳節的心情,慶幸自己終於壓對了寶,這個國家也終於可以向前邁進。自從一次世界大戰戰敗以來,生活在這個國家的許多人,都認為自己只有當輸家的份,永遠萬劫不復。現在,大家都想聽聽收音機裡究竟給國社黨地方小組組長弗德烈‧瓦特(Friedrich Walter)——卡爾的爸爸——家裡帶來什麼佳音。每個人無不渴望分享柏林街頭因為歡迎新時代來臨而舉辦的火炬遊行。新任總理阿道夫‧希特勒對所有支持他的群眾講話,不多時,那個無比刺耳的嘶吼聲,就固定出現在每個家庭中。
8歲的卡爾也覺得,這個晚上是對他個人的一種證明,因為他老早就和他的死黨們「1、2、1、2」地穿梭在大街小巷,踢著響亮的行軍正步。他們就像小小軍人一般,把雙手貼在短褲的接縫處,雄糾糾氣昂昂,一步接著一步前進,同時還高聲唱著「德國必須生存/德國必須生存/即使我們因此犧牲,即使我們必須犧牲!德國必須永續生存!」
唱著如此簡捷有力的歌詞,他們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已悄悄對未來做了充分的心理準備。還在和平的年代,他們就讓自己習慣於戰爭時期的思想,並練習在血腥的嚴肅中尋找樂趣,為自己年輕的生命,打開一扇死亡思想的大門。他們也相信,納粹在接下來的數年裡不斷幫人民洗腦的這些思想,都是出於他們原本的意願:每個單一個體都有義務參與這個人民共同體──任何人皆不准置身事外。他們所練習的一致步伐,將來也應穿越全國每個角落;誰若拒絕參與,就會被排擠在社會之外。
戰爭結束後,瓦特和父親合力開了一家製作畫框的小商店,靠著這份工作,勉強維持一家人的生計。正如其他的市井小民一樣,他也希望國家的命運能徹底改變,完全抹滅戰敗的不堪記憶,並因此改善個人的生活環境。
他經常向兒子卡爾述說一個可怕的故事:一名法國士兵如何用槍托將他的牙齒打落,只因為這個德國人不願意讓位給他。這個勝利者在戰敗者面前耀武揚威的故事,也使得他半大不小的兒子無法漠然以對,父母親沒完沒了地抱怨,說德國人民如何受到不平等的對待,讓卡爾成了忠實的聽眾。因此,他也從中學習到,如何判斷誰是朋友,誰是敵人;如何分辨好壞;誰和你同一陣線,誰又是你必須小心提防的人;還有,究竟誰該為家中的一貧如洗負責。
因為1929年秋發生的致命的世界經濟危機,也讓這孩子的家庭強烈感受到其後續效應。父親在祖父去世後獨立經營的商店必須被迫關門,誰還有能力在這個時機來裱畫?人們必須為了每日的麵包,為了月底的房租,為了孩子的鞋子而努力奮戰。零用錢對卡爾來說,只是個遙不可及的夢。
1933年的德國有幾近700萬的失業人口,在弗德烈‧瓦特的眼裡,民主制度實在脆弱得不足以解決如此嚴重的問題,尤有甚者,德國之所以淪落到如此悲慘的境地,民主制度本該負起責任。在我們的帝國議會裡,只有高談闊論,卻無具體行動。瓦特將全部的希望都寄託在國社黨的身上,這個充分展現出說服力、有著嚴格秩序與紀律的政黨。
1930年,他開始擔任國社黨地方小組的組長,滿心驕傲的他,經常身穿棕色的制服在城裡漫步。對他來說,一個先前完全失敗的生命,隨著1933年的來臨,所有的夢想都將實現。他在國家義務勞動處的行政部門又有了穩定的收入,全家人也遷至更寬敞美麗的公寓。卡爾十分崇拜爸爸,希望將來也能像他一樣偉大。
也由於這個緣故,卡爾8歲就加入希特勒青年團。原本他的年紀還太小,因為在1933年以前,青年團團員的最低年齡為14歲,在納粹掌權後下修為10歲。但該團破例將卡爾視為特別個案,這等於是一項殊榮。雖然納粹政權亟欲掌控所有的青少年,但組織中的特例情況仍應只能做為一種獎賞的形式,不可被視為理所當然。
☆希特勒青年團☆
1936年12月1日,希特勒青年團宣布改名為國家青年團(Staatsjugend)。年滿10歲者,可以成為「納粹小傢伙」;年滿14歲起,則自動歸屬原來的希特勒青年團。而女孩們在14歲以前可加入少女團(Jungmadeln,縮寫為JM),之後可加入德國女青年聯盟(Bund Deutscher Madel,縮寫為BDM)。
1933年初,希特勒青年團擁有大約10萬名團員。到了1934年底,青年團與女青年團的人數便已暴增到將近360萬,這個數字幾乎囊括了全國所有介於10到18歲的青少年。
任何人只要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團,就等於置身在另一個世界當中,陌生人的話,會比自己父母的話來得更有力。倘若成年人也和納粹站在同一陣線,就如卡爾的父母親,便不至於太過突兀。但如果父母與納粹保持距離,或甚至持批判態度,親子關係就會變得極其複雜。究竟誰的話比較權威?是青年團的領導,還是父母親?而自己的親生孩子又可能會把什麼居家閒談的內容,報告給青年團呢?
卡爾並沒有這些問題,他的爸爸相當自豪,自己的兒子會被教育成一個規矩的小伙子、一個剛強的男子漢、一個堅毅不拔的戰士。卡爾和朋友們練習著野外偵查遊戲、潛近、掩護藏身、守候打探以及匍伏潛行,同時還高唱一些效忠國家、決心身先士卒和發揚團隊精神的歌曲。
某天,卡爾的遠親來訪,是個嚴峻的希特勒少年,也和卡爾一同參與組織在附近鄉間所安排的課外活動。一項行軍活動即將開始,亦即所謂的小旗行軍,150名興奮的青少年即將動身出發。他們手扛旗幟,全黑的旗幟上印有白色的閃電標誌。一如往常,在行軍的路上他們高聲唱著進行曲,因為進行曲不但能控制步伐,還能控制思想。「向我們的旗幟敬禮,向我們的標誌敬禮,向創造它們的領袖敬禮,向所有為他們犧牲的烈士敬禮,忠誠地追隨他們的呼喚!日以繼夜奮勇抗敵,讓我們成為旗幟的守護者,無論我們勝利還是倒下,我們的旗幟永遠聖潔。」
這群少年期待從身旁經過的人們對旗幟表達敬意,對這個象徵行威嚴之禮,對他們而言,這就是納粹運動的體現──當然還有他們所獲得的新權力。他們已經不再是無知的小孩子──這些納粹小傢伙象徵著未來。路旁有人不願對這方布料行禮,但這方布料對少年們而言,卻擁有幾近崇高的宗教意義。他既不肯伸直手臂,亦不願互撞腳後跟立正。卡爾的親戚立刻毫不猶豫地反應:他重重摑了那人一掌。卡爾就在身旁,冷漠以對。他絕不會給予那些妨礙國家信念的人絲毫同情,因為這些人只會成為絆腳石。
該敬老尊賢嗎?對這些少年們來說,它早已不再是理所當然的禮教。誰是棕色運動的一員,誰才值得尊敬。隨著一次次的野外露營、一次次的行軍踏青,父母與孩子之間的隔閡被離間得更深,而新舊價值觀之間的鴻溝,也變得愈發不可跨越。又如,將心比心已不再屬於為人的美德之一,此乃孩子們在社團晚會上被反覆灌輸的新戒律。相反地,他們應該如皮革般強韌,鋼鐵般堅硬,獵狗般迅猛。這是他們口中所謂的「領袖」希特勒,在1934年的紐倫堡黨大會上,在聽眾如雷的掌聲中所要求的。他們,這些希特勒少年,就是新德國的象徵。
家中的門鈴總是響個不停,親朋好友們不時來串門子,為的就是共同舉杯慶祝納粹運動的勝利。個個滿懷著歡度佳節的心情,慶幸自己終於壓對了寶,這個國家也終於可以向前邁進。自從一次世界大戰戰敗以來,生活在這個國家的許多人,都認為自己只有當輸家的份,永遠萬劫不復。現在,大家都想聽聽收音機裡究竟給國社黨地方小組組長弗德烈‧瓦特(Friedrich Walter)——卡爾的爸爸——家裡帶來什麼佳音。每個人無不渴望分享柏林街頭因為歡迎新時代來臨而舉辦的火炬遊行。新任總理阿道夫‧希特勒對所有支持他的群眾講話,不多時,那個無比刺耳的嘶吼聲,就固定出現在每個家庭中。
8歲的卡爾也覺得,這個晚上是對他個人的一種證明,因為他老早就和他的死黨們「1、2、1、2」地穿梭在大街小巷,踢著響亮的行軍正步。他們就像小小軍人一般,把雙手貼在短褲的接縫處,雄糾糾氣昂昂,一步接著一步前進,同時還高聲唱著「德國必須生存/德國必須生存/即使我們因此犧牲,即使我們必須犧牲!德國必須永續生存!」
唱著如此簡捷有力的歌詞,他們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已悄悄對未來做了充分的心理準備。還在和平的年代,他們就讓自己習慣於戰爭時期的思想,並練習在血腥的嚴肅中尋找樂趣,為自己年輕的生命,打開一扇死亡思想的大門。他們也相信,納粹在接下來的數年裡不斷幫人民洗腦的這些思想,都是出於他們原本的意願:每個單一個體都有義務參與這個人民共同體──任何人皆不准置身事外。他們所練習的一致步伐,將來也應穿越全國每個角落;誰若拒絕參與,就會被排擠在社會之外。
戰爭結束後,瓦特和父親合力開了一家製作畫框的小商店,靠著這份工作,勉強維持一家人的生計。正如其他的市井小民一樣,他也希望國家的命運能徹底改變,完全抹滅戰敗的不堪記憶,並因此改善個人的生活環境。
他經常向兒子卡爾述說一個可怕的故事:一名法國士兵如何用槍托將他的牙齒打落,只因為這個德國人不願意讓位給他。這個勝利者在戰敗者面前耀武揚威的故事,也使得他半大不小的兒子無法漠然以對,父母親沒完沒了地抱怨,說德國人民如何受到不平等的對待,讓卡爾成了忠實的聽眾。因此,他也從中學習到,如何判斷誰是朋友,誰是敵人;如何分辨好壞;誰和你同一陣線,誰又是你必須小心提防的人;還有,究竟誰該為家中的一貧如洗負責。
因為1929年秋發生的致命的世界經濟危機,也讓這孩子的家庭強烈感受到其後續效應。父親在祖父去世後獨立經營的商店必須被迫關門,誰還有能力在這個時機來裱畫?人們必須為了每日的麵包,為了月底的房租,為了孩子的鞋子而努力奮戰。零用錢對卡爾來說,只是個遙不可及的夢。
1933年的德國有幾近700萬的失業人口,在弗德烈‧瓦特的眼裡,民主制度實在脆弱得不足以解決如此嚴重的問題,尤有甚者,德國之所以淪落到如此悲慘的境地,民主制度本該負起責任。在我們的帝國議會裡,只有高談闊論,卻無具體行動。瓦特將全部的希望都寄託在國社黨的身上,這個充分展現出說服力、有著嚴格秩序與紀律的政黨。
1930年,他開始擔任國社黨地方小組的組長,滿心驕傲的他,經常身穿棕色的制服在城裡漫步。對他來說,一個先前完全失敗的生命,隨著1933年的來臨,所有的夢想都將實現。他在國家義務勞動處的行政部門又有了穩定的收入,全家人也遷至更寬敞美麗的公寓。卡爾十分崇拜爸爸,希望將來也能像他一樣偉大。
也由於這個緣故,卡爾8歲就加入希特勒青年團。原本他的年紀還太小,因為在1933年以前,青年團團員的最低年齡為14歲,在納粹掌權後下修為10歲。但該團破例將卡爾視為特別個案,這等於是一項殊榮。雖然納粹政權亟欲掌控所有的青少年,但組織中的特例情況仍應只能做為一種獎賞的形式,不可被視為理所當然。
☆希特勒青年團☆
1936年12月1日,希特勒青年團宣布改名為國家青年團(Staatsjugend)。年滿10歲者,可以成為「納粹小傢伙」;年滿14歲起,則自動歸屬原來的希特勒青年團。而女孩們在14歲以前可加入少女團(Jungmadeln,縮寫為JM),之後可加入德國女青年聯盟(Bund Deutscher Madel,縮寫為BDM)。
1933年初,希特勒青年團擁有大約10萬名團員。到了1934年底,青年團與女青年團的人數便已暴增到將近360萬,這個數字幾乎囊括了全國所有介於10到18歲的青少年。
任何人只要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團,就等於置身在另一個世界當中,陌生人的話,會比自己父母的話來得更有力。倘若成年人也和納粹站在同一陣線,就如卡爾的父母親,便不至於太過突兀。但如果父母與納粹保持距離,或甚至持批判態度,親子關係就會變得極其複雜。究竟誰的話比較權威?是青年團的領導,還是父母親?而自己的親生孩子又可能會把什麼居家閒談的內容,報告給青年團呢?
卡爾並沒有這些問題,他的爸爸相當自豪,自己的兒子會被教育成一個規矩的小伙子、一個剛強的男子漢、一個堅毅不拔的戰士。卡爾和朋友們練習著野外偵查遊戲、潛近、掩護藏身、守候打探以及匍伏潛行,同時還高唱一些效忠國家、決心身先士卒和發揚團隊精神的歌曲。
某天,卡爾的遠親來訪,是個嚴峻的希特勒少年,也和卡爾一同參與組織在附近鄉間所安排的課外活動。一項行軍活動即將開始,亦即所謂的小旗行軍,150名興奮的青少年即將動身出發。他們手扛旗幟,全黑的旗幟上印有白色的閃電標誌。一如往常,在行軍的路上他們高聲唱著進行曲,因為進行曲不但能控制步伐,還能控制思想。「向我們的旗幟敬禮,向我們的標誌敬禮,向創造它們的領袖敬禮,向所有為他們犧牲的烈士敬禮,忠誠地追隨他們的呼喚!日以繼夜奮勇抗敵,讓我們成為旗幟的守護者,無論我們勝利還是倒下,我們的旗幟永遠聖潔。」
這群少年期待從身旁經過的人們對旗幟表達敬意,對這個象徵行威嚴之禮,對他們而言,這就是納粹運動的體現──當然還有他們所獲得的新權力。他們已經不再是無知的小孩子──這些納粹小傢伙象徵著未來。路旁有人不願對這方布料行禮,但這方布料對少年們而言,卻擁有幾近崇高的宗教意義。他既不肯伸直手臂,亦不願互撞腳後跟立正。卡爾的親戚立刻毫不猶豫地反應:他重重摑了那人一掌。卡爾就在身旁,冷漠以對。他絕不會給予那些妨礙國家信念的人絲毫同情,因為這些人只會成為絆腳石。
該敬老尊賢嗎?對這些少年們來說,它早已不再是理所當然的禮教。誰是棕色運動的一員,誰才值得尊敬。隨著一次次的野外露營、一次次的行軍踏青,父母與孩子之間的隔閡被離間得更深,而新舊價值觀之間的鴻溝,也變得愈發不可跨越。又如,將心比心已不再屬於為人的美德之一,此乃孩子們在社團晚會上被反覆灌輸的新戒律。相反地,他們應該如皮革般強韌,鋼鐵般堅硬,獵狗般迅猛。這是他們口中所謂的「領袖」希特勒,在1934年的紐倫堡黨大會上,在聽眾如雷的掌聲中所要求的。他們,這些希特勒少年,就是新德國的象徵。